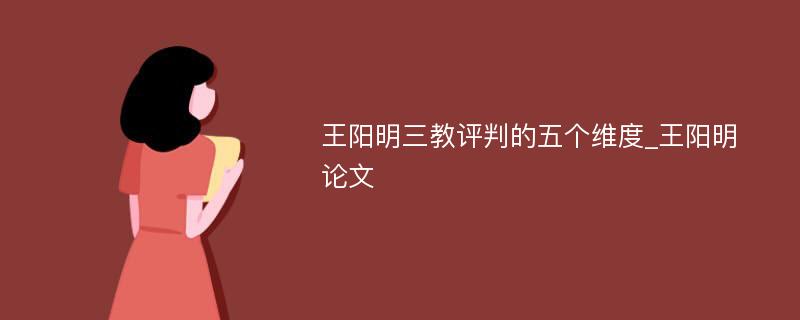
王阳明三教之判中的五个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阳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学家多有早年泛滥词章、出入佛老而后反求六经、归宗儒门的共同人生轨迹。归宗认祖、卓然自立的大儒们反过来对佛老二教总是要进行一番“清算”,“三教之判”遂成为理学家运思的共同主题。不过,宋儒多严守三教界限,横渠、明道、伊川、晦翁均有力辟佛老之言,而有明一代,阳明心学一系在三教关系上则多持融通、调和立场。那么,心学一系调和三教,个中缘由何在?
从阳明心学本身的义理架构入手,揭示心学一系三教之判所牵涉的理论向度,乃是本文之任务。本文认为,从理论上导致阳明心学走向三教融通的思想因素是多元的,计其大端,有以下五个向度:(1)“道一而已”,(2)“吾之用”乃第一义,(3)现世生命的关怀,(4)中国意识,(5)终极认同。兹分别述之如下。
一、道一而已
王阳明晚年致弟子邹东廓信云:
道一而已,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释氏之所以为释,老氏之所以为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宁有二乎?……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见,而又饰之以比拟仿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训,其为习熟既足以自信,而条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诳己诳人,终身没溺而不悟焉耳!(《新编王阳明全集》,第219页)
“道一而已”,本出自《孟子·滕文公》:“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滕文公二见孟子,似有疑孟子初见时“言有不尽”之意,故孟子曰,天下之道,一言而已,惟有性善,复何疑也!(见焦循,第319页)这里的“道一”并无深意,后来的理学家们则往往用之阐发三教关系。有趣的是,“道一而已”可用来证成全然不同的宗教立场。如横渠在《正蒙》之《乾称篇》论及儒佛之别时说:“道一而已,此是则彼非,此非则彼是,固不当同日而语。”(《张载集》,第65页。黑体为引者所标。本文以下所有引文中之黑体均为引者所标)而在王阳明这里,“道一无二”之说为诸宗教的“共通性”奠定了根基。细味之,“释氏之所以为释,老氏之所以为老”说法实意犹未尽,“儒者见之谓之儒”似是言外之意(阳明后学赵大洲即有此说)。倘如此,则三教均为见道之“一偏”,“教”虽是三,其“道”却是一。意识到“偏”,即已不偏,即当超越一己之偏,而成就大道之全。但世儒囿于“一偏之见”而“自安”、“自信”,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殊不知:
道无方体,不可执着。却拘滞于文义上求道,远矣。如今人只说天,其实何尝见天?谓日、月、风、雷即天,不可;谓人、物、草、木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识得时,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见,认定以为道止如此,所以不同。(《新编王阳明全集》,第23页)
这样,王阳明通过彰显“道”之超越性、普遍性,而将三教纳为“同道”。王阳明之用意是要突破名相之“界限”,而直通那不落知解、超言绝相的大道本身。在大道面前,儒(世儒之儒)、道、佛皆不过见大道之一端。于是,三教之隔不过是知解之隔、“门户”之隔。为超越三教之隔,就必须透过一番概念名相的拆卸工夫,将历史中积淀的种种“一隅之见”加以悬搁,追根溯源,而上达三教之肇端:
或问三教同异。师曰:“道大无外,若曰各道其道,是小其道矣。心学纯明之时,天下同风,各求自尽。就如此厅事,元是统成一间,其后子孙分居,便有中有傍。又传渐设藩篱,犹能往来相助。再久来渐有相较相争,甚而至于相敌。其初只是一家,去其藩篱仍旧是一家。三教之分,亦只似此。其初各以资质相近处学成片段,再传至四五则失其本之同,而从之者亦各以资质之近者而往,是以遂不相通。名利所在,至于相争相敌,亦其势然也。”(同上,第1611页)
三教“其初只是一家”说并非王阳明发明,元代全真教中已屡见,不过通过三教的谱系学考察而证成之,无疑是王阳明新说。在这幅寥寥数笔勾勒出的三教演化“谱系”中,我们看到的是三教由起初的一家之团契关系,渐渐演变为门户界限(“相较相争”),而复演为与世间利益(“名利”)交织在一起的意识形态的宗教纷争(“相争相敌”)。何谓“各求自尽”?是不是说三教仍是三教,并行不悖,相忘于江湖?观王阳明“心学纯明之时”的独特含义,此解自不成立:
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愿,惟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视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乐,而不耻于不明礼,视夷之通礼,即己之通礼也。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同上,第60页)
三教谱系学亦即人之谱系学,“心学纯明之时”,虽然人之“资质”、“才质”有异同,但并未因此而造成隔阂,相反,各自视对方之长若己之长。三教虽可以说仍是三教(资质不同),但三教又可以说是一教:对方之“教”若己之教。“心学纯明之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这就从大本大源上认定三教之同源关系。在此时,三教之关系既不是并行不悖的,更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却又自成一类之关系。
“道一无二”成了阳明后学三教异同论的基本理路,如焦竑曰:“道一也,达者契之,众人宗之。在中国曰孔、孟、老、庄,其至自西域者曰释氏。由此推之,八荒之表,万古之上,莫不有先达者为之师,非止此数人而已。昧者见迹而不见道,往往瓜分之而又株守之。”(焦竑,第196页)“非止此数人而已”,此话耐人寻味。无论此时焦竑有无结识利玛窦(参见安田朴、谢和耐;利玛窦;裴化行),毫无疑问,在逻辑上耶稣基督也当属于“八荒之表”的“先达者”之列。阳明心学这种道一无二的逻辑一直贯穿于当代新儒家如牟宗三对上帝与基督教之区别中(参见《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3册,第205-206页),而唐君毅中外无数圣贤共济于“中国新庙宇”的设想(唐君毅,第394页),则可视为焦竑“非止此数人而已”之现代翻版。
二、“吾之用”乃第一义
王阳明在越期间,张元冲舟中问学,谈及佛道二家“作用”,认为儒当兼取二氏,王阳明遂以三间厅堂说示之:
说兼取,便不是。圣人尽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新编王阳明全集》,第1298-1299页)
此段话有两处提及“吾之用”,先看前者:“二氏之用,皆我之用。”这里,“我”才是主体,这个我系“性命”之我,成全这个我、实现这个我(所谓“尽性至命”)乃是终极目的。“二氏”之中,道教之“养身”、佛教之“不染世累”,从自我成全(“即吾尽性至命”)的立场看,均有其“用”。实际上“圣学之全”在根本上即是要全方位地成全这个“性命之我”,即是要在身体(自然)-心灵(吾心)-社会(人伦)三位一体之中充分地实现自我之潜能。就此而言,注重养身的道教与注重明心见性的佛教本是圣学大全之中固有的身体(自然)与心灵向度,而“后世儒者”蔽于陋见,自抛祖产,将“心灵”向度割让与佛氏,将“身体”向度割让给老氏,自处于“社会”向度之中,致使儒家成为“小家”,儒道成为“小道”,儒家信仰成为单面信仰。所谓“二氏之用,皆我之用”,不过是收复“失地”、重聚“祖产”的举措而已。
至于后者,“儒、佛、老庄皆吾之用”一说,则又将三教并置,皆称“吾之用”。这里面涉及王阳明的“吾”之地位问题。任何所谓的“道”与“教”如揆之自家心身性命而了无干涉,则不成其为“道”与“教”,儒教亦不例外,自家身心性命的受用(“吾之用”)才是第一义的。此第一义的确立,让圣经、圣人、圣传、圣学皆处在客体的地位:
圣贤垂训,固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一涉拘执比拟,则反为所缚。(同上,第288页)
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同上,第82页;参见第846页)
儒家对外教经典的接纳,必求诸“心”之主体地位。曾巩曾讥讽王安石读佛经,后者回以:“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见惠洪,第47页)在王阳明这里,学圣经、圣人、圣传、圣学不过是学此心,是为了“调摄此心”、“明得自家心体”。在此心面前,儒、道、佛都是“被解释者”,其地位都是“客体的地位”。这与基督宗教上帝的话语是主体、解释者(explicans),个体体验是客体、被解释者(explicandum),形成了鲜明对比。
王阳明甚至有“因错致真,无非得益”之说法(《新编王阳明全集》,第1550页),这种“自我得益”、“自我受用”、“自我成全”的基本价值取向,从根本上超越了蔽于一隅之见的三教异同论:
郑德夫问于阳明子曰:“释与儒孰异乎?”阳明子曰:“子无求其异同于儒、释,求其是者而学焉可矣。”曰:“是与非孰辨乎?”曰:“子无求其是非于讲说,求诸心而安焉者是矣。”(同上,第254页)
今世学者……其能有若老氏之清净自守、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彼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彼其心犹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新编王阳明全集》,第246页)
三教异同论如失去与自家身心性命的生存论关联,则成为纯然无趣之问题;与其执着于三教异同,不若超越异同,而归宗于“吾”之受用与安定。“心安”与“自得”才是目的,三教之为教不过是引人走向心安与自得的路径而已。
三、现世的生命关怀
在此,王阳明显示出其现世的、当下的生命关怀。此种现世的人道取向清楚地表现在他对佛教理论的独特诠释之中:
座间有言:“今人动曰生西天。”先生曰:“如此岂不堕落在苦海了?尝闻西域人皆欲生中华,今中华却欲生西天,不知何见?且佛言西天有极乐园,亦非以地言也。西天只在眼前,人不善礼,往往以生西天为福,不知人行好便是极乐,便是生西天。如一家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雍雍熙熙,有多少自在处,即此便是极乐园。若父子、兄弟、夫妇之间乖戾不和,细粒必争,睚眦必报,终日忧愁烦恼,就是兹地狱。然则天堂地狱,俱在乎我,又何事于他求哉!”(同上,第1642页)
“西天”(“极乐园”)、“地狱”均不是“空间”概念(“非以地言也”),而是昭昭于眼前的生存论范畴,它即体现在人之现世的生存活动中。同样,佛教之“轮回”亦不是超越世间时间的彼岸概念:
释氏轮回变现之论,亦不必求之窈冥。今人不能常见自己良知,一日之间,此心倏焉而夷狄,倏焉而禽兽,倏焉而趋入悖逆之途,倏焉而流入贪淫之海,不知几番轮回,多少变幻。但人不自觉耳。释氏言语,多有欺弄精神者。大概当求之方之外,得其意而已矣。(同上,第1616页;另见第1825页)
“轮回变现”即是当下的人性波动。人之良知之或隐或现、时存时失,即是“轮回”。
王阳明这里对佛教“西天”、“地狱”以及“轮回变现”的“人道”解读,颇类当代生存论神学对基督教天堂、地狱之看法——天堂与地狱不再是酬报与惩罚的观念,而是生存论的概念:前者彰显的是存在的圆满与人之生存的“上限”之体验,而后者则表达了存在的丧失与人之生存的“下限”之体验。(参见麦奎利,第350-355页)王阳明这种解读之立足处自是人之当下的生存:现世的人道关怀乃儒者的本色,当下的生活乃是精神生命关注的焦点。
值得指出的是,王阳明三教之判中的这种现世人道关怀向度,在当代新儒家的相关论说中仍有其深刻的影响,如牟宗三在《中国文化大动脉中的终极关心问题》一文中指出:“就儒者的立场说,一个人如能真实无妄地‘践仁’,为国家社会做事尽其忠心,事奉父母尽其孝心,与朋友交尽其信实之心,在兄弟姊妹之间尽其友爱之心,在夫妇之间尽其和顺之心,便是‘心安理得’。说得救,这‘心安理得’就是得救;说解脱,这‘心安理得’就是解脱;说逍遥自在,这‘心安理得’就是逍遥自在。你能这样‘心安理得’,现实世界就是你的天堂,现实世界就是你的极乐世界。否则,你没有这‘心安理得’,谁也救不了你,你永远不能解脱、不得逍遥,现实世界就是你的地狱。”(《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3册,第426页)
“吾之用”之“吾”,在王阳明处一直是现世的、人间的“吾”,这个“吾”同时也是扎根于社群与文化之中的“吾”;三教之判亦不能脱离“吾”之扎根的社群及其文化传统,是为王阳明三教之判中的“中国意识”。
四、中国意识
在《谏迎佛疏》(稿具未上)中,王阳明写道:
夫佛者,夷狄之圣人;圣人者,中国之佛也。在彼夷狄,则可用佛氏之教化以化导愚顽;在我中国,自当用圣人之道以参赞化育,犹行陆者必用车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国而师佛教,是犹以车马渡海,虽使造父为御,王良为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车马本致远之具,岂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则技无所施。(《新编王阳明全集》,第313页)
就身位而论,佛与圣人乃是同等的,三教圣人不必较高低。但每个民族皆有其本己之“教”,佛固为夷狄之圣人,然而既为夷狄,则其教化自当施于夷狄;圣人固为中国之佛,然而既为中国,亦自当以圣人儒教教化群生。儒教作为中华文化慧命之最高体现,自应是吾中国人教化之道的不二选择。
这种三教之判之中的“中国意识”并不限于王阳明本人的论述,即便在于三教观上持更加开放态度的焦竑那里依然有所表现。他曾明言“道是吾自有之物”:
友问:“佛氏之道与吾道不同,于何处分别?”先生曰:“道是吾自有之物,只烦宣尼与瞿昙道破耳,非圣人一道、佛又一道也。大抵为儒佛辨者,如童子与邻人之子,各诧其家之月曰:尔之月不如我之月也。不知家有尔我,天无二月。”(焦竑,第745页)
“佛氏之道”与“吾道”不再有任何分别,道本是“吾自有之物”,岂有二道?好发三教异同论者乃心智幼稚者,如小儿争月,不知天无二月。然而,就是这位焦竑又同时断言:“内典所言心性之理,孔孟岂复有加?然其教自是异方之俗,决不可施于中国。”(同上,第738页)在地意识(“用非其地,则技无所施”)与风俗、文化的观念(“异方之俗”)成为阳明心学一系三教之判的一个重要向度。
这一三教之判中的“在地意识”(“中国意识”)实际上反映出阳明心学的民族文化自觉。当年甘地通过非暴力运动领导印度争取独立而获得举世声誉,一西方传教士对甘地说,你的行动方式完全符合耶稣基督的精神(“匿名的基督徒”),你为何不信仰我们的基督教呢?甘地回答说,我已生而为印度人,我信仰的是印度教、婆罗门教,我所做的事,照你说是合乎基督精神,然而我却是根据我们的婆罗门教义而来的,既然婆罗门教能启发我、指引我,我又何必作基督徒呢?牟宗三在论及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时,屡屡引甘地的这个话头。(《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3册,第353、446-447页)王阳明“在我中国,自当用圣人之道以参赞化育”之掷地有声的说法,不同样折射出“真正的民族精神”、“真正的文化智慧”吗?
五、终极认同
多重宗教参与乃至多重宗教认同自波士顿儒家白诗朗、南乐山提出后,一时成为讨论儒教开放与包容性经常被提及的话题。(参见彭国翔,第141-168页;李晨阳,第143-168页;Griffioen,第294-306页)持三教融通立场的人大致均认为三教因其各自的胜场,而各有其相应之用。宋孝宗的佛家治心、道家治身、儒家治世的提法即是例证。然而无论如何,就终极的认同而论,一个人不能同时以同样程度献身于不同的宗教,此是不争的事实。
面对偏好仙佛的弟子关于二氏之教的请问,王阳明屡屡以“悔”字应对。在《答人问神仙》一文中,他称自己好神仙已三十余年,结果是,“齿渐动摇,发已有一二茎变化成白,目光仅盈尺,声闻函丈之外,又常经月卧病不出。”(《新编王阳明全集》,第842页)王阳明归宗儒教,在一定程度上乃是他在道教修炼方面遭遇到挫折的结果。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龙场悟道,使他体验到二氏精微之面向实是“圣道之全”所固有的:
王嘉秀问:“佛以出离生死诱人入道,仙以长生久视诱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极至,亦是见得圣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极处,与儒者略同,但有了上一截,遗了下一截,终不似圣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诬也。后世儒者,又只得圣人下一截,分裂失真,流而为记诵、词章、功利、训诂,亦卒不免为异端……”先生曰:“所论大略亦是。但谓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见偏了如此。若论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彻上彻下,只是一贯,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同上,第20页,句读略有改动)
在王阳明看来,三教(其中儒教乃俗儒、世儒之教)均有所偏,这种偏乃是封闭于一隅之见、自是非人之“偏”,是凝固化的意识形态之“偏”,而不是“心学纯明之时”“各以资质相近处学成片段”之“偏”;后者实不是“偏”,而只是因人资质不同而所得自然不同,但此不同并未导致排斥异己,相反是“往来相助”而无有人我之间。王阳明所归宗的既不是佛老二教,亦不是世儒之教,而是“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圣人之学”。
王阳明虽坚持佛老皆吾之用,但并不认同佛老,究其理由无非有二:其一,二氏“遗了下一截”,所谓“外人伦,遗物理”:
故圣人之学不出乎尽心。禅之学非不以心为说,然其意以为是达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于其中则亦已矣,而亦岂必屑屑于其外,其外有未当也,则亦岂必屑屑于其中。斯亦其所谓尽心者矣,而不知已陷于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伦,遗事物,以之独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同上,第273-274页)
在王阳明看来,释氏之心学乃是要“尽绝事物”,最终与世间无交涉,而不可治天下。其二,即便在“上一截”二氏仍有“未尽处”,所谓仍不免有毫厘之差:
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氏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与本体有障碍。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同上,第117页)
先生尝言:“佛氏不着相,其实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实不着相。”请问。曰:“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着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妇的相?”(同上,第108-109页)
问:“儒者到三更时分,扫荡胸中思虑,空空静静,与释氏之静只一般,两下皆不用,此时何所分别?”先生曰:“动静只是一个。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应事接物的心。如今应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心。故动静只是一个,分别不得。知得动静合一,释氏毫厘差处亦自莫掩矣。”(同上,第107页)
虚无、不着、空静本是佛老之本色,亦是其胜场所在,然在王阳明看来,佛老于此等处仍然有所添加、有所执着、有所分别,故仍未至究竟、未造化境。故他对佛老二教之超越不仅是对其“遗了下一截”之超越,更是对其“上一截”之超越,不妨再看下一条目:
或问:“裴公休序《圆觉经》曰:‘终日圆觉而未尝圆觉者,凡夫也;欲证圆觉而未极圆觉者,菩萨也;具足圆觉而住持圆觉者,如来也。’何如?”曰:“我替他改一句:终日圆觉而未尝圆觉者,凡夫也;欲证圆觉而未极圆觉者,菩萨也;具足圆觉而住持圆觉者,罗汉也;终日圆觉而未尝圆觉者,如来也。”(《新编王阳明全集》,第1615页)
裴公美号称深得华严宗旨与禅宗心要,王阳明不避班门弄斧之嫌,“终日圆觉而未尝圆觉”,寥寥数笔,圆觉之化境出矣。冯友兰说,新儒家更为一贯地坚持道家、佛家的基本观念,他们比道家还要道家,比佛家还要佛家(冯友兰,第364页),至哉斯言。
王阳明亦不认同世儒之教,实际上他对二氏之批判往往是跟批判世儒之教联系在一起的:
世之儒者妄开窦径,蹈荆棘,堕坑堑,究其为说,反出于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厌此而趋彼也!此岂二氏之罪哉!(《新编王阳明全集》,第139-140页)
彼释氏之外人伦,遗物理,而堕于空寂者,固不得谓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务讲求考索,而不知本诸其心者,其亦可以谓穷理乎?(同上,第192页)
荒木见悟在《邓霍渠的出现及其背景》一文中指出,晚明三教一致论“不是串同三教,也不是凑集三教之长,而是超越三教,从根本源头重新认识三教”。(荒木见悟,第124页)就王阳明本人而论,其所最终认同之“教”实是超越了三教之教。观王阳明将二氏之教与世儒之教并称之文本,其正面所推崇的乃是“圣人之道”、“圣学之全”、“简易广大”的“圣人之学”,此是他本人所虔诚归宗者、所终极认同者,这不再是与佛老鼎足而立的儒教,而是“范围三教之宗”的“良知教”。
六、结论
“道一而已”与“吾之用”从信仰之对象与信仰之主体两个面向,超越了儒门“狃于世儒崇正之说”而画地自限的封闭心态。前者通过强调道之普遍性而将佛老之教纳入“同道”范围之内,后者则藉凸显自家身心性命受用之第一义,而将佛老二教连同儒教一起成为“吾之用”者。其实在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吾性自足”的体验中,“道是吾自有之物”实是题中应有之义,三教皆不过是成全这个“吾自有之物”而已。“道”之给自我带来的“转化”(变化气质)说到底是一种自我转化。就三教之道皆是大道之一端、三教之教皆为“吾之用”而论,王阳明对弟子每每提及的三教异同问题,往往不予正面的回应,“教”与“吾”之生存论的关联方是吃紧问题。
这个“吾”在儒家的理解中,从不是绝缘的个体,而是处于世间之中、扎根于社群与文化传统之中的“吾”,故“吾”之心灵之洒脱与身心之安顿一定是在地化的,是处于世间、扎根于社群与文化传统之中的。“现世的生命关怀”与“中国意识”,彰显出王阳明三教之判之中的儒家本色以及相应的文化自觉。是的,儒家之“道”总要落实于“人道”与文化之道。
王阳明所终极认同者即是此“吾”之“道”,这是超越三教的“大道”,是自然(身体)-社会(文化)-心灵三位一体之“大道”;固执于其中之一端,皆是“自小其道”。
从“道一而已”这个整全的立场看,王阳明思想的最高端其实是超越三教的(这是其良知教所逼出的觉悟境界,也显示儒学的极高明之处)。“吾之用”与“道一而已”两个向度则恰为一事之两面,前者是“体”,后者是“用”。在这两点,无论说“体”说“用”,都是在超越的层面立论。在此层面,王阳明只信任“心”、“良知”这一全体大用。在此良知之心的烛照下,三教圣人与经典都处于客体之地位,而不具有至上性。而后三个向度,都是从道(良知)之落实的现实层面立论,便不能不“分殊”,不能不现实地有所“偏向”(此时不“偏”,反倒是“偏”,况王阳明认为儒学比二家更中正圆融)。这一点从其“终极认同”(生命底子仍是儒教)可得到证明。因为相较于佛老,儒教无疑更适合中国实际,更具有“在地性”。这一立场使其更加重视现世关怀,更加重视中华文化慧命的特殊性,因之而导出“现世的生命关怀”和“中国意识”。要之,前二者可破世儒之“法执”,后三者则破而又立;前两者可以证成儒教(良知教)之普遍性、全球性,后三者则显示出普遍性、全球性的信仰同时亦是在地性的(localization);所谓的全球在地性(glocalization)实已暗含在王阳明的三教之判中,惟隐而未发而已。
需要补充的是:(1)“道一而已”与“吾之用”两个向度,在王阳明的论述之中往往是针对世儒偏狭的“崇正”意识或弟子拘于三教异同、为名相所缚不知实地用功而发的,其用意自然是为了打破此故步自封的心态,建立“吾”与“大道”的生存论之关联。而王阳明通过“心学纯明之时”,“吾”与“大道”的圆融无隔的三教谱系学的塑造,一方面展现出“圣学之全”的景观,另一方面则让一切有偏执心态者自跻于“拘于俗、束于教”的“一曲之士”之列。(2)“现世的生命关怀”与“中国意识”向度,则往往是从政治层面、从民族文化层面上立论,前者见于《南赣乡约》,后者见于《谏迎佛疏》。这已暗含着作为国家与民族层面的信仰必须考虑其世间性与文化性之因素的意思。(3)“终极认同”向度通常在王阳明与弟子辨析圣人之学与二氏之教“毫厘之差”时展现出来,是属于其建立“良知教”共同体之论说。
(本文系在提交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哲学2012威海论坛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承陈少明、林安梧、赵广明、孙海燕诸师友评论与指教,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