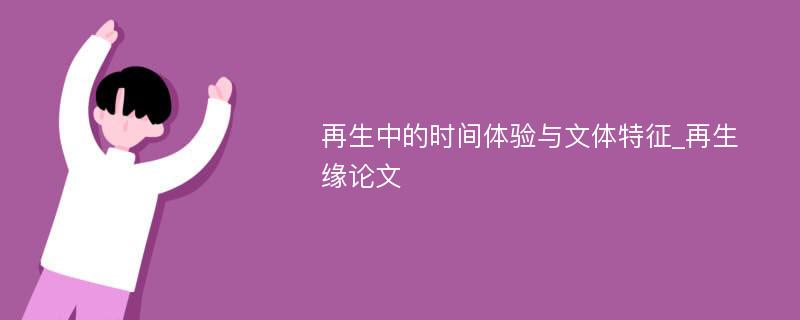
《再生缘》中的时间经验与文体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体论文,特征论文,经验论文,时间论文,再生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4)04-0113-06 陈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一文中提及了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他指出:“端生杏坠春消、光阴水逝之意固出于玉茗堂之‘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之句,却适于《红楼梦》中林黛玉之感伤不期冥会。”[1](P59)在陈寅恪先生看来,《牡丹亭》《红楼梦》和《再生缘》这三部作品在内在意涵和精神归属方面是相互关联的,联结点就是时间经验和身处时间之中的自我意识。我们一般可以看到陈寅恪先生对《再生缘》结构文辞的辨赏、陈端生生平事迹的考述,但较少注意到他将这部处于边缘的女性作品置于上自《牡丹亭》下至《红楼梦》的文学文化脉络中。所以,本文拟从《再生缘》中的时间经验这一角度,将此问题展开论述。借此,我们也可以重新审视和发现女性弹词这一文体,以及对其中的女性书写重新评判和思考。对于《再生缘》这部女性书写的经典之作,研究者的讨论常常集中在它是否具有“女权意识”这个问题上[2](P118-121)[3](P244-256)[4](P97-101)。事实上,女性主义的问题不光是一个女权的或性别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关于主体和自我本身的问题。《再生缘》与《牡丹亭》《红楼梦》对于时间、自我和欲望等问题的探求一脉相承,但它也利用弹词特殊的体例特质来表现独特的女性经验与困境,使之成为一种具有对话意味的、开放性的生命写作。 一 时间焦虑与生命之流 在《牡丹亭》和《红楼梦》中,时间、生命焦虑都是发生在花园中的。《牡丹亭》的《惊梦》一出中涌动的生命力在花园里随处可见——“姹紫嫣红”“青山杜鹃”“莺歌燕语”——所有这些意象都暗示着自然的生命力。在那里,女主人公杜丽娘重新发现了自我和生命之美。杜丽娘的花园经验体现了强烈的时间焦虑感,并最终获得一种超越时间的内在经验。花园是她获得永恒性体验和生命认同的中心场域[5](P259-288)。她之后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找回花园梦境中那个对时间没有焦虑的时刻。对时间的沉迷也同样贯穿于《红楼梦》。大观园中的时间似乎是静止的,贾宝玉执迷于大观园所呈现的永恒的青春之美。它不仅为主人公也为作者提供了一种超越时间、获得解脱的方法,令作者从创作本身获取愉悦与安慰,渡过时代与个人的危机。另外,大观园体现了无尽的时间变化、消长和循环,从而提示了人生的有限性,并唤起与之对抗的努力。它将瞬间与永恒、过去与现在回环往复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既是叙事的也是人生观照的多元视角[6](P168)。 诚然,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传统中存在大量以花园为故事背景的作品,但《牡丹亭》与《红楼梦》这两部杰作在刻画花园意象时所展示的强烈的抒情意味,以及与生命时间的交合,是其他作品的花园情节难以企及的。时间问题的引入也赋予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以丰富的内在性。而恰恰是在这些方面,《再生缘》也表现卓越,显示出与这两部作品的呼应之处。《再生缘》的写作是向着两个时间维度展开的:一是写作当下的现实时间,这主要体现在作者自叙部分对自己生活经历和写作状态的交代,特别是其中对庭院的描绘,标识着作者生活与创作空间的存在,而这些空间的细微变化则凸显了时间的流逝;二是虚构故事中的叙事时间,它是女作家存在的另一个维度,为自我提供了一个想像性的出口。 《再生缘》在每一卷的开头和结尾都有一段作者自叙,是作者关于生存和创作的自我呈现。《再生缘》之前的另一部弹词作品——《玉钏缘》虽然也有相关内容,但主要集中在每卷的开场诗中,一般不在正文中涉及。而《再生缘》则在开场诗中总结前一章节的故事内容,把自叙段落、庭园描写都放在正文部分,与虚构情节更为直接地展开对话和呼应。后来的女性弹词小说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写作方式,大大扩展了自叙段落,比如《笔生花》甚至在每一回的头尾都有类似的自述,且篇幅亦有所增延。这些段落通过对庭园的诗意书写,传达出对时间的敏锐感知,以及记录时间之流的内在冲动: 一片夕阳笼远树,满阶残叶绕疏帘。砚池薄薄冰初结,庭院深深雪未翻。夜拨炉火还静坐,晓怜日影趁闲篇。[7](P53) 仲春初七启新篇,时值融和二月天。芳草未生窗外绿,和风已解户边寒。春深庭院拈诗句,日暮楼台放纸鸢。清静书窗无别事,闲吟才罢续残篇。[7](P158) 季春十二又开篇,时值风和日暖天。新雨过时花气好,晴风来处树阴偏。长画静,小庭闲,双燕窥入爱卷帘。檐草春生青浅浅,瓶花吐艳媚娟娟。清幽情况深堪喜,再作新篇续旧篇。[7](P256) 编书愈觉时光速,逢节方当午日迟。艾叶飘香簪鬓绿,榴花带雨映阶鲜。明朝正是天中节,成得观书且暂闲。[7](P374) 这些对庭园风致与生活的抒写呈现给我们一些与创作紧密相连的当下时刻;同时,它们又前后勾连,形成时间之流,而时令和节候是这一流程中的关节点。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对时间的呈现方式也与《红楼梦》“不期冥会”,因为年节也是《红楼梦》表现大观园诗意生活的重要结构因素,寄寓盛衰之意,象征人生起落[8](P81-82)。一方面,对四季轮回变迁的书写与记录展现出自我生命与自然、时间相同一的状态,在这种田园诗般的时间状态里流露出写作的愉悦;另一方面,花开花谢暗示时间的流逝及其所带来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在作品的后半部分愈加明显,比如卷十六开篇和收尾的两段: 一声声,莺啼晓院催残梦,一对对,蝶舞闲庭陈午风。睰指算,节令方交圆月夜,转眼看,时光又届禁烟中。研旧墨,罢谈人世荣枯事,展新篇,再续书间上下衷。[9](P858) 前几本,虽然笔墨功夫久,这一番,越发芸缃日月遥。起头时,芳草绿生才雨好,收尾时,杏花红缀已春消。良可叹,实堪夸,流水光阴暮复朝。别绪闲情收拾去,我且得,词登十七润新毫。[9](P923) 与之前的同类描写相比,这两段的节奏显然加快了,它造成了一种时间上的迫促感。一边是杏坠春消,光阴水逝,一边是在想像的故事中获得自我确证,以对抗时间。这就引出了虚构空间和叙事时间的展开,它们与现实时空进行有趣的对话:或是现实时间与叙事时间的巨大反差——“书中虽是清和月,世上须知岁暮天”;或是庭园空间与虚构空间有趣的平行对应关系,如[10](P615): 日暮隔窗闻鸟语,夜长歌枕听潮声。佳时莫赘升平象,妙笔仍翻幼巧文。七字包含多少事,一片周折万千情。才如美自吟香态,又转兴风作浪声。好似琵琶传曲调,真同琴瑟鼓和鸣。慢来薄露飘银汉,急处飞流下翠岑。闲绪闲心都写入,自观自得遂编成。 庭园中的自然景致:鸟语花香,潮浪之声,似乎都令女作者产生创作的冲动,仿佛它们一一对应着虚构故事中的种种起伏不平、种种烂漫欢畅。所谓“闲绪闲心都写入”,作者强调了虚构时空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内在连接。而在虚构的时空里,花园又是一个梦想之地,是引导她的人物逃脱困境的出口。 《再生缘》的女主人公孟丽君女扮男装从自家的后花园逃走,一路颠沛来到都城,易名为郦君玉,在科举考试中一举成名,随后在朝堂上开始了一段奇特的冒险。如果说杜丽娘是通过艰辛地重获花园梦境中的完美时刻,获得与她才貌相当的配偶来实现自我,那么孟丽君则是从花园逃离,企图在公众领域实现她的才能。从时间维度上来说,《牡丹亭》中的花园场景是一个被不断回望的高潮时刻;而在《再生缘》中,花园是面向未来的新起点,之后女主人公将经历一段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生改变。 在孟丽君易装出走前还有一段颇有意味的情节设置,即孟丽君像杜丽娘一样为自己画了一幅小像。杜丽娘自写真容是为了将她的青春之美留迹于尘世,在情爱理想中实现自我。她还在画上题诗一首——“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11](P78)——预示了与梦中情人柳梦梅的相遇。可以说,自画像是她隐秘愿望的外化,她要将时间凝滞在自我表达的最完美的时刻,这也是其自我确证的方式。可是对孟丽君而言,情形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孟丽君的自画像也描绘出鲜妍动人的女性之美,但她的题画诗却表达了换上男装、追求事功的愿望和决心——“今日壁间留片影,愿教螺髻换乌纱”[7](P135)。这样,孟丽君的自画像反映的是一种女性生存的困境,是自我形象和性别身份的暧昧。 后来,孟丽君的未婚夫皇甫少华得到了这幅画像,他想借此揭示孟丽君的真实身份。这时的孟丽君已不再愿意回归传统的女性生活空间,因而也无法像杜丽娘那样回应情人的呼唤。但是当她又一次看到她的自画像时,画中形象唤起了一种复杂的时间经验、一种“物是人非”的伤感[10](P476): 凝眸一览知亲笔,不觉心中暗痛酸。珠泪欲来忙忍住,悲声将吐又将含。心暗想,意私言,不道真容在此间。忆昔当年亲手画,如今忽忽又三年。 对孟丽君来说,这幅画像如今只代表一个遥远的记忆,而不是一个确定的关于自我的表述。如果说杜丽娘的自画像使得时间和生命凝滞在梦境般的丰盈完美中,孟丽君则让时间停留在一个充满疑惑的时刻,标志着生命时间的断裂,是对自己的女性形象和过往经验的一场不无遗憾的告别。 《再生缘》为我们展示了复杂而多样的时间经验。从作者自叙层面的现实时间到故事发生的虚构时间,再到人物易装改扮所带来的时空的断裂感,表明真实与虚幻之间相互渗透和互补的关系。正如第五十三回和第五十四回的标题所呈现的——“假小娘句句如真”“真女儿时时装假”——反讽性地传达出真假转换的深刻意涵。在这一点上,《红楼梦》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最丰富而深刻的诠释。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大观园中那些感性、自足、理想的存在最终证明是虚幻的,而关于贾宝玉的故事又代表了存在的某种真实状态。如果说孟丽君的女扮男装只是一场白日梦境,那么她的虚构故事也在一定程度上演示了女性的内在真实,创造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时间体验,从而丰富了自我的存在。像陈端生这样的女作家正是有效地运用了弹词这种体裁来延展创造性的时间体验。 二 开放性与对话性 无论是花园的建构还是自画像的创作,都是企图构筑一种超越时间的状态,同时又不断提示着人生易逝,唤起新的焦虑、恐惧和欲望。但是在对抗时间或展示生命时间的方式上,《再生缘》与《牡丹亭》《红楼梦》又有所不同。《牡丹亭》所描写的事件被凝固在了《惊梦》一出中最具表现力的瞬间,杜丽娘始终回望生命中那一理想时刻;《红楼梦》试图构筑大观园这个永恒的理想世界,使时间停滞其中,将之空间化了。可是,《再生缘》却呈现给我们一个更为动态的、开放性的、生命意义生成的过程,从而丰富地展现和塑造了女主人公的主体经验和内在性。可以说,《再生缘》在塑造女主人公的心理、自我的成长和发展过程方面,更为丰满生动。弹词的体例特征使之兼具戏曲、小说之长,而它的边缘地位又令它可以摆脱叙事和修辞的成规,因而给予了女作家以更大的灵活性和可能性来书写这个过程。 一般而言,高度风格化的戏剧体裁提供了相对闭锁的想像空间,表演的成规、程式化的修辞和规定情境都限制了自我表达的范围和独特性。比如不少明清女作家在她们的戏剧作品中都对易装主题特别地关注,并借助男性角色表达她们作为女性的挫折感,像叶小纨的《鸳鸯梦》、何佩珠的《梨花梦》等。但这些作品仍然集中在对才子佳人以及相关的情爱主题的描绘上,而很少涉及易装女主人公的社会活动,比如考试做官等。王筠的《繁华梦》可以说是将易装主题发挥得较为彻底,她让女主人公在梦中变成一男子,不仅考取功名登上庙堂,而且四处寻访美人,终得一妻二妾[12](P29-137)。但是在这部作品中,女主人公从“旦”变成“生”后,就被角色惯例所束缚,完全成为了才子佳人剧中享有男性特权的才子角色,而无法让我们知晓作为女性在穿上男装之后特殊的心境和困扰。而这一方面恰巧是很多女性弹词作品可以补充和呈现给读者的。 由于戏剧作品的篇幅限制和舞台呈现的特点,整部作品一般只围绕几个人物和集中的事件展开,正如李渔所谓作传奇者,“头绪忌繁”,好的作品“一线到底,并无旁见、侧出之情”。这也与表演的性质有关,因为“戏场脚色,止此数人,纵换千百个脚色,也止此数人装扮”,所以戏曲作品倾向于集中笔墨在“一人一事”上[13](P18)。戏剧形式的表现主要是在空间的存在里,因而倾向于封闭的叙事结构,而女作家们的弹词作品已几乎完全成为案头之作,篇幅上的灵活和结构的松散让女作家们蔓生枝节,延搁复装的时刻,从而让女主角经历一个更长的内在化的转变过程,而这种变化在杜丽娘那里是不明显的,她的人生目标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就是要将她的梦境现实化。但在《再生缘》中,伴随着各种情感、欲望和心理波动,孟丽君的易装行为逐渐形塑和改变了其人生追求及自我认知。 起初,孟丽君的改装潜逃有着两方面的动机:主要原因是躲避国丈之子刘奎璧的陷害,保持对未婚夫皇甫少华的忠贞;其次是模仿女状元黄崇嘏一展才华的游戏心态。后来她科举成名,位列朝堂,渐入佳境,便常以妇德为由,延迟身份的揭示。当她成为兵部尚书后,她越来越认真地对待她的社会角色,不再把它看作短暂的游戏和不得已的避难。她说:“今朝复任尚书位,也算得,世上裙钗第一人。何须洞房花烛夜,安心且做几年官。九重丹陛皇恩重,做一个,赤胆忠心保国臣。”[7](P270)于是又演绎出平边乱、靖国难之举,皇甫少华婚配燕玉(刘奎璧妹)、孟丽君拒说真相之事。当她官至宰辅后,其社会角色对她而言已不只是一种责任或“皇恩”,而成为她的人生抱负和自我实现的方式:“为什么,定要复姓配皇甫?丽君虽则是裙钗,现在而今立赤阶。……何须必要归夫婿,就是这,正室王妃岂我怀?况有那,宰臣官俸嵬嵬在,自身可养自身来。”[10](P607)这样,随着孟丽君心理现实的转变,故事情节也波澜起伏地不断延宕——种种揭示孟丽君身份的设计圈套与她的种种抗辩、自救,甚至出现了真假孟丽君的耐人寻味的场景;而在这种不断的延搁中,她的情感、困境以及自我辩难得到了越来越丰富的探索。即使孟丽君下定决心不再回归传统的女性生活空间,她仍然流露出对女性自我和女儿、未婚妻等女性身份的些许依恋。作为女儿,她因无法对父母尽孝而自责:“郦明堂啊郦明堂,可嗔尔聪明盖世的才人,倒做了世间的逆女”[9](P762);“别人多报劬劳德,惟有我,未尽心来未尽肠”[9](P763)。作为未婚妻,她也有柔肠百转之时:“秋水盈盈将泪下,春山脉脉已心伤。容惨淡,意凄惶,感动情疏铁石肠。”[9](P870)由于这些对心理现实的不断探求,孟丽君在易装后并未像王筠的剧作《繁华梦》的女主人公那样完全以社会对于男性性别身份的定义和要求来思考或行动,而是作为女性主体表达易装时性别身份的暧昧所带来的心理的、现实的困境,以及内在自我的成长过程。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孟丽君的女性身份为她带来的犹疑并非由于等级秩序或道德观念的界定,而是出于个体的情感诉求。 《再生缘》以女主人公的心理变化为线索,不断敷衍生成传奇性的情节内容,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了弹词这种边缘性的文体,使之具有了某种开放性。当然,章回小说在篇幅上也没有太多限制,因而也提供了类似的便利。但是,毕竟小说的传播方式、男性叙述者的口吻、内容方面的不“纯净”等都有碍于女作家的参与。事实上,女作家们极少涉足小说的创作。就小说传播的高度商业化而言,闺秀作家们自然不愿意卷入高度商业化的传播体制中而影响到自己的清誉,正如陈端生所说:“不愿付刊经俗眼,惟将存稿见闺仪。”[7](P106)因为小说的受众千差万别,涵盖的社会内容也较为驳杂,在这些方面并不适合女作家们自我表达的需求,而弹词女作家们的读者却和自己的生活处境乃至心境颇为类似,把弹词的写作和阅读看作生活、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和理想读者的距离非常接近。这样,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对话性就更强了。在此意义上,弹词比一般的小说更具有某种“私化”或个人化的特点。 韵散相间而以韵文为主体的弹词可以在叙述、描写和抒情之间自由转换。韵文形式有利于人物以抒情的方式创造内在性,表达人物的心理现实。在这一点上,一方面,弹词与戏曲更近——比如像《牡丹亭》那样深刻的内在自我的表达——而比传统小说更具有优越性;另一方面,弹词是在讲述故事,而不是像戏曲那样的舞台呈现,作者甚至时常在自叙段落跳将出来,与自己的作品、读者进行有趣的对话,这种叙述的灵活性又非戏曲可比,倒是和《红楼梦》跳脱的叙事视角的转换有类似之处。前文已经论述过处于现实时空的作者如何与自己的作品对话,谈论光怪陆离、瞬息变幻的虚构空间中的人事:“才如美自吟香态,又转兴风作浪声”[10](P615),又如“天孙织锦千丝巧”“孔雀开屏五色重”[10](P733)。在这些语句里,作者还不时地与读者对话。从卷一开篇“知音未尽观书兴,再续前文共玩之”,到卷十七末尾“仆本愁人愁不已,殊非是,拈毫弄墨旧时心。其中或有差误处,就烦那,阅者时加斧削痕”,与读者的对话强调了女性弹词文本特殊的能动性,即作者与读者两个主体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创造。特别是卷十七结尾的这一段文字,表明作者的生存处境和创作心态已与初时大不相同。根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证,陈端生的丈夫此时因科考弊案的牵连已流放边地,她独自抚养两名幼子,生活困顿,心力交瘁[1](P60-62)。因此,其创作意旨以及对人物心境的揣摩都已不同于初衷,研究者也因此对故事结局和人物命运的争议不断。女作家到底是要让孟丽君回归家庭还是自杀反抗,抑或是在这未完成的文本中无限延搁她的抉择呢?其实,我们不必纠结于这样的判断,重要的是作者生活经历的变化和对性别困境的体会逐步地随着弹词作品的发展而表达出来。它表达的不一定是直接的现代女权主义式的反抗,但是对生命境遇、女性自我的呈现更趋复杂了。 有论者指出,女性弹词作家们在她们的作品中展现了强烈的自传性意味[14](P62-99)。但更为有趣的也许是这些弹词作品充满活力的对话冲动。陈端生在她停笔之处邀约读者参与她的创作,这种对话的状态使得作品具有一种未完成性和未定论性。这种对话性的构造不仅存在于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于作者与主人公之间。弹词是以诗的形式来讲故事,而诗歌中的抒情/叙述人称是不确定的。这种不严格的叙述人称给弹词作品带来了多重声音的可能性。叙述人称可以非常自由地转换:时而是“她”,时而是“我”;一会儿作者/叙述者的声音强一些,一会儿人物的声音强一些。叙述者可以从适当的距离观察她的人物,又可以很便利地让位于人物的大段独白,让人物自己去感知、思索、表达,从而揭示人物自己。比如在孟丽君身份揭晓时对其内在冲突的描绘就得益于此。孟丽君最终为皇后所陷,酒醉后脱靴露真。她酒醉醒来发现身份败露的这段描写是作品中最动人的片段之一[9](P952): 痴呆呆,一体四肢如土木;渺茫茫,三魂七魄赴泉台。真个是,不生不死浑无二;真个是,如痴如醉乱了怀。叠着脚,锦袜乌靴都撇下;低着头,明眸秋水不能抬。恨一声,无言无语情愈急;叹口气,含怒含愁意转哀。顷刻间,撩乱千端无可理;顷刻间,缠萦万绪力难排。心神一动伤心血,樱口中,几点鲜血喷出来。 《再生缘》将这一戏剧化的时刻表现为悲剧性的场面,这一悲剧性既来源于人物内心伤痛的激烈表达,也来自叙述者或是作者同情的目光。这一段文字的人称是不确定的,既可以说它是叙述者的观察,也可以说它是女主人公内心情绪的直接表白。“痴呆呆”“渺茫茫”“真个是”等三字头句式的连续使用加强了那种逼人的悲剧气氛,展现了女主人公在易装过程中逐步建立的内在自我与社会现实的冲突达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而这个过程也是作者与女主人公隐秘的对话过程,是其自我意识形成的过程。在有些独白段落中,当情绪高涨时,我们还会看到第二人称的出现,比如之前提到的,孟丽君决定保留其男性身份而不得已对父母造成了伤害。这时,她展开了激烈的自我辩难:“郦明堂啊郦明堂,可嗔尔聪明盖世的才人,倒做了世间的逆女。”第二人称的运用造成了另一种可能性,即叙述人对人物的发问。也就是说,作者对主人公的态度,有时也像是一种辩难,把主人公当作一个对话者,它既是作者的理想自我,又不时超出作者的掌控。正是在这个对话过程中,女作家努力寻求和实现她的自我意识,确立她的主体性,进行自我探索。 《再生缘》的写作几乎贯穿陈端生的一生,作者与主人公、与读者的对话是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构成因素和特征。而对于许多弹词女作家来说,情况大都如此。最长的女性弹词作品《榴花梦》长达360卷,和《再生缘》一样,其创作也伴随女作家的整个人生,展现了其生命时间的流程,且最终亦未完篇,而由后人补续[15](P323-328)。实际上,这些女作家的弹词作品往往前后缠连。《再生缘》开篇即表明其人物乃是接续《玉钏缘》中的前世姻缘,而《再生缘》又激发了候芝、邱心如等女作家的弹词创作。有研究者指出,这些弹词作品之间“互文性”的关联特征以及它们如何关联在女性中构筑了一个“想像的社群”[14](P3-41)[16](P222-224)[17](P105-115)。女性的弹词创作是一个漫长、绵延的对话过程,既展现女性独有的时间、生命体验,又反映她们各自不同的存在样式。 三 结语 《红楼梦》和《牡丹亭》都表达了一种动人的时间关怀。不论是杜丽娘的寻梦之举,还是贾宝玉的大观园情结,都是出于对人生易逝的焦虑而试图摆脱现实时间的控制。这也是女性弹词作品的重要关注之一。人生易逝是中国文学传统中根本的主题之一,对于身限闺阁、人生抱负无法实现的女作家来说尤为真切,这大概也是女作家酷爱《牡丹亭》和《红楼梦》的原因之一。弹词女作家常常强调其写作梦幻般的性质。在《再生缘》中,陈端生写道:“悠悠十二年来事,尽在明堂一醉间。”[9](P924)这种梦中时间与现实时间的对比显现了摆脱现实时间控制的可能性与局限性。这种冲突与《红楼梦》对于个人记忆和理想世界的自省意味亦不谋而合。 《再生缘》对自我的思考和呈现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语境,明清时期对个体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新的觉识和质疑即是其一。曼素恩强调了盛清时期的复古运动(汉学的兴起)是影响当时社会性别关系的主要因素[18](P30-35)。但是,晚明哲学及社会思潮在清代的回响也同样不可忽视,尽管它常常以一种幽微曲折的方式存在[19](P7-22)[20](P443-474)。《牡丹亭》和《红楼梦》都从特别的女性视角探索了个体意志自由的问题,通过“情”为个体生命找到了最热烈的形式;而《再生缘》却试图在情爱话语之外寻求女性个体的自主与自由,即在公众领域获得尊重和认可。至于人生与梦幻、虚与实这样贯穿明清文学与文化的主题,在《再生缘》中也有所体现。不过,像《再生缘》这样的女性弹词作品往往述说了独特而复杂的女性经验和困境,而不仅仅是对男性文人们简单而轻松的回响。 弹词女作家的写作行为本身就像易装行为一样,昭示着变换社会身份和角色的欲望。易装女主人公是作者自我和生命经验的延伸,是多种可能性的显现和探索。女作家正是在这些体认、写作过程中不断创造新的美学身份,试图超越或否定现实自我,对社会提出质疑。弹词(此处仅指女性弹词小说而言)作为一种特殊的女性写作的文体,其开放性和对话性赋予女性叙事文学以独特的面貌,它呈现了女作家连续的生命记忆和自我、意义生成的踪迹,因此有助于一种集体的女性意识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