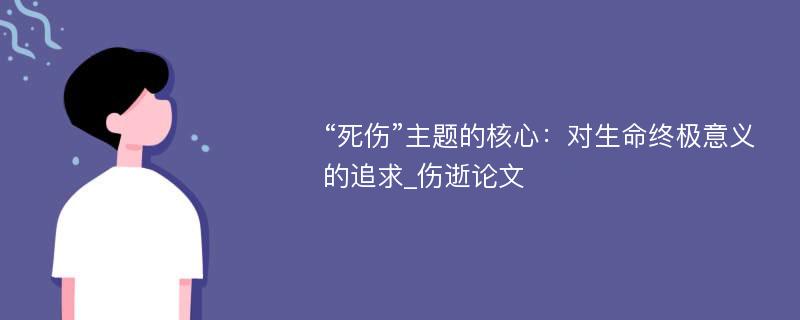
《伤逝》主题内核: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核论文,意义论文,生命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不同意关于《伤逝》主题的传统看法。认为《伤逝》的主题内核是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并将作品的意蕴揭示过程分为终极意义的憧憬期、现实生活的品味期、凡俗人生的彻悟期、生命追求的抉择期等四个阶段。鲁迅对这部小说的创作主旨的卓然确立和题材的独特处理,体现了他“开掘要深”的创作主张,使小说超越了《娜拉走后怎样》单纯分析社会问题的深度,超过了当时许多同类题材的社会分析和心理分析小说。
关键词 思辨性抒情文体 生命终极意义 凡俗人生 “真的人”
一
鲁迅的《伤逝》以沉郁舒缓的笔调,谱写了一曲失败爱情的悲歌。小说艺术上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了“涓生手记”的叙事方式。这就使作品偏离了对男女主人公爱情历程的全面考察,而将叙述重心落到涓生身上,把笔力集中于涓生的思辨、感叹过程及其追忆的外在和内心生活的情景,小说的内涵也随之超越了情节包含的显态社会价值而别具深意。
《伤逝》发表以后,论者对其主题作了各不相同的阐释。
解放前,有论者认为《伤逝》表现了奋斗者“生的意志”,也有人认为它是表现青年一代为什么“捐弃旧友,走向新生”。这种看法是论者身处其境对涓生、子君人生故事的一种知性把握,对《伤逝》主题的一种朴素的直观,它具有相当的准确性,但缺乏对作品内蕴周密细致的考察,理论深度和历史深度都嫌不够。
周作人则几十年不变地坚执一个“怪论”,认为《伤逝》表现的是“兄弟失和”的痛苦和悲哀。笔者认为,周作人观点的精辟独特之处在于,他别出心裁地抓住了作品人生体验方面的内涵,并从创作者的心态入手进行分析。但周论的偏狭之处恰恰也在于用对创作者个人心态的“索隐”,取代从作品出发对其主旨的科学分析,并以此抹煞了小说的多重意蕴和典型意义。
建国后的评论者大多从反映论、认识论的角度剖析《伤逝》,对涓生子君爱情悲剧的根源,提出了经济压力、个性解放未能和社会解放相结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和不足等几种主要看法,并相应地形成了关于小说主题的几种观点。这些看法都说出了《伤逝》的部分内涵,但他们实际上是首先观察分析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涓生子君这一类人的生活轨迹和精神特征,再以之去套《伤逝》这部作品,并将社会历史原因看作人物悲剧的最终根源,从文本的具体实际出发则做得不够。如果《伤逝》这部作品,并将社会历史原因看作人物悲剧的最终根源,从文本的具体实际出发则做得不够。如果《伤逝》是一般的写实型社会问题小说,他们的方法是能够毕其全功的。但是,鲁迅对涓生子君爱情悲剧的认识,已经超越了社会历史层面,并创造出思辨性抒情体这一文体形式作为他思维成果的相应载体。社会学批评论者却将社会历史原因看作人物悲剧的最终根源,而把小说的情感内涵和形上意蕴仅仅当作人物性格的表现。这种本末倒置就导致他们对《伤逝》意蕴的把握失之肤浅,对涓生子君爱情悲剧原因的剖析本身,也存在隔靴搔痒和难以自圆其说之憾。
“经济压力”论者认为,没有经济的独立,涓生与子君的爱情缺乏相应的物质基础,这才引起感情的变异,导致双方关系的最终破裂。在这些论者看来,《伤逝》是沿着《娜拉走后怎样》强调人格独立依赖于经济独立的思路,对“娜拉”们出走以后“不是堕落,便是回来”的形象化剖析。其实,“涓生手记”形式表明,《伤逝》的创作主旨已发生变化,艺术重心转移到了男主人公涓生身上。从作品本身看,涓生失业是涓生子君爱情的一个重要转折,但事实上在失业的打击来临之前,他们的感情就已存在裂痕和危机,失业起的不过是催化剂作用;而在涓生失业的最初阶段,短暂的慌乱、怯弱之后,“外在的打击其实倒是振作了我们的新精神”。涓生反省爱情生活形成的核心观念是,“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但在涓生乃至鲁迅看来,纯粹物质性的“活着”乃是一种“苟活”,“人必生活着”的“生活”一词指的应当是在“为了奋斗者而开的生路”上活着。何况从常理来看,偌多的人间夫妻在更艰难的经济境况下,同样相濡以沫、白头偕老,“夫妻恩爱苦也甜”,就是中国贫贱夫妻爱情生活的写照,即使经济压力真成了涓生子君爱情悲剧的决定性因素,不也恰恰显示出他们身上存在着其他的主观原因吗?
“个性解放”论者认为,涓生和子君没能把个性解放和社会解放相结合,未能在社会解放的历史洪流中找到共同的思想基础,结果他们美好的爱情被强大的社会黑暗吞没了。这是一种社会一解放就天下大吉,“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庸俗社会学思维。其实“多余人”自有”多余人”的爱情,问题恰在于,子君对做家务、侍奉自己爱人的“多余人”位置心满意足,涓生则认为如此活着卑琐无意义,不是位置本身而是对这种人生位置的价值判断才是他们的分歧所在。而认为涓生子君投身社会前进的历史洪流,爱情就保险了,则是一种简单幼稚、一厢情愿的乐观构想。共同的集体事业能暂时冲淡和压抑个体对自我人生意义的追求,甚至造成集体理想就是个体价值所在的表象,但它决不可能永久地取代和消泯这种追求,因此,相同的社会理想不等于爱情的共同思想基础。殊不知,在革命胜利后,革命队伍内因种种原因造成婚姻悲剧的比比皆是。历史决定涓生一代人大多数会走上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相结合之路,这也造就了许多美满的爱情,但它并不是消除涓生子君“这一个”的爱情悲剧的充分条件。
“知识分子缺陷”论者立足于从对象主观上寻找原因,较前两论有其深刻性。然而,当时同类知识分子中,携手前进或共同妥协堕落而保持爱情婚姻关系的均有其人,何以唯独涓生子君不能进则同进、退则同退,而是互相失望、冷漠,以至最终分手呢?关键在于他们各自对爱情所要求的内涵实质上是不相同的,作品对这种歧异的深刻揭示显然被论者忽略了。
80年代以来,论者以西方现代哲学为参照系,着力挖掘《伤逝》包含的生命体验的现代性特征,寻求其存在于社会功利目的之外的普遍意义。这类评论实际上是对作品体验方面意蕴的形而上解说,而且片面地突出了《伤逝》对人生荒谬性、虚无性等无价值方面内涵的抒写。事实上,《伤逝》既包含着直接的现实功利目的,生命意义、人生价值的探索又比对生命的体验占有更突出的地位。论者削《伤逝》之“足”以就西方现代哲学之“履”,结果造成了论者探求路向与作者主观意图的偏离,对《伤逝》永恒性的揭示,反而使作品成了时代背景模糊的普泛的人生慨叹,这种抬高实质上是一种贬低。
《伤逝》的独特文体使这部小说形成了一个意蕴系统,即具有生活层面、内心体验层面和哲理层面。孤立地抓住作品某一层面、内涵来立论,确实有可能找到依据,但只要我们综合起来从总体上把握,就会发现,上述各种对主题的见解都是各执一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存在着把《伤逝》多重意蕴的相容互补关系变成对立排斥关系的方法论局限。
二
《伤逝》的副标题实际上已提示了小说的文体特征,即思辨性抒情体。从这一角度看,涓生的价值判断和追求才是《伤逝》的思想基点和主题内核,那么,涓生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
小说中相当频繁地出现了“路”的意象和“奋斗者”一词,在渴望开辟新路的过程中,涓生眼前反复出现的代表理想的意象是:“怒涛中的渔夫,战壕中的兵士,摩托车中的贵人,洋场上的投机家,深山密林中的豪杰,讲台上的教授,昏夜的运动者和深夜的偷儿。”这些意象性人物的社会身份各不相同,唯一共同之处是,他们都处于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价值的位置、生命最辉煌的时刻。在涓生心目中,具备这样的特征,才是真正的“奋斗者”,这样的生存,才是理想的人生之“路”。因此,我们认为,涓生是站在追求生命终极价值的角度来对待人生以及他与子君的爱情的,他对子君爱情的追求与放弃,都与他对生命最高意义的追求紧密相连,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对涓生来说,实际上是一曲生命终极意义追求的悲歌。
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我们将作品的意蕴揭示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小说的开头到“这样的热烈,这样的纯真”,是终极意义的憧憬期。
憧憬期的涓生,充满激情、信心和浪漫的幻想。在关心子君的担忧和“宁贴”中,在放谈的满足中,他获得了青春期浪漫的快乐,“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于她能算什么东西呢?”这既是子君,也是涓生的激情和信心的反映。这时的涓生显然把爱情当作人生的全部和最高的意义所在。恋人不在身边即看不进书、百无聊赖的情态,不仅体现了陷入情网的年轻人的心理状态,而且是涓生思想认识不自觉的外化。
从表面来看,涓生大谈男女平等,伊孛生、雪莱,俨然是一个资产阶级个性主义者,但实际上,他对子君大谈男女平等,采取的却是居高临下的姿态。子君说出“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思想时,涓生“狂喜”之余的评断充满权威意识。所有这些都证明,涓生未脱封建男权社会男性的优越感,未脱启蒙者心理和人格上的潜在优势感。憧憬期的涓生在思想认识上新旧杂陈,这新的和旧的思想统一于他乌托邦式的爱情设想,爱情构想的完美又体现出他对人生完美性即人生终极意义的美好憧憬。在这时的涓生眼里,对爱情的憧憬追求与人生完美性的憧憬追求是同一的。
涓生迷于构想却弱于行动。他送子君时隔十多步远,他对求爱方式不知所措,都说明了这一点。涓生对下跪方式的“浅薄”庸俗感到“愧恧”,显然是觉得体现人生最高价值的行为应有同样完美的新形式,而不能如此俗气落套。其间已露出将终极价值与凡俗形态对抗的苗头。倒是子君敏锐地抓住了俗气的下跪方式所包含的深意,长久地温习和品味它,这又恰好现出两人意趣有别的端倪。
从“去年的暮春”到“未忘却了我的翅膀的扇动”是现世生活的品味期。
这一时期的涓生有过“最为幸福”的感受。骄傲地反抗讥笑猥亵的目光,苛酷地选择住所,共同出钱买家具,相对交谈和沉默,所有这些,都使涓生感到生动、快乐和充实,感到相互的体贴和温情。这是一种新婚的快乐,是日常生活的具体琐事所引发的新奇和愉悦。这时双方的矛盾隐而未显,即使有花草与鸡狗爱好的差异,两人也用轻描淡写的告诫,用“领会地点点头”,忽略过去了。但这种快乐充实的本身就潜伏着危机,那就是日常生活存在着生动特性的反面——平淡,人不可能天天忙碌新奇,一旦告别惊喜,进入天长日久的平淡状态,他们还会那么快乐和心满意足吗?
“灯下对坐的怀旧谭”表明了他们激情的衰竭。生存的琐事挤掉了读书散步这类颇具文人乃至封建士大夫雅趣的诗意生活方式。因为操劳家务,子君“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丧失了青春少女诗意的柔美。这些让涓生甚感痛惜又颇不满意。子君已经在操持家务之中体会到了生活的艰难,艰辛的劳作却未获丈夫的夸赞与慰藉,她于是“有点凄然”。在这种情形下,一旦辞退职业的通知摆到面前,实际上仍是个弱女子的子君就“变了色”、“较为怯弱”了,表达也变得“浮浮的”,底气不足。外在的打击使他们不得不以“坚忍倔强的精神”为基本生存而痛苦拼搏,从而忘却了为自身的生存意义而烦恼,生存过程无价值无诗意的部分却因此又一次丧失了被从容理解的机会和可能性。
在现世生活品味期,涓生于“此在”的生活中,既尝到了幸福与充实,又体会到了平庸和艰难。那么,他是因为平凡蕴含的丰富而珍重它的深厚和宁静呢,还是因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对平庸于心不甘、坚决地予以摒弃,去追求人生的终极目标?显然,前一种价值取向是现世的、凡俗的、承认人生有暗淡部分的,后一种取向则带有永恒超越性,是浪漫的,要求人生完美的。
从“小广告是一时自然不会发生效力的”到“它回来了”,是凡俗人生的彻悟期。
一开始对子君消磨了诗意的美,涓生还只是感到痛惜,现在子君“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贴了”,涓生则产生了反感和厌烦。涓生一直以十全十美为标准来衡量子君,而子君不过是一个大胆的纯情少女而已。这样,在清醒地读遍了子君的“身体和灵魂”,揭去人生诗意的面纱,看到其平凡的骨架之后,涓生便难免失望。涓生日常烦恼的内容,是“弥漫着煤烟”,是两家的争吵,是川流不息的吃饭,是子君除了为这种生活操劳之外便很颓唐,似乎常觉得凄苦和无聊,总之,是失望和痛心于生活的凡俗和子君的平庸。同样,涓生对子君的隔膜感,子君对涓生不能理解她的操劳时的“凄然”神情,都源于对“心心相印”这一准则,对人与人之间精神沟通的完美性的信任。也正因为此,子君在失望之后转而凄然、冷漠,进而逼涓生修旧课示温存,而涓生在看到了相互关系的缺陷后,便烦躁、冷漠、转而决绝地要遗弃子君,以期出现新的奇迹。
涓生和子君的失望表现出,他们的爱情确实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盲目之处在于,子君只求理想的爱人,凡俗的爱情生活,涓生则要求完美的爱人和理想的、能最大限度地体现生命价值的爱情生活,他们对各自在爱情方面的实际追求却并不自觉,于是,当经济、社会压力增强,对他们的同居生活形成严重威胁时,他们的内在精神差异便凸现出来,最终导致了双方的分手。由此可见,涓生子君恋爱悲剧的根源,在于对人生意义的不同追求。
涓生把生活、人生的路分为两类,最能体现个体生存意义的奋斗者生命形态具有创造、生命力最大限度的发挥、个体价值最大程度的体现等特征,它与凡俗生命形态的因袭、生命无价值消耗、生存形态低质量维持的特征是对立的、不可能相容的。对奋斗者生命形态的追求构成涓生的生命欲求,为此,他或者与子君携手同行,或者孤身奋往,绝不会受拖累而停滞不前。爱情曾被涓生当作“人生要义”,现在它与人生追求的同一状态已不复存在,却成为他终极追求的拖累,涓生也就自然地要予以摒弃了。
但是,囿于凡俗的子君在爱情失败后,却只能退回家庭,结果必然地死于“无爱的人间”,连作为生理构成的生命也被毁灭。涓生未曾达到自我人生的终极目的,子君却为他的追求付出了生命最基本形态泯灭的代价,这其中表露的自我中心意识、自私特性使涓生不能不深深自责。而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仅未前进一步,反而退回了原来的起点,这就更令涓生感到悲哀。早知如此,当初何不留住子君,相互维持价值贫弱的生存,也免得子君生命惨遭毁灭呢?可见,涓生这时忏悔的根基也并非爱情本身,而是生命和生命的意义,他对离异并未内疚,只是源于对生命的珍重,而对离异的后果痛悔自责。这种后果却是涓生彻悟人生后欲追求生命终极意义所导致,涓生的终极追求也就具有了悲剧意味。
从“我的离开吉兆胡同”到结尾,是生命追求的抉择期。
涓生以凡俗生活的维持为异化状态,为“苟活”,为“真的人”不存在的“虚伪”的生命形态,而以揭穿这种虚伪为真实,目的却在追求新的生活,然而,新生活未能变成现实,虚伪的生活形态也已消失,于是生活就成为一个“虚空”。涓生退回会馆时期,就正处在这样的“虚空”之中。
“虚空”中的涓生面临两种选择。
首先,涓生“愿意真有所谓地狱”,以便去寻觅子君,乞她宽恕或使她快意,实际上是珍重和维持生命基本形态,回到凡俗生活。但以涓生的生命终极关注的眼光来看,它是无价值、不存在的,因而是“更虚空于新的生活”。然而,“阿随”的归来使他怦然心动。子君珍爱俗物,阿随回归体现的历难不渝的情意和忠诚,似乎暗示着凡俗生活自有深厚之处存在。这就更让涓生痛悔不已,以致他生怕自己的“悔恨和悲哀”未能向子君倾诉,却被地狱的“孽风”和“毒焰”所毁灭。
然而,往事已不可更易,涓生只能“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忘却对生命基本形态消泯的痛惜,“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这种情况下对终极意义的追求,实在是在对凡俗生活绝望之后,对绝望本身的反抗,它充分体现出一种对生存虚无、悲剧本质有着深邃形上体验之后的、非同凡响的意义探求精神。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涓生主观方面,与子君的恋爱、同居和离异,都源于他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鲁迅采用“涓生手记”形式创作《伤逝》,正是为了强调涓生、子君爱情事件所包含的这种形而上层面的意蕴。所以,哲理层面的内容才是《伤逝》的意蕴内核、文本骨架,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才是鲁迅创作这部小说的主旨所在。
三
鲁迅选取个体生命的角度探讨涓生和子君的恋爱悲剧,因而看到了两人离合之间的主观精神联系,为涓生的思想行为矛盾找出了极具说服力的解释,并为他深邃多变的生命体验理出了明晰的脉络。《伤逝》对题材处理的这种独特高明之处,体现了鲁迅“开掘要深”的创作主张,使小说超越了《娜拉走后怎样》单纯分析社会问题的深度,超过了当时许多同类题材的社会分析和心理分析小说。
在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方面,鲁迅同样有其卓越之处。作者对子君这样一个大胆纯情的弱女子,无疑是赞赏和爱惜的,对她“死于无爱的人间”则深感愤慨。他却又严苛地剖析了子君以世俗因袭的幸福为满足、人生观狭隘平庸的局限。对涓生,鲁迅从道义上有着深沉的谴责,甚至让他想到了地狱的“孽风”和“毒焰”。但是,对于涓生在追求生命终极意义与珍重子君个体生命之间的二难处境,鲁迅流露出深深的体谅。涓生一方面深深忏悔,另一方面又感到有苦难言,感到说不出的自我生存的悲哀,并坚忍地违背自己的忏悔决然前行,这里显然熔铸了鲁迅的自我情感体验和生存感悟。同时,鲁迅还冷峻地揭示出涓生在追求过程中表现的局限和追求本身的虚妄性。
鲁迅对涓生子君的双重态度,既体现出他生命体验的深邃复杂性、现代性,又表现出他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坚定的启蒙主义立场。
鲁迅一贯主张文艺“为人生”并且“改良这人生”,致力于揭示国民的精神病苦。不按照“从来如此”的方式苟活,力图成为“真的人”,这是他在《狂人日记》中提出的社会性人生理想。“真的人”的概念又出现在《伤逝》之中,成为涓生的人生目标,它表明鲁迅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在创作中是一以贯之的。《伤逝》诞生于鲁迅的“彷徨”期。这种彷徨不仅指他社会思想立场方面的矛盾,而且也应该包括他在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对个体生命意义把握上彷徨苦闷的心境。成于《伤逝》同时期的《野草》,就集中体现了鲁迅对个体生命的心理体验和形上感悟。而且,1925年正是鲁迅与许广平恋爱、与朱安断绝旧式婚姻关系、与兄弟周作人失和的时期。鲁迅有极高、极严苛的精神追求,同时又有着极强的道义感、责任心,个人生活的严峻演变显然会促使他广泛深刻地思考个体生命的许多问题。鲁迅这时期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他从生命角度对“人间苦”的探究和思索。这样,研究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时,鲁迅选择生命意义的角度,并且采用思辨性抒情文体创作出《伤逝》这样一部作品,也就自然而然、不足为怪了。我们习惯于从启蒙斗士的社会身份来判断鲁迅并分析其作品,却忽略了他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忽视了对鲁迅1925年个人生活和心境的具体分析,因而未能对《伤逝》的意蕴进行多层面的立体的把握,也造成了对《伤逝》主题内核的误读。
收稿日期:1996-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