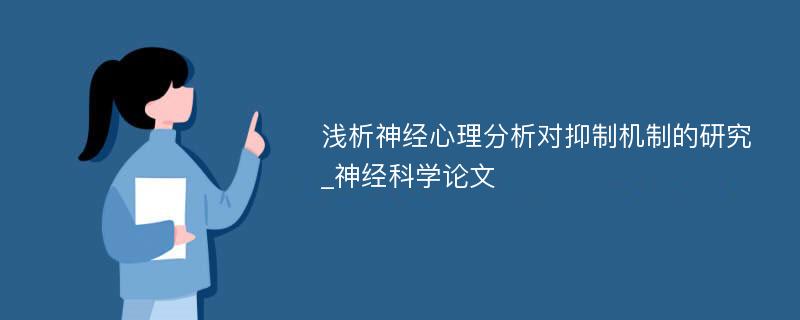
神经精神分析学对压抑机制的研究简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神经论文,机制论文,精神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R395
1 前言
神经精神分析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国外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而目前国内关于神经精神分析学的研究还很少,根据目前搜索的资料来看,只有南京师范大学的郭慧(2008)在其硕士论文《精神分析的科学化》一文中对神经精神分析学做了较系统和详细的介绍。今年又是神经精神分析学创立10周年,在这短暂的10年中,精神分析学发展迅速,而且其影响力也不断扩大,与我们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压抑是精神分析的一个重要概念,弗洛伊德(1914)将压抑看做是精神分析的整个结构建立其上的基石,是精神分析最重要的一部分(见Boag,2006)。Bankart(2006)指出,压抑这一概念在弗洛伊德关于谈话疗法的所有作品中部出现过。也许弗洛伊德的所有概念中最为被广泛研究的便是压抑(Sharf,2000)。同样,压抑也是神经精神分析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近年来很多神经科学家试图从不同角度来探讨压抑的神经机制,并取得了一些新的发现。本文希望通过介绍神经精神分析学对压抑机制的研究,使大家对神经精神分析学这一新兴领域有更多的了解,同时关注传统精神分析在当代的发展趋势。
2 神经精神分析学的诞生
身心关系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从未停止过,古往今来无数哲学家、心理学家、生理学家都曾对心理与生理的结合进行过构想和思索。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就是其中之一,在他于1895年撰写的《科学心理学的规划》一书中,试图建立一个心灵的神经物理学(医学)模型,其目的就是以纯粹的神经物理学术语来解释心理现象。弗洛伊德从1895年到1915年的著作都承认保留神经学支持的某种希望(熊哲宏,1999)。然而,因当时技术所限,弗洛伊德这一梦想未能实现。下面这段话出自弗洛伊德的《科学心理学的规划》一文,从中也许可以看到弗洛伊德对神经精神分析的一种预见:
除了从自然科学获得观点之外,每一个心理学理论必须满足另一个主要的要求。它必须对我们所知道的进行解释,通过我们的意识,这是最令人费解的方式,因为这种意识对我们目前所假设的一无所知,量化和神经元应该为我们解释这部分缺乏的知识。(这段话目前就在国际神经科学中心的网站主页上)
弗洛伊德的预言在20世纪末成为了现实。精神分析和神经科学经历了疏远、抵触、消融和对话四个阶段后(郭慧,2008),终于迎来了神经精神分析学的诞生。1999年《神经—精神分析》杂志的创刊和2000年国际神经精神分析协会在伦敦成立标志着它的正式建立。神经精神分析学旨在结合精神分析学与神经科学的视角,促进精神分析学与神经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成为21世纪精神分析研究的新范式。神经精神分析并不是要改变弗洛伊德所建立的精神分析实践,而是为通过其研究找到精神分析的科学依据(Bueno,Nora,Vansan,2007),神经科学让人更能成为主体,并有助于保持精神分析的独特性。
3 传统精神分析中的压抑概念及其争议
3.1 弗洛伊德论压抑
关于弗洛伊德的压抑的概念在四川大学徐云(2005)的硕士论文《关于弗洛伊德著作中压抑之物概念的文献复习》中已有详细的论述,这里我们只做简要介绍。
弗洛伊德在与布洛伊尔合著的《癔症研究》一书中第一次使用压抑一词,即对于癔症患者希望忘却的事情,有意的从他的思想中压抑着(弗洛伊德,布洛伊尔,1893)。在这里压抑是一种有意识的认知活动。另外,弗洛伊德(1916)在《精神分析导论》第19讲“抵抗与压抑”中提到,潜意识中那些不为意识所接受的冲动是被压抑的。弗洛伊德(1915)认为压抑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避免不愉快,如果压抑不能避免不愉快情感或焦虑的出现,那么就可以说压抑失败了。
关于压抑与防御的关系,在车文博(2004)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6——自我与本我》的附录中对此进行了说明:
弗洛伊德在英文版第163页关于他使用这两个术语的历史说明,可能有一点误导作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值得进一步展开说明。在布洛伊尔时期,这两个术语的使用都是很自由的。……然而,这两个词的用法似乎有某种差异:“压抑”似乎是指实际的过程,而“防御”则是这一过程的动机。……在对他的观点的历史发展进行回顾以及在说明后布洛伊尔时期时,弗洛伊德曾提到过这一观点并写道:“……‘压抑’(现在我开始用它来代替‘防御’)……”……弗洛伊德在讨论布洛伊尔时期的结束时又说,“我注意到,作为某一排斥过程的结果,精神机构发生了自我分裂。这一过程我当时称为‘防御’,后来称为‘压抑’。……然而,直到十多年后,在目前这本著作中,才对这两个术语的不同用法做出明确说明。
由此可见,在弗洛伊德理论发展的不同时期,压抑与防御的关系都极为密切,甚至可以等同或互换。尽管后来弗洛伊德指出了二者的不同,但压抑作为最为基本和最为重要的防御机制,历来是国内外学者的共识。
3.2 关于压抑的争议
3.2.1 压抑与抑制
目前的学界普遍认为弗洛伊德提出了两个关于作为防御机制的概念,一个是“压抑”(repression),另一个是“抑制”(suppression),压抑被看做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而抑制被看做是一种意识的过程。然而有学者对这种区分提出了质疑,纽约市立大学的Erdelyi(2006)在对弗洛伊德的作品进行学术分析后提出:弗洛伊德认为压抑可以是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过程,而且在弗洛伊德的作品中,弗洛伊德也将压抑(repression)与抑制(suppression)交换使用。Erdelyi认为是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为了整理其父亲“杂乱的作品”(messy work)才提出了这种区分。
3.2.2 压抑记忆的真实性
目前最明显的趋势是从记忆方面来定义压抑(Boag,2006),而关于压抑最大的争议是被压抑记忆的真实性问题。
弗洛伊德在诊治歇斯底里症患者过程中发现,歇斯底里大都是由创伤性经验引起的,而这种记忆往往被患者所遗忘。由此弗洛伊德认为,由于这类经验是创伤性的,因此它受到压抑——也就是说,由于想到它就会引起焦虑,因而它被主动地抑制于潜意识之中。所以歇斯底里症的原因正是因为这类经验无法得到充分的表达,因而只能以躯体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
很多学者并不接受这一观点,因而对压抑记忆是否真实存在的验证性研究持续存在,其中Esterson和Elizabeth Loftus的研究使弗洛伊德的观点受到强有力的挑战。Esterson(2002a,2002b)在两篇评论中指出,弗洛伊德的所谓被压抑的记忆是建立在其对患者症状的分析性解释的基础之上,他自己将推理出的病因告诉患者,并使患者相信这是患者自己的潜意识记忆。Elizabeth Loftus从她自己的研究出发,同时在综述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献之后总结出,尽管不是全部但大多数关于被压抑记忆的报告都是虚假的,虚构此类记忆可以满足个人的某种需要:即为自己混乱的经验和情绪提供一种逻辑上的解释(见赫根汉,2003)。
4 神经精神分析学对压抑的研究
根据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同弗洛伊德本身一样,精神分析中压抑的概念也存在很多争议。毫无疑问,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需要修正和澄清,而且很多人已经做了许多工作。然而,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关于弗洛伊德压抑的讨论大部分充满了神话色彩而不是严格的科学的争论(Boag,2007)。正因为如此,或许神经科学的研究可以为弗洛伊德压抑提供更加科学的解释。
4.1 记忆与压抑
因为记忆与压抑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将首先介绍关于记忆与压抑关系的相关研究。
目前普遍认为我们的脑中存在两个记忆系统:外显记忆(explicit memory)和内隐记忆(declarative memory),二者有不同的功能。外显记忆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有意识记忆,或者是陈述性记忆。这是由Squire及Schacter首先提出的。它是对与人物、地点、物体、事实以及事件等的有意识的回忆。其主要负责的脑区是内侧颞叶和海马。内隐记忆也被称为无意识记忆,或者是程序性记忆(procedural memory)。它构成习惯、敏感化、经典条件反射、感知与运动技能,比如骑自行车或者打网球等的基础(Milner,Squire,& Kandel,1998; Kandel,2007,2009)。目前对内隐记忆的了解还很少,目前已知的是内隐记忆涉及许多脑区包括:大脑右半球的后侧联合区(posterior association cortical areas),小脑,纹状体,杏仁核,这些脑区大多与情绪加工有关(见Mancia,2006)。Milner报道的H.M.的案例,第一次用实验证实了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的分离(Milner,Corkin,& Teuber,1968)。
目前,关于压抑的神经机制的主要研究范式是想/不想(think/no- think)任务,通过观察被试在做“不想”任务时大脑的活动来推断压抑的神经基础。
Anderson等人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考察了自主记忆抑制的神经基础。研究人员发现,被试在执行“不想”任务时背外侧前额区(DLPFC)、腹外侧前额区(VLPFC)和前扣带回(ACC)活动增强而海马活动显著下降,我们知道前额叶皮层涉及反应抑制,海马对于记忆的提取至关重要。这表明了主动的抑制不顾或干扰回忆——额叶的网状系统的参与会阻碍海马的活动,以至于记忆无法提取而导致遗忘(Anderson et al.,2004)。
最近在雷根斯堡大学Hanslmayr及其同事使用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记录被试在做想/不想任务时的脑电活动,实验时,被试首先会得到一个提示,提示被试“想”还是“不想”。研究者发现:在“不想”线索出现之前的300ms左右会在右侧额叶诱发一个正电位(P300),表明预先的加工过程,在线索呈现时也会出现一个正电位,强度比第一个稍强,结果表明了调解有意识压抑记忆的预期机制的存在(Hanslmayr,Leipold,Pastotter,& Bauml,2009)。
然而也有学者对上述实验范式提出了批评,有学者认为这种实验研究中的实验材料是中性词汇,而不是创伤性的或引起焦虑的刺激。(Rofé,2008)
4.2 梦的遗忘与压抑
弗洛伊德(1911)认为,梦的遗忘是有倾向性的,服务于抵抗的目的。梦的遗忘在很大程度上是抵抗的产物。
Thomas和Michael(2007)的研究为弗洛伊德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他们的研究中,研究者让25名被试记下自己的梦然后分别对自己的和他人的梦的内容进行自由联想。一周之后,对他们对自己梦的内容的记忆情况进行测试。测试之后让他们对记住的内容和忘记的内容进行自由联想。同时记录被试的皮肤电(SCR)和觉知到的不愉快感。结果表明,与记住的梦的内容相比,对那些忘记的内容进行自由联想时被试的皮肤电增加更为频繁,更多报告不愉快感。研究人员认为这一发现与弗洛伊德关于梦的遗忘的假设是一致的。
4.3 心理病理现象与压抑
4.3.1 疾病觉缺失症
神经精神分析的创始人Mark Solms 2004年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行为神经学家Ramachandran在1994年对“疾病觉缺失症”(anosognosic)进行的研究。该症患者的右侧大脑顶叶区域受到损伤,他们不知道自己有明显的身体残障,例如肢体瘫痪等。在研究者向一位患者的左耳灌入冷水来刺激其右大脑半球后,Ramachandran发现,患者突然说自己左臂是瘫痪的,而且从八天前中风后就一直瘫痪到现在。这表明,虽然这段时间,她一直意识清醒的否认自己有任何问题,但是她确实能够知道自己有肢体残障。而且还在过去八天中无意识地记录了这个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当刺激效应消退之后,这位妇女不仅重新相信她的手臂是正常的,而且忘记了她承认手臂瘫痪的这段访问,却又记得访问过程中的其它所有的细节。Ramachandran(1995)得出结论:“这些观察结果的重要理论启示在于,记忆的确可以选择性地受到压抑……这位病人让我首次相信,构成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基础的压抑现象确实存在。”
4.3.2 分离性身份障碍
分离性身份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DID)以往被称为多重人格障碍(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MPD),其特点是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身份或人格状态反复控制患者的行为,每一种有自己相对持久的感知、联系以及思考环境和自身的方式。
19世纪末,对创伤、分离以及心理创伤的躯体症状的研究已经非常普遍。弗洛伊德在对他女性的“歇斯底里”病人的治疗中开始广泛使用分离理论(赵冬梅,申荷永,2008)。目前学界对分离与压抑的关系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分离与压抑是有区别的,有学者认为对体验(feeling)的压抑是分离产生的原因,并认为分离是一种新的压抑(Mann,2008)。分离的极端形式便是分离性身份障碍。Pearson(1997)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介绍到,目前对分离性身份障碍的原因尚未确定,但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与早年的创伤经历有关。儿童受到信任的看护者(父母或监护人)的伤害,因为儿童不能与侵害者脱离关系——还需要侵害者的保护,便将伤害的记忆压抑到潜意识,随后这种压抑的记忆便形成了一个分离的人格(Varcarolis,Carson,Shoemaker,2005)。而且在临床研究中发现,大多数分离性身份障碍患者都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标准(Armstrong & Loewenstein,1990)。而且最近的研究发现DID患者的海马和杏仁核体积要比正常人小(Vermetten,Schmahl,Lindner,Loewenstein,& Bremner,2006)。
新西兰格罗宁根大学的Reinders及其同事记录了11名DID患者主观反映(情绪,例如恐惧;感觉运动,例如,烦躁)、心脏血管反应(心率,血压和心率变异性)和脑激活模式。患者在两种精神状态下分别向他们宣读其精神创伤和非精神创伤的自传事件。当在中性的精神状态下,患者对其创伤性经历的反应与中性记忆的反应相同,并宣称想不起来。当在创伤人格的状态下,他们对创伤性记忆有明显的主观反应和心脏血管反应,并且大脑的激活模式有变化,他们说想起了该事件。这似乎表明在一个大脑中确实可以有不同的身份(Reinders et al.,2006)。
前文已经提到,右脑在情绪加工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神经科学的研究还发现,负性的情绪经验会激活大脑右半球,但过度的负性情绪可能会妨碍大脑右半球的加工(Gadea,Gómez,Gonzáilez- Bono,Espert,& Salvador,2005)。在此基础上,神经科学家提出了大脑对创伤事件压抑的方式:当遭遇创伤性事件时,负责注意和痛苦加工(pain processing)的右脑将注意从内部消极的情绪状态转移开,进而产生了分离(dissociation)——将与痛苦情绪有关的负性经验排除于意识之外(Schore,2009)。
4.4 关于压抑的其他实验研究
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对压抑机制进行了研究,Berlin和Koch(2009)提出在观看两可图形时,我们会产生花瓶—面孔错觉(face- vase illusion),当我们将图片看成一个花瓶时,我们对人脸的知觉便被压抑了,反之亦然。另外,他们认为双眼竞争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压抑的过程。
Qiu等人(2009)对花瓶—面孔错觉进行了实验研究,在呈现图片之前先给被试呈现一个线索(面孔或花瓶),使线索成为随后呈现的两可图片的目标刺激。同时用ERP记录被试的脑电活动。结果显示,在两可图形呈现后的前100ms出现了负电位,这与对两可图形的早期加工中的目标刺激的识别(面孔还是花瓶)有关,在320ms时会有一个反转的负电位,与无意识的知觉反转相关。(从面孔到花瓶或从花瓶到面孔)。该研究也许可以证明压抑的神经基础的存在,但要找到与压抑相关的具体脑区还需进一步研究。
有研究人员在一项研究中测量了六名运动障碍患者的对刺激的觉知时间与压抑的关系,他们发现压抑的被试对刺激的觉知需要更长的时间。证明了神经生理学的时间因素(neurophysiological time factor)可能是压抑发展的必要条件(Shevrin,Ghannam,& Libet,2002)。
5 总结与展望
詹姆斯(1907)在其《心理学原理》一书中曾提到:特定数量的脑生理学必须作为心理学研究的前提,或者说它就包含在心理学的研究之中。这也许就是神经精神分析学的作用之一,即证明精神分析理论的科学性,解决争议。从上述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神经科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压抑进行了研究,例如关于记忆与压抑的研究表明了有意识压抑相关神经基础的存在,关于梦和生理病理现象的研究似乎可以证明,作为无意识过程的压抑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其与有意识压抑的神经基础是不同的。另外关于DID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对创伤性记忆的压抑不仅是存在的而且这一过程主要有大脑右半球负责,这对解决压抑记忆真实性这一争议是有极大帮助的。然而神经精神分析的作用不仅仅是为精神分析提供理论依据,对心理治疗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例如关于DID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其形成和发展的神经机制而且有助于帮助我们找到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方法,从而减少其发病人群的数量。
然而,我们不能否认,神经精神分析的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首先,对于压抑的神经机制还没有达成一致共识,很多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其次,身心关系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无论是“身心分离”还是“身先而心后”抑或“心在身之前”的观点都曾在历史上存在很长一段时期。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同“身心一体”这一观点,正如梁漱溟所提出的:“身心是矛盾统一的两面,身在心中,心透过身而显发作用,一般莫不如是。”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对神经精神分析的研究做出因果关系的解释时也需谨慎,比如,虽然通过脑成像技术证明DID患者的海马和杏仁核体积比正常人小,但我们却无法得知是DID影响了海马的杏仁核的体积还是海马和杏仁核体积小的个体更容易患DID。因此,仅仅通过脑成像技术还无法明确压抑与相关神经生理的改变孰为因果,要解决这一问题,还需更先进的技术和更成熟的实验范式。其三,由于神经科学家对有百年历史的精神分析的理解还不够深入,这些研究还都停留在简单的结合层面,缺乏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尽管存在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精神分析的发展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新颖的角度,神经科学研究的新进展为精神分析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随着神经科学家对精神分析理解的深入并以其作为指导,一定会启发神经科学的研究,并实现神经科学和精神分析学的共同突破,使我们对身心关系这一古老命题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收稿日期:2010-0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