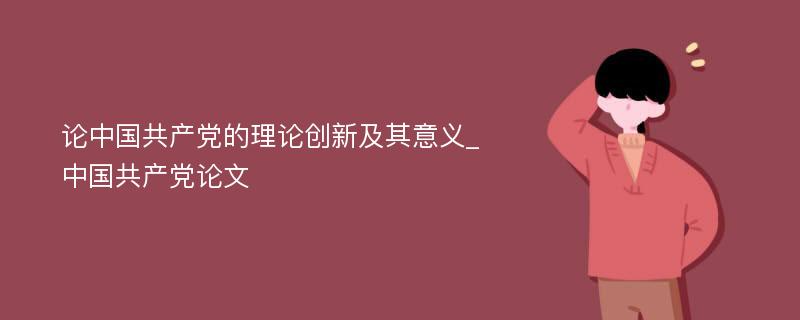
试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试论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1287 (2000)05—0001—04
对历史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描述事件、讲述故事这一初级阶段,应该更进一步对事件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解释,找出其发生与演变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理论的催化力。因为在中国共产党近80年的革命实践中,事件往往只是理论创新的导火索。中国革命和建设往往演绎着“事件——理论创新——阶段性胜利或成就”这么一个发展的逻辑。也就是说,突发性事件引发理论创新,而每一次理论创新的过程都犹如闪电,为中国革命带来万钧雷霆;都犹如凤凰涅槃,为古老的中华文明带来新的生命活力!因此,探讨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揭示其对未来中国命运走向的历史价值……应该成为新一代党史研究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一 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决策与开拓的统一
事件是学习历史的起点。过去,我们总是以事件为中心,由事件展开过程,在过程中把握人物。于是乎,历史就变成了时间、地点、人物和过程的集合体,变成了历史人物的行为描述史和行为激励史。历史本身的内在规律反而被排除在历史的视野之外,不能不说这是“历史的”遗憾。
历史的胜利、革命的成功,无数的实践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就在于其不断地理论创新。但重大的历史关头,重大的历史事件,只是这种理论创新的前奏,而不是理论创新本身。比如: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只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创新的前提或必要条件,而并不等于这个理论的形成;同样,西安事变之于“抗日游击战”、“论持久战”的理论;1976年3月“天安门事件”和10 月粉碎“四人帮”之于改革开放理论的形成,都一再证明了这样的历史结论:事件并不等于理论创新,但理论创新绝对不能离开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
那么,透过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大事件同其理论创新之间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关系,我们如何把握其内在的本质呢?
1.事件的确认 并不是所有的重大事件背后都预示着将有理论创新的跟进,只有在那些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事件之后,才会产生导致新的前途和光明的理论。那么,何谓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事件呢?这要看该事件本身固有的性质是否包括着肯定和否定两种因素。即这一事件首先应该是对于过去的长期积累,积而待发;其次,它还应该面向未来,为未来拓展方向,指出道路。如西安事变,它既是当时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总爆发,又暗含着新的历史转机。由此可见,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事件也可以叫做关节点或临界点。它既是旧的量变的结束,也是新的量变的开始。这样的历史事件,不仅在行动上打破了旧的格局、旧的秩序和旧的模式,而且从人的心理状态上、从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建设上,都给人和社会提出了为创造一种新的范式而理性求索的紧迫感。因为旧的社会生存模式的破坏将必然伴生社会心理结构、社会意识形态的无序和失衡,从而向往、呼唤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生,以便尽快地建设新的社会生存基础。所以,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事件往往成为新的理论的催化剂。
2.理论创新的理解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闹革命,翻身求解放是没有什么经验可以直接地吸取或借鉴的。事实证明:凡是直接照搬别人经验、理论的革命和建设活动都遭到了失败,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破坏。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从血泊中站起来,从废墟中走出来,从失误中醒悟过来,从弱小到强大起来,完全是依靠自己的理论创新。所以,理论创新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应该成为特别引人注目的专有名词,就其实质而言,它是历史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决策与开拓前进的辨证统一。科学决策过程,其实就是优化选择的过程。把这一过程放回到历史情景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总是选择走自己的路(即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外国革命经验和本国具体的国情之间;精英政治和人民大众之间等等方面进行选择),以便为理论创新进一步寻找理论来源、群众基础和实验空间。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以上关系的处理是辩证的。正是这种对立统一的辩证选择方式,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思维温床。这一温床犹如为喷薄欲出的红日铺垫了万里霞光。太阳每天都是新的。通过辩证选择的理论也就具有开拓性: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这些关系时虽然是辩证的,但似有所偏重。言下之意就是,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外国经验和本国国情、精英政治和人民大众等等)的关系时,偏向了后者。其实,这是不全面的。纵观每一次的理论创新所取得的成就既不是完全照搬前者,也没有抄袭后者。完全照搬和抄袭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是外国科学家、专家,还是中国先哲们都不可能为中国革命设计好现成的方案。因此,这种辩证的选择就是把以上诸种关系内在地结合起来,融合出能够指导中国实际斗争和建设的崭新理论。由此说,这种理论只要出现就必须带有革命性、开拓性。开拓是新理论神圣的使命。
3.开拓的境界 每一次理论创新,每一次开拓无疑都会将中国革命和建设带入新的境界。但是,我们要科学地认识和把握这一新的境界,要看到这一新的境界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是破与立的统一;是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也就是说,我们既要充分认识这种境界在当时社会情况中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所能完成的对旧思想质的跨越,也要充分看到这种境界的社会局限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理解理论创新的开拓性,而不至于把这种开拓性理解成直线前进的单向度成果。因此,理论创新的境界是一个高度,但同时它又是一个起点,一个更新的理论创新的起点。尽管历史的风风雨雨可能会剥蚀其华丽的外貌,但理论创新所形成的精华也就是这种境界的实质,它作为绝对真理的一个成分,其颗颗是永恒的。如“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在夺取政权的年代里是如此,在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依然是值得认真遵循的思路。在中国,农业问题没有搞好,农村的小康富裕问题没有解决,就难以可持续发展。因此,面对工业化、现代化挑战的中国,如何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解决农村问题必然是一个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二 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性、人民性和追求真理的执著性的统一
从时间上来把握历史事件,就可以看到事件是短促的,每一次历史事件的爆发都犹如一闪即逝的火光;但随之而来的理论创新则是一个艰苦的充满荆棘的过程。经典作家曾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摸着石头过河”等等词语来描述这种创新过程中认识的困难和行动的不易。但困难归困难,每当中国革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到了需要新的理论指明出路的时候,总会有新的理论顺应时势的需求,恰到好处地适时地产生出来,使革命的航船得以驶进胜利的航程。叶剑英曾说过: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断地提出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能力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的政党;是一个需要在创造中获取新的生命,并有能力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政党。这也许为人们揭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如此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生存,并能永葆其美妙之青春的奥秘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但是,中国共产党近80年的革命实践中成功的理论创新过程本身却还是“历史之谜”。我们只有透过历史的烟尘,剥开历史现象,从事件深入到过程,在过程中去探寻这一“历史之谜”的谜底。
1.理论创新的缘起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不难看出理论创新是“逼”出来的。这种“逼”从时势方面看就是中国革命处于“山穷水复疑无路”的状况,迷失了前进的方向,有毁于一旦的危险;从策略上看就是旧理论已经“江郎才尽”,无力回天,而又没有别人现成的经验可供“拿来”就用。由此可见,这种“逼”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可以说是一种生存考验。其实,正是这种压力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勇气、意志和智慧。创造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不公正的待遇、受限制、受惩罚、甚至是严重的压迫等等都是刺激个人或集团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何况,中国共产党是由最优秀的人们所组成的团体,在危机时刻所激发的整体创造性思维能力之强大是难以估量的。但是,这种“逼”并不意味着割断历史。也就是说,它不是源自于革命进程之外“神秘”的压力,而是本身隐含着新理论的某些因素或成分的压力。尽管这些因素或成分是那么地弱小,那么地不起眼,但在富有创造力的人们视野里它恰恰是一个又一个闪光点。
2.理论创新的时空持续性 面对着生存的压力,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没有止步不前。路没有了还是要往前“闯”。“闯”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摸索过程。正确的,保留起来,坚持下去,继续前进;错误的,就退回来,总结经验,再往前闯。新时期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不就是在将近20年的改革开放的风雨中闯出来的吗?再往前追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同样也经历了几十年的战火考验!所以,设想某种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一蹴而就,像自然科学理论那样一步到位,那是不尊重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由此也可以进一步推论:新理论之所以“常新”,是因为它既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产生,同时又要受到一定时间和空间的制约,超时空的社科理论是不可能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因此,可以说特定的时空塑造了特定的理论,特定的理论解决特定时期的社会发展问题。
3.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是领袖智慧和人民群众创造性活动的相互作用在革命最危急关头,也就是说,在被“逼”的时候,最先站出来从事理论创新活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领袖是指一个集体,而不是指个人。它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是历史任务的发起者,是历史进程的影响者。所以最初的理论创新活动也可以说是抽象的方向性的。说它抽象是因为刚开始不可能作详细地论证、形象地建构和完善的装饰,这样它就成了人们难以理解,但却极富吸引力的新生理论。说它具有方向性是因为这种新生理论对人们来说虽然是陌生、难懂,但能够让人们感到好奇,感受到唯一的出路和光明的未来。譬如,遵义会议之于毛泽东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于邓小平理论等等都显示出了这一特点。新生的理论幼芽在由抽象向具体、由方向性向指导性的演进过程中,人民群众的拥护和选择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这种理论才有可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才有可能不断地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不断完善中走向成熟。反之,则只能成为人类思想史上一次美丽的火花。人民群众自觉的社会历史活动不断地为领袖提供新的理论框架增添着色彩,丰富着内容,有些甚至是丰富了实质性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整个理论创新过程就是领袖智慧和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劳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这种相互作用就是新的理论得以吐故纳新、新陈代谢健康成长、壮大的内在推动力。没有这种相互作用,新的理论就不可能通过自我发展而达到成熟。这种相互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最为关键的一环,也是启开理论创生之谜的钥匙。因此这种相互作用的机制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过程所独有的,其它任何党派都不可能产生,甚至无法模仿这种机制。
4.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是一个追求真理和检验真理的过程 新理论的创生并在实践中的初步运用不可能一帆风顺。它那弱小的生命随时都可能被来自各个方向的反对势力所扼杀。在这个时候,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执著性就显得十分重要。毛泽东曾经说过,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而共产党员就最讲认真。短短的一句话,再结合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革命实践,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执著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是“坚定不移”坚持真理、发展真理和检验真理。这种执著性造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理论与政党一起成长;理论成熟同革命胜利一齐到来!其实这种相辅相成的历史结果浸透了许多执著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血汗。在这里丝毫的犹豫、丝毫的动摇都意味着前功尽弃,都意味着背叛!试想1989年夏天,如果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不执著、不坚定,那将会出现多么令人可怕的后果!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同一切创造过程有着很大的区别。因为在这里,创新还包含着坚持,包含着磨练!在这种坚持和磨练中,真理就像燧石一样不断地被敲打,不断地被检验,最终走向成熟!
三 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历史价值
人们习惯对有价值的发明成果进行价值评估。有些科技项目,特别是高科技创新项目更是沽价待售。可是,从来没有人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作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价值评估。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成果的价值是无法度量的。无法度量是不是就不去度量?不去高扬它的价值呢?答案显然应该是否定的。我们应该穿透它的金钱价值,去积极地寻找它的历史价值,从而达到让历史告诉未来的目的。
1.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是创新过程的客观性和创造者的能动性的有机统一 从上文的论述中,证明了理论创新过程是客观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是什么人,并不是你想创造新的理论就能够创造出新的理论来。自我标榜只不过是为历史准备闹剧,而随意制造的理论只会给社会带来罪恶和灾难。如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的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人们,甚至把人民共和国也引向了崩溃的边缘。
由此看来,判断一个理论创新必须要根据社会发展的状况来进行。首先要找到发展过程中那空前的危机感、紧迫感;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然后再寻找理论创新的导火索——事件。只有这些必要条件都具备了,理论创新才有可能到来。当我们再一次受“逼”的时候,就不会措手不及,就不再会犹豫、徘徊走许多弯路,而会像高尔基笔下的海燕一样勇敢地迎接理论创新时代的暴风雨。因此,把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行为从被动应战变为主动挑战,应该是新时期每一位共产党员的历史责任。江泽民同志非常重视这种理论创造能力。他常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我们每一位党员都以创造为己任,都为理论创新增砖添瓦,那么我们党将会更加充满朝气,我们的国家也将会更加繁荣富强!
2.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对于21世纪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因为随着多极化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和一体化经济时代的来临;随着社会发展节奏的加快,中国共产党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问题,越来越多的压力。这些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步伐加快,否则就难以面对和难以解决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所以,必须对理论创新的方法论进行较为系统地研究,以便提高理论创新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创新过程是历史的,但我们研究它、总结它的目的是要面向未来,面向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只从自然环境、资源方面研讨可持续发展那是不够的。因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可持续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在这方面前苏联已经有了很好的前车之鉴。
3.理论创新的历史价值在于“新” “新”就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具有远大的前途和强大的生命力。相反,如果表面上“新”,而实际上不新那就会断送党和国家的前途。如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表面上看似新,其实质是在偷售社会民主主义的旧货,其恶果是导致前苏联的瓦解。所以,我们加强对理论创新的认识、研究,有助于人们,特别是广大党员炼就金睛火眼,识别哪些是真正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哪些是披着理论创新伪装的旧货;从而准确地选择它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这在世纪交替的转折关头弥漫着焦虑、忧患、盲从气氛的今天,应该是一种很好的清醒剂。
收稿日期:2000—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