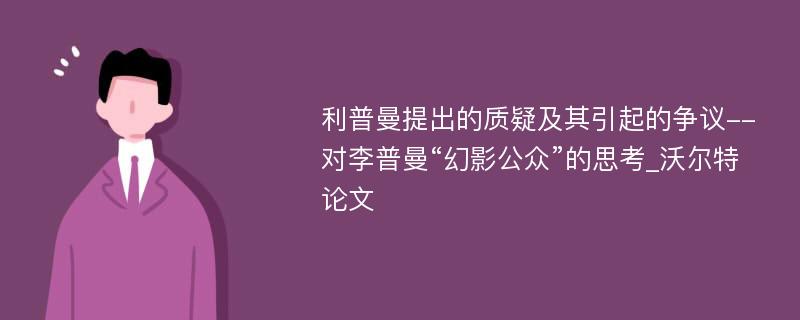
李普曼提出的质疑与其引发的争议——沃尔特#183;李普曼《幻影公众》引发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幻影论文,沃尔特论文,公众论文,李普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幻影公众》作为传播学的经典著作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总体而言,学者对于这本著作的解读分析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种是文本解读,对李普曼提出的对传统民主理论的质疑加以分析。大多数学者的分析集中在李普曼对公众非理性智慧的认定、李普曼指出的民主程序和民主制度中虚假的设计以及如何实现或者由谁带领而实现民主这几个方面。他们认为李普曼推翻了先人对理性公众的判断。李普曼把神圣智慧的公众当做一个幻影,因为公众处于事件的外围,他们应该归位让了解问题的“局内人”采取行动。李普曼对于选举方式的思考角度具有创新性却又有些悲观和极端,他对于如何实现民主的观点有精英主义的倾向。
第二种是关注该著作引起的后世影响。学者认为这部作品和《公众舆论》首次对传统民主理论提出质疑,注意到了在当时政治学领域都不曾注意到的新问题。学者对这部作品对后世影响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他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对于民主理论截然不同的看法上。他们认为李普曼的分析过于关注个体,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交往。杜威的观点则太过理想化,期望和现实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将李普曼和杜威之间的思想交流转换为一种“论战式”的学术话语,开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中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对李普曼的批评被广泛引用,他赞同杜威的思想。而且学者普遍认为,这部作品继承《公众舆论》对公众、舆论、民主三者及其关系的深刻批判分析,对后来的舆论思想甚或舆论观的变化也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种是从文本提供的研究方法出发,分析李普曼给我们带来的全新视角。学者肯定了李普曼运用批判挑战传统的思维,给读者提供了多元化思维的借鉴。另外李普曼的思考也闪烁着理性主义的光华,他不是冒昧的解决问题而是不断地提出问题进行连续的思考。此外,文本体现出哲学思辨,努力阐述人类与其外部生存世界的关系,李普曼深入的思考让理性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最后一种是借用李普曼的分析对当今时代的舆论环境、舆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等作出进一步思考。这些思考分析主要包括对当今媒体格局嬗变的解读,对当下网络舆论及其影响的分析,以及重新看待公众舆论的变化。
早在1911年,年仅22岁的李普曼就开始反思“民主的局限性”。当时还信奉社会主义的他就清醒地认识到选民为自己的生活忙碌奔波根本无暇他顾。这也可以证明他对民主弊端的反思很早便开始。1922年《公众舆论》出版,随后《幻影公众》也公布于世。这两部作品都是围绕“公众”这个核心主体,去揭露传统民主理论依赖的“公众神话”,并抨击依照这些理论塑造的民主而产生的弊端。李普曼对民主理论公众形象的主要分析包括公众无法保持清醒且对选举投票冷漠,不应对他们抱有幻想。教育无法实现培育优秀公民的理想。社会选出能够了解掌握信息的代理人,其他信息不对称的公众则是旁观者,他们是平衡专制的力量。公众舆论是力量储备,在危机时发起挑战。除了危机时刻,公众可以不作为。社会系统的变化很大,我们需要找准两个变量挑战他们的关系,价值观就是来自事物之间的对比,解决冲突找到双发的妥协方式去调解,权利义务的建立也是一种妥协方式,社会契约由此形成。公众辩论就是为了识别党派偏见者与私立维护者。而民主最为窘迫的是,一方面他们将遭遇失败,除非制定获得广泛认同的规则,而另一方面,他们似乎无法找到解决重大问题的方案,除非通过集权统治推行其制定的规则,而无视认同原则。[1]这些分析从实用主义而非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在不同程度上对传统民主理论及其塑造的公众形象提出了挑战。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后世的争论。詹姆斯·凯瑞(下文简称凯瑞)就并不推崇李普曼的思想,他还将约翰·杜威(下文简称杜威)和李普曼的观点形成了“论战式”的对话。
一、“前世之争”——李普曼提出的新质疑
在西方启蒙时代,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约翰·密尔顿(John Milton)等一批早期民主理论家认为应崇尚理性自由,“天赋人权”。在十八世纪中期,受到启蒙主义的影响,这些传统的民主理论思想家认为公众可以尽情自由地发表言论,发现或发展真理。而公众是由个体公民组成的有机统一体,拥有超越个体的共同意志。他们是有理智且有智慧的,神圣而至高无上,在了解事实后可以对公共事务做出明智的决断。一百年以后,西方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李普曼对这些启蒙时代的理论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认为像卢梭这样的传统民主理论家所描绘的公众只不过是根植于错误哲学理论的一个“幻影”。他说公众只不过是“坐在剧院后排的聋哑观众”,[2]他们茫然无知,时间、经历和信息都极其有限,无法对公共事务理性解读并妥善处理。所以,除了在危机时刻,公众最好不作为,让信息掌握更充分的“局内人”去采取行动。对于公众定义的本质区别是他们思想产生争论的根本原因,而他们思想上巨大的差异与他们所处的完全不同的时代有着直接关系。
(一)时代环境的本质区别
十七世纪以来,西欧的手工工场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而封建专制制度严重地阻碍了资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发展,迫切希望能破除封建制度的枷锁。这一即将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在思想文化领域率先出现,也为其后真正革命的发生提供了思想保障。所以这一时期的思想家认为公众舆论[3]为资产阶级逐步发展壮大而产生的推动作用,催动当时民众推翻封建制度和等级特权的桎梏、为争取自由平等而努力的革命精神。所以,传统民主理论构建了李普曼所说的“公众神话”,提出的公众的意见可以实现公民的公共福祉,它具有法律和道德的功能,在不知不觉中以习惯的力量代替传统封建权威等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思想早已超出学理意义,而是为世人提供了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民主政治的理论武器。
但是李普曼生活的时代,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已经开始转移,西方社会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以后,迅速推进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普曼认为现实世界变得纷繁复杂,公众很难清醒认识这个外部世界。他们只能通过媒体报道和自己的想象完成这一认识过程。而且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让公众有了更精彩的生活,也让外部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人们很难进行简单的规则判断,建立统一的价值逻辑。因为公众的知识水平和时间精力有限,而且媒体报道也是对信息进行了精心地加工,所以公众不能完全了解外部世界,或者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不想去了解。公众产生的声音很难有理性可言,公众只是看到了“拟态环境”,产生的意见源于“刻板印象”,对民主建设毫无益处可言。李普曼的思想被后人评价为洋溢着浓浓的悲观主义色彩,这兴许是中产阶级对引导公共事务产生的忧虑。
(二)经济技术力量
经济技术的发展也是这两种理论思想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传统民主理论思想家所在的启蒙时代,集会仍然可以看作是公共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当时的人口规模和城市规模都不大,思想家们仍然可以想象像罗马人的日常集会一样,公民聚集在一起处理某些事物,公众意见的形成切切实实是一个开放互动的过程。这样的民主决策比封建专制而成的决策的优越不言自明。这样的民主理论也给当时进步的资产阶级带去希望。
但是李普曼所处的复杂的工业时代,技术使一切变得便捷也使得一切变得复杂。随着人口城市规模的扩大,就像李普曼指出的一样,公众只有指望代理人参加集会,代替他们表达观点,这时信息不对称就出现了。而且处理的事务变得更加复杂而琐碎,公众不可能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也不可能建立一劳永逸的解决标准,也没有普世的道德标准能够平衡各个利益集团的需求,而更有可能的是在相对安逸的环境里,公众已经不再关心公共事务了。受众通过机械复制技术提供的媒介产品了解这个世界,他们不可能看完所有的信息了解这个世界的全貌,而重要的信息都是经过精心调配的,公众只是了解了自己以为了解的世界。如此一来,公众的舆论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它不过是被操控的激情,或者被煽动的工具。
(三)新闻传播领域的巨大变化
从传统民主理论的思想家所处的启蒙时代到李普曼所处的二十世纪工业飞速发展的时代,相隔一百年的时间里,新闻传播从启蒙时代冲破枷锁而发扬的新闻自由观进入社会责任观。启蒙运动时期正是一个观念变迁的时代,新兴的新闻事业逐步体现出了它强大的传播效果和舆论功能。这个时期以英国为主的西方报业的繁荣发展是启蒙运动的保障,也是它的成果。传统民主理论的思想家们看到了舆论惊人的力量,看到了处于混沌中的社会被启蒙开化。他们认为把公众的意见集合起来并不困难,而且他们的意见要比独裁统治者出于私利考虑的意见要理性智慧的多,最关键的是这些意见集合而成的舆论在真正推动社会的发展,民主的形成。
李普曼所处的二十世纪,现有的审查与保密制度成为了公众与真实事件之间的屏障。不论官方是否了解真实情况,他们都只提供某些最有可能稳定人心的事实,以营造有利于自己目的的舆论去安排或制造虚拟环境。李普曼是新闻记者,一生中曾直接或间接地为十二位总统出谋划策。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威尔逊政府的战时新闻管制政策之后,李普曼的民主舆论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深知新闻无法成为公众获取客观真实信息的保障,而这些信息决定了他们的判断和立场,因而这些得不到真正信息的公众不能治理国家或者提供政策建议。
两个时期的舆论导向也明显不同。启蒙时代正是自由主义繁盛的时代,法国又是新闻自由的发源地之一,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呐喊声中,舆论的制高点已经被民众所掌控,他们不畏发声并吸收进步的声音。舆论是由公众制造并被公众迫切需要的,舆论的主体当然是公众。不同于启蒙时期由公众主导舆论,李普曼所在的二十世纪初的西方社会,政府和与他们利益相通的资本家更迫切需要合适的舆论环境也牢牢地掌控着舆论。我们大胆的设想他们便是启蒙时代的革命者,深刻意识到了舆论的重要。所以当资产阶级政权稳固以后,他们也保证了舆论控制权的稳固。资本家需某种对其企业有利的舆论氛围,这是他们的公关目标,以获得市场,获取利润。而舆论与政府的合法性息息相关,他们需要舆论塑造形象,需要舆论赢得选民,需要舆论为他们遮掩而不是对他们进行揭露。对于公众而言,他们已经很难聚合有效统一的意见,而且他们默认或根本没有意识到现有规则存在的合理,其实他们已经被操控。
二、“后世之争”——李普曼引发的新争论
在李普曼的《幻影公众》问世后,杜威也于1925年发表作品《经验和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并继续于1927年出版《公共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1929年出版《追求确定性》(The Question for Certainty)。杜威也从这个时代独特的工业化标志出发,他也看到了这个时代越来越不容忽视的经济力量,但他却不像李普曼那样,认为民主的问题源于“幻影的公众”,而认为问题根源还在政府,截取和操控了民意。这场“隔空”的交锋论战,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詹姆斯·凯瑞的介入而成为了一场“论战式”的学术对话。1982年,凯瑞在他的论文《大众传媒:批判的观点》(Mass Media:The Critical View)中用争论和冲突来形容这场对话,将杜威和李普曼的关系描述为对抗性的。但是凯瑞明显支持杜威的观点,他在1987年发表的论文《媒体与公众》(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Discourse)中认为,李普曼将“公众置于政治之外,将政治置于公共生活之外”。
凯瑞的这种“论战式”话语的建构简化了李普曼的观点,也夸大了李普曼和杜威的分歧。其实杜威和李普曼的出发点都是现在的民主不能有效运作。李普曼主张通过精英代理,公众必要时的参与来推动民主的有效运作;而杜威则认为应该让公众更多的参与,比现在还要民主才能拯救现在的民主。他们二人产生这样不同的认识,根本还是在对“公众”的认识上存在分歧。李普曼否定了“公众神话”,也反驳了教育能帮助培育公众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和素质,他觉得公众关心很多事情,并不把参与公共事务放在多么重要的位置,他们有很多和利益相关的事情更需要操心。民主的结果是公众的生活福祉提高,他们就会满足,不需要有所作为。而杜威则认为民主是让最大多数的人福利最大化,这个过程需要每个人的参与,以实现个人目的和群体目的的和谐统一。所以公众当然关心政治,关心公共事务,这关系他们最根本的利益。
(一)个体与整体
正如上文分析的一样,李普曼与杜威理解的“公众”并不相同。杜威认为组织起来的个体是构成公众的条件之一,公众能否稳定有效地决断或参与是由公众是否具有管理能力决定的。也就是说,杜威并不认同李普曼声称的公众冷漠、掌握少的信息,素质能力有限等设定,他把公众看成了一个整体,整体一起参与和行动。杜威认为社会中的个体相互依赖,他们共同参与追求民主生活。杜威把公众当做整体看待,公众集体行动促进民主的发展,而且整体的发声促成舆论产生,并不需要依赖媒介,其内部的协调也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对如何做出决策进行参考。
李普曼认为工业社会极其复杂且难以理解和管理。公众自身的局限不可能使其有能力参与解决公共事务。而且在这个复杂的现实中“我们无法想象,世间的万事万物彼此都能和谐相处,没有矛盾”。[4]因为我们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需求设定标准,我们的价值观念来自于对宇宙万物的对比。所以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利益标准,人们在不断的妥协中可以形成规则,但是没有“永恒”的视角,倘若真要对整个宇宙进行衡量的话,只能像上帝一样置身于宇宙之外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李普曼把公众当做每个个体去看待,他不认为能有什么方式能让这些个体达到高度的思想、目标、原则统一。那么,一个个体面对的外部世界何其广阔复杂,他无法正确的做出判断,他可能就此只关心自己的事情,这些都是可能的情况。
(二)视角的切换
李普曼和杜威产生这样不同的思想也与他们不同的研究视角有关。李普曼作为著名的专栏作家和记者,活跃于政府高层,他是从国家社会这样宏大的视角出发看待问题。因此他更关心民主建立的结果,他把民主看成一种制度,一种政体,要能帮助实现国家的壮大和社会的进步。所以,他怀疑公众有这样的专业素质和远见,帮助政体的完善。而且李普曼看得到政府对新闻的控制,他从根本上怀疑公众能够通过新闻形成舆论,进而指导国家治理的可能性。所以,在这样的境地下,李普曼能想到的最好的制度建构,能带来最大的福利的政体,便是精英治理。
但是,杜威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他关注整个社会态势,更喜欢以美国的社区进行样本观察,他的视角是一种从民众出发的微观草根视角。他更愿意把民主看成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需要每个人的参与以使其变得更好。媒介扮演了信息传递的中介,并确实对公众的集体意志有所回应,再刺激公众的参与。杜威看好民主的未来,他并不觉得信息是重点,而是在乎这个互动交互的过程。民主是不断寻求利益最大化,不断妥协的过程,杜威认为这就是需要每个人的参与,不断的实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融合,这样的和谐互动才能使民主变得更好。
(三)理想与现实
李普曼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新闻记者,他对现实有非常清楚和深刻的认识。现代工业社会不断地生产、流动、传播各种各样的信息,而分析、利用这些信息不是普通公众能够胜任的。他在新闻行业的从业经验告诉他,无知的公众通过新闻媒介获取信息而形成的想法是扭曲的,他们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笔者认为新闻记者总是容易在不断挖掘真相的过程中陷入悲愤情绪中,长久积累便容易形成悲观主义情结。他认为在现代社会里,公众没有办法获得真相。便开始否定现有的民主,认为只有通过精英治理,也就是掌握信息的“局内人”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但是杜威是一个学者,据洛克菲勒的研究,出生在佛蒙特的杜威少年时感受过精神上不统一的折磨,后来他一直试图在哲学理论上寻求解决办法。杜威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而且还有广为流传的教育思想启迪后人。杜威观念的出发点是权力的来源应该来自于公众,他们应该是被治理的对象,他们需要参与建设发言。如果治理的源头得不到有效保证怎么能保证结果?他的逻辑是从理论出发,有着辩证的思维和惠特曼的民主思想。而且杜威认为公众的素质和能力可以通过教育得以提高。
李普曼和杜威的思想也都受到了后世的批评。学者认为李普曼的观点太过尖锐,把真理和意见过分的对立,公众会慢慢成熟起来,不应该用这样苛刻的目光去分析他们。而杜威仿佛太过理想浪漫,建立一种知识策略就能使公众终结困惑的想法有些理想化,而且公众集合成整体的困难也被低估了。
总体而言,李普曼的《幻影公众》继承了《公众舆论》,对公众、舆论、民主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和梳理。他对启蒙时期思想家提出的传统理论提出了批判和质疑,认为公众只不过进入了民主的程序,他们冷漠无知而又缺乏信息,不能起到民主自治的真正作用。李普曼对传统理论提出这样的质疑,最根本的原因是时代背景发生了根本改变,他作为记者时刻关注社会和现实,发现了当时民主困境的原因在于过分关注政府的起源而非施政的过程和结果。他进一步分析,将这一问题归根于无法清醒且冷漠的公众。而新闻传播领域内的嬗变也刺激了李普曼舆论思想的变化,认为舆论是被操控的。他将这些密切相关的因素进行运算,得出了他全新的民主理论构想。
但李普曼提出的质疑也引发了新的质疑。杜威、凯瑞等思想家认为,让精英治理背离了民主的初衷,他们不认为公众如李普曼所认定的那样,公众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有效地形成舆论,参与到民主生活中,在不断的互动中形成有效的民主。公众可以通过教育提高自身的能力素质。
本文对前人的思想进行分析比较,意图看清这些争论的实质,找到争议双方真正合理的部分。不同的环境背景,人们会生发不同的认知,进而产生不同的思想理论,找到理论与现实的对应点,才能更好的启发现世,这些思想理论的意义也更能被彰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