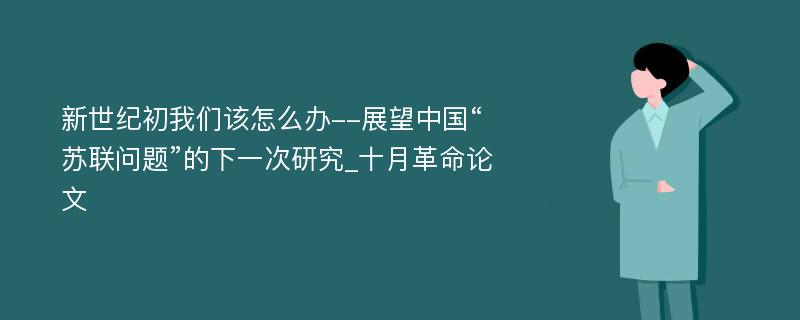
新世纪初我们做些什么——展望我国下一步的“苏联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新世纪论文,下一步论文,做些什么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苏联问题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具体地说,我们为中国的成功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系。但是必须看到这一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首先,我们有时囿于陈旧的观念,对大胆地开拓创新不免缩手缩脚,前瞻后顾,畏首畏尾;另有一些人出于种种原因,摇摆幅度很大,客观上造成了研究队伍的某些混乱。其次,由于人力物力的原因,我们对发掘已经到手的档案资料力度,仍嫌不足。
总之,对照前苏联社会主义失败提供的惨痛教训,我们的研究现状,离邓小平理论和党中央创造性社会实践已经达到的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在此新世纪新时期来临之际,很有必要就已经出版的论著,讨论一下我们的薄弱环节和所面临的紧迫的研究课题。本文作者认为,这些课题的解决,可能有助于我国制订21世纪的发展方略。
我们究竟有哪些问题急待于深入下去呢?
一 必须扎扎实实地研究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国情和历史
迄今为止,我们研究苏联问题,特别是苏联模式问题,都是从十月革命,即1917年开始的,使人读来总是不免有些“浮悬”、“飘荡”之感。这是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影响的结果。《教程》把联共(布)作为叙述的主线,本无可厚非, 但是它把俄国社会1917 年前和1917年内的大变革,也仅仅归为联共(布)一党奋斗的结果,就必然把十月革命描绘成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忽略或者抹煞了产生十月革命的诸多历史“合力”因素。这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起码常识的,违背我们大家都熟知的恩格斯著名的“合力论”原则的。恩格斯是怎么说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697页。)
这里仅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第一,如果没有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创造的历史机遇,即列宁所说“目前在世界各交战国中,俄国是最自由的国家”(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105页。)这样一种历史机遇和社会环境,布尔什维克的崛起从何谈起呢?第二,如果没有其他党派,特别是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合作,布尔什维克怎么能够争取到农民(包括穿军装的农民)大多数的支持和拥护,因而顺利地夺得十月武装起义的胜利呢?第三,如果不是列宁反复地坚持与说服,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核心怎么会抢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抢先起义,因而避免走漏起义风声,避免反革命来得及聚集力量,使得临时政府落得个“瓮中捉鳖”的下场呢?换句话说,如果党中央多数派占了上风,历史将会怎样改写呢?
研究类似的“偶然”因素的渊源,要求我们做些什么?
首先,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俄国史,特别是俄国近代史,因为任何重要的和看似偶然的社会现象和实践,都必然包含着传统或反传统的巨大作用或反作用。其次,必须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俄国社会近代思潮和政党史。布尔什维克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也不是布尔什维克匹马单枪、孤军奋战得来的。
远的且不说了。仅从18世纪彼得大帝打开通向西方的窗口开始,俄国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派别就已风起云涌。可以说,俄罗斯步西欧的后尘,开始了社会转型的漫长进程。这期间,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地主—贵族自由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在不同的时期登上历史舞台,虽然角色不断地变换,但是他们的存在却一直延续到1917年。因此,不能否认各个阶级及其政党在推动俄国历史进程中的进步作用或者“合力作用”。例如,1824年底地主—贵族自由派发动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就起过社会进步催化剂作用。再比如,反映俄国农民利益的民粹派和民粹主义的长期存在以及它对沙皇专制制度构成的巨大威胁,还是我们研究领域的“空白”。在近代,争取召开立宪会议曾是俄国社会各种进步力量的奋斗旗帜,连布尔什维克也不例外,直到十月革命前夕,它也没有轻易放弃这面旗帜。十月革命后,立宪会议的流产,布尔什维克党如何吸收立宪会议的积极因素,也是值得重新研究的课题。
只有把上述历史因素清晰地理顺,才能科学地说明俄国社会为什么于1917年继二月革命之后又选择了十月革命。就是说,只有在充分搞清楚俄国社会诸阶级的利益组合及变化情况,我们才能真正地回答,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却使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动员口号:“面包、自由、和平!”和“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为什么起义夺权成功后,很快又出现了同全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相悖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为什么1921年不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为什么在列宁那里,新经济政策由“被迫退却”很快地又转变为苏俄通向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一切”(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第262页。)?
总之,深入研究苏联和苏联模式问题,一是要研究哲学—历史学的立场和方法论;二是要具体探讨俄国史的方方面面的有关问题。关于列宁主义,只是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论”)开始研究列宁学说的发展脉络,而不去研究列宁的早期和中期著作(例如,《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等),我们不但不能掌握列宁主义,而且会吃亏上当,陷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我们掘好的“陷阱”。还可以说:如果我们不研究俄国史,就解释不通苏联史。
二 怎样看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
关于列宁主义,邓小平的评价是:“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92页。)这里,邓小平明确地把列宁主义“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在俄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如果把这些真知灼见放到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去,肯定会被斯大林定性为“贬低”列宁主义。
斯大林严厉地批驳了持有类似见解的人。他的理由是:“列宁主义是根源于整个国际发展过程的国际现象,而不仅仅是俄国的现象。”他还斩钉截铁地说:“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注:《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3、64~65页。当时首先遭到批驳的是季诺维也夫, 因为季认为,“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环境的特殊条件下的应用”,另可参阅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其实,季诺维也夫并没有反对斯大林,他的书开宗明义就完整地重复着斯大林的观点(详见《列宁主义》第1~5页)。虽然如此,季诺维也夫也还是“在劫难逃”。)(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这里,斯大林强调的,一是“国际根源”;二是片面的“无产阶级专政”。俄国国情——产生列宁主义的基础和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保障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都不见了。看来,邓小平同斯大林的分歧,可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其实,这种分野也是必然的,合情合理的。
列宁又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俄国国情相结合的呢?他反复强调的是,俄国与一般的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98页。 列宁关于这一定义有多处论述,参见姜长斌:《苏联早期体制的形成》,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斯大林是很不喜欢列宁对旧俄国的这一科学概括的。在斯大林的著作中找不到对它的阐述,尽管斯大林一向声称他是列宁的“忠实学生”。1934年斯大林严厉批判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之后,苏联理论界对列宁的这一定义,就噤若寒蝉了(注:斯大林在20年代的著作引用过列宁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7页, 但是后来他似乎变得非常忌讳对沙皇俄国的科学批判了,当然,在批判恩格斯的《论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问世之后,苏联理论界也深受影响,详情参阅А.Л.西多罗夫《列宁论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载〔苏〕《论俄国帝国主义特点》(论文集),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对于我们来说,列宁的定义异常重要。说它是打开俄国之谜的钥匙,丝毫不为过分。它起码包含三层内容:第一,直至十月革命前,俄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国家,俄国革命的实质“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第二,沙皇俄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成分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它比一般资本主义的垄断性更强,更集中,特点更加鲜明;第三,俄国在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其对内滥用暴力,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传统,不是减弱了,而是大大强化了(注:参见《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161 页(摘自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年),列宁的同一观点在1905年撰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里有更加充分的展开,见上书,第527页起。至于列宁论及沙俄内政外交特点的著述,可以说是贯穿其全部学说的始终的。)。
那么,又如何看待一战爆发后,列宁把俄国革命定义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这一问题呢?这就需要我们联系一战的国际环境和俄国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加以具体的分析。简言之,十月革命的指导理论、领导阶级及其政党力量决定了这一革命毫无疑问地属于社会主义范畴,而且是人类破天荒首次成功的探索。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摆脱民主革命的社会内容。列宁后来对新经济政策路线的大力肯定和论述,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了(注: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详见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第一篇第一章:《探讨十月革命的社会内容是认识前苏联社会主义历程的“入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也可以说,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其早期思想的回归。
综上所述,十月革命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只能在这一意义上谈论十月革命的国际示范作用和伟大影响,绝对不能像斯大林那样“毫无根据”地、从“天上”去谈论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十月革命的启发下,找到了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取得了自救、自立、自强和自我发展的结果。例如,俄共领导人民夺取政权,走的是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中国革命走的却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斯大林曾经指手画脚,要求中共照搬苏俄模式,结果给我们造成了空前的损失。所幸的是,中共及时总结了教训,清算了斯大林派到中国来的“瞎指挥派”,才得以使革命“起死回生”。邓小平说得很深刻:“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页。)
三 苏联模式的哪些具体教训特别值得深入研究?
前面我们谈了苏俄建设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新经济政策的思路——理论渊源和实践的巨大意义。这一点在我国理论界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没有异议了。但是,我们对新经济政策之前的军事共产主义还研究得很不够,特别是,俄共为什么和怎样从取得十月革命胜利时,以《土地法令》(农民苏维埃)为象征的工农联盟转向剥夺农民、破坏工农联盟的“余粮征集制”(贫农委员会)的,亦即试图“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
由此出发,有如下一系列问题需要回答。
第一,“世界革命”思想的产生和它的深远后果问题。关于“世界革命”,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有一段完整的表述,即:“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是,在贵族地主的大量土地没有触动的情况下,在有1905年经验的基础上,俄国这个国家的农民性质能够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使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90页。)这里,列宁对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 亦即十月革命社会内容和突出特征的看法,显然没有变,同他早期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他对革命形势的估计明显地改变了。这种改变显然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同他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命运,同他对战争导致的社会危机的总体估计有关。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一估计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是无法用后来的事变加以证明的。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对当时的列宁有关普遍推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学说,是否符合西欧工人政党的实际?对此应该如何进行再评价?还有,与此相联系的更大的问题是,应该如何估计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国际共运左派同第二国际各主要政党的论战与分道扬镳?近年来,我国有的学者提出,社会主义也是多样的,而马克思主义有各种流派则是不争的客观事实。那么,从当时第二国际西欧各主要政党几乎都已参加了各自国家政权(议会或政府)这一事实看,他们在交战国中都采取了维护本国利益的立场(例如,投票赞成增加军费),是否有其合理性?须知,恩格斯晚年对社会民主党参加普选并进入政权,是持赞扬态度的。恩格斯在认为“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的同时,称赞利用普选权为无产阶级谋取利益的和平斗争方式是“最锐利武器中的一件武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0、600、601、603页;还可参阅宫达非等主编:《苏联剧变新探》第125、126页,那里有关于恩格斯思想较详细的介绍。)。
总之,20世纪十月革命迄今的历史证明,俄国革命没能成为列宁式的“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重点在西欧),但是却出乎列宁的意料,成了东方国家革命的“序幕”。对此,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回答?
第二,东方国家与农民问题。如果我们系统地研究列宁学说,就可以发现,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对俄国无产阶级都有极其精辟的分析。其中,最著名的论点是,同西方相比,俄国资产阶级要更软弱,而无产阶级就其组织性和战斗力来说,要更坚强。但是,不知为什么对俄国农民问题的分析,相对说来却要差一些。直至1917年之前,布尔什维克在农民中的组织和影响都一直大大逊色于社会革命党。据统计,当时拥有两万多名党员的布尔什维克,在农村只有4个农民支部494名农民党员,在1917 年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大发展时期, 在农村也只有203个农村支部和4122名党员。 不论十月革命之前还是之后(包括1918年),布尔什维克在农民苏维埃组织中都居极少数或少数地位(注:徐天新:《评左派社会革命党》, 载《苏联现代史论文集》, 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95~112页。)。 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列宁不可能不知道,马克思早在1881年就曾指出过,农民在俄国社会变革和革命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革命必须给予农民充分的经济和政治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8~269页:《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有必要指出的是,这封信只是马克思的最后定稿,此前,马克思还写过初稿、二稿、三稿,那里还有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思想。载上书,第430~452页。)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的建设实践,完全证明了马克思这一根本思想的科学性。它对东方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称得上是一项普遍原理。可是,从十月革命前到“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结束,俄共一直没有处理好同农民的关系。后来列宁找到了新经济政策。但是不久,斯大林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和高速工业化,重新走上了剥夺农民的道路,至今,严重后果还难以消除。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也在农民问题上走过很长的弯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非常重视纠偏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无庸讳言,农民和农业仍将是我们长期面临的中心课题之一。
问题是:为什么在农民国度里,绝大多数执政的共产党却在农民问题上犯有路线错误,而且是反反复复,屡改屡犯?原因究竟在哪里?
第三,关于“以我为中心”的政党价值取向问题。列宁在论及俄国革命将会揭开“世界革命的序幕”时并没有忘记特别指出:“俄国无产阶级十分荣幸的是,帝国主义战争在客观上必然引起的一系列革命由它来开始。但是我们绝对没有这样的想法:俄国无产阶级是各国工人中间最优秀的革命无产阶级。”(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 卷,第90页。)到了斯大林那里,问题就面目全非了。他的一些话令人难以理解,甚至毛骨悚然:
1926年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宣布说:“党所持的出发点是:苏联无产阶级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融合为一个共同的任务,即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各国无产者的任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利益完全融合为一个共同的利益,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国的胜利。”(注:《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5页。 )(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1927年,斯大林把上述观点发展到了极限:“谁决心不开秘密军事会议而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要知道,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注:《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47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但是,20世纪整个国际共运史经历的却是反面的教训:谁绝对地听从斯大林及其继任者们的“指挥”,谁就会导致革命的损失直至失败。
其实,剥开苏联这种“以我为中心”的“国际主义论”外衣,我们看到的只能是民族利己主义(实践上是既害己又害人)和扩张主义的内核。
问题是:这种“以我为中心”、“惟我正统”的观念,流毒极广,坑害着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马列主义者该怎样科学地总结这一沉痛教训,既从苏联的反面教训中彻底解脱出来,又能起到共产党人应该起的“引路人”的作用?
第四,关于“造神”运动问题。斯大林时期,最沉重的教训就是“造神运动”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给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造成了一系列难以容忍的灾害。
但是,在俄国社会主义史中,“造神论”和“造神运动”非自斯大林始。
早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以后,紧接着就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过一股强劲的思潮和“运动”,即“造神论”和“造神派”运动。以卢那察尔斯基为首的一派人(包括高尔基)对信奉东正教的俄国工农群众能否接受马克思主义丧失信心。他们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同宗教调和起来,创立一种“无神的”新宗教,或“劳动宗教”。他们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哲学就是“宗教哲学”,社会民主运动本身就是“新的伟大的宗教力量”,无产者应当成为“新宗教的代表”。列宁及时地看出了这一派别的危险性及其产生的“土壤”,并且给予了系统的分析和严厉批判。列宁为此专门写了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和论文《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他在《唯批》的《序言》中称“造神派”是在“跪着造反”(注:《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2卷,第13页。)。在论文《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中,对“造神”现象详加分析,认为像“造神论”这种东西,只有在仍然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俄国发生,而且是对历史的反动。列宁指出,反对对“神”和宗教的崇奉,“在西欧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他们自己的革命时代,或者说在自己冲击封建制度和中世纪制度的时代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完成了(或者着手完成)这个任务。无论在法国或德国都有资产阶级反宗教斗争的传统,这个斗争在社会主义运动以前很久就开始了(百科全书派、费尔巴哈)”。“在俄国,由于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这个任务几乎完全落到了工人阶级的肩上。”列宁提出:“无产阶级应当成为反对一切中世纪制度的斗争的思想领袖,这一斗争还包括反对腐朽的、官方的宗教,反对任何新宗教、重新建立或用另一种方式建立新宗教的尝试等等。”(注:《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2卷,第255~256页。)
列宁的真知灼见,预示着在俄国的土壤上还会产生某种“重新建立或用另一种方式建立新宗教的尝试”。(注:十月革命后,有人几番试图对列宁歌功颂德。根据回忆录记载,列宁的态度是这样的: 1918年9月列宁遇刺后养伤期间,报刊上出现了不少歌颂列宁的文章,列宁看后马上招来办公厅主任邦奇—布鲁也维奇说:“你看报上都写了些什么?不好意思去读。都是写我的……把我叫作天才,说我是个特殊人物。看,这里还有一篇莫名其妙的东西,竟然集体地希望、要求祝福我健康。哼,弄不好还会为我的健康去祈祷呢!真可怕!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一生都为在思想战线上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崇拜个别人而斗争,关于英雄问题也早就做出了决定。可是又突然出现了个人崇拜!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行的。我是和大家一样的人。我已经有最好的医生给我治病了。还要什么?!老百姓还得不到这样的护理和治疗,我们还来不及把一切都给他们办好。现在却把我这样突出起来,这真是可怕的事情。”1920年4 月召开俄共(布)九大期间,正逢列宁50岁诞辰,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加里宁等)在发言中开始祝贺列宁诞辰,历数列宁的丰功伟绩。列宁立即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十月革命后,列宁愤怒地拒绝对他歌功颂德或者祝贺50寿辰一类的活动。
但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就大不一样了。192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50寿辰。在他的默许下,中央领导人精心地策划了祝寿活动。当天的《真理报》整整8个版面都是祝寿文章, 肉麻地吹捧“伟大领袖”、“列宁的忠实学生”斯大林。不仅斯大林的亲信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把斯大林吹捧为“列宁第二”,连被斯大林打倒的反对派人物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也不得不违心地参加这一“大合唱”。斯大林又是如何对待这一切的呢?他竟然在《真理报》上公开地向“为他祝寿的一切组织和同志”表示深切的“布尔什维克的谢意”!(注: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5页。)先河一开,到了30年代,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注:苏共20大以后,我国对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出现了两种译法,即“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由此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解释,如,认为“个人迷信”要不得,“个人崇拜”还是要有一些的。其实,这是误解。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只同宗教迷信有关。)终于成了苏联社会制度的主轴,在血雨腥风的政治大清洗中,社会主义法制被破坏殆尽了!
在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和新出现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中,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造神”传统。而且,这一现象都在不同程度上危害过社会主义事业,甚至是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垮台的重要因素之一。把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和社会基础研究透彻,仍然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四 新经济政策的历史意义不容低估
遍查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的著述可知,他对苏联的体制模式始终是持严厉的批判态度的。当然,只有一处例外。那就是他对新经济政策的评价:“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1921年春,俄共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党内几乎是一致通过,因为当时是没有别的出路的。这种“一致”是在迫不得已、只能从军事共产主义路线实行“退却”的基础上达成的。因为,饱受长期战乱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之苦的苏俄经济,已是民生凋敝,破败不堪。城乡居民不仅食不果腹,连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如肥皂、蜡烛、煤油、火柴等等都成了稀世之物,而且缺医少药,瘟疫流行。经济危机开始转变为政治危机,工农联盟大有决裂的危险。1921年2~3月俄共(布)十大期间发生的喀琅施塔得暴乱,就是一个最明确的信号。暴乱参加者大多是穿着军装的农民。同时,乡村农民抗粮抗政的行为也在迅速蔓延。国内战争后,农民再也不能忍受“余粮征集制”了。他们的口号是:“要苏维埃,但是不要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
但是,接下来,当经济情况稍有好转时,党内分歧就出现了,而且愈演愈烈。论战集中在一点上,即如何理解新经济政策的“退却”问题,它是从社会主义原则立场上的退却,还是从空想急躁的冒险主义路线——军事共产主义的退却?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必须巩固和扩大新经济政策的战果,沿着新经济政策道路走下去,还是就此停步,收缩乃至停止这一政策?1922年,列宁是在什么意义上谈论“停止退却”的?
列宁继续发展着新经济政策这一思路。他在1922年3 月俄共(布)十一大上说:“我们还没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但我们有找到这种途径的唯一办法,这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就要结束或者已经结束。现在提出的是另一个目标,就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已经)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你比资本家占优势,因为你手中有国家政权,有多种经济手段,只是你不善于利用这些东西,观察事物要清醒一些,扔掉华而不实的东西,脱去华丽的共产主义外衣,老老实实地学着做些平凡的工作,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来谈论停止退却……”(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90~91页。 )这时列宁谈论的“停止退却”已经包含着从正面肯定新经济政策的思想了。此前不久(1922年2 月),列宁在给司法人民委员部下达的指示中说得很明确,即为了新经济政策的发展,必须建立起一整套苏维埃法制体系,他说:“做生意吧,发财吧!我们允许你这样做,但是我们将加倍严格地要求你做老实人,呈送真实的表报,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共产主义法律的条文,而且要认真对待它的精神,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这些就应当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方面的基本准则。”(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428页。)(着重号均为原文所有)到了1922年底1923年初,列宁写作(口授)《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时的思路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飞跃到“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的阶段。这时的列宁强调的是,共产党人要“学做文明商人”。他怀着焦虑、迫切的心情,急于把他对新经济政策的全部看法,告知全党和全国(注:《论合作社》于1923年5月26~ 27日公开发表,《论我国革命》于同年5月30日发表。)。
但是列宁的愿望没有实现。他的新思路没有变成俄共全党坚定不移的指导思想。他逝世不久,俄共“左”倾反对派就开始猛烈攻击斯大林任总书记的党中央核心,认为,新经济政策实质上是富农路线,该是停止的时候了。除了布哈林等少数人之外,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对“左”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左”派主要理论家)等人的反击,是软弱无力的。当时,斯大林的注意力集中在权力之争上,忙于拉一派打一派。事实早已证明,斯大林从内心里并不赞成新经济政策,他后来(1928年以后)实行的政策,比起“左”派有过之而无不及,“左”派只能望其项背而已。这里要提一下被大家忽略的一件事。1925年4月25日, 布哈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说:“应该对全体农民,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应当永远贫穷;现在我们应当采取的政策,是要能在我国消除贫穷的政策。”(注:《布哈林文选》上册,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68页。)这里, 布哈林不过是重复了列宁关于“做生意吧,发财吧”的思想,但是“左”派却揪住布哈林的“发财吧”不放,说布哈林是在公开号召走资本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其实,“左”派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整垮以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多数派。但是斯大林又是怎样“保护”当时多数派的理论骨干布哈林的呢?他在同年12月十四大上竟然玩了个“舍车保帅”的花招,说:“……当时他(按,指布哈林)脱口说出了‘发财吧’这句话……不是别人,正是我声明说,‘发财吧’这个口号不是我们的口号……大多数中央委员建议布哈林在报刊上作一个声明,承认‘发财吧’的口号是错误的……布哈林……这样做了。”(注:《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19~320页。 )斯大林在这里不仅同“左”若即若离地站到了一起,而且为日后打倒布哈林埋下了伏笔。果然,到了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做政治报告时,就一锤定音,斩钉截铁地宣布说:“‘发财吧’的口号实质上是号召恢复资本主义……”(注:《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7页。 )这实际上是为继续执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定性”,也是为斯大林自己的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定性”的问题。 果然, 在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做出了如下的结论:“战时(军事)共产主义是用冲击、用正面进攻来夺取城乡资本主义的堡垒的尝试。在这个进攻中,党向前跑得太远,有脱离自己根据地的危险。列宁这时主张稍许后退一点,暂时退到较接近于自己后方的地方去,由冲击堡垒转到较为长期地包围堡垒,待积蓄起力量后,重新开始进攻……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所采取的,正是这种暂时的退却。”(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3~284页。)
综上所述,我们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为什么当时的斯大林和联共能够不惜付出那么沉重的代价,“轻易地”斩断新经济政策?第二,为什么今天我们对清算斯大林—苏联模式仍然有相当的“保留”,总是纠缠在功与过的抽象“比例”上?这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究竟有什么益处?
我们不仅要研究新经济政策的正面经验,也要研究实行新经济政策时遇到的困难。具体可以列举如下:1.所谓的富农阶级问题;2.所谓的耐普曼资产阶级问题;3.失业问题;4.产生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5.产生农业商品率降低和解决的办法;6.关于工业化的目的与资金来源的争论;7.关于工业化内容、速度和质量的争论(注:参见拙作《苏联早期体制的形成》,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328页。)。
五 关于十月革命后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如果说,苏联存在的70余年中,经济体制方面确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可资研究的话,那么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它提供的主要是沉重的教训。即使是“教训”,也是不容忽视的宝贵财富。
十月革命前,列宁对革命后的政治体制想象得比较简单,认为,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新型的、“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国家就是了。但是革命后不久,列宁就发现,问题并不这么简单。1919年列宁就提出了反对苏维埃机关官僚主义的问题。到了1922年,官僚主义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严重了。同年年底,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尖锐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他指出:“……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在和平已经到来和免于饥荒的最低需要已经得到保证的现在,全部工作都应该集中到改善机关上。”“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1、373页。)列宁甚至愤怒地写过:“国家机关的一般情况:坏极了;低于资产阶级的文化水平。”(注:《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 第36卷,第610页。 )(黑体字在原文中均有着重号)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列宁在其“最后的”著作《论合作社》中指出:“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收过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这种机关,我们在五年来的斗争中还来不及也不可能来得及认真加以改造。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7页。)
当时造成上述严重局面的原因有三:一是许多机关沿用了沙俄的“旧货色”;二是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由于一切工作都要依靠行政命令,国家机关急速膨胀,人员臃肿,情况甚至比沙俄时期还要严重;(注:参见拙作《苏联早期体制的形成》,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 章《加速实行工业国有化及总局管理制的形成》。)第三,最为严重的是俄共党出现了“机关化”的倾向,原来设想的干部选举制或党外协商制,改为俄共各级组织局直接委任制。总之,列宁早先预想的民主制落空了。列宁对实行民主制期望极高,早在1916年就说过:“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含两个意思:(一)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二)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 28卷,第168页。)
众所周知,斯大林建立的体制不仅没有走向民主化,反而更加官僚化了。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历届领导人的“改革”,只不过是使斯大林体制更加“精致化”,更加僵化了。到了戈尔巴乔夫一举“放开”民主化时期,苏联犹如烈火烧炙的高压锅一样,爆炸成了碎片。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讲过多次,其中一次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
看来,在新世纪里我们深入研究苏联的教训,必将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的参考。
标签:十月革命论文; 斯大林论文; 斯大林全集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历史论文; 新经济政策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列宁全集论文; 邓小平文选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列宁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