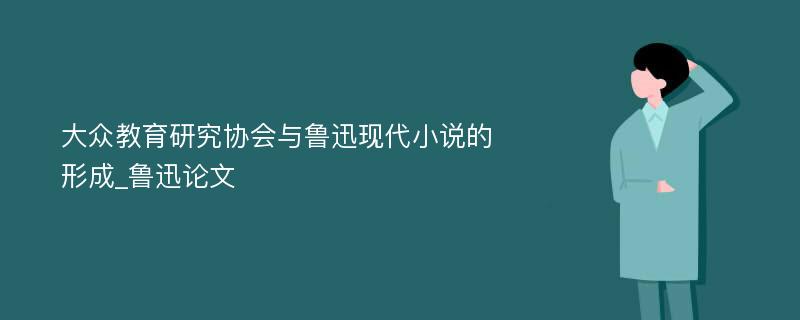
通俗教育研究会与鲁迅现代小说的生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研究会论文,通俗论文,现代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对自己为什么从事现代小说创作,曾经这样说过:“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①学术界也基本上顺承了鲁迅的自我言说并予以分析论证。但是,这样的解释无法说明,同是受外国作品和医学影响的鲁迅,为什么没有赋予《怀旧》以现代的品格,却将这一现代品格赋予了《狂人日记》?从鲁迅现代小说创作的阶段来看,这固然与正在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为什么同处于这个历史时期的其他作家,却没有最早创作出现代小说?其实,中国现代小说之所以能够在鲁迅的手中生成,与鲁迅在现代小说理论认识上的飞跃是分不开的。通俗教育研究会正是促成鲁迅对现代小说的认识产生质的飞跃的节点所在。通俗教育研究会,作为民国教育体制内的一个半官方机构,对中国现代小说的生成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但学者们在对中国现代小说发生的阐释中,却忽视了这个半官方机构的重要作用。因此,重新审视通俗教育研究会这一民国教育体制内的机构,审视其对现代小说的发生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实现的,应该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华民国成立后,为了能够较好地完成与晚清政体的切割,同时适应民国政体的现实要求,在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做出了政策上的调整。一方面,把学校教育纳入民国教育体制之内。具体到教科书的编撰上,删除了那些不符合民国政体要求的话语。另一方面,把学校之外的社会教育也纳入民国教育体制之内,在教育部首设了社会教育司,专门掌管社会文化教育,与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并立。“教育部官制于普通司专门司外,特设社会教育司实力督促进行。”②教育部为了能够更有效地推进通俗教育的发展,于1915年增设了“通俗教育研究会”这一半官方机构。该会“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③。该会由教育部设立,受教育总长直接监督,会长、各股主任均由教育总长指定,会员由教育部职员以及学务局、教育部直辖学校、京师劝学所、京师教育会、京师通俗教育会的成员充任。对此,有学者认为“通俗教育研究会与教育部之间仍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④。其实,通俗教育研究会与教育部之间并不仅仅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本身便是在教育部主导下设置的,并履行了教育部的某些行政职能。因此,对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准确定位应该是,它是隶属于教育部、但与教育部又有所疏离的半官方机构,这与纯粹的社会团体有着显著的区别。 通俗教育研究会作为半官方的机构,又分为三股:小说股、戏剧股、讲演股。其中,小说股负责对新旧小说的调查、审核、选择、编辑、撰译、改良等工作,除设一名主任主持办理股内事务外,又设调查、审核、编辑干事各三人分工负责股内工作。⑤作为半官方的机构,通俗教育研究会各股的主任是由教育部任命的,那么,担任小说股主任的候选人,不仅要熟悉中外小说翻译和小说创作实践,而且还要获得教育部总长的认可。显然,鲁迅⑥正适合这一要求。早在留学期间,鲁迅便刊发了《摩罗诗力说》等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还翻译了《域外小说集》,可谓是对中外小说翻译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与此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怀旧》这部文言短篇小说。显然,深谙中外小说创作和翻译的鲁迅,从专业素养上是适合担任这一职务的候选人;当然,作为带有半官方性质机构的主任,还需要承载官方的意志,否则的话,专业素养再高,也无法担此大任。从做人行事来看,这一时期的鲁迅,与上级的关系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搞到剑拔弩张甚至是对簿公堂的地步。从政治思想来看,此时的鲁迅正好暂时收起了自己的文学启蒙之梦,专注于抄古碑和研究古代小说,这种困顿的人生状态,相对于官场来说,恰好是其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标志。从文艺思想来看,鲁迅还没有完成对既有的传统审美法则的决裂,其小说翻译和创作,依然使用文言文,这在人们既有的文化心理结构深处,反而是一个人学养深厚的象征。正是这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鲁迅被任命为小说股主任,并主导起草了《小说股办事细则》,规范了有关审核小说的范围及程序等事项。这说明,小说作为通俗教育的一翼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并通过制定有关小说创作及其奖赏的体系,对小说的创作和翻译将起着导引作用。 细读《小说股办事细则》,第一节作为“总纲”主要是对整个小说股的工作进行全面界定。第二节对调查进行了全面的规范,指出:“不论内外国新旧小说,本股均应设法训查。”⑦这样一来,就把通俗教育研究会对小说的调查,扩充到了“内外国新旧小说”这样一个相对宽泛的范围中。这一界定,对扩展小说股的主任和相关人员的“训查”意识具有导引作用。然而,要想对小说做出较好的“训查”结果,调查员不仅需要深入实际,到社会中去,还要带着一种审视的眼光,得出“意见”,这一“意见”再经过“本股主任”提交给“委员会”。第三节主要是就审核的办事细则进行规范,指出“本股得调查员之报告后,应按照调查目录分别搜集,交由审核员审核”,特别强调“审核员应加具评论及意见书交由本股主任经由股员会报告大会”。这就使得审核员兼具了批评家的职能,要对其搜集到的小说作出评判,然后呈交给主任。自然,经过主任过目的“评论及意见书”,便不再是“审核员”的个人评论和意见,而是获得了主任认可的评论和意见。其中,那些在主任看来不符合要求的评论和意见,就会被屏蔽掉。然而,在这一工作过程中,由于“审核员”和“主任”所站的文化立场的不同,他们作出的评论和意见不可能完全一致,这就使得内部的“评论和意见”恰如社会上的“评论和意见”一样,都显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第四节的编译细则和第三节的审核细则基本上相似。最后的附则强调《小说股办事细则》需经过“教育部核准”⑧之后才能有效,这就突出了小说股对小说的审核权力恰是来自民国教育体制的赋予。将小说股及其所管理的小说纳入到民国教育体制中,这既是对民国教育体制下的小说股权力的认同,也是对小说作为一种通俗教育形式,已经在民国教育体制内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的确认。它为“新小说”的诞生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 小说股在制定了较为详尽的办事细则之后,又在第四、第五次会议上确立了《审核小说之标准》。在小说股制定的小说审核标准中,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小说股对小说进行类型划分,突破了传统的题材疆域。在中国传统小说中,人们对小说尽管有所分类,但是分类还是比较粗疏的。但总的来说,显然传统小说分类没有像民国初期所制定的审核标准那样细致。因此,我们如果从分类的角度来看,在传统小说中被置于边缘乃至被抑制的小说书写对象,开始进入了小说家的视野中,这就为现代小说逸出传统小说的疆域提供了诸多的可能性和合法性。 小说股对小说的分类,主要是从题材的维度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划分。值得追问的是,这个时期小说股为什么会从题材的维度上对小说进行分类,而不是根据其创作方法来进行分类呢?这或许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客观社会现实的需要。在中国传统小说中,题材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题材的问题,而是一个隐含着在题材之上的政治问题。从政治的维度来看,有些题材是不允许书写的,像政治小说便是如此,否则的话,如果小说涉嫌影射或诋毁政府,就会使书写者锒铛入狱。在清政府那里,不但有关政治题材的作品不容许书写,而且即便是那些“自然书写”也被置于政治的维度而予以查禁,这便封杀了诸多题材书写的合法性。二是区别于中国传统小说划分的传统。中国传统小说往往是根据其题材进行大而化之的划分,如《西游记》被当作志怪小说,《三国演义》被当作历史小说。这种划分标准,与西方小说侧重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创作方法来进行划分具有显著的差异。因此,在民国教育体制下,从题材入手,尤其是从社会现实客观存在的题材入手,来划分小说类型,这就为小说由题材的属性划分向以创作方法属性为标准的划分推进了一步。 在民国教育体制的保障下,小说创作的题材在法理上已经没有了政治禁区,小说创作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小说股把小说主要划分为教育之小说、政事之小说、哲学及宗教之小说、历史地理之小说、实质科学之小说、社会情况之小说、寓言及谐语之小说等七类⑨,这七类之外的小说则被纳入到了“杂记一类”中。在这种小说类型的划分中,教育、政事、社会情况三类是根据社会客观存在进行划分,哲学及宗教、历史地理、实质科学、寓言及谐语四类是从思想层面上确定的。就前者而言,客观现实题材突破了传统的政治禁区;就后者而言,哲学及宗教层面的思想题材,则突破了传统的思想禁锢,这就为思想解放拓展了空间。 其次,小说股对小说类型的评审标准进行了界定。对教育之小说的最高要求是“理论真切,合于我国之国情者,为上等”;对政事之小说的最高要求是“宗旨纯正,叙述详明,有益国民之常识者,为上等”;对哲学及宗教之小说的最高要求是“理想高尚纯洁,足以补助道德之不逮者,为上等”;对历史地理之小说的最高要求是“取材精审足资观感者,为上等”;其对实质科学之小说的最高要求是“阐明真理,有裨学识者,为上等”;对社会情况之小说的最高要求是“以改良社会为宗旨,词意俱精美者,为上等”;对寓言及谐语之小说的最高要求是“言近指远,发人深省者,为上等”。小说股对各类小说的这种评审标准,从理论话语的表述来看,尽管对各种标准的内涵尚没有明确的界定,但这种建立于宽泛标准之上的理论表述,便为审核者依照其所认同的“理论”来裁定小说之上乘与否提供了可能性。 小说股的主事者对小说审核标准之所以采取了这种表述方式,其背后的动因在于对这种政治修辞策略的认同。从中华民国的建立来看,民国体制无疑已经得到了确立,但在用什么思想作为中华民国的指导思想上,还存在着争议。孙中山热切期盼的中华民国的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其所皈依的是民主共和的政体。袁世凯梦寐以求的中华民国的指导思想则是封建专制思想,他所皈依的是专制独裁的帝制政体,他对小说的要求是“寓忠孝节义之意”。孙中山、袁世凯之外,还有一批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人物,如康有为等,则主张中间路线,他们期望着实行杂糅西方现代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的君主立宪的政体。只不过第三种路线仅仅停留在思想和言论上,并没有强有力的承载主体。因此,就其根本来说,“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此情形下,小说股在对小说审核标准的确立上,如果要采取一种明晰的话语表述方式,如采用民主、科学、平等等话语来表述,则会受到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激烈反对;要采用专制、独裁、等级等话语体系来表述,则有悖于中华民国作为现代政体的基本要求。正是基于这种复杂境况的考量,他们只能采取一种较为普泛性的表述方式,从而为持有不同思想、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上的人提供“话语各表”的足够空间。惟有如此,小说股所制定的有关“标准”,才会在袁世凯主导下的教育部获得通过。 关于鲁迅在通俗教育研究会工作的意义,尽管人们也作了很多的阐释,但这些阐释更多地是从政治上确认了鲁迅。认为他“从思想政治方面有力地坚持了民主革命的基本方向,直接地抵制了帝制复辟主义者们妄图利用小说股作为反革命舆论阵地的阴谋活动”⑩。这一立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的主流话语还是把政治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在此情形下,人们将鲁迅在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意义停留在政治层面加以确认,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中国社会和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学界对鲁迅在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意义依然缺乏深入研究。那么,通俗教育研究会之于鲁迅的意义,究竟在哪些方面呢?我认为,这更多地体现在其对现代小说的孕育和生成上。换言之,鲁迅在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工作,对其小说创作从传统小说《怀旧》到现代小说《狂人日记》的转变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节点。 鲁迅在创作《狂人日记》之前,既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小说家,更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大学教师,而是一个在教育部担任一定职级的官员。他这个教育部的官员,还不是纯粹行政意义上的官员,而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立思想和操守的人,这种独立思想和操守有时会和现实政治发生矛盾。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在教育部任职时期,鲁迅对教育部颁发的那些与自己的认同相悖的行政命令,采取了“有权在手,便当任意作之,何必参考愚说耶”(11)等对抗措施。这样一来,鲁迅担任小说股主任,在起草有关标准时,能够较好地灌注进自我的意愿。 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这一角色,使鲁迅从如何建构民国政体这一根本点上来考虑新小说的发展。从鲁迅在这一阶段的文化身份来看,作为小说股主任的鲁迅,自然就要站在民国教育的基点上,思考着如何利用新小说来为新建立的民国政体服务等根本问题。这样的社会角色,客观上便需要鲁迅有更为宏观的文化视野,而不再是就小说论小说,也不是就通俗教育论通俗教育。身在教育部,鲁迅更多地感受到袁世凯为了称帝而实施的尊孔教育是对中华民国政体所宣示的民主思想的背离。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全体会员大会于十月二十八日正式开场。新经任命的教育总长张一麐在会上大肆鼓吹封建主义,公然为卖国贼袁世凯复辟帝制大吹喇叭,他说什么:‘……中国社会自游牧时代进入宗法时代,而宗法社会遂为中国社会之精神,一家人咸听命于其家长,孝悌贞节,皆为美德,著于人心,蒸为风俗,此诚我国社会之特长也……’等等……为此目的,当他在后面讲到小说股的任务时,就搬出了腐朽不堪的孔孟之道:‘而积极一方面,则编辑极有趣味之小说,寓忠孝节义之意,又必文词情节,在能引人入胜,使社会上多读……’并‘极望’‘本会会员’能‘戮力同心,进行不懈,务使于一年二年之后成绩日进。'”(12)“企图尽量缩短审核时间,以便仍能‘尽快编译’那些宣扬所谓‘忠孝节义’的东西。鲁迅对此坚不相让,他针锋相对地坚持‘此期限规定极难’,结果这次会议以议决‘审核时间暂不规定’作为结束。”(13)这说明鲁迅在教育部期间,对袁世凯要求宣扬“忠孝节义”之类的东西,从内心里是排斥的,在行动上是抵制的,只不过这种排斥和抵制并没有达到“针锋相对”的地步而已。至于教育部官员秉承袁世凯的旨意对通俗教育研究会提出的诸多要求,鲁迅有了切实的感性体验和深刻的理性审视,所以,鲁迅在制定小说股审核小说的标准上,便自然地卷入政治的漩涡之中:一方面,由其主导制定的审核小说的标准,自然要体现出鲁迅本人的意志和思想;另一方面,作为教育部指导下的小说股,制定出来的审核小说的标准,更要体现出教育部尤其是身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的意志和思想。毕竟,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再次设立,本身就是袁世凯推动的结果,而袁世凯之所以要设立这一研究会,自然是把研究会的职能纳入他的政治意志,即把中华民国颠覆之后建立的“帝制”之中。这样一来,鲁迅在制定小说股审核小说的标准上,就会和教育部代表袁世凯意志和思想的一部分人发生冲突。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鲁迅在制定出了小说股的审核小说标准之后,还是辞去了小说股主任这一职务。这使得鲁迅对中国社会现实有了更真切的体验,情感和思想有了更大程度上的压抑,这就为其后来的爆发积蓄了能量。这恐怕也正是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出诸如“救救孩子”之类的“呐喊”、愈加沉郁和愤激的内在缘由。由此说来,鲁迅在教育部这个官场所获得的情感体验和理性认知,就使得他比创作《怀旧》时有了较大的提升,这便为鲁迅成长为文学大家所必需的文化品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由于鲁迅置身于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才使得他对礼教等一套规范体系有了更真切的认知,使得他创作出来的小说主题总是能够回应社会关切的重大问题,从而使得“狂人”的形象从历史的雾霾中走了出来,成为第一个承载起反封建礼教主题的勇士形象。鲁迅在创作《狂人日记》时,在对现实社会富有深度把握的基础上,结合自我的人生感悟,先创造出“狂人”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再把“狂人”这个人物的社会关系创造出来,又把这个人物与社会的关系相互作用下的矛盾创造出来,这恰恰是小说超越前人的关键所在。中国历史上不乏类似狂人这样的人物,但他们大都被看作“疯子”,没有在小说中获得正面的书写。所以,鲁迅塑造的狂人这一人物形象,相对于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来说,无疑具有惊世骇俗、振聋发聩之效能。 值得深思的是,鲁迅通过狂人这一人物形象传达给读者的“言外之意、象外之旨”是什么?这不能不与鲁迅切身体验到的社会现实有着极大关联。创作《狂人日记》时的鲁迅,不是一个偏居于一隅、与时代激流毫无干系的纯粹意义上的作家,而是一个置身于社会漩涡的中心,既切身感受到袁世凯倒行逆施推崇专制的寒意,也切身感受到陈独秀为“总司令”的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科学、民主的春意的作家。这样的双重体验赋予了鲁迅创作的《狂人日记》以双重文化品格:一是对旧文化的反叛和清理,这表现为对被奉为圭臬、且是“历来如此”的“吃人”礼教的否定;二是对新文化的皈依和呼唤,这表现为“救救孩子”的吁求。显然,这样的立意,如果没有对袁世凯为代表的帝制政体及其所推崇的对传统文化的全盘继承的清醒认知,没有对大转折时代价值体系的紊乱所带来的底层阻力的切身体验,那种既接“地气”又回应“天气”的囊括时代风云之作,便失却了孕育和生成的机缘。正是这种情感体验和理性认知,使鲁迅的小说主题具有了时代所能企及的深度和广度。如果说“文章合为时而作”是一切优秀的作家成长为文学大家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亲炙时代的风霜雪雨的鲁迅,其所发出的每一声呐喊,每一次反抗,不仅仅是听从于己方的将令,更是积极主动地剑指对峙的敌方,这恰是其成长为文学大家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的思想正是植根于中国社会最为坚实的文化土壤之中的。离开了这一点,我们就无从把握鲁迅的思想会达到如此高度的原因。显然,这一角色定位使鲁迅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家,更不会像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家那样,循着既有的小说路径进行小说创作,而是要在新文化发展基点上,赋予新小说参与建构新文化的现代品格。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的职责,使鲁迅对新小说的如何发展具有了宏观的视野。所以,在新文化运动氛围氤氲之际,鲁迅便感知到了时代欲来的风雨,并作出迅即回应。这便是鲁迅在《狂人日记》这一日记体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深刻主题,以教育作为切入点,指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这样的主题,既是对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专制行为的强有力回击,又是对社会上复古思潮的坚决回应,由此使得其创作出来的小说《狂人日记》不再是游离于社会主潮之外的“风花雪月”,而是紧随着时代的脚步而发出的“铿锵之声”。 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这一角色,还为鲁迅从政府官员的身份向现代小说作者的身份转变提供了可能性。鲁迅要制定带有指导性的新小说发展方略,就需要对中国小说进行理论上的反思,其具体表现就在于鲁迅通过对“内外国”和“新旧小说”的界定,隐含了对“新小说”的想象性建构。 在通俗教育研究会对小说的阐释中,关键的两对概念得到了确立:一是中西的小说概念;二是新旧的小说概念。就前者而言,中国的小说和外国的小说概念,是从中西两个空间的维度上确立了中国小说的发展方向。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我们往往片面地把中国的小说视为正宗的小说,而将西方的小说视为偏离了正宗的小说。这种观念随着晚清翻译小说的传播,尤其是林译小说的传播而发生改变,人们逐渐接受了西方的小说尤其像具有中西一体的某些共同特征的林译小说。林纾在其翻译的《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序言中,便把瞿、翁视为“两孝子而已”(14)。其实,林纾对西方小说有所保留地认同乃至推崇的思想,对中国传统士大夫而言是痛楚的。他们承认中国在“物”的层面上不如西方的同时,往往认为自己的文学要高出西方小说不知道多少倍。因此,在教育部主导下的有关通俗教育的条文中,把西方小说和中国小说置于同一平台上,便表明了已经开始承认西方小说和中国小说处于平等的地位,这为人们理解和借鉴西方小说打开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二是从新旧出发所确立的新旧小说概念。新小说和旧小说是自晚清以来就逐渐确立起了的概念,当正统的古典小说被视为旧小说时,那种与旧小说面貌截然不同的小说,便不再被人们视为离经叛道而受到排斥,相反还被人们冠之以新小说的名目而得到承认。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里的“新”比“旧”更带有值得肯定的价值,这种情形相对于那些推崇古人乃至古典的人们来说,其进化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建立了新旧的小说概念,人们自然对新小说怀有更多的期待和遐想,也就自然地为创造出新小说提供了更多的精神支持。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新旧小说概念的确立就为新小说的诞生提供了温床。至于谁能在这温床上分娩出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新小说,那最大的可能便是规划这种新旧小说的设计者了。毕竟,当这样的设计者开始确立了新旧小说概念时,便会在主观上开始谋划着区别于旧小说的新小说将以何种面貌示人。既然这种小说规划,除了小说新旧概念之外,还有“内外国”的空间概念,那么我们可以期许的是,其所创作出来的新小说既区别于中国的旧小说,又自然地会汲取西方小说的精华,用我们惯常的说法,则是中国的新小说,是中西小说的“宁馨儿”。 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过程中,如果说是先有一种蓝图然后才能创造出一种新小说的话,那么,小说股对小说审核的标准的确立,便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其意义是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的。从人类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方式来看,任何一种新形态的物质和精神的创造,都是在大脑中通过想象等方式先勾画出来,然后再把勾画出来的想象物外化出来。作为新小说,从其被创作的路径看,也应该是先有了作家在头脑中的勾画,然后再根据勾画出来的小说样式创作出来。从鲁迅对新小说的想象性建构来看,其所要创作出来的新小说自然是“由旧到新”的蜕变之作,是“新旧杂糅”的过渡之作。实际上,鲁迅创作出来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狂人日记》,正是这样的作品。 从小说形式来看,《狂人日记》与中国传统的小说形式相比,不仅在于它采用了日记的体裁,更在于它采用了横断面的体式。对于“横断面”的小说形式,胡适在论及中国传统小说时,曾经有过专门的论述:“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15)据此,胡适对中国传统短篇小说“某生,某处人,幼负异才……一日,游某园,遇一女郎,睨之,天人也……”(16)的一派滥调书写方式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那种流水账式的短篇小说形式中,其所注重的不是对人的性格的描写,也不是对人的自身的本质呈现,而是注重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的书写,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既遮蔽了人的主体性,也遮蔽了人的性格,更不会像“特写”那样,通过一种深入的解剖对人的性格进行深层次的透视,进而发掘出其所承载的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等诸多社会关系。中国的传统短篇小说仅仅通过人与社会关系的书写,来展示其矛盾冲突,尤其是注重小说情节的营构。因之,融合在这种短篇小说形式之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往往成了像木偶一样演绎故事和理念的符号。正是基于这一点,胡适通过对西方短篇小说的深入解读,从理论上深入阐释了现代短篇小说的形式及其形式的思想意义,这就在理论上把握了短篇小说的现代品格。显然,胡适对西方现代小说的解读与鲁迅的短篇小说创作实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鲁迅担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时制定的“审核小说之标准”,在鲁迅蜕变为新小说作家的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至于后来鲁迅被小说股聘任为审核员对《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所作的审读报告,作为一个历史进化中之不可或缺的链条,同样参与了他蜕变为现代小说作家的过程。这不仅促成了鲁迅对新小说现代思想的赋予,而且还促成了他对新小说的想象性建构。 鲁迅作为小说股的主任,其工作职责所在,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审查中国小说上,还要审查那些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及理论。如此一来,鲁迅就把“内外国”小说都纳入到一个公共平台上进行审查,其所使用的审查标准自然也是一以贯之的。这种打通“内外国”小说之间的壁垒的做法,自然就规避了过去那种排斥外国小说的成见,从而使得小说审查者具有了世界小说的意识,这为他在创作小说时赋予小说以世界性的品格奠定了坚实基础。 鲁迅作为晚清时期便开始翻译外国小说的翻译者,对外国小说及其翻译的内在规律是有着切身的体会的。鲁迅和其弟周作人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尽管并没有获得他们所想象的那种成功,但从他们自身对文学特别是对域外小说的翻译的认识来说,其所接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鲁迅正是从翻译《域外小说集》出发,获得了汲取域外小说之精华来建构中国新小说的切身体验,他由此意识到,翻译西方小说不仅要注重选择那些与中国国情有所关涉的小说,而且还要采取“拿来主义”的翻译方略,唯此,翻译出来的西方小说才会获得中国读者的认可和推崇,才会对中国小说的营构起到应有的作用。也许正是基于这一考量,鲁迅虽然辞去了小说股主任一职,但是,基于他对外国小说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还是成了周瘦鹃所译外国小说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的审核者。 《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由中华书局于1917年3月出版。同月,鲁迅向蔡元培介绍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任职,获得了蔡元培的同意。4月1日,周作人从浙江到北京。对此,鲁迅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夜,二弟自越至……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17)到了5月13日,鲁迅在日记中又记下了这样的话:“上午得二弟妇并三弟信,九日发,又《或外小说集》十册。”(18)该审读报告尽管于11月30日刊登于《教育公报》上,但教育部的“褒状”所署颁奖日期却为1917年9月24日。该“褒状”这样写道:“兹审核得中华书局出版周瘦鹃所译之《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三册,与奖励小说章程第三条相合,应给予乙种褒状,经本会呈奉教育部核准,特行发给以资鼓励。此状 右给周瘦鹃收执 通俗教育研究会会长袁希涛(签章)。”(19)这说明,鲁迅审读该小说的时间区间在3月到9月之间,最大的可能是在4月到8月之间。 这一时间节点,看似平淡,但如果把这一时间节点放在鲁迅创造现代小说的前夕加以审视,我们就会发现,鲁迅于1918年在《新青年》刊发的《狂人日记》恰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孕育期和成型期。也就是说,这个时期鲁迅担任小说股主任、出任小说股审核者等一系列活动,对其孕育《狂人日记》不可能不产生显性或隐性的影响。鲁迅审读《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有三个因素值得重视:一是鲁迅担任小说股主任时期制定的《审核小说之标准》,真正地开始了与审核对象的对接,由此更加清晰地印证了鲁迅对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加以评判时所操持的“标准”,而这样的标准对即将出世的《狂人日记》不能不产生某些影响;二是与鲁迅合作翻译过《域外小说集》的周作人,已经到达北京,因而周氏兄弟合作审读了这部翻译小说,并合拟了这份审读报告,这对《狂人日记》中所表现出来的兄弟关系不能不产生某些影响;三是周氏兄弟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依然作为一种在场因素,对他们撰写的审读报告产生着潜在影响,尤其是对他们的小说观产生某些深刻影响。周氏兄弟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反响寥寥,周瘦鹃翻译的外国小说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上中下三卷却受到读者的欢迎,两相对比,不能不对鲁迅即将创作的《狂人日记》起到某种指导作用。可以说,这三大因素综合构成了鲁迅孕育和创作现代小说《狂人日记》的直接语境。 那么,鲁迅对《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是如何评价的呢?我们不妨对1917年11月30日《教育公报》上刊出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核小说报告》加以解读。该报告属于鲁迅和周作人合拟,至于是谁草拟,谁来定稿,没有更多的资料可以佐证。但是,不管是谁来起草,这一报告体现了鲁迅的意志和思想是无可置疑的。该报告这样写道:《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凡欧美四十七家著作,国别计十有四,其中意、西、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在中国皆属创见,所选亦多佳作。又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惟诸篇似因陆续登载杂志,故体例未能统一。命题造语,又系用本国成语,原本固未尝有此,未免不诚。书中所收,以英国小说为最多;唯短篇小说,在英文学中,原少优制,古尔斯密及兰姆之文,系杂著性质,于小说为不类。欧陆著作,则大抵以不易入手,故尚未能为相当之绍介;又况以国分类,而诸国不以种族次第,亦为小失。然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20)。鲁迅的这份审读报告,既是对周瘦鹃翻译作品的审读意见,也是鲁迅自我文学思想和趣味的外化。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该审读报告对其翻译过来的小说的国别进行了大体的介绍,尤其对其所翻译过来的五个国家的小说特别肯定,认为这在中国“皆属创见”,这便肯定了其开拓性的价值,而这样的开拓之作“亦多佳作”。这说明了鲁迅特别看重欧美弱小国家的短篇小说。鲁迅于1933年谈及自己最初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就说过:“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21)因此,鲁迅对周瘦鹃翻译弱小国家的短篇小说这一举动给予了特别的认同和推崇;相对而言,对英国小说的认同和推崇就远不如前者了。其次,鲁迅对“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的做法给予了大力的肯定,甚至由此提升到“足为近来译事之光”的高度予以推崇。其实,就翻译而言,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的确有助于读者了解作者的情况,尤其是“小像”这样的图片,对读者感性地“认识”作者具有积极的作用,二者正可谓“相得益彰”。鲁迅在作出这一价值判断的背后,隐含的正是他对装帧图画设计等形式的特别看重。我们知道,鲁迅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外,对图书的装帧图画设计也非常看重。为此,他经常亲自设计图书的封面,努力追求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如鲁迅亲自为自己的小说集《呐喊》设计了封面;他还为许钦文编选的短篇小说集设计了封面,用了一幅《大红袍》的图。许钦文在《鲁迅和陶元庆》中写道,鲁迅看到了《大红袍》,认为“有力量;对照强烈,仍然调和,鲜明。握剑的姿态很醒目”,于是便建议“把《大红袍》用作《故乡》的封面”(22);鲁迅对陶元庆设计的《彷徨》封面非常欣赏,便在1926年10月29日给陶元庆的信中写道:“《彷徨》的书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23)所有这些都说明,鲁迅所拥有的身份并不是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作家,而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巨人频出这一现象,恰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频出现象一样,标志着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24)。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的前后次序颠倒过来,也可以说是频出的巨人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而他们则成为人的诸多方面素养都得到全面健康发展的典范。鲁迅正是基于这一品格,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在小说这一主体之外“附小像略传”的设计看作“近来译事之光”。显然,如果我们把这种看法放在中国小说历史长河中,尤其是结合蔡元培提出的“美育”教育思想加以审视的话,此种“新做派”的确像他即将面世的《狂人日记》一样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鲁迅在充分肯定《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的同时,还对其体例未能统一和命题造语略有微词。如果说指出体例未能统一这样的问题还略显中立的价值判断的话,那么,对“命题造语”问题的批评便深刻地反映了鲁迅的小说翻译观。鲁迅认为“命题造语,又系用本国成语,原本国未尝有此,未免不诚”。这表现了鲁迅在翻译中更注重“硬译”。鲁迅的翻译,努力保持着原作的口吻和精神,即“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25)但是,依据这样的原则翻译出来的小说,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如周氏兄弟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竟然到了没有几个读者购买的地步。相反,一些不注重“硬译”的翻译,像林译小说恰是通过意译乃至改译,得以赢得中国读者的欢迎。与此类似的是,被鲁迅视为“未免不诚”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反而拥有了更多的读者。这恰恰说明,鲁迅在翻译的“理想国”中坚守的“硬译”原则,从理论上说是切实可行的,从实践上说也是可行的,但就其特定时空下的特定读者来说,在“硬译”的同时如果不重视“意译”,其“诚”倒是做到了,但由“诚”而来的翻译则成为没有几个读者能读懂的“天书”(林语堂语)。如此说来,那翻译者努力得来的“诚”又有多少意义呢? 从理论上说,“诚”既然有其二重性,那么,鲁迅在审读时推崇的“诚”到底有没有值得肯定的方面呢?显然,这便涉及到鲁迅对“诚”带有偏执性的追求了。就翻译作品而言,对“诚”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是,对“诚”的执着追求对于鲁迅孕育和创作《狂人日记》来说,则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原则”。鲁迅的文化视阈下的“诚”,并不是一个“如何变通”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国民性格的大问题。鲁迅早在1907年论及国民性时便这样说过:“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26)与对“诚和爱”的推崇相对应的是,鲁迅把“瞒和骗”看作国民性的弱点:“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27)这一正反对比,说明了鲁迅是把“诚”上升到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两种东西之一的高度来看待的。也惟其如此,鲁迅才会在评判翻译时特别凸显“诚”的原则;惟其如此,鲁迅才会在孕育和创作《狂人日记》时规避了文艺上“瞒和骗”(28)这一老路上的陷阱,创作出了中国历史上真正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开启了“新小说”的崭新范式。 鲁迅对《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存在的其他“小失”虽然也有所提及,但总体上来说,在他的审读报告中依然肯定了这部翻译小说之于“当此”这一时间节点上的意义:“然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显然,鲁迅对长期以来的文学界之现状是非常不满的,即便是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这种现状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改观。在鲁迅看来,文学界流行的以言情为主的通俗小说是一些一味地凸显“衷情”“惨情”的“淫佚文字”。在此情况下,《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作为“更纯洁之作”便犹如“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弥显珍贵。鲁迅在此发出的议论具有两重含义:一是对文学界流行的文学作品极为不满,这便意味着,如果鲁迅要着手进行小说创作的话,自然不会随波逐流,而会另辟蹊径,创作出完全迥异于既有的通俗小说之品格的“更纯洁之作”;二是表明对“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的文学境界的神往之心。如果鲁迅要着手进行小说创作,便会自觉地追求小说应达到昏夜里的微光、鸡群里的鸣鹤之境界,以一种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姿势,成为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昏夜”里照亮人们心灵世界的第一缕微光。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当鲁迅在嗣后创作《狂人日记》时,便把“昏夜”意象纳入到了作品之中,诸如“全是发昏”、“全没有月光”、“半夜”、“胡涂”、“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太阳也不出”、“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等等,都为我们营构了“昏夜”的意境。而作为“人之子”的狂人在觉醒后发出的第一声“呐喊”——“救救孩子”(29),则犹如洞穿这漫漫黑夜的一缕“微光”,照亮了这千年以来的“昏夜”,新世纪的曙光由此开始降临了。 总的来看,当我们把通俗教育研究会纳入历史的视野中加以审视时,便会发现,《新青年》并非中国现代小说发生的唯一源头,象通俗教育研究会这样的机构也许同样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新青年》以其显性的形式,通过文学革命等口号,用鲜明的话语,把文学革命的诉求提了出来,并借助北京大学这一公共领域,迅疾地使文学革命成为名噪一时的文学运动;而通俗教育研究会则以隐形的形式,把小说创作和翻译纳入到了中华民国的政治诉求之中,用相对温和的话语,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新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鲁迅正是在通俗教育研究会对如何创作中国“新小说”有了现实的调研和理论的思考,并初步形成了现代小说的意识。因此,当时间的脚步迈进到1918年4月时,怀抱着创造中国之“更纯洁之作”这一豪迈激情的鲁迅,在S会馆里创作出了别离“哀情”和“惨情”,饱含着“诚和爱”的现代小说——《狂人日记》,并刊发于《新青年》,这意味着通俗教育研究会和《新青年》这两大阵营得到了贯通,中国现代小说也因此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确立。 ①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会务纪要》,《通俗教育研究录》第1期,1912年。 ③⑤《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教育公报》第4期,1915年7月。 ④施克灿、李凯一:《江湖与庙堂:北洋政府时期社会教育的路径选择——以通俗教育研究会为考查对象》,《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年第5期。 ⑥关于鲁迅(周树人)担任小说股主任的区间以及所作所为,陈漱渝在《鲁迅与通俗教育研究会》一文中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该文还针对沈鹏年刊发于《学术月刊》1963年第6期的长文《鲁迅在“五四”以前对文坛逆流的斗争》进行了反驳。本文重点阐释的是鲁迅主持制定的审核小说标准对他创作出中国第一部现代小说的作用。应该说明的是,“鲁迅”作为周树人的笔名,是后来才使用的,其在担任小说股主任时,官方采用的名字是“周树人”。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也延续了前人惯常使用的“鲁迅”来指代周树人。 ⑦⑧(12)《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参阅孙瑛:《鲁迅在教育部》,第49—51,第49—51,第53—5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⑨《学事一束》,《教育杂志》7卷12号。参阅孙瑛:《鲁迅在教育部》,第51—5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⑩(13)孙瑛:《鲁迅在教育部》,第61—62页,第5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1)鲁迅:《180820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4)林纾:《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序》,《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4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5)(16)胡适:《论短篇小说》,《胡适全集》第1卷,第125页,第12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7)(18)《鲁迅全集》第15卷,第280、2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9)桑农:《读书抽茧录》,第2—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 (20)《教育公报》第4年第15期,1917年11月30日。 (21)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2)钦文:《鲁迅和陶元庆》,《〈鲁迅日记〉中的我》,第8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3)《鲁迅全集》第11卷,第5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5)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2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6)许寿裳:《回忆鲁迅》,《新华日报》(重庆)1944年10月25日。 (27)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2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8)鲁迅曾经这样说过:“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254—2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9)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4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标签:鲁迅论文; 域外小说集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现代小说论文; 小说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教育研究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短篇小说论文; 袁世凯论文; 读书论文; 狂人日记论文; 怀旧论文; 教育体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