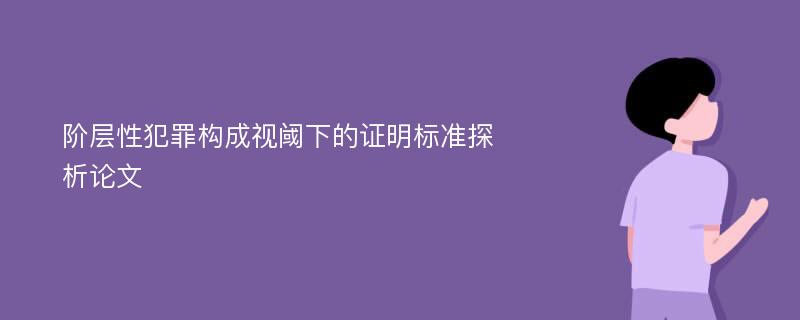
阶层性犯罪构成视阈下的证明标准探析
邓 超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1)
摘要: 犯罪构成理论是对犯罪事实进行型构和评价的工具,其目标是从纷繁的事实中找寻出具有刑法规范价值的因素,刑事证明标准用来测量这些因素是否违反规范,以及违反规范程度的规格。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对证明标准具有不同的指引功能。阶层性犯罪构成体系使得待证对象得以类型化,并具有层层推进的逻辑演绎功能,不仅规制了犯罪是否成立的思考路径,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证明标准更加周延、合理,更具实质意义。以阶层性犯罪构成体系为指引,有利于实现“主观性”证明标准研究的再推进,为主观性证据的证明提供制度空间和逻辑基础,也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层次化”标准的含义,为辩方寻找出罪路径提供一种方向指引,还有利于实现“进阶式”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各阶段中的有所侧重,增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更好地实现刑事证明标准的指引功能和人权保障功能。
关键词: 阶层性犯罪构成;标准细化;形塑功能;法律真实;完善进路
从证据证明的角度来看,任何一项证据的形成都意味着“构成要件该当”的实践发现和理性证明;从犯罪构成理论分析,任何一个犯罪的成立都需要经过“入罪”和“出罪”构成要件证明标准的判断和证成。“入罪”和“出罪”作为相反的两种价值诉求,不仅体现在构成要件的定型性之中,而且从相反的两个方向对证明标准的适用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石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为“入罪”提供了价值导向和实体依托,但是“出罪”路径的选择会因为不同的犯罪构成体系及其衍生的“出罪”证明模式不同而有所差异。我国目前的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更多地呈现出平面性、组合式的特征,对于案件的整体事实和犯罪行为缺乏逻辑性的考量和细致化的审视。传统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将犯罪构成要件划分成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其耦合式的思维结构无法平衡各个要件的顺序,这就决定了各个犯罪构成要件在被发现过程中的杂乱无序,没有层层推进的逻辑要素,“有忽视客观的要素与主观的要素各自内在的差异之嫌”。① [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第4版),有斐阁2008年,第113页。 再者,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只规定了成立犯罪的规格,却没有明确列明出罪因素,也就没有给辩护留下空间,不利于保障人权的实现。相比之下,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个问题,其形成一种递进式的行为评价进路。通说认为,大陆法系的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包括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三个阶层,② Vgl.C.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4.Aufl.,C.H.Beck,2006,p.281. 其中,构成要件该当性是根据刑法理论和规范对行为进行的事实性判断,是案件事实向规范事实涵摄过程中的第一步,即事实的初步判断和裁定;违法性是根据行为的属性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否存在冲突而做出的一种规范性评价,在涵摄事实的基础上对行为性质的梳理和认定;有责性则是在得出结果之前所作出的最后一层评价,是对行为的主体性评价和主观性评价,作为行为定性的最后一道门槛。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是符合认知逻辑的,上一阶层的定性是下一阶层判断的逻辑起点和导向依据,经过层层推进和筛选,最终定位出具有规范性和道义性的行为规制范围。正如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所指出的,以客观的、记叙性的构成要件的行为为切入,进而再去考虑它的违法性和责任性,这种思考过程与现代刑事审判中的审理过程是一致的,是反映了构成要件理论的实践品格的。③ 参见[日]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王泰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另外,这样的犯罪构成体系也为刑事证明提供了一种递进性的路径,不仅明确了证明对象和证明范围,厘清了证明过程,还能动地连接了案件事实和规范事实,促进了案件事实向规范事实的合理转化。
这些题目着重考查了中学学习阶段的基础知识和主干内容,这些知识是今后进入大学学习以及终身学习所必须掌握的“必备知识”,这体现了高考对进一步学习的学生需要具备适应大学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能力和基本素养的“基础性”考查要求[6].
从某种意义上讲,刑事诉讼证明中的基本问题,都必须回到犯罪构成的层面,才能获得妥当而可靠的解决④ 参见杜宇:《犯罪构成与刑事诉讼之证明——犯罪构成程序机能的初步拓展》,《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1期。 。从纵向看,犯罪构成体系逐渐收缩,有利于发现案件的“法律定型”。从横向看,在实体认定中引入证明判断,有利于形成案件的“整体样态”,符合人类认知的基本顺序和轨迹。犯罪构成是一种犯罪的法律规格,其目的在于为犯罪的司法认定提供法律标准。⑤ 参见陈兴良:《犯罪构成理论与改革》,《法学》2005年第4期。 证明标准是一种证明规格,其目的在于对行为和事实进行一种合乎规范和理性的判断标准。可以这样认为,犯罪构成体系是一种大的认定标准,刑事证明标准是一种小的认定标准。犯罪构成体系筛选出了符合刑法规范的事实和行为,进而需要通过证明标准去实现对这些事实和行为的裁量,合理地赋予这些事实和行为以法律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入罪”和“出罪”,进而实现对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追求。那么,在阶层性的犯罪构成体系下,如何准确测量每一个行为的法律匹配度,实现合目的性和合规范性的公平正义呢?笔者认为,深度剖析阶层性犯罪构成体系对刑事证明标准的形塑功能,还可以使证明标准更加精细化,它也是一条很好的研究进路,进而使证明标准更好地发挥其指引性功能。
微带线之间的耦合特性通常会影响滤波器的通带带宽。因此,可以通过改变微带线之间的间隙的宽度,控制所提出的滤波器的通带带宽。
母婴店经常推荐很多宝宝能够食用的功能性饮料和食品,宣传点十分有噱头,并且吸引家长的眼球,这些功能性饮料和食品是否对宝宝有帮助呢?
一、阶层性犯罪构成体系的优越性——对证明标准的细化具有形塑功能
其次,违法性阶层的“实质性”考量为证明标准的细化提供了衡平进路。构成要件该当性通常是一种不法行为的类型化描述,但同时也存在虽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却不具有可处罚性的行为事实。构成要件是关涉现象的考察,是形式违法的重要体现,但违法性阶层关涉行为的本质和价值性判断,是对违法行为性质的实质性考量。“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是关于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类型的所谓类型性判断,而违法性判断则具有更实质意义的非类型性判断的性质。”② [日]大塚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9页。 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认为违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此处的客观违法不仅仅限于违反刑法规范,更应该是对刑法保护法益的侵害和破坏,是一种实质性判断,因此对违法性的认定除了应当正向考量其对法律规范的违反程度,更应该考量其对社会秩序和价值的伤害。违法性阶层主要是违法性阻却事由的判断,例如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即一项行为即使完全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要素,但是在一种紧急情形下做出的不得已的损害他人利益,或者是出于对另外一种危害行为的反击而做出的违法行为,虽然违反了刑法规范,但是不具有可处罚性。违法性阶层的判断是构成要件伴随例外思维的表现,是在违反规范之后的又一次审视,是在客观判断之后的实质性考量,由此决定了违法性的判断不能仅仅从规范上进行考察,而更应该从对法秩序的实质破坏层面去解读。因此,这个犯罪阶层中的证据考量标准,应该集中在其“实质性”上。实质性考量的思维模式,要求在周延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证据的基础上,反向地筛选出更为合理的法益价值进行保护,其不是因预设的刑法条文而让步,相反是在法益衡量的基础上对实质正义的强化,保护更为重要的法益,在利益权衡之间通过反向阻却的价值判断实现更为合理的刑法控制功能。违法性阶层的“实质性”考量使得违法性判断在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之间趋于衡平,增强了规范类型的适用力和协调力,也为“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提供了一种衡平进路,使得证明标准在实践运用过程中更加注重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实现法理和情理的高度融合统一。
刑事诉讼是一个“目的性”的展开过程,抛开自身的程序逻辑,刑事诉讼的核心目标是“实体形成”。⑦ 参见前注③,小野清一郎书,第202~204页。 这个实体形成过程的基础性框架是犯罪构成体系,不同的犯罪构成体系会造就出不同的实体形成。犯罪构成是对犯罪事实的型构,是一个评价行为性质的过程,从纷繁的事实中找寻出符合刑法价值分析的因素,并用证据佐证这些因素,进而通过刑事追诉厘清刑法和刑罚的价值范式;其起点是原始的犯罪事实,终点是模型佐证下的法律事实,中间过程是证明规则与法律适用相结合的过程。然而,“客观事实”终究无法实现全面的还原,如果能够实现“法律事实”的对应,已然可以形成刑法运行的重要目标。阶层性犯罪构成体系的逻辑性和层次性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案件事实,为人们理清案件事实提供基本的框架,使得案件事实向规范事实的涵摄过程更加清晰。阶层性的分析和筛选,使得待证对象得以类型化,并产生逻辑上的关联,实现了体系化构造,不仅规制了犯罪是否成立的思考路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证明标准得以细化,为证明标准在实践中的应用提供了理论指引。
“法律真实”的实现需要一个科学合理的犯罪构成体系作为基础。“法律真实”不仅包括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真实,也包括刑事实体法意义上的真实,而犯罪构成体系就像刑事实体法的“骨骼”一样,为司法案件提供定型化的指导,其与刑法规范相结合,形成一个有力的框架涵括事实行为、整理事实行为,并为规范行为的形成发挥指引作用,其科学与否直接决定了对事实行为的认定路径是否正确。犯罪构成不仅是犯罪成立或者不成立的最终判断基准,而且是刑事诉讼过程中整体性的“指导形象”。① 同前注③,小野清一郎书,第199页。 从价值和功能考量,犯罪构成具有“工具”和“界限”的意义。一个行为与犯罪构成的匹配程度和衔接程度,是该行为进入刑法规范领域的重要衡量指标。一项要素是否具有裁判价值,也要根据其形式特征和内容特征进行结构性地判断,才能厘清其所承载的规范必要性。
标准是一种尺度,是一项行为被评价为具有某种性质或特征的裁量根据。具体到刑事领域,刑事证明标准是发掘出某一行为与刑法规范的匹配度,进而对其进行裁判与规制。英国学者摩菲(Peter Murphy)对证明标准的含义有一个较为完整的阐述,即“证明标准是指卸除证明责任必须达到的范围或程度,它是证据必须在事实审理者头脑中形成的确定性或盖然性的尺度,是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在有权赢得诉讼之前必须运用证据说服事实审理者的标准……”⑥ Richard Glover,Peter Murphy.Murphy on Evidence.Blackstone Press Limited,1997,p.109.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目前的刑事证明标准可以概括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012年修改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在这个标准基础上又引入了“排除合理怀疑”,初步实现了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排除合理怀疑”中的“排除”是一种逆向的思维方式,作为“证据确实充分”的有效补充,从思维的另一个侧面增强了刑事证据的可把握性和可执行性。排除合理怀疑的起点在于对控辩双方的主张以及所依赖的证据进行评判,无论是法律适用错误还是证据链条中的论证瑕疵,只要能够引起怀疑,都应该继续进行补证和质证。排除合理怀疑要求综合运用客观检验、逻辑验证、价值判断等方法,在对控方主张和辩方主张的循环考量基础上,对单个证据以及证据与所论证命题的常态联系进行逻辑验证,如果依然能够引发合理怀疑,则需要对怀疑的内容进行解答。它的说理阶段即为“排除”过程。从主观上讲,它不断追求司法人员对“合理”的界定和认知,强调对合理怀疑的寻找,进而对怀疑进行排除;从客观上讲,“排除”的过程也依赖于对证据的重新审视和客观规律的分析总结,是一个主客观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
我国目前的证明标准,从实施以来就被认为具有模糊化、执行性差的弊端。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以证明目的代替证明标准的表述,③ 参见龙宗智:《中国法语境中的“排除合理怀疑》,《中外法学》2012年第6期。 究竟依据怎样的标准来判定“证据充分”,是立法者未给出明确答案的问题,④ 参见陈瑞华:《刑事证明标准中主客观要素的关系》,《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 其笼统概述式的表述确实会造成实践过程中很多问题的出现。也有学者认为,在相当一部分案件中,法律制度上的“高标准”并没有在实践中做到“严要求”,在证明标准的话语表达与司法实践之间似乎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悖反”现象,⑤ 参见陈虎:《制度角色与制度能力:论刑事证明标准的降格适用》,《中国法学》2018年第4期。 因此,对证明标准的优化是完善刑事证明制度一个必要的切面。
犯罪构成体系先于案件事实而存在,证明标准也先于案件事实而存在,换言之,犯罪构成体系和证明标准作为两种工具一起发掘案件行为中的法律事实,从两个维度上对案件事实进行评价,从不同的方面进行规制,使其规范含义和保护目的并驾齐驱,逐渐实现两者的违法判断评价机能。从历史的角度看,犯罪构成的概念最先是出现在诉讼法范畴中的。德国学者克拉因在其1796年出版的《德国刑法纲要》中首次把构成要件当作刑法上的概念使用,此后才出现了从作为程序意义的证明犯罪行为的全部客观事实向实体法上的犯罪事实本身转化的倾向。② 参见何秉松:《犯罪论体系》,“全球化时代的刑法理论新体系”国际研讨会(北京)文件,2007年10月。 犯罪构成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以还原事实为目标,同时兼顾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和文化情感,以犯罪成立条件的总和为前提进行定罪的操作过程和思维方法,是规范合目的性和有效性辩证统一的概念载体。如前所述,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具有清晰的认知逻辑,不仅为两造对抗提供了基本的对象,加快了实体认定的节奏,而且明晰了证明责任的分配,使得证明标准逐渐细化,为事实与规范之间的不断靠拢,实现证明标准的“法律真实”提供了方法支撑,使实体形成的构筑形式更加类型化、精确化。同时,三阶层的犯罪构成体系使得行为和事实基础上的刑事论证更加显性化,为合理的、可预见的裁判结果提供了制度保障。“法律真实”是一种理性真实,对理性和真实的探寻,不仅仅是证明标准的实质侧面,也是架构构成要件事实和规范事实的桥梁。
在日常教学中,鼓励跨学科的融合式教研,在各学科研究课活动中,参与听课、评课的教师未必是本学科教师。课程改革中综合性课程的开设、实施、推进,势必需要学校和教师开发并利用跨学科的综合性主题,发展学生的综合素养,不断提高课程的育人实效性。
二、“法律真实”视野下的证明标准依赖于一个科学合理的犯罪构成体系
从理论上看,关于证明标准的目标有“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两种学说。其中“客观真实说”是指法官在认定被告人有罪时必须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应当与客观上实际存在过的事实一致,⑥ 参见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页。 认为“任何案件事实,通过正确地收集、分析证据,是可以查清的”。⑦ 张子培主编:《刑事诉讼法教程》,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页。 然而,客观真实的实现只是一种愿景,在实践过程中因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无法再完全复原彼时的状态和情况,因此,我国大多数学者对此种学说持否定观点,认为“这是一种认识乐观主义,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差”。⑧ 龙宗智:《中国法语境中的“排除合理怀疑”》,《中外法学》2012年第6期。 随着“客观真实说”弊端的逐渐显现,“法律真实说”被很多学者肯定并用于指引实践。“法律真实说”,简言之,就是“从法律的角度看是真实的”,具体是指“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证明的过程中,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应当符合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达到从法律的角度认为是真实的程度”。⑨ 樊崇义:《客观真实管见——兼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不可否认,我国“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极大地体现了客观事实和实体正义的追求,但“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有限,任何人对于事实之存在很难达到绝对确定的程度”,⑩ 陈朴生:《刑事证据法》,三民书局(台北)1979年版,第581页。 并且2012年修改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将“排除合理怀疑”明确为刑事证明标准的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客观真实”说的消解。“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引入从侧面说明,正是因为没有办法完全地复原所有犯罪事实状况,所以才需要在综合考量已经获得的证据基础上,由裁判者作出一种合理的衡量和评价,剔除掉一切可能引起怀疑的因素。排除合理怀疑为无罪推定提供了前提性的判断基础,是一种最终说服责任,由于证明距离所产生的剩余怀疑必须达到合理的界限才能使得评价作用于事实,这项标准拉近了主客观判断的距离,也促进了客观行为与主观意志的融合,使得主观判断更加具体化、类型化。
首先,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的“周延性”为证明标准的细化提供了实践路径。构成要件该当性是犯罪构成体系的逻辑始项,其研究基础是现象和行为,是观察基础上的描述,融合了各种行为情状和法律要件,圈定了基本的犯罪事实,是在阐释现象的基础上实现的类型化。理论通说认为,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的对象主要是行为的各种相关要素,⑧ 关于故意是否应该在这个阶层讨论,有学者认为,故意由最初的罪责要素发展为构成要件要素,在新古典和目的论结合体系那里,又由构成要件要素分裂出了罪责要素,从而形成了故意的双重机能。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内,法律效果转用之罪责论通过将故意加以双层定位,从而逻辑自洽地解决了“回旋飞碟”问题,且能在共犯成立上,将共犯问题做共犯处理。参见蔡桂生:《论故意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双层定位— —兼论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6期。也有学者认为,按照结果无价值论的观点,故意属于责任要素;按照行为无价值论的观点,故意属于主观的违法要素。参见张明楷:《阶层论的司法运用》,《清华法学》2017年第5期。 具体包括实行行为、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犯罪的主体、行为的客体、行为的状况以及行为的条件等。古典的二分理论指出,犯罪由“物理力”和“精神力”组成,其中物理力即主体的行为,这种认知从朴素的价值观出发,总结了犯罪构成的本体性要素。构成要件最初是一个程序法上的概念,首次将“犯罪构成”从诉讼法移植到实体法上的是费尔巴哈。他认为犯罪构成是“违法的(从法律上看)行为中所包含各个行为或事实的诸要件的总和”。⑨ [苏]A.H.特拉伊宁:《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王作富等译,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5页。 构成要件该当性是辨别刑法意义的基础规范模式,具有事实评价的客观性价值,适应了罪刑法定原则关于具体、明确的法律形态的要求。构成要件该当性关注案件的发生进程,以及每一个行为所折射出的刑法意义。从证据法的观点来讲,刑事诉讼中的主要证明事项就是构成要件事实。⑩ 参见前注③,小野清一郎书,第241页。 因此,在认定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对全部事实和行为的收集,进而实现证据收集的全面性和证明标准的周延性,不能忽略任何一个可能具备规范意义的行为。在证据真实的基础上,实现对行为主体、危害行为、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等相关证据的全面搜集,进而根据刑法条文的分则规定和总则规定,实现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规范化。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证明标准的表述,笔者认为,证明标准的周延性应该是“证据确实充分”标准的亚类型,是对“充分”标准的再细化。证明标准的周延性着眼于事实基础上的判断,重在分析事实行为的内在逻辑结构,进而在刑法条文覆盖范围内寻找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可能进路和可能出路。何谓“周延”?周延是一个判断的主词(或宾语)所包括的是其全部外延。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05页。 具体到构成要件该当性的阶层,不仅仅要注重对证据的全面收集,更应该充分挖掘每一项证据背后的内涵和价值,寻找其全部外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周延性的标准只应该在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应用,在其他两个阶层就不存在或者不应该被适用,而是指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的特殊属性,使得周延性的标准在这个阶层显得十分重要。从结构支撑的构筑形式来看,构成要件该当性为刑法规范的主客观统一的认知过程提供了逻辑起点和实体形成,推动案件事实向规范事实的转化,也使得构成要件该当性的第一道关卡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在这个阶层的判断中,全面搜集相关证据和对证据进行周延的判断不仅为接下来的违法性和有责性的判断提供裁量基础,而且为犯罪行为的定型和定性提供了素材,同时,“周延性”标准的确立也促进了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细化,提高了“证据确实充分”的可执行性。
阶层性犯罪构成体系不仅为证明标准的细化提供了理论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四要件构成理论的耦合性弊端,不局限于“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定罪思维模式,即其中一个构成要件不具备,则不构成犯罪,同时具备,才构成相应犯罪。这种平面式的思维方式不仅加大了实践过程中的证明难度,更忽略了犯罪构成体系的“出罪”功能,“平面体系的入罪化表明该体系的重点在于对‘可罚性’的重视,而忽略了对不可罚行为建立应有的出罪机制”。⑤ 刘艳红:《犯罪构成体系平面化之批判》,《法学研究》2011年第5期。 明确的阶层性判断,在圈定了“入罪”范围的同时,也梳理出出罪事由,进而为出罪判断提供逻辑进路,更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阶层性犯罪构成理论不仅仅服务于发现实体真实的目标,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实现了证明对象的类型化,每一个犯罪阶层都有不同的证明对象和证明范围,不同的证明对象所对应的证明标准是不同的,这就为证明标准的细化提供了对象基础,也使得定罪量刑的过程更加清晰。
三、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完善进路
最后,有责性阶层的“合理性”判断为证明标准的细化提供了价值指引。有责性之责任确定,不仅仅需要综合考量行为人的责任能力和责任形式,而且需要通过分析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与动机,在心理判断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发现违法行为人的主观侧面。有责性的判断是刑法规范对事实行为涵摄的最后一道关卡,然而“责任是主观的”,如何适当地回应客观行为的先行期待,给事实行为准确地赋予价值评价和主观判断,并且尽可能将主观判断过程可视化、可验证化,需要结合相关的证据进行判断。然而,“你无法看到犯意,甚至最先进的现代技术也无法发现或者衡量犯意”。③ Jerome Hal,General 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Lexis Law Pub,1960,p.106. 因此,在有责性阶层的判断过程中,一定要在“周延”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要件和“实质”的违法性衡量基础上,对行为人的责任性要素进行综合衡量,既不能为了实现高定罪率的绩效考核标准而忽略对主观的审查判断,也不能在其他证据都确实充分的基础上模糊了对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认定。此时,在对证据审查的过程中,“合理性”性标准就显得尤为重要。何为“合理”?合理,不仅要求合乎常理,也要求合乎法理。笔者认为,合理应该是一种中间高度,是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公约数”。因此,应该在客观之中去解构这个概念,综合已经收集到的所有证据进行分析,找出其“入罪”的可能进路,再筛选出这其中的不合理因素进行排除,最终保留下来的判断将会最大程度地趋近真实。因为主观上的明知和故意在实践中很难判断,甚至很难收集到与其相关的证据,仅仅依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难以真正地还原案件事实,因此,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基础上,围绕着何谓“合理”以及何谓“不合理”进行正面论证和反向解析,解释其不同的成因和推进进程。这样点段式地理解主观要素不仅为有责性的判断提供了入罪依据,而且为出罪事由的厘清和选择提供了路径。这种合理性的判断标准为证明标准的细化提供了价值指引,使证明标准在主观方面判断的缺陷得以改善,在不能实现或者不能全部实现主观方面的“确实充分”时,通过反向解构出何为“不合理”来判断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主观方面,即“如果在审查了证据以后,在你脑海里对他实施犯罪仍然存在任何合理怀疑,那么他有权获得你们作出的无罪判决”。④ John H.Langbein,The Origins of Adversary Criminal Trial,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263.James Q.Whitman,The Origins of Reasonable Doubt:Theological Roots of the Criminal Trial,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pp.193.
(一)“主观性”标准的再推进
在司法实践中,因为指控方占据天然的优势,在证据的搜集能力和技术水平上都远远高于辩护方,所以,对于控辩双方的证明标准,我国理论界通说认为,应当采取层次化的标准。② 参见卞建林:《刑事证明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然而,对于层次化的具体操作范式,我国却没有一套明确的规则体系,只是集中于对辩方提供证据的标准可以略低于控方证据标准的表述,司法实践中,辩方证据标准的判断大多数依赖于法官的主观裁量。由于我国法官素质参差不齐,单纯依靠法官的主观判断,难免会造成证据裁量过程中的误差。再加上法院绩效考核标准的普遍运用,使得法官群体倾向于追求案件的定罪率,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法官对辩方提供的有罪或者罪轻证据的“高”标准要求。因此,无论是出于对证据裁量标准的指引,还是出于对目前司法现状的矫正和人权保障的进一步实现,都应该进一步明确“层次化”标准的含义,为辩方寻找出罪进路提供一种方向指引。
(二)“层次化”标准的再细化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明知”是很多罪名的构成要素,但是如何认定“明知”,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有很多障碍。目前,相关机构出台了很多关于个罪的司法解释,已经在不断地梳理对犯罪故意的认定,综合分析这些司法解释,不难看出大多数运用了推定的思维模式。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并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可推定为明知,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行为人实施……,有以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属于上述条款所称‘明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于腐败犯罪案件中的“明知、故意或者目的等要素”,也规定可适用推定。⑥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8条规定:“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所需具备的明知、故意或者目的等要素,可以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予以推定。” 所谓推定,是指基于合乎规律的常态联系,从已经收集并确定的事实中推断出另一事实的推论过程。欧洲人权法院在审查推定时也会考虑三个层面,首先是被告人应当承担的证明范围;其次是这些事项的证明于被告来讲难度的大小;再次是推定的适用对社会会带来怎样的价值和风险。关于推定是否应该被引入刑事证明,目前存在两种态度。有学者认为,应该引入推定,认为推定是一种司法技术方法,基于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和刑事政策的需要,应该被引用;⑦ 参见汪建成、何诗扬:《刑事推定若干基本理论之研讨》,《法学》2008年第6期。 出于人类认知的局限以及对法益的保护,应允许少数情况适用“明知”的推定;⑧ 参见周光权:《明知与刑事推定》,《现代法学》2009年第3期。 推定是一种补充性认定事实的方法,对于无法收集和收集成本比较高的证据可以适用推定。⑨ 参见宋英辉、何挺:《我国刑事推定规则之构建》,《人民检察》2009年第9期。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推定是证明过程的中断,是一种暂时性假定,不具有证明性。⑩ 参见张保生:《推定是证明过程的中断》,《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 推定是刑事证据证明的末位规则,其依赖于客观事实,推定所得结果也是客观事实,但其本身却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思维过程,具有的强烈的主观色彩,在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的转化过程中,其天然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在限制的基础上优化其使用路径,即在客观的事实证据认定过程中,不应该适用推定,推定应主要适用于主观证据的提炼过程之中。在理论和实务上,推定都只能是一种辅助方法,但推定又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问题解决之道。推定可以推进证明过程,推定是双方主体思维方式跳跃过程的呈现,其在充足的基础事实之上积极地创设法律关系以期推导出假定事实,是对证明过程的调整。同时,三阶层的犯罪构成体系也为推定的适用提供了逻辑基础。推定主要集中于对主观方面“明知”或者“目的”的确认,而“明知”或“目的”的判断主要体现在有责性的阶层。如前所述,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是层层推进的过程,只有在完全符合前一阶层的要件之后,才会进入对后一阶层的判断,有责性位于第三个阶层,其是在对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和违法性阶层充分的认识和证明之后的探讨,因此其基础事实是完善且周延的。与四要件平面式地解构和分析相比,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更能为推定的适用提供制度空间和逻辑基础,即在充分且周延的行为构成要件和行为正当性分析基础上的推定,应该更能接近客观事实。并且,推定的主体过程是一种寻找常态联系的过程。何谓“常态”?常态的标准是否仅仅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呢?这可能是我国立法实践中一直没有确立推定制度的重要原因。常态并不是完全不能把握的,笔者建议,建立一个“推定”标准适用数据库,即凡是案件的主观判断过程中适用了推定规则,都应该将推定的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以及推定的逻辑适用详细过程录入数据库,在寻找常态联系的过程中,以数据汇总的标准为主要参考标准,这种推论“主要是基于经验的推论,也就是适合逻辑的复杂化推论,这种推论使事实的确定成为可能”。① [德]卡尔·恩吉斯:《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这样不仅可以为以后的推定提供裁量标准,而且有利于监督法官主观裁量权在推定过程中的过度使用,真正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结合。综上所述,推定的适用使得有责性阶层的主观判断更加清晰,提高了其可操作性,也优化了“主观性”标准的认定路径。
如前所述,阶层性犯罪构成体系的分析范式是一种层层递进的思维方式,在具体的案件分析过程中,通过一层层地判断和认知,逐渐厘清案件事实,因此阶层性犯罪构成体系为出罪的实现在每一个阶层都提供了路径选择,这就为辩护方选择辩护根据提供了清晰的方向指引。辩方可以通过对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诸要素进行判断,找出符合出罪进路的因素,进而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也可以在已经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基础上,直接进入违法性和有责性的探讨,在这两个阶层寻找出罪进路。这样不仅仅可以减轻辩护方的证明负担,使辩护方集中所有精力将辩护事由放在重点之上,也优化了对被告人人权保障的路径。在一个刑事案件中,辩护方提供证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证明被告“无罪”或者“罪轻”,其中,有的是针对指控方提出证据对立性证据,有的是辩护方为了证明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而主动提供的证据。证明“无罪”和“罪轻”是两种不同难度的证明标准,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具体区分出两者的证明标准,才能更好地实现辩护方证明标准的指导性意义。笔者认为,辩方证明标准的细化可以集中在以下两个维度:横向来看,包括无罪证明标准和罪轻证明标准;纵向来看,包括对指控方提供的有罪证据进行的对立性的反驳证据(对立性证据)和为了证明被告人不具有犯罪构成要件要素而主动提供的证据(主动性证据)。考虑到这两个维度具有交叉重合的部分,笔者建议以无罪证明标准和罪轻证明标准作为分析进路,厘清辩护方证明标准的细化进路。根据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的结构,三个阶层的判断是有先后顺序的,构成要件该当性是违法性的前提,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又同时构成有责性判断的前提,每一个阶层都为辩护方提供了出罪途径,每一个阶层的否定都意味着整个行为无法被评价为犯罪行为。辩护方若想证明被告人无罪,在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可以否定犯罪行为、犯罪结果,或者因果关系的存在等;在违法性阶层,辩护方需要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或者有其他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有学者认为正当化事由的数量非常多,而且来自于各种不同的法领域;③ Vgl.C.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4.Aufl.,C.H.Beck,2006,p.648. 在有责性阶层,辩护方需要对被告人的责任能力、主观认知、违法性认识和期待可能性进行证明,这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缺失,都可以有效地证明被告人整体上不具有犯罪性。因此,在无罪或者罪轻证明过程中,针对指控方已经提出的证据,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辩护方只需要证明指控方的证据是不确实或者不充分,或者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即可证明被告人是无罪或者罪轻的。这其中运用的是“反向解构”的思维范式,即当“确实充分”和“合理怀疑”不易从正面进行把握时,人们可以通过反向解构其概念,通过司法解释逐渐厘清何为“不确实”、“不充分”以及“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形,进而使行为出罪。在很多情况下,反向解构可能会使概念更加清晰化和具有可操作性。那么,针对辩护方提出的独立性的无罪或者罪轻证据,又该如何细化其判断标准呢?这些证据是具有独立性的,并没有针对控方的举证,那么这类证据应该同指控方的证据标准相同,只有达到“确实充分”且“排除合理怀疑”才能被法官采信。然而如前所述,三阶层的犯罪构成体系为被告人的出罪在三个阶层分别提供了出罪进路,对任何一个阶层的否定都可以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控方需要结合三个阶层的所有要素,并且在这些要素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时才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是有罪的,而辩护方如果要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无罪或者罪轻的,只需要对一个阶层的某一要素进行否定,例如对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的行为要素或者因果关系要素进行否定,都可以证明其是无罪或者罪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辩护方的证明标准低于指控方的证明标准。
极域多媒体电子教室软件应用方向广泛,根据基础性教学功能的不同,分为多个教学管理系统,能够对综合性教学工作进行深层优化,提高计算机课程教学效率,并有效的对多种教学内容进行分类,确保学生在计算机知识学习阶段,能够有效的对部分基础性内容进行掌握,充分提高学生计算机知识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计算机知识学习意识,改变学生对传统计算机知识学习的基础性认知,提高学生计算机知识学习方面的实践水平。从教学广播技术应用实现在知识题目作答方面的一体化应用,在为师生建立良好沟通管理的同时,也使计算机教学工作的开展更符合实际需要。
(三)“进阶式”标准的再确认
我国目前的刑事证明标准从侦查到审查起诉,再到审判阶段,呈现出一元化的特征,即不同的阶段适用同样的证明标准。这样的做法看似是对证据收集和采用施加严格要求,实际上在实践中模糊了证明标准的指导意义。例如,侦查阶段和审判阶段运用同样的证明标准,直接的后果就是架空审判阶段的质证,如果在侦查阶段已经实现了证据的“确实充分”,那么审判阶段对证据的审查将会流于形式,这也是导致我国多年来“侦查中心主义”困境的根本原因。同时,审查起诉标准和审判标准同一化,也会造成未审先判的怪象,即检察机关在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基础上进行审查,最终提交给法院,这似乎是对“确实充分”的又一次加码,也就促使了庭审阶段对证据的审查更加流于形式,庭审就起不到对证据进行监督的最后一层保障的作用,这也导致了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另外,一成不变的证明标准也不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审查起诉的前提应该是“确认”,审判阶段才应该是根据已经取得的证据作出裁判。侦查阶段的证据更接近于证据的原始状态,而审判阶段的证据是经过反复质证和判断,被赋予规范意义的证据,如果不加区分地用同一的证明标准进行规制,不但不会起到追求实体真实的作用,反而会造成侦查人员、检察官和法官对案件判断的模糊化,看似严格的证明标准会因为其不具有区分性和可操作性,沦为空洞的存在。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要求的提出,庭审的实质化作用越来越被重视,有学者提出,从各诉讼阶段认识活动的本质属性出发,只有审判阶段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活动才达到了“证明”之程度。④ 封利强:《司法证明过程论——以系统科学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 然而,笔者认为,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的证据收集过程也需要依靠清晰的证明标准作为指引,只不过每个阶段的证明标准应该有所侧重。侦查阶段的主要任务应侧重“发现”,不仅仅发现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和事实,也要发现符合刑法规范意义的行为和事实,这样才能为接下来的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圈定基本的判断对象。审查起诉阶段的主要任务应侧重“审查”,是对已经取得的证据的证明力进一步认知、确认和排除,在此基础上最终做出是否提起起诉的决定。当然,审判阶段的证明过程就更应该受到高度重视。审判阶段是控辩两造集中对抗的阶段,也是证据充分展示的过程,在这个阶段中,证据应该是所有主张的实体支撑,即指控方依靠证据打击犯罪,辩护方依靠证据保障人权,法官依靠控辩两造提出的证据作出公平公正的裁判,在这个过程中,证明标准的实质整合性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笔者建议在目前的证据标准基础上,细化进阶式的证明标准,即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的证明标准不仅应该逐渐递增,而且应该有所区分,并各自有所侧重,进而实现证据裁量过程的不断深化,形成更加周密的符合逻辑的证明体系。这样,“进阶式”的证明标准有利于出罪机制的形成。目前我国对各个诉讼进程的证明标准的统一化要求,类似于“四要件”平面式地陈列构成要件,没有逻辑分析,也没有层次解构,无法为出罪机制的形成提供一种制度运作环境。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中的“证据确实充分”是一种单方面的确实充分,其不是在证据展示过程中与辩护方进行充分的辩论质证过程中形成的,而是公安机关或者检查机关为了查清楚案件事实,利用自身特有的公权力优势所获取的,这样的证据入罪功能有余,出罪效用甚弱。进阶式的证明标准并不意味着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不以“确实充分”和“排除合理怀疑”为指导,而是应该梳理出这两个阶段作为审判阶段的基础所应挖掘出的证据的证明标准。综上所述,侦查阶段应在“发现”的过程中侧重“全面”,审查起诉阶段应在“审查”的过程中侧重“有效”,审判阶段的证据证明标准因立足于法庭的调查和辩论,故更容易实现实质整合性的的“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进阶式证明标准的有所侧重,可以节省司法资源,缩短诉讼时间,提高诉讼效率,其指引下的出罪机制的构建,在更高程度上实现了“以审判为中心”改革过程中对人权保障的追求。
四、结 论
诉讼认识的结果只能无限地接近客观事实,却无法完全还原客观事实,我们不能以法律真实替代客观事实,却可以在发现法律真实的路程中,不断找寻符合逻辑性和实用性的工具和标准。犯罪构成是对原始的犯罪事实的分析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找出具有法律意义的案件事实,进而筛选出具有类型化特征的行为,并寻找相关证据进行支撑。从运行机理来看,犯罪构成连接了事实和规范之间的融合,对控辩双方进行规范,实现了证明范围、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的权威性分配。从结构功能视角来看,待证对象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对应是刑事诉讼控辩双方依据证明规则对证据进行筛选的支撑,也是证明规则的实体回归路径。因此,在犯罪构成的视阈下研究证据的证明问题,不仅可以促进刑事一体化的实现,而且有利于刑事证明规则的结构优化和证明标准的细化。在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下,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分析进路和分析对象,每一阶层证明对象及其特征都是不同的,其为我国刑事证据标准的细化提供了方向指引。与此同时,刑事证明制度不仅是用来发现和确认证据种类和证据功能的,而且是为了实现与事实行为的有机衔接。有效的证明标准可以为犯罪行为的实体认知提供路径和方法指引,客观行为的界定和涵括不仅依赖于实体进程,而且需要理清阶段性的判断范围和认知对象,这个过程就是在有效的证明标准指引下进行的。我国目前的刑事证明标准的单一化的存在,使得证据在判断过程中陷入形式化的窠臼,囿于篇幅和能力所限,笔者于本文中只能就其中部分问题进行阐述,并试图通过实体认知的路径为证明标准的细化提供建议。犯罪的客观发现不仅着眼于行为,而且要注重行为背后的证据支撑,每一项行为在进行规范判断之前,都要有充足的证据支撑,否则将不会进入规范判断的阶段。“无罪推定”是刑事诉讼过程开端的价值指引,“疑罪从无”是刑事诉讼结果形成的规范依据,两者都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的重要原则。从诉讼过程开始到诉讼结果形成,证据的证明制度在其中发挥着很重要的推动性作用,一套清晰又具有操作性的证据认定标准非常必要。因此,不断地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操作范式和检验方法,将会对证明过程的完善和保障人权目标的实现大有裨益。
An the Analysis of the Standard of Proof under the View of Hierarchical Crime Constitution
Deng Chao
Abstract: The theory of crime constitution is a tool for modeling and evaluating the criminal fact,with an aim to find out factors with normative value of criminal law in complicated facts,while the criminal standard of proof is used to measure whether these factors violate norms and to scale the degree of violation.Different theories of crime constitution have different guiding functions to the standard of proof.The hierarchical crime constitution system classifies the objects to be proved and has the layer-by-layer logic deduction function.It not only regulates the thinking path to reach a conclusion whether the crime is established,but also makes the standard of proof more inclusive,reasonable and substantial to a certain extent.At the same time,taking the hierarchical crime constitution system as the guideline is conducive to the further advancement of the research on"subjective"standard of proof,which provides institutional space and logical basis for the proof of subjective evidences.It is also conducive to further clarification of the meaning of"hierarchical"standard and provides a guiding direction for the defense to find a way of acquittal.In addition,it helps realize the"progressive"standards of proof in various stages of criminal proceedings,strengthens the enforceability and operability of China's criminal standards of proof,and better achieves guiding function and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function of those standards.
Keywords: Hierarchical Crime Constitution;Standard Refinement;Shape Function;Legal Fact;Improvement Route
中图分类号: DF7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512(2019)05-0152-10
作者简介: 邓超,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江 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