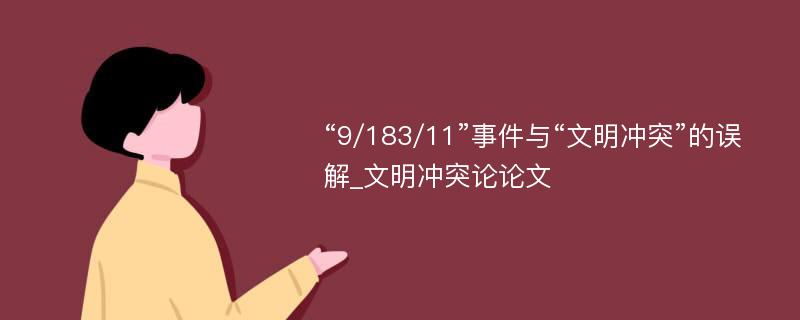
“9#183;11”事件与“文明冲突”的认识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区论文,冲突论文,事件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11”恐怖袭击发生以后,关于文明冲突论的争论又热了起来,一部分人搬出文明冲突论的版本,惊呼文明的冲突已经到来,美国必须作好准备,迎接文明(文化)、宗教战争的挑战。另一部分人则搬出国家主义的范式,指出这决不是一场文明的冲突,而是国家利益和原则的分化组合。另有一部分人指出“9·11”事件是一次严重的对人类共有基本价值的袭击,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是野蛮与文明、邪恶与正义的对抗,反恐战争是一场超越各个文明与文化的国际社会共同的事业。
在这场新的争论中,问题的实质涉及对文明冲突论的理解。同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的情形一样,批评者对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批评有几个重要的误区。澄清这些误区和误读有助于全面准确地解读文明冲突论的主旨和政策含义。概括起来,批评者的误区主要有三点。
1.把文明和国家、价值和利益简单对立。
批评者通常从现实主义和民族国家范式出发,指出文明(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并不构成世界政治的主要内容,民族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行为体,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政治和权力政治仍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内容。批评者最通常的理由是:“不是文明控制国家,而是国家控制文明”。(注:Fouad Ajami,“The Summoning”,
Foreing Affairs,September/October,1993,p.9.)
亨廷顿把以上批评者的意见概括为“国家范式”(statist paradigm),并称之为“虚假的替代性范式”(pseudo-alternative)。亨廷顿认为,这一范式人为地制造了国家与文明之间的对立。亨廷顿认为,用“控制”(control)来界定文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毫无意义。国家只对所察觉的威胁作出反应。亨廷顿承认,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事务中最有力的行为体,但他认为,正如在冷战时期国家属于三个世界中的一个一样,现在国家属于不同的文明。随着三个世界的消亡,民族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标准来界定其认同与利益。
文明冲突范式同国家范式争论的焦点在于文明(文化)因素同利益(权力)因素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实际上也就归结为国际政治行为的根源是什么。国家范式主张国际行为的根源是“利益—权力”因素,而文明冲突范式则认为是文明(文化)因素。这里确实存在着亨廷顿所说的“人为地制造了国家与文明的对立”。亨廷顿的初衷是想突出冷战后文明(文化)因素相对于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文明冲突范式本身是对国家范式的批评和替代,但却并不排斥国家在当今世界舞台的重要作用,并不否定利益政治的本质。亨廷顿想表明的只不过是文化(文明)在界定和认识利益中的过滤作用。亨廷顿说:“人们并不只靠理性活着。只有在界定了自我之后,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时才能理性地筹划和行动。利益政治以认同为先决条件。”(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95页、第252页、第57—58页、第58页、第43—47页、第25页、第26—27页、第88页、第88—89页、第88页、第88页脚注。)由此可以看出,把文明同国家相对立的原因在于把“利益”(interests)和“价值”(values)相对立。多尔(Ronald Dore)批评了这种做法,他说:“将‘利益’和‘价值’区别开来是一个谬误。一种利益只有在被认为有价值时才成其为利益。……在这里,真正应探讨的不是价值和利益的区别,而是像领土、贸易机会这样的普世性价值—利益同特殊的价值—利益之间的区别,后者是某些国家根据其‘文化’所特有而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注:Ronald Dore,“Unity and Diversity in world Culture”,in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eds.,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Socie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410.转引自王缉思:“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春季卷。)陈少明在评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时也作了类似多尔的区分:“人类价值可分为精神(宗教、审美)与行为(政治、经济)两大层次。前一层次可以是特殊的、民族的甚至是个人的,后一层次则是普遍的、全人类的。”(注:陈少明:“利益认同的模式转换”,《现代与传统》,1994年第3期。)
导致把文明和国家、价值和利益、精神和行为、文明冲突范式和国家范式简单对立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混淆了冲突的根源和冲突的结果。许多批评者质疑亨廷顿的常见方式之一就是主张“冲突的不是文明,而是国家”。其实亨廷顿只是指出了冷战后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来自文明的认同和文化上的差异,由这种根源导致的冲突的形式和结果仍然是现存的各种政治组织,主要是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这时实力和权力关系便完全适用了。所以亨廷顿说:“冲突的根源来自文化差异,冲突的结果则反映了权力关系的变化。”(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95页、第252页、第57—58页、第58页、第43—47页、第25页、第26—27页、第88页、第88—89页、第88页、第88页脚注。)在这里,通过权力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亨廷顿实现了文明冲突论范式同国家范式的有机统一。
文明是利益政治的过滤器;文化实体借助政治实体实现自身伸张;政治实体把所归属的文化价值的伸张视为自身的利益。这也正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和政策意义的基础所在。
2.简单地认为亨廷顿忽视了文化的融合和文明的普世性。
批评者认为亨廷顿忽视了文化的融合,以一种静态的观点看待各文明板块之间的差异;还有的批评者认为,他没有看到随着全球相互依存的上升,一种普世性的全球文明已经存在或将可能诞生。
其实,亨廷顿从未否认文明间的交流或融合,也从未以静态的眼光看待文明与文化。亨廷顿认为,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人们可能而且确实重新界定过它们的认同,结果,文明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各民族的文化既相互作用也发生着相当大的变化。正如有贸易才有贸易战一样,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当然也是以文明的接触、相遇、碰撞作为前提的。亨廷顿认为,在文明互动的历史中,正是相互交往的扩大强化了人们的认同。“随着贸易、通讯和旅游的增长扩大了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日益赋予其文明认同以更大的重要性。”(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95页、第252页、第57—58页、第58页、第43—47页、第25页、第26—27页、第88页、第88—89页、第88页、第88页脚注。)“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其特征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明的社会的和其他模式的相互依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这些模式的广泛意识),文明的、社会的和种族的自我意识加剧了。”(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95页、第252页、第57—58页、第58页、第43—47页、第25页、第26—27页、第88页、第88—89页、第88页、第88页脚注。)这也正是文明冲突论的逻辑前提。
针对那些认为一个普世性的文明已经存在或将要存在的批评意见,亨廷顿把它们归为“不现实的替代性范式”(unrealistic alternative),并且鉴别了这种普世性文明的三种形式:(注:Samuel P.Huntington,“If not Civilizations,What?-SamuelHuntington Responds to His Critics”,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1993,pp.186—194.)
(1)认为苏联共产主义的跨台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自由民主在全球的胜利。亨廷顿认为这种看法犯了“唯一性选择”的谬误,忽视了世界的多样性和各种宗教力量。
(2)认为不断扩大的交通和通讯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共同的文化。但亨廷顿认为相互作用同时也会强化既有的各种认同,引发对抗。
(3)认为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具有同质化效应,从而产生了一个类似20世纪西方文化的现代化。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文化,像日本、新加坡和沙特这样的国家是现代的繁荣社会,但分明是非西方式的社会。那种假定现代化会使非西方人变得“像我们一样”的想法本身即是文明冲突的例证。
某些相信普世性文明(文化)的批评者产生误解的原因还在于对文明(文化)的语义使用上的混乱。亨廷顿界定了普世文明这一术语在使用中实际上能够指代的四种误区。(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95页、第252页、第57—58页、第58页、第43—47页、第25页、第26—27页、第88页、第88—89页、第88页、第88页脚注。) (1)首先,在所有的社会中,人类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
(2)“普世文明”一词可以指文明化社会所共有的东西,如城市和识字,这会使它们区别于原始社会和野蛮人。
(3)“普世文明”一词可以指亨廷顿称之为“达沃斯文化”(Davos Culture),因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达沃斯召开而产生的各国的精英文化的同质性。
(4)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但亨廷顿认为这些只是些缺乏重要文化后果的技术或昙花一现的时尚,并不改变文化本身。
的确,某些批评者之所以相信某种普世性的文明存在或即将存在是陷入了以上语义上的误区。亨廷顿所说文明(文化)的要素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95页、第252页、第57—58页、第58页、第43—47页、第25页、第26—27页、第88页、第88—89页、第88页、第88页脚注。)“文明既根据一些共同的客观因素来界定,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也根据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界定。人们所属的文明是他们强烈认同的最大的认同范围。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各
种他们”。(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95页、第252页、第57—58页、第58页、第43—47页、第25页、第26—27页、第88页、第88—89页、第88页、第88页脚注。)在以上各种因素中,亨廷顿特别强调了宗教的因素在进行文明(文化)分类中的关键性作用。
在对普世性文明的观点进行批评的过程中,亨廷顿又一次架起了权力同文明之间的桥梁。亨廷顿认为,当今并不存在普世性的文明,“普世性文明只能是普世性权力的产物”。(注:Samuel P.Huntington,“If not Civilizations,What?-Samuel Huntington Responds to His Critics”,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1993,pp.186—194.)“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95页、第252页、第57—58页、第58页、第43—47页、第25页、第26—27页、第88页、第88—89页、第88页、第88页脚注。)亨廷顿借用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硬权力”与“软权力”的论证,说明软权力只有建立在硬权力的基础上才成为权力。(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95页、第252页、第57—58页、第58页、第43—47页、第25页、第26—27页、第88页、第88—89页、第88页、第88页脚注。)亨廷顿认为,正是由于现代化过程中本土文化的伸张,促使人们把自己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的增长归因于本土文化的优越性,所以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所带来的非西方社会权力的日益增长,正导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95页、第252页、第57—58页、第58页、第43—47页、第25页、第26—27页、第88页、第88—89页、第88页、第88页脚注。)正是立足于以上逻辑,亨廷顿批评“那些认为一个普世文明正在并且一定会出现的人们,以及那些认为西方化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的人们,几乎普遍忽略了权力和文化之间的联系。他们拒绝承认,其论点的逻辑需要他们支持西方扩大和巩固其对世界的控制,而且如果其他社会能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它们就会恢复旧的信条、习俗和实践,而这对于普世主义者来说是有碍进步的。然而,那些为普世文明的优点辩护的人,通常不为世界帝国的优点辩护”。(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95页、第252页、第57—58页、第58页、第43—47页、第25页、第26—27页、第88页、第88—89页、第88页、第88页脚注。) 正是因为注意到了权力与文化的关系,亨廷顿才为当今西方非西方之间均势的变动感 到忧心忡忡,并呼吁西方社会内部强化自身独特性的认同,加强自己的团结,保持自己 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优势地位,迎接非西方的挑战。这正是文明冲突论的政策意 义所在,也是权力同文化关系的聚合点。
3.许多批评者产生误解的根源在于忽视了亨廷顿一生学术思想的连续性。
同许多批评者的意见正相反,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恰恰反映了亨廷顿学术思想的连续性。这一连续性的核心是根深蒂固的反理性选择理论和保守现实主义的取向。自50年代以来,在亨廷顿著作中就一直体现了他对理性选择理论的鄙视,他一直强调要把人类本性中的非理性和文化因素作为既定的和想当然的事物加以接受,并作为决策的假定前提。亨廷顿还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保守的现实主义者。他信仰保守主义,并承认自己是一个老式的柏克主义(Burkeian)的而非现代的里根主义(Reaganite)的保守主义者。他的现实主义立足于其反理性选择论的基础之上。他相信尼布尔关于“人性罪恶,必须用强硬手段维持秩序”的信条,并把这一信条称为“道德同务实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原则。亨廷顿还继承了尼布尔的那种悲剧式的敏感性(tragic sensibility),即虽可被认作一个狂热的冷战分子,但尼布尔却从未陷入道德上的必胜信念,他相信历史更多的是反讽而不是进步。卡普兰认为,尼布尔主义中的这种悲剧敏感性构成了亨廷顿主要著作的主线,同时也是理解亨廷顿保守主义的关键。(注:Robert D.Kaplan,“Looking theWorld in the Eye”,The Atlantic Monthly,December,2001.)亨廷顿认为,外交政策并非是建立在法治之下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基本上是无法治可言的领域中的国家或其他组织相互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从50年代起便一直以一种最富悲剧色彩和最悲观的方式主张美国加强自身军事与情报能力,以便保护自己。(注:Robert D.Kaplan,“Looking the World in the Eye”,The Atlantic Monthly,December,2001.)
正是这种亨廷顿式的保守现实主义加上反理性选择理论铸造了文明冲突论的灵魂。文化与认同的决定性意义,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而非普世性,文明冲突中权力和均势对冲突结果的最终裁决权,所有这一切都由亨廷顿学术思想连续性的两个核心要素而引发,并最终回到同样由这两个要素所界定的文明冲突论的政策意义:即西方应加强自身的认同,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保持优势,促进基于文明共性基础上的合作,以继续在可能到来的非西方对西方的文明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要做到这一点,西方的核心国家美国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亨廷顿对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上升感到担忧的主要原因。在这里,亨廷顿的保守主义色彩特别浓厚。他极力呼吁美国强化其传统上单一的主导文化,其核心是欧洲传统、基督教、英语、新教价值。
“9·11”事件之后,亨廷顿多次谈到文明冲突论的适用性,认为文明冲突论并没有过时。在2001年12月的一次访谈中,亨廷顿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世界,有许多人仇恨我们的富有、权力、文化,积极反对我们劝说或强迫他们接受我们关于人权、民主、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的努力”。美国不应当再抱着文化普世性的观点不放,在文明和种族冲突正在凸显的世界上,美国必须认识到世界被文化和文明分割的事实,“学会区分哪些是同我们同甘共苦的真正朋友,哪些是同我们只有部分共同利益的机会主义的盟友,哪些是同我们有复杂关系的战略伙伴和竞争者,哪些是我们仍能进行谈判的对手,哪些是我们必须首先摧毁的残酷无情的敌人”。但与此同时,亨廷顿又委婉地提出,人们并不愿意使用文明冲突的提法来指称实际是由文明差异导致的冲突。他认为西方应当谨慎地避免使反恐成为一场文明间的战争,否则就正中了本·拉登的下怀。美国应该聚焦于残忍的恐怖主义本身,组建跨文明的反恐联盟。亨廷顿还进一步重申了他在文明冲突论中所提议的政策建议,他认为,美国还要利用反恐这一机会来完成两件事:第一是把西方国家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第二是以一种更现实的态度理解其他国家对世界的看法。(注:Robert D.Kaplan,“Looking the World in the Eye”,The Atlantic Monthly,December,2001.)
在2001年10月22日发表的一篇访谈中,亨廷顿认为拉登已向西方文明宣战,但恐怖行动同时也唤起了文明的认同,正像拉登试图通过宣战动员穆斯林一样。他同时也重新赋予了西方一种共同的认同感和保卫自身的使命感。他建议美国和欧洲必须实现更大程度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一体化,并且协调他们之间的政策,以免其他文明利用西方内部的分歧;要继续扩大欧盟和北约至中欧,把拉美西方化,接受俄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的安全利益和合法性,并联合它一道打击恐怖主义;要保持西方在军事上和技术上的优势,遏制伊斯兰和中国的军事力量。他同时警告说,西方要认识到干预其他文明的内政在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中是唯一最具危险的全球冲突的根源。(注:“Global Viewpoint”,Oct.22,Los,Angeles Times Syndicate International,a Division of Tribune Media Services.)
可以看出,亨廷顿的结论仍然是文明冲突论的一贯基调。他认为,恐怖主义的根源仍然是非理性的文明(宗教)的差异,但恐怖主义的结果和危害则在任何国家都被视为犯罪行为,对恐怖行为作出反应和参与反恐联盟的则是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或其他组织。但是在“9·11”事件之后,文明冲突论又有了新的发展,即针对非传统安全因素的上升,文明冲突论的政策意义在两个层面上深化了。第一,加强西方自身的凝聚力的同时,还要构建跨文明的反恐联盟,反恐应当成为一项世界性议程,这是对传统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的超越。第二,反理性选择的意味加重了。恐怖主义问题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个人和小团体在国际政治中的回归。个人和小团体已经拥有了国际政治结构上的力量。个人和小团体的非理性文化和心理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文明冲突的复杂性。恐怖主义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因素,反恐战争作为一场非对称战争,国家变得更加脆弱,构筑安全的任务加重了,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预防性防御的要求凸显出来。
从“9·11”事件之后的美国国内思潮来看,确实反映了保守主义的上升这一事实。多数的民众在面对反恐同开放社会、法治社会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矛盾时,倾向于把反恐和安全置于优先次序。从“9·11”事件之后的美国政策来看,确实反映了亨廷顿的政策建议的适用性。首先美国谨慎地避免使反恐战争成为一场文明的战争,刻意淡化恐怖主义同伊斯兰之间的因果关系,着力构建反恐联盟;其次,美国大力加强自身本土的安全,由于未来的威胁可能出自不可预料的来源,美国把其注意力从追踪和防范固定的威胁转向防范和监控现有的杀伤性能力的资源,以确保它们不会落入“邪恶”国家和恐怖分子手中。
从文明冲突论的实质和政策建议看,有人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称作“披了文明外衣的现实主义”也就毫不奇怪。同时还应看到,文明冲突论即便是许多人的思想根源,但由于美国和西方政治文化中怕犯政治禁忌,人们还是不愿明确使用这一字眼,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决策层刻意避免产生这一印象。但“9·11”事件产生的根源,美国和西方大众文化中保守主义思潮的上升和其他文明中反美和反西方情绪的滋长都说明,有效地管理文明和文化的冲突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紧迫议题。
标签:文明冲突论论文; 亨廷顿论文;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塞缪尔·亨廷顿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范式论文; 政治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