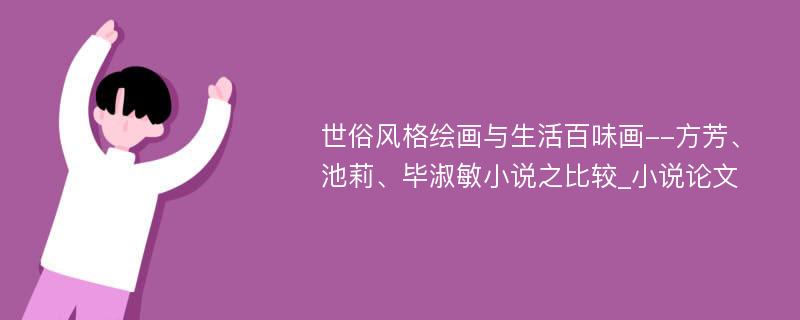
世俗风情画,人生百味图——试比较方方、池莉、毕淑敏的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情画论文,世俗论文,百味论文,人生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中国小说界活跃着一支女作家队伍,她们的作品绚丽多姿,异彩纷呈,令人难分轩轾。本文仅就为广大读者所瞩目,常有新作问世的方方、池莉、毕淑敏的小说,从比较的角度发一点管窥蠡测之议。
先谈谈她们创作上的共同点:
第一,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是平头百姓、市井小民,她们把这些“芸芸众生”庄重地请进了文学殿堂,并对他们倾注了无限深情。用彩色画笔描绘百姓们的悲欢离合,摹写小民们的酸甜苦辣;写他们历尽坎坷,说他们奋力挣扎;写他们心火不灭,说他们坚韧不拔。
方方多描写装卸工人忍辱负重和艰难跋涉,和知识分子的窘困与倔强。池莉擅长刻画工人,职员和市民的形象,叙说他们的苦恼、彷徨和追求、进取。毕淑敏前期小说反映戍边战士的生活,近期小说则描写市民在商海中弄潮。她们没有把小人物写得灰不溜秋、可怜巴巴,而是有火有光,有雷有电,一个个挺直了脊梁。
第二,三位女作家都严格忠实于生活,取材都真实可信。她们都基本上采用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创作方法,当然并不排斥借鉴一些新潮流派的表现技巧。
出于她们是写普通人的生活情景,所以选择的都是司空习惯的琐屑小事。本来这样的内容最易平淡无奇、枯燥乏味,但在三位女作家笔下却平地陡起波澜,芝麻粒榨出了香油。事情虽小,意义却不小,即所谓见微知著,“一粒沙中看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作家通过对这些琐屑事件的“煎炒”,烹饪出人间生活的百味。
方方的《风景》是一部长江码头工人有血泪也有欢笑的历史,她对七哥曲折经历和倔强性格的描述,使人产生万千感慨。《祖父在父亲心中》记录了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在不同的历史道路上留下的迥然有别的脚印。
池莉的《烦恼人生》中,印家厚所遇到的烦恼,不就是现实社会中普通人诸多困扰的写照吗?当然也是他们渴求心态平衡的折光。《太阳出世》写出人们灵魂的净化,思想的升华,由庸庸碌碌到勇于进取。
毕淑敏的《阿里》中的女边防战士热爱高原,自愿来到艰苦的地方饱餐风雪。为了使神圣的自卫战争获得胜利,她宁愿忍辱含垢,毅然献身。《女人之约》反映在改革大潮中工人的觉醒,她以兴厂为己任,不怕吃苦,不怕伤身,勇敢挑起讨债的重担。
秤砣不大压千斤,钻石虽小值连城。三位女作家写的是生活中的小小涟漪,却可以令读者听到长江、黄河的奔腾;写的是道路上扬起的灰尘,却可以让人们看到历史前进的脚步。文学要不要反映时代?三位女作家已经作出了回答。
第三,三位女作家对于小说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有极其精致细密,韵味十足的摹写。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历如绘,作品里浸透着浓郁的有特色的地方风味。读着小说,那浓得化不开的乡情乡韵,始终缭绕在人物周围,使读者宛如置身于江城喧闹的街巷,或风雪弥漫的高原军营。
方方描写的汉口“河南棚子”,那狭窄的木屋,潮湿的地面,拥挤的床铺,缭绕的烟雾,使人如临其境。池莉描写的汉口花楼街居民,那特有的姿势、气质、心态、脾性,说话象吵架,吵架似夜叉,真是入木三分。毕淑敏描绘了昆仑山、阿里环境的艰苦恶劣,使读者仿佛看到高原上暴风雪的肆虐,听到荒野里恶狼的嚎叫,感受到在空气稀薄中气喘吁吁。
三位女作家当然也有各自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彼此迥然有别的描述方法和写作技巧。
首先谈谈她们在题材的采撷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各有高招,各有所长。
方方多写城市装卸工的生活。这一领域过去几乎无人涉及,在方方的笔下却展示出一幅幅生动活泼的图画。《风景》一家九口人挤在简陋而狭窄的“河南棚子”里,演出了何其有声有色,有笑有泪的人生悲喜剧。《桃花灿烂》中的青年装卸工该有多么丰富细腻,柔肠百结的感情。
方方所塑造的人物中颇具特色的是《风景》中的七哥,他是一个自我奋斗的强者,但七哥所走的道路有异于常人,在一般的小说中是看不到的。他为了摆脱贫困和低下的地位,选择了一条自己营造的蹊径:依靠妻子的力量跃上仕途的龙门。为了实现飞黄腾达的梦想,他找了个年龄偏大,相貌平平又不能生育的高干之女为妻,而抛弃了热恋多年,年轻美貌,情投意合的女朋友。当那个老姑娘问他:“假如我父亲不是省委的部长,你会爱我吗?”七哥回答得很坦率:“如果你没有任何毛病,你会想到要嫁给我这个没有地位没有钱财的平头百姓吗?咱们是各有所求,你又何必非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七哥没有用甜言蜜语来哄骗她,而是小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七哥为了能当官,为了离开那又脏又黑又低矮又潮湿的“河南棚子”,他付出了代价:牺牲了爱情和子嗣,他的奋斗目的是达到了,但其中也有难言的苦涩。方方对七哥的行径只作冷静客观的叙述,并无褒贬之意。七哥不属于传统文学中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然而七哥类的人确实是客观存在,是方方发现了这样的典型,将他放置于文学的画廊。
方方所写的人物多是悲剧的结局。但方方式的悲剧多是人物自身性格的悲剧。如栖和星子的爱情悲剧是他们自己酿成的,并没有什么邪恶势力在作梗。七哥的结局(他虽然住上了小楼,坐上了汽车,出入于豪华宾馆)也应该是悲剧性的,这也是他不顾一切千方百计要改变处境的顽强性格所致。七哥的行为或多或少有点象《红与黑》中的于连。但于连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他是以爱情为诱饵不择手段来向上爬。而七哥却有自我牺牲并不伤害别人的特点,方方有借鉴,但更多的是创新。
恋爱,婚姻,家庭是女作家们擅长的题材,由于大家都挤在这条胡同里舞文弄墨,就不免撞车,大同小异。然而池莉却能挥笔杀出重围,开辟一条写爱情题材的新路。
《太阳出世》是池莉的得意之作。这篇小说题材小得不能再小,然而开掘之深刻令人意想不到。写一对青年工人夫妇生下一个女儿,作为人父人母的小赵和小李顿感自己责任重大而神圣,他们发誓要把孩子培养成栋梁之材,父母当然应该作出表率。于是两人决心一改落后,愚昧、浅薄、骄横,浑浑噩噩,庸俗无聊的面貌。男的在百忙中考取了业大,女的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知识。他们的精神面貌大变样,变得连他们的父母亲都感到认不出来了。作品充满了耀人的温暖的光辉,表达了对新生活的热情赞美。过去有谁把生孩子这样的芝麻粒琐事,列入小说题材?那简直不可思议。而池莉却能把它敷衍成中篇,处理得妙趣横生,体现出池莉在题材选择上以小见大,平中见奇的风格。
与方方的悲剧性小说不同,池莉的小说多是喜剧性的,小说的结尾都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尽管生活中并不都是鲜花开放,但池莉却弹奏出春天奏鸣曲来为生活歌唱,在叙述中不乏风趣,在字里行间时不时出现幽默,使作品充满了春意融融的气氛。这就是池莉的风格。
以西北边防战士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不算少,但多是讴歌主人公不畏自然条件的恶劣,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奋斗精神。毕淑敏也瞄准了这个题材,却不走这条轻车熟路。她选择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反映戍边女战士的服役生涯,跳出了雷同的窠臼。《阿里》是一篇与众不同的小说。女主人公游星是军区司令员的女儿,她之所以自愿来到高寒缺氧的阿里当兵,不为别的,就因为她父亲对她说过:“阿里是一句古藏语,意思是‘我的’,或者是‘我们的’”。这一段话一下子就把游星那淳朴真挚的爱国之情毫无摭拦地展示在读者面前。游星一天夜晚同一个地方男青年乘吉普车兜风未能按时回营,违犯了军纪。协理员关了她的禁闭并且开除她出党。恰在这关键时刻,游司令员亲临阿里指挥自卫反击战。游星完全可以借此机会向父亲申诉委屈。然而她却假装失足落井而自殒了。死前留下遗言:“弄脏了井水很抱歉,我不愿意随着狮泉河水葬身异国。”很显然,游星不打算在保卫阿里的战斗即将打响的时候干扰父亲的指挥和分散父亲的精力。在游星心中,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她宁可舍弃生命,撇下年迈的父亲,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死,但她死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这种新颖大胆的,别开生面的写法,令读者瞠目结舌,一时甚至难以理解,经仔细琢磨后才为之茅塞顿开,不禁为作家的巧妙而独特构思,石破天惊迂回曲折的安排而拍案叫绝。这就是毕淑敏在创作上左冲右突的风格。
改革的题材挺热门但很难着笔,作家们多写厂长如何雄才大略,扭转乾坤。而毕淑敏却绕开厂长把眼光投向工人。《女人之约》中青年女工郁容秋自揭招贤榜,为工厂去讨债,历尽艰辛将帐索回,而她累得住进临终关怀医院。在弥留之际,郁容秋并不后悔,只是盼望女厂长履行诺言:向她鞠躬致敬。可是厂长却自食其言,她遗憾地离开了人世。这篇小说与其说是歌颂一个女子舍己为人,不如说是为改革事业呼吁破除偏见,不拘一格重视人才,这样它的主题就显得深刻,时代感强烈。
毕淑敏也多写悲剧,与方方式悲剧相比,是有区别的。方方式悲剧是对人生的叹息和对历史的反思,显得深沉凝重。毕淑敏式悲剧则体现出雄浑壮美,如同普罗米修斯的殉道。悲剧人物多是女性,突出了她对妇女问题的关注。
其次作家不同的风格也表现在刻画人物的方法与技巧的差异上。
方方往往把人物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刻画,主人公性格的展示是通过他同社会环境的不断抗争或较量来表现的。池莉常常选择人物在婚恋中的矛盾来描写,这种“杯水风波”却能显示人物的光彩。毕淑敏总是把人物置身于艰苦恶劣的环境中,使主人公产生剧烈的思想动荡和行动措施。方方刻画人物善用反衬对比,池莉则让她的人物同对立面相龃龉。毕淑敏将人物置身于“黑云压城浊浪排空”的环境中,使她顽强的搏斗,拼命地冲击。方方的小说不重故事的编织,而以突出人物的性格为目的。池莉的小说写的都是日常生活琐事,却有引人入胜的内容。毕淑敏的小说则有娓娓动人的,波澜起伏的情节牢牢吸引读者。
营造好的细节,对刻画人物大有帮助,方方写七哥小时候睡在潮湿黑暗的床底下,还被哥哥们踢来踹去,反映他在家里所受的非人折磨。池莉写赵小兰去买磁带,说:“我要冼星海的天鹅湖”,表现她的无知。毕淑敏写郁容秋临终时,手里一直握着从外地给女厂长捎来的纽扣,一直盼望厂长来看她。写出郁容状诚实守信,心地善良。这些精彩的细节是作家生活的丰富积累,是人生长河里涌出的朵朵璀璨浪花,是风格这株树上结出的漂亮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