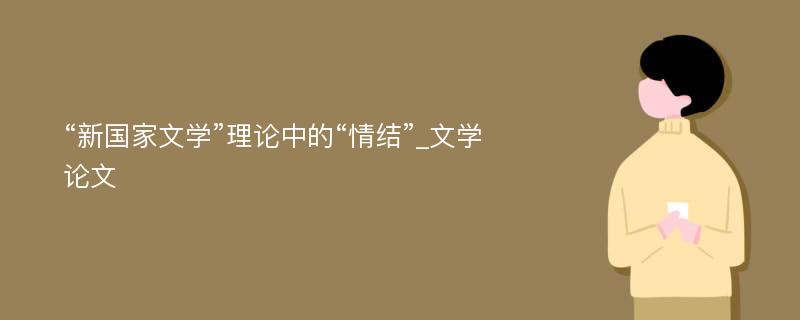
命名的“情结”——“新状态文学”论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情结论文,状态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去年以来,由几位颇富才情的青年批评家率先举旗,在几家很有影响的文学刊物的参与下,沉寂许久的我国文坛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热点”——关于“新状态文学”的讨论。
“新状态文学”论的提出者和倡导者们已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座谈纪要、作品评论,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而持反对态度的论者也发表了一些意见,但相比之下并不很多,更不系统;文学理论、批评界更多的人则保持沉默或冷淡。因此,目前“新状态文学”论继续在一个应者寥寥的比较小的圈子内流行:倡导者依然在积极地鼓吹,冷淡者依然视而不见、置之不理。
笔者拜读了有关的一些讨论文章,有一些未必成熟的想法,特提出来就教于有关方家。
一
首先,我很佩服“新状态文学”论的倡导者们的学术敏感和理论勇气。
文坛进入90年代之后,确实悄悄地在发生着许多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变化愈益明显。前两年已经有一些敏锐的批评家在一些作家的新作中感受、体验、发现了某些与以往不同的因素,并在批评中予以初步的揭示。但是这种发现与揭示大都是局部的感性描述或就作品论作品,很少有跳出具体作家、作品,从宏观的全局角度予以理论上的把握与概括的。“新状态文学”论的提出和倡导者们显然棋高一着,他们一开始就站在较高的起点上:他们不拘泥于对几部具体作家作品细微的审美感受和读解,而是从中国市场经济发育带来的社会和文化转型出发,把90年代我国文学的发展放在一个广阔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加以重新审视;他们不满足于就作品论作品,而是从整个中国文坛、作家的变化的现状中来把握文学的“新状态”;他们不停留于研讨90年代的文学现状与发展态势,而且也注重对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回顾与反思,通过历史与现状的比照来揭示“新状态文学”的新特点;他们也不局限于对当前中国文学的思考,还关注在东西文化交流日益深化的前提下,把“新状态文学”论与他们的“后新时期”、“后现代主义”文学论联系起来研究。因此,他们的立论就有相当广阔的文化视野和一定的理论深度。这是“新状态文学”论问世以后比较引人瞩目、产生一定影响的主要原因。
应当承认,“新状态文学”论的倡导者们,理论上确实比别人更为敏锐。他们常常能在文学的变化刚刚开始在地层深处萌发时,已经听到了岩浆的涌动,并及时地提醒人们注意;而且,他们善于借鉴、吸收西方文化(包括文学理论、批评)的新话题、新概念、新思路,以最快的速度创造性地应用于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实际操作中,往往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因此,他们常常能领导文学理论、批评新潮流,在相对沉寂的文坛上制造出一、二个热点效应。“新状态文学”的讨论就属于这种情况。它毕竟给冷清的文坛带来一点刺激,注入一点生气与活力,无论对当前文学创作还是批评、理论都会有所促进。为此,我们应当感谢“新状态文学”论的倡导者们。
也应当承认,“新状态文学”论确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在我看来,这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90年代文学,特别是部分小说创作,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同于80年代的新特点。“新状态文学”的倡导者们列举了一些新、老作家的作品,如王蒙的《恋爱的季节》、刘心武的《风过耳》、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张承志的《心灵史》、朱苏进的《接近于无限透明》,以及何顿、陈染、马建、韩东、张昊、海男、鲁羊等新一代青年作家的一些作品为例证,对这些作品的特色作了一些分析与概括。应该说,其中一部分对作品的感受、领悟、读解是相当细腻、准确的,评论与概括也是相当精辟、独到的,确实很敏锐地觉察并把握了90年代以来部分作家作品中显露出来的不同于以往作品的若干新特点,如指出90年代部分小说既不象“新写实小说”那样完全站在一个外在视角,以“零度感情”纯客观地描述对象,也不象“实验”、“先锋”文学迷恋于文体、语言的形式探索,而是以一种不经意的自由状态,自然而充分地呈现经作家自我体验的当下生存状态流;又如有的论者结合对若干作家作品的剖析,强调它们的个人性、精神性话语的凸现,指出作家以自身个体的当下情感形态(包括私人性、隐秘性的状态)投入写作,使作品带有浓重的自传性。这种感受与概括,同他们所分析的一些具体作品,确实有不少吻合之处,说明他们的审美感觉十分灵敏,能在许多人还未引起注意之时,已经发现并予以描述、揭示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新状态文学”论倡导者们将上述部分90年代小说出现的新特点自觉地与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转型这样一个大背景联系起来,努力揭示其中的必然联系。他们认为,90年代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生巨大变化,一是国内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新经济体制已初具规模;二是国际上“冷战后”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及利益关系的调整,导致中国文化的转型:如雅俗文化的分流和多样化,纯文学从中心向边缘转移,实验文学与新写实小说受到冲击和冷落,80年代文学的“启蒙”与“寓言”“神话”的破灭及紧步西方后尘的“模仿”的终结;与此同时,作家受到的外部强制与自我心理障碍却也大大缩小,写作的选择性与可能性迅速增大,文学反而获得了解放与超越、并贴近文学本体的契机。这就造成了文坛与作家的“新状态”,进而形成了“新状态文学”。这样的论证有一定的说服力,其思路从社会、文化大背景着眼,来揭示、阐述文学出现“新状态”的原因与必然性;理论视野相当开阔,的确可以自成一说。
第三,“新状态文学”论的倡导者们都兼备良好的艺术感觉和较厚实的理论素养,同时,他们又是80年代新时期文学批评、理论队伍中的重要成员或“过来人”,对于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实际了解较深,其中有的成员还对新时期文学向90年代文学的过渡与“转型”起过推波助澜作用,譬如对转型时期“新写实小说”的命名与鼓吹。这样,他们心中就有一杆对八九十年代文学进行历史的对照与比较的“秤”,就能说出一些比较切实、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见解,不完全是空对空的纯理论推演,也不是较琐碎的对具体作品的感想、议论。因此,“新状态文学”论的提出,本身还是严肃认真的,是经过反复思考的,而且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一定的启发性,至少可以成为一家之言;也因此,“新状态文学”论提出后,获得了理论、批评界一定的反响,有持批评立场的,也有持赞同态度的,更有受到启发加以发挥补充的。
一个理论,如果得不到社会的任何反响,那么它很难存在下去;“新状态文学”论,不但获得了一定的反响,而且在文学理论、批评界引起较多的关注,并形成小小的“热点”,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
二
然而,如果对“新状态文学”论的倡导者们的发言、论文细细加以研究的话,人们就会发现,它在理论上是很不严谨的,逻辑上亦存在不少自相矛盾之处,概念上相当模糊混乱,尤为重要的是,它同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与实际有很多不符之处。它在总体上给人一种用先验的命名强加到90年代文学发展的现状上的感觉,显得很勉强,因此,基本上不能成立。关于“新状态文学”论在理论上的不当和失误,我想主要谈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新状态文学”论即使用以概括其倡导者们所列举的数量十分有限的那些新、老作家作品的“新”的共同特点,也显得捉襟见肘,牵强附会,顾此失彼,难以自圆其说。譬如朱苏进的中篇小说《接近于无限透明》,表面上看,确有点象“新状态文学”论的倡导者所总结出的那样具有某些特点,如“个人性的话语之流越来越倾向于自身的拟传记的书写方式”,以呈现“私人性的、隐秘的状态”。但实际上,小说通过“我”在儿时与精神病人李觉在住院期间的一段交往,以及现在与濒临死亡的所长李言之(可能即李觉)的微妙关系,深入到人的心灵的幽深处,认真而深刻地探讨了人的生与死、正常与病态、清醒与疯狂等一系列具有人类普遍性的哲理课题,向人们发出了“什么是合理的人类生存状态”、“人应当追求怎样的人生”、“生与死的意义与价值何在”等一系列诘问,体现了相当的人性深度与对人的终极关怀,因此,说小说从审他转为“自审”,消解了象征与隐喻,只努力表现“个人性的精神深度和凹度”,显然是不符合小说实际的。小说虽然说不上有新时期某些作品的“民族性深度”,却有着不亚于这种深度的“人类性深度”和“人文精神深度”,这可以说是新时期“深度模式”的一种延伸和发展,而并非对“深度模式”的背叛与抛弃。王安忆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是“新状态文学”论者又一部引为“经典”的津津乐道的作品,他们认为这部小说“完全是‘自审’”,其中一半有关家族的寻根史“已丧失了象征的历史感与民族感,完全是小说家自身智力冒险与语言游戏的载体”,另一半是作者自身成长史,完全是“自身当下状态”的“没遮拦”的“书写”,“不再是那种隐喻性的文学思维的产物”。这同样是令人难以苟同的。小说的写法确实比较琐碎,特别是写自己成长过程那一半,颇有点婆婆妈妈、唧唧哝哝,但是我们阅读后感到的决非只是个人性的自传和私人性隐秘的无拘束的流淌。小说这一部分用笔虽十分随意,常有点幽默乃至俏皮,但却时时注意交代或点明时代背景、环境氛围,无论是解放前从曾外祖母、外婆到母亲的生活经历的回忆,还是解放初随母“打着腰鼓扭着秧歌进入上海”,或者“文革”时期风风雨雨,连细节描写都很逼真,因此,这部分“纪实”写的虽只是“我”与一家的经历,却也真实勾勒出一个出身于破败的大户人家的女性从孤儿到参加革命,其女儿则从一个红旗下长大的中学生经历“文革”沧桑,终于成长为知名作家的、具有一定典型性的大家庭的历史。这个家庭在近百年中国社会发展中虽然极为平凡普通,却也因其平凡普通而与千千万万的普通家庭有着共同的经历,因而就有了相当程度的普遍性。小说自然并未着意渲染这种普遍性,却在看似随意抒写个人经历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写出了一个大家庭的深刻的历史变动,而在这变动背后则倚托着中国的、民族的历史变动的大背景。因此,硬说小说丧失了民族感与历史感,而仅止于个人性的自身当下状态的书写,恐怕有悖于小说实际。至于小说虚构部分的“寻根”,从一开始就明确宣示了作者“将一个象征意味变成现实的方式”的“思路”:以“诗意”方式“追根溯源”,从茹姓联想起“那一大片无边无际的茹草波动起伏的情景是多么壮观而优美”,由此追寻到古老的柔然部落,“柔然是一个立马横刀的游牧民族”,“柔然的兴亡将带我到广阔的漠北草原,那里水土肥沃,日出日落气势磅礴,部落与部落的征战刀枪铿锵,马蹄得得,这给我生命以悲壮的背景。”作者并鲜明坦率地承认:“追根溯源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选择,还是一种精神漫游”。小说另一半寻根正是这样一种选择和精神漫游;而作者的选择显然是按上引那种悲壮、广阔、磅礴的气势和基调来展开想象和虚构的。这种史诗般宏壮的追寻与勾沉为近百年“我”的家族兴衰提供了一幅惊心动魄的历史背景,同样体现出作者不满足于个人性隐秘的娓娓倾诉,而选择了具有历史沧桑感、民族感和悲剧感的史诗格调。所以说,王安忆作品更趋成熟了,但王安忆还是王安忆,她并未失落其社会、民族的深度模式。从我们对上述两部“新状态文学”论者视为“经典”性代表作的分析可知,“新状态文学”的概括首先缺乏实践的、事实的根据,它仅根据少数作品的表面特征就匆忙作出判断或概括,然后拿来硬套其他作品,把并非真正具有他们所概括的特点的作品硬塞进“新状态文学”的狭小框子里。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决非明智之举。
其次,90年代更大量的纯文学作品,是“新状态文学”论者们所未提及的,它们中有不少优秀之作,如张炜的《九月寓言》、陈忠实的《白鹿原》,张承志、刘恒、苏童以及一批新生代作家的作品,都很难用“新状态”来加以概括,“新状态文学”论者们概括出的一些所谓“特点”很难套到他们的作品的头上。而如果把他们90年代以来许多力作排除在外,则奢谈90年代中国文学的“新状态”、“新趋势”便显得十分软弱无力。
再次,“新状态文学”论的倡导者们自己对“新状态文学”似乎也显得认识模糊,概念不清。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们对“新状态文学”的范围心中无数。一开始,他们对“新状态文学”从文坛的新状态、作家的新状态和文学的新状态三个方面来研讨和界定,而搞得很宽很大,似乎90年代文坛上一切新的现象都可纳入“新状态文学”讨论的范围,这样人们就觉得“新状态”无所不包,过于宽泛,也就没多少意义了。而谈到“新状态文学”的创作实际时,几位倡导者也力图加大其普适性,不仅讲小说,而且讲散文,讲诗歌,似乎一切文体都进入了“新状态”,他们甚至呼吁文学批评“也应走向自己的新状态”,但到后来,具体探讨“新状态文学”的特征时,他们又只谈小说,不谈其他文体,实际上不知不觉收缩了“新状态文学”的范围,准确地说,“新状态文学”论变成了“新状态小说”论。可见,倡导者们自己对“新状态文学”的范围本身并无定见,或者说,他们主要是从小说中感到了某些“新状态”,就急急忙忙想把这种想法推广、扩大到其它文体上去,以便提出一个囊括范围更大、更有宏观气派的大概念、大命题。第二,他们对“新状态文学”的界定也不太明确,他们之间的论述也不尽一致,有时同一人前后的说法也有不统一之处。这不能不使人感到疑虑:“新状态文学”论的倡导者们在提出这一理论时究竟是否经过深思熟虑?譬如有人说“新状态文学”“不是一种创作手法,也不是一种主义,它是社会文化的转型给创作带来的一种转折机制”;又说90年代一些作家作品“体现出的一种新的面貌”或“总体面貌”,他们“称之为‘新状态’”;又有人说,90年代市场经济与文化转型,必然造成“文学创作出现新的趋势,即新状态文学”;还有人认为,90年代进入多媒体、信息化时代,中西交错的现实及电视体系、文化工业的挤压,逼得文学作出选择,“进入新状态”,即“呈现状态”。如此种种说法,叫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第三,关于“新状态”之“新”,他们的说法也模糊不清,令人难解。有人说,共时性使人无法区分新旧,“新状态”之“新”是打引号的,“它并不表明一种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对立”,而只是表明这是当下时代的当代文学。当代文坛正在从有序状态回归到一种无序驳杂的自然状态”,“新”的含义大约即这种“自然状态”吧;有人则认为,这“新”主要是作家身份调整与改变,作家走向“边缘化”,从“仰视”西方、“俯视”本土到“平视”生活,文学写作“正是把这种新的空间状态表达出来”;还有人说“新状态”指写作的“新的参照系”,为回归自己、回归文学而写作,写真实的自己的当下体验,这就是“新状态”;还有的说得更神秘莫测,说“新状态”是不可拆解为“新的状态”的“一个词”,“新状态文学”是一次“倒计时”,不可与“莫须有”的“旧状态”对立,而是“表现为对过去时代的一次悲剧性告别”,真是说得玄而又玄,叫人莫测高深;同一位论者,在另一场合却堂而皇之地宣布“新”状态小说是对80年代小说的一次“革命”,这不是对“旧状态”的一种反拨吗?这样一个含义不清、又过于宽泛的概念,怎能担当概括90年代中国文学发展新趋势的重任呢?况且倡导者们说法不一,又有点玩弄词藻之嫌,使人觉得“新状态”一词在此处似乎成了飘浮在半空的一种“不能承受之轻”。
又次,即使纯粹从术语与命名角度看,“新状态”一词也过于普泛、过于一般。以汉语的习惯,“新”只能作为形容词修饰“状态”,而不可能与后者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单词,更不可能不相对于“旧”而单用“新”。无论其倡导者们如何解释、赋予它以特别涵义,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在汉语使用的当代语境中这种常规意义是约定俗成的,非一、两篇文章能改变得了的。而“状态”一词含义尤为普泛,与新写实之“写实”,新感觉之“感觉”、新体验之“体验”等诸种文学现象都不一样,它可以成为每种文学写作状况之显示,到处适用,而缺乏特定内涵;同时,“状态”一词往往与“过程”相对立,它表示的是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段内的事物的状况,这无论从物质状态还是人的精神、心理状态来说都是如此,因此,用一个仅适用于很短时段且变幻不定的概念来描述、概括整个90年代这样一个较长时期、复杂过程的文学现象,显然是很不合适、很不恰当的。所以,即使纯粹从语言、修辞角度看,“新状态文学”这一概念也缺乏科学性,因而难以为公众所认同和接受。
当然,我们注意到“新状态文学”论现在也有了一批追随者。但是,我们同样注意到,多数支持“新状态文学”论的朋友,在理解和阐述上与提倡者们的看法并不很一致,有的甚至很不一致。如有人对“新状态文学”的提法持保留态度,而对“文学新状态”的提法表示赞同,而对“新状态”涵义的解释更为宏观,指“面临世纪之交的文学的组合、变异、趋向等”,是一个“关于文学格局的综合态势的概念”,表示“传统的回归,多元的融合”,具体指“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融合”,这就与“新状态文学”论倡导者们的看法大异其趣了;还有人干脆把“新状态文学”阐释为“开放”的文学;如此等等。这样,“新状态文学”论,还刚刚奏响,就已经走调变音。这种情况是耐人寻味的。
三
从上面分析可知,“新状态文学”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很难成立的。那么,它为什么会出现并在一定范围内被“炒”热呢?我想原因主要在于一部分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心中存在的“命名的情结”。
“命名”的情结其实倒不是什么新玩意,也不是什么中国的特产。远的如古希腊哲学家们为世界本体寻找水、火、土、气、数、存在等各种命名,或为中国古代孔夫子的“正名”说,老子把世界本体命名为“道”等等,都显示出古代先哲们的“命名”情结,这里不必多说。单就我国80年代以来学术文化界来说,“命名”的情结就十分强烈。特别是1985年全国范围的“方法论”热,在吸收西方学术研究方法和移植自然科学方法的热潮中,新方法伴随着新观念蜂拥而至,也纷纷进入文学批评、研究领域,于是理论家、批评家们的“命名”欲望大增,采取中西嫁接、移植加创造的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名词、新术语,以至于到80年代末期被另一些理论家嘲讽为“新名词的狂轰滥炸”,“新术语的大换班”,即使他们也曾或多或少参与过这种命名活动。
这种命名的欲望从80年代末以来虽然有所减退,但并没有消失,在一部分人的心中仍然十分强烈。这就是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随着实验文学、先锋文学的退潮,所谓的“新写实文学”、“新感觉小说”、“新体验小说”等半有实践支撑,半靠“命名”推动接踵而来呈现于文坛的重要原因。这些创作现象并非全无根据,但坦率地说,至少有一半是理论、批评家通过“命名”方式鼓吹出来并“炒”热的。象“新写实小说”,当初就由一些批评家借助某些文学刊物集中,推出并给以“命名”、予以吹捧和阐释的,然后,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流行和承认。但是,迄今为止,“新写实”已退潮,还有些被封为“新写实小说家”的人自己并未承认这种外加的封号。“新状态文学”正是这种80年代以来理论、批评界“命名”欲望和情绪继续延伸的产物。
“新状态文学”论的倡导者不仅是“新状态文学”的命名者,而且是一系列“后”字号的命名者,如“后新时期”、“后现实主义”、“后殖民主义”及其文学等。“后新时期”是以90年代文化转型为标记划出的不同于80年代“新时期”的另一个时期。“新状态文学”的命名可能就是与“后新时期”的命名相配套、呼应的。问题在于,这种分期与命名究竟主要是从实际出发的,还是人为制造、强加于现实的。
在我看来,近一、二年一系列“后”与“新”的命名,总的说来,来自于现实情况的概括的成分较少,主观匆忙地超前命名的成分较多。换言之,“命名”与现实有较大的脱节。如果说,前几年“新写实”一类命名还具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的话,那么最近这一系列“后”与“新”的命名,特别是“新状态文学”的命名就显得现实依据越来越稀薄,主观想象、臆测的成分却越来越浓重。这样一种命名,往往是命名者对当下文学中若干似乎是新的现象稍有感觉,马上迫不及待地加以提炼概括,寻觅若干例证,其间还往往有意无意地加以夸大与普遍化,进而大张旗鼓地予以命名,推向文坛。而当命名者发现其命名与许多现实的文学现象不甚相符时,又自觉不自觉地对这些现象加以“误读”,将它们改造成“命名”可以囊括的东西,然后也纳入命名的范围中来。这种命名策略明显地带有主观先验设定名称,用概念来限制、框定现实的人为制造倾向,是与科学的实证精神相违背的。
这种命名的先验性、主观性,源于一种焦虑的文化心态。明明现实中还未提供充分的依据,就急急忙忙出来命名,并力图用命名来调控文坛的发展走向与趋势,这是一种浮躁心态的表现。而在浮躁背后,恐怕还未能超脱急功近利的动机。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确实出现了重大变化,文化上也处在转型的过程中,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这种社会的变动,并非同步快速地反映到文学上来。文学创作当然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但这是不能与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同日而语的。当前中国文学的发展一方面是多元的;另一方面是渐变的,与80年代文学很难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而且这种发展变化目前尚在进行中,虽然出现了一些过去没有的新特点,但也只限于局部范围,很难用以概括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更难预测整个90年代中国文学的未来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匆忙地把一些刚露头的,前景未卜的文学现象、特点加以夸大、凸出,并用“命名”形式凝固下来,反过来去限制、框定正在发展的文学现实,显然是削足适履、本末倒置。命名者的意图,据我推测,首先当然想形成热点,以推动当前文学与批评的健康发展,这个用意无疑是好的,但效果未必佳。其次,也不能排斥有个别人想藉形成热点之际,形成新的文学批评中心与权威,以指导中国文学与批评的发展。他们一方面反复声称作家、文学批评家90年代已退出“中心”,日趋边缘化,而且认为继续想保持“中心”地位简直是一种“神话”,但从他们一而再、再而三起劲地在文艺界大搞超前的、先验的命名活动的实践看,其背后似乎仍有重返“中心”的情结在作祟。也许这是妄测,但愿也是妄测。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命名情结背后,隐含着一种人文精神和价值的背离与失落。综观“新状态文学”论者们的观点,他们在将“新状态文学”与80年代文学作对比时,最强调的是,“新状态文学”宣告了80年代文学“寓言化”、国家和民族“寓言模式”的终结,而走向个人化、私人化的当下情绪体验和状态的随意显现。他们认为,80年代的作家处在“中心化”时期,有“代言人的身份,具有启蒙者的地位”,是“精英式的知识分子”,其写作是“制造寓言”,“热衷于寓言模式的创造”,“对国人担负着全面灵魂塑造的重任”;而90年代的“新状态文学”,则消解了这种“寓言模式”,也“排除任何功利价值的主导性”,“新状态”作家有闲暇来关心自身的生存状态……他们不必以自己的写作去对应整个民族的生存,一种摆脱政治文化干系的小说家正在诞生,他们……不需做社会的良知、生活的治疗者和灵魂的工程师,因此不必微言大义影射万千,不必向社会提供象征性的真理。他们有时间也有理由为自己写作了”,这就是所谓“新状态”的“知识分子叙述人的诞生”,同时也“宣告了知识分子神话、启蒙神话、人道主义神话、蓝色文明神话这些‘新时期’表象与灵魂的死亡”。很明显,“新状态文学”论者们扯起“新状态文学”大旗,寻找了、或更确切地说强拉了一批貌似“新状态文学”的作品为例证,目的是要消解80年代文学对民族生存和社会的责任感,取消作家对人民精神、灵魂塑造和引导的使命感,把文学引导到纯粹个人、当下的随意、即兴的情绪宣泄的道路上去。在我看来,这并不是文学的进步,而是倒退,是文学和批评的价值迷失,是80年代发扬、培育起来的人文精神的遗弃与失落。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的转型,当然会引起文学与文学家的变动,但这种变动不应以抛弃人文精神与价值为代价;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民族的良心、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金钱的诱惑比过去政治的压抑更需要人文精神圣火的点燃与引导。如果“新状态文学”论命名和鼓吹的“新状态”意味着人文精神圣火的熄灭,那将是最为可悲的;如果“新状态文学”命名者倡导的是一种反人文精神,一种置民族生存、社会前途、国家命运于不顾,而沉缅于对纯然个人当下的杯水风波的情绪宣泄中的“新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其实一点也不“新”,不过是中外文学史上曾出现过的标榜“自我表现”的文学在当代的翻版而已!
“新状态文学”论还在发展中。其“命名”的成败最终还得由实践来检验。上述看法仅为个人浅见,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