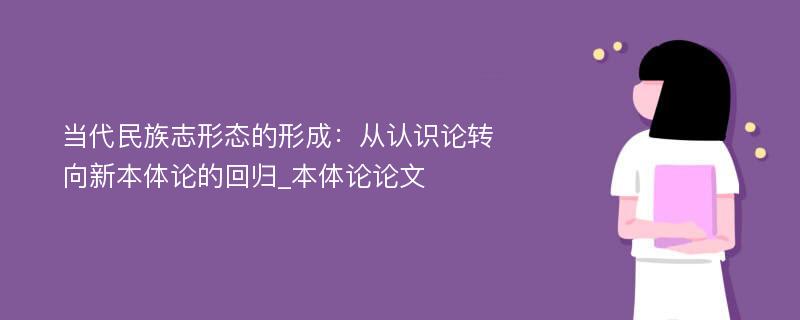
当代民族志形态的形成:从知识论的转向到新本体论的回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论文,到新论文,形态论文,当代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有国家对民族志的理解都是一样的。它是[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初级阶段:观察和描写,田野工作(fieldwork)”。①然而,民族志并非一成不变,它得到过不同国家不同学者的不同定义,总体形貌又有过数度改变。与过去一样,当下民族志有着它的时代特征,而关于这一特征为何,身处其中的学者有各自的解释。如后文将重点解释的,当下越来越多学者将这一特征形容为“本体论转向”。②在本文中,笔者以这些特征的由来为线条,③素描出当下民族志形态的历史样貌,同时对这一形态进行具有自我倾向的评论。 一、民族志:一种人文科学方法的出现 在欧亚大陆这个广阔的地域中,在诸古代文明板块(尤其是印欧,特别是欧洲,以及闪米特—阿拉伯、华夏)上,相近于民族志的“文类”,早在上古时期就与博物志一道出现了;之后,这些文明板块所涌现的旅行记(含与远征有关的记述及诸如朝圣行纪之类的记述)、方国—贡物志也带有后人说的民族志色彩。然而,民族志却特指一种人文科学方法,它的名号是近代学者据古希腊文综合改造而成的,用以形容一种近代史上再创造出来的“认识”与“文类”。民族志既指研究的过程(田野工作),又指研究的成果(作为志书的民族志)。 作为人文科学方法的民族志,有了相当科学性的早期实践,出现于19世纪中后期。此前,启蒙运动给欧洲带来文明和进步的观念,随后,德国出现文化论,法国出现关于进步的“科学研究”,英国出现诸多文明论述,圣经学者对创世纪作出了新解释。在19世纪中后期,不少传教士对民族学问题产生兴趣,而民间古物之研究也演变为民俗学,接近体质人类学的论述也得以提出。在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地,出现了民族志类的记述,进化论思想得以系统论述与传播。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蛮荒中人”与欧洲“文明人”之间到底属于祖孙关系还是属于异—己关系,再度得到关注。④ 对于19世纪的人类学(正是在这门学科下,民族志得以系统阐述),人们的主要批评是,那时的代表之作都是根据探险家、商人、传教士、移民等所写的“业余民族志”和史料写就的,人类学家自己是书斋中的学者,不做民族志研究,也不写民族志。这些代表之作,如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的《原始文化》、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的《金枝》及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古代社会》,体现了古典人类学家的这些“性格特点”。然而,如一位民族志史研究者指出的,19世纪还是存在着不少民族志研究: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摩尔根对易洛魁人的研究,80年代库兴(Frank Kushing)对祖尼人的探究、波亚士(Eranz Boas)对因纽特狩猎—采集人的研究,90年代斯宾塞(Baldwin Spencer)对于澳大利亚土著的研究,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里弗斯(W.H.R.Rivers)对于托达人的研究。⑤这些古典人类学家的民族志研究,各有所长:摩尔根擅长对社会组织、仪式、政治、社会变迁的观察,且最早具有参与观察的精神;库兴最早用土著语言展开调查,且重视土著宇宙论调查;波亚士田野工作比较肤浅些,但在搜集故事和文献方面,功夫极深;里弗斯对于亲属关系谱系的研究法则形成了富有启发的经验。 “做民族志”似乎始终是人类学家的理想。19世纪人类学兴起之初,一些人类学家已基于田野研究书写了一批重要的民族志;尽管泰勒和弗雷泽没有机会做民族志,但在19世纪70年代积极为英国民族志调查手册的设计出谋划策,⑥也积极鼓励学生从事民族志田野工作。 到20世纪初期,民族志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与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这个名字紧密相连。1914年至1918年间,马氏在西太平洋进行民族志田野工作实践,并于1922年开始发表一系列民族志文本。从他的工作过程和撰述看,这位人类学家所做的民族志,综合了19世纪民族志的几乎所有优点。马氏有摩尔根的参与精神和对社会结构的兴趣,有库兴般的宇宙论研究素养,而马氏对波亚士那样的故事、文献整理专长及里弗斯(马氏相当直接地受此师长的启发)那样的谱系学研究法,也充满兴趣。在田野工作中,马氏研习土著语言,活跃于他们的生活之中,努力从土著的观点理解土著文化。这些工作行为,日后成为民族志田野工作的程式。对理论概括有浓厚兴趣的马氏,还赋予民族志撰述以思想价值,他的民族志描述细致入微,但却总是充满着现实和思想关怀。⑦在其最著名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他借助大量民族志细节论证了经济不能摆脱社会而独存的论点;这个观点,既影响了许多同道,又影响了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波兰尼(Karl Polanyi),波兰尼的“嵌入”概念即主要来自马氏的民族志。⑧ 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与书写,一方面有里弗斯的方法学铺垫,⑨另一方面,还有在他之前早已进入其研究领地的前辈的“业余民族志”基础。⑩致力于创新的马林诺夫斯基通过再综合、再思考,给予民族志方法学规则富有开创性意义的展示。此外,马氏还培养出大批学生,他们多数从事具有民族志性质的工作;其中,后来开启了牛津大学民族志风气的埃文思—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写出《努尔人》(11),这是一部堪称20世纪民族志最高成就的著作。马氏的影响范围波及美国,使波亚士的文化人类学研究风格退居二线;更波及东亚、南亚、非洲与法国,对这些地区的社会科学研究之革新,起到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1850年前后的美国人摩尔根,到1920年的波兰裔英国人马林诺夫斯基,经过70年的时间,现代民族志的传统得以建立。(12) 民族志成熟于20世纪上半叶。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14-1945),民族志迅速成长;此间,有了田野工作法、文本构成、比较价值的系统论述,在此基础上,民族志拓展了研究的地理区域覆盖面。在英国人类学界,学者们长期在大洋洲从事研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们拓展了“领地”,进入非洲、印度和中国研究领域;(13)在美国,若干著名大学与英国学界保留着关系,深受英国民族志工作风格的影响,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转向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其中包括中南美洲、环太平洋地区、南亚等地,不再局限于北美印第安人研究;(14)在法国,在马林诺夫斯基民族志时代到来前后,带有浓厚民族学旨趣的年鉴派社会学家们,采纳从民族志研究得来的结论,并对之加以归纳、综合、比较,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社会理论,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社会理论渐次回馈于民族志,使之得以丰满。(15) 二战后,美苏“第一世界”地位居高不下,势力与观念形态之地理覆盖面随之推展。在美国,民族志在文化人类学之下工作,在苏联,则在民族学中工作,有各自的研究“地盘”;在其“地盘”的覆盖范围内,被研究民族已渐次建成“民族国家”(第三世界的“新国家”),他们为了国族建设,已经培育出研究自己社会的民族志工作者;(16)而两个超级大国的民族志研究者,则主要还是在“他者”中进行研究。由于“冷战”,位于第三世界的众多田野调查地点,对外来学者关门,使身处“第二世界”的优秀人类学家丧失了从事实地民族志研究的机会。但也正是由于这一遗憾,英法人类学家获得了开拓民族志新视野的机遇,他们有的通过民族志素材的综合比较提出新见解(如牛津大学和曼城学派人类学家的比较政治制度研究和“冲突理论”,(17)及法国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18)),有的对民族志的做法提出新的看法(如剑桥大学利奇提出的“过程理论”(19))。与此同时,第一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激发了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之间的相互观望和刺激。在苏联社会科学研究者致力于批判地梳理“资产阶级民族学”的线索之同时,美国人类学界出现了受苏联民族学启发而致力于复兴进化人类学的重要努力,在这些努力中出现的“多线进化论”与“生态人类学”都实属重要的创造。(20) 二、民族志:本体论到知识论的转向 到20世纪70年代,民族志身后已留下一条拉长了的背影;这一背影里,从帝国到“新战国”(指作为民族国家时代的20世纪上半叶),再从“新战国”到阵营对垒的世界格局转变,历史情境出现根本变化,民族志的研究和书写方式不免随之产生改变。然而,这些方式的变化,似都未曾改变它自出现之初便已表明的主张:从具体地方入手,由外而内,进入“社会事实”的内里,并将之与外部环境(自然与历史地理环境)相联系。 为了建立社会科学客观方法,涂尔干(Emile Durkheim)曾把“社会事实”定义为“物”,并表明,这一定义意味着:“在着手研究时,要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对事实的存在持完全不知的态度;事实所特有的各种属性,以及这些属性赖以存在的未知原因,不能通过哪怕是最认真的内省去发现。”(21) 若说哲学上的“本体论”(ontology)是指对存在者的本质和“真实”的要素的思索,那么,涂尔干对于作为“物”的“社会事实”的定义,便可被理解为一种对人的社会存在的“真实”的本体论认识。这一本体论认识可以理解为一种区分与融通的辩证,它先在作为认识者的“我”与被认识者的“物”之间划出一条界线,以“分离物我”,而后,又要求认识者暂时悬置“我”(尤其是“内省”的我),使之进入“对事实的存在持完全不知的态度”的“无我之境”,而沉浸于“物”(“社会事实”)中,对“物”所指的作为事实的“宇宙人生”,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在物我之间达成社会与知识的汇通。涂尔干的这一论述是19世纪末才提出的,但之前的民族志研究者,却早已暗自实践着其所概括的研究取向,(22)20世纪到来之后,它更得到人类学界的广泛认同。 对于什么是“事实”,民族志书写者产生过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它是可见的行为本身及规范行为的制度,有的认为,它犹如涂尔干所说的“集体表象”,是集体的宇宙论和人生论的观念体系;对于民族志试图复原的“事实”到底是一种秩序,还是一种被秩序化的冲突,他们也产生不同看法,有的(如功能主义者与结构—功能主义者)把民族志反映的“现实”形容成如“桃花源”一样的“和谐社会”,有的(如冲突论者)则反之,认为人间的“乱”必定是“治”的前提。另外,不同民族志书写者之间也常产生有关被研究地方的地理与历史处境问题的不同研究取向:功能主义者、结构—功能主义者、文化论者,多视其民族志描绘的“世界”为与历史和外部地理场合有清晰界限的社会体或文化体;传播论者、过程论者和结构人类学家,倾向于在田野地点周围更广阔的地理空间里寻找“社会事实”内涵的来源;而进化论者、政治经济学派人类学家则倾向于将民族志田野地点放在古今人类史的广阔时间视野下加以解释。 不同学者之间对于作为“物”的“社会事实”有不同的评判,且带着这些评判赋予作为民族志对象的“社会事实”以各自的含义。然而,在视“社会事实”为“物”,以对之加以客观研究这一“方法的准则”上,他们之间没有异议。 至于民族志到底是科学还是人文这个问题,历史上的众多民族志书写者似乎也并不存在过多争议:无论是受涂尔干影响的社会人类学家,还是受波亚士影响的文化人类学家,多数倾向于兼容康德(Immanuel Kant)与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所代表的两种对立而同构的因素,并蓄科学与历史、自然与人文、规范与思想等不同立场。(23)在学科存在的大多数时间里,他们中曾有不少人反复提及“科学”两字,用以表明,民族志是一种不以答案而以问题为出发点的,不以学者生活中形成的观念形态为情感偏向而以审慎的归纳和推论为判断前提的“科学研究方法”。然而,在实际的调查研究过程中及撰述中,很少民族志书写者隐瞒从客观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所具有的道德的、政治经济学的以至世界观的和人生观的丰富含义。若这些含义因具有主观性而可被界定为与“科学”不同的人文思想,那么,那时的民族志便已可谓是一项不缺乏历史、人文、思想内涵的工作。正是这样一种既科学又人文的研究姿态,容许了一些具有反思性倾向的民族志书写者将自身的作为界定为人文主义的。埃文思—普里查德将民族志解释为一种接近于历史的人文学、一种以自己的语言翻译别人的文化的工作;(24)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将民族志定义为一种“浓厚的描述”,认为描述充满研究者田野之所见的“细枝末节”,有“科学”的所有特点,但并非局限于“科学性”,它主要陈述被研究人群的“精神”、“世界观”,但其中也兼有研究者的主观看法。(25) 20世纪70年代,来自几个方向的挑战,冲击着民族志的这些固有特点。首先,在“冷战”尚未结束、后现代主义尚未流行的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界出现了对民族志与殖民主义之间密切关系的批判性研究,(26)这些研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它们揭示出作为观念形态的现代民族志书写如何由其政治经济基础(近代殖民制度)所决定。与此同时,一批致力于第三世界研究的欧洲学者提出依附理论,(27)以之解释“现代化”如何将第三世界化为发达国家的附属地带。至20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直接进入美国社会科学界,并渐渐在其中获得广泛接受;在它的影响下,新一代人类学家对帝国主义缔造的“现代世界”与在其支配下的“他者”之间关系进行了批判性研究,这些研究,即已引发对于民族志描述的怀疑。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进而在“破”了20世纪前期的民族志三原则(经验论、整体论及相对论)的同时,“立”了将民族志撰述中的“他者”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关联的近代世界史研究模式。(28) 从20世纪70年代起,法国继结构主义之后出现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其中,不少著述从知识论(epistemology)的不同角度介入现代性的研究;(29)解构主义,及与之相联系的其他法兰西思想,传到英语世界后,成为另外一些理论,(30)这些理论,起着破除“现代派民族志”的“科学”体制与“结构”观念的作用。在英语世界,在引进法兰西人文思想之同时,从苏联引进文艺理论,一时也成为潮流。随之,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对话、狂欢、复调等源于文学研究的概念,(31)成为社会科学家赖以替代“科学民族志”的“社会”、“文化”、“结构”概念的东西。 若后现代主义者玩味过涂尔干关于“表象”即“事实”的论点,他们也许便能理解,自己展开的批判性论述,只不过是将“表象”概念施加在知识者身上,指出其为“社会事实”的本质。(32)然而,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后现代主义,似乎对此不假思索。 后现代主义民族志论述得以确立的前提有两个:一个前提是,到20世纪70年代,人类学界的新一代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思想潮流和法兰西式的话语解构与知识—权力理论推导出一种将权力与知识、知识与观念形态相联系的观点,并将之施加在过往民族志研究的构成上,揭示这类研究与西方对非西方的支配之间存在的关系。这个前提进而与1978年出版的赛义德(Edward Said)《东方学》(33)一书相结合,成为民族志批判者借以考察学术与政治关系的方法。另一个前提则是文学批评,借这种批评(其中显然也借重了前面提到的巴赫金的文艺理论),后现代主义者可以把民族志文本等同于小说来解读,通过这样的解读(尤其是通过揭示这类文本缺乏作者第一人称的特点),揭开民族志的“科学面具”,(34)指出“科学报告”与小说一样有虚构。 后现代主义民族志的批判性论述的确是有着明确的新异之处,它反对被运用一个多世纪的“客观方法”,认为现代民族志知识体系的建立,是为了支配其他社会,为了通过政治经济支配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因此需要在文本形式上有所伪装(在文本中清除作者的“我”字,便是伪装的手法)。有这样的主张,后现代主义者便既不能接受涂尔干关于作为“物”的“社会事实”的论述,又不能接受波亚士从康德与赫尔德哲学里综合引申出来的科学—人文研究态度了;在他们眼里,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被研究者,都是有主观意见、情绪和偏见的“人”。他们提出的观点,带有浓厚的知识论色彩。 所谓“知识论”,研究的是知识的本质,可以指作为集体表象的物我关系,也可以理解为研究者的“表象”。在知识论转向(亦即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前,民族志书写者能涉及知识的前一种含义,即被研究社会共同体的“社会知识”,但他们极少想到他们自己的民族志知识到底有什么本质,这些知识又到底是否反映“真相”。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代思考者一反他们的前辈的“常态”,将精力集中于思考民族志知识(及它的文本表达方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而总是得出一个结论,这种知识的本质是权力,因而,不具有其所宣称的“客观性”。 三、民族志:新本体论的回归 在现代主义(本文中即指自19世纪中叶起形成的民族志方法的总体取向)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一条界线,它区分着两种处理“物”与“词”(35)关系的方法:在现代主义那里,叙述者的言辞与被其加以民族志描述的“对象物”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距离,但民族志工作应旨在尽研究者之所能缩小这一距离(如,通过学习马林诺夫斯基的做法,采纳“土著概念”对“土著”的生活和观念世界进行解释);在后现代主义那里,这一不可避免的距离,事出有因,是在“我者”的认识论背景(现代性以来的“词”与“物”的分离术)中形成的,因此,克服它带来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使民族志不同程度地“回归于我者”,对其词物分离术加以反复辨析和不断批判。 持后现代主义观点的论者并非是只破不立的“破坏主义者”,在对“词”“物”分离术加以批判之后,其中一些也设计出若干具有建设性的民族志计划。这些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为三个人物所代表,他们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马尔库斯(George Marcus)及泰勒(Steven Tylor)。他们在大的主张(后现代主义民族志)上有一致意见,但提出的具体方案却不尽相同。紧随拉宾诺(Paul Rabinow),(36)克利福德主张将民族志改造成跨文化对话过程的记录,认为,作为研究过程,民族志本就是代表“本文化”的研究者与代表“异文化”的被研究者之间对话的过程,因此,作为志书,民族志若不反映这个过程的本质内容,便不“真实”,若以“科学”来形容我们的调查研究,那就等同于将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一笔勾销了,民族志应反映田野过程中的各样声音、各种故事,并使自身成为“寓言”。(37)马尔库斯主张将民族志改造为基于“异文化”研究经验展开的文化自我批评,尤其是对近代西方世界体系的自我批评。(38)泰勒则对后现代主义者自身尤其爱好的“表述”(representation)一词发难,认为这个概念等同于说明还是有“事实”存在,而对书写者而言,民族志的对象世界除了不可知的一切之外,仅存一些书写者可以主动“召唤”(evocation)的观念,这些观念的总特征是,它们与“我者”的理性存在巨大不同,将之“召唤”出来后,“我者”可达成对自身的理性的批判。(39) 这些主张并非毫无价值,至少,它们能使学者在认清民族志“形势”(其与“我者”的生活与观念的关系)的情况下,富有“文化自觉”地定位自身。(40)然而,在将民族志导向“我者”的“寓言”、“罪恶”和错误观念(如纯粹理性)的自我剖析过程中,它们存在着将民族志改造为漠视“其他人”的内省术;其最终的结局可能是,“词”替代了所有“物”,成为覆盖以致磨灭世界(“物”)的秩序,而这正是被后现代主义者们奉为圣贤的法兰西新旧结构主义者所不愿看到的。 后现代主义内化于一个悖论:一方面,这些批判者坚持一种知识论的泛权力主义观点,并时常以之批判作为现实的民族志文本;另一方面,为了赋予民族志的“我者”以良知,他们在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划出一道供自己穿越的绝对界线,这条界线,实有极端相对主义的色彩。(41) 后现代主义者将对立的“我者”与“他者”概念施加于民族志史的认识上,将历史上存在过的研究都一一描绘成“我者”与“他者”之间对话的过程;殊不知无论是“我者”还是“他者”,都不是纯一的,研究者们相互之间存在着经验与心态上的诸多差异,而被研究者更是分布于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人文世界的“人”。而在认识实践中,现代主义民族志书写者向来不可能真的落实所谓的“我他二分法”。一如法尔顿(Richard Fardon)指出的,回到民族志研究的历史现场便可以知悉,研究者从来没有二分的“自我”与“他者”关系圈定;相反,他们的研究和书写,首先是针对在不同区域生活的不同的被研究群体展开的,为了对所去往地区进行深入研究,研究者除了要了解学科的一般性论述之外,还要费更多心思了解相关于所研究地区的既有民族志文献和它们的解释。这就使研究者既要与有特定地区的人群产生关系,又要与研究同一地区的民族志作者产生关系。从民族志升华理论的工作,正是在两种关系的关系中进行的,它久而久之孕育出几个“民族志书写的区域传统(regional traditions of ethnographic writing)”。这些区域传统,有内部的关系机理,但相互之间也存在观念上的交流对话,在交流对话中曾涌现一些影响力超出其所研究的特定区域的概念或理论。一言以蔽之,“不同民族志叙述之间弥漫着明显的或隐晦的相互参照关系,这些参照关系既存在于学者所研究的地区内,也存在于不同地区之间”。法尔顿的这些观点,是在其主编的《地方化策略:民族志书写的诸区域传统》一书的长篇导言中表达的。(42) 这本1990年苏格兰学术出版社和斯密松年研究院联合出版的文集,收录了14篇来自不同民族志区域传统的论文。(43)这些论文的作者,绘制了一幅民族志的“世界地图”,展现了西方人类学中担当主角的几个地区,包括“狩猎—采集区”(分处南北半球的爱斯基摩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亚撒哈拉非洲(苏丹、埃塞俄比亚、西非、中南非洲、东非)与美拉尼西亚区”及“亚洲区”,该书主要涉及中东、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印尼、日本的民族志。 《地方化策略》叙述的“区域”,不是美式“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意义上的区域;(44)后者之设置,意在通过社会科学的学科综合促成区域知识的形成,前者则将视野严格限定于民族志内部,将区域知识的形成视作民族志研究的前提。 这本书旨在阐述有几个区域持续得到学界的关注,这些区域曾对人类学整体作出过重要贡献:首先是对爱斯基摩和澳大利亚土著的民族志叙述,这些叙述告知人们狩猎—采集社会的简单生活,因而,曾引起关注人类史与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的学者之重视;其次是非洲和美拉尼西亚民族志区域,与狩猎—采集区一样,这些区域也位于世界的不同地方,但随着研究的深化、对话的密集,它们成为亲属制度、政治人类学和交换理论的来源地,为社会人类学上的“自然法”、社会组织、无政府主义、相对于理性经济人的社会人等理论的形成提供素材,自身也成为对理论争论反应最敏感的地区;亚洲区是个巨大的板块,在这个地区做研究,研究者面对着世界宗教和厚重的文献记载的压力,不能像从事部落社会的人类学家那样轻松地获得承认,(45)矛盾的是,在这个地区从事民族志研究的人类学家多数选择在村庄中研究,他们的主要辩论是,到底村庄研究能不能代表“文明”的整体面貌。 为《地方化策略》贡献论文的,是十几位长期致力于各自区域民族志研究而且在社会人类学一般理论上有显要建树的学者,(46)他们各自将其在不同地区从事研究的经历与这些地区的民族志历史遗产相联系,指出既往所有的人类学理论都是在区域民族志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而这些研究地区的内部对话与对外交流,对于推进理论起到关键作用:不能想象,倘若没有狩猎—采集、非洲、美拉尼西亚、印度这些区域的实实在在民族志,生育制度、继嗣制、交换、等级人等概念,是否有可能会出现。 《地方化策略》一书,运用了一种地区特殊性与理论一般性的辩证法,这一辩证法的存在,让其作者们能够避开分离经验与理论的后现代主义陷阱。作为这本论文集的主编,法尔顿清楚地看到了“新批判”(后现代主义批判)依赖的泛权力主义前提,(47)但并未纠缠这一前提的是非,更未从其反思中引申出有益于丰富民族志内涵的主张。幸而,在《地方化策略》出版前后,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一系列历史人类学与宇宙论研究的著述中,矛头直指政治经济学与话语理论的泛权力主义倾向。萨林斯指出,后现代主义者犯的一个最大失误是,以自我批评为戏法重新扮演了进化论的故事:在欧洲文明进入世界其他地区之前,那里没有过历史;这一失误又使他们误以为,被研究者的文化在民族志研究者到来之前并没有存在。而事实上,即使是在西方势力扩张的年代,它带着的那些政治经济学和权力概念也没有成为能够普遍适用于解释世界之实在的理论,原因是,与这一势力接触的“土著人”,仍旧以自己的宇宙论解释着世界,并将外来的白种人改造纳入自己的社会,使之成为被动的存在者。(48) 致力于重建文化理论的主流地位的萨林斯,以“文化”和“宇宙论”来与政治经济学和话语构造的近代世界史作斗争,这就使他的著述留给人们一种相对主义色彩;然而有深厚结构理论(这是一种普遍主义学说)涵养的萨林斯,观点并不是相对主义的——正相反,他主张,通过民族志式的研究(萨林斯的研究是历史民族志类的)进入被研究者的世界(尤其是其心灵世界),能使我们获得具有普遍启发的认识,这些认识,甚至有益于解释古希腊和基督教文明,而那些声称是普遍适用的泛权力主义理论,则不过是自古有之的、特殊的西方宇宙论的变相。(49) 法尔顿等英国人类学家在回应后现代主义的主张时,致力于重新焕发民族志书写区域传统的活力,他们告诫我们,没有一项理论创新不是与民族志研究者沉浸的特定区域有关;萨林斯这位美国人类学家在回应同一主张时,则致力于重新焕发民族志书写中的宇宙论传统,(50)他告诫我们,恰当的人类学诠释,只诞生于与“我者”自身所处的观念形态(宇宙观)处境疏离的“习惯”之中(即只能从远离“我者”的观念形态中提炼出来)。可将二者分别比拟成保守的英式经验主义和典型的美式文化主义,但必须认识到,正是这两种“再创造的传统”所表达的信念(这些信念也为那些并不这么表达的研究者所坚守),足以使民族志从知识论的压抑中脱身而出,在否定(本体论)之否定(知识论)中,将后现代主义时代之后的民族志带入一个新阶段。 这个新的阶段起初并没有得到标识,十来年前,“本体论转向”这个新名词出现,之后,不少人借它来形容民族志所处的“现时代”。2008年曼城大学召集了一次题为“本体论不过是文化的代名词”理论辩论会,这次辩论的记录,于2010年作为专辑发表于《人类学评论》。(51)专辑主编在引言中追溯了“本体论转向”的由来,说这与巴西人类学家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在2003年曼城大学召开的社会人类学学会年会餐后发言中提出的一个观点有关。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当时说,“一贯影响人类学的那个基本价值是(人类学家)致力于创造人或人群的概念——我指的是本体论——自决(self-determination)”。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的这一宣言,迅即在人类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在2007年出版的《由物而思》中,(52)何纳尔(Amiria Henare)等三位主编提出,民族志的本体论进路,不重视知识论的研究,认为知识论的研究主要关注被研究的人如何“表述”唯一的现实世界,而本体论进路重视的是诸世界(multiple worlds)的存在。对他们而言,本体不同于文化,正是文化这个概念将世界定义为一个单一的现实,将世界观(文化)定义为多样的。本体论反对文化的这种观点,它承认现实(realities)与世界(worlds)的复数存在。(53) 从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自己的一篇讲话稿看,其所谓“本体人类学”的号召包括三项:致力于把实践定义为与理论不可分的领域,并在这一我们可称之为“知行合一”的领域之中展开“概念”(concepts)研究;基于对“知行合一”的世界民族志叙述,提出一种关于概念想象的人类学理论,以此为方法,创造出知识与知识的关系,以共同丰富诸人文世界的内涵;为提出这一理论,尽力从一个事实中引申出所有必要的含义,这个事实是土著话语论述的事情绝非只与土著有关,这话语论述的是整个世界。(54) 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的这些号召,听起来十分接近马林诺夫斯基在近一个世纪前说的,即“若我们怀着敬意去真正了解其他人(即使是野蛮人),我们无疑会拓展自己的眼光”。(55)这些号召,不是空谈,而是由其长期的亚马逊流域印第安人民族志所支撑。 在民族志研究中,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极其重视萨满的贯通;在他看来,在萨满的存在方式中,“土著”用接近于泛灵论的观念看待他们的世界,将自然看作是多样的,将人看成是多样自然中的一个无文化区分的统一种类,而在其中,精神不是文化的,而普遍存在于自然世界中。(56)这种多样自然与单一文化的存在方式,全然与西方的唯一自然、多样文化观念相反,而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认为,这一美洲印第安人宇宙论,自身即为哲学概念,表达着一种别样的本体论。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将自然与社会两分,并将二者之关系定位为自然性质的;与此不同,美洲印第安人本体论(宇宙论),贯通自然与社会,认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社会性质的,这一本体论的泛灵论内涵(即其自然多元主义、文化一体主义的内涵),表达的是自然与社会的社会贯通性。(57) 这一从“土著”的本体论(即“土著”的生活与观念中的“在”)直接引申概念的做法,不同于后现代主义阶段的泛权力主义和自我反思做法,而与早已为人类学家坚持的“土著宇宙论”研究主张相续。(58)这类民族志,对于贯通被研究者与研究者的本体论,给予了空前的关注;并且,由于其侧重点不是“作者的解释”而是作者与“被书写者”之间关系所依赖的共同概念基础,因而,无论是相对于萨林斯的结构—历史论,还是相对于主张“召唤”的后现代主义者,都更具有现代主义的风格(尽管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刻意将自己与所有几乎现代主义人类学家区别开来)。“本体论转向”将民族志研究者的注意力引向被研究“世界”本身的生活之认识,引向这些“世界”的构成原理之求索,因而,有着促进民族志书写者与“土著”形成合乎情理的道德和政治关系的作用。(59) 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对民族志所作的本体论界定,是过去一二十年间旗帜最鲜明的主张。(60)然而,在地方化的深入民族志研究中贯穿本体论关注这一学风,不是他引领的那个“学派”所独有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堪称“本体论民族志”的文本,既有与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相联系的贯通自然与社会的民族志,(61)有受亚马逊河谷民族志影响出现的狩猎—采集区宇宙论民族志,(62)又有致力于贯通民族志与现象哲学的“生活世界民族志”,(63)更有基于既有区域性人类学概念(如来自印度民族志研究的“等级”概念)而拓展开来的比较民族志。(64)应当承认,致力于恢复“土著”活动和思考的“地方”的“世界”本质的学者,也早已有之;(65)这些学者通过将“地方”历史化和世界化,指出了被社区、群体、民族、社会、文化等等概念“缩小了”的“世界”之难以化约的丰富。这些基于丰富经验素材的研究,呼应着早些时间出现的有关民族志区域书写传统与文化—宇宙观的论述,共同开创了一个“后知识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回归于被研究者(即所谓“土著”)的生活与世界(复数的“诸世界”),成为理论或哲学背景不同的民族志书写者的共同事业。 四、结论 在19世纪后半期的实践和论述基础上,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家给民族志以体系化的方法学阐述,以“科学”为名(仅是“名”,其“实”含有诸多“人文”色彩),对研究实践加以规则上的界定;之后,民族志内涵得以丰富,研究得以深化,地理空间的覆盖面得以拓展。随着20世纪下半叶的来临,民族志出现了两度转变:首先,其所述“对象”在地理、历史上的上下文关系(contexts)引起了关注;接着,批判知识论视野被引入,民族志先后由诠释学加以反思以及由后现代主义加以批判。两次先后发生的转变,使民族志的本体论求索(66)退让于知识论的“考据”。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情况再次出现了变化,民族志走出知识论批判,回到了对知识形成的区域性的关注,并以新姿态重新进入宇宙论与本体论的经验研究领域。此后,民族志研究空前重视存在的关系性与世界的意义,由此被概括为“本体论转向”。基于这一对民族志的历史形成的论述,可以得出以下三点认识: 第一,20世纪70年代之前,民族志书写者侧重于理解被研究的“土著”(67)的存在与价值,而这符合本体论一词的含义,亦即,对存在之本相及现实之意义的研究,因此,可被称为民族志的本体论阶段。 第二,之后的民族志研究者多侧重于处理外在于民族志“对象”的政治经济上下文关系及民族志“认识主体”与其制造的知识或文本之间的“权力”关系,做法颇类旨在探求“知识之本质”的哲学知识论,因此,可被称为是民族志的知识论阶段。 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志领域中,涌现出不少致力于在既有民族志书写的传统区域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研究和思考,致力于以文化概念的复兴而回归被研究者世界观和社会观,以及致力于结合民族志与哲学思考而直接从“土著观点”的描述提出概念的学者。他们建立的风范,在接近民族志的本体论阶段被广为运用的规则之同时,有其新意(尤其是以“世界”概念替代“社会”概念),可谓是民族志的新本体论阶段。 以本体论、知识论、新本体论来表示民族志三个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并不是说各个阶段都只有一种民族志范式。本体论与知识论总是并存于每个阶段中,并且可能是难解难分的。以“本体论转向”为例来说,这种论述主张回到本体论,但事实上,“回到本体论”的主张,却又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知识论主张,只不过是这一主张与后现代主义主张不同,后者几乎认为知识论是一切,却又放弃不了“在世界中解释世界”的本体论追求。一个阶段被我们形容成“本体论的”或“知识论的”,原因只在于在那个特定的阶段中,“本体论”或“知识论”成为民族志两面中相对突出的一面。既然不应设想一个完全没有知识论的本体论阶段的存在,也不应设想一个完全没有本体论的知识论阶段的存在,那么民族志的历史,便可谓是由本体与知识两个概念代表的两种并存做法之间关系结构的两次反转(alternations)构成的,(68)其本质内容为两种方法学势力消长的过程。 当下民族志在后现代主义知识论的反复自我反思中解脱了出来,回到重视民族志“世界”本体的传统,并赋予这一传统以新的内涵。这一具有创新性的回归表明,被后现代主义者形容成“现代主义”的那套民族志认识方法,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质疑之后,声名和活力得到了部分恢复。这意味着,所谓“现代主义”早已蕴含着“后现代主义”的内涵,有穿越“我他”界限、自我批评及“召唤非现代性的宇宙论”的“自觉”。(69)用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话说,现代主义民族志的本体论求索,与现代性对世界的二元主义区分之间的关系不是单一的:民族志书写者既可能通过所谓的“纯化分类(purification)”,扮演人—物、我—他、文化—自然、人—神之间疆界的勘定者或守护者的角色,又可能通过“翻译式的穿梭(translation)”,扮演分类鸿沟两边的对立类别牵线搭桥的角色。(70)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的努力,在于在“土著本体论”中发现贯通土著与人类学话语的概念,但在贯通之前,他也花费大量笔墨对土著话语与人类学话语加以区分。(71)他的这一两面性,正源于现代认识—本体论的“纯化分类”与“翻译式穿梭”。 哲学家兼人类学家盖尔纳(Ernest Gellner)说,世间的知识立场只有三种:相信自身拥有真理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发誓抛弃独特真理的观点而假装所有文化和话语都是“真的”的后现代主义相对论;相信一个独特而科学的真理存在但从未相信我们可以确然地占据这一真理的启蒙理性。(72)若盖尔纳的评论有什么启发,那么这个启发便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跌宕起伏,民族志书写者们终于认清,原教旨主义宗教式的“科学”和后现代相对主义相对论式的“巫术”,都无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的生活与知识的本相;民族志书写者除了遥望“真理”之外还能做的,是在拒绝伪装成通灵者似的“真理代言人”之同时,尽其所能谨慎地接近于它,“敢于求知”。 后现代之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阵营”的研究者对民族志书写的区域传统的整理、对宇宙论的历史人类学的“考据”、对作为“关系的土著”的被研究者与研究者的本体论的贯通,构成了民族志的新形态。以田野工作和书写为主业的民族志,是人类学研究的“初级阶段”,而正是在对这一“初级阶段”的内涵之界定、反思、再界定中,人类学走出它的“殖民”阴影,渐渐趋近于一门人文科学。它未能使我们克服长期面临的两难抉择,即如涂尔干所言:“如果把人类高超的、特殊的能力与他们的卑贱的存在联系起来,把理性和感觉联系起来,把精神和物质联系起来,去解释人类的这些能力,那么就等于否认了人类的绝无仅有的性质;而如果把人类高超的、特殊的能力归结为假定的超验实在,那么又无法通过观察使之得以确立。”(73)然而,它却已通过对经验、整体、相对的民族志观的再界定、再综合,及对区域知识、世界观及“土著哲学”的再辨析、再提升,创造着本体—知识兼合的“民族志理论”,接近着人文科学的那个“物”。 注释: ①[法]列维—斯特劳斯著、张祖建译:《结构人类学》(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5-326页。 ②相关学者最近对此一提法的表述,参见伦敦大学霍博拉德(Martin Holbraad)、哥本哈根大学彼得森(Morten Axel Pedersen)、里约联邦大学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为2013年美国人类学会年会(在芝加哥举行)的一次相关圆桌讨论所写的召集书“本体论的政治:人类学立场”(The Politics of Ontology:Anthropological Positions)(未刊稿)。 ③之所以说是“线条”,是因为笔者在此既不可能对现存民族志成果作全面梳理,又不可能对所有民族志方法学著述作分门别类的概括,而只能择其要者加以“过滤”。 ④参见George Stocking Jr,Victorian Anthropology,New York:The Free Press,Toroto:Maxwell Macmillan Canada,New York: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1987。 ⑤参见Roger Sanjek,"Ethnography," in Alan Barnard and Jonathan Spencer eds.,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London:Routledge,1998,pp.193-198。 ⑥马林诺夫斯基正是带着这本手册去往特洛布里恩德岛的。关于此手册的形成,及英国经验主义民族志的历史状况,参见[英]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著,冷凤彩译,梁永佳审校:《论社会人类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46-60页。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本手册已得到中国民族学家的认识,凌纯声曾部分根据它写出“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一文。参见凌纯声、林耀华等著:《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 ⑦参见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143页。 ⑧参见[英]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⑨马氏同样承认19世纪前辈对人类学的贡献,他说:“在民族学中,巴斯蒂安、泰勒、摩尔根、德国民族心理学派的早期努力,重新塑造了旅行家、传教士及其他人早先的粗糙信息,并向我们展示了使用更深刻概念与抛弃粗糙和误导的概念的重要性。”参见[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梁永佳、李绍明译,高丙中校:《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⑩参见George Stocking,Jr.,"Maclay,Kubary,Malinowski:Archetypes from the Dreamtime of Anthropology",in George Stocking,Jr.ed.,Colonial Situations: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ledge,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pp.9-74。 (11)参见[英]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著,褚建芳、阎书昌、赵旭东译:《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12)由于马林诺夫斯基带来的转变具有革命性意义,因此,人们时常将他的作品与之前人类学家的民族志作对照,认为他导致的学术变迁是根本性的、断裂式的。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是马林诺夫斯基突然创造了这一传统,而事实上历史则不是由这样或那样的突变构成的。 (13)参见George Stocking Jr.,After Tylor: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1888-1951,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5,pp.367-426。 (14)在美国民族志的境外拓展中,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提出的“文明人类学”起到关键的作用,“文明人类学”尤其关注中南美洲、中国、印度的文明上下关系研究。参见Clifford Wilcox,Robert Redefiel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Lanham:Lexington Books,2004。而更早一些,米德(Margerate Mead)于20世纪20-30年代在南太平洋展开的部落社会调查,与其导师波亚士坚持的美洲印第安人调查形成了鲜明区别,开拓了美国人类学的南太平洋视野,其研究在风格上更接近于马林诺夫斯基。有关米德的民族志,见一部批评之作,即Derek Freeman,Margaret Mead and Samo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15)参见[法]埃米尔·涂尔干、马塞尔·莫斯著,汲喆译,渠东校:《原始分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法]埃米尔·涂尔干著,汲喆译,渠东校:《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法]马塞尔·莫斯著,汲喆译,陈瑞桦校:《礼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以上即属此类,它们后来成为民族志研究者的思想源泉。 (16)以中国为例,20世纪50年代,在新政权的直接组织下,民族志方法被运用于国内少数民族“识别工作”和“民主改革工作”之中。这一方法是从此前留学归国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那里因袭而来的,却既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社会的论述及苏联的民族学结合,又带有中国古代史志的色彩。这些研究焦点放在作为新国家“内部他者”的少数民族,旨趣既在于重新拟制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认同秩序,又在于赋予这一秩序“进步”的动力。 (17)(19)参见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文集》,第294-308页。 (18)参见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文集》,第309-321页。 (20)参见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文集》,第322-336页。 (21)参见[法]埃米尔·涂尔干著,狄玉明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页。 (22)在这方面,马林诺夫斯基堪称典范,在他的民族志里,“我”很少出现,存在的似乎只有“他们”(也就是被其观察和描写的“其他人”),而这被悬置的“我”,则通过穿行于我与“他们”之间的界线上,以“无我”为形式表述着“有我”的内容。由此,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库拉圈代表一种新鲜却不荒诞的事实,它“事实上是基本的人类活动或思想态度的形态”。参见[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梁永佳、李绍明译,高丙中校:《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第445页。 (23)参见George Stocking Jr.,"Introduction:The Basic Assumptions of Baosian Anthropology," in George Stocking Jr.ed.,A Franz Boas Reader:The Shaping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1883-1911,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4,pp.1-20。 (24)参见[英]爱德华·埃文斯—普里查德著,冷凤彩译,梁永佳审校:《论社会人类学》,第128-144页。 (25)参见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Basic Books,1973,pp.3-32。 (26)参见Talal Asad ed.,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London:Ithaca Press,1973。 (27)参见Samir Amin,Le Developpement Inegal,Essai sur les Formations Sociales du Capitalisme Peripherique,Paris:Editions de Minuit,1973。 (28)参见[美]埃里克·沃尔夫著,赵丙祥等译:《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8页。 (29)此外,固然还有深有影响的“实践论”。参见Sherry Ortner,"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6,No,1.1984。 (30)参见Paul Rabinow and Hubert Dreyfus,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31)关于巴赫金的著述,参见[苏]巴赫金著,晓河等译:《巴赫金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2)如瓦格纳(Roy Wagner)所言,民族志描绘的“文化”,无疑可谓是在民族志书写者与其“对象群”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创造出来的。参见Roy Wagner,The Invention of Cul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 (33)参见Edward Said,Orientalism: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rient,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8。 (34)为这些批评者所不能理解的是,诸如马林诺夫斯基之类现代人类学家使用“科学”一词时,关注的其实是“人文”的事。马氏说过,现代科学使民族志研究显示出“土著生活”的关系制度与政治秩序,并使人们理解到,“野蛮人”也有着他们自己的“冒险事业和活动”,且“对艺术品同样不缺乏意义和美感”(参见[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梁永佳、李绍明译,高丙中校:《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第7页)。这无异于说,“科学”就是对于被研究者生活世界的整体性的把握。 (35)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译:《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36)参见Paul Rabinow,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 (37)参见James Clifford,"On Ethnographic Allegory," 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Marcus eds.,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98-121。 (38)参见George Marcus,"Contemporary Problems of Ethnography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Marcus eds.,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pp.165-193。 (39)参见Steven Tyler,"Post-Modern Ethnography:From Document of the Occult to Occult Document," 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Marcus eds.,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pp.122-140。 (40)参见Akhil Gupta and James Ferguson eds.,Anthropological Locations:Boundaries and Grounds of a Field Scien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41)参见Ernest Gellner,Postmodernism,Reason and Religion,London:Routledge,1993。 (42)参见Richard Fardon,"General Introduction" in Richard Fardon ed.,Localizing Strategies:Regional Traditions of Ethnographic Writing,Edinburgh:Scottish Academic Press,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90,pp.1-36。 (43)这些论文曾于1987年1月提交于苏格兰圣安德鲁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此次会议是为了回应1986年在大西洋彼岸问世的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之作(《写文化》和《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而召开的。 (44)参见David Szanton,"The Origin,Nature and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avid Szanton ed.,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pp.1-11。 (45)在亚洲区做研究,得到承认的学者主要是东方学家、历史学家、印度学家、汉学家。 (46)这些学者包括研究狞猎—采集区的马克奈特(David McKnight)、瑞奇思(David Riches),研究非洲的詹姆斯(Wendy James)、童金(Elizebeth Tonkin)、瓦伯纳(Richard Werbner)、帕金(David Parkin),研究美拉尼西亚的斯特雷森(Marilyn Strathern),研究中亚的吉尔思南(Michael Gilsenan)、斯特瑞特(Brian Street),研究印度的博尔嘎特(Richard Burghart),研究斯里兰卡的卡培菲勒(Bruce Kapferer),研究印度尼西亚的霍巴特(Mark Hobart),研究日本的莫瑞安(Brian Moerian)。 (47)参见Richard Fardon,"General Introduction," in Richard Fardon ed.,Localizing Strategies:Regional Traditions of Ethnographic Writing,pp.5-7。 (48)参见[美]马歇尔·萨林斯著,蓝达居等译,刘永华等校:《历史之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9)参见[美]马歇尔·萨林斯著,王铭铭、胡宗泽译:《甜蜜的悲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50)另一个美国人类学家戴木德(Frederick Damon)也从被研究者的角度定义着民族志的世界,通过库拉圈北部的研究,他表明,这个地区也构成一个“世界体系”,只不过是此体系不同于彼体系,相比而言,它具有更为深刻的关系性。参见Frederick Damon,From Muyuw to the Trobriand:Transformations along the Northern Side of the Kula Ring,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90。 (51)参见Ontology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Culture:Motion Tabled at the 2008 Meeting of the Group for Debates in Anthropological Theory,Critique of Anthropology,Vol.30,No.2,2010。 (52)参见Amiria Henare,Martin Holbraad,and Sari Wastell eds.,Thinking through Things:Theorising Artefacts Ethnographically,London:Routledge,2007。 (53)考虑到人类学中“文化”既已用以指多样的现实与世界,有的与会的学者坚持认为,本体论不过是文化的代名词。 (54)参见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2003年在社会人类学学会年会上宣读的讲话稿,题为“AND”。 (55)参见[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梁永佳、李绍明译,高丙中校:《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第447页。 (56)参见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Cosmological Deixis and Amerindian Perspectivism,"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N.S.),Vol.4,No.3,1998。 (57)尽管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指责列维—斯特劳斯为文化—自然二元论的实践者,但正是列维—斯特劳斯指出,包括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所研究的人群在内的“看来完全屈从于维持生计的民族”,“能够完全不受这种利益关系的影响而进行思考”,“他们被需要和愿望所驱使,去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大自然和社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完全同哲学家一样,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同科学家一样,用理智的方法去思考”。参见列维—斯特劳斯:《神话与意义》,叶舒宪编选:《结构主义神话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9-108页。 (58)不应忘记,泰勒于19世纪70年代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十一章至十七章),主要讨论就是围绕“泛灵论”(万物有灵论)展开的。参见爱德华·泰勒著,谢继胜等译:《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的发展之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9)从某个角度看,“本体论转向”起到纠正民族志知识论反思的“事实虚无主义”偏向的作用;在“转向”之后,民族志取得的主要成就在于拓展了“社会”的概念,并将其从僵硬的“团体格局”(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1-28页)的囚牢中释放出来,使之回归于其来自的民族志世界,成为充满灵动、易于适应非“团体格局”社会的民族志与比较民族学概念。“社会”有时也可被理解为“民族精神”或“文化”,而其基本内涵是“关系性”(relatedness)概念的边界。沿着这一方向的努力,早在莫斯的论著中即已出现(参见王铭铭:《莫斯民族学的“社会论”》,《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莫斯阐发了他从涂尔干那里继承的将经验和知识(尤其是作为“集体表象”的分类)放在作为“物”的“社会事实”中考察的观点(参见[法]埃米尔·涂尔干著,汲喆译,渠东校:《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莫斯的民族志世界,包含着广义的“它”(“它”物、“它”神及他)的意味。 (60)基于这一界定,2011年《奥:民族志理论杂志》(Hau: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得以创刊,其宗旨在于直接在民族志中阐述理论。此外,“本体论转向”在其他诸多领域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参见Benjamin Alberti,Severin Fowles,Martin Holbraad,Yvonne Marshall,Christopher Witmore,"'Worlds Otherwise':Archaeology,Anthropology,and Ontological Difference," Current Anthropology,Vol.52,No.6,2011。 (61)例如,Philippe Descola,trans.J.Lloyd,Beyond Nature and Cul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 (62)例如,Rane Willerslev,Soul Hunters:Hunting,Hunting,Animism,and Personhood among the Siberian Yukaghir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此类民族志易于被英格尔德(Tim Ingold)看待为“狩猎—采集人本体论”,即,一种将人与动物之间关系视作“能动者间关系”的看法。参见Tim Ingold,The Perceptions of the Envirnoment:Essays in Livelihood,Dwelling and Skill,London:Routeldge,2000,pp.40-60。 (63)例如,Michael Jackson,Lifeworlds:Essays in Existential Anthrop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 (64)例如,Knut Rio and Olaf Smedal eds.,Hierarchy:Persistence and Tranformation in Social Formation,New York:Berghahn Books,2001。 (65)例如,Steven Feld and Keith Basso eds.,Senses of Place,Santa Fe:SAR Press,1996; Frederick Damon,From Muyuw to the Trobriands:Transformations along the Northern Side of the Kula Ring。 (66)有必要重申,“本体论”是相对于“知识论”而言的;后者辨析的,主要是认识者的知识之本质,前者辨析的则主要是存在的本相与“真实”的要素。 (67)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所谓“土著”并不实指“原始人”,而是指作为民族志认识之“物”的广义“对象”或广义的“其他人”,既包括“原始人”,也包括“乡民”、“城里人”,甚至“文明人”。 (68)关于结构的“反转”概念运用于历史时间形态研究上之可能,参见王铭铭:《人生史与人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61-235页。 (69)参见王铭铭:《王铭铭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361页。 (70)参见Bruno Latour,trans.Catherine Porter,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71)参见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The Relative Native," Hau: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Vol.3,No.3,2013。 (72)参见Ernest Gellner,Postmodernism,Reason and Religion,London:Routledge,1992。 (73)参见[法]埃米尔·涂尔干著,汲喆译,渠东校:《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584页。标签:本体论论文; 知识论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民族志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人类学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民族学论文; 认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