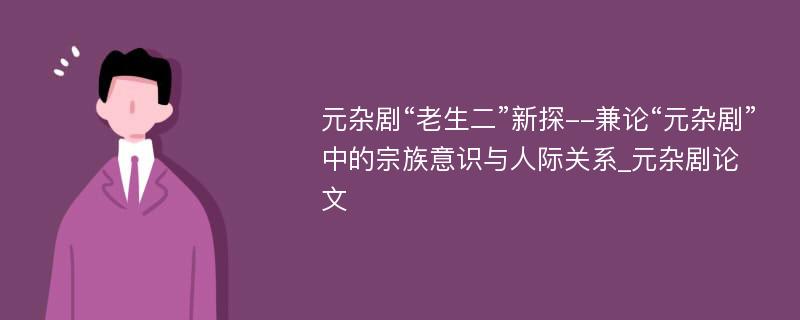
元杂剧《老生儿》新探——兼谈元杂剧中的宗族意识与人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伦论文,宗族论文,老生论文,元杂剧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武汉臣的《老生儿》杂剧,在现存元杂剧作品中独标异格,值得引起我们的特殊重视与深入研究。
首先,它以“曲白相生”而著称,尤以宾白的饶有机趣而为后世人们所赞赏。王国维在谈到元杂剧中宾白是剧作家所作还是伶人自为的问题时,曾论及《老生儿》,谓“苟不兼作白,则曲亦无从作”,并称赏《老生儿》说:“然其杰作如《老生儿》等,其妙处全在于白,苟去其白,则其曲全无意味。欲强分为二人之作,安可得也。”[①]王国维不仅将《老生儿》视为“曲白相生”之典范,同时认为它又是元杂剧中有代表性的杰作。刘大杰先生也看到了《老生儿》的独特之处,以为此剧“有揭露黑暗现实,讽刺世俗丑恶的一面”,在重曲而轻白的元剧作品中,“武汉臣则反是”,“《老生儿》一剧,对白是主,曲辞是宾,这种形式,在元杂剧里,是极少见的。”[②]
第二,《老生儿》又是元杂剧作品中最早被翻译成欧洲文字的作品之一。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的“余论”中,谈及元剧之译为外国文字者,说“英人Davis之译《老生儿》在一千八百十七年。[③]此后在1819年,又有德索尔桑的法译本,再后又有德文选择本和宫原平民的日文全译本。如此看来,《老生儿》杂剧又是最早产生世界影响的元剧作品之一了。有的学者认为:此剧因围绕财产继承权问题,展开几组矛盾,又写得很工巧,故深为西方友人所喜爱。”[④]这个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老生儿》以精采的对白为主,较为适合于欧洲人的欣赏习惯,未始不是原因之一。早期外国人翻译中国元杂剧,往往从西方的话剧意识出发,弃曲而存白,如普莱马赫神父在翻译《赵氏孤儿》时,“竟省略了作为该剧灵魂的43首曲词”,[⑤]这与我国元刊杂剧略白而存曲的情况恰恰相反。施叔青女士也曾提到最早的《赵氏孤儿》法文译本,“略去唱词不译”[⑥]王国维在《译本琵琶记序》中说《老生儿》译本亦如此。这说明,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人们审美意识以及情趣上的差异。实际上,“工巧”也好,重白轻曲也罢,都不是西方人偏爱《老生儿》的主要原因,该剧深厚的文化意蕴以及西方人对不同文化模式、不同价值取向的新奇感,才是西方人注意这本杂剧的根本原因所在。或者说西方人注意到了《老生儿》杂剧的文化意义和思想价值。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三,《老生儿》杂剧的关目设置和结构安排看似平淡,实为奇警。武汉臣将一个极其平常的故事,写得有滋有味,于古朴浑厚中见出灵巧与机敏来。还是王国维所说:“如武汉臣之《老生儿》、关汉卿之《救风尘》,其布置结构亦极意匠惨淡之致,宁较后世之传奇,有优无劣也。”[⑦]王国维将《老生儿》与关汉卿的喜剧代表作《救风尘》齐观并论,以为其结构关目胜于明清传奇。看来,王氏对《老生儿》真是情有独钟,近乎于偏爱了。
那末,何以对于这样一本元杂剧杰作,长期以来却很少有人去对它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探讨呢?“世人治元剧者,多不注意它”,[⑧]究其原因,或以为“它竭力宣扬封建宗法观念”,[⑨]其思想倾向必然是消极的;或以为“此剧主题无非是行善得子和宗族的血缘观念,剧情较复杂,不够精练,文辞也缺乏光采”。⑩]前者好在并未涉及作品的艺术技巧问题,立论之时在六十年代;后者成于八十年代中期,竟连《老生儿》的艺术成就也否定了,显然是未作深入研究即急于下断语,是大可商榷的。如果说王国维对《老生儿》是带有一定的偏爱倾向,那末彻底否定《老生儿》则明显是一种偏见了。已往的戏曲史、文学史著作,有的对《老生儿》杂剧索性避而不谈,即或是谈,也只是闪烁其辞,语焉不详。[(11)]便是如王国维、刘大杰那样,虽充分肯定了《老生儿》,却未能展开来做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这大约是由于写史体例上的局限所致吧。因此,对这本杂剧做进一步的研究探讨,深入分析,以便重新去认识和评价它,对元杂剧研究,乃至对整个戏曲史和文学史的研究,都将是很有意义的。
二
《老生儿》剧作的主要矛盾冲突是家庭内部的财产继承权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冲突的解决,矛盾的化解,明显带有浓重的理想色彩,但同时它又是完全可能的和令人信服的。由于结局的皆大欢喜,使全剧在形态上表现为不失为感伤的悲喜剧。深入思考,如此结局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种调和与折中,它恰恰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伦思想和宗法观念,有着极灵活的弹性或言回旋余地。它有时可能构成敌视与仇恨,成为悲剧的起因;有时它又可以转化为谐调与亲和的凝聚力。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而在宋元之际,这种亲和力和凝聚力往往又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内蕴,成为寄寓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的象征之载体。中国人家与国常是交互而称,又经常是以天下观代替国家观,再以家族观去实践国家观,即是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个人命运与家庭、民族利益融为一体,从而使“故园”与“故国”具有互文甚至难以区别的意义。这正为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乎此,我们才有可能对文学史上一些倾向复杂的作品,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老生儿》的确宣扬了宗族血缘的人伦思想,但它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作品,情况相当复杂。况且,它的倾向并非单一的。
《老生儿》杂剧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将宗族意识和人伦观念渲染得那样深沉有力,亲切动人,绝非无端。在元代前期宣扬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伦理思想,也不能断言就是消极的。究竟这本杂剧是否有隐幽而又曲折的寄托,这似乎不宜遽断,我们还是来看作品。
在《楔子》中,引孙从伯父家被赶出来时,他指着张郎自语道:“他强杀者波姓张,我便歹杀者波我姓刘,是刘家的子孙阿(呵)!”第三折中,刘从善在自家祖坟再三对妻子李氏强调:“则俺这坟所属刘,我怎肯着家缘姓张?”([鬼三台])又说:“姓刘的家私着姓刘的当,女儿也不索怨爹娘。”这里一次次强调姓氏宗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深思。《老生儿》的强调姓氏和祭祀祖坟,实际上正是借以曲折地呼唤汉民族传统文化。第三折中集中描写了宗法社会的这一重要的礼仪活动,分明藏着更深的内蕴和寄托。古代之祭墓活动本指祭后土,子孙祭父祖之义是后世衍变出来的。《老生儿》竭力渲染祭祖坟,实际上隐含着祭后土地神之意,隐含着社稷江山之忧,亦即深深的故园之情,故国之思。此外,《杀狗劝夫》第一折也写到孙氏兄弟到祖坟祭祀,用意指归俱与《老生儿》有相通之处。
姚枢于德安获儒服之赵复,力劝其同赴燕地—道弘扬儒业,谓“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年之绪者将不在是身耶”?[(12)]意思是说正是靠你我这样的人来复兴汉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位江汉先生赵复随姚枢北上,果使北方儒学得以昌明。过去我们的元杂剧研究过多地强调了“儒人颠倒不如人”的一面,而忽略了元前期儒人“承祀垂绪”的一面,因而对《老生儿》这一类作品就无法深入探讨。在礼崩乐坏,“纲常松弛”的元代,提倡汉族之人伦精神甚至宗族观念,既有其特殊含义,又有其特定环境,未可与其他时代同日而语。可以说,终元一代的儒学与文章,贯穿着一条使儒业不坠的精神,这是非常明显的。“纽结三纲重接续,灰寒万劫独光明”。[(13)]官至南台御史的李思衍,分明在这两句诗中透露出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心志。而以宋之遗民身份于至元间隐居的鲁仕能,则吟出了“万劫灰中藏世界,千层浪里惜儒珍”[(14)]以诉衷肠。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来。可见,对元杂剧中的所谓宣扬封建礼教的作品,未可一概斥之,当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多做些深入细致的具体分析。在这方面,《老生儿》杂剧可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
武汉臣笔下的主人公姓刘,张口闭口都是刘家如何如何,究竟有无特殊用意和寄托?如果说,《赵氏孤儿》是以“赵”氏隐指赵宋王朝,那末,《老生儿》中的刘家晚年得子,会不会是以刘姓隐指汉家天下,而以幼子象征着恢复之希望呢?有人说马致远的《汉宫秋》“口口声声不离‘汉家’、‘汉朝’”,是有所寄托的。“马致远故意利用这个字的双重含义,极尽皮里阳秋之能事,重重地烘托出民族意义上的‘汉’字,连题目《汉宫秋》也埋藏着这个意思”。[(15)]《老生儿》中的“刘家”,何尝不是转着弯子以扣紧“汉家”呢?虽然这样的推论多少有点臆想之嫌,却也不是全然不着边际的无根之语。
徐朔方先生曾在谈《赵氏孤儿》时引陶宗仪《辍耕录》卷四中“发宋陵寝”事,以说明杂剧的深层寄托,说“至少是当时某些具有强烈故国之思的志士对赵氏孤儿传说的联想”。[(16)]在陶宗仪看来,唐玉潜冒险去收拾南宋皇陵中的骨殖,与程婴、公孙杵臼保护赵氏孤儿之举同样壮烈,是“两雄义当,无能优劣”。《老生儿》中有许多地方都能唤起人们的联想。引章保护刘氏新生儿的情节虽是作为伏线来写的,其隐喻意义仍然曲折透露出来,它与祭祖的情节合起来构成了完整的象征意义。由此可知,早期传入欧洲的三个元杂剧作品——《赵氏孤儿》、《老生儿》及《汉宫秋》,都曲折寄寓着故国情怀和民族意识,在揭示主题的方法上,它们的精神是相通的。包括后来译成欧洲文字的《灰阑记》,也是围绕着财产继承权问题展开矛盾冲突的家庭伦理剧。西方人对这类题材的剧作似乎有着特别的兴趣,这足以引起我们文化上的思考。
三
第三折刘从善在自家祖坟苦劝妻子李氏的戏,无疑是全剧中的重场戏,它是作者的着意之处,也是全剧的主题思想之所在。
武汉臣是元前期作家,《录鬼簿》中将他列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一类,与关汉卿、白朴、马致远以及王实甫等是同辈作家。因此,曲中的“每日放群马和这群牛”,不是又令我们联想到“悉空其人,以为牧地”[(17)]的记载吗?甚至我们从中味出了后世《桃花扇·余韵》中[哀江南]套的韵致来。一句话,感伤与哀痛背后潜藏着的是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浓厚的故国之思。只是,与《赵氏孤儿》与《汉宫秋》相较,《老生儿》的曲意似藏得更深,倾向显得更隐蔽罢了。唯因如此,长期以来治元曲者,才多不注意它。然而,表面上的平淡与琐屑渲染得愈是充分,剧作的情趣就愈是美妙;芒角隐蔽得愈深,其艺术魅力也就更加独特。这正是《老生儿》鲜明的艺术个性。内敛而厚藏,含蕴而不露,可说是武汉臣的风格。
剧中的所谓“外姓人”,只有刘家的女婿张郎,这个人物在全剧中的戏并不多,但却不能说不重要。他可以被看作一个符号化了的“侵入者”的角色。说来张姓本是汉族大姓,作者或许是取了“施弓弦也”(《说文解字》的字之本意吧,甚或又取了扩张和侵入之引申义亦来可知。中国古代家族重血统,讲嫡庶,财产继承权正是建立在这基点上的。元杂剧中的“自报家门”,往往说“嫡亲的×口人”云云,这是很有意味也值得注意的。是不是可以说,一个血统,一个道统,差不多是元杂剧家庭伦理剧的两根支柱。不错,元杂剧中有些作品的确崭露出与礼教相抗衡的重角与芒刺,但另一方面,尊礼教、重道统的倾向也是明显的。这毫不奇怪,须知宋儒之道学浸淫百姓日用,深入市井人心,实肇端于元代。“朱学”正是在元代被确立为官方哲学的。纲常伦理秩序的强化,发端于南宋,而付诸于世俗化的实施与推行,却始于元代。这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综合作用的结果,情况极为复杂,未可以好与坏、利与害一言论定。施叔青女士曾引用其老师俞大纲先生的话,来说明元杂剧《合汗衫》的意外之意“如《合汗衫》,把一个陌生人引了进来,却造成了一家人妻离子散的悲剧。……中国人极端保守,从建筑的结构就可以看出是十分防御性的,农业社会十分封闭,对于外来的闯入者在恐惧之余,多半不受欢迎,认为外来的力量具有侵略性,甚至足以造成摧毁一个村子、一个宗族的导火线,元杂剧的《合汗衫》正是反映了中国人疑惧外来者的心态。”[(18)]类似的例子还有《货郎担》、《酷寒亭》等。有宋一代,边患不断,南宋就更不消说。两宋王朝的始终处于防御状态,终于半壁亦不能保,被金元“闯入者”所摧毁,于是民族的心理,时代的脉搏,都在防御中悸动,惊恐中颤抖。表现在杂剧创作中,便构成了一些剧作家的潜在意识,在他们的笔下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防御性心态和固守家园的情结。将张郎看作是“外来的闯入者”,是从“角色论”的意义上而言的,至少是在家庭财产再分配的问题上,他充当了“侵入者”的“角色”。
《老生儿》中的一个细节,也大有文章,这就是象征刘家财产的十三把钥匙。刘从善在李氏的怂恿下,曾将掌管家私的十三把钥匙交付张郎,后又由李氏出面,索回钥匙,交由引孙。钥匙是权力和财产的象征,更是江山社稷的隐指。十三这个数恐非剧作家随意为之,汉代中国的行政区域正是划分为十三部的,“凡十三部置刺史”(《汉书·地理志》)。又古代中国有九州之称,九州而加四方,数亦为十三;阴阳八卦加五行恰也是十三之数。倘若我汉臣能想到以刘姓隐指“汉家”天下,他就不会不知道汉代分为十三部区划之制。可知十三把钥匙之细节描写,很有可能是影射执掌天下社稷之意。
结局之三分财产,却并不意味着三分天下。引孙及从善幼子均为刘家子孙,实为一也,幼子更是宗子血脉,自当领财产大宗。因为剧中只说将财产分作三份,却未曾言是三等份。至于引璋,不隔代固是刘家血亲,且用心保护刘家宗嗣有功,论功而赏,亦在情理之中,只有张郎,与刘家财产全无干系。这样的结局既不越宗族法规,又有一定的变通,使全剧有了一个圆满的喜剧性收束。
中国文化模式,既基于宗法人伦思想,古代中国人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自然也就围绕着宗族意识和伦理情感方得以体现,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作品反映这种体现和体现的满足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不唯元杂剧作品,表现在中国戏曲中的宗族意识与伦理情感,可以说几乎是无所不在,只是《老生儿》、《合汗衫》等元剧作品更为突出和明显罢了。
四
《老生儿》杂剧在艺术上的独步与卓异之处,在于其宾白的朴拙之趣,这一点早已为前辈学者所指出。事实上它的曲词也写得少而精,极尽本色自然、当行出色之妙。只是它为宾白的浑朴之美所掩,未曾引起人们的注意。且看第二折之[滚绣球]曲:
我道那读书的志气豪,为商的度量小,则这是各人的所好。你便苦志争似那勤学。为商的小钱番作大钱,读书的把白衣换作紫袍,则这的将来量较,可不做官的比那做客的妆么。有一日功名成就人争羡,抵多少买卖归来汗未消。便见的个低高。
此曲明白如话,朴茂老到,与宾白浑然一体,互为发明,相得益彰,在元曲中堪称别一家法。从内容上来,亦见出宋元之际人们在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方面新的意识。尽管从善一生以经商致富,细绛曲文,他对读书与经商似并无偏见,主张各从其所好,按性情去选择。或许剧作家正是站在元代文人自身价值失落的立场上来说话吧,他对科举制度又留恋又向往,隐约流露出元代文人对传统文化承传的深深忧虑。与此相联系的是剧作家对世风的激愤之情,于曲白中时有流露。如第三折中一开始张郎的上场诗云:“人生虽是命安排,也要机谋会使乖;假饶不做欺心事,谁把钱财送我来?”愤世嫉俗之情脱口而出。元代文人失意无奈中的复杂心态,借剧中人物之口渲泄出来,是讽世,亦是牢骚,更是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揶揄与讥诮。
说到于平淡琐屑中见出巧思的笔触,我们以第一折中李氏到别庄告知从善,说小梅出走之描写为例。从善盼子心切,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接受这个近于残酷的消息。他自言自语般地反复说这是老伴在与自己开玩笑——实为一种绝望之中的自我安慰之词。武汉臣在这里大作文章,将人物的心理活动写得细微真切,从而清楚而又准确地揭示出两个人物对同一事件完全不同的心理反映。
《老生儿》的圆满结局,固然有理想化的一面,然却未始不是剧情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大团圆结局有许多的不同。新生儿既有特殊意义上的象征,宗族意识和人伦思想又寄托着剧作家潜在的含意,结局就是注定的,似未可厚非。从欣赏者的角度而言,处在元代的特定环境中,人们亦须从中捕捉到某种朦胧的希望——那怕是幻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武汉臣既迎合了观众,也迎合了时代。同时,这又不违背其艺术构思的完整性和艺术追求的个性发挥。
武汉臣的《老生儿》无疑是一部适于演出的作品,故其圆满结局(快乐收场)或多或少含有“对观众让步”的意味。但通观全剧,剧作家处理得还是水到渠成,毫不勉强的。
《老生儿》中的科诨穿插,也恰到好处,其风致颇类关汉卿。所幸《元曲选》本保留了此剧较为完整的科白,使我们得以全面把握武汉臣的语言风格和科诨设置技巧。《老生儿》实为一部带有浓重感伤情调的悲喜剧,其科诨穿插很有特点,与关汉卿的善为科诨一样,在元杂剧中有一定的典范性。
至于武汉臣对于俗语俚言的自如运用,亦见出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极强,为剧作平添了不少意趣。这是构成其戏曲语言风格的一个侧面。《老生儿》的关目与语言之间的谐调与相辅相成,在元剧中是有代表性的,故它是现存元杂剧作品中真正的出类拔萃之作。王国维称其为杰作,绝非溢美之辞。
注释:
①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元剧之文章》,《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82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②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册862——8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③《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112页。
④刘荫柏:《元代杂剧史》第162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⑤参阅(美)时钟雯:《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杂剧》第2页,西莱尔·波奇之《前言》,萧善因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施叔青:《西方人看中国戏剧》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⑦《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85页。
⑧同②。
⑨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3)2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⑩邵曾祺:《元明北杂剧考略》第14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1)如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也只是说:“《老生儿》的宾白很出色,在元杂剧中是有代表性的。”见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上册132页。
(12)姚燧:《序江汉先生事实》,《牧庵集》卷四,四部丛刊本。
(13)李思衍:《吊李肯斋》,《元诗纪事》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77页。
(14)鲁仕能残句诗,《元诗纪事》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147页。
(15)余秋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211—21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此外,阿英先生在评论《赵氏孤儿》时也说:“这里所说的‘赵家’,虽指的是赵盾,实际上还是影射宋朝。”(《元人杂剧史》),见《剧本》1955年第6期第126页)谢柏梁则谓纪君祥“以赵氏孤儿的复仇段子,来为三百多年的赵宋王朝唱一曲悲壮的挽歌,织一出绚丽的‘恢复’之梦……”(《中国悲剧史纲》110页,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
(16)徐朔方:《金元杂剧读后》,《徐朔方集》(1)17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7)《元史·耶律楚材传》。
(18)施叔青《西方人看中国戏剧》第2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