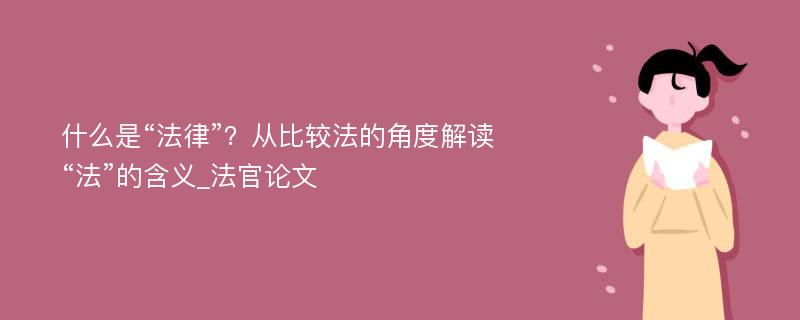
“法学”是什么?——比较法视域中的“法学”含义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学论文,视域论文,比较法论文,含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003(2006)04-0032-06
迄今为止,学者们对“法学”下定义时大致停留于法学是“关于人和神的知识,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的学问”之认知上。倘若按此理解,法学只是知识与学问,至多也不过是知识理论体系。难道法学仅仅是意味着一种关于知识与学问的行而上之谱系吗?若是,则会与法学之实践理性品格相悖。因为,法学不只是一种知识谱系,它本质上应当是基于对法的具体场景运用的实践活动的回应。法学是一种知识、一种逻辑、一种学问,却更是一种实践、一种经验、一种解释。故而从比较法的角度,对“法学”的认知有待深化。英语世界对“法学”的理解是:Jurisprudence is knowledge of things divine and human,the exact discernment of what is just and unjust.①对这句话的正确解读应当是:法学是“关于神的和人的事情的知识,是关于正义与不正义的严格的判断与解释。”由于我们所研究的当代“法学”实际上是外来文化的产物,对“法学”本身的含义理解和把握倘若有所偏失,将直接影响到中国当代法制化理念确立与制度建构,为此本文从比较法之视域对“法学”之原初含义作一阐释,以期加深对“法学”认识的理解。根据笔者对“法学”含义的解读,可把它概括为三个判断:法学是公平之学、法学是智识之学、法学是判断与解释之学。
一、法学是公平之学
在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中,皆存在着神筮法律文化,从古希腊的“狄克”(dike)和“特弥斯” (themis)正义女神到古罗马的基督教,西方法律始终与神法纠缠不休,由此而奠定了西方法律之二元论思想,神法或自然法与人法或人定法成为认识和分析西方法律的基本范畴,二元思想贯穿于整个西方法哲学之始尾。其中的人法即是关于人的事物的法律,神法则是关于神的事物的法律。而古希腊与古罗马宗教文化中的“神”皆是人格化的,宇宙之上帝为宙斯,基督教之上帝为耶和华,无论宙斯或耶和华,都有自己的“家庭史”,它们是正义与公平的化身,它们的法即“神法”不仅建构了宇宙神界秩序,也同时奠定了人间俗界法律的绝对原则和基础。古希腊和罗马法学应当是关于法律二元的知识与价值判断的学说,这种学说就是公平与正义之说。不言而喻,神法本身就代表着公平与正义,而人法之价值基础又必须基于神法与合乎神法,所以在查士丁尼的《法学阶梯》中关于法学是神的知识的判断命题,就是对古希腊与罗马法文化的高度概括与确切反映。如果说这里的“神”在当时所指称的是“上帝”的话,那么当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之后,其中的“神”即非宇宙之宙斯之神,亦非上帝耶和华之神,而应转换为一种价值或精神之神圣,这种价值或精神就是“公平”、“正义”,它们构成了法律之神。西塞罗说过:“真正的法律是符合自然的正确理性,它是普遍的适用于所有人,是稳定的、永恒不变的;它以命令的方式召唤人们履行义务,以禁令的方式约束人民制止犯罪。……元老院或人民的决议都不能摆脱这种法律的制约,无须有人进行说明和阐释;它不可能在罗马是一种法律,在雅典是另一种法律,在现在是一种法律,在将来是另一种法律;这样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律,无论何时何地,都将是有效的。”②[1]其实,无论古希腊还是古罗马,都不可能存在什么“上帝”之类的“神”,有的只是人类对公平与正义的向往,所以所谓的“神”只不过是人类对公平与正义理想之表达。法律不仅是控制社会关系的规则体系,而且也是反映着人类出于对公平、正义表达之价值体系,这种价值是人类对公平正义之记载。在规则与价值之间,公正之价值是神圣的,规则应当体现这一价值,反映这一价值,这是衡量法律规则善恶的标尺,以公平为价值基础的法律就是善法,否则即是恶法。即使从分析实证法学的规则主义观点看来,规则运用之程序不公正,其审判结果也是无法令人接受的。因此,在关于人的或神的法律的知识中,惟有且只有公平之价值才是神圣的,由此我们即可作出第一个基本判断:法学就是公平之学。
我们还可以从中西方文化最初对法律的理解中,认识法学是公平之学的命题判断。我们认为,中国古“法”至少包含三层含义:(1)强调了审判主体的独立性,即由于神兽进行审判,它不受其他因素所影响,所以其审判活动是独立的;(2)强调了审判程序的公平性,从“触”到“去”的过程是公开的,是一种看得见的正义,对二造双方而言在程序上都是公平的;(3)强调了法前人人平等之原则,所谓的“法”就是神兽,由它来掌握法的标准和尺度,由于它被赋予了“神”的地位,是公平的化身,所以当事人在神兽这一“法”面前是平等的。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法文化中,法之原初意义就蕴涵着公平,代表着公平。无独有偶,在西方法文化中对法的意义之赋予也同样被铸入了公平之价值。 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封面一幅图面即深刻地表达了西方人对“法”的意义的理解。该画面是:一位少女,蒙着双眼,一手握天平,一手执箭,其脚下是一头狮子和一只公鸡。少女即代表着法律的纯洁无瑕,蒙着双眼则表明断案者不能先入为主,天平代表着公平,箭则代表着力量,无箭之公平是软弱无力的,无公平之箭则意味着赤裸裸的暴力,法律面前,强者与弱者一律平等。东西方人虽然文化背景存有差异,但对法的意义阐释确是高度的一致。这表明:法律虽然具有地方性,但法学观却具有世界性,东西方人类从各自的文化中得出了相同的关于法学的判断,此即法学是公平之学。
另外,在对法学的价值定位中,一些学者把经济学中的效率价值引入到法学中,把效率视为法学的价值。其实,这是一种对法学价值与经济学价值的混淆。法学的价值就是公平,法学是以研究公平价值为目的的,公平是法学之特有价值;而经济学之特有价值才是效率,正如不讲效率的经济学不是经济学一样,不讲公平的法学就不是法学。法学不能脱离人的法律资格的平等之基础而研究法学,而经济学也不能脱离成本与收益之基础而研究经济学;从效率价值而言,法学的公平价值自身已蕴涵着效率,而且愈是公平的程序与公平的判决,就愈是最富有效率的。也就是说,程序的公正与判决的公平,就会使当事人和社会民众对法律予以充分的信任与尊重,从而避免了因对裁判的不服而导致的上诉或申诉的诉讼成本的增加。许多当事人因为判罚不公或不公平对待而不断上访或信访,从而使个人和社会都付出了超额成本,这种超额成本的付出,使法律的效率反而降低了;因此,公平的判罚与公正的程序,就是具有效率的法学。在经济学中,效率是理性经济人如何以最少的成本投入而获取最大化的产出一种比值关系,这种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既包括物量投入,也包括时间和人力的付出;如果把效率引入到法学中,则必然会考虑如何才能以最快的时间或在最短的时效内完成某一法律程序,而法律程序的设定恰恰是基于对人的意志的过滤和“作茧自缚”,即使考虑到处理个案的效率问题,也必须是在公平前提下的效率,如果像经济学一样,法学也仅仅把追求效率作为其价值诉求,那么就会忽视或舍弃了公平,而不公平的处理结果又必然会导致当事人不停地上诉、申诉或上访等各种制度性或非制度性的成本的增加,最终使法律毫无效率可言。所以,公平是法学所特有的价值,如果说法学也讲求效率的话,也必然是在公平之前置下,因为公平即孕育着效率,包含着效率。既然如此,在公平价值之外再强调效率价值,或者单独把效率作为法学的独立性价值,是没有必要的,甚至是多余的,法学只有在公平之中寻求效率才是人们所欲的。
二、法学是智识之学
法学是一种知识理论体系,也是一套思维体系和经验智慧体系。早在罗马共和国时期,随着相对独立的法律家群体的诞生和他们对一些法律问题专门解答、法庭技巧传授以及对法律原则的研究,就业已形成了一套关于法律的系统知识,这套知识即被称之为“法律科学”(legitima Scientia)或“法学”(jurisprudentia)。在中世纪,法学和神学是大学中两门最重要的学科,它们以注解和阐释经典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只不过法学所面对的经典是罗马法,而神学所研究的是圣经。这种研究方法的系统性特征使法学继续保持着“科学”的地位。而且,这种以揭示“意义”(meaning)为主要目的的方法经过人文学者的不断发展,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方法学,即关于“解释”(interpretation)的科学。近代所有关于人类自身的科学皆是在该方法学基础上建构与发展起来的。作为科学,法学自身构成了一整套知识理论体系,首先有自己的范畴与概念体系,一门科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独立于其他的知识系统,就在于它具有自己学科独立意义的概念范畴,而不同的概念范畴又构成了该学科的独特的思维方式。法学自有法学的概念范畴。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法律权利、法律义务、法律行为、法律责任、法律制裁、故意与过失、法律时效、法律程序与法律诉讼等,即构成了法学所特有的基本范畴体系。这些概念范畴在法学上都具有丰富的法学意义与内涵,作为一种法学知识,则必须通过系统地、专门的学习方能掌握。其次,法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从古希腊的斯多葛自然法学到近代的古典自然法学、分析法学、历史法学,再到现代的法社会学、现实主义法学、新自然法学和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法学理论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产生、变更和丰富发展,各自的法学理论都是一部法学史,它们各自都有其自己的观点与理论体系,各自都有对法的意义的不同阐释,这种对法的意义的不同理解和解释,形成了日臻丰富的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对这些法学理论的理解和掌握,也必须经长期的系统学习才能达到。最后,法学有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思维模式,法律发现、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价值或利益衡量等法学方法又使法学成为不同于其他科学的技艺性学科。法学的思维模式是独特的,它是一种严格的程序推定和逻辑证据推定,凡是法律问题,必须是程序启动在先,依程式而行;凡是客观事实问题,则必须以法律证据呈现,依证据而定;处罚程序之前,罪责从无。
由于法学既是一种知识体系,又是一种具有独特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学科体系,由此决定了法学还是一套经验智慧体现。它并非像17世纪英国詹姆斯一世所想象的那样,法律是以理智为基础的,只要一个人具有理智就能够像法官那样审理案件。也就是说,从事法律或法学职业的人,绝不是仅仅靠对法律或法学知识的学习就能够具备其资格条件的。基本知识的掌握是必要的,却是远远不充分的,因为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掌握它之前,得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2]法学具有实践理性和经验理性,法学思维方式是从事法律的人借助规则在对具体个案的适用中凭其感悟与体验而逐渐习得而成,而非仅凭其规则理性获得。对法学的经验性哲学认知在英美法系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从作为“法官的理性”的普通法创始到近代的培根、霍布斯、洛克之经验哲学史观,法学一直是以经验理性为其历史传统的,离开了判例经验的把握,法学就可能不成其为法学,法律家们就会感到无所适从,19世纪的英国之所以未走向法典化之路,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法律家们业已形成的固有的普通法经验思维模式与传统之抵抗力使然,而美国大法官霍姆斯的“法律是经验而非逻辑”的判断恰是英美法律这种经验主义的一种最适当的总结。殊不知,大陆法系之历史渊源的罗马法之最初形成同样是来自于大法官的判例经验,公元前367年罗马共和国时期由设立的最高裁判官判例而成的市民法和前242年再由设立的最高外事裁判官判例而成的万民法,都是法官经验判例的产物,可以说,罗马法像普通法一样也是由判例演化而来,只是到了罗马帝国时期随着法学家对法律的注释和“五大法学家”②的法律解答成为具有法律效力渊源之后,“法学家制定了罗马法”才成为其后的传统和事实,尤其是当继受了查士丁尼的“国法大全”的法典编纂之历史渊源之后,欧洲大陆才走向了不同于英美法系之途,并继而形成了以其理性建构为特色的法律传统。但是,伴随着19世纪后半叶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对法官解释法律权的承认,法学是实践性的经验判断最终在大陆法系亦获得了认可,法律需要法官的解释性适用这一实践活动,即把经验理性写在了法学的旗帜上。也就是说,既然法律是解释性的实践活动,对法学之本性认知就必然带有经验的烙印,从而就必然要求法律职业者尤其是法官需具有长期从事法律或法学之经验,经验其实就是一种对法学事业的体验过程,也就是对公平与正义的道德价值在内心确认的过程,当人们说法律职业者的伦理道德是公正与对法律的服从时,这种伦理道德绝不是凭立法者使其成文化写在法典中就能够塑就的,更非为法律职业者所背诵而确立,它必定是通过法律职业者本人在长期的对法律的解释和对公正价值的内心体认中确信而立的,假如没有这种对法律的经验实践历程,就无法完成对法律或法学的公平价值在其内心认知的伦理使命。由于法学是一种经验之学,所以对法学问题的判断就需要具有充满智慧的法官才能胜任,而智慧型的法官又须是来自于长期从事审判实践活动的法律职业者阶层,因而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对法官资格的要求就比较严格,譬如在普通法系国家,对法官的职业资格要求首先是应毕业于正规法学教育的大学法学院和相当长的司法实践,然后根据其在实践中的表现和成绩、在法律职业同行中的声誉与政治影响等因素,通过任命或推选而任职,所以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往往是中年人或老年人,这种任职被视为一生中迟来的辉煌成就。在各种职业中,大致三种职业由年老型的人任职为佳:宗教业中的神甫、医生业中的中医以及法律职业中的法官,神甫以解释圣经为使命,中医则以解释病理为使命,法官则以解释法律为使命,他们由于都关涉人生经验之谈,所以人生阅历积累越深厚,其处理人生问题的能力就越强,所谓智慧,只不过是理性与经验之结合,只有知识理性而无经验,充其量是知识与规则的堆积,而只有具有了经验,其知识体系才能成为智慧的活动。由于法学是一种实践性活动,所以就离不开经验与智慧,甚至缺乏经验与智慧,就不懂得法律的解释活动,就无法把握法律的意义和法学真义,那些没有学过法律或仅仅通过短期的培训或者缺乏法律经验的人充当法官,无疑是对法律的亵渎。这也说明为什么在我国大多数法官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审理活动就是解释法律的实践活动,多数人仍然停留于“依照法律”而非“解释法律”的思维上。知识是法官的智慧之本,经验则是法官的智慧之源,没有掌握法学之知识的人是法盲,而不具有法学经验的人则只是审理案件的机械师,永远不能成为一个智者和艺术大师。法学的公平价值在经验的智者审理中方能得以体现。
三、法学是判断和解释之学
法学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判断和解释问题。法学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法律问题的学问,法律亦非单纯是一个规范性命题,法律是什么的判断,不是单单取决于法典中写下来的规则,还取决于对法律真正意图和目的的解释。这也就是德沃金所提出的“明晰的法律”与“隐含的法律”的问题。即使是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法律解释者也不见得认为那就是法律,是否为解释者所适用的法律,还取决于解释者对法律含义的解释。英国诗人奥登曾写到:法律是什么?一如法官居高临下所说的话,他清晰而最庄严地宣布:法律就是我以前所告诉你们的;法律就是我的猜测,正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法律只不过是我重新作出的解释,法律就是“那个”法律。[3]
如果法律真的像奥登说的那样是法官的猜测和解释的话,法律应该允许或者禁止什么,它赋予法律帝国的臣民以何种权利,那么法律是什么?所以法律是什么的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尽管我们生活在法律之中并受制于法律的统治,但人们还是对法律是什么,它赋予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到底是什么,引发了不同时代与各个历史时期的法学家和法律家的争论。在法学上人们对法律问题的思考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答案,惯例主义的、法律实证主义的、实用主义的、道德主义的,不同的法学学说与不同的法学理论观点彼此交锋,但都在“民主”的司法实践下得到了统一,无论是哪一种解释在司法判决中占了上风,虽然这种远不是最好的答案,但却是一个尽其完美的答案,是一种尽可能最妥善的叙述,因为法律是一种不断解释性的概念。所以,在法学上,对法律的解释主要存有两类主体:一是法学家的法律解释,二是法官的法律解释。法学家对法律的解释建构了法学各个流派,每个流派的法学家对法律的意义作出了甚至完全不同的阐释,由此才演绎出了风格迥异、观点鲜明、认识深刻的法学流派。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则是真正揭示实际上法律是什么的最终判断,所以法律是什么之命题其实就是法律解释之命题。法学就是对法律之判断与解释的问题。
法律解释的本质是解释者确定法律文本的意义问题,如果法律文本的含义明确、清楚,并直接可以适用于具体宪法案件,那么就没有解释法律之必要;之所以需要解释,恰在于法律文本在适用中有存在模糊或空缺的时候,所以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就需要解释者对宪法的意义作出权威性的阐释或说明,故法律解释的本质即是阐明法律文本的意义。然而,法律一旦进入阐释学的领域,其意义似乎即难以捉摸和确定:是立法者所确定的历史意义,还是法官—解释者所理解的现实意义,还是文本自身所固定化的意义?法律的真理到底由谁决定?这看似十分简单的问题,但却蕴涵着自启蒙运动以来所确立的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进而渗透和影响社会科学之客观性及其批判与反思的两种思潮的较量。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承认知识即真理,或真理是可以认识的。近代自然科学所探求知识真理的重要方法是实验,凭借这一方法,自然规律性的知识才成为可能。这种科学思潮对精神科学的直接影响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使人文精神这一“学科”成为“科学”,即试图从方法论上超越主观性而达到历史认识的客观性。这反映在实证分析方法上。实证分析的核心在于抛弃道德价值分析,倡导价值无涉,相信只有真理才能够成为社会现代性进步的力量。在这种方法中,要求人们尽量消除一切主观偏见,从而保证客观性。在法律实证主义看来,从事法律科学的人只要使自己摆脱道德正义的主观性因素之影响便能够获得客观性的法律真理。法治的真理即存在于法律的确定性、明确性与规范性上,如果法律失去了确定性的内容,法治则不复存在。但是,社会科学不是纯粹描述性的科学,它在深层意义上说是阐释性科学,尤其是法学这样一种本质上属于实践性的科学更是如此。因为,精神人文领域不会向人们自动展开其结构和状况,以便让人去简单地复制或描绘;实践性科学的真理不是对以往历史现实世界的客观实体的反映,而是解释者与立法者视域交互融合的结果,因为解释者从事着实践事务,法学作为社会科学是解决人与人的关系的,它不纯粹是证成知识与真理的科学,而是一种价值判断,即需要法官的判断力去正确评价具体情况,以便把法律具体化。然而,法官的价值判断即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创造性,那种要求解释者完全抛弃主观性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客观主义的观点就是一种对事实的歪曲。因为,“现代阐释学摈弃了以追求客观性为目的的超然外在观察者的行而上学,转而赞赏虔诚的科学家的形而上学:这位科学家属于某种传统,以该传统的智识资源来开展工作。真理在阐释学方法论中的地位是什么?它并不是关于外在观察者企图将之带回到非反思的洞穴居民中的自我认识的主张,而是在行为和意义所属的传统中对该行为和意义的表达和解释。”[4]因此,任何阐释都必定带有解释者所属传统的主观印记,而不可能完全抛弃解释者自身的主观性。
法律之所以是解释性概念,是因为它并非就是法律文字所写明的,它既有明确的含义,又有隐含的含义,也就是文字与法律的真正意图是统一的。在法律解释中,有三种意图需要判断,一是立法者的意图,二是文本自身的意图,三是解释者的意图。[5]法律文字所记载的内容是无法言语的,立法者把其意图赋予给了一个不会说话的“法典”,而法典一经诞生却又具有了独立的“意志”,这就是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习惯、风俗等等赋予了法律文字新的含义,这时它已经脱离了立法者对它的意图的束缚,而揉进了许多新的内涵,从而丰富了法律、发展了法律,进而完善了法律。即使当初的立法者依然存在,恐怕连他也无法说清楚这时的法律的真正内容是什么,因为他面对的同样是一个独立了的文本,对他而言,这一法律文本就是新的,一个附加了内涵的法律。更何况这只是一种假想,因为历史上哪些人被视为立法者?如何发现这些人的意图?当这些意图彼此不同时,如何整合为统一的意图?人们要发现朋友、同事、对手或者恋人的意图都相当困难,怎能指望法官发现或许都已死去的过去那个时代的立法者的陌生人之意图呢?那么仅仅依靠法律文字所说的意图可以吗?这里尖锐的问题是:由于法律是个无法表达的“哑巴”,不仅如此,还是一个只存一张嘴的“残疾人”,它除了具有不能说话的“嘴”,没有一切肌体。如果仅仅是个哑巴,那么他的意图还可以借用形体语言进行表达,然而法律呢?它不能进行任何意图的传递和表示,它的意图完全交给了它的翻译者或解释者。所以,法律决不是一个“事实清楚明白的观点”(the plainfact view),这就需要法官对法律是什么作出解释。也就是说,法律是什么,不是由国家权力机关确定的,也不是由法律程序确定的,而是把法律视为一种判断与解释,这种态度一经确立,法律制度便不再是机械的东西,人们试图赋予制度以意义,然后按照这种意义进行调整。解释不仅决定了法律为什么存在,而且还决定了法律现在所要求的是什么,法律的价值与内容合二为一了。法律的文字只是法律的形式,而内容及其意义是通过法官的解释来阐明的,法官借助于解释深化了法律的含义,拓宽了法律的适用领域,是一种更加尊重法律的表现。因为所有的解释都力求完美地理解法律。每个解释者都会选择最能确定法律的价值进行解释,经过通盘考虑之后,把它表达出来。只有通过这种解释才能达到对法律是什么的真正把握。所以,德沃金才说,“判断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好的法官把类推、技巧、政治智慧和他的角色意识融合到直觉判决之中,他‘领会’法律胜于解释法律。”[6]
[收稿日期]2006-06-03
注释:
①五大法学家是:巴比尼安(Papinianus)、盖尤斯(Gaius)、乌尔比安(Ulpianus)、保罗士(Paulus又译:保罗)和莫特斯蒂努斯 (Modestianus)。
②Wayne Morrson,Jurisprudence:from the Creeks to post-modernism,by 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1997,pl.原文是:Law,says the judge as he looks down his nose,Speaking clearly and most severely, Law is as I've told you before,Law is as you know I suppose,Law is but let me explain it once more,Law is The Law.
标签:法官论文; 法律论文; 科学论文; 法律学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公平正义论文; 比较法论文; 政治与法律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