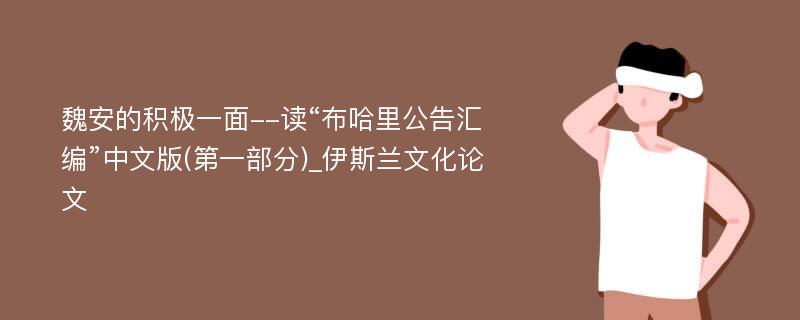
伟岸的正面——读汉译本《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一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伟岸论文,第一部论文,哈里论文,实录论文,全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当远行将归的时候,我总是在别离的瞬间愣怔一下,心里总是在那一瞬闪过这个无法理解的背影。你什么时候才肯转过身来呢?生我养我的母族!要等到哪一次沧海桑田的时刻,你才肯从这世界上迎面而来呢?
——张承志《背影》(注:《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散文卷》第161页。海南出版社, 1995。)
历史与现实无可辩驳地显示出,伊斯兰文化已经成为多元化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大地上的一分子,中国穆斯林已经和正在为祖国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不容忽视的贡献。但是,对很多人来说,伊斯兰只是一个“浪涛般涌动不息、又象高原大山般遥远的背影”(注:《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散文卷》第165页。海南出版社,1995。 )而已;对更多的人来说,伊斯兰甚至只是一个被倾斜的光线扭曲了的丑陋的影子。又有多少人能够稍稍窥视到它真实的正面呢?
文化的主体应该拥有对自己文化的阐释权。中国的穆斯林应该担负用汉语文阐释伊斯兰的责任。这既是文化主体的自我阐释,也是对中华文明的真实奉献。在中国穆斯林的自我阐释之中,伊斯兰将迎面走来,与所有的人正面相向。
一
人类世界历来是一个文化多元的世界。不同的文化之间不是彼此孤立,而是彼此互动的。通常,不同的文化在互动中互相交流、借鉴,并不断地创新、发展。而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互相交流的重要环节。
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上,阿拔斯王朝前期(公元750~847)出现了中世纪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穆斯林学者对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的古籍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和校勘、诠释。著名埃及伊斯兰学者艾哈迈德·爱敏把这一时期称作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近午时期”,翻译运动赢来了学术、文化的发展与创造,那就是公元九世纪中到十一世纪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正午时期”,即文化繁荣灿烂的时期(注:参见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一册“译者序言”。第四册。纳忠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1990。)。
在中国文化史上,佛教自汉代传入以后,经历了以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和玄奘(公元602~664)等为代表的历代高僧大德的译经活动,在隋唐时期形成了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并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一部分(注:参见方立天:《佛教哲学》第27、2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基本上是以民族化的形式实现了中国化。民族化扼杀了伊斯兰教的普世性,滋生了保守性和自闭性。虽然有历代穆斯林先贤筚路蓝缕的奋斗,但至今为止,可以说尚未形成一个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学术翻译和创造的运动。明末清初的汉文译著活动无疑是学术翻译和创造的一次尝试,但由于清代政治气氛和穆斯林社会地位的变化,这次活动没有能够彻底而完整的进行下去。以至于有国外学者认为汉文译著只是“中国穆斯林的辩护性的著作,解释伊斯兰的信仰并努力去证明伊斯兰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主流生活和文化及其传统的儒教是一致的”;“中国伊斯兰教的孤立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其在智识上的相对贫乏”,“在这片土地上从未产生过在伟大的伊斯兰思想传统及其神学的、哲学的和教法学的成就方面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注:Raphael Israeli, Muslims in China: A Study inCultural Confrontation(以斯莱利著《穆斯林在中国:文化冲突研究》),Preface by C.E.Bosworth,New Delhi,1980。)这种说法尽管片面,却也道出了不少个中滋味。
汉文译著学者的学术活动基本上是寓“译”于“著”,以刘智的《天方性理》等著作为代表,实际上是一种融入了作者自身思想的创作活动。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伊斯兰正统教义学、苏非主义、儒家思想甚至古希腊新柏拉图主义的痕迹,作者在不悖离伊斯兰基本教义的前提下,运用这些资料建构自己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学术体系。而在经典和学术著作的纯粹翻译、介绍方面,汉文译著活动没有充分展开。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穆斯林的经堂教育一直使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教材,汉语文的使用很少,汉文译著在传统经堂教育中的影响也很有限。因此,从伊斯兰的基本经典《古兰经》和圣训,到其它一些重要的伊斯兰学术著作,其汉文翻译是很晚近的事。直到1927年才出版了第一部《古兰经》汉文全译本(注:铁铮译:《可兰经》,北平中华印刷局,1927。)。近代以来,以马坚为代表的一批接受了现代教育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在翻译介绍伊斯兰经典和学术著作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解放后极左路线的干扰又使这一努力陷于停滞。因此,伊斯兰经典和学术著作的汉译活动一直没有能够充分展开,这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伊斯兰学术研究的发展。
作为文化主体,中国穆斯林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实践者和创造者。但是,伊斯兰经典和学术著作汉译活动的薄弱,限制了中国穆斯林对优秀伊斯兰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削弱了中国穆斯林对本文化的阐释能力,也制约了中国伊斯兰学术研究与整个世界的交流和接轨。结果是,伊斯兰的背影尽管庞大,却正在离我们远去(或者是我们在离它而远去);它投射在身后的影子,也越来越扭曲和不真实。
二
改革开放为学术研究带来了又一个春天。中国伊斯兰学术研究取得了众所周知的巨大成就,而第一部汉文圣训全译本也随之诞生了。
“圣训(al-Khadith al-Nbawi )”意指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语、行为、指示或默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圣门弟子(直传弟子)和再传弟子及三传弟子的言论和行为也被收录了进去。经辑录定本的圣训集被视为仅次于《古兰经》的伊斯兰教基本经典,是对《古兰经》基本思想的阐释,是伊斯兰立法的第二位渊源和依据,对伊斯兰文化的传播有重要作用。公元十世纪时,已先后出现了多种正规的圣训集和成文的圣训法典。布哈里、穆斯林·本·哈贾吉、艾布·达乌德、提尔密济、奈萨仪、伊本·马哲等人分别辑录的圣训集,后世学者称之为“六大圣训集”。其中《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被称为“圣训两真本(alSahihān)”,最具有权威性。(注:参见康有玺译:《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译者序”第20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第502—503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
中国穆斯林中广泛流传的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圣训集《虎托布》 (Khutab),是经堂教育的传统教材之一。李廷相(虞辰)将其译为汉文的《圣谕详解》,1923年由天津光明书社印行(注:庞士谦:《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见于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附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庞士谦翻译了《脑威四十段圣训》(al-Arba'ūn al-Nawawiyyah),1947年由北平伊斯兰出版公司印刷、 黎明学社发行(注:《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第422页, 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这两种是较早出版的圣训汉译本。
解放后比较重要的汉文圣训译本主要有以下几种:(1 )《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马宏毅译;北京黎明书社1950年版。(2 )《圣训经》,陈克礼于1952年译出;( 3 )《圣训珠玑》,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1982年出版了阿拉伯文版,穆罕默德·奥斯曼于1984年译为汉文印行;(4)《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宝文安、 买买提·赛来从维吾尔文译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这些圣训集大都是六大圣训集的摘录本,虽然各有特色并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了各大圣训集的精华,但不足以反映圣训的全貌。《古兰经》已经有了十几个汉文译本,与此相比,六大圣训集尚无一个完整的汉译本,这显然已不能适合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上述几个圣训汉译本都没有公开出版,发行范围与影响力都存在问题。
此时,环境的许可,现实的需要,再加上译者个人的虔诚举意和不懈努力,共同促成了第一部汉文圣训全译本《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的出版,这是中国穆斯林和中国伊斯兰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事件。
三
《布哈里圣训实录》是伊斯兰教内公认的六大圣训集之首。布哈里(al-Bukhān), 全名穆罕默德·本·伊斯玛仪·本·伊卜拉欣·本·穆吉拉·布哈里,伊斯兰历194年(公元810年)生于中亚布哈拉。他用16年时间周游世界各地,搜集、鉴别、整理圣训,最终编纂成了《布哈里圣训实录》,于伊斯兰历256年(公元870年)逝世。《布哈里圣训实录》共计97章,3450节,始于“天启章”,终于“讨黑德章”。共收录了9082段圣训,除去重复的,传述世系完整的圣训共计2762段(注:康有玺译:《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译者序”第25页。)。
《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的汉译者是一位年轻的穆斯林学者,他凭着信仰及对学术的追求,独立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翻译工作。译者参考了阿拉伯文《布哈里圣训实录》的七、八种版本,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国王印刷厂版,巴基斯坦拉合尔版,黎巴嫩贝鲁特书局版以及伊朗版等。译文共九卷约160万字,将分四部(四册)陆续出版, 第一部(一、二卷合订)已经出版发行。
《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的汉译不仅是单纯的翻译工作,译者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在领会、表述原文的含义及体例编排等方面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在译者序中对圣训的基本知识做了介绍
译者在卷首的“译者序”中简要介绍了自己翻译这部圣训集的动机,认为“译五洲之学术,以裨华夏学术,是中国学术之一大任务”(注:康有玺译:《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译者序”第19页。)。然后对圣训的定义和意义、圣训传述和记录、圣训的辑录、布哈里的生平及《布哈里圣训实录》的概况等作了介绍,使读者开卷之初能对本书有一个大略的了解。
2.部分篇的开始加了导言
鉴于《布哈里圣训实录》是分类、分篇编排的,译者在部分篇的开始加了“导言”,对该篇的主题作了言简意赅的解释。例如第一篇“启示篇”的“导言”中,译者简要解释了伊斯兰教中“启示”的概念,以及本篇涉及的主要内容。导言使读者对本篇的内容及所涉及的宗教内涵有一个大概的把握,对于那些对伊斯兰教不太熟悉的读者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3.在每段圣训后列出了与该段圣训相关的圣训段数
译者在每一段圣训的后面都列出了与之相关的其它圣训的段数,以便于读者查找和相互参照、理解圣训的教导。这是一项艰苦、浩大的工程,译者全凭记忆和对每一段圣训的熟知而完成这项工作。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付出的艰辛,以及他对圣训的熟悉程度。译者的这项工作还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先知穆罕默德对同一类事情的处理方式并不一定完全雷同,而是有很大的灵活性。有的穆斯林往往只抓住某一段圣训,忽视其它相关的圣训段落;这往往是穆斯林各执一端、互相纷争的原因。如果互相参照、全面理解和把握圣训,则可以减少这些无谓的纷争。
4.在文意的理解、翻译和表述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译者在对某些圣训段落的文意理解、翻译和表述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例如“天启篇”第一段圣训:
欧麦尔传述:我听见安拉的使者说:“任何行为都取决于动机。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其动机所导致的结果。一个一心为获取现世享受或为娶得一位妇女而努力者,其努力不会付诸东流”。(注:康有玺译:《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3页。)
同一段圣训,马宏毅译为:
由欧默尔传来:他说:我听主的使者说:“一切行为,惟凭立意。每人获得他所立意的。为主圣而迁徙的人,他的迁徙是为主圣了;为谋取现世,或为聘娶妇女而迁徙的人,他的迁徙,是折本的,是卑鄙的”。(注:参见马宏毅译:《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
这段圣训的主旨可以简单图示为:动机→行为→结果。先知肯定每一种努力会获得报偿;但穆斯林追求的是两世吉庆,后世的报偿更具有终极意义。对于追求现世享受或女色的人来说,他所获得的只在他追求的那件事情本身。这其中的含义既有肯定又有否定;肯定他的努力会有回报,否定他的努力会有终极意义上的回报。《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的汉译者在这里译为“其努力不会付诸东流”,强调了对人的努力的肯定,这是以前的译本所没有注意到的。可见译者在理解文意、推敲词句上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5.不使用晦涩的经堂语
经堂语是中国伊斯兰教清真寺经堂教育中使用的一种专门语言。指运用汉语语法规则将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三种不同词汇或词组交互组合成句的独特汉语表达形式。中国穆斯林习惯在讲解教义、翻译经训时使用经堂语,如陈克礼译《圣训经》就使用经堂语。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经堂语晦涩难懂。这无形中阻碍了更多的人来了解伊斯兰教义。在这部《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中,译者完全避免使用经堂语,而用流畅、平实、简洁的现代汉语来表达,使任何人都能够毫无困难地阅读和理解,这是该译本的特色和成功之处之一。
四
汉译《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是作为季羡林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西亚北非文化编》的一种出版的。季羡林先生在“《东方文化集成》总序”中指出,世界文化“共可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再扩而大之,全人类文化又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我们责怪西方不了解东方文化,不了解东方,不了解中国,难道我们自己就了解吗?如果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就应该坦率地承认,我们中国人自己也并不完全了解中国,并不完全了解东方,并不完全了解东方文化。实在说,这是一出无声的悲剧”。(注:季羡林:“《东方文化集成》总序”。参见《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卷首。)
中国穆斯林处在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交汇点,这既是优势又是劣势。试问,中国穆斯林对同样博大精深的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有怎样的认识和把握呢?季羡林先生的上述反省毫无疑问地适用于中国穆斯林。可以欣慰的是,以学术泰斗季羡林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并开始纠正这一缺陷,而其中也包括中国穆斯林学者。汉译《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的陆续出版,就是一个例子,将有助于让更多的人从正面认识伊斯兰文化。这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
《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的汉译者的“译者序”中指出,“到目前为止,除了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有若干汉语译本外,其他有关介绍伊斯兰思想文化的汉语书籍,不仅品种和数量很少,而且极不系统,就连在伊斯兰教中其地位仅次于《古兰经》的六大部圣训集,也没有一部完整的汉语译本;学术界对此的研究也是凤毛麟角,而且多从西方学者的第二手资料入手。至于那些上承古希腊哲学并对欧洲哲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伊斯兰东方和西方的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诸如艾什尔里、铿迭、法拉比、伊本·西那(阿维森那)、安萨里、伊本·路世德(阿威罗伊)、伊本·阿拉比和伊本·泰米叶等等,及他们的著作,在中国至今仍是一片空白”(注:康有玺译:《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译者序”第19页。)。把东方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伊斯兰文化介绍到中国,让中国人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东方文化,中国穆斯林学者在这一工作中似乎负有更多的责任。因为,作为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实践者和创造者,中国穆斯林对伊斯兰文化的理解和阐释就不仅仅是一个翻译介绍的问题,而且更是一个认识自我、适应社会、更新发展的问题。
对于《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的汉译者来说,该书的翻译只是一个开始。 以下几部著作的翻译已经提上了日程:伊本·哈勒敦(IbnKhlidun )著《历史绪论》(Muqddimath ); 伊本·泰米叶(Ahamadibn Taimyyath)著《信仰论》(Kitab al-Yiman);勒什德·利达(al-Said Muhammad Rashid Ridra )著《穆罕默德的启示》(al -Wahay al-Muhammad);伊本·图菲利(Ibn Tufail)等著《觉民的儿子灵活》(Hyyi ibn Yaqzan);等等。 仅以伊本·哈勒敦为例略加介绍就可以看出,这些著作是何等的重要。伊本·哈勒敦(1332—1406),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活动家。这是第一个承认经济和政治之间有协同作用的中世纪思想家。他在《历史绪论》中对政权和经济的兴起、成熟和衰落的周期性做了深入、清晰的分析。他认为,正常的经济产生于基本的需求和社会的团结。一旦生产力过剩,社会凝聚力就会减弱,人就会堕落,这往往是追求享乐所致。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他的著作在欧洲翻译出版后引起了广泛重视,被列为“一千年中最杰出的十大经济学家”之一。(注:肯巴·邓纳姆:《一千年中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原载香港《亚洲华尔街时报》1999年1月 15日;转载于《参考消息》1999年1月29日第四版。 一千年中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分别是: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伊本·哈勒敦(1332~1406),亚当·斯密(1723~1790),约翰·穆勒(1806~1873),卡尔·马克思(1818~1883),莱昂·瓦尔拉斯(1834~1910),约翰·凯恩斯(1883~1946年),密尔顿·弗里德曼(1912~)。)但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中国穆斯林学术界却仍对这样的著作知之甚少,如季羡林先生所言,“这是一出无声的悲剧”。
目前,国内回族研究、穆斯林与伊斯兰教研究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有一批固定的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有定期、不定期举行的各种学术会议,有各种不断问世的学术著作;但是毋庸置疑,在翻译介绍伊斯兰经典和学术著作方面仍很薄弱,这使我们在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和接轨时出现错位和力不从心的现象。所谓“知己知彼”,我们这些中国人,我们这些中国穆斯林,应该怎样做呢?
人是文化的能动的主体。一个文化不会离人远去,除非是人自己弃绝了它。伊斯兰经典和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将为我们展现伊斯兰文化的伟岸的正面。她迎面走来时,我们就认识了我们自己。
《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一部),康有玺译,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