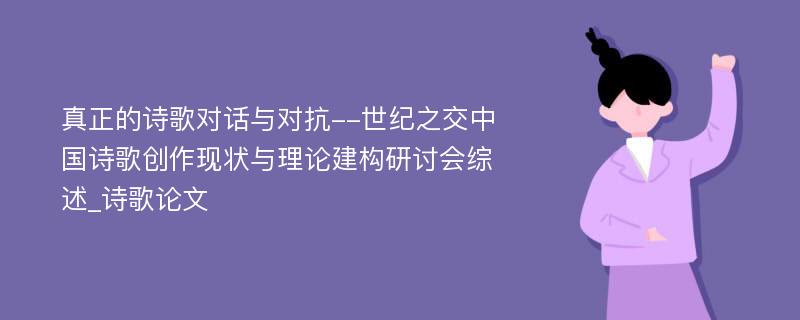
一次真正的诗歌对话与交锋——“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中国论文,态势论文,研讨会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4月16日至18日,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室、 北京作家协会、《诗探索》编辑部、《北京文学》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市平谷县盘峰宾馆召开,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近40位重要诗人,诗歌理论家和批评家与会,并就一系列诗学问题展开了热烈的对话与研讨。这是继去年3 月在北京召开的“后新诗潮研讨会”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的诗歌会议,同时也势将成为世纪末的一次具有总结与清理意义的重要会议。它既是对20年来新诗潮发展历程的认真回顾,也是对新世纪诗歌前途的认真面对,也是对诗歌在当下的处境、情状、以及诗人应持的写作立场的认真检讨、辨析与反省。谢冕、吴思敬、李青、兴安共同主持了此次会议。
一.承接与回应
1998年3 月召开的“后新诗潮研讨会”在整个诗界与新诗潮内部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因此这次会议既是对这些“反响”的回应,也是试图将问题再予深化和向前推进一步。正如在会议开幕时吴思敬所说的:去年的新诗潮研讨会之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有的报刊(如广东的《华夏诗报》)连续发文“批判”,在青年诗人内部也发生了观点上的分歧分化,从《诗探索》陆续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也可以看出这些不同的乃至相反的意见。基于这样的背景,此次会议想把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希望大家能各抒己见,有交锋和对话。
谢冕在主持发言中对此次会议的意义作了阐发,他说,现在距“南宁会议”刚好是20年,距朦胧诗的首次发表也是20年,新诗潮浮出地表整整20年了,马上就要进入新世纪,因此这是一次有“象征意义”的诗会。去年的会议侧重围绕着新诗潮的历史进行争论,今年的会议着重讨论诗歌怎样发展。毕竟历史是前进的,过去的争论与现在的不同,那时争论是不平等的,作为当事人,我有压力。现在是不同意见的交换,现在的争论是内部的,是艺术中的争论。而过去新诗潮的处境是很困难的,不光有来自意识形态的否定,就连艾青、臧克家和田间等前辈也都不赞同新诗潮。
回顾新诗潮的历史,谢冕认为,无论如何都应看到历史的进步。不要小看分歧和争论,这是好事。关于新诗潮的争论是20年来的一件大事,其影响不仅是诗,而是整个文学,它是一个打在历史上的“楔子”,在病变的时候,呈现了生机,打破了单一的模式,统一的文学成为分裂的文学,僵硬、刻板的思维表达被改变,恢复了现代性的追求,改变了文艺观念,广大的批评者、作者、读者全部拒绝了教条。谢冕指出,基于此,大家都要珍惜这一笔精神财富,新诗潮既是历史进程的成果,无疑是接受了已有的诗歌传统,但它本身也已成了一个新的传统,不管是否承认,它都影响着今天。
在评估当下(包括90年代以来)的诗歌“态势”时,与会诗人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分歧,这种分歧显然由来已久,在此前的数种“诗选”和“年鉴”(如程光炜主编的《岁月的遗照》和杨克主编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中已经反映出来,由于各自的立场有所不同,评估的对象和态度也就有差异。来自天津的徐江认为,目下的诗歌的确远离了读者,完全成了书斋性东西,语言本身缺少活力,缺少原创性。明清时代的诗为什么没有力量?那是因为还在使用古代的语言。于坚说:有人讲诗歌衰落了,我认为,衰落的不是诗,而是伪诗、伪诗人。诗的衰落始自50年代的假大空话,现在它又变了一副面孔——庄严、不可侵犯,仍据守着关口。另外,权威诗歌刊物实则是平庸的刊物,真正的好诗都在民间。与之持近似观点的还有伊沙和杨克等。伊沙说,有的诗集像是在造“密码”,“不说人话”,拒绝读者必然也被读者拒绝。 杨克认为, 90年代诗歌被公众所冷落,除了诗歌天然的原因以外,还应从对比中找些原因。小说界不断地推新人,诗歌界却总是“那一个房间中的几个人”,缺少新桃换旧符,缺少更灵活的方式,有些诗增加了一些叙事的因素,但对现实语境的关注却很不够,玄虚成为一种风气,不能有效地进入公众的审美空间。
另一些诗人和批评家对此则持不同意见,认为抽象地以“脱离生活”和“现实”这样一些词语来评估目下诗歌的缺点,与某些媒体或心存偏见的人的“调查”并无二致。唐晓渡说,诗歌界有一种不断变换着面孔的“权威”,就是以其对“生活”和“人民”一类词语的解释权来压制别人,究竟是谁给了你这种解释权?孙文波说,“生活”这个词非常有权力的意味,诗人本来都在生活之中,所想所写其实都未离开“生活”,当一个人在谈“深入生活”时,说明他已经高高在上了。陈超认为,评估90年代的诗歌要有种兼容的眼光,有不同的立场和标准是好事,就像一座树林,不能只栽一种树,否则就会生病,对立也不是什么坏事,但还要讲多元性,老虎不应责备羊不那么凶猛,也不能用孔雀的立场要求老虎。有一些批评家炮制出来的隐喻性说法和据此所作出的判断是有些武断的,比如说某种诗是“乌托邦写作”、“寄生性写作”、“集体写作”等等,应在具体辨析之后下判断。其实,个人乌托邦的建立是消除“集体乌托邦”的真正开始;“寄生”于种族历史、记忆与事件的写作对改变原有的御用性的寄生写作不是很有意义的吗?甚至有些还不够;比如对文革,就没有达到对专制主义的个人与集体心理学的研究层次,还应加强;另外,“集体写作”不是一个地缘化的问题,而是现代性艺术的一个普遍特征,真正的诗人并不害怕运动性;只有比较弱小的诗人才害怕它,因为他那点可怜的个性很容易被淹没。
二.交锋与对话
在诗学主张和写作立场上,与会诗人与批评家之间产生了明显甚至尖锐的分歧。对这种分歧,大家普遍认为是正常的。在80年代,由于新诗潮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强大的外部压力,所以其内部虽然主张各异,但却有相近或互为呼应的立场。90年代,随着市场与物质主义时代的来临,诗人的写作立场则趋于更加深刻的偏执,并带上明显的“表演”色彩,其根本性的“立场”和特定情境或对立关系中具体“策略”的关系更加暖昧、难以区分,所以误解和分歧是难免的。当然也不排除某种“圈子”的因素,不排除某种对于“权力”的谋求,但总体上仍然是出于对当代诗歌前景与方向的认真关注。
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分歧与对话的双方分别站在了“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旗帜下。其中前者比较明确,力主倡导民间的,与日常生活与现实语境发生密切关联的“原创的”、富有活力的口语性写作,批评过分依据知识优势的,以翻译诗歌为写作资源的“让人头晕”(沈奇语)的“知识分子写作”(这当然不是“知识分子写作”的全部内涵与特征),基于此,另一些不同意见者就自觉或“不得已”地站到了“知识分子写作”的旗帜之下,发言为之辩护。
对“知识分子写作”批评比较尖锐的是于坚。他说,我为什么批判知识分子写作?是出于诗歌本身的考虑。你为知识分子辩护,为什么不为诗辩护?诗人首先是一种异类、赤子,他要关心大地、关心环境、关心日常生活,在自己的母语之光的照耀下写作。在鹿特丹参加诗歌节时,一个美国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学英语?他不是恶意,我却很生气。我为什么要学英语?汉语诗歌本身就有丰富的表现力,当时我朗诵我的诗,现场翻译为荷兰语时,一片笑声,荷兰人说想不到中国人如此幽默,中国人怎么就不能幽默呢?汉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我们完全不必去用西方人的“话语”。诗人的立场就是诗人的立场,立足于观察生活,不必给自己制造某种“被压抑”的身份。“日常生活”并不是一个贬意词,但50、60年代以来却被排斥在写作之外,诗人热衷于写宏伟的观念,但却离开了真实。我渴望平庸地活着,写不朽的作品。某种意义上,没有庸俗的德国小市民的歌德,就没有伟大的诗人歌德。但在我们的当代历史中,我们却一直没有稳定的与历史相联系的日常生活,变来变去,文化的变动使大家成了没有记忆的人,永远生活在一个地震后的唐山里面。我们没有“存在的诗人”,只有“关心存在的诗人”,没有原创性的写作,这一点比不上古代。西方人非常尊重古代的中国诗人,可李白、杜甫连越南老挝都不知道。
持批评“知识分子写作”立场的还有伊沙、沈奇、杨克、徐江等。沈奇说,“知识分子写作”也反映了一种“文化心态”,即理论贵族的心态。我20年来坚持无旁顾地阅读诗歌,可读“知识分子”的诗还头晕,这是否说明它有问题?伊沙与徐江主张诗歌界应向公众敞开,诗人应在今天的市场时代谋求生存之道。甚至“中性”意义上的“炒作”也是可以的、必需的。伊沙说,我不为读者写作,但却不拒绝阅读,至少应在语言的第一个层面上让读者进入。有时误读也很好玩,总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对于上述批评,王家新作了尖锐的反驳,他说,有人讽刺我是写“国内流亡诗”的,说我的诗“不够鲜活”。“知识分子写作”何罪之有?任何伟大的诗人都不可能完全与他的时代保持一致,不是一致感、而是错位感造就一位伟大的诗人。主张写所谓鲜活的“日常生活”、还讲什么“炒作”,这同“生活的美容师”有什么区别?这种诗人不过是消费时代的弄臣。孙文波也为“知识分子写作”作了辩护,他认为这一概念是相对的,李白和杜甫也是“知识分子”,因为在知识系统里他更高些。这一概念的提出和使用与当代语境的变化有关系,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于坚说诗人“不左也不右”,这种所谓的“民间立场”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另一种潜在的有针对性的语义。在我看,“知识分子”不是一种特别的身份,而是一种理解。在目下的语境中,资源共生是一种必然,许多伟大的诗人都同时是知识分子,写作无法回避西方的文化与精神资源。诗人西渡也反驳了否定知识分子写作的观点,他说有人不能从知识中获得乐趣,但知识并不脱离生命,人对知识的热衷是人类前进的动力,将利用西方的诗歌资源说成“买办”是一种强辞。伊沙说诗要写得都让人懂,这也是老问题了,没什么新意,懂不懂不能以人数论,以发行量论,即便是发行两万册,相比13亿人那也还是少得可怜。
唐晓渡在发言中也为“知识分子写作”进行了辩护,他指出,这一概念是当代中国特定语境中的产物,之所以这样提,是因为它的缺席。它不是一个诗学命题,如“个人写作”一样,大家心里都清楚它在当代语境中是什么含义。这怎么能变成一种被攻讦的口实呢?以前对现代诗的指责是“数典忘祖”,现在这些曾多受西方现代诗及文化资源的恩惠的人又反过来“扮演”西方文化的反对者,是否有点“过河拆桥”的味道?关于“原创”问题,能否有真正的原创?作为诗学问题,不要把它变成一种尺度。诗歌当然有反对已有的知识体系的东西,但它在根本上仍是要建立一种文明,而不是破坏。
程光炜、臧棣等人的发言既是为“知识分子写作”辩护,也是为批评工作辩护。程光炜说,我在编选《岁月的遗照——90年代文学书系·诗歌卷》时,心情比较复杂。我倾向于持“知识分子写作”立场的诗歌,但阐述他们与西方诗歌的关系主要是客观分析,并不全是赞成。批评当然会带有倾向性,有其艺术的旨趣,而不是以人事为标准的。臧棣说,我有自己固定的趣味,但在扮演批评家角色时我尽量开阔视野,以多样性的角度来整合诗歌。但许多事实证明这很难,批评家现在被迫只能做有倾向性的工作。
三.静观与辨析
对上述双方各自在“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名义下争论与交锋,一些“局外”的批评家认为,显然双方的态度是认真的,但置身其中,表达难免有某种“角色感”,同时也意识到一种由来已久的分歧正在加深。因此他们的发言集中在比较客观的分析上。陈仲义全面分析了两种诗学立场的优势与不足,倡导在强调差异的同时也要看到共同性。他说,这次争论与分歧看来很难绕过去。我从沈奇、于坚等人的文章中看到先锋诗歌内部的分歧,我想这可能不是一两年的问题。它非常复杂,既包含了一些非诗的因素,同时也是各自对自己的写作向度的极端推崇。在我看,“知识分子写作”所着重强调的是一种独立的和批判性的立场,它在文本特征上接近于一种“智性写作”;而“民间写作”所强调的是写作的某种“平民”立场,从文本角度看比较接近于一种“口语”写作。从前面的发言中,我看到于坚对神学、知识写作是予以坚决否定的,陈超是兼容的,唐晓渡和程光炜是维护“知识分子写作”的。我想对两者作些具体分析。首先,口语写作的优势是它立足生活的原生态,强调写作的原创与本真,80年代以来对当代诗歌有很大贡献,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在清除语言的文化积垢上做了很大的推进工作。但问题也在于:口语诗是否也特别容易炮制?举个例子,杨黎的《大声》:“我们站在河边上/大声地喊对面的人/不知他听见没有/只知道他没有回头/他正从河边/往远处走/远到我们再大声/他也听不见/我们在喊”。这样的诗我好像也能写,而且一天可以写三首(他读了自己的一首“戏仿”之作),但杨黎的诗却能入选《1998年中国新年鉴》,我的却不能(笑)。所以从质量上是难以判断的,每种诗都有其长处,也都有局限,但诗人的排他性常常会把一种写法当成唯一的。我看,在这个多元化的相对主义时代,还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吧”。其实,刚才过多强调了差异性,两者的共同性也不少,比如就日常性和及物性来说,臧棣的《燕园纪事》也有这种特点,但他的日常性与于坚不同。其次,再看“知识分子写作”,优势不说了,缺点也是明显的:写作趋向弱化,走向学院的、书斋式的写作。新诗写作的资源比较少,没有多少既成的东西可以遵从,因此模仿大师是可以的,但西方的写作成为唯一的资源,轻视当下本土,诗中过多的引用,修辞至上,语言艰涩,也是比较明显的问题。与之相比,口语诗体现了对强势文化的反抗,但掌握不好,差之毫厘就很容易掉入陷阱,成了“口水”。由此看,双方的优势和不足互现,不足互现没有必要一争高下。
唐晓渡的发言中也提到,要警惕把诗歌批评变成一种“舆论”,把正常的争论变成“态势”。去年的“后新诗潮研究会”后,有人在报纸上发表了“述评”,把会议上的讨论归结为“拥护和反对”的两派,成了一种煽动性的渲染。现在有人又以“诗歌的真相”为题分析“态势”,这也接近于一种舆论操作,“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怎么会产生了对立?这是个很大的玩笑。沈奇说,要警惕“把信号放大”的做法,批评家要看到诗歌的“新的增长点”,把目光移出旧圈子。在先锋诗歌的处境改善之后,要防止诗人的心理发生隐秘的变化,防止利益取代责任,冲淡情怀。
张清华的发言强调了“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统一性和互补性。他说诗人之间的分歧并不令人惊讶,令人惊讶的是双方竟然是在“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两个词语下进行交锋。在我看,它们的含义不但不是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在当代的语境中尤其如此,“知识分子”的非体制性同“民间”的概念很接近。从写作来看,两者一个强调活力,一个强调高度;一个倾向于消解,一个倾向于建构,正好优势互现,因此大家要达成兼容互谅,保持自省。不过大家都共同交往这两个诗学命题,我认为是出于一种寻找秩序的责任感,不是偶然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处理得好,诗歌有幸。
四.“依然没有结论”
会议经过近三天的讨论,与会者充分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和立场。应了主持人谢冕先生所提倡的三个原则:“交流就是目的,理解高于一切,依然不会有、也不试图有任何结论。”
任洪渊的发言自称是“独白”,但实则既强调对西方诗歌资源的整合,又更强调对汉语自身资源的认识。他认为,汉语自身的整合力与生命力是非常强大的,它曾把梵语的佛改写为中国的禅。自老子的“名可名、非常名”开始时,这一伟大的语言运动就开始了。在这一思考下,我才读懂了巴特和德里达。汉语中的每个词都是活的,富有弹性的,而西方的翻译语体却很可怕。李贺的“凄凉四月来”比之艾略特的《荒原》中的“四月是残忍的月份……”如何?早就点破了这一点的还有李清照的“绿肥红瘦”。当代的中国诗人为什么没有充分表现出汉语的丰富性?我们曾经看到了带回了里尔克的冯至,看到了带回了凡尔哈仑的艾青,当代的诗人在效仿西方诗人的时候是否是成功的呢?
林莽分析了此次会议上的争论,认为非常有意义,它是对80年代一些诗学论争的继续。他认为当代诗歌还没有显示出某种丰富而又统一的成熟。现在的争论开始逐步接近深层的问题,应沉下来。作为个人来说,他表示我只想写一点使我的生命能够颤抖的诗,写出对生活的某种痛感。
刘福春认为论争和交锋是正常的,新诗已有80年的历史,接收了传统经验与西方的诗歌资源,世纪末的新诗应该是丰富的。原来是“辫子军”与“先锋”的对立,现在先锋诗歌内部又出现分化,这是好事,分化得还不够,还得继续,也许过几年伊沙与于坚就会分道扬镳,虽然他们现在还观点一致(笑)。 但要警惕形成圈子。口号要提, 也要注意到分寸和尺度。
会上发言的诗人还有车前子、小海、侯马等。最后主持人李青与吴思敬分别作了总结发言。李青说,北京作协已先后举办了多次这样的会议,伴随了当代诗歌的历史进程,很有意义,今后还要继续为推动诗歌事业的发展献力。
吴思敬在最后的发言中对此次会议内容进行总结概括。他指出,在世纪之交,这次会议是先锋诗歌的一次汇聚。大家真诚坦率地交换意见,对“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和“口语化写作”等问题的认识都深入了一步。比如“知识分子写作”目前虽然有一些问题,但体现的精神却值得尊重。“口语化”似易实难,十分复杂。还有与外来文化的衔接问题,和古代诗学传统的联系问题等等,大家都有认真和深入的见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大家有分歧不要紧,只要态度真诚,就会达成谅解。我个人认为,诗歌还是不宜“炒作”,另外诗人有点“大师情结”也不是坏事,自信心是必要的。
最后,吴思敬代表《诗探索》表示,他们将为推动当代诗歌的发展竭尽全力,理论上的对话与争鸣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诗人要拿出文本,用自己的创作实际影响和获得读者,真正的诗人是不会被历史淹没的。参加会议的还有:刘士杰、西川、章德宁、柴福善、静矣、张颐雯、杨少波等。
[本文根据在会议上的记录整理,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
199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