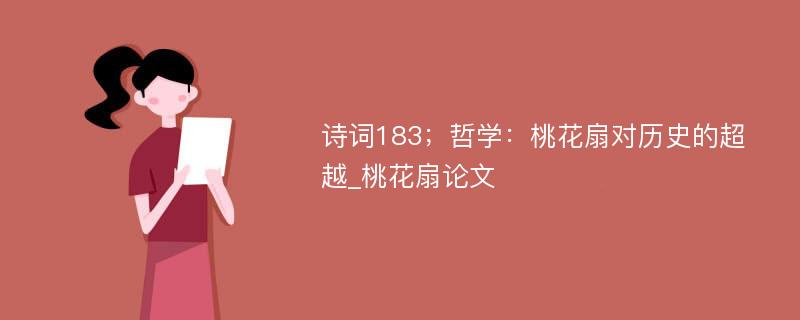
史断#183;诗意#183;哲思——《桃花扇》对历史的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思论文,诗意论文,桃花扇论文,历史论文,史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8)01-0090-05
《桃花扇》是文学史戏剧史上最优秀的历史剧。康熙三十八年,剧本甫脱稿,“王公荐绅,莫不借抄,时有纸贵之誉。”(《桃花扇本末》,后文随文注均见于刘叶秋《桃花扇》整理本及附录)此后京城搬演《桃花扇》“岁无虚日”。300多年来,《桃花扇》或被改编为影视,或继续活跃于舞台,或作为文学读本,其艺术魅力历久弥新,其中的奥妙何在?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1
作为历史剧,《桃花扇》严格遵守了历史真实的原则。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说:“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这一条材料透露了两个信息:一,孔尚任早在出仕之前就有写作《桃花扇》的打算;二,作者所追求的创作目标是“信史”。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作者在十数年间,阅读了大量的资料,仅《桃花扇考据》里列举的就有11个作者的12种集子,其中既有历史著作如《樵史》、《绥寇纪略》,也有清初人的诗文别集。事实上远不止于此,如余怀的《板桥杂记》,也是作者必读之书。有关秦淮旧院的情况,清初人的口头传说自然是一个重要的渠道,作者亲历其境观察感受可以说是更重要的途径。我们知道孔尚任在淮扬等待疏浚下河入海口期间,曾经游历江宁,遍访名胜古迹和前朝遗逸,其中不乏有针对性地重点寻访,如往栖霞山拜访张薇就是一例。但是更具体细致的信息则直接来自于《板桥杂记》。剧本《访翠》、《传歌》、《眠翠》的描写和材料均源于《板桥杂记》。既然如此,那么作者理应将此书列入《考据》之中。事实也确实如此。据袁世硕先生《孔尚任年谱·孔尚任交游考·余怀》一文所云,孔尚任与余怀有过交往,亟思拜谒,“搜讨旧闻”,并与其子余宾硕过从颇密,而且《桃花扇》康熙四十七年的刊本《考据》里确实有《板桥杂记》,并列了16条。后来的刊本为什么又把是书从《考据》中删去?笔者认为重要原因之一是《板桥杂记》无关乎“南朝新事”,或者说与“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关系甚微。由此我们也可推知孔尚任《考据》中所列书目,大都关乎南明朝政、剧中人物、剧中重要情节。以此为原则,《考据》所列书目只是一部分,相关的大多数书并不在其中。
除了阅读大量的文字资料,孔尚任还走访了与剧情有关的南明遗逸及侯、李情事的知情者,核实史料,增加感性认识,揣摩氛围细节。治河三年,于孔尚任的仕途并无帮助,却成就了他创作《桃花扇》的夙愿。他利用河工迟迟不开自己无事可做的闲暇,走访扬州、仪征、南京等地,结交遗逸名士,袁世硕先生《孔尚任交游考》表明仅与《桃花扇》有关的人,除了旧交孔尚则、秦光仪、贾应宠3人外,还有21人。
少年时萌生的感兴,出仕前的创作计划,数十年间“搜讨旧闻”,孔尚任对南明旧事有了清晰具体的认识,不致于让其作品有“戏说”的成分。功夫不负有心人,《桃花扇》一剧让作者最自豪的两点,一是其“实录”的品格,一是“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结构。我们看第一点。《桃花扇·凡例》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把这一段话放在《凡例》中,可以看作是该剧的创作准则,也是作者最得意之处。因此,剧中每有时机,就要作出提示和表白。《先声》、《孤吟》借老礼赞之口说:“实事实人,有凭有据。老夫不但耳闻,皆曾眼见。”“司马迁作史笔,东方朔上场人。”“当年真如戏,今日戏如真。”老礼赞既是剧中人,也是观众,以南明王朝过来人观看反映南明朝政得失的戏剧,赞叹其真实性自然有极大的权威性,远远超过观众印证历史后得出结论,有力度。借老礼赞突出剧作的真实性,恐怕是孔尚任剧中安排两出老礼赞独角戏的用意之一。如此安排,作者感到仍然不能做到醍醐灌耳,于是不惜自己出来直接说话,每一出均有句批和总批。这些批语,除了抉发本出在全剧中的结构作用,另外一个重要主题是提示该剧的历史真实性。《阻奸》出曰:“句句曲白,可作信史,而诙谐笑骂,笔法森然。”《逮社》出曰:“此折俱从实录……如太史公志传,不加砭刺,而笔法森然。”《迎驾》出曰:“描画拥戴之状,令人失笑,史公笔也。”《沉江》出评论左良玉、黄得功、史可法不同死法,曰:“三忠之死,皆临敌不屈之义。而写其烈烈铮铮,如国殇阵殁者,岂非班、马之笔乎?”这些批语与《凡例》前呼后应,互相印证。
批语中出现两次“笔法森然”、两次“班、马之笔”,显然作者对自己叙述史实的史家笔法十分满意,情不自禁地给予史家最高的奖誉。史家笔法有何特点?同样是叙事,历史学最优秀的传统是直。因为直历史才产生了学科的本体价值,然而真实客观地叙事,只是历史最基本的要求;皮里阳秋,直而能断,所谓的“史断”才是历史叙事的最高境界。达到如此境界,称之为“笔法森然”、“班、马之笔”方可当之无愧。我们如何才能知道孔尚任不是自我感觉良好?《阻奸》一出写崇祯自缢后南都各种政治势力的惶惑不安和蠢蠢欲动。立福还是立潞,不仅涉及皇统再续的问题,而且是晚明以后朝廷党争的继续。史可法显然毫无主张,只是幻想崇祯或太子南渡。因此,当马士英提出迎立福王时,说:“若果如此,俺纵不依,他也竟自举行了。况且昭穆伦次,立福王亦无大差。”侯方域提出“三大罪”、“五不可立”,其实最具有本质意义的只是两点:一是“福邸藩王,神宗骄子,母妃郑氏淫邪”。也就是说福藩曾经借助母妃郑氏的得宠觊觎皇帝大宝,所以今天不能承继大统。这种理由显然是讲不通的。侯方域并非不知此理不通,但他借此勾勒出福王的渊源。万历中期,围绕着立储、正位等类事情,朝廷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东林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政治势力。但是古代立嗣,血统是第一要素,因为有了这个要素才使许多问题简单易行。福王是神宗嫡亲的儿孙,总不能放着直系子孙不立,而立旁支,这也是马士英们拥立福王最有力的根据。因此侯方域提出了第二点:“这中兴之主,原不必拘定伦次的。”并举出历史上最典型的汉光武刘秀的例子。显然史可法、侯方域们拥戴潞王,马士英、阮大铖们拥戴福王都是渊源有自。孔尚任对此洞若观火,拥福拥潞,直书而已,诚为信史。同时作者又不能不表现自己的识断。阮大铖夜访史可法,说:“须将奇货归吾手,莫把新功让别人。”夜访被拒后又说:“老史!老史!一盘好肉包子掇上门来,你不会吃,反去让了别人,日后不要见怪。”《迎驾》出,马士英独白:“幸遇国家大变,正我辈得意之秋。”马、阮借拥戴之功而达到夤缘幸进、谋取私利的真实目的昭然若揭,不加砭刺,而褒贬自现。如此等等,既直且断的《春秋》笔法是《桃花扇》叙事的基本风格。《桃花扇·题词》中沈成垣所说:“云亭作《桃花扇》,是读破万卷之时,其胸中浩浩落落,绝无全牛矣。”也就是说作者已然跳出历史真实的层面,升华出历史的义断。作者的见解,光明洞达,诛乱臣贼子,正世道人心。
2
据上文所述,如果我们认为《桃花扇》事事俱实,则不免又过分胶柱鼓瑟。孔尚任是诗人、剧作家,不是历史学家。尽管他对南明历史有相当深的研究,但并不想以一部戏剧代替南明史,因此对题材人物的剪接、挪移、点染、甚至虚构,都是题中之义,自不用赘叙。《桃花扇》最成功之处在于余音缭绕的诗意,让诗意去感动读者和观众,使其唏嘘感慨,掩卷沉思。于此孔尚任做了非常精辟的说明:“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家,无理不备。至于摹写须眉,点染景物,乃兼画苑矣。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于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桃花扇题辞》)戏剧是综合艺术,作者需要多种艺术准备和才华,因此虽“小道”而能达康庄。《桃花扇》就是如此,史家之笔法和《春秋》之义断只是就叙事而言,而“旨趣”则本之于《诗》。
诗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戏剧史上孔尚任是少有的耽于意味和注重形式的作家,在他接触《桃花扇》题材的数十年间,始终徘徊于意味与形式之间。少年时获得了一点感兴和意味,但这时只是个单薄的空壳。三年治河期间获得的所有资料填充了这个空壳,数十年人生阅历和对弥漫于清初知识阶层反思历史思潮的把握,使这一题材获得了历史与时代个性的品格和内涵。与此同时,表达意味的形式逐渐清晰起来: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儿女离合如何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桃花扇小引》讲出自己的思路:
传奇者,传其事之奇焉者也。事不奇则不传……桃花扇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业也。帝基不存,权奸安在?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
这段话的前面说,如果仅仅是“妓女之扇也,荡子之题也,游客之画也,皆事之鄙也”,即使“甘嫠面以誓志”,“亦事之细焉者也”。借血染花,私物表情,密箴寄信,又事之猥亵者也,这类桃花扇皆不足传。所传之桃花扇不仅是忠贞爱情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其扇的男女主人卷入了与权奸的斗争,卷入改朝换代的历史洪流,男女离合与国家兴亡纽结在一起。我们知道,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叙述方式不始于孔尚任,但孔尚任在两组故事情节的互动及逻辑关系的构成、两条线索时而交叉时而分离的有机绾结上达到最高水平。以往的兴亡剧,男女主人公大多是帝王后妃,即使是《浣纱记》中的范蠡、西施,最后也居于权力的核心地位,与兴亡发生了直接的关系。《桃花扇》则不同,男女主人公转换为名士妓女,由男女主人公的活动延伸到社会结构之中,反映社会各阶层在国家兴亡之际的关系及其作为。无疑,这种描写在反映兴亡的大关目上,深度广度是其他同类结构无可企及的。
不同的社会角色,承担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品格。明代南京的繁华绮丽几乎是明末清初几代人挥之不去的追忆和遐想,难计其数的诗文在述说着如梦如幻的陪京梦。孔尚任感知到了这种情怀,他在《桃花扇》里除了把南明覆亡的历史搬到舞台上,还要让观众咀嚼旧国昔年的笙歌靡丽以及诗骚气韵,从纷繁杂乱的南明文化现象中紬绎出三道风景线:清流名士、秦淮名妓、清客艺人,他们互相交融、点缀、张扬,构成了意气风发、情趣盎然的文化诗意。这种文化特征是明朝独特的陪京体制、晚明城市经济繁荣、党争激烈、思想解放以及金陵历史文化积淀综合作用的产物,因此它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应该说孔尚任的把握是准确深刻的。如何表现南明文化的交响曲?作者采用了诗歌意象化的手法,让男女主人公承担起文化构成的主要两翼。
明末的文人接受了个性解放思潮的沐浴,生活上自由放纵,出入歌楼妓馆,寻求冶游艳遇。同时,边患频仍,民生凋敝,实学思潮正在兴起,士人的学问也开始注重经世致用。党争异常激烈,形成了裁量执政,品核人物,讲求气节的清流和左右社会舆论的清议。名士这个社会群体以其具备家世、道德、才望、倜傥风流诸种要素的面貌出现。其中的道德主要是指在政治斗争中的立场和节操,因此,名士一般是东林、复社中人物。侯方域身上集中了当时名士清流的种种品性。他为东林后裔,复社盟主,“南京四公子”之一。风流放纵也是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家国已破,避乱金陵,仍然是“春情难按”(《访翠》)。作为名士清流,更重要的是文采和经世之略。侯方域自称“早岁清词,吐出班香宋艳;中年浩气,流成苏海韩潮”(《听稗》)。贾静子《侯公子传》说他“豪迈多大略,少本有济世志,尝与吴应箕、夏允彝登金山,指评当世人物,临江悲歌,二人以方域比周瑜、王猛”。《桃花扇》中《修札》、《阻奸》、《争位》、《和战》、《移防》等出戏描写侯方域在南明覆亡之际为稳定局势,挽救明祚所作的努力,表现了不凡的才华和胆识。但最终他没能完成周瑜、王猛一流的事业,没能效铅刀之一割,起码是历史没有提供这种可能性。
如果说侯方域是明末思想解放、党派斗争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清流名士的代表,而李香君则是明后期空前高涨的妓女文化的产物。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加上哲学上对情欲的默认赞美,被程朱理学禁锢了的情欲一经开放,就以变本加厉之态走向了纵欲,妓业随之繁荣。万历时娼妓遍天下,北京、扬州、苏州、盛泽等城镇妓馆林立,金陵当为之最。“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指为土”[1]462。妓女文化的高涨,掀开了妓女生活史上令人瞩目的一页,秦淮以至于江南名妓形成了具有共性的人格表现,富文采,任侠使气。李香君正是在这一块土壤中崭露头角的新苗。她出众的姿色、文采、见识、胆略,既有文士风,也有侠者概。如此的文化品位,在生意场上,逐渐形成了名士和妓女互相点缀、互相张扬的关系。名士如能得到名妓的青睐,愈益倜傥风流,为人艳羡;反过来,一个妓女能否成名,除了自己具备的色艺外,有无名士的题品也至关重要。士人们乐此不疲,选美活动频频举行,一时间《秦淮士女表》、《莲台仙会品》、《金陵妓品》等册子络绎而出。李香君未出道之前,已有“张天如、夏彝仲这班大名公”的题赠。蓝瑛、杨龙友都有题画(《传歌》),这是李香君跻身名妓行列的第一步。第二步是“梳栊”。“梳栊”并非只看钱钞不看人。《桃花扇·眠香》李贞丽曰:“只因孩儿香君,年及破瓜,梳栊无人,日夜放心不下。”显然这是一件关乎妓女身价、名誉的严肃事情,道德、才望兼具的名士当然就成了首选。李香君在《骂筵》出云:“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顾彩《桃花扇·序》也说:“胜国晚年,虽妇人女子亦知向往东林。”东林代表的是道德气节。侯方域“家道才名皆称第一”(《眼香》),色艺双绝的名妓得配才德兼备的名士各得其所。侯、李这样的风流佳话,明季的江南何止二三,才学、道德、红颜打成了一片。妓女和名士长期自由的接触,濡染了明末士大夫谈兵说剑,裁量政治,议论九边形势的风气,这些聪慧侠概的女儿们有一种当时看来异化的心态,政治嗅觉敏感,生发出预身国事政治的热情。这样把儿女之情与政治得失、国家兴亡捆绑在一起势在必然。
侯方域、李香君两个形象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信息,不仅可以作为国家兴亡的结构者,更是南明文化的承载者。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奢靡、绮丽、文采、节义,加上柳敬亭身上所透露的雅俗文化的交汇,怎能不让清初的观众唏嘘叹息!
《桃花扇》的诗意还表现在浓郁的抒情性上。我们知道,戏剧史上《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都是抒情性很强的作品,甚至人们称它们为诗剧。《桃花扇》在曲词方面明显不具备优势,吴梅曾批评全剧无耐唱之曲(《桃花扇·跋》)。《桃花扇》的抒情性并不依赖明清文人传奇擅长曲文的传统,而是另辟蹊径,用结构来表现抒情性。《桃花扇》在40出正戏外,又附加试1出《先声》、闰20出《闲话》、加21出《孤吟》、续40出《余韵》。其中《先声》、《孤吟》是老礼赞的独角戏。剧中,这个人物是南明兴亡的见证人。崇祯十六年三月,南京丁祭,复社名流群殴阮大铖,率先动手的是老礼赞。《拜坛》出,老礼赞目睹南明王朝君臣在崇祯忌日祭奠时种种表演;《沉江》出,南京失陷,老礼赞出城遇史可法沉江,收拾其衣冠;《余韵》出与柳敬亭、苏昆生共话沧桑。作为一个剧中人,老礼赞并不是重要角色,但作为一个剧外人,则是“场上歌舞,局外指点”之犹存父老的代表。他见证了南明王朝由初建到灭亡的全过程,他又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全过程。这个人物的设置,产生了许多戏剧功能。其一,如上文所云,由老礼赞评价《桃花扇》,增加了权威性。其二,老礼赞时而在剧中表演,时而又是现实中“指点”之人,历史与现实,时间与空间交叉在一起,造成一种如梦如幻、一唱三叹的情境。其情形正如《桃花扇·本末》中所说:“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炮酒阑,唏嘘而散。”这样的抒情方式虽然不是以曲词的婉转华美令人荡气回肠,却把难以言说的情绪转换成情境,其抒情功能在结构方式中得到了强化。
《桃花扇》最具抒情功能和诗意情境的莫过于结尾的《余韵》出。按照剧情的发展,40出《入道》已经完成,而且作者一改传奇大团圆的套路,按照剧情人物的内在逻辑虚构了国亡情空的悲剧结局。但是从作者到作品,再到观众(读者)都意犹未尽,正是“水外有水,山外有山,《桃花扇》曲完矣,《桃花扇》意不尽也”(《余韵》尾批)。于是又有续四十出《余韵》。《桃花扇》除去试、加、闰、续4出,其他40出戏都是叙事性较强,抒情性略弱,而《余韵》出却以抒情为主,篇幅也较其他任何一出都长。这一出的时间安排在顺治五年,南明灭亡三年后,改朝换代终于结束,隐于渔樵的苏昆生、柳敬亭和老礼赞“把些兴亡旧事,付之风月闲谈”。主体是老礼赞的神弦曲《问苍天》、苏昆生的弹词《秣陵秋》和柳敬亭的北曲《哀江南》,描写前朝遗民穷困不堪的处境及“地难填,天难补”的无奈,总结南明的得失兴亡,抒发离黍之悲、沧桑之叹。全剧蕴蓄已久的亡国沉痛犹如江河决堤,终于喷涌而出。本来就弥漫着浓重感伤情绪和痛定思痛心理的清初人得到了一个最好的情感宣泄方式,场上歌舞,局外指点,艺术的共鸣调动起观众的心灵震荡。剧终后,怎能不“掩袂而独坐”,“唏嘘而散”呢?
3
一个没有思想、不能把握时代思潮中的精华、不具备体认历史洞察现实能力的作家是不可能写下好作品的。历史剧也是如此,讲述历史,使历史艺术化自是必不可少,也是艺术家中很多人都能做到的;但是超越历史,从历史题材中升华出一种理论则与作家本人的思想水平有直接的关系,也是历史题材中最具有个性最具魅力之所在。孔尚任关注南明历史,做到了对这一段历史了然于心;三年治河期间,耳闻目睹了江南遭到战争摧毁、山河残破之状,他还接触了很多前朝学者、诗人。这诸多的因素,加上他本人一触即兴的感悟力和执着沉潜的思索,敏锐地捕捉到了清初最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国家。国家的概念早已有之,但我们今天的国家观念直到近代才形成,而明末清初正是近代国家观念重要的生成期。《桃花扇》以当时最先进的国家理论为出发点,针对明代暴露出来的体制、观念、伦常等问题进行反思和质疑,表现出作者可贵的理论勇气。
一、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帝王与国家的关系。晚明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个体、个性、私利得到了人们普遍的承认,“我”得到了极大的张扬。但是个体的东西是承平时期人们的宠物,在国家民族面临危机的关头,应该怎样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桃花扇》从多方面写到个人甚至帝王与国家民族的关系。弘光代表着明王朝在东南半壁的延续,代表着国家民族。皇帝与王朝、国家的关系应该说是清楚的:国家兴则王朝兴,王朝兴则皇帝才可以享用其“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的特权。弘光一出场,就表现出国家与王室的相互依存。《设朝》一出,弘光自表:“中原板荡,叹王孙乞食江头,栖止榛莽。”那时弘光还有“王业重创,不共天仇,从此后尝胆眠薪休忘”及“收复中原”的堂皇之言。但正位后的第二年(纪年只是弘光元年),便把这种历史责任抛之九霄云外,一心关注的只有声色和性命。以荒淫为风流,热衷于“采选淑女,册立正宫”,还为“帝王之尊,无多声色之奉”而闷闷不乐。王朝一旦冰消,弘光自以为聪明,“千计万计,走为上计”,“但能走出南京,便有藏身之所了”(《逃难》)。实际上弘光的依托是朝廷、国家,有这两个依托,皇帝本人才可以拥有至尊之位,享受声色之乐,性命可保,家室安全;失去这两个依托,便连常人也不如。弘光投奔旧臣魏国公徐宏基,徐宏基佯装不识;来到黄得功营中,弘光此时也别无奢望,“寡人只要苟全性命,那皇帝一席也不愿再做了”(《劫宝》)。殊不知不做皇帝,谈何性命?由于弘光只知享用为君之威福,不愿承担为君之职责,丢了国之根本,最终失去了为君之依托,嫔妃全散,性命不保。
马、阮排挤正人,肆兴大狱,不思防卫,更遑论恢复,苦心经营的是权势和富贵。《设朝》出,马士英结党营私,相约“内外消息,须要两相照应,千秋富贵,可以常保矣”;《迎立》、《媚座》、《骂筵》、《逮社》、《逃难》几出戏中,马、阮相互依倚,作乱朝政,他们确实是两相照应,但是否就能尊荣富贵可以常保呢?且看《逃难》一出,平时官居首辅,权握中枢,威震朝野,炙手可热,一旦“报长江锁开,石头将坏,高官贱卖无人买”。此时权势在哪里?尊荣在哪里?破巢之下安有完卵。马士英还惦记他“一队娇娆,十车细软”,要“随身紧带,殉棺货财,贴皮恩爱”;阮大铖“受人笑骂,积得些金帛,娶了些娇艾”,刹那间乱民涌来,哄抢而去。马、阮经营的富贵还在哪里?马、阮颠倒了朝廷、国家与个人权势富贵的关系,说:“幸遇国家大变,正我辈得意之秋。”(《迎立》)“天子无为,从他闭目拱手;相公养体,尽咱吐气扬眉。”(《媚座》)把国家朝廷的大不幸当作自己的大幸。本末倒置,最终本末皆亡。
昏君国贼如此,以侯方域为代表的清流名士如何呢?侯方域一出场就高歌:“莺颠燕狂,关甚兴亡。”(《听稗》)与陈贞慧、吴应箕谈及国事,又曰:“中原无人,大事已不可问,我辈且看春光。”亡国在即,侯方域与复社朋友们在一起不外饮酒看花,观灯赋文,欣赏戏文,寻访佳丽,有道义色彩的活动是写了《留都防乱揭帖》,哄打了混入文庙丁祭的阮大铖,最后为保护门户中人请左兵东下,引起移兵堵江,江北一空,南明覆亡。正是社稷可更,门户不可破。侯方域们“莺颠燕狂”也罢,闹门户也罢,凭借的无非是国家。国家一失,那些可以证明清浊的门户还依托什么呢?国破之后,陈贞慧、吴应箕才恍然大悟:“日日争门户,今年傍哪家!”(《沉江》)孔尚任把这种思考渗透到那些细枝末节上。徐宏基为了全身远害,不纳逃难的弘光,结果如何?《余韵》出徐宏基的儿子徐青君交代了国公府的结局:“生来富贵,享尽繁华。不料国破家亡,剩了区区一口,没奈何在上元县当了一名皂隶。”
二、情欲与国家的关系。情欲始终是儒家学派讨论的问题之一,从孔孟对情欲的适当承认,到宋明理学的禁锢,情欲越来越被扭曲。晚明人思想解放,情欲被认可直至走向纵欲。全社会掀起了趋“情”若骛的狂潮,弘光、马阮、以道德名节相标榜的清流在政治上大不相同,而征歌逐色却如出一辙。清初反思明亡的原因,有亡于王、李之说。这种观点不能说全部正确,但也不能说没有根据。追求情欲成了庙堂学校的第一要事,那些才情色艺并茂的女子就有了倾国倾城之价。明季人已经意识到情欲被极度推崇后产生的负面影响,开始思考寻求欲与理之间恰当的度,寻求正欲求理的途径。易代之后,这种反思更加明确、深入,视角也发生了变化——以国家的观念反拨晚明的情欲观。孔尚任领略到了这一时代精神,《桃花扇·入道》出举重若轻地表现了这一思想。南都覆灭后,侯方域、李香君乱离乍遇,叙述颠沛之况,庆幸乱后重逢,被张薇道士当头棒喝,从根本上否定了侯方域的“人之大伦”,对何为大伦,何为次伦进行了调整,国家、君父才是人之大伦,大伦不存,“情根欲种”何在?国家和男女的关系,犹如皮和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里张道士的一番话无疑是代孔尚任言。可贵的是作者把国家放在封建伦常之上。
三、忠君与忠于国家的关系。孔尚任以国家、君父之伦拨正晚明的情欲观,但他不是那种“规规然以为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陋儒”[2]3,《桃花扇》对五伦之首“忠君”进行了深入思考。左良玉不能说不忠,打着清君侧、救太子的旗号率兵东下,致使江北移防,清军直入;黄得功也可谓忠臣,“闻报时如此忠,见帝时如此敬,夺驾时如此勇,毙命时如此烈”(《劫宝》),但在《截矶》一出中又把左良玉认作“心腹之患”,放下长江一线不防,却去燕子矶截杀左兵;史可法是剧中第一个忠臣,以“恢复北朝”号召四镇,迂阔不切实际。《劫宝》出总批曰:“南朝三忠,史阁部心在明朝,左南宁心在崇祯,黄靖南心在弘光,心不相同,故力不相协。”这三个忠臣,忠则忠矣,但于国事都是成事不足,甚而败事有余。这三个人的悲壮而令人遗憾的命运,直接导因是君主制与国家的矛盾造成的。君主代表了王朝,王朝代表了国家,君主把朝政当作家政,把国家当作私产,以自己的大私要求普天下臣民绝对忠诚,无私无欲,这种不合理的伦理观念势必走向反面,人有人私,集团有集团之私,大臣有大臣之私,造成“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无一非私”,“文争于内,武斗于外,置国事于不问”的局面(《拜坛》眉批)。
君主制还造成了明末的门户之争,君主的门户之分造成了大臣党争。明末的东林党也叫“后党”,这个党派的产生、发展以至于受到阉党的残酷镇压始终伴随着王室内部的权力之争。南明时,忠臣们各有所忠,没有一个忠臣考虑过和衷共济,励精图治,国家在忠臣的光环下被葬送。君主代表国家的制度和臣忠于君的伦理观念在南明受到了历史大大的嘲弄。无疑,孔尚任通过展现忠君之臣不可靠,旨在昭示一种新的伦理观念——忠于国家。这种观念肯定在当时不能被统治者甚至臣众们认同,但它代表的是一种全新的方向,表现的是作者先进的思想境界和理论高度。
收稿日期:2007-0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