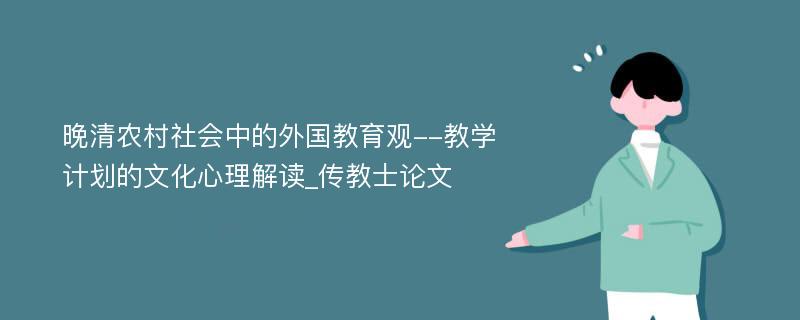
晚清乡村社会的洋教观——对教案的一种文化心理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教案论文,乡村论文,心理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侧面,是西方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挟船坚炮利之威,大规模向中国乡村突进的历史。乡村民众同西方教会之间的冲突,逐渐演化为近代民族矛盾在底层社会舞台上的主戏之一。晚清教案的背景和原因比较复杂,但就意识角度而言,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民教冲突的规模和烈度,不仅取决于西方教会如何做,也取决于中国民众对他们如何看。由此,就引出了乡村社会的洋教观。
一、洋教观界说
所谓乡村社会的洋教观,是指晚清乡村民众对基督教及其在华教会的信仰、伦理、组织与活动所持的基本观点和态度。乡村民众的洋教观与哲学或政治学关注思想家的思想建树不同,它不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性、系统性,而带有相当强烈的情绪性,有时甚至是以随意的、多变的讹言流播为基础的。尽管中国各地区的乡俗颇有差异,但是,乡村民众在对基督教的基本评价和态度上,却有大体一致甚至是固定化的倾向。概言之,我们所说的洋教观是统计性归纳的(即大致趋向的)民众观念的集合。
首先,这种洋教观属于社会心理范畴,是在乡村社会中自发形成并互相影响的对于基督教存在和活动的主体反应,属于一种大面积的共识。尽管其中掺杂有大量失实和神秘的因素,但在晚清特定的社会氛围中,乡村民众对这类认识和判断几乎都确信不疑,并积极参与传播。其次,由于这种洋教观反映了乡村社会各阶层共同的情绪和情感,因而具有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庞杂交错的特征。在形成初期,它受到了乡绅的诱导,并被他们通过各种媒介所强化。这些人在19世纪下半叶,“刊为书说,编作歌谣,绘为图画”,广泛传播了反教会的舆论。乡村百姓对基督教的看法,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乡绅的认识。乡绅是皇权统治在底层社会得以实现的中介,被老百姓看作“代圣贤立言”的偶像,他们对洋教的认识和态度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不过,在社会动荡加剧的情况下,乡村小知识分子和社会底层能人(诸如僧道、巫师、术士、拳首、教门或会党首领等所谓布衣领袖)的作用有逐渐增大的趋势,人们对洋教的评判也相应地从泛道德主义滑向更浓厚的神秘主义。本文所考察的是,乡绅与乡间小知识分子及能人所持有的并为一般乡民所广泛接受的关于基督教的观念。
其三,这种洋教观的形成与发展同时局变化有共相关系。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越深,这种洋教观就越流行,其在民众心理中的固定化,恰是由侵略而导致的普通老百姓对西方势力产生普遍恶感之结果。事实上,当西方教会势力侵入近代中国之初,在最早接触这种陌生文明的南海之滨,是不存在如上洋教观的;而在帝国主义势力被逐出中国之后,当宗教信仰已经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而不再同政治的、经济的特权发生联系的今天,当年那种“人言籍籍,众口雷同”的洋教观,也就像过眼烟云一样地逐渐被人们淡忘了。
其四,这种洋教观以乡村民众对教会的恶感为中心,常常又把恶感推及西方人、西方文明以及与教会有联系的中国人。
洋教观边际的模糊性,往往又反过来强化了乡村民众对教会本身的恶感。比如,有一部分教民(尤其是一些天主教教民)来自于土棍、匪类或懒汉无赖,他们本来在乡村社会的名声就不佳,而这种社会的刻板印象又往往由于这些人的入教而被带进了教会。
本文所谓的洋教观,不包括中国教民和那些接近教会的人们的认识。虽然有大量的文献和口碑资料证明,相当一部分乡村教民(即被士绅们鄙为入教的“佣工平民,村子灶妾”),由于受经济地位、文化素质和传统信仰思维的制约,在归主的动机和需要上往往带有浓厚的实用色彩。他们的洋教观同样值得研究,但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况且教民的人数在晚清年间特别是庚子以后虽然呈上升趋势,但其绝对数量同非教民相比还是少得不成比例。因此可以说,这种边际模糊的洋教观至少是终清之世的民众心理定势,并没有因教会势力的相对扩张而有根本性的改变。
二、乡村民众视野中的基督教
1.关于洋教来华的目的。基督教各教派在近代中国的活动是西方列强对华侵略扩张的一部分。乡民普遍认为,洋教来华是出于政治目的。他们觊觎中国疆土,欺罔中华黎民,甚至“谋朝篡位”。这种认识除反映了民众对于基督化追随殖民化的直观感受之外,也包含着他们对政治现象的某些习惯性见解:入侵必定是为了改朝换代,取而代之,1888年1月,流传于山东兖州府的一份“绅帖”说:基督教诱人“入教后,有事即以教民为兵,逼令捐输金银,充其兵饷,并驱令打头阵,使我中国人自相残杀。即以此术占据印度、暹罗、缅甸、金边等国”,“据其疆土,人所共见闻”①。1886年7月,出现于四川的一份揭帖则按照造反称王的图式来塑造基督教,说洋人在重庆鹅项颈修建教堂,意在“永爱金殿,哄惑生人。每逢朔望,登殿称君”②。1869年7月的遵义揭帖也抨击教会“名为经堂,实是梁山”③。在这里,教会被描绘成割据叛乱的形象。“凡洋人必贪”是当时多数中国人对于入侵者的认识定势。人们认为,传教士同巫师相似,可以用“搬运之术盗人藏金”,可以借千里镜发现和掠取中国的宝藏。流传于直隶一带的民间故事“鱼童”,到了近代情节演变为传教士勾结官府巧取豪夺老渔翁的白玉鱼盆④。图财似乎就可能害命,人们把教会图财又同“取睛”“挖肝”联系在一起。民间曾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是“洋教取人之睛”,“以中国铅百斤,可煎银八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为了增强这种传言的可信性,这份材料又解释说:“惟其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⑤。如果说洋教的图谋不轨在乡村民众的意念中还算是一种推断的话,那么传教士的贪婪在他们头脑中则是确信不疑的。直到当代,广西农民还有人认为,法国传教士“挖走我们不少宝贝”⑥。
2.关于教会的行为。晚清乡村社会对教会行为的评价,可以用淫、恶、邪来概括。不仅是教会出格的举止,而且其日常仪式和习规也蒙上了这三字恶谥。把入教洗礼(浸礼)说成是“男女同浴”,教士为入教者沐浴是借机奸淫。将作礼拜看成“使各贫苦妇女每月入堂四次,迨入堂后给以钱文,令吞凡药,逼使顺从,逞其色欲”⑦。认定作弥撒是“群交”、“乱伦”。视行终傅礼(临终祈祷)为“奸尸”或“挖睛”。有的还被编为“三字经”:“人死时,夷入房,代殡葬,刳割取,心肾肝”⑧。对于最难理解也最易误解的“密室忏悔”(特别对女教民而言),被人们毫不犹豫地判定为“密室宣淫”。几乎所有关于教会的传言都渲染修女(童贞女)与传教士有两性关系,进而传说教民也需将女儿留当“童贞女”,而教民娶妇第一夜要留给传教士(把中世纪欧洲封建领主的初夜权附会到了教会头上)。对收养弃婴的育婴堂,乡间以为是残害儿童:以小儿心肝眼睛配药,摄取童精或处女元红等等。对于传教士医生,则说他们借行医奸淫或盗取病人的“人体之宝”。
3.关于基督教的本源。乡绅的看法以署名为“饶州第一伤心人”的《辟邪实录》最有代表性:“天主教始自耶稣,乃西洋诸国通行之教。习之者,妄谓耶稣生有天授,能通各国土音,创教劝人为善,后被恶人钉其体于十字架,剖割以毙。其徒号其教曰天主,以耶稣为先天教主,造书曰天经,遍相引诱,自郡国至乡闾皆建天主堂,供十字架……其教之总名有二:一曰洗礼,一曰圣餐。教之分名又二十有五,难悉举。”⑨这件材料对基督教的本源的了解虽然若明若暗,并且掺杂进了中国民间教门关于“转换天盘”的世界观,但总算是勾勒出了一个模糊的轮廓。而一般民众的说法则更加芜杂。他们将基督教列为“斜(邪)教庞(旁)门”一类⑩。邪恶和良善不能相容。所以有一份农村的打教告白宣称:“吾思此教乃系外国丧良之人,捏出天主教人灵魂亦可升天。谁知他意,入我中源,欲害良人。”(11)凡此种种表明农民对基督教信仰对象、来源和归宿的模糊认识,这种认识的基调就是不屑和轻蔑。
4.教士教民的人格画像。民间对传教士的看法似乎十分简单,一句话:“非人也”。1873年3月,山东德平李家楼一份告白说:“鬼子其形,于(与)中(国)大有不同,羊眼猴面,淫心兽行,非人也。行事不敬神,不敬先人,不学孔孟,不知礼仪(义),丙(并)无人伦。”(12)这种看法很有代表性,它反映了乡民对传教士从表象到精神的勾勒。洋教士之所以化为“非人”,一半是由于他们的形(金发碧眼,异腔怪调),一半是由于他们的行(不敬神佛,不学孔孟)。由于传教士禁止教民恪守中国传统的礼教风俗,因而在民众眼里教民成了丧失人格的“禽兽”。在民众看来,传教士“流传丑教,败坏纲常。害我中国男女,变猪变鬼,其臭异常”(13),所以,教民往往被称为“二鬼子”。
5.关于洋教传播的后果。由于对传教士来华目的、行为和宗旨的猜忌,以及对于神职人员与教民的恶感,民众自然认为基督教是一种扰乱乡村正常生活、干扰传统习俗、破坏伦理关系、蔑视道德原则的异己势力。用农民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携(邪)教庞(旁)门,不为正道”(14)。之所以“邪”,关键就在于基督主义向中国伦理主义的挑战:“不敬神佛,背祖忘宗”。笔者在当年意大利天主教势力颇大的河北威县,听到过这样一件逸事:一个小家族里信教的叔叔同不信教的侄子拌嘴,叔叔说:“你们的菩萨是泥捏的。”侄子反唇相讥:“你们的菩萨是纸画的(按:指圣母像)”。气得老奶奶痛骂了两人一顿:“叔不像叔,侄不像侄。”透过这件最简单的、靠大家长权威平息的“家族教案”,可以看出当教会势力渗入家族之后,引起了血缘关系内部“你们”和“我们”的分野,导致了家族伦理秩序的失衡。当民众看到矗立在土屋茅舍、寺庙族祠其间的教堂时,总会感受到传统宗教氛围和社会秩序所面临的威胁。而如果失去这类社会意识和行为规范的依托,民众就会找不到自己在既定社会格局中的位置,产生无可凭依的失落感。
三、猜忌和恶感的背后
上述乡村社会的洋教观,在局外人看来,不过是一种谩骂,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它表述了什么,而是说明了什么。
首先,它表现了遭受侵掠和奴役的人们对侵略者的抗争和呐喊。包括许多国外研究者在内的史学家都认为,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对近代中国,既有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侵略,也有对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目标的挑战与摧残,这些改变了中国历史上各种宗教和教派的传播模式与交流常态,基督教的信仰和习规从教堂辐射到乡村社会的各个生活层面,并通过人生的出生洗礼、坚振、礼拜弥撒、婚礼和终傅,把社会日常活动和习俗牢牢地笼罩在宗教的统治之下。正如孔汉思所言:“传教士和所有的白种人一样相信自己的种族优越,一旦面对它国本地传统问题,他们十有八九表现得不体谅、不变通并且倨傲不逊。”(15)因此,民众对洋教的态度是民众的实际利益和文化传统受到严重威胁和伤害后的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讲,恰恰是因为他们首先是受到损害和凌辱的弱者,只能采取“精神胜利法”,即戏谑、嘲弄和诅咒强大的对手。
第二,种族中心主义因素。白种人种族优越感的冲击,势必激化华夏种族中心主义的苏醒,洋教观在本质上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特色。一份“儒帖”引经据典,用“华夷之辨”的理论,说洋人“其种半人而半畜,山书所谓倮虫,汉译所谓鳀人者也”(16)。无疑,这种华夏中心主义是乡村社会对洋教取轻蔑态度的认识基点。在列强的侵略行径引起普遍敌忾之后,他们的种族特征更进一步化为令人厌恶的表征。民众对传教士的种种称谓,多少蕴含了这样的命题:洋人之所以坏得不可救药,盖出于他们是“非我族类”的“化外蛮夷”。人们越是在现实生活中遭到欺凌,就越是要从历史传承中寻求自我保护的心理防线。因此,各种反教舆论往往用大量的篇幅对此作出论证。在反教浪潮最高涨的时候,“鬼子眼珠俱发蓝”(义和团揭帖)也成为消灭侵略者的证据。因此可以说,在民族危机深化的大背景下,民众对基督教的厌恶是同种族厌恶杂糅在一起的,而其中的种族厌恶因素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宗教排拒。
第三,文化中心主义因素。华夏中心主义的心理基础是长期积累和传承的文化优越感。洋教观中表现的文化倾向性几乎都带有排斥异端文化的色彩,要“黜异端以崇正学”(17)。在这里,乡绅们要捍卫的重心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和知识系统。而一般老百姓固然也追随乡绅捍卫“正道”(比如同治年间,直隶乐亭一位画匠刘滔在天主教传教书上大批“邪说崇(祟)正”字样)(18),但他们更注重的倒不是维护书院儒学的地位,而是保卫乡土风俗和日常伦理的稳定性。“俗者,习也”。对于每一个民族来说,总是认为在本乡本土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是最好的。中国乡里民众把教会的“男女并收”、“锢蔽儿童”、教民“佛前不烧香,坟前不化纸”的风俗反叛看得很重。民族文化无不受到伦理原则的制约。士绅阶层倡导的儒学和乡村社会执著的风俗习惯是以中华文化中的伦理精神(以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为依托的“家族精神”)为纽带而联系在一起的。惟其如此,教会的所谓“丙(并)无人伦”才成了从士绅到民众所不齿且又切齿的事情。民众对于教会的抨击几乎都是道德性的。从严格意义上讲,与其说教案是宗教冲突,不如说是利益冲突和文化伦理冲突。洋教观对教会的谴责集中反映了它包含的传统伦理精神。其一,它将教会为反对偶像崇拜而禁止祭祖渲染为不要祖先,不讲孝道,进而“毁弃人伦”。其二,从教会活动中的男女同堂而认为教士、教民犯淫乱伦。在士绅阶层的宣传下,越是下层民众就越是看得认真。其三,正因为判定教会“不讲人伦”,背弃中国道德原则,所以教会自诩的“劝人为善”就是虚伪的,他们的慈善事业也被认为是居心叵测,从而在民众心里加重了道德批判的分量。伦理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每个人都是一定伦理关系上的集结点。人们对各种世象的评价都要直接或间接地归宿到伦理标准上来。洋教观的文化内涵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尺度来衡量西方教会。列强的侵略已经给教会蒙上了否定的色彩,道德评判进而将人们对洋教的否定从政治和社会层面延伸到文化冲突的领域,将反侵略和反“邪恶”联系在一起。在当时的抗争中,道德上反“邪恶”的基调是乡村社会最能引发人们投入全部身心的精神武器。
第四,文化本土运动的一种意识表征。根据文化人类学者林顿(R.Linton)的定义,所谓本土运动(nativistic movement)是指两种不同质的文化接触时,某一文化载体(因感于外来文化的压力)企图保存或恢复文化传统的有意识及有组织的行动。金耀基先生的观点更为简洁:本土运动即是一个主体文化因客位文化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这种重整反应牵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人们在屈辱和抗争的过程中,对文化重整做过各个角度的和不同方式的探索。而乡村社会的洋教观反映了底层社会的人们企图恢复古老的文化传统,再塑因洋人洋教介入而紊乱了的文化情境的努力。洋教观的形成过程就是文化的复归和重整的意识表达过程。当乡村民众的精神文化岌岌可危时,所谓的“本土运动”就会成为他们自发的和竭尽全力的行动。这种底层的文化重整,一般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以正统文化价值为目标,即以上层文化的价值恢复为运动目的。农民跟着“学者”(乡绅)走。二是在传统上层文化的价值逐渐破碎,底层社会奋起以重整边缘的文化价值(教门模式和民俗信仰)为己任,即义和团运动。虽然人们可以说这种文化本土运动是向后看和非理性的,它激扬的民族精神之中掺杂着浓厚的神秘主义,但是就文化参与的角度而言,中国近代又没有哪一场运动像拳民闹教那样深入人心。因此,它又为后来理性的文化重建提供了必要的经验。
四、洋教观的成因
乡村民众为什么对基督教有这样一种特殊而强烈的心理回应呢?在我们看来,这种洋教观形成与传播的首要原因,是民众敌忾心理引起的情绪化的认识扭曲。
在近代,列强的侵略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物质损失和精神创伤。虽然侵略行径的主导者是政客与军人,但是确有一部分传教活动与列强的对华侵略相伴而行,一些传教士为侵略军搜集情报,充当翻译,有的甚至从戎作战。传教事业不仅要凭借炮舰索来的特权,而且往往还要依赖炮舰的直接支援,凡有教案发生,必有强权随之。同治八年(1869年)十二月初,法国公使罗淑亚因风闻江西有位传教士被活埋,遂带炮舰3艘抵九江示威,然而事实是这件传闻纯系子虚乌有(19)。山东的德国圣言会一遇教案,动辄请兵据城,杀人害命,造成了十数起血案(20)。在乡村民众眼里,洋教士和洋兵的界线模糊了。在这种敌忾情绪弥漫的情况下,民众的认识出现偏差是很自然的。
诚然,一种属于异质文化的宗教在本土传播过程中不可能不遇到抗阻,但是像基督教在晚清史上引起如此强烈和普遍的抵制,却是超常的。中国底层社会有着包容性的信仰心理,人们追求神,但一般不太在乎教义的歧异、教仪的奇特,甚至恰恰是因为其歧异奇特而对其产生较之信仰正统宗教更强烈的求异心理。比之士大夫,他们对光怪陆离的神教信仰更加宽容。在中国历史上,景教、拜火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在民间找到了自己的信徒。我们在明清两代的民间教门里也常常可以发现它们溶入的踪影。太平天国的历史也表明,乡村民众对基督教的嫌恶与敌忾不是天然的。在这个农民政权统治的中心地区,浸润过一种被改造过了的基督教情韵。一些前来访问的外国传教士也曾被起义农民真诚地当成了朋友和老师。贺麟先生早年曾说过这样的话:“日本一获得独立,反基督教的情绪马上就消失了,现在基督教在日本发展,一点麻烦也没有了。我相信,一旦中华民族的危机克服了,那么基督教所面临的危机,会像在日本一样,也会得到克服。”(21)显然,贺麟先生看出了“侵略的前因”在教案中的分量。被侵略、奴役的前提,是乡村民众认识扭曲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不同的文化习俗及观念差异对乡村民众洋教观的形成产生了影响。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教会(主要是天主教修会)兴办的慈幼机构中的行为规范不合中国国情,更不被人们所接受。育婴堂的修女们一般都有急于事功的心态和表现,收养弃婴把灵魂获救放在首位,先要让他们受洗。不少孩子进堂前已经奄奄一息,入堂后对他们又照顾不周,因此育婴堂里的死亡率一般都比较高。死后的婴儿,往往又集中在堂内掩埋,以致有“尸堂”、“尸窑”的说法。修女们有时为了扩大收婴面,还常常雇人四出收集,于是就出现了匪类为了获得雇佣费而拐骗幼童冒充弃儿的案件,从而引发了连锁反应。于是教会由收养弃婴,化为拐骗幼儿,进而演绎为采生析剖的“魔道”。无人收养的弃婴零星地夭折在荒郊野地、街头巷尾不会引起人们的惊异,但大批地死亡并掩埋在育婴堂而又恰被当地人目睹,一般都不可能把这件事往好处想。没有什么事能比目睹成堆的婴尸而更能引发人们仇教怒火的了。有时,仅仅因堂内掷出或讹传其掷出小儿衣帽也会激起民众的狂怒。四川南充“五月初五(1898年6月23日)午后,城内有以小儿衣鞋各件狂呼于市者,云称:‘此由堂内得来,洋人实食小儿’。时龙舟竞渡,闻者莫不深恨骨髓。于是大动公愤,毁室发屋,两教堂一时化为乌有。”(22)
教会对教案的索赔也无异于火上浇油。美国学者柯文说过:“不论天主教或新教徒,通常都同意政府采用武力索赔。天主教的传教士为了索还在反洋教暴乱中所遭受的损失,照例要求占有诸如文人会馆或庙宇这类建筑。而这些建筑是用公款建造的,对中国人具有重要象征意义。”(23)教会索赔往往怀有报复心理,索赔额大都高于损失额,还要加上诸如罚席赔礼等等令当地绅民难堪的附加条件。
我们对于殖民侵略和宗教征服促成洋教观形成与强化的分析,并非意味着就此否认当时乡村文化心理自身的各种弱点,也不否认由于中西文化隔膜而导致的人们对于西方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的认知失误。
格式塔心理学表明,人的知觉是整体性的,现时的感知同由过去经验堆砌而成的主观先验框架有直接的联系,人们习惯于用过去的框架来容纳整合他们第一次见到的“新事物”。乡村民众的主观经验往往受到小农自然经济的制约,以偏执、滞守和缺乏因时变通为特征,他们习惯于以固有的伦理和风俗为尺度来衡量一切。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是,他们常常以中国出家人的形象来评判传教士:出家人不应有家眷,但不少传教士却挈妇将雏(他们不理解这是新教教规允许的),从而传教士“犯淫”就有了明证。教堂里有妇人在内,这自然令人联想到佛堂宣淫的罪恶。1864年,福建闽侯拱星铺村村民看见教堂打更人夫妇留宿堂内,遂认定教堂暮夜私藏少妇而掀起打教风波(24)。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当时的乡村民众很难理解基督教的信仰、仪式和习规所蕴含的宗教哲理。一个追求社群和谐、执著血缘亲情,将信仰目标归属于现世安福的乡村社会的人,很不容易接受人人与共的上帝的价值,并置诸高于世俗血缘价值的位置上。他们对基督教倡导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否认耶稣的血缘关系的神话,以及由此派生的种种旨在使每个人在精神上超越世俗关系而向上帝敞开心扉的仪式和活动,感到匪夷所思。这种以亲情为核心、以家族的和谐与绵延为目标的中国伦理精神,同以自我为核心,以归宿与荣耀上帝为目标的基督主义之间的歧异,涉及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虽然人类的各种文化体系(包括宗教体系)中并不乏美好的共同点,如追求人类生活的和谐完满,相信公正、善良终究会战胜自私与邪恶,同情心和献身精神等等。但各种文化类型对于这些带有永恒性质的命题自有其不同的思考方式,而它们之间的交融互补更需要一定的历史机遇和长久的时间过程。
19世纪后半叶的教案呈多发趋势,遍及许多省区,大规模的民教冲突数以百计,小的不下千数。教案达到了如此的广度和烈度,显然并非全部起因于那些危言耸听的讹传。而只有经过讹言和教会自身行为的交互作用,并在人们内心形成了一定的认知、判断和思维定势,讹传才会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人们的行为。一些重大教案所以发生,往往是由于洋教迷淫妇女、拐骗幼童、取眼挖心的流言不同程度地起了某种导向和催化的作用。事实上,乡村民众可以有种种正当理由去反对教会征服,但是他们却偏偏选择了这样的理由和方式。尽管在形式上和内容上乡村民众的洋教观并不雅驯,有失客观,但它在当时却是乡村民族主义觉醒的一种表征,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一种初始的表现形式。当然,乡村社会的洋教观所包含的浓重的迷信、落后的内容,不言而喻地又为民族意识的近代化造成了障碍。不过这些问题,已经超过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
注释:
① 《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414页。
② 王明伦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28页。
③ 《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1612页。
④ 《义和团的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63-270页。
⑤ 《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9页。
⑥ 《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6页。
⑦ 《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1628页。
⑧ 《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1487页。
⑨ 《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7页。
⑩ 参见《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405-406页,宝坻揭帖之一部分。
(11) 《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1677页。
(12) 《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399页。
(13) 《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167页。
(14) 《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403页。
(15) 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20页。
(16) 《教务教案档》第1辑,第906页。
(17) 《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31页。
(18) 《教务教案档》第1辑,第1627页。
(19) 《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957页。
(20)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
(21) 《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58页。
(22) 民国重修《南充县志》卷六,第16页。
(23)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4-35页。
(24) 《教务教案档》第1辑,第12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