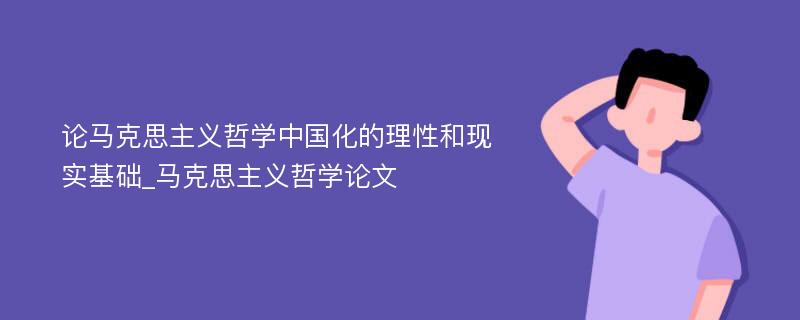
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性依据与现实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理性论文,现实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491(2003)05-0010-04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性依据来自于哲学传统间的可相融性
任何一个哲学系统都具有“可解析性和可重构性,观念要素之间具有可离散性和可相容性”[1]。因而,中国哲学所包含的观念要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初语境而存在的,它附着于产生它的历史的上下文,只有置放到那个特殊的历史情景中(如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与各种观念体系一道作整体性理解时,才是有价值的。这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含义;而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而融纳到别的哲学系统中,经过互掺、互动、整合与升华而产生新的哲学体系。这就是“中国哲学传统”的基本含义。正像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是有区别的一样,传统哲学与哲学传统也是有区别的,它们是“隐”与“显”的关系。哲学传统间的融合,由于应用的功能性原则,会产生部分接纳或接纳置后的情况。由于产生哲学传统的思想环境不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文化积淀、民族特质、自然条件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等差别很大,且起点和发展基础不同,因而对引入的外来哲学传统中那些与本土传统具有相似性或相关性的部分,很容易直接认同;而对引入的那些与本土传统不熟悉、不相关或者当下没有功能意义的部分,要么不被强调、不被重视,要么则会间接接纳或者接纳置后。这也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一种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它满足需要的程度。
一般地,哲学传统间的融合,越是在深层越具有内在一致性,其共度性越大,其对流、互补和融聚的可能性就越强。由于中国哲学传统所固有的韧性、气度、张力都很大,受其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精神指向所决定,它不可能只在表层接纳异质哲学传统,而是能够在深层即在世界观、价值观层面,找到哪怕是思想血统最不相干的哲学体系中足够多的共点而作为互相融合的基础。中国哲学传统是指在历史流变中的精神性活体,体现的是华夏民族精神特质的世界观系统,它与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融为一体,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社会历史发展和文化演进中,它作为“硬核”或“范式”被积淀下来,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其理性基础异常坚固,绝不会被一次大的事变而冲垮并发生断层,形成哲学传统缺席或空场的局面;但它又并非是打不开的超稳定结构,相反,它作为“流动中的变体”,具有很强的开放性、自我调节性和延展 性,既凝结了过去又包含着现在并开拓着未来,它的这种超越指向性表明,它决不会轻易地死在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境域中。
任何哲学传统都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都是二者的辩证统一。中国哲学传统的民族性是指它们民族特性或民族个性。具体是指:它是以汉族为主体,各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特殊的世界观、价值观体系,它以儒家哲学为主流,融聚佛、道哲学观念并融通了世界上各种先进文化因子和哲学理念为一炉,以凸现华夏民族的特有风貌和精神心态为己任。它的基本内容是: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主体性精神,崇尚和谐统一、民族团结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重义轻利、顾全大局的价值取向以及日生日成、刚健行为的实践品格等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各种哲学传统只具有民族性,而在此之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传统由民族性向世界性的转换,因而中国哲学传统只有经过马克思主义化才能走向世界,对世界哲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并作为世界哲学的一部分而存在,实现哲学传统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形成“世界性的哲学合题”。[2]
中国哲学传统中的进步要素、现代性理念能从深层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有特定的理性基础和思想根据。从整体角度看,中国哲学传统中的“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与科学形态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具有学理上的相融性、相通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方便、最快捷的思想桥梁[3]。从具体层面看,中国哲学传统中有某些可以校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代生活的具体关系的东西,如天人合一的合和精神;有某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创造性发展提供现实条件的东西,如人学思想;有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向深层开掘和存在的合法性根基的东西,如二者逻辑上同构;有经过和异民族哲学传统进行对话而达成重叠共识,并形成交往互惠的东西,如哲学基本问题的一致;有经过双方互补和对流找到互相印证和发明的东西,如大同理想等等。中国哲学传统的现代性转化,不是平面的、线性的对接,而是立体、互动的,而且它只有首先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转化”[4]才能真正成为现代性的、世界化的哲学,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相结合的过程,既是中国哲学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日俱进、开拓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因其正确的揭示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深刻的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代表了人类理性认识的正确方向,因而它已不再是“同其它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5]。作为世界性的学说,它只有通过民族化的形式,找到与中国哲学传统相对接的可运行的、可操作的具体实现方式并带有中国作风、中国特性、中国气派,其理论指导功能才能发挥出来。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经过中国化才能走向现代化、世界化,它的未来趋向不能绕过中国哲学传统而发展。
总之,哲学传统间在深层的可相融性、会通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性根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基础取决于它的实践性品格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在当代面临着严峻挑战,主要是:苏东巨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上处境恶劣,遭到的攻击最甚,西方理论家一再宣称要埋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改革深层次矛盾不断涌现以及执政党中的腐败问题,使之原有的影响力下降;全球化浪潮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多方面渗透,所造成的严重威胁;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提出许多颇富挑战性的新问题、新领域;由于近代化的知识论的误读、苏联教科书框架的误读、第二国际式的误读等等而拼凑出来的僵死的原理体系,严重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义;市场经济在功利方面的张扬,造成人文理性的低迷,封建文化毒素沉渣泛起;各种反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借助各种媒介尤其是互联网大量涌入,严重危机到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话语的生存等等。这些挑战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实现现代性的转向即在根本立场、思维方式、理论课题等一切方面发生现代性的划时代的变革,才能挺立时代潮头、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而这种“现代转向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取向”[6]。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走向和21世纪中国哲学的现代走向的交汇处,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与创新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及在何种程度实现中国化的问题,关系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中国能否顺利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关系到世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更关系到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问题。在当代中国,离开中国化而谋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同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而谋求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一样,都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经过中国化而走向现代化,它的一切创新和发展都集中体现在中国化上,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最大弊端就在于没有实现中国化,而哲学改革的唯一出路也在于使之全面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真正旨趣在于:实现多种哲学传统的实质性融合,使中、西、马都成为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再塑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和民族灵魂。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不再是并列或独立的两种不同的哲学,而是在当代实践基础上实现合二为一的同一种哲学的两个方面: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要义和实质融入到中国原有的哲学理念中,构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传统和理论体系;意味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将有一个实质性的飞跃,最终实现它的中国化、大众化,“使之成为中国人普通大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人生指南和生活智慧”[7]。由于人类生存方式的同一性,决定人类的思想诉求,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具有一致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现代、后现代哲学的关系就是这样。西方现代、后现代哲学对传统基础主义的批判、对主体性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对传统理性与非理性的摧毁等,这一切都是对现代性哲学的批判或重写,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批判框架具有内在一致性。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除了要克服原有的西方近代化的先在性强制之外,还要充分吸收现代、后现代哲学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瞥见到的许多有价值的先进哲学元素。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使现代哲学活在中国更活在世界上,在现代性哲学平台上经过多种哲学传统的互相提问,增加互惠知识,形成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和人类普遍精神指向的“问答逻辑”。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代价值取向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诉求,更在于它的实践性指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基础就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所固有的实践性品格。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只有立足于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文化或精神文明的发展以及执政党的建设等基本规律,用“三个代表”的精神,力意在理论上研究和解决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最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并在这一探索和解决的过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才能不断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8],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新的实践,在创造性的运用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此,必须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着眼于如何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为之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政治保证,以确保社会主义建设避免犯重大的原则性错误,确保在理论上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正确认识和解决,从而夯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中国化”的几种错误观点的评析
为了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性依据和现实基础,很有必要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中国化”的几种错误观点[9]进行驳斥。
1.中国无哲学传统论。历史上,黑格尔曾说中国无哲学,有的只是些思想和意见。无独有偶,现代学界也有人按西方的形上理性标准,认为中国根本无哲学可言,其哲学传统更无从谈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相结合的理性对接点,压根就不存在,更不要指望能化出什么结果来。还有人虽承认中国有自己的哲学传统,但却认为其理性基础异常薄弱或脆弱,它经受不住任何性质的一次大变革的折腾,且武断地说,事实上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声中,中国哲学传统的脊梁骨已被打断,出现了哲学传统的断裂。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到中国,已成为无根的浮萍,不可能实现中国化。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与历史事实相悖不说,在理论上也难成立。
2.哲学传统整体理解观。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哲学传统不分类、不分家是它的最明显的特点,它的哲学观点都包容在其它各种思想中,且只有在一个思想体系中作整体性理解时,才能开显出它的原有价值。根据这个特点并错误的推断说,中国哲学不可能脱离产生它的原初语境与具体实践,而抽象出一个所谓的哲学传统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融合。中国只有具体的哲学观点,无哲学传统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只能是一句空话。还根据福柯知识与权力关系的理论,错误的认为谁在经济、政治、军事上拥有霸权,谁自然就能在文化上拥有绝对解释权,充当文化霸主地位。在哲学发展上亦如是,西方哲学作为强势话语已将一切非西方的哲学拆解了,中国哲学传统只能处于被支配的从属地位,只是作为西方哲学被考察的一个对象或课题之一而存在,它不是用来解释他人思想的活话语,而是被拆的七零八落、丧失了原有的思想意义和力度,或被荒淡化了、或被边缘化了、或被西方化了。总之,中国传统哲学已被现代化掉了,被抛在当代视界之外了,世界哲学的未来趋向可以绕过中国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命题已被“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化”而取代了。比如: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已经忙着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写悼词了,就是最典型的一例[10]。
3.中国哲学自我消亡论。有人反思中国哲学现状,荒谬地认为,中国哲学传统自己培育了自己的异化力量,中国哲人为了迎合西方的同化而自己对自己进行了西方式的诠释,并善于借助西方的现代框架为自己吹一个西方式的牛,替别人忙活儿,完全忘了我们自己的哲学还有自我,只能用西方现代哲学的镜子照出自己的一脸无奈,或者将自己打造成西方话语的代言人,或者平白增添自己的一些傻气。一句话,中国哲学还没有入世,还不是作为世界哲学的一部分而存在,中国哲学已自我消亡了,从而只能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不出”的结论。而且有人断言中国哲学传统已发生断裂,其相当大部分理念是在图书馆里而不是在生活中,是在高楼深院的书斋里、讲坛上,而不是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而存在;再加之西方哲学的先在性强制的负面效应,中国哲学早已失去与之平等对话的资格与能力。即使得到西方哲学的同情,也只是一种有距离的承认,这并不能保证真正的接纳,更无法期待它能从“地方话”变成“世界通用语”。并错误地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哲学传统与其它一切哲学传统相比,是思想血统最不相干的一种,且由于深层冲突性和不可公度性,中国哲学传统的价值观、世界观是形成交往互惠、视界交融的最大障碍。因而,中西合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都只能是一厢情愿。
我们认为以上几种错误观点的共同失足之处在于:一是将哲学传统与传统哲学混为一谈,并错误的推断中国哲学传统已死在古人的句下;二是将经济全球化错误的等同于文化的一体化、哲学的西方化;三是将哲学的一元性与时代表现割裂开来,看不到西方“和平演变”阴谋的文化陷阱和政治陷阱;四是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起来,变相的消解马克思主义;五是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价值和实践意义,要么使之教条化、要么使之西方化。总之,只有在理论上与这些国错误观点划清界限,才能确证与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性根据与现实基础,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收稿日期:2002-11-18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