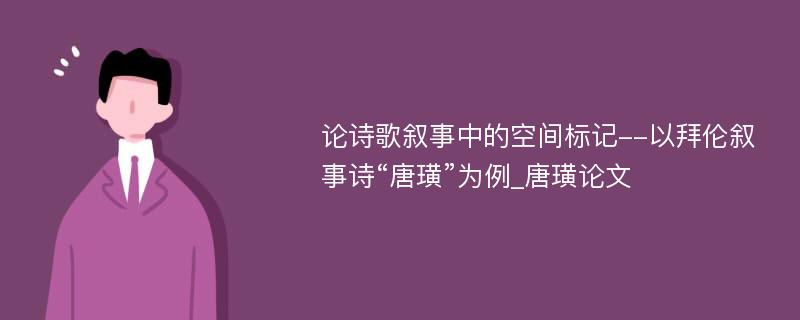
论诗歌叙事中的空间标识——以拜伦的叙事诗《唐璜》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拜伦论文,叙事诗论文,为例论文,标识论文,论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I1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198(2009)05-0184-05
尽管时间和空间同为叙事的基本要素,但在传统的叙事学研究中,空间往往遭到忽视,因而被看做是“可有可无的附属物”[1]。可事实上,空间不是叙事中可有可无的要素,而是构成叙事活动的必要基础。从文学史上的实际情况来看,很多有创造力的作家之所以创作出了伟大的作品,就是因为他们对空间有着深刻的把握和合理的运用,如有学者所论:“他们不仅仅把空间看作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事必不可少的场景,而是利用空间来表现时间,利用空间来安排小说的结构,甚至利用空间来推动整个叙事进程。”除了把空间作为叙事的技巧加以运用,叙事与空间之间还存在着更为本质的关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格雷马斯(Greimas)及其同事库尔泰(Courtés)就揭示了叙事的时空本质,并讨论了叙事中的空间定位问题。[2]在谈到空间与叙事的关系时,有学者认为:“人类的叙事活动与人类所处的空间及其对空间的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们之所以要‘叙事’,是因为想把某些发生在特定空间中的事件在‘记忆’中保存下来,以抗拒遗忘并赋予存在以意义,这就必须通过‘叙述’活动赋予事件以一定的秩序和形式。”这揭示了叙事动机的空间诱因及空间意识与叙事活动的本质性关联。近年来,叙事与空间问题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甚至认为叙事学研究正在经历“空间转向”。然而,以往这方面的研究大多限于小说作品,对诗歌叙事作品中的空间问题还鲜有涉猎者。此外,关于叙事中的“空间标识”问题,也往往为一般的叙事学研究者所忽视。基于此,本文拟以拜伦的叙事诗《唐璜》为例,来探讨空间标识与诗歌叙事的关系。在叙事活动中,空间标识往往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是建构叙事文本的基本要素,戴维·赫尔曼说:“空间标识不是故事可有可无的或是非本质的特点,而是有助于建构叙事域的核心特质……叙事在人、物、地点之间建立了关联,从而造就了空间与事件的多姿多彩的融合。”[3]赫尔曼在此所说的叙事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叙事(主要是小说叙事),而在语言高度凝练、信息高度浓缩的诗歌作品中,空间标识的重要性尤为明显:文本最表层意义上的空间,其按图索骥的功能无疑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把握诗歌的内容;文本深层结构上的空间,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领略诗歌的精神。
一、空间标识与故事场所
人类的活动总是离不开一定的场所,事件的发生也必然涉及特定的空间。那么,“场所”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日本学者香山寿夫认为:“场所就是在不断叠加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在那里发生的地方。”[4]挪威建筑理论家诺伯格·舒尔茨则把场所提到存在的高度:“场所是存在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5]美国史学理论家菲利普·J.埃辛顿则认为:“‘场所’以种种方式触及实质性的问题,它们不仅是时间问题,也是空间问题,它们只能在时空坐标中才能得以发现、阐释和思考。‘场所’不是自由漂浮的能指。”[6]从本义来讲,场所就是各种事件发生于其中的一种特殊的地方(空间);但从引申义讲,场所则可指代容纳某类主题的话语或思想于其中的框架性的“容器”。当然,本文并不想过多涉及场所的象征意义,我们只想从叙事学的角度关注作为空间标识的故事发生场所。
空间标识在故事中确实“扮演了一种至关重要的,而非微弱的或是派生的作用”[7]。在《唐璜》中,拜伦展示给读者的便是诗歌主人公唐璜人生历程中的一个个“驿站”及其间发生的各种故事。这一个个驿站——亦即发生多种事件的地理空间(场所)的切换,把唐璜传奇般的一生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些“储藏”着各类事件的场所构成了叙事的要素,而把这一个个场所串连起来,就构成了叙事的线索或情节的结构。诗歌的叙述者由唐璜的出生地塞维尔开始,围绕其周游列国展开叙述。故事涉及的主要场所(地理空间及其所承载的事件)如下:塞维尔(唐璜的出生地及其与朱丽亚发生私情的地方)——海上(唐璜的主要历险地)——希腊岛(海难后唐璜获救之地及其与海黛坠入爱河的“伊甸园”)——君士坦丁堡(唐璜被卖为奴及其与王妃发生情感纠葛的地方)——伊斯迈城(唐璜在此参加伊斯迈战役)——彼得堡(唐璜为女皇宠幸并由此被派往英国)——英国(唐璜在此经历种种奇遇)……这些场所就像是旅途中的路标,是起着事件“标识”作用的符号。《唐璜》中的一切事件都是围绕着这些场所而联系和组织起来的。
按照拜伦的设想,他打算让唐璜在完成欧洲的漫游、体验和经历各种各样的战斗与冒险之后,最后来到法国,让他参加法国革命并最终死于巴黎。根据诗歌开篇的交代,唐璜未及天年就死了。具体时间和死亡方式,随着拜伦的英年早逝已是谜了。尽管最终的诗歌文本少了拜伦预设的结局,但因全诗充分地利用了空间标识来组织事件并构成情节,其结构显得非常严密、清晰且呈现出了开放性的特点,所以《唐璜》的完整性并没有受到影响,它作为传世名著的地位也没有受到丝毫的撼动。
在《唐璜》中,我们很少看到直接的时间标识,即使存在时间标识,多数也仅仅涉及一年中时间的变换、一天中时间的变换等等,但究竟为何年何月何日并不是很确切的。例如:“那是夏季的一天,在六月六日——/我愿意在日期上力求说得准,/不但说某世纪,某年,甚至某月,/因为日期像是驿站,命运之神/在那儿换马,教历史换调子,/然后再沿着帝国兴亡之途驰奔;/它所终于留下的,不过是编年历,/还有神学答应死后兑现的债据。”[8]由这样的诗句,我们不难看出拜伦强烈的空间意识:时间稍纵即逝、一去不复返,可拜伦却把时间空间化了——“日期像是驿站”,见证了时间的流逝和历史的兴衰。在一般的叙事作品中,作者总是要通过时间的线索来组织情节,而《唐璜》却通过蕴含着时间的空间的切换来见证事件的发生、发展并揭示事件间的因果关联,从而形成诗歌的叙事线索和情节结构。
唐璜一生中关键或重大事件的发生都离不开一定的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时间概念已变得淡漠。对于读者而言,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整部诗歌阅读完毕,读者脑海中最清晰的莫过于几个重大的事件以及事件发生的空间,感触最深的也莫过于描写细腻、叙述生动的特定的场景。因此,如果说一个个大的地理空间所起到的作用是勾勒出故事的框架和脉络,那么,包含在每个大空间中的众多小空间,便为事件的细节演绎、叙事的逻辑展开以及故事的可信性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要素。以塞维尔为例,叙述者对唐璜的家庭状况颇费笔墨,如唐璜的身世、家教等,这些既为唐璜性格的形成作了铺垫,也为朱丽亚和唐璜私情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唐璜出生贵族门第,父亲早逝,在寡母的督导下,他骑马、击剑、射击样样精通,人文、艺术、科学无一不晓。唐璜长期以来被母亲禁锢在情感的真空里,可在十六岁那年,他和母亲的朋友朱丽亚双双坠入情网,于是情感的闸门被打开,感情的潮水一发而不可收拾。在朱丽亚的家,唐璜和朱丽亚的私情被其丈夫揭穿,唐璜被逼离家,远走他乡。唐璜在塞维尔的故事由自家始,在朱丽亚家终。“家”这一场所始终是诗人关注的焦点,但在唐璜的身上,前一个家不是避风港,而是堕落的开始;而后一个家纯粹就是风暴眼,是丑闻的发源地。德博拉·卢茨(Deborah Lutz)曾对唐璜一类的拜伦式英雄做过这样的分析:“拜伦式英雄,尤其是异教徒和恰尔德,不带留恋地离家流浪,他在上流社会的家庭生活中已没有位置……他深沉的思虑使其不断地迁移,延缓了其安顿下来,并且带着智力的终结和完全成形的思想,平安抵达故乡的可能性。”[9]在卢茨看来,这样的漂泊是带着寻找理想家园的梦想上路的,但这一理想是永远也无法实现的,这一旅行必然是悲剧性的,主人公离开自己的家、自己的恋人,最后走向其生命的终点。
二、空间标识与动态空间
关于空间在叙事中的作用,荷兰学者米克·巴尔这样写道:“空间在故事中以两种方式起作用。一方面它只是一个结构,一个行动的地点。在这样一个容器之内,一个详略不等的描述将产生那一空间的具象与抽象程度不同的画面。空间也可以完全留在背景中。不过,在许多情况下,空间常被‘主题化’:自身就成为描述的对象。这样,空间就成为一个‘行动着的地点’(acting place),而非‘行为的地点’(the place of action)。”[10]如果说,前者——“行动的地点”是事件发生的场所或“容器”;那么,后者——“主题化”的空间则不仅是场所或“容器”,它还是促使事件发生的重要方式。关于这两种空间的差别,米克·巴尔认为前者偏向于静态地起作用从而构成“静态空间”,而后者偏向于动态地起作用从而构成“动态空间”:“静态空间是一个主题化或非主题化的固定的结构,事件在其中发生。一个起动态作用的空间是一个容许人物行动的要素。人物行走,因而需要一条道路;人物旅行,因而需要一个大的空间:乡村、海洋、天空。童话中的主人公得穿过黑暗的森林以证明其胆量,因而就有了森林。那一空间并不是作为一个固定的结构呈现出来,而是一次迁移,可以大规模地变动。”[11]在《唐璜》中,除了作为事件发生场所的“静态空间”,还存在大量的“动态空间”,也即“主题化”空间。对于这种“动态空间”,诗人不惜笔墨地予以详实的描述,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动态空间”有着比作为事件发生场所的“静态空间”更重要的“标识”作用。打开《唐璜》,给人印象最深的动态空间是“希腊海岛”和“土耳其后宫”:前者是一个美丽的世外桃源,而后者则是东方神秘的异域空间的代表,它们都强烈地吸引或震撼着唐璜,从而导致了叙事文本中一系列围绕着这两个动态空间而产生的行动,这使得此类动态空间或“主题化”空间的叙事标识作用非常重要而明显。
(一)希腊海岛:理想的家园
深受卢梭自然思想浸润的拜伦所向往的,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是一个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的空间,那是“没有染上文明色彩,居民的个性没有为礼俗所束缚的地区”[12]。《唐璜》中的希腊海岛便是这样一个梦中的家园、理想的生存空间,它强烈地吸引着唐璜,从而导致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诗人这样描述他的梦中乐园:
那是个浪花拍击的荒凉海岛,
在宽阔的沙滩上有悬崖高耸,
沙丘和岩石像是重兵守着它,
只有些小港,水面是那么平静,
饱经风涛的人倒会被它吸引;
但傲然的巨浪不断咆哮沸腾,
只有在漫长的夏日它才停歇,
那时一湾海水像湖泊在闪耀。[13]
平静的海岸,没有沙子的滚动,也没有海浪的翻卷;只有海鸥的喊叫,海豚的跳跃和细波的冲刷。“大自然鸦雀无声,幽暗而静止,/好像整个世界已融化在其间。”[14]海岛的一切都那么静谧,让人抛开那个喧嚣的尘世,沉醉其间。在这里,相偎相依的唐璜和海黛与大自然水乳交融,“形成了一组雕塑,/带有古希腊风味,相爱而半裸”[15]。这就是拜伦理想的家园:远离尘嚣,与心爱的人相依相伴,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是自然的空间,生存其间的人是自然的:他不用戴上假面,可以以最本真的面目示人。这样的空间孕育的爱情甜蜜无忧,不需要承诺、更不必算计。
然而,世外桃源终归是诗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理想的家园依然抵不过外界力量的摧残。布兰洛一归来便棒打鸳鸯,于是唐璜和海黛一个被卖为奴,一个香消玉殒。
如今那海岛全然零落而荒凉,
房屋坍塌了,居住的人都已亡故;
只有她和她父亲的坟墓还在,
但也没有一块碑石把他们记述;
谁知哪儿埋下了如此美的少女,
她的往事再也没有人能够说出;
呵,在那儿听不见挽歌,除了海啸
在为那已死的希腊美人哀悼。[16]
同样的空间,前后的反差却是泾渭分明。在唐璜和海黛的爱情故事上,拜伦显示出他的唯美倾向,他宁愿爱情和生命都在绚烂间戛然而止,也不愿它们在平淡和衰败中走向灭亡。对此,凯瑟琳·阿狄森不无感慨地评价说:“即使是在喜剧模式中,拜伦式的悲观主义依然是至高无上的。”[17]拜伦的自然观在希腊海岛这样一处饱含自然风光、孕育自然情感的空间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而尤为重要的是:在这里,空间不是附带提及的一个地理符号,它既是诗人观念、思想和情感的寓所,更是诗人着力描写的起叙事标识作用的动态空间。
(二)土耳其后宫:异域空间
除了对希腊海岛之类自然空间的偏好,唐璜也深深地为土耳其后宫之类的异域空间所吸引。在《唐璜》的土耳其篇中,诗人对于东方神秘的异域风情作了大肆渲染。他领他们穿出大厅,一直来到
一列华丽的宫室,却鸦雀无声,
只有一间屋内听见大理石喷泉
透过夜的幽暗发出碎落的水声,
还有另一处,可能是一个女人
好奇地推开门窗而有了响动:
她睁大了黑眼睛,把头伸出来,
想看看是什么妖精跑来作怪。[18]
拜伦诗歌中这些有关异域风情的描写有别于其同时代骚塞、柯勒律治等诗人的东方题材创作,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拜伦的东方故事不是单纯地借鉴他人或是鸦片刺激下的产物。在谈及东方故事诗的创作时,拜伦说过这样的话:“我的脑子里充满了东方的名字与场景,我仅选择接近平铺直叙的尺度来讲述一个故事或描绘一个地方,它们曾使我感动过。”[19]“它是我的故事与我的东方(我在此有无人匹敌的优势,我从那里亲眼看见的东西,我的同时代人只能从其他人的作品中抄过来),我能做到绘形绘色。在按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他们一道的生活之中,我的脑子里便被塞满了他们的场景与方式。我相信如果我不按他们的方式呕吐的话,我将被送进圣卢克(精神病)医院。”[20]从拜伦此番表述中,不难窥见其东方故事诗在西方世界风靡一时的奥秘:走近东方,感受东方,体验东方。
拜伦出色的有关东方场景和情节的描写并非某个单一因素所致,它是诗人对他人的借鉴、自身的游历和奇思等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拜伦对东方的憧憬和向往由来已久。从他能够读书的时候起,他就养成了爱读历史和游记的浓厚兴趣。在十岁以前,他便读了六部有关土耳其的长篇作品,此外,还读了若干记述旅行和冒险经历的书以及阿拉伯故事集。[21]
拜伦不仅喜欢阅读游记,也喜欢自己去游历,他始终相信:“亲眼看看人类,而不是通过阅读去了解他们,这是大有好处的。”[22]拜伦认为避免“岛民的狭隘偏见”的最好方法就是到国外去学习,而了解其他国家最好的方式就是亲自体验、亲身观察。尽管拜伦在其东方表述中的事实精确度得到了批评家的普遍认同,但也有人认为其中不乏偏见和种族主义的成分。当然,也不排除《唐璜》中的“东方”反映了拜伦自己以及其他东方学者的幻想,而并非所有写到的人、事、物都源于他自己的所见所闻。而事实上,此类奇思妙想在《唐璜》的叙事建构中也是功不可没的,它们的“空间标识”作用由于“幻想”的神奇力量而得到强化。
尽管声称描写是自己的专长,可拜伦还是不止一次地流露出诗歌较之绘画艺术在描绘上的劣势:“但愿我是画家,能把诗人的/琐琐碎碎的描述都一笔点到!”[23]是的,如何在诗歌创作中实现绘画艺术对于色彩差异和空间形态的把握,这是拜伦一直深觉困惑并不断在创作中加以探索的问题。应该说,诗人的探索是成功的,比如在对像希腊海岛和土耳其后宫这样起明显的空间标识作用的动态空间的描写中,拜伦就创造了与绘画艺术同样的效果。
三、空间标识与诗歌结构
除了事件发生的场所和动态空间在叙事中具有空间标识作用,空间化了的诗歌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这种作用。
诗歌中的情节线索是诗歌结构空间化的最表层的体现。王佐良对此作了比较详尽的阐释,尽管他没有用到“空间化”之类的概念:
唐璜所作的两次越过欧洲的旅行,一次由西往东,主要是海行;另一次是由东往西,则是坐着马车疾驰……而与之平行的则是诗篇本身也由第一、第二章的滑稽歌剧式的轻松逐渐转到对人生意义和欧洲现实的更认真的探索……这越过欧洲的两次旅行不仅使读者看到不同旅途上的不同风景与人物,而且把全部情节串成两条长线,而以战火纷飞的伊斯迈城为二者的遇合点,正是在伊斯迈城头,唐璜碰上了他命运转折点——前此他是纯洁青年,后此他变成女皇宠臣。[24]
通过王佐良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唐璜的两次旅行构成了诗歌的两条情节主线,这样的情节结构的表象之下,还隐藏着诗歌风格的转换:由滑稽到严肃,由浪漫到现实。伊斯迈城是唐璜命运的一个大转折点,我们还可以根据两次旅行中唐璜命运的大大小小的跌宕起伏,以唐璜人生轨迹中的变化为横坐标,以其命运的变化为纵坐标,勾勒出唐璜命运的曲线图。正是一个个富于戏剧性的情节和场景的变化,使《唐璜》的形式空间化了,而这种空间化了的形式在诗歌中起到了“空间标识”的作用,从而增添了诗歌叙事的感染力。
在《唐璜》显见的情节结构之下,西方学者辛西娅·韦谢尔也做了深入的探索,发现了其中隐藏着的情感结构。《唐璜》有三个主要的部分或分支,这样的情节结构的划分在西方的拜伦作品研究中已达成广泛的共识:《唐璜》由朱丽亚开始的头五章在海黛部分中达到了高潮,以唐璜被卖为奴隶而告结束,这构成了全诗的第一部分;第二个五章由伊斯兰后宫篇始,导向伊斯迈战争,在凯瑟琳女皇篇达到高潮,这构成了全诗的第二部分;最后七章则为英国篇,把年轻的唐璜带到了英国,描述了他与英国社会的交往,以黑僧人的鬼魂篇作为结束,这构成了全诗的第三部分。在诗歌的结构上,拜伦看似要坚守传统,实则“拒绝把一个传统的、表面的结构强加给该诗”[25]。在传统结构分析的基础上,韦谢尔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她认为诗歌在两个层面,即情感和哲学层面上展开。韦谢尔对于诗歌广泛的情感层面展开了大量的分析,认为在该诗三个部分的任一部分中都有清晰的情感结构的证明。较之情节,情感结构是一种不太显见的结构形式。韦谢尔探寻了该诗的深层意义,梳理了三个部分的逻辑关系,证明该诗“远非漫无目的、没有结构,而是黑格尔辩证法所阐明的逻辑或智力发展的典范”[26]。韦谢尔的分析证明,随着《唐璜》情节的展开,拜伦所使用的词语在读者心中所引发的情感,以一种一致而非随意的方式在起起落落。一个包含许多愉快词语的诗节会在读者心中引发愉悦的情感,而一个包含许多不愉快词语的诗节会促成相应的不快情感的支配。基于这一认识,韦谢尔用一种被称做“情感词典”的工具结合计算机程序来考查《唐璜》中的每个表示愉悦程度的词。结果显示:《唐璜》中25000多个词语在愉悦程度上与词典中的词相配,这些表示愉悦程度的词与愉悦的数字价值相关联。韦谢尔对《唐璜》各章中匹配词语的愉悦程度计算出平均分,零代表该诗平均的愉悦度,进而韦谢尔用图表显示出各章所含愉悦程度的波动,找出其中的规律。韦谢尔发现,该诗三个部分中的第三章(唐璜与海黛的海岛恋情)、第八章(伊斯迈战争)和第十三章(介绍阿曼德维勋爵夫人)分别构成了正V或倒V的低潮或峰值,由此可以看出各部分情感有规律的起落。[27]
韦谢尔的研究证明:《唐璜》并非诗人漫无目的、随兴所至的产物,而是一部构思和布局均非常巧妙的浪漫主义杰作,其中,呈正V或倒V状的空间化的情感结构更是匠心独运、富有创意的,这一情感结构具有强烈的节奏感,也有着明显的“空间标识”作用,我们完全可以顺着这些标识去把握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和情感变化。
综上所述,空间标识在《唐璜》中广泛存在,无论是诗歌文本中直接出现的空间标识——故事场所或动态空间,还是以此为基本要素所搭建起来的情节结构和情感结构,空间标识均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在诗歌叙事中扮演着各自的重要角色:或提供事件场所,或渲染叙事背景,或构建叙事线索,或增强叙事节奏。在充分发挥传统的时间要素作为叙事素材提供者之功能的同时,拜伦极大限度地利用了空间标识,从而大大丰富了《唐璜》的表现形式,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