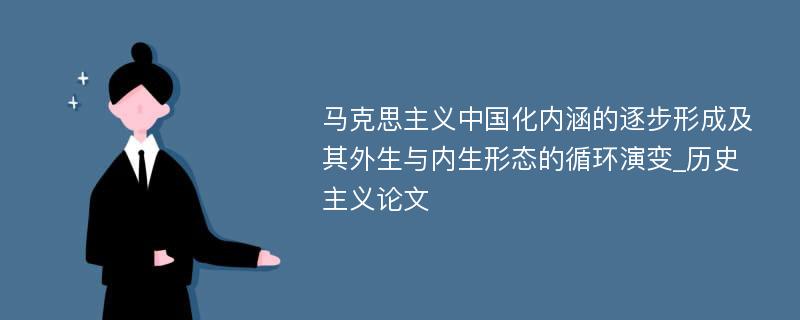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渐次生成及其外生、内生形态的循环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形态论文,内涵论文,内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迄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研究尽管不乏灼见,但既忽视了该概念内涵是由对中国人民解放发展事业而言的外生、内生形态的渐次生成、循环演进所构成的矛盾统一体,也忽视了该概念内涵的生成所具有的可完成性与不可完成性矛盾统一的特性,把该概念内涵理解为一次成型、一成不变的无内在相互作用的凝固抽象体。对问题的这种误解,难免误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有鉴于此,本文试对该概念内涵作一改进性解读,以期深化对该问题的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研究文献综述
艾思奇于1938年4月提出“哲学研究的中国化”[1]387,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萌生。毛泽东于1938年10月率先直接提出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1941年他又对该概念作了进一步阐述:“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3]374
以上论述无疑是诠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初始性、经典性文本。它首先肯定中国革命需要学习、内化本民族优秀历史遗产和外来马克思主义,以获得相应的思想支撑。对其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资源学习、内化,总是在中国人民主客观条件约束下进行的,为其学习之后所内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再是原生态马克思主义了,而是被这种约束中介了的打上了中国印记的马克思主义,因而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既然如此,那么,学习、内化马克思主义,生成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及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题中应有的第一层含义。
但这一层含义在经典性文本中并没有被直接揭示出来,而只是隐含于上下文逻辑中。该文本直接阐发和着重强调的则是:中国人民学习、内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及结果,是受中国人民优秀历史传统、中国现实特点、中国特定民族文化等国情约束的过程,必须使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内化统一于这些约束条件,为这些约束条件的内在要求服务。这种从上述国情约束出发,由统一和服务于这些约束内在要求的学习、内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及结果所生成和获得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再是原生态的而是被上述国情所中介了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该文本所阐述的这一层内容,自然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题中应有的第二层含义。该文本对概念内涵的这种界定,为对中国革命具有现实契合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生成提供了思想前提,是对该概念内涵部分精髓的科学揭示。但这一层面的界定由于未打通与上述第一层面界定的内在逻辑联系,使它与上一层涵义的历史承接关系处于被遮蔽状态,从而忽视了该概念内涵渐次生成的历史特性。
经典性文本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中国人民学习、内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及结果,必须与国际背景相融通。但由于这种被国际背景中介了的学习、内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及结果,仍与中国国情相契合,所以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因此,该文本所内蕴的这一层内容,自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题中应有的第三层含义。遗憾的是,这一重要含义也只是内在地潜涵于该文本上下逻辑中,而并未为该文本的直接揭示和明确阐发。
经典性文本继而既然认为,“提高”而不“降低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来实现。那么,由此所提高了的“理论”尽管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毕竟既非原生态马克思主义,也非无民族特性的一般马克思主义,而是基于“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这一点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题中应有的第四层含义。但该文本同样未揭示这一层含义与上述几层含义的逻辑联系。
综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初始性、经典性文本内蕴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上述几重界定,其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中国人民在国情和国际背景约束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生成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从“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生成中国本土新马克思主义,来为中国革命提供具有民族和历史契合性的马克思主义支撑的过程及结果。这种界定,直接、间接地勾勒出了该概念内涵的基本方面,是关于该问题认识的初始性、经典性成就。但由于该文本主要是基于现实政治而非主要基于学术视野来阐述该问题的,故从学术角度看,存在着前述缺陷。由于科学的本质在于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而该文本所做界定存在的前述缺陷的要害,就在于未揭示该概念不同层面的内在联系,这使得它并未有效地完成关于该问题的科学认识。因此,系统、深入、历史地认识该问题,是后人所必需承接的学术使命。
后人迄今关于该问题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其一,“适合性结合论”,即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实际,并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4]1这种较为普遍的观点,不但是对毛泽东前述观点的承袭,而且由于未揭示“结合”的具体构成及其历史性,未回答“结合”的内容是凝固、外在并列的,还是历史的、互动演进的等问题,较之于前者还有所倒退。其二,“创造性应用和创新发展论”,即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加以创造性地应用,并将实践经验加以提炼,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5]与毛泽东前述观点相比较,该观点不但在重复前者,而且离开学习强调创新,从而相对于前者也有所倒退。其三,“具体化、民族化、新鲜化论”,即对马克思主义而言,使它适合中国情况,并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赋予它中华民族的风格和特点,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着眼于中国新的实践,把它的发展不断推向新阶段。[6]与毛泽东前述观点相比较,该观点不但同样在重复前者,而且也未揭示学习和创新间丰富的历史性联系。其四,过程论,即是一个对应于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7]该观点尽管正确地把问题看做一个历史过程,但并未揭示“过程”的具体构成及其内在联系,使所谓“过程”显得模糊、抽象、空洞。其五,阶段论,即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传播、运用和创新的中国化等三个阶段。[8]该观点正确地肯定了问题具有历史性,但却把体现这种历史性的不同阶段间的关系仅看做是线性、单向、机械叠加关系,从而把问题简单化、片面化了。需要指出的是,除过上述代表性观点外,一些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例如,“世界视野论”[9]3、“世界观的自由提升论”[10]、“主题”论[11]等,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某一属性,但所揭示的并非问题的本质属性、直接属性,而只是其非本质属性、间接属性,故不但不足以构成关于问题内涵的规范界定,而且可能误导人们关于该问题的认识,需谨慎对待。
后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上述研究,尽管把毛泽东关于该问题的前述经典界定一定程度上具体化了,但总体上是在复述、演绎和细节性地修补这一经典界定,既无对该经典界定的反思、深化和超越,对问题的认识仍局限在该经典文本的限度内,也未能形成统领该概念不同层面内涵的完整逻辑系统,未能形成把不同向度的、散乱状态的研究有效整合起来的基本范式。导致这一切的成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确当框架。因此,探寻确当的解读框架,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确当解读框架的选择与内涵的解读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基础概念。正确界定“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概念,是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需要确立的解释框架的首层含义。从语义角度看,该概念中的“主义”,指对“对于自然界、社会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理论和主张”[12]1294,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达尔文主义。可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层面的东西,是由一定基本原理构成的关于人类解放发展事业科学性的理论支撑系统。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还包括其经典作家在特定条件下,对人类解放发展实践中具体问题所做的具有特定针对性、适用性、有效性的具体论述。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客观地区分为由其根本精神、基本原理构成的第一层面,和由其关于特定条件下具体问题的具体论述构成的第二层面。本文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理解和运用,限定在它是上述两层面构成的这种理论预设的框架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无缘无故的,也不是先验、前定的,而是基于特定的背景、历史需要生成的。杜威指出:“倘若要彻底明了任何复杂的产物,最好的方法是追溯它的构造的经历,——推源它的发展所经过的继续相承的时代。”[13]394可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着眼于其由以生成的具体根源、过程及结果来解读其内涵,这构成了其内涵由以被正确解读所必需的基本解释框架的第二层含义。由于这种解释框架着眼于被解释对象生成的根源、过程及结果,所以本质上是一种生成论的解释框架。不难看出,解释框架前一层面的功能,在于为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基本的语义保障;解释框架后一层面的功能,在于为正确解读该概念提供基本的着眼点。这两个解释框架的层面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该概念内涵被正确解读的必须的基本解读框架的整体。
从上述基本解读框架的整体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是由下述四重依照特定逻辑而依次生成、内在关联的内容所构成的完整历史性的整体系统。
从该解释框架看,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发展,是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完成该任务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可是,中国既有思想文化传统并不具有这样的科学理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14]796但对中国人民而言,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种异质文化,其精髓、核心和基本原理并不具有自明性;中国人民对它的理解和接受,也不可能不受自身文化传统、生存经历和内在品性等因素约束。这决定了正确地学习、认识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绝不可能是一个顺畅的线性过程,另一方面又是马克思主义能有效引导中国革命走上正确轨道的首要环节。然而,被正确学习、认识了的马克思主义,毕竟已是被中国人民主客观条件中介了的马克思主义,即打上了中国印记的、与中国国情相契合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可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可见,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初始涵义只能是指中国人民在自身主客观条件中介下,学习马克思主义,把其内化为自己所掌握的、与中国国情相契合的理论的过程及结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重内涵。
中国革命的民族特性及其发展所不断引生的一系列新问题,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既有形态难以始终有效地引导中国革命。上述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一定程度后,中国人民就能凭借其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创立能有效指导中国革命发展的新的科学理论。这种新创立的科学理论是以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基础的,所以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毕竟是新创立的中国本土性马克思主义,因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态。可见,基于对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解和掌握的基础,中国人民基于自身实践创立中国本土性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及结果,自然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题中应有的第二重内涵,即相对于前述初始内涵的次生内涵。
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不断深入而不断创立中国本土性新马克思主义,必然以中国人民马克思主义修养不断提升为前提。这就要求不断学习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及基于中国实践所创生的次生态马克思主义。这种不断学习的过程及结果,本质上是中国人民基于新的实践和理论背景,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既有资源的理解和认识,积聚和提升契合中国革命要求的马克思主义修养的过程及结果。中国人民由此所理解、掌握的深化、提升了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中国化形态。可见,这一过程及结果,自然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题中应有的第三重内涵。对第三重内涵与第一重内涵而言,其区别在于:前者是有自觉革命实践基础的学习,且是对原生态和次生态马克思主义整体的学习,是一种以提高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关于它的修养为向度的学习;后者是没有自觉革命实践基础的学习,且只是对原生态马克思主义以启蒙、传播、普及为预期的学习。第三重内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学习的过程,不是一次性的,也不是简单重复性的,而是一个适应中国革命实际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实际,不断扩展、提升、深化的历史过程。
不断深化的中国革命,需要中国人民不断创生出中国本土性新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人民顺应中国革命不断深化的历史进程,基于不断提升的马克思主义修养,进一步创生中国本土性新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及结果,自然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题中应有的第四重内涵。该重内涵与第二重内涵的区别在于:第二重内涵所刻画的创新主要是基于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该重内涵所刻画的创新以原生态和次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而第四重内涵所刻画的创新的实践基础,与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已有了质的差别,因而该重内涵所刻画的创新更具探索性、挑战性。
当然,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发展事业是一个无限深化的历史过程,所以,以上述学习和创新为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会不断在新的高度循环再现,以至无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首先,其内涵是渐次生成的,而不是一次成型的、凝固的。其次,其内涵不是无内在差别的单质,而是由学习和创新构成的矛盾统一体;再次,学习和创新不是相互外在、相互孤立的,而是互为背景、相互渗透、相互驱动的;最后,学习和创新间这种相互渗透、相互驱动是无限上升的,而不是简单重复、同质循环的封闭圆圈。综上述,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中国人民在继承民族优秀传统、国际化视野、中国革命和社会实际等变量约束下,以学习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将其内化为与中国国情相契合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为起点,着眼于“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创立中国本土新马克思主义,继而适应革命实践发展要求,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基于此在新的实践中,创立更新形态的本土马克思主义,从而遵守这种学习和创新互动,为中国人民解放发展提供具有历史契合性的马克思主义支撑系统的过程及结果的统一体。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初始生成:“中国化”外生形态及其实质
前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形态,作为中国人民通过学习,把外在于中国人民解放发展实践的、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与中国国情相契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过程及结果,是该实践逻辑的和理论的前提。没有这一逻辑的和理论的前提,中国人民解放发展事业在当时条件下就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14]796。而“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就意味着学习、掌握它,把它内化为与中国国情相契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生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形态,从而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形态,在客观上只能生成和展开于中国人民自觉、自为地追求解放发展的事业之先、之外,只能主要是由外在于该事业的资源孕生、发育而来的,也主要是由该事业之外的资源规定并在该事业之外历史地实现的,而不是内在地生成于中国人民解放发展事业展开的具体实践过程,不是该事业实践过程经验的理论表达。该事业在这个发展阶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初始形态的关系,主要是学习、内化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并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基本原理。它尚不能在自身内部创生出中国本土性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尚不能为马克思主义贡献新的内容。这一切表明,前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形态,客观地生成于中国人民解放发展事业之外,呈现为对该事业而言的外生形态。它具体表现为中国人民通过学习而获得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具体掌握形式,并呈现为思想渊源和世界背景两个不同层面的形态。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初始形态而言,它的外生性在其思想渊源层面主要表现在:首先,它是由作为其外在思想渊源的西方原生态马克思主义转化而来的,并受该思想渊源约束;其次,它是对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发展事业思想前提的西方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学习、继承的产物;再次,这种学习的能动性使它不可能是西方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简单摹写,但这种学习的启蒙性质决定了它对该思想渊源的统一性远高于对其的差异性;最后,它仍未超出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固有水平,烙印于其中的中国特性,只是对所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转换性表达,而非对它的创新和超越。
如前述,由于马克思主义可区分为第一和第二层面,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思想渊源层面的外生形态的生成,既必须彻底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前述第一层面;又必须坚持以历史、批判的态度来统一于其前述第二层面,决不能秉持原教旨主义态度,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向教条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整个世界近现代化大背景下发生、演进的,必然为该背景所规定和塑造。就此而言,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这一外在于中国人民解放发展事业的世界背景生成的,从而有着对该事业而言的一定程度的外生性,表现为对该事业而言的外生形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5]1471,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世界背景层面的外生性的一种具体表现。这一世界背景层面的外生形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成了多重限定。首先,外在世界背景的复杂性,决定了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其次,必须在世界视野与民族国家视野相结合的高度来驾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其既具有世界历史内涵,又切合民族特性。再次,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其世界化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和驾驭,在二者相互促进中共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内涵的生成既然对中国人民解放发展事业具有外生性,那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初始性外生形态,对该事业具有一定独立性。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生形态的根本规定性和实质所在。这种根本规定性和实质,深刻约束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生形态:首先,它决定了这种外生形态对中国人民解放发展实践自在状态的终结、自为状态的生成,具有逻辑和理论前提的地位。其次,它决定了这种初始性外生形态,只能是向异质文化学习、为中国人民解放发展积聚理论前提的过程。再次,它决定了这种外生形态只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环节,因而必须向其发展了的环节转化、提升。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继起生成:“中国化”内生形态及其实质
中国人民解放发展事业的民族性、历史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生形态不可能为其提供普遍有效的支撑。该事业历史发展需要不断获得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支撑,也就不再可能仅仅通过学习外在于该事业的马克思主义既有资源来获得,而只能由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生形态基础上,立足于其解放发展实践来创立。承前分析可知,由此创立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及结果,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及结果。该过程及结果在多种意义上内在地生成于中国人民解放发展实践:
首先,从主题上来看,驾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力量,是作为追求解放发展实践主体的中国人民,这一主体具有双重身份。作为中国化过程主体的中国人民,依据其追求解放发展实践的经验、历史遭遇、现实处境、内在偏好、具体成就等诸方面属性,创立中国本土性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及结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及其成果,自然就对中国人民解放发展实践具有内生性。
其次,从孕生的母体和基础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及结果,既然是基于中国人民解放发展实践的规律、趋势和要求,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既有内容的同时,对它的创新和发展,那它就必然因符合于中国人民解放发展实践的规律、趋势和要求等规定性,并随着该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而自然对中国人民解放发展实践具有内生性。
再次,从生成和展开的环境框架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及结果,并不具有抽象性和先验性,而是依托于中国人民解放发展实践这一基本的环境条件,并随着该环境条件的历史展开而相应地生成、展开和确定的,从而使得该过程及结果自然就内在地孕生于中国人民解放发展实践之中。
最后,从被约束和限定的根本度量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及结果,既然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发展过程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及结果,那它就必然为该解放发展过程所约束,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为该解放发展过程约束的函数,从而自然对该解放发展实践具有内生性。
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生形态基础上,创立中国本土性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及结果,既然内在地生成于中国人民解放发展实践过程,那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内生形态,对中国人民解放发展实践过程具有根本的依赖性、统一性。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生形态根本规定性和实质之所在。这种根本规定性和实质,具有多重内在意蕴。一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用来直接指导各民族解放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前定、先验、凭空而生的,只能来源于人类特别是各民族追求解放发展的实践活动,只能来源于对该实践活动内在的要求、规律、经验的理论概括、理论反映和理论预瞻,因而,在根本上只能统一于人类一般性特别是民族性的解放发展的具体实践,对该实践具有根本的依赖性。二是指导中国人民解放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人民解放发展的内在规定性相契合,绝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外在地裁剪中国人民解放发展事业。三是这种内生形态对中国人民解放发展实践的依赖性、统一性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中国人民通过能动地认识、理解、提炼、预瞻其解放发展实践内在要求、规律、约束条件、经验、趋势、前景等基本内容,以创立本土性新的马克思主义方式,统一于中国人民解放发展实践的。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非只是马克思主义简单输入、与中国实际简单结合的过程,而是学习性输入、结合和立足本土实践创立新马克思主义这二者的统一体。五是这种内生性形态生成的过程,是为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向异族文明开放的。因此,不能把内生和外生对立起来,同时必须积极向外部文明学习。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外生、内生形态的无限循环演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上述外生、内生形态渐次生成之后,并不意味着该内涵最终形成。中国人民解放发展事业无限深化的历史特性,决定了该内涵必然随之不断深化。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发展事业的无限展开,对支撑它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需要必然是无限的、历史的,而该事业对中国本土性马克思主义的孕生也必然是无限的、历史的,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外生、内生形态的渐次生成,也必然是一个无限的历史过程。这种无限性,具体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生成,以初始性外生形态的生成为起点,催生初始性内生形态生成,接下来又促使继生性外生形态生成,进而又激发继生性内生形态生成,并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发展事业的无限深化和无限上升,继续沿着新的内生形态催生新的外生形态、新的外生形态催生更新的内生形态这种矛盾运动模式,朝前无限循环演进,从而在无限深化和无限上升的历史趋势中,为无限深化、上升的中国人民解放发展事业,提供具有历史契合性的马克思主义支撑的无限过程及结果的统一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渐次生成,尽管具体地表现为一个内生形态在继外生形态之后生成,并与之形成无限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但二者间这种相互作用,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任意的,而是以解释学循环形式向前无限推进的。在中国条件下学习和创立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是根据条件约束来理解、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而“解释是在三种相互渗透的关系中循环:解释首先要以语言形成的文化背景作为理解与意义得以发生的整体。相对于这个文化背景而言,解释者和被理解对象都是置身于其中的部分关系。尤其是这个语言中的文化背景,正是提供了解释者之所以具有理解能力的‘前理解’的存在基础。而这个作为解释者和被理解对象的文化背景,是由解释者的‘前理解’或‘先见’来间接地作为理解发生的整体意义关系。”[16]33-34对外生形态和内生形态而言,前者一定程度上孕生了后者,是后者得以生成的“前理解”或“先见”和基础,前者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后者。就此而言,后者一定程度上是由前者转化、衍生而来的。不过,后者也构成前者新的形态生成的“前理解”或“先见”,也始终处于向前者新生态不断生成、转化的过程之中:后者提出和规定着前者进一步发展的课题、方向、内容。就此而言,前者进一步发展的状况,一定程度上就是由后者转化、衍生而来的。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发展进程的无限展开,二者间这种通过互为“前理解”或“先见”而相互驱动的解释学循环关系,也必然随之无限展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外生、内生形态间这种循环演进并不是抽象的,它必然要通过外生、内生形态二者内容的相互渗透、相互转化来进行。对外生、内生形态而言,其各自内容的真理性程度并不是抽象同一的,而是存在着高低差别的。那些其真理性不具有较高普遍有效性的内容,必然因不具有充分的内在活力而在“中国化”过程中被淘汰,逐渐走向寂灭;那些其真理性具有较高普遍有效性的内容,必然因其具有较为充分的内在活力,而不但必然在“中国化”进程中存活下来,而且必然会超出其原来外生或内生形态的存在范围,对作为其对应方的内生或外生形态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渗透、融入对方,为对方所吸收和包容,作为对方的内容而继续存活下去,并激发对方的真理性具有较高普遍有效性的内容有效生成,进而与之结合在一起,向其新的对方渗透、转化和融合,或者说向其原来的出发点复归。
当然,这种情形的出现和存在,并不是偶然的,一次性的,而必然会在外生、内生形态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发展事业的历史演进,而不断展开的相互作用中持续地生成和存在。不难看出,这种情形的本质,正是外生、内生形态各自内容间解释学循环展开的过程。既然能够进入这种解释学循环的内容,是那些其真理性具有较高普遍有效性的内容,而那些不能进入这种循环或在这种循环中被淘汰的内容,则必然是那些其真理性不具有较高普遍有限性的内容,所以,那些能够进入这种解释学循环并在其中保持持久活力的内容,一般来说,总是具体表现为外生、内生形态所内蕴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表现为那些对中国人民解放发展事业具有普遍有效支撑功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容。正因为如此,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历史生成过程中,逐渐积淀、凝聚、升华和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熟、确定和具有持久生命活力的内涵。相应地,那些不能进入这种循环或在这种循环中被淘汰的内容,一般来说,总是具体表现为外生、内生形态中只适应于特定时空条件的内容,即马克思主义的原生形态及由其“中国化”而来的继生形态中,那些关于特定的具体问题所做的具有严格“时效”、“域效”的具体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外生、内生形态的这种循环演进,也是通过这二者相互地位的历史的、周期性的更替而展开和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性外生形态发育到一定程度后,内生形态必然随之继起生成。认识的积累性发展规律,决定了“中国化”初始阶段,外生形态相对于内生形态必然处于主导地位,后者只能处于从属地位。但中国人民解放发展实践的不断演进所遭遇的各种新挑战的有效应对,对马克思主义既有理论所不具备的新的理论支撑的内在需要,必将促使内生形态在“中国化”课题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外生形态尽管也要进一步发展、演替,但其地位会逐渐相对下降。按此趋势演化下去,内生形态较之于外生形态必将逐渐上升到主导地位,外生形态则必将逐渐下降到从属地位,“中国化”随之进入到以“出新”为主导的新阶段。而中国人民解放发展进程的深化,则迫切需要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汲取支撑该进程的更进一步的理论力量。这必将使继生性外生形态随之由此生成,并必然相对于逐渐萌生的继生性内生形态,在“中国化”课题中居于主导地位,逐渐萌生中的继生性内生形态则必然处于从属性地位。但这种地位关系,同样会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发展事业的演进及其对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支撑内在需要的生成,而内在地实现循环性的替换性否定,使这种继生性内生形态的主导地位,被新的继生性外生形态所替代,这种继生性内生形态则下降到从属地位,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生成,进入一个新的高度。但二者相互地位的这种循环性的替换性否定,并不会到此终结,而会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民解放发展事业互动关系的无限展开,在不断更新的继生性内生形态与不断更新的继生性外生形态之间,周期性地无限循环演进,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走向新的高度。这一过程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生、内生形态,分别在各自内容相互渗透和相互地位的周期性更替这两个层面,以前者作为后者的基础、向后者转化为起点,通过后者反过来规定、驱动前者、向前者的深化形态生成,经由前者和后者各种历史形式,并在前者和后者内在地互为基础、背景和“先见”,相互向对方渗透、生成、转化的关系中,形成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发展事业的无限发展而无限深化的周期性的解释学循环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在其历史演进中整合在一起,历史地生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完整内容。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民解放发展事业的思想前提地位、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该事业所具有的外来文化性质,以及该事业的发展对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撑系统的期待等因素,既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是中国人民在其解放发展事业内外变量约束下,通过学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来为该事业提供具有历史契合性的马克思主义支撑的过程及结果的统一体;也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内在构成、内在关联、内在趋势及其具体特性的有效解读,所可能依凭的确当解读框架的基本范式,既必须是生成论的,也必须是结构论的。从这种生成论与结构论相统一的解读框架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既不是先验、前定、一次成型、一成不变的凝固态的东西,也不是简单同一的封闭单质,而既是渐次生成、无限演进的,同时也有着显明的内在构成形态的差别和特定的内在互动范型。
综括性地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是沿着对中国人民解放发展事业而言的外生和内生两条路径,以其外生形态的生成为起点,以其内生形态的继起生成为阶梯,并通过这二者的无限循环演进,而渐次生成的由这二者所构成的无限深化的矛盾统一体。外生和内生这两种不同构成形态,分别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生成和存在,对中国人民解放发展事业的相对独立性和内在依赖性。但这两种构成形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中并不是简单并列着的,而是始终处于以解释学循环形式所构成的无限互动关系之中,并在这种解释学循环驱动之下,凝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既无限更替又无限深化的有机历史系统。不过,由于外生和内生形态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发展事业的无限上升所形成的解释学循环关系,受马克思主义内在固有的前述两个层次的差别的约束,同时也受中国人民解放发展实践历史性的约束,并不是一种封闭的、简单重复性的循环,而是一种开放的、淘汰性、批判性循环,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生成,既具有可完结性,也具有不可完结性,是可完结性和不可完结性的矛盾统一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这种内在本质特性、内在生成特性、内在结构特性、内在关联特性和其内在历史特性,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驾驭,只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上述一系列基本内容、基本特性相契合,才可能免于误入种种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