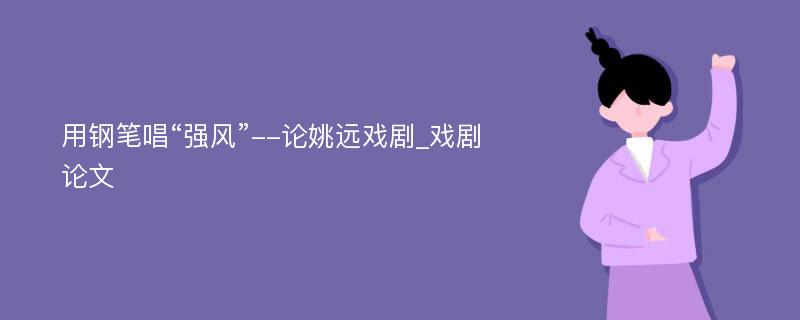
携笔从戎唱“大风”——姚远剧作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作论文,大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开场铃已经响过了。和观众一样,我也正等待着大幕徐徐拉开。每到这个时刻,我心里总惴惴不安:台下能有多少观众呢?——也许,今天又来得很少。是的,现在喜欢看戏的人越来越少了,可我却愈来愈爱上了这块小小的天地。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奇怪,命运为什么要这样来安排。
——摘自姚远剧作《下里巴人》剧中人的话
姚远五幕话剧《下里巴人》里串场人物上官淑华的这一段幕前语,也正是我们的剧作家执著于话剧事业的内心独白。命运为我们安排了这样一位剧作家:因为有了他,剧坛少了些许寂寞。这位“携笔从戎”者,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已成为军队剧作家队伍中承上启下、年富力强的一代中的佼佼者。近年来他独立完成的大型戏剧作品有:《下里巴人》(1985)、《天堂里来的士兵》(1986)、《商鞅》(1989)、《李大钊》(1992);与人合作完成的作品有:《迷人的海湾》(1992)、《窗口的星》(1994)、《青春涅槃》(1995)、《伐子都》(1995)。此外还有多种小戏和影视作品问世。在剧作家构筑的这一座座戏剧殿堂中,观众既可领略万面鼓声、怒澜飞空的雄阔,亦可感受蝶飞南园、池生春草的诗意,甚至还会有沐猴而冠、措大言志的戏谑。他的作品多次获军内外大奖。其中《商鞅》获“田汉戏剧奖”,《李大钊》获国家文化部“文华新剧目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今天,谈论部队的戏剧创作,姚远已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名字。
也许正是因了“携笔从戎”的缘故,较之在部队“土生土长”的剧作家,姚远的创作视界更为开阔和丰富。他有一段下乡插队和地方剧团的生活经历。参军之后,他又多了一份军旅生活。一个作家,总有自己题材的热点和生活的敏感区。姚远自不例外。作为历史剧大师、《大风歌》的作者陈白尘先生的研究生,姚远显然对历史剧情有独钟。不妨说,他的作品在整体上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线上的同时,其“含金量”并不总是相等,其最出色的作品乃在于历史剧。
史诗·超越
如果说人们称赞姚远的作品“大气”只是一种感觉式的赞语,那么换一种确切的说法,这种“大气”是因为姚远的作品特别是他的重要作品突破了一般描写个人遭遇和家庭问题的模式,而将主要笔力放在广泛深入地表现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历史题材。在这方面显示出作者善于驾驭这类题材的功力。
“史诗剧”是布莱希特对戏剧的重要贡献。大概可以把它看成戏剧中的奥林匹克。“史诗剧”的难度,不在于事件的繁复和结构的宏大,更在于作家对时代、历史、人生的独特感悟,在于作家目光的穿透力。一个只“拥有”生活的剧作家,也可能写出好的作品,但难以写出伟大的作品。剧作家一定还要“深思”。一个剧作家的视野是在对自己的经验进行不停的反思中被打开的。这个反思的过程一方面是心理的过程,一方面是智力的过程。王国维所谓“大家之作”的奥秘在于“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是很有道理的。最好的例子是《商鞅》。怎样写商鞅?在历史上,商鞅总是和、也仅仅是和变法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目光停留在再现商鞅变法的历史事件,虽然也会在某些方面给今人以借鉴,但将仍停留于政治的层面,仍属“短期效应”。艺术的目的是要从精神上深刻地影响人。因此,作者决心取另外一条路子。《商鞅》写商鞅从弃婴到魏公叔家的家臣,从魏国之逃犯到执掌秦国的政柄,写他为图大业而置母亲、弟弟的生死于不顾,割断与韩女的恋情,把最忠于他的学生孟兰皋断送作人质,骗杀有恩于他的公子卬,写他为他的“商君之法”,不惜残害黎民以致“渭水尽染”。最后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作法自毙,被车裂而死。显而易见,作者笔力下在写一个英雄的悲剧,而不是悲剧的英雄。这样就把戏的“格”定在写人的存在上。《商鞅》中的商鞅虽是个强者,但仍不能摆脱一些不可克服的弱点,比如其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欲望的产生,比如一些不可摆脱的孤独。这些注定商鞅是个悲剧性人物。剧作借写商鞅,提出的是人的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而使剧作的主题超出政治批判剧的层面,上升到人生哲学的层面。因为商鞅的悲剧性命题,同样横亘在当代人面前。因此两千多年的商鞅,在今人看来不是一个僵死的面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朋友。以这样的“主脑”剪裁史料,诘难者可能会说离历史真实远了,可谁又能不说它离艺术真实近了呢?
现代史剧《李大钊》的成功虽然是多方面的,但究其荦荦大者,首先还在于作者能够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上理解一位伟大的先驱者。谈到这部剧的创作,作者曾说;“起初有人建议我截取李大钊和孙中山开创国共合作新局面的一段来写。但我觉得,如果不写李大钊的死,不足以反映他那璀灿而壮烈的一生。”《李大钊》把对时代的描写,准确定位在旧时代的垂死和新世纪的临产。李大钊正是一位站在这一临界线上的巨人。应当说这样来把握李大钊同志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便站在了一个思想的制高点上。对于《李大钊》的创作来说,能否拥这样一个制高点,大体说来有着“一着不慎,全盘皆输”的重要。而取材于“文革”普及样板戏岁月剧团生活的《下里巴人》,以“上级”强令锡剧团改唱京剧为艺术契机,着力透视的,是那段历史中的种种荒诞不经。从艺人们为了生存,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揭开了人在社会强力下渺小、无奈的一面。又通过对文化局副局长沙一蜂等正面形象的刻画,显示了美的无处不在和人的伟大,从而把生存价值的思考留给观众。近作《伐子都》则从一个表现因果报应的戏曲故事中看出了人类存在的某种荒诞。于是作者将其反其道而行,假历史为依托,大胆虚构,透过郑国老君王驾崩、新君王未立的历史转折关头,两位公子庄公和子都,以及两位皇亲考叔和素盈为争夺王位和周天子送来的美女如意而展开的一场勾心斗角的“窝里斗”,和如意为了坐上王后宝座,也机关算尽,力图使人们从这一出四男一女的闹剧中思索自我在今天的存在。
文学上有著名的“冰山理论”。戏剧大师也有类似的格言,即与其说观众要看舞台上的优孟衣冠,不若说他们更希望看到这优孟衣冠背后的东西。画界则早有“象外之象”之说。艺术的规律是相通的。剧作家是否成熟,往往取决于他或她超越题材的能力。对于这一功力的取得,应该倾听一下法国浪漫主义理论家弗·希勒格的说法:“为了写好某一个题材,应该对它不再发生兴趣。我们想深思熟虑地表达出来的思想,应当是我们已经疏远的思想,应当是不再引起我们兴趣的思想。当艺术家热情奋发地创作的时候,他至少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方面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中。”思想靠读书滋养,思想在沉淀中完成。依笔者陋识,当代戏剧创作之所以缺少大手笔,之所以缺少生命力久远的作品,剧作家这方面功力之不逮,恐怕是不能讳言的一个原因。而姚远却善于在人生哲学的层面上实现其超越。他的重要作品犹如陈缸之老酒,虽放置经年,一旦打开却依然透着袭人的香气。这实为难得的创作上界。
“反写”·画魂
艺术作品没有思想统领不行,但在真正的艺术中,思想却不应有赤裸裸的形式。文艺的伟大使命在于塑造活生生的人物。“人”,无疑应是艺术应当关注的真正中心。这个道理,人皆能知。但在艺术实践中,却并不能人人成功。原因之一,在于不会以艺术辩证法去完成塑造。在戏剧作品特别是大型作品中,对于人物的塑造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面来完成。第一个层面是外型。仅仅给予人物性别、年龄、相貌特征、服饰等的若干描绘。这类人物是人物造型上最简单的一个层面,由于它只显露出角色的外观特征,因此在剧中可能不会影响戏剧行动。第二个层面是社会的。包括一个人物的经济地位、职业、宗教、家庭关系等。显然这类人物比之第一个层面的人物具有了一定的立体感。第三个层面是心理的。它显露出一个人物的习惯、态度、欲求、动机、爱憎等。不论是情感的或是智性的,由于思想情感的习惯与行为较之外型与地位更能代表一个人的特质,也由于戏剧行动多半起于欲求的冲突,因此这一层面是戏剧人物塑造的一个关键。第四个层面是道德的。一切戏剧创作都有最广义上的道德教育意义,特别是严肃剧。道德抉择是人物性格的试金石。从人物面对道德考验时所做的选择便可以看出他或她是自私的、虚伪的、或是正直的。此时戏剧人物的本性便会在观众眼前暴露无遗。这是一个最深的层面。这四个层面的人物虽然有深浅之别,但在一部剧作中是按需要被使用的。作为被剧作着力塑造的主人公,却必须进入上述中的第四个层面才能“立”得住。《李大钊》中对李大钊的塑造是很见出作者功力的。如果把李大钊写成一切正确原则的化身,有可能超出观众的“可接受度”而失败。剧作家是从两个方面深入刻画李大钊形象的。一是李大钊从赞同“好政府主义”转到信仰马克思主义后,与先前的朋友出现了分歧,比如与军阀幕僚白坚武,与蔡元培、章士钊。剧作写李大钊并不因友情而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亦不因见解的岐异而损害他们之间的友情,即使如已入敌人营垒的白坚武。这样做是很难的。但李大钊做到了。他像马克思一样,只有公仇而没有私仇。乃至李大钊与他们完全分手、为主义而死之时,白坚武甚至也为之求情,对刽子手杨宇霆说:“他骂了我,可是骂得有理呀。因为他的救国之心是可以见得天下,而你我的救国之心就未必了。你可以讨伐赤化,我可以镇压乱党,因为我们是各为其主争夺天下。”这种由其他角色对人物评价呈现的塑造方式,揭示了李大钊形象的特质。二是李大钊是反封建、妇女解放的斗士,但他却给自己包办婚姻的童养媳妻子赵纫兰以忠贞不二的爱。这是一种真正的无私与牺牲。剧作设计的李大钊与赵纫兰诀别的一场戏感人泣下:
李大钊:“我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赵纫兰:“不,我要比别人都有福气,因为你从没嫌弃过我。大钊,你先走吧,等到下辈子,我再找你,我就会比你年轻许多许多。”
剧作写李大钊恪守着中国“士”的传统道德,却又高举着共产主义的大旗。他是那类用自己的身体肩住旧时代的闸门、让青年一代踏着过去的真正的巨人。这就写出了与同样是共产主义创始者的陈独秀的根本不同。公正地说,《李大钊》从道德上刻画李大钊胜于从主义上刻画李大钊。姚远是深谙艺术辩证法的。所谓“若要甜,加点盐”,所谓尽可能反写而不是顺写者也。《商鞅》中的商鞅之所以丰满、有光彩,也是得益于在“盐”中写“甜”。作为一个历史上早有定评的英雄人物,很容易循着某个固定的思路写得陈旧。作者却能够将商鞅置于“两难”中刻画。一方面,写商鞅大刀阔斧变法,特别是一场为太子加冕的戏,商鞅重赏奴隶乌丑、断公子虔左足、革太师职,刺字于面,使朝野震惊,从此“法令无不遵行”,充分展示了商鞅的强者风采。另一方面,又通过写他断亲情、立酷刑、赵良避、尸佼走,写了权力对他的异化,写出了他人性中“恶”的一面。这样,便在商鞅这个人物身上写出人的全部复杂性和矛盾性,同时也有力地规定了商鞅作为“这一个”人物的特质。在艺术中,唯有这样的形象才能算“鲜活”,才能有较为久远的艺术生命力和强烈的艺术冲击力。故而姚远不赶所谓“时髦”,去进行所谓“三无”:无主题、无故事、无人物的戏剧试验,甚至也对“散点透视”、“景片拼接”等凡是无助于以人为本的样式敬而远之。
如果说《李大钊》《商鞅》显示的是姚远对英雄人物的成功把握,那么在《下里巴人》中我们领略的则是姚远为“小人物”画魂的努力。《下里巴人》中的地方小剧团团长、演员、乐手、伙夫等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整日坐着“噗噗”作响的机帆船沿江飘泊。他们在政治高压下被剥夺了生活与爱的努力。但即是这样,他们仍然钟情于艺术,以自己台后的辛酸换来台下观众的欢乐,向人们奉献上美。他们可谓“烛灯烨氍毹,涕泪泫笙管”。这种精神美具有强烈的冲击力。
一部大型戏剧作品,哪个人物应当浓笔重彩,哪个人物只是轻描淡写,取决于该人物在剧中的地位。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恰如观众不需要知道上场仅说一句“准备好了”的战士甲的性格。但对主要人物缺乏有深度的刻画,台上只见人影幢幢,不见“人物”则仍是当前我们戏剧创作的宿疾。戏剧如果不能进行成功的人物塑造,便不能使观众“再现”为演员,也便打消了观众身上本应有的那种深刻的内心情绪。一旦观众既不为演员的懿德叹为观止,也不为演员的恶行怒不可遏,一旦他们成了真正的“观”众,那么戏剧的意义还在哪里呢?
“意味”·“趣味”
艺术是什么?它和非艺术的区别在哪里?按照现代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的说法,艺术应当是“有意味的形式”。艺术又是花招,是圈套。对于戏剧艺术来说,就是要求剧作家在两个多小时里“套”住观众,令他们相信不会受骗,令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兴奋的殿堂,接受愉快的精神按摩,受到身心的洗礼。作为一个成熟的剧作家,姚远自然不敢放松对“有意味的形式”的追求。综观姚远的剧作,可见其在内在张力、情趣语言等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若干艺术上的特色。
姚远不是一个刻意追求表层结构新颖、或者说“玩形式”的剧作家。他的作品,大都是所谓传统结构,即以事件发展的正常时序为序,依次展开开始部、展开部、高潮部、结束部。但他无疑在刻意追求结构的内在张力。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通过人们对其各个部分的相关性的理解来被充分把握的。而在戏剧中,部分之间的关系的特征就是一种张力的关系。在戏剧中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张力——在台词被理解的不同方式之间,在两人物之间等等。但是潜在的、持续的张力是在随时出现的情境和完成的行动之间的张力。这在一部剧的开头尤为重要。因为它规定了整个行动从中发展出来的情境,并且确立了这部剧所要求关注的中心。姚远的大型作品,场面大,人物多。《商鞅》和《李大钊》出场的人物仅有名有姓的就有十数个。如何“先声夺人”?《商鞅》把商鞅的死提到开头,设置了商鞅与主要对手之一巫的鬼魂的对话,把戏的关目商鞅惨死先亮给观众,从而使剧本在行动的开端时就已经将观众被期待的东西建立起来了。《李大钊》则在一开幕先来一个剧中人的“自报家门”,依人物在戏中的地位,由徐世昌开始,四或五人一组次第上场。最后是毛泽东和李大钊。这一方面是因为这出戏的历史背景复杂,非如此不能使观众一下子入戏。另一方面,对李大钊也起了渲染、烘托的作用。这样,开头显然已经明确无误地指向了剧的中心(商鞅、李大钊),但决不是已经“明戏”,观众近期和长期的期待都要等戏的终结才能完全实现。这实在可称为“凤头”式的开头。
但是,要让一个剧本保持某种不完美的均衡状态直至行动的完成为止,要使观众产生“连环期待”,还必须设计出情境的悬念性和惊奇性。几乎所有的戏剧大师都是制造未解决的或只有部分得到解决的悬念的大师。以莫里哀《达尔杜弗》(《伪君子》)为例说明这一点。伪君子达尔杜弗向他恩人奥尔贡的妻子埃尔米尔求爱。但奥尔贡拒绝相信会有此事。于是妻子在和伪君子见面时,让丈夫藏在桌下。然而,尽管她不断咳嗽和敲桌子提示,丈夫始终未一跃而出。由于埃尔米尔在面对一种寡廉鲜耻时处于毫无援手的地位,她能否洗清自己?她将如何向丈夫表白自己的爱?于是便在戏的现在和它还未产生的结果之间造成了一种张力,也就是所谓“戏剧性幻象”。以《商鞅》为例,作者选择的这个题材,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因素。商鞅一心事秦最后反被车裂,观众是有兴趣要看个究竟的。《商鞅》写得一波三折,扣人心弦,充满了戏剧性冲突。如第四幕商鞅出征伐魏,对手恰恰是与他相知二十年且有恩于他的公子卬。商鞅在以孟兰皋为人质骗公子卬来帐中“叙旧”前,早已蓄意杀公子卬。公子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一点。于是,公子卬的死于商鞅手下,便成为观众一种“想象的真实”,观众期待被验证。在电视文学剧本《爱神的眼睛》中,指导员单国刚与在照相馆的姑娘邓蕾之间也很有“戏”。两人由错寄照片到发展成“恋爱”关系;及至见面才知姑娘有一双小儿麻痹的腿。于是又转真成假,单国刚退缩;尔后才是“弄假成真”。一个情境发展成另一个情境,引导观众从一种期待发展成另一种期待。至于惊奇,姚远也运用得很多。《李大钊》剧本第17节,李大钊正与章士钊夫妇在家议事,警察敲门,问:“李大钊先生在屋里吗?”众惊慌,把李推进里屋,情境是急迫的。不料,大钊却又大笑着从里屋走出。原来大钊听出这是已被他“争取”过来的两个警察。这种“突如其来的进场”,在已经确立的情境中突然引入新的因素,从而造成戏剧的“特殊重音”。姚远的剧作之所让人感到饱满、引人入胜,正是因为他的内在结构是“密针线”的。
艺术的“意味”大半还在于它的“趣味”。戏剧亦不例外。“趣味”的范围极广。这里仅从“机趣”角度考察一下姚远的剧作。李渔在谈“机趣”时,特别指明是反对一种道学气。“所谓无道学气者,非但风流跌宕之曲、花前月下之情当以板腐为戒,即谈忠孝节义与说悲苦哀怨之情,亦当抑圣为狂,寓哭于笑。”在《李大钊》中有一场陈独秀与李大钊初次在章士钊的日本家中见面的戏。这两个政治“巨头”见面,处理得“板腐”一些似也无可多怪。但姚远却让陈独秀先是狂妄得躲进厕所不见,且以大钊的文稿作手纸。等到在厕所里听到大钊与章士钊的一番宏论后,竟然在厕所里大喊“行严哪,给我送草纸来!”随后重新与大钊以礼相见。可谓神来之笔。《商鞅》是古代史剧,人物对白用的是韵古。但唯独公子卬用的完全是当代痞子的语言。如公子卬送商鞅逃离魏国时的一段对话:
公子卬:来人,给卫鞅套西装!
商鞅:西装?
公子卬:向西而行,岂能不穿西装!
又如:
公子卬:拿钱来!
商鞅:既去秦国,赠魏国之钱又有何用!
公子卬:傻帽!到了秦国,这就是外币!
亦可谓之庄出谐中。《伐子都》更是将严肃与调侃,真实与荒唐,高贵与庸俗,理智与狂放放进同一个足以暴露其不合理性的架构之中,熔情境喜剧、仪态喜剧和人物喜剧于一炉,形成强烈的喜剧效果。其中以“击鼓传花”的方式确立王位,这一从封建现实中提炼的黑色幽默,准确而又独到,完全符合莫里哀“以滑稽突梯的描画,攻击我们世纪的恶习”“通过娱乐来改正人的错误”的喜剧性原则。从《伐子都》可以看出剧作家创作心态的自由。这出剧表现形式奇巧怪诞、不合规律,违背人们的常识常理,表明剧作家真正进入了如柏格森所说的“心的麻木”的喜剧创作心态。亦即脱出创作的严肃心态,取得一种自由的、居高临下的嘲弄心态。只有在这时,剧作才能导引观众进入喜剧审美。
戏剧是一种困难的形式。19世纪伟大的小说家巴尔扎克也曾写过剧本,但都失败了。他承认:“写剧本的尝试不顺利,暂时需要放弃。历史剧要有强烈的舞台效果,我又偏不熟悉……”狄德罗则认为“喜剧和悲剧是戏剧创作的真正界标。”他说,一切自觉有戏剧天才的作家必须首先练习写严肃剧。在练习写严肃剧的过程中对人作了长期研究的戏剧家,方可进一步选择悲剧与喜剧。如果可以认为严肃剧是戏剧创作中最容易的一种,那么我们便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伐子都》在姚远戏剧创作道路中的意义和地位。
困惑·突破
如是,我们可以回到本文的开头来认识姚远:他的作品在整体上包含了较高的思想文化品位的同时,其“含金量”并不总是相等的。他最出色的作品还在于历史剧。相对而言,他的军事现实题材剧作则显得逊色。写于1986年的多场次话剧《天堂里来的士兵》,剧作者的初衷是通过战争证明新的历史条件下军人存在的价值。可以看得出,为使剧本“好看”,作者在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以及将剧的生活面由军营拓宽到社会等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在当时同类题材剧作中,此剧也算是比较好的。但由于作者对作品所确立的主题的理解尚停留在社会如何评价军人群体而没有进到军人自我审视的层面,由于急于去“证明”而不是去“显示”,所以创作并没有处在一种自由的状态。又因此,尽管戏够火爆,战场戏、情感戏、牺牲戏轰轰烈烈,但仍使人感到是一出外张内弛、缺少内在张力和心灵震撼力的戏。与人合作、写于1994年的另一部大型作品《窗口的星》是一出证实九十年代军人生存方式和存在价值的戏。就敏感地感受生活、提炼新的戏剧矛盾、塑造新的军人形象而言,剧作在同期部队话剧创作中当属上乘。但由于剧中主要人物抵制“灯红酒绿”的方式以及因此确立的剧本结构和人物关系,与《霓虹灯下的哨兵》相类,而贯穿全剧的主要矛盾又难以如《霓》剧那般彻底(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于是,“焦点”的模糊使得这出戏在《霓》剧的巨大光环下显得相对黯淡了。
依姚远对生活的理解和对艺术的把握,他是应当能够克服上述创作的不均衡状态,在军事题材剧作上作出突破的。然而他在大多数军队剧作家都处于的困惑面前也显得一筹莫展。综观姚远军事题材剧作的苍白,可以发现剧作家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困惑。一是对和平时期军人价值如何体现。战争年代,军队军人解民于倒悬,其社会价值和在文艺中的地位是摆定了的。和平时期,军人保卫和平并非靠看得见、听得着的隆隆炮火,更多的却是靠了自身默默存在的威慑,遗憾的是这一点并不会被所有的人清楚地认识到,军人也因此常常陷入不能证实自己的痛苦之中。改革开放的社会变迁,价值取向的多元也愈来愈不利于取向单一的军人获得社会承认。正如生活中被无理地讥为“大兵”的军人们无法向歌厅舞场上的人们证明,那令人陶醉其间的欢乐与他们的抛妻别子有着怎样的联系;在艺术中,军人剧作家也苦于不能再让主人公像当年赵大大那样冲上去断喝一声,进而痛快地扫除社会垃圾。于是,社会转型期军人自我的不确定成为剧作家无法回避的困惑。二是由于前者,便出现了一种创作路数,即企图以“诉苦鸣不平”以乞求世人对军人的理解,或者,演绎新的战争故事来达到为军人“正名”。姚远的军事题材剧作亦大体在这一路数之中。应当说,这体现了军人作家的一种政治责任感。这类剧作,也会收到好的宣传效果。但是在这种以情感感化而非理性认识的价值确认方式下,多少是一种对于戏剧应有深度的削弱,也是对于探讨和平时期军人内涵这一创作课题的逃避。无论从建立具有阳刚美的军旅戏剧舞台文化考虑,还是从艺术家应当具有“知难而进”的精神考虑,都需要剧作家的笔触深入到商品大潮与神圣职责撞击下的军人的内心世界去探幽抉微,由军人的自审写出他们的自立,从剖析军人作为生命个体所承受的种种社会压力及其对世界的感知中发现崇高,从而提高军事题材戏剧的整体水准。
艺术的过程是双重的。艺术家伴随着他的艺术一起成长。我们寄希望于,像在历史剧领域已取得相当成就那样,在军事题材领域中再走出一个新的姚远。正是:“开场铃已经响过了,我们正等待着大幕徐徐拉开。”
1995年10月1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