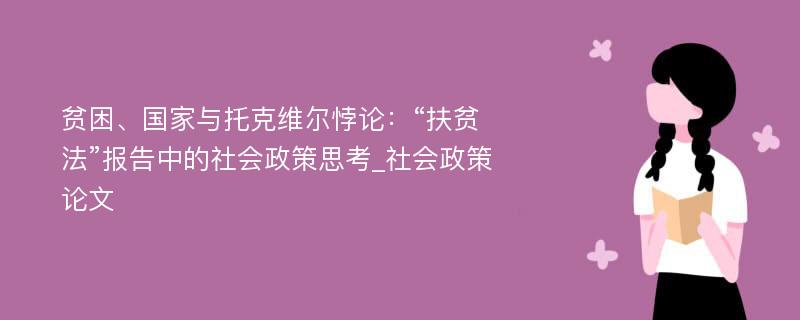
贫困,国家与托克维尔悖论:《济贫法报告》中的社会政策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维尔论文,贫困论文,思想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去岁以来,研读托克维尔蔚然成风。国人津津乐道于《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提出的托克维尔悖论,大意是革命暴力往往是在一个富裕而不是贫穷的国家发生,越是自由的地方,真诚改革反而越会触发革命。①说来也神奇,在很多转型国家,托克维尔悖论确实如同魔咒一般灵验,世人也因此惊叹托克维尔一些神人般的政治预言。这样一来,反而很少注意到他的预测亦有失灵之时。1830年代,欧洲最富裕、最自由的国家英国同时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议会改革催生了社会运动,数以百万计的城市中产阶级投身其中;济贫法的修正则深深触动了下层民众的传统福利,各地的抗议和骚动此起彼伏,席卷英伦。②形势如火如荼,仿佛革命风暴近在眼前,以至于托克维尔在1833年匆匆忙忙赶往英国,要亲眼目睹英国历史上难得的一幕。③可是,最终英国的改革并没有引发暴力革命或者阶级对抗。那么,为什么托克维尔悖论会在英国失效呢? 有人或许争辩说,托克维尔日后曾经做过解释,认为英国的贵族体制更加开放。④可是,这种说法充其量只是告诉我们英国社会中产阶级何以丧失了“革命斗志”,可无法解释下层民众为什么也没能形成暴力革命?其实,托克维尔本人倒没有忽略英国下层民众。在1833年和1835年,他两次访问英国,走街串巷,从西南乡村到工业中心城市曼切斯特,探访下层民众生活,认真思考贫困、两极分化和阶级冲突等社会问题,回国之后写下了《济贫法报告》。他得出结论说:“我预感……济贫法,这个……丑恶而巨大的溃疡……迫使富人仅仅只是穷人的佃农……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暴力革命。”⑤ 可是,托克维尔的这个预言百年之后亦只听阁楼响不见人下梯,以至于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他预言的不是革命而是出现下流阶层。⑥为什么这次预言没能成为现实呢?本文认为这和托克维尔的社会政策思想和社会问题研究方法有关,他误解和低估了社会政策在社会控制功能方面的作用。具体来说,通过解读《济贫法报告》,本文发现托克维尔尽管有些独到见解,但总体上他的研究方法存在瑕疵,既缺乏扎实的实地调查,也没有做细致的文献梳理。他忽略了英国福利制度复杂的历史背景,没有理解普通法系之下社会权利的渊源和现实意义,其社会政策绩效评估也不加审视地接受流俗之见,从而忽略了旧济贫法等社会政策的重大作用,结果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社会政策大致上包含着四个层次,一是探究社会问题何以成为一个社会事实?⑦其产生的客观社会经济结构是什么?人们的社会问题的意识是如何产生的?二是社会权利,所指向的问题是即什么人获得福利,获得何种福利?⑧三是实施社会政策的体制,研究的是什么样的政体或者行政系统来实现社会权利?四是如何衡量社会政策的绩效。本文按照这四个层次分别考察托克维尔的社会政策视角。 托克维尔的社会政策思想 托克维尔的社会政策思想可分为四点:从主客观因素讨论贫困的起源;阐释济贫法中的社会权利;分析济贫体系以及评价政策效果。 1.贫困何以成为社会事实?虽然社会政策研究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成熟,但是托克维尔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思路远迈同代学人。他意识到社会问题的出现不仅有客观的社会经济结构因素,还与人主观的社会认知密不可分,是集体认知的一种事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社会问题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进一步演变为一种制度事实,即存在法律意义上权利与义务关系。因此,分析社会问题除了阐释社会经济结构,重要的是要解释社会问题如何从个人主观认识转化成社会乃至制度的事实。这种分析方法从他对贫困问题的思考中可以体现出来。《济贫法报告》一书分为两卷,上卷集中探讨了贫困的社会起源,体现了他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经济结构关系的思考。在英国期间,他坐着马车穿街走巷,从大都市伦敦到西南部乡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一开始,他为英格兰富庶所震惊,说自己“置身于现代文明的伊甸园之中”,“维护很好的宽广道路,整洁的新房,膘肥体壮的牲畜悠然在丰草上,健壮的农场主。”⑨但是,当他安步当车,进入一些地方教区、翻阅地方政府台账时,发现“这个繁荣的王国有六分之一的人口是靠公共慈善的开支而维生的。”⑩相形之下,即便欧洲穷弊之国如葡萄牙者,纵然乡村满眼尽是陋屋草棚,人们愚昧而尚未开化,衣衫褴褛,贫困人口亦不过二十五分之一。为什么英格兰富甲欧洲,同时也是贫困率最高的国家呢?英格兰并不是特例。在法国,最富裕的诺德(Nord)地区,每六个人中有一个穷人,而最落后的克吕斯地区,每五十八个人中才有一个穷人。(11)也就是说,经济越发达,贫困人口比例越高。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托克维尔认为贫困问题是三个层次的问题,它根本上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客观结果,其本质上也是个人的主观认识,同时还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一个制度事实。 中古之世,社会结构简单,社会成员主要分为有地的封建主和无地农奴。当时经济落后,封建地主即便社会地位较高,生活上也无舒适可言。至于农奴,无论是庄园还是村社,大部分实行敞田制和三圃制,他们被分配一定的土地,但这些土地高度细碎化。(12)所以,“农民生产出的基本的必需品,市场可能有时较好,有时较坏,但是基本上还是有所保障,如果一个突发的原因阻止了农业产品的业务,至少这些农业产品能够使得它的收获者维持生计并且让他能够等待好的时机。”(13)加上教会施舍等措施,也就保证了社会中下层生活在糊口线上。(14) 随着经济发展,分工更加细密,工业社会逐渐取代了农耕文明。在托克维尔到访时,英国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他自己估计英国人口中只有九百万从事农业,其余一千四百万转入工商业。(15)但与农民相比,庞大的工商业阶层有更大的生活风险。确实,这些工人收入较高,但可一旦有新技术应用或者外贸冲击,那么传统行业就会受到冲击,生意萧条,工人则常常失业。这种社会化风险明显超出了个人控制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贫困是工业化的产物。托克维尔明言:“我认为工业阶级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特殊而危险的使命,通过他们所冒的风险和危难来保证所有其他人在物质上的幸福。”(16) 除了客观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因素,托克维尔还敏锐地注意到了社会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主观认识的产物:贫困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它是贫困。同样的客观社会生活条件,未必人人都认为贫困。比如托克维尔探访过的印第安土著,其生活水平与美国新英格兰城镇社区生活可谓天壤之别,但是衣食原始的印第安人并不认为自己生活在贫困状态,除了火枪他们并不羡慕白人。托克维尔认为社会发展和地方风俗差异造就不同的贫困标准。换句话说,不同的贫困主观感受和认知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在某种情况下更是一种集体认可的制度性事实。托克维尔时代绝大多数普通法国人食物单一,主要是面包,蛋白质的来源基本上靠大豆和鱼类,至于苹果酒和肉类则属于稀罕之物。法国穷人更是连面包都不足,常常在灾荒年代用麦子换取栗子橡果为生。据估计,当时法国人人均摄取卡路里热量还不到3500卡路里,连生存线都没有达到。(17)在法国大批中下阶层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候吃糠咽菜已经司空见惯,没有人因此而被视为贫困并收到救济。而此时,英国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免于饥荒的国家。英国人普遍认为不仅饥饿是痛苦的,没有体面衣服及房屋也是痛苦的。英国贫困标准自然要高于生存线。在17世纪教区的记录上不绝于缕的是英国穷人领到衣物,在教区举办的各项欢庆活动或者过节的时候,畅饮啤酒,大块吃肉。(18)所以,尽管就生活水平而言,英国许多穷人生活要比法国中等农家还要舒适。 2.贫困何以成为一种制度事实? 贫困不止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如果穷人由此可以获得某种福利,那么它就成了一个制度事实。那么是什么使得它变成了一个制度事实呢? 托克维尔指出,获得救济的社会权利是构成贫困制度事实的根源。从一开始,托克维尔的济贫法报告就认真讨论社会权利问题,从他选用穷人这个词汇就可以反映出来:他选择Pauper而非poor来表示穷人。Pauper一词具有特定法律意义,指的是那些在特定社区里有资格领取救济的穷人。选用Pauper一词,实际上也表明他在法律层面探讨穷人领取救济权利问题。托克维尔的社会权利观念有两个特点。其一,他阐述这些权利都是采用列举方法描述的,明确而狭窄。但权利主体是特定的,他说那些“无能为力的婴孩,衰残的老者,疾病者,精神错乱者”等都应该由公共慈善机构承担照顾他们的义务。其二,与同时代的学者相比,他又扩大了救济权利内涵。传统救济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救急,较少考虑如今阿玛蒂亚森所说的能力(capability)问题。托克维尔则意识到这一点。他说:“我所理解的公共慈善应该是对于穷人的子女开放免费的学习,并且培养他们能够通过劳动获得基本的物质必需品这样的谋生能力。”(19) 虽然托克维尔明确提出了特定群体的社会权利,但是总体上他否认穷人享有社会权利,不认为仅仅贫困就有领取福利的资格,特别是坚决否认那些身强力壮的男性具有领取福利的资格。他说人性都是天生懒惰的,世界上只有两种情况才能使得人辛勤工作,一是饥饿,二是出于安逸生活的追求。对于穷人来说,只有饥饿才能使得他们勤奋工作;如果一旦生存无忧,那么绝大多数穷人就会变得好逸恶劳,心思花在申请救济上而不是寻找合适工作。(20) 托克维尔的断言绝非纯粹逻辑推理,而是亲历法庭观察的结果。他发现贫民普遍在滥用社会权利,不少身强力壮者不去努力寻找工作,却三番五次要法官给予更多救济金,因而社会权利也会大大腐化社会。他说:“试图创立一个有规则,持久,一致的法律来缓解贫困,却不考虑带来贫困人口的增长,每一次满足他们需求的同时也会助长他们的懒惰和他们恶习所带来的无所事事。”(21)结果“所有这些滥用的权利……就像是种下一个橡果,当根茎发芽,然后长叶,开花,结实,总有一天将会从土地里产生出一片森林时,对于我们只会是震惊而茫然不知所措。”(22) 3.社会福利体系:现代社会的恶之花 如果说托克维尔认为社会权利会腐化社会,尤其是毁灭新教工作伦理,那么英国社会救济体制在他看来简直是不可救药的。他指出:“在我去英国旅行的这段时间里,济贫法已经得到了修正。许多英国人自以为是地认为这些改变将极大地影响到穷人的未来,可以提高他们的道德,并且减少他们的数量。”(23)主张改革济贫法的英国人士认为旧济贫法导致了懒惰,福利开支剧增等等,因而坚持加强中央政府管理体系,合并组成大型救济区,结束室外救济,设立济贫院强迫穷人工作等。(24)托克维尔对此并不以为然,他说尽管“非常欣然地能够去分享他们的这些期望,但是却无法认同这些能够实现。“当下英国的这种新的法律只是再一次重申了伊丽莎白两百年前所引进的原则。”(25) 托克维尔认为福利体系无论如何改革,都只有两类:除了私人慈善外就是公办慈善。民间慈善机构实施的福利是个人本位的,强调要消除影响个人发展的各种不良因素。私人慈善“很少出于本能,更多地出于推理;很少出于情绪,通常更多地出于能力,导致社会去关心它不幸的成员,并且系统化的预备来缓解他们的痛苦。这个模式产生于新教,并且仅仅在现代”。(26)相比之下,公共慈善则不同。它立足于共同体本位,基本假设是,如果社会成员遭遇种种不幸,国家当仁不让要帮助他们。英国的公办福利看上去很美,但是实际后果却无助于解决贫困问题:“没有什么比区分因为恶习导致的不幸还是本不应当遭受的不幸这两种差别更为困难了。有多少的穷困是这两者同时所导致的啊!前提是要深刻了解每一个人的特点以及他所处的环境,要具有相当的认识,相当敏锐的观察力,还要有相当冷静而决断的推理!”(27) 托克维尔虽然在《济贫法报告》中没有更为详细解释这个问题,但是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述了中央集权官僚济贫体系的低效低能:“御前会议根据总的税收情况,每年拨给各省一定基金,总督再将它分配给教区作为救济之用。穷困的种田人只有向总督求告。饥荒时期,只有总督负责向人民拨放小麦或稻米。御前会议每年作出判决,在它所专门指定的某些地点建立慈善工场,最穷苦的农民可以在那里工作,挣取微薄的工资。显而易见,从如此遥远的地方决定的救济事业往往是盲目的或出于心血来潮,永远无法满足需要。”(28)由于对于公办慈善制度的轻视,托克维尔没有深究英国济贫制度中的具体操作方法。 4.济贫法的效果:社会腐化的温床。 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政策绩效评估需要几个步骤:选择特定群体,确定标准,进行抽样调查获取相关数据,检测绩效评估。但是托克维尔的访问并没有现代社会的调研条件和工具,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从整个社会而不是仅仅从目标群体角度来评估政策绩效的。他所考察的评估标准一共有以下四个: 首先,公共慈善行为不会提升穷人行为。“穷人获得社会救助的权利不仅不能够提升人的内心,反而降低了良心的标准。”(29)他们“就像动物那样看待未来,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当下和下贱而短暂的享乐,他野兽般的本质根本不会意识到命运对其的主宰。”(30)所以,“尽管整个国家其他人群已经教育普及,道德提高,品味也变得高雅,举止更为优雅,穷人却仍然没有改善,甚至有些倒退。”(31) 其次,济贫法制造了福利依赖阶层。穷人本来无论从工作技能还是社会交往行为能力都远远脱节于主流社会,只能寻找一份苦力工作,勉强温饱。如今既然济贫法把救助变成了权利,那么出于好逸恶劳的人性,穷人自然会依赖济贫权利维持生计。 其三,收入分配更加不公平,经济发展逐渐迟滞。由于穷人的生计越来越依赖于济贫税,富人承担的济贫税负越来越重。有些地方甚至出现10%不到的富人缴纳了近90%以上的济贫税。(32)于是,富人沦落为“穷人的佃农,储蓄的源泉,也会干涸,资本的积累也将停止,贸易的发展变得迟缓,人类的勤勉和活力渐渐麻木。”(33) 其四,社会疏离因此大大增强。在传统的基督教社会中,得到施舍的穷人会感激施舍者,施舍者也会因为救济获得救赎,这本来是两全其美的事情。除了教会,大家庭也是提供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但是,济贫法让国家越俎代庖,承担了原本大家庭的责任,导致了传统的退化和失效。一方面穷人滥用济贫法,满足了肉体生存需要,却依然“带着绝望和妒恨,思索着自身的不幸。”而富人却因为税负日重而越来越却害怕和厌恶穷人。最后结果就是,济贫法“在单一的民族中,能够破坏(穷人和富人)彼此之间那仅有的联结。它将每个人安排在一个旗帜之下,数点他们,然后使他们面对面,为彼此争战做准备”。(34)长此以往,“任何永久性的,定期的,以提供给穷人生活必须为目标的行政体系,最终将会产生比其所治愈的问题更大的灾难,也将会使人变得堕落,只想获得帮助和安逸,到那时将只会迫使……给这个国家带来暴力革命。”(35) 托克维尔社会政策思想的缺陷 托克维尔在社会政策思想方面不乏洞见,认识社会问题层次分明,尤其多角度分析贫困问题让人叫绝,但耐人寻味的是他所写的《济贫法报告》及其思想却长期受到冷遇。他在1833年开始写作《济贫法报告》,1835年发表,几与《美国的民主》同期。前者默默无闻,而后者却一时纸贵,两者境遇,云泥之别。即使1968年《济贫法报告》英译本问世之后依然反响平平,连雷蒙阿隆在介绍托克维尔社会学思想时,也没有提及此书。与英美学者热捧他的政治思想相比,他的社会政策观点几乎无人关注,这种巨大反差部分可以归咎于他做出的与后世大相径庭的预言。托克维尔预言英国的福利政策不过是饮鸩止渴,迟早将会触发革命。可之后150年,英国的福利制度规模越来越大,体系越来越完整,即便上世纪80年代新保守主义政治家撒切尔等发誓要拆散福利国家,福利体系依旧完整。(36)其他欧洲发达国家更是步英国后尘,在二战之后纷纷建立起福利国家,逐渐消弭了历史遗留的等级分化和社会不平等,以至于马歇尔等相信福利制度让英国告别革命。而托克维尔社会政策研究得不到学术界重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济贫制度的观察描述及济贫法历史的阐释方面确实存在不少值得商榷地方。 托克维尔一再声称济贫法腐化工作伦理,并且说这是基于现实的观察。可是,由于他的这种观察基于英法两国社会环境相同的假设,所以他的结论并非客观,免不了主观臆断。以《济贫法报告》中申请救济的妇女为例。其丈夫远航海外,音讯渺然,她独自抚养孩子。托克维尔以为她的公公既然有钱,理应由大家庭照顾。可是他忽略了英国和法国的家庭结构的不同。13世纪以来,英国的核心家庭越来越多,与欧洲大陆主流的扩大家庭结构差异越来越大。(37)到了18世纪,如果说法国乡镇大家庭尚能向年轻夫妻提供很多帮助的话,那么同时期英国来自大家庭的帮助肯定远远不及法国,(38)因此政府的干预非常必要了。但即便如此,也并非意味着政府要承担所有费用。政府首先根据家庭资产而非家庭亲疏关系来评定介入的程度,比如按照英国普通法,在丈夫离开时候,如果孩子没有抚养,那么就要看其资产来决定政府提供的资金数额。(39) 再比如三个青壮男子申请救济的案例。托克维尔认为当时工作很容易寻找,他们要求救济不过是好逸恶劳本性罢了。可是,英国失业情况有别于法国。斯内尔等学者指出英国劳工的失业,很大一部分是季节性失业,而非自己懒惰或自愿性失业。他根据剑桥,诺福克等地教区的档案分析,发现十一月开始到二月份,失业率接近15%。三月份开始下降,到八月份达到谷底3%,然后又开始上升。(40)英法两国农业经济的环境因素不同。法国面积大,其南部属于地中海气候,所以全国一年四季都能农耕放牧;许多法国北方农民可以一路南下,寻找工作,终年不息。但是英国不同,四季分明,一到冬季,农活结束,大量农业工人失业;救济的作用在于帮助他们度过寒冬,也使得农业资本家有足够的劳力。(41) 除了托克维尔那些带着有色眼镜的观察,他的有关济贫制度历史的描绘也很模糊,有误解乃至错误的地方。他说是1601年的伊丽莎白济贫法规定了各地教区的征税,可实际上英国在1536年就开始允许地方教区征税来进行救济,而最早的强制性征税则出现在1572年。至于1601年的那部济贫法,并不是第一次制定济贫法律,不过完成了之前半个世纪的各地实践的总结和整理而已。(42) 托克维尔认为亨利八世冲冠一怒,引发的教会改革,没收教产,大大削弱了教会力量,使之无力承担社会救济。这一观点与史不符。中世纪早期,英国约克大主教曾经把济贫作为教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明文提到十一税收入中一部分用于救济。但是到了14世纪,十一税的收入连维持教会运作都很勉强,更不用说济贫开支了。(43)正是为了克服自愿捐赠不足的问题,英国才出台济贫法,在教区基础上建立了全国性网络型的地方政府,获准强制征收济贫税。 托克维尔说济贫法限制了人们的迁徙自由。表面上看,济贫法似乎在束缚劳动力的流动。济贫法对于四处流浪,家无居所的青壮的处罚可谓严苛。可是细察历史,可以发现真实情况并非如此。随着经济发展,济贫法有关的惩罚变得有名无实。到了18世纪,一般市镇很少处罚或者驱逐年轻力壮的劳动力,原因之一是为了获得稳定的有一技之长的劳工。许多市镇,在经济萧条时候还特别为外地劳工提供救济,以期经济恢复后发挥他们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是成本问题。驱逐令需要上级法院核准,实施时要提供交通工具,费时不少,成本不低。所以,尽管济贫法有驱逐的法令,但各地实施得并不多。斯内尔估计英国东南部乡村的教区每年驱逐的案例一般只有一两例。(44)真正被驱逐的,绝大多数是老弱妇幼,而不是劳动力。(45)实际上,济贫法的目的是控制流民,而非劳动力。 托克维尔认定济贫法中的居住地条款把福利资格和出生地紧紧绑在一起。确实,济贫法中的福利申请与发放同居住地密切相关,有点近似于中国人福利权益同户口挂钩一样。可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各地地方政府的推动,济贫法中出生地和福利资格的法律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一个人的福利资格中,出生地是最为重要的因素,1662年英国颁布的居住地法案中就明确把出生地作为首先考量的社区身份资格。但是同一条法律中,也宣称住满40天以上有资格成为当地居民。(46)但是如何证明一个人居住40天呢?1692年,又颁布法律,说要在教堂公示之日起才算天数。(47)日后,随着经济萧条,许多教区无力承担救济任务,对外来陌生人的救济也更加严苛,取得居民身份途径也越来越窄,只有那些对社区有实质贡献的才能取得身份。衡量实际贡献采用直接和间接办法。直接的就是具有劳动能力,最好是专业技能的人,法律规定学徒在满师之后就能够成为当地居民。(48)此外为地方政府和社区工作的人,包括值更员也都取得居住资格。(49)间接的就是按照居住房屋的房租。比如居住房屋或者其它资产年租价值超过10英镑,并且住满一年就取得了身份。(50) 如果不属于上述群体,主要也就是从事非技术劳动的那批人,往往可以按照法律在公示日期满40天之前被当地人驱逐出去。但是,执行法律成本相当高。驱逐需要当地治安法官同意,签署命令。如果被驱逐者不同意,也可以向上级法庭申诉,这样就会花费相当时间。当申诉失败,那么流动人口所在社区将负担驱逐费用,主要是交通费用。所以,驱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时间既长,成本也高。日久天长,出现了居住许可和领取福利分开的情况。即允许人居住,但是不能获取福利救济。(51)如果居住地区不能领取福利,怎么办哪?英国学者金(King)等依据大量当地档案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后,发现由于英国各地的教区建立起一定的互信,所以同意教区之间存在转移支付福利资金。这些资金最主要的是养老金,也有部分是紧急救助。(52)正是这种教区间在福利事务上横向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跨地区的福利救济,推动了人口流动。 托克维尔社会政策的研究方法问题 托克维尔的著作一向以充满洞见和材料详实著称,为何《济贫法报告》中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从而导致其长期湮没无闻呢?这和托克维尔研究方法和他有关国家和社会的理论观点有着关联。研究贫困问题,一般来说是需要扎实的长时间实地研究(field research)。作为一种定性的研究方法,实地研究需要研究者深入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环境中,与研究对象生活一段时间,通过观察、询问,靠自己的感受和领悟,理解所研究对象的行为模式及其背后的心理状态。19世纪的Charles Booth以及Rowntree都曾经组织实地调研,分别写出经典名著《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和Poverty,A Study of Town Life。到了20世纪,实地研究更是得到深入广泛运用。怀特的《街角社会》,利博的《塔利的角落》,或者斯太克的《都是我们的亲戚》,都是建立在长期实地研究基础上。而托克维尔在英国仅仅数周时间,根本无暇展开扎实深入的实地研究。他更多依靠当地朋友帮助来观察和了解。他探访的不是他研究的对象穷人,基本上都是社会经济精英。比如,他拜会新济贫法改革的设计者经济学家西尼尔,希望从中得到很多知识。西尼尔是济贫法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他自认是改革济贫法报告的主写入。他不仅给了托克维尔济贫法报告初稿,而且向他介绍了许多思想,尤其是马尔萨斯的理论,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53)托克维尔在英国考察贫困问题,没有住到伦敦东区等中低收入社区。(54)他寄住在一位大实业家家里,而这位实业家又是坚决支持济贫法改革的。带托克维尔到基层访谈的也是一个要求改革的地区治安官雷德。(55)他领着托克维尔去法庭观察申请救济的贫困者,然后在一旁给初来乍到的托克维尔详细解释。托克维尔极少自己过问研究对象心里想什么,无法长时间观察他们日常生活的行为模式,理解他们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价值观念。他反而一股脑接受雷德的解释,不顾英法两国巨大的社会差异,更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批评所谓英国穷人道德上的腐败,这自然造成了上文提到的许多误解。 其实,如果托克维尔接触的全部是精英,也未尝不可,不同的精英会给出不同的思考。但问题是他交往的精英几乎是清一色支持济贫法改革的。而当时英国是不乏维持旧制,反对改革的社会名流的,例如李嘉图学派的领袖经济学家麦克库罗赫、反对谷物法的社会活动家科贝特等。(56)单向的交流使得托克维尔失去了一个机会来深入探讨济贫制度复杂历史背景,尤其是济贫法中社会权利问题。 迄今,济贫法中的社会权利依然还是一个存在争论的问题。近来大多数英国学者都否认济贫法给予穷人一种社会权利,哈特利迪恩教授更是直认这是一项特权。(57)如此看来,托克维尔把获得救济视为一种权利似乎值得商榷。可是,正如查尔斯沃斯(Charlesworth)所说,承认和否认社会权利的两派与其说是观点不同,不如说是视角不同。(58)否认社会权利的一派更多的是从成文法角度看待,支持社会权利的一派则更多从自然法或者普通法角度看待。成文法角度的社会权利指的是有议会立法赋予公民的福利待遇。比如,德国二战后的宪法中明确宣布德国是一个福利国家,公民享有居住等各项福利。但英国不同。作为一个普通法治国的国家,英国的社会权利在一战之前更多的是借助地方法院的判例来确定的,比如国家应该如何干预特殊家庭,提供何种社会服务和资金等等。我们对这些判例进行追根溯源的分析,就会发现所谓社会权利根本不是神秘之物。它早已蕴含在中世纪的法律中,只不过形式不同罢了。具体说,中世纪时候庄园或者村社都有各种习俗权,包括拾麦穗,在公地上放养牲畜,定期分配土地等等,通过这些权利,一般穷人能够保障生存,也就是说地方共同体赋予每一个成员基本生存权利。(59)圈地运动之后,土地产权发生渐次变更,成了私人所有,维系共同体的道德经济瓦解了,许多习俗权也逐渐消失了,穷人不能在秋收后捡拾麦穗,也不可以公地上放羊自己牲畜,(60)以前的习俗权利一下子变成了侵权。如此,底层佃农乃至小薄计农的生计发生了困难。1597-1599年的接连三年的灾害,导致全国各地城镇大街小巷到处可以听到婴儿求食的哭声,各项争取恢复传统习俗权利的犯罪也急剧增加。(61)因此,英国议会制定济贫法,在承认地方共同体无法使用各项土地使用权作为保障成员生存权的前提下,通过征税方法进行救济,从而完成习俗权利的转型。当时很多支持旧济贫法的学者精英都意识到了这种看法。科贝特就宣称获取救济权利是传统共同体赋予的。可是在法国这样一个浓厚成文法国家成长的托克维尔感触不深,以为救济是国家强制给予的社会权利。 除了实地研究方面问题,托克维尔的文献梳理工作也有欠缺。所谓文献,既包括各种档案,历史上各类法规判例,也包括相关的研究。就档案而言,众所周知,英国作为一个自治社会的模范,各地留下的济贫档案非常齐全。救济申请人的姓名,年龄,出身,大致生活状况,平时在教区表现,申请的事项等都有案可查。可惜的是,托克维尔完全不像他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在法国各地审读档案卷宗。如果他真的埋头调查,那么他可能不会轻易接受许多流俗之见。长期以来,世人一直相信济贫法导致劳动力效率下降,破坏乡村经济。从尼古拉斯、马尔萨斯到西尼尔,乃至韦伯夫妇和卡尔波兰尼,都持类似看法。可是新近的学者如马克布劳格和博耶尔等,发掘、研究了原始档案,通过时间序列分析,推翻了传统的观点。马克布劳格的研究表明旧济贫法的室外救济并没有导致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崩溃。(62)博耶尔的分析指出,没有证据表明旧济贫法阻碍了劳动力流动和减缓经济增长。(63)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较少接触第一手档案,托克维尔并不清楚英国救济体系运作细节。在他眼中,救济制度就是两类,一类是公办的慈善,一类是私人办的。至于公办慈善体系,他认为世界各国都是同一个模式,也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控制下的机构。救济事务给人印象,一边是冷冰冰的官僚,一边是厚颜领取救济金的穷人。这样的描画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托克维尔母国法国的济贫制度。 根据欧洲一古老立法规定:“领主应监督穷苦农民受教育。他应在可能范围内,使其附庸中无土地者获得生存手段。如果他们当中有人陷于贫困,领主有义务来救助。”(64)自从路易十四把各地贵族迁到凡尔赛宫附近,以便加强控制以后,大批的乡村领主便随之到了巴黎。“没有任何地方政权、议会、省或教区联合会取代他的位置。法律不再赋予任何人以照管乡村穷人的义务;中央政府果断地单独负起救济穷人的工作。”但是,如果把英国救济体系也类同于法国,则是张冠李戴了。如果把官僚化看作政治现代化的一个标志,那么如政治史学名家埃尔顿所说,英国政治现代化始于1530年代,只是指中央层面而言。济贫体系虽然在17世纪以后一直在国家化,但其过程极为特殊。笔者将之概括为国家化而非官僚化,是地方自治化而非中央集权化。这种做法与新教思想一脉相通。马丁·路德最先主张城市自治,自行征税济贫;加尔文继而在瑞士日内瓦城加以实践;英国则把济贫制度的自治原则,从城市推广到了乡村。(65)英国在1601年之后数百年间,以教区为单位的地方政府达到15000多个,(66)它们构成了伯特尔所说的“一个平面型的邦联体系”。(67)中央对于这些机构除了做出一些司法仲裁和财政审计方面的介入,基本上不加干预。各地的济贫因地制宜,征收不同的济贫税,采取不同的救济标准和办法。这些地方政府所征收的济贫税等社会项目收入,西德尼韦伯估计要占整个财政收入的20%。(68)这些机构与其说是地方政府,不如说是社区组织。地方济贫官基本上是兼职,不带薪水。大多数济贫官由教区各种小业主或者手工工匠轮流担任,多是教会人员,特别是执事。在很多地区,他们在教会每个礼拜后与穷人交谈,时不时地访问贫寒之家。这些兼职济贫官比较清楚穷人的状况,会视情况决定救济方式,比如发放现金还是实物,以及发放数量。这些判断大体还算适当,能够有效满足穷人的需求。这一方面克服了托克维尔一直担心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另一方面也鼓励各个阶层参与,增加教区认同感,而不是疏离感。(69) 托克维尔在瑟堡演讲时曾经许诺,他还要继续思考福利制度,提出解决办法。他相信私人慈善是最佳的社会救济方式,并热切希望私人慈善能够完全替代公共救济体系,可是他却不知道如何让私人慈善机构获得足够资金承担来所有的救济,而且也未必高效。直到大革命前夜,法国的济贫工作基本上就是靠社会力量,尤其是教会承担的。但是教会救济方面的工作效率低,组织慈善事业的教士们自己生活奢侈,提供救济时不分对象、不问理由,结果终日在教士身边溜达者是众多吃白食的人。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曾经多次抨击教会的救济是养活了一大批寄生虫。整个法国,除了安格尔(Anger)一个地方的教会作为社会救济的模范教会确实有效解决了当地济贫工作,其他地方的教会,根本没有足够财力提供救济。根据美国经济史家林德特的研究发现,在1750-1820年间,法国在社会项目上的开支,从来没有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0.3%,而大举公共慈善的英国则在社会福利上开支超过2.5%。显然,如果没有现代国家的参与,根本无法为社会提供充足的资金。(70) 我们不难发现,托克维尔苦恼和无解源于他的私人和公共慈善二元绝对划分,而这种二元观又来自于他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分的狭隘观念。其实,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有许多中间状态的组织,比如自治社区政府等。这些组织既不同于教会和兄弟会,也不是官僚机构的延伸,但是却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颇值得玩味的是,在《美国的民主》以及《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深刻阐明了中央集权国家与联邦政府和自治地方政府之间的差异,而在分析贫困问题时候,他却没有顾及到英法两国制度上的不同,只是一味强调公办和私人慈善的本质不同,根本没有洞察到公办慈善中中央集权体系和地方自治体系巨大的差异。从历史上看,很多福利制度问题,与其说是来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张力,还不如说是来自地方自治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英国早期济贫制度的有效性,正是由于它本质上是邦联体系,没有官僚机构的僵化和暮气,再加上地方自治政府财源充足,所以英国济贫工作成果斐然,几乎让所有外国人都赞叹不已。美国国父本杰明·弗兰克林说过,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英国那样,大方地让穷人过得那么舒适。(71) 今天人们大谈特谈托克维尔悖论,绝大多数的讨论都是从政体和社会发展的矛盾角度出发的,很少察觉社会政策在其中的意义。其实,托克维尔悖论本质上是转型社会都会面临的一个普遍性的挑战。当传统共同体遭遇私有化市场经济强力扩张时,凝结传统共同体的嵌入性制度,特别是习俗性福利自然就逐渐消失了,这却导致了大批弱势群体开始游离于社会之外。(72)如果国家进一步放松治理,那么社会势必骚动不安以至于发生革命。社会救济体系的意义在于,用国家的力量建立新的嵌入性制度,替代传统体现福利权利的习俗,重构共同体,从而为新的政体打下稳固基础。托克维尔正确地指出中央集权体制在社会福利方面存在的种种障碍,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英国实际上已经摸索出一套自治分权的社区型政府体系来走出转型中的困境。这种政府既能够有足够权威获取资金,又能够因地制宜的给不同群体提供救济和福利。因此,英国幸运地避开了托克维尔悖论,在全世界第一个在没有革命的情况下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从这点来说,英国的经验尤其值得当下中国借鉴。 ①关于托克维尔悖论,参见高毅《“托克维尔悖论”评析》,《世界历史》2013年第5期。 ②关于各地反抗济贫法的改革,近来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参看Nicholas Esdall,The Anti-Poor Law Movement,1834-1844,Manchester U.P.,1971 ,pp.45-116。 ③Tocqueville,Journeys to England and Ireland,Edison,Transaction Publisher,1987,p.36. ④托克维尔认为英国贵族更为开放,不像法国贵族成了一个类似印度种姓一样封闭阶层。参见Journeys to England and Ireland,pp.47-48。 ⑤济贫法报告中文版2013年出版时,是附在《托克维尔的政治经济学》中的。此段文字出自斯威德伯格《托克维尔的政治经济学》,李晋、马丽译,格致出版社,2011年,第493页。 ⑥美国学者Gertrude Himmelfarb在《济贫法报告》的英文版导言中认为托克维尔预见到了福利制度导致了下流阶层的出现。参见Alex De Tocqueville,s Memior on Pauperism,Lanhm:Ivan R.Dee,1997,p.13。 ⑦社会事实取自于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指的是外在于个人却能制约个人行为的现象,而制度事实则来自于约翰塞尔的著作《社会实在的建构》,指的是包含法律习俗规则及其相关的权利义务的现象。 ⑧社会权利一词源自于T.H.马歇尔的演说,他把现代公民身份分为三类,社会公民权利是最后到来的部分。参见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Inequality and Society: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W.W.Norton & Company,2009,pp.148-154。 ⑨⑩(11)(13)(15)(16)(19)(20)(21)(22)(23)(25)(26)(27)(29)(30)(31)斯威德伯格:《托克维尔的政治经济学》,李晋、马丽译,格致出版社,2011年,第471、472、472、480、485、481、498、486、497、497、496、496、483、487、491、491、492、498、491、498页。 (12)Ashley,William,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ngland,pp.1-24. (14)Brian Tierney,Medieval Poor Law,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9,p.15. (17)Rose Friedman,Poverty:Definition and Perspective,Washington D.C,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1965,p.6. (18)伊丽莎白·拉蒙德编:《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1页。 (24)有关新济贫法支持者的观点,博伊尔做了简洁的介绍,参见George Boyer,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oor Law,1750-18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pp.1-5。 (28)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1页。 (32)Lynn Botelho,Old Age and English Poor Law,p.19. (36)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都是新保守主义者,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他们目标也是削减福利开支,可是他们在任内福利减少程度远远小于预期,反倒是主张第三条道路的克林顿等自由派执政期间大幅度削减了福利。参见C.Pierson,Beyond the Welfare State,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Welfare,Polity Press,Cambridge,1991。 (37)Wall Rihard,"Mean Household in England from Printed Sources" 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Peter Lalett & Richard Wall,edit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 (38)Biraaben Jean-Noel,"A Southern French Village",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Peter Lalett & Richard Wall,edit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 (39)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游云庭、缪苗译,第501页。 (40)Snell,Annals of the Labouring Poor,p.20. (41)Boyer,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oor Law,1750-18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268-270. (42)Slack,The English Poor Law 1531-178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19. (43)(45)(51)(56)(65)Sidney Webb and Beatrice Webb,English Loal Government,Volume 7,Poor Law History,Part 1:The Old Poor Law,Hamden,Shoe String Press,1963 ,p.3,p.341,p.337,p.405,p.30. (44)Snell,"Settlement,Poor Law and the Rural Historian:New Approaches and Opportunties",Rural History,3,2,1992,145-172. (46)(48)Michael Nolan,A Treatise of the Laws for the Relief and Settlement of the Poor,vols,l,p.148,p.375. (47)Lynn Hollen Lees,The Solidaritis of Strangers:The English Poor Laws and the People,1700-194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48. (49)(50)Michael Nolan,A Treatise of the Laws for the Relief and Settlement of the Poor,vols 2,p.2,p.15. (52)Steven King,It Is Impossible for Our Vestry to Judge His Case into Perfection from Here:Managing the Distance Dimensions of Poor Relief,1800-1840,Rural History,16,2,pp.161-189. (53)Tocqueville,Seymour Drescher Translated,Alexis de Tocqueville's Memoir on Pauperism,1997,p.4. (54)David Green,Pauper Capital,Surrey,Ashgate,2010,p.54. (55)Alexis de Tocqueville's Memoir on Pauperism,1997,p.4. (57)Dean Hartley,Welfare,Law and Citizenship,Hertfordshire:Prentice-Hall,1996,p.94. (58)Lorie Charlsworth,Welfare's Forgotten Past,Arbington:Routledge,2010,p.4. (59)J.M.Neeson,Commers:Common Right,Enlcoure and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1700-182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p.35. (60)E.P.Thompson,Customs in Common:Studies in Traditional Popular Culture,New York,1993,p.126. (61)Clive Emsley,Crime and Society in England 1750-1900,2nd edn,London:Longman,1996,p.156;也可参见Steve Hindle,On the Parish? The Micro-Politics of Poor Relief in Rural England.1550-1750,Oxford:Clarendon Press,2000,p.82. (62)Mark Blaug,"The Myth of the Old Poor Law and the Making of the New",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46,1963,pp.41-30. (63)George Boyer,"The Old Poor Law,Migration,and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46,1986,pp.41-30. (64)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81页。 (66)David Green,Pauper Capital,London and the Poor Law,1790-1870,Surrey,Ashgate,2010,p.3. (67)Poynter,Society and Pauperism,English Ideas on Poor Relief 1795-1834,London,1969,p.XX. (68)72Sidney Webb and Beatrice Webb,English Loal government Volume 8,Poor Law History,Part 2:The Last Hundred Years,Hamden,Shoe String Press,1963,p.3. (69)一般来说,济贫官员都是轮流担任,没有薪水。后来随着一些教区发展成为城镇,规模大扩大后,便开始逐渐聘请给薪的助理,这些人成为日后社会工作者的先驱。他们了解社区情况,按照当地习惯共识支付福利补助。 (70)Peter Lindert,Growing Public Spending:Social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Camb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7. (71)引自David Green,Pauper Capital,London and the Poor Law,1790-1870,Surrey,Ashgate,2010,p.1.标签:社会政策论文; 英国法律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时间悖论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英国工作论文; 法律救济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经济论文; 法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