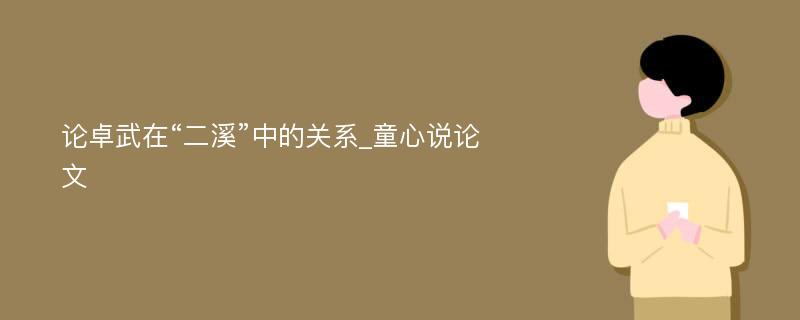
“二溪”卓吾关系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二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4)01-0026-07
一
李贽(字卓吾,号宏甫)当时被称为“二大教主”(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释道·二大教主》:“温陵李卓吾聪明盖代,议论间有过奇,然快谈雄辨,益人意智不少。秣陵焦弱侯、沁水刘晋川皆推尊为圣人。流寓麻城,与余友邱长儒一见莫逆,因共彼中士女谈道,刻有《观音问》等书,忌者遂以帏箔疑之,然此老狷性如铁,不足污也。独与黄陂耿楚侗(定向)深仇,至詈为奸逆,则似稍过。壬寅曾抵郊外极乐寺,寻通州马诚所(经纶)侍御留寓于家,忽蜚语传京师,云卓吾著书丑诋四明相公,四明恨甚,纵迹无所得。礼垣都谏张诚宇(明远),遂特疏劾之,逮下法司,亦未必欲遽置之死,李愤极自裁,马悔恨,亦病卒。次年癸卯妖书事起,连及郭江夏,并郭所厚者数君,御史康骧汉(丕扬),因劾达观师,捕下狱。有一蠢郎曹姓者,笞之三十,师不胜恚,发病殁。师已倦游,无意再游辇下,有高足名流方起废促之行,师遂欲大兴其教。慈圣太后素所钦重,亦有意令来创一大寺处之,不意伏机一发,祸不旋踵,两年间丧二导师,宗风顿坠,或为怪,虽惧出四明相公力,然通人开士只宜匿迹川岩,了彻性命。京都名利之场,岂隐流所可托足耶?郭泰申屠蟠,所以不可及也。”(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91页))之一,影响之大,使得“一境如狂”,褒之者说:“听李百泉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注:《汤显祖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第1229页。),贬之者视其为洪水猛兽,如东林党人、王夫之、方以智乃至四库馆阁之臣都是如此,视其为“坏名教、乱天下之渠魁”。(注:方以智:《东西均注释·名教》,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56页。)《四库全书总目》谓之:“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藏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因其思想“异端”,著作屡遭禁毁。值得注意的是,对卓吾提出批评的多为王学反对者,事实上,卓吾的思想正是受到阳明学派尤其是泰州、龙溪的影响而产生的。
但是,卓吾与阳明学的关系又颇为复杂,黄宗羲《明儒学案》虽然将唐顺之等人也列为南中王门,但卓吾并未见列其中。同时,王门后学论旨有别,可分为诸种不同的派别。(注:龚鹏程先生将王学的分化问题,引述了历代学人的不同分解方法:“以地域分布来说明,是较早被运用的方法,黄宗羲分王门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各派,大体即成为后人掌握王学流衍的依据。明朝当时也已有人是如此看的,如泰州一派,万历间即已被称为淮南派。这显然是以地域为分派依据。但因地域性列分有时并不能显示义理间的差异,故另有其他的方法,如冈田武彦分王门为现成派(王龙溪)、修证派(钱德洪)、归寂派(聂双江)三大派。钱明分王门为“现成”、“工夫”两大系统:现成者含虚无派(龙溪)、日用派(泰州),工夫者含主静派(双江、念庵),主敬派(东廓、彭山、师泉)、主事派(钱德洪)。陈来则分为主有(钱德洪)、主无(王龙溪)、主静(聂双江),主动(欧阳南野)四派(详见《阳明学研究·罗近溪与晚明王学的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根据卓吾的自述,他承润王学甚多,但是卓吾受阳明学派中何人影响较大,尚需分析。卓吾自谓曾师事王襞(字宗顺,号东崖),云:“后泰州有心斋先生,其闻风而兴者欤!心斋之子东崖公,贽之师。东崖之学,实出自庭训,然心斋先生在日,亲遣之事龙溪于越东,与龙溪之友月泉老衲矣,所得更深邃也。东崖幼时,亲见阳明。”(注:《续焚书》卷三《储瓘》,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0页。)但是,除此之外,对王襞绝少论述,对王门后学论述最多的是王畿与罗汝芳。
王畿(字汝中,别号龙溪)与罗汝芳(字惟德,号近溪)被时人并称为“二溪”。如,陶望龄《近溪先生语要序》云:“新建之道传之者为心斋、龙溪,心斋之徒最显盛,而龙溪晚出,尤寿考,益阐其说,学者称为二王先生。心斋数传至近溪,近溪与龙溪一时并主讲席于江左右,学者又称二溪焉。友人有获侍二溪者,常言龙溪笔胜舌,近溪舌胜笔。”(注:《近溪先生语要》卷首,载《耿中丞杨太史批点近溪罗子全集》,《四库存目丛书》,据明万历刻本影印,第130册。)“二溪”是王门后学中重要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说:“浙中派以钱绪山与王龙溪为主,然钱绪山平实,而引起争论者则在王龙溪,故以王龙溪为主。泰州派始自王艮,流传甚久,人物多驳杂,亦多倜傥不羁,三传而有罗近溪为精纯,故以罗近溪为主。”(注:《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对泰州、龙溪之于阳明学的作用,黄宗羲云:“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注:《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03页。)近溪又是泰州学派中尤其卓异者。因此,讨论卓吾与二溪的关系,其实就是讨论其与阳明学派的关系。
卓吾极度尊崇二溪,所撰之《王龙溪先生告文》、《罗近溪先生告文》对二溪去世的悲痛至为深切。哀叹龙溪道:“圣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无瑕,黄金百炼,今其没矣,后将何仰?”在《龙溪王先生集抄序》中说:“龙溪先生集共二十卷,无一卷不是为学之书,卷凡数十篇,无一篇不是论学之言。”“读之忘倦,卷卷若不相袭,览者唯恐易尽”。“先生此书,前无往古,今无将来,后有学者可以无复著书矣。”(注:《卓吾先生批评龙溪王先生浯录钞》,见《四库存目丛书》,据明万历刻本影印,集部第99册。)“世间讲学诸书,明快透髓,自古至今,未有如龙溪先生者。”(注:《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页。)又说:“先生之学俱是矣,学至先生而后大明也。”(注:《李温陵集》卷十《龙溪小刻》。)对龙溪的推敬几乎超过了所有的往圣昔贤。这与其对孔孟言论亦不尽信,视其为“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注:《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9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卓吾对近溪也甚为推敬,在《罗近溪先生告文》中屡屡将其视若仲尼,云:“然吾闻先生之门,如仲尼而又过之。”“先生之寿七十而又四矣,其视仲尼有加矣。”自视为得近溪心印最深者,云:“能言先生者实莫如余。”对近溪之死的悲恸情感也表现得深切自然:“盖余自闻先生讣来,似在梦寐中过日耳。乃知真哀不哀,真哭无涕,非虚言也。”慨叹:“天丧予,予丧天,无父何怙,而子而望孤者耶?”(注:《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2.124页。)推服之意溢于言表。
阳明后学,流派众多,持论不一。严格说来,近溪与龙溪也有不同,黄宗羲根据龙溪《答楚侗》中的一段话,说明二溪学问之不同处在于“近溪入于禅,龙溪则兼乎老,故有调息法。”(注:《明儒学案》卷十二《浙中王门学案二·郎中王龙溪先生畿》,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8页。)其实这还是二溪学问异趣之表象,二溪论学更重要的区别龙溪自己曾有明确的表述:“近溪之学,已得其大,转机亦圆,自谓无所滞矣,然尚未离见在。虽云全体放下,亦从见上承当过来,到毁誉利害真境相逼,尚未免有动。”(注:《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之四《留都会纪》,清道光二年刻本。)从龙溪对近溪的评价中,可见二溪为学的区别在于近溪重在顺适,一念不起,只重见在。近溪也讲本末、体用合一,但是,近溪与泰州学派的大多数学者一样,是在浑融合一的前提下消解了对本、体证悟的意义而突显了末、用所秉赋的本、体性质;龙溪则重在体认源头,重在证悟良知,悟得自然之良,即可神感神应,无往而不适。如其所云:“若彻底只在良知上讨生活,譬之有源之水流而不息,曲直方圆随其所遇,到处平满,乃是本性流行,真实受用。”(注:《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之十《答谭二华》。)龙溪从体用合一的前提下突显了“体”之于“用”的统摄作用,着眼于“体”而非“用”。但从学术的大致路径看,他们都是良知现成派,都是先天派。
卓吾对二溪的崇仰,源于二溪具有相似的理论取向。二溪都主张在先天立根,摒弃后天诚意功夫,他们直接把吾心的自然流行当作本体和性命,因此,他们论学一依自然为本。龙溪认为后天诚意难免私欲杂念,云:“吾人一切世情嗜欲皆从意生,心本至善,动于意,始有不善,若能在先天心体上立根,则意所动自无不善,一切世情嗜欲,自无所容。”(注:《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之一《三山丽泽录》。)他与季彭山、张阳和之间曾因自然与警惕关系进行了一次争论。彭山曾著《龙惕》一书,主张警惕,而龙溪认为学当以自然为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有所恐惧便不得其正矣。“警惕只是因时之义”(注:《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之九《答季彭山龙镜书》。)真性流行,自见天则,龙溪论学的特质在于此,被讥为荡越亦因乎此。罗近溪也以为后天诚意为拖泥带水,即使有所得,也成留恋光景之病。他不重戒慎恐惧的修持功夫,只求坦坦荡荡,自然任我,不必把持,云:“若果坦荡,到得极处,方可言未发之中。既全未发之中,又何患无中节之和耶?君子戒慎恐惧,正怕失了此个受用,无以为位育本源也。”(注:《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70页。)无坦荡即无法位育本源,“自然”是言未发之中的前提。
二溪论学的另一个共同点是都主张良知现成,不学不虑而自得。龙溪云:“良知者本心之明,不由学虑而得,先天之学也。”(注:《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之六《致知议略》。)近溪之学,也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的”(注:《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62页。)。二溪之间的细微区别则在于近溪强调不学不虑,主要是以说明孝弟慈等道德理念是赤子孩提之固有,即他所谓:“孝弟慈原人人不虑而自知,人人不学而自能,亦天下万世不约而自同者也。”(注:《盱坛直诠》,台湾广文书局据明刻本印行。)而龙溪之“不学不虑”重在说明良知之体性特征,他说:“良知在人,不学不虑,爽然由于固有,神感神应,盎然出于天成。”(注:《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之五《书同心册卷》。)比较而言,龙溪之不学不虑更具普适性。显然,“二溪”良知现成、不学不虑的思想对卓吾“童心说”形成具有直接的影响,卓吾是这样描述“童心”遽失的过程的:“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注:《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8页。)概而言之,童心是由于道理闻见,亦即“学”、“虑”而后失,是因多读书识义理障其重心。卓吾依循二溪的路径极为明显。
二
比较而言,卓吾有得于近溪的理论形迹似乎更为显豁。首先、近溪赤子良心之论对“童心说”的启迪。近溪论学以赤子良心为的,陈省《重刻近溪子续集序》云:“先生之书,总之二,言仁也,孝弟也,赤子之心也,而归之性善,归之中庸。”(注:载《近溪子续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之130册。)诚如陈省所言,一部《盱坛直诠》“赤子良心”在在皆是,论述也尤为详备。近溪认为赤子之心不失而大人入圣之事备矣,否则,从思索以探道理,泥景象以成操执,虽自认为用力于学,而其实“不知物焉,而不神迹焉,而弗化于天然自有之知能。日远日背,反不若常人。虽云不知向学,而其赤于之体尚浑沦于日用之间,若泉源,虽不导而自流,果种虽不培而自活也。”近溪认为赤子之心非力学而后得。他论学尤为注重拆穿光景,而不重义理的分解。因此,他的理论能够“一洗理学肤浅套括之气”。显然,这与卓吾之“童心”摒除闻见的思想正相契合,卓吾所谓“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与其极为相似。稍有不同的似乎有其二,一是近溪的赤子之心,重于道德的色彩,卓吾则鲜有此论(详见下文);二是近溪强调赤子之体浑沦于日用,自然流行则无有不善,无有不当,要在于强调见在之合理,卓吾则强调童心之绝假纯真的品性及童心遽失的原因。
其次、贵身与论“私”。近溪贵身与卓吾的承认“私”所论相通。近溪重身之论甚多,云:“盈天地之生而莫非吾身之生,盈天地之化而莫非吾身之化。冒乾坤而独露,恒宇宙而长存,此身所以为极贵而人所以为至大也。”近溪还孜孜求证为保身之合理,他说“吾人此身与天下万世原是一个,其料理自身处,便是料理天下万世处。”近溪还期期以证明“我”与“天地之德”的互融不碍,当有人问其“吾人心与天地相通,只因有我之私,便不能合”这一问题时,他说:“若论天地之德,虽有我亦隔他不得”,“即有我之中,亦莫非天地生机之所贯彻,但谓自家愚蠢而不知之则可,若谓他曾隔断得天地生机则不可。”(注:《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67-768页。)“有我”即为天地生机之流行发用,与天理妙合无痕,本为一体。他还以“我”与“气”的统一,描述了一个直达顺施、生天生地的自然过程:
夫合天地万物而知其为一气也,又合天地万物而知其为一我也,如是而谓浩然而充塞乎其间也,固宜如是而谓大之至而弘足以任重,刚之至而毅足以道远也,亦宜,是故君子由一气以生天生一,生人生物,直达顺施而莫或益之也,本诸其自然而已也,乘天地万物以敷宣一气充长成全而莫或损之也,亦本诸其自然而已也。(注:《盱坛直诠》,台湾广文书局据明刻本印行。)
“我”成为一个弥存六合,而与“气”地位相埒的虚拟化的本体,虽然,近溪的这一理路与人性启蒙的意识不尽相同,近溪强调的是个性的普适性,而现代人性论重在张扬个性,但是,“我”这一与“私”十分相近的范畴地位的提升,无疑是为卓吾重“私”理论的提出作了必要的理论铺垫。至此,我们对卓吾所论就不感到突兀了。卓吾说:“富贵利达,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势然也。”(注:《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页。)“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注:《藏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44页。)即使圣人之辈也无不有私,亦“不能无势利之心,势利之心亦吾人禀赋之自然。”(注:《李氏文集》卷八《道古录》卷上。)人心皆私,人心必私,“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说也。”(注:《藏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44页。)
最后,近溪主要讲认取当下,讲浑沦顺适,以百姓日用为要,这充分体现了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的论学特色。他说:“大人之所以不失赤子良心者,是不失此个赤子良心,后世道术无传于天命之性,漫然莫解,便把吾人日用恒性全不看上眼界,全不著在心胸,或疑其为恶,或猜其为混,或妄第有三品,遂至肆无忌惮而不加尊奉。”(注:《盱坛直诠》,台湾广文书局据明刻本印行。)詹事讲《近溪罗夫子墓碣》谓近溪:“常语人曰鸢飞鱼跃,无非天机,声笑歌舞,无非道妙。(注:《近溪子附集》卷之二,《四库存目丛书》本集部第130册。)将“百姓日用”向道体的提升,是近溪作为泰州学派传人的一个重要表征。对此,卓吾也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同者也。”(注:《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页。)显然,卓吾的思路明显依循了近溪及其泰州学派,但是,卓吾没有沿用“道”这一范畴,而是说“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这是因为“道”这一范畴在理学家那里被涂上了浓重的道德色彩,因此,在卓吾那里,“道理”、“道学”常常被视为是障蔽童心的。卓吾以“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既将传统哲学中的“体”“用”关系合一,从而将“用”提升至“体”的层面,同时,又切断了理学家那里本体论与道德论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实现了他在哲学方面的一个重要超越。在这方面,卓吾的理论贡献其实并不下于“童心说”。而这一思想无疑是直接受到了近溪的启示。学者认为阳明言体用关系有两条途径:一是即体而言用在体;一是即用而言体在用。(注:钱明《对“二王”思想同异问题的再思考》,载《阳明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龙溪沿着第一条路径,泰州学派则沿着第二条路径。显然,卓吾无疑也是沿着第二条路径,承绪了近溪及泰州学派的思想发展而来而与龙溪相异趣的。
尽管在卓吾的“童心说”及其整个思想体系中近溪的烙印如此之明显,但是,近溪毕竟不是卓吾,他们的异趣仍然十分明显。近溪的理论并未脱略阳明学的基本内容。知体与仁体全然为一,这是王阳明及王门诸子的基本前提。卓吾的童心说,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童心是洁净的,童心不包括天赋道德意识。在卓吾看来,童心的丧失,正是道理闻见、道德规范戕害本心所致。卓吾的童心说,但证其“真”,而不究其仁,不究其善。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注:《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8页。)显然,近溪等人所论是“赤子良心”,卓吾所论的是童子“真心”,这是卓吾的童心说与二溪学说的最大不同。近溪论“赤子”,是以其举证道德善性是先验所存,他论学的目的还是在论证“仁”的存在,“仁”的地位,道德的先天性,道德的至上性,亦即“浑然天理”。他说:“夫孩提之爱亲,是孝敬,兄是弟,未有学养。子而嫁是慈,此之孝弟慈原人人不虑而自知,人人不学而自能,亦天下万世不约而自同者也。”因此,近溪之论“赤子”,期以恢复赤子原初本善的自然和熙之状,以使“家家户户共相敬爱,其相慈和,虽百岁老翁皆嬉嬉如赤子一般”,这样就可达到“雍熙太和而为大顺之治。”最终目的在于治道,在于开物成务,明明德于天下。
近溪所论之“此身”与卓吾所论之“私”又有明显的不同,这就是卓吾之“私”是一己之“私”,而近溪的仁体,其实就是一个大我,他说:“夫仁者人也,能仁,夫人斯人而仁矣,是故我与物皆人也,皆人则皆仁也,皆仁则我可以为物,物可以为我,是通天下万世而为一人者也,通天下万世而为一人,是人而仁矣。”近溪的“吾身”是通乎天地,遍及人人的社会的“吾身”,他说:“我身以万物而为体,万物以我身而为用。”近溪之“身”其实是消解了个体性而主要更多地具有普遍性的抽象理念,这就是他所说的“大人”,他说:“道大则身大,身大则通天下万世之命脉以为肝肠,通天下万世之休戚以为发肤,疾痛疴养更无人我,而浑然为一,斯之谓大人而已矣。”(注:《盱坛直诠》,台湾广文书局据明刻本印行。)近溪的“人”、“身”诸范畴是掩映于道德理性之下的,因此,在近溪的话语体系中,仁是大体,仁是超乎自己最终并泯灭自己的更本质意义上的范畴,因此,近溪论身,论仁,就其路数而言,是“以明明德于天下为宗旨”(注:程开祜《镌盱坛直诠序》,载《盱坛直诠》卷首。),是要开物成务,以近溪之解,这才是“大学”,如此才是“大人”。这就是卓吾与近溪为学的重要不同。近溪之论还是秉持了阳明学的传统,秉持了《大学》三纲领的核心。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或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注:《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68页。)这就是卓吾与近溪为学的重要不同,近溪论“身”,意在其“大”,卓吾则论人之“心”为“私”。近溪所谓“大”即阳明的“大人”之学,而阳明的“大人”之学是杜绝私欲的,阳明说:“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注:《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68页。)正因为如此,卓吾对近溪亦有微词,说:“若近溪先生,则原是生死大事在念,后来虽好接引儒生,扯着《论语》、《中庸》,亦谓伴口过日耳。”(注:《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28页。)意谓近溪尚未能彻底解脱,尚有规矩戒律束缚在。这个规矩戒律,就是近溪所谓“仁体”。
三
尽管近溪对卓吾的影响十分显著,但是就卓吾对龙溪、泰州的亲和程度而言,对龙溪的敬奉更胜一筹。卓吾特别推重龙溪,无疑是由龙溪学问的特点决定的。龙溪之学直截源头,重在讲良知平满,讲先天本善的性体自然流行,而鲜有论述消解后天动意的方法,这样,就免去了对理学人性论的前提——天理人欲关系的正面讨论,因此,在龙溪的著作里,多讲先天正心,对道德的正面阐沦并不多见,而对传统道德理念的突破,对自然人欲的肯定正是卓吾所要关注的理论重点。因此,在龙溪的理论前提下,给卓吾提供了较充分的理论空间,这样卓吾就甚少与作为理学家的龙溪之间正面的理论撞击,而近溪之学多有道德论说,近溪理论的道德色彩较之于龙溪要浓郁得多。
在论述良知不学不虑等方面龙溪与近溪也有细微不同,龙溪详细论证了不学不虑的根据,他论析良知无知而无不知,这个“学问大头脑”(注:《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之十《答吴悟斋》。)时说,“良知如明镜之照物,妍媸黑白,自然能分别,未尝有纤毫影子留于镜体之中,识则未免在影子上起分别之心,有所疑滞拣择,失却明镜自然之照。”(注:《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之十《答吴悟斋》。)龙溪这一承祧了阳明学的思想对于卓吾的童心说的理论支撑更为直接,因为这一妙喻很好地解释了不学不虑的理论问题。而近溪的赤子良心,虽然与卓吾童心说更为形似,但是,由于近溪论解赤子良心之时,还是期期恢复赤子原来的心,保任原来的心,说明了赤子之心先验本善的特征,还是留于形似的层面,对于为何不学不虑,缺乏必要的理论说明,因此,到头来,还是不能将此理论归结到底,所以,当有人问他,良知是不虑而知,只可在孩提时说,待年长时许多事物如何容得时,他就说:“不虑而知,是学问宗旨,此个宗旨要看得活,若说是人全不思虑也,岂是道理,盖人生一世,彻首彻尾只是此个知,则其拟议思量何啻有千万种也,但此个知原属天命之性,天则莫之为而为,命则莫之致而至,所以谓之不学不虑,而良也。”(注:《近溪罗先生一贯编·孟子》,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9册。)
卓吾特别推敬龙溪,还与龙溪较之于近溪在文学方面的论说更多有关。“童心说”本质上是为论文而发的,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而立论的。对六经、《语》、《孟》的质疑,实质上是以极端的方式,从反面求证“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的价值。而龙溪堪称是阳明学派中文论最为丰富的学者之一,他主张创作当以自然为本,反对雕琢粉饰;得古人意脉,而反对蹈袭古文辞,云:“夫子长法《国语》、《左传》,孟坚法《史记》固也,然其文皆自为机轴,而不相沿袭,殆师其意者非耶?”(注:《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之十三《精选史记汉书序》。)主张“尽去陈言,不落些子格数。”创作应如“风行水上,不期文而文。”推赞“行乎所当行,止乎不得不止”的“天然节奏。”(注:《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之八《天心题壁》。)其门人萧良在龙溪的文集序中说:“世之为文者,雕心镂肝,掇藻华,锻炼于体裁,于词句,以为文在是,譬之剪采刻楮,非不煜煜可观而生意索然,终瘁已尔。盖文与道歧而文始裂矣。龙溪先生非有意于为文者也,其与人论议,或有所著述,援笔直书,罔事思索,繁而不加裁,复而不为厌,非世文章家轨则。要其发挥性真,阐明心要,剔精抉髓,透入玄微,其一段精光有必不可得而泯灭者。”(注:《王龙溪先生全集》卷首。)萧良笔下的龙溪,不仅仅是中晚明革新派文人们的理性依傍而存在,而直接是一位直心而动,真性流行的文道兼擅的学者,其天机活泼的难掩锋芒,对摹拟之风的批难是如此之峻厉。同时,龙溪这种援笔立就的风格,是因掇藻华的现象而发的,显然,这并不是指铺陈道德理性的风气,而是因文坛弊端而发。因此,龙溪与文士们的交往尤为多见,他的学术思想许多是通过与唐宋派代表人物唐顺之、王慎中以及徐渭等人的答问之中表述出来的。在这方面,龙溪与阳明也有明显的不同,阳明论文重道德教化,龙溪论文重赋写性情,与卓吾等人更为神契。这与近溪有明显的区别。现存近溪文集中的文论十分罕见。据杜应奎《近溪罗先生集跋》:“(近溪诗歌)原稿多散轶,海内外学者愿刻以传而卒不可得。”《近溪集》中的文论非常鲜见。
在性情方面,龙溪高迈俊爽,颇具狂者之气,他说:“夫狂者志存尚友,广节而疏目,旨高而韵远,不屑弥缝格套以求容于世。其不掩处虽是狂者之过,亦其心事光明特达,略无回护盖藏之态,可几于道。”(注:《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之五《与阳和张子问答》。)龙溪所秉赋的几分狂侠之气,是他论学不谨守师说,不谨守孔孟先贤,务求自得的心理基础。他对于经典的怀疑精神显得特别明显,他说:”学须自证自悟,不从人脚跟传,若执着师门权法以为定本,未免滞于言诠,非善学也。”(注:《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之一《天泉证道记》。)又说:“就论立言,亦须一一从圆明窍中流出,盖天盖地,始是大丈夫所为。傍人门户,比量揣拟,皆不技也。”(注:《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之十六《曾舜徵别言》。)为学“须打破自己无尽宝藏,方能独往独来,左右逢源,不傍人门户,不落知解。”(注:《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之一《三山丽泽录》。)所谓“自己无尽宝藏”,当主要指被普遍尊奉的儒学经典,从这个意义上说,龙溪之于传统儒学,就如同妈祖之于佛教,事实上,他对儒学经典的立教之旨提出质疑。云:“一部《论语》,为未悟者说……若为明眼人说,即成剩语,非立教之旨矣。”(注:《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之七《南游会语》。)
卓吾承龙溪之势而又进一步发扬光大,他“自幼倔强难化”,游宦二十五年几乎与一切权要发生了抵触,(注:《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7页。)他正是以这种狂傲之气,张皇己说,形成了“一境如狂”的独特景观。他大胆地提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是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注:《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页。)对权威经典的贬落,为张扬个性,突出个体原则提供了可能,虽然这也是心学师心自用、自尊自信原则发展的自然结果,但是,至卓吾这里,较为彻底地将个体原则与传统的道德原则剥离开来,使其成就了最具时代色彩的理论构架。其中,本于王学尤其是龙溪的豪杰精神,狂者气象,是卓吾形成“异端”之论的重要的心理基础。在这一方面,近溪对卓吾的影响远不及龙溪,近溪泛爱容众,无论是牧童樵竖,钓老渔翁,市井少年,织妇耕夫,还是布衣韦带、黄冠白羽,缁衣大士,罗汝芳都能抵掌其间,坐而谈笑。卓吾崇奉近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同流合污”,“有柳士师之宽和”,“有大雄氏之慈悲”,泛爱众生的性格。但在近溪身上,鲜有龙溪那样的狂傲脱俗的气象,目空一切的豪杰精神。
总之,卓吾的“童心说”及其异端之论,并非突兀而生的,它是受阳明学派,尤其是二溪的直接启示而形成的。卓吾对二溪的推敬叹服,缘于其对二溪理论的汲取,对二溪思维路向的承绪和发展。概而言之,得于近溪的形迹较明显,而得于龙溪的神韵更为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