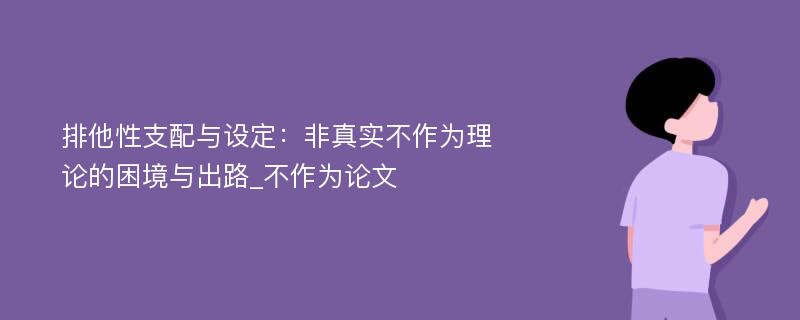
排他支配设定:不真正不作为犯论的困境与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作为论文,出路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意识 在我国刑法学中,不真正不作为犯①的研究似乎走进了一个死胡同。一般来说,作为(实行行为)的结果犯的场合,其探讨的中心课题是因果关系的确定,只要能够查明作为(实行行为)和结果之间存在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基本上就能肯定成立犯罪。但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场合则恰好相反,其中心课题是作为义务,即对作为义务的来源、限定基准的确定。而且,随着所谓作为义务判断的实质化,这种倾向更为明显,到了只要能确认行为人违反了所谓“实质的作为义务”,就能认定不真正不作为犯成立的程度。② 但是,这种以作为义务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在我国刑法规定的背景之下,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和我国《刑法》第3条所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协调问题。和德国有“依法有义务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而不防止其发生,且其不作为与因作为而实现犯罪构成要件相当的,依本法处罚”的明文规定(《德国刑法》第13条第1款)不同,我国刑法中没有以作为义务为根据认定结果犯的条款,因此,在不作为的因果关系发展过程尚不清楚的状态下,仅以行为人未履行特定义务为由而追究其结果犯的罪责,根据何在,成为问题;二是和法益保护原则之间的协调问题。近代刑法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确立了刑法第一位的任务就是保护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即法益的观念。③从此观念出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只要不是侵害或者威胁法益的行为,就不能将之作为犯罪考虑(没有法益侵害,就没有犯罪),因此,行为是不是侵害法益,应当成为判断行为是否成立犯罪的第一要素,即便在所谓不作为的场合,也必须如此。但作为义务中心论则偏离了这一命题,其将不作为是否成立犯罪的判断偷换为了抽象的、要结合法官的价值判断才能加以认定的作为义务的判断。这种认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做法,从保护法益原则的角度来看,值得怀疑。 受刑法理论上重作为义务违反而轻不作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思潮的影响,我国的司法实务部门在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认定上,就显得比较随意。如就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而言,近年来的一个普遍的倾向就是,只要不作为人和被害人之间存在某种关系,或者不作为人对被害结果的发生存在某种过错,就能轻易地认定不作为人具有作为(救助)义务,对于死亡结果必须承担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如就夫妻之间的情形而言,在著名的“宋某某见死不救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人宋某某与其妻李某关系不和,在争吵厮打中用语言刺激李某,致使其产生自缢轻生的决心。被告人宋某某是负有特定救助义务的人,却对李某的自缢采取放任的态度,致使李在家中这种特定环境下自缢身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不作为)。④就恋人之间的情形而言,在著名的“李某某故意杀人案”中,一审法院认定李某某构成故意杀人罪。李某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原审被告人李某某与项某某相恋并致其怀孕,在未采取措施加以妥善处理的情况下即提出与项分手,并在争吵中扔打火机刺激项,致使项坚定服毒自杀的决心。当李某某发现项已服农药后,非但未施救,反而持放任态度锁上房门离开,且李某某对项及其腹中胎儿负有特定义务,而不予救助,致使项某某在李某某单身宿舍这种特定环境下得不到及时抢救而服毒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⑤就债务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情形而言,在著名的“赵某见死不救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人赵某在受害人李某某向其讨债过程中,双方发生口角,李某某无奈用头撞墙壁寻死要挟。此时,被告人赵某应预知李某某头碰墙的自伤行为会发生死亡的严重后果,理应上前劝阻,却视而不见,擅自离去,以不作为的方式放任李某某死亡结果的发生,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间接),判处被告人赵某有期徒刑四年,并附带民事赔偿20810.53元。⑥但是,在另外一些案件中,即便不作为人和被害人之间存在某种关系,或者对被害结果有某种过错,却并没有被追究不作为犯的刑事责任。如在著名的“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中,法院只是追究了联防队员杨某某及其同伙强奸罪的刑事责任,并没有追究被害人丈夫杨某不救助的责任。当地警方称,这个案件中,受害者丈夫杨武也有一定责任,他实在是太懦弱和软弱了,面对妻子被殴打、强奸,他不敢上前制止,也没有及时拨打电话报警。如果杨武能够挺身而出,也许悲剧就能够避免发生。⑦同样,在著名的“肖志军拒签字案”中,尽管有学者认为,丈夫肖志军具有法定救助义务而拒绝签字,导致妻子死亡的行为属于不作为的故意杀人,⑧但作为“丈夫”的肖志军最终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⑨ 对于刑事司法而言,将处罚和不处罚界限的明确化、可视化,应当是最为重要的任务。但从上述案例来看,至少可以说,在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处罚上,我们尚未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如此轻易地将不救助行为就认定为杀人行为,从罪刑法定原则的角度来看,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为,对于干涉人们的行动自由而言,和处罚作为犯相比,处罚不作为犯的场合效果更为强烈。作为犯的场合,法所不禁止的就是允许的,人们的自由活动范围相当大;相反地,不作为犯的场合,法所命令以外的都是禁止的,人们的自由活动范围相当小。⑩正因如此,近代刑法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以处罚作为犯为原则,而以处罚不作为犯为例外。(11)轻易地将不救助行为作为作为犯加以处罚,恰好是对上述原则的背反。 本文认为,不真正不作为犯,作为最终依照作为犯条款处罚的犯罪形式,其本质上是作为犯,因此,在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认定上,应当淡化其不作为犯的形式特征,而回归其作为犯的实质特征,重视其因果关系,从行为人主动设定了对法益的排他性支配的事实角度而不是从具有作为义务的规范角度来探讨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条件和处罚范围。 以下结合我国的相关学说和司法实践,就上述观点展开分析。 二、不作为犯因果关系的诸见解及其缺陷 在以结果犯的条款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的时候,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该不作为是如何引起结果的,即不作为的因果关系如何认定?对此,刑法理论上有过多种尝试,现在似乎已经不成问题。但是,从本文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一)传统见解 在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认定上,不能不考虑因果关系。和作为的场合一样,不真正不作为要符合结果犯的犯罪构成,该不作为和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因果关系。只是在不作为的场合,行为人什么都没有做,形式上并没有给结果的引起注入能量,不存在事实上的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因此,不真正不作为的因果关系该如何理解,便成为首当其冲的难题。 从学说史的角度来看,不作为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曾经是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研究中心,有过多种学说。最早出现的“他行为说”根据行为人所进行的其他行为中包含有引起结果的原因力来说明不作为的原因力;之后出现的“先行行为说”主张先于不作为的作为即先行行为对于结果的发生具有原因力;再之后,“干涉说”认为不作为之所以存在原因力,是因为不作为人的心理状态上存在着使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后来,出现了认为只有在行为人具有作为义务的场合,其不作为和结果之间才具有原因力的“义务违反说”,但这种见解容易将不作为的违法性和因果关系问题混为一谈,导致不作为因果关系认定上的主观性。因此,现在德日刑法学中,关于不作为因果关系的一般看法是,必须将其和行为人的作为义务分开来论。如果实施特定作为,十有八九能防止结果或者具有接近该种程度的回避结果可能性的话,才可以说该不作为对结果具有原因力。(12) 在我国,情况则恰好相反,传统学说在探讨不作为的因果关系时,一直将其和作为义务联系在一起。如“条件说”一方面认为,不作为与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无中不能生有”,无作为,自无结果,不作为不是结果的原因,只是促成结果产生的条件;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不作为因其违反作为义务,违反法律规范,而且对社会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因此,应负刑事责任。(13)同样,“作为义务违反说”也认为,不作为的原因与不作为义务是分不开的。如果一个人负有作为义务,且经过履行特定的作为义务,确能保证危害结果不致发生而不作为的话,该不作为就是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14)“转辙说”也认为,负有作为义务的人不履行自己的义务,进行必要的“转辙”即阻止结果发生,则这种不作为是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15)这种将因果关系与作为义务捆绑的作法,迄今也没有什么大的改观,主流学说依然认为,在认定不作为的因果关系时,必须十分强调行为人所具有的应当作为的法定义务。(16) 之所以要这样理解,是因为上述见解的论者担心,在不作为因果关系的判断上,如果不考虑作为义务,则不具有作为义务的人的不作为也会具备作为犯的构成要件,使得构成要件丧失其推定违法的机能,扩大不作为犯的处罚范围。(17) 但是,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一方面,作为上述观点前提的犯罪论体系不同。构成要件的推定违法机能,来自三阶层的犯罪构成体系,但在我国,主张不作为因果关系的判断必须以作为义务为前提的见解,基本上(18)都是采取了与“三阶层”的犯罪构成体系不同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不存在形式上符合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大体就能推定该行为具有违法性的前提,因此,以这种理由来说事,根据不足。另一方面,这种理解也是不妥当的。在孩子落水,包括孩子父亲在内的多人围观而没有救助,结果导致孩子死亡的例子中,即便说包括孩子父亲在内的围观者的不救助行为(不作为)都和孩子之死(结果)之间具有因果(条件)关系,也并不意味着围观者的不作为马上就具备作为犯的构成要件。不救人和亲自动手杀人毕竟是两回事,不能同等看待。就不真正不作为犯而言,仅仅存在不作为与构成要件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尚不能肯定构成要件符合性,还要求该不作为和作为具有同等价值,即该不作为与作为所生侵害能够同等看待,否则就不能按照作为犯的条款加以处罚。因此,认为在不真正不作为犯因果关系的判断上,不考虑作为义务,就会扩大处罚范围的见解是没有道理的。(19) 相反地,在不真正不作为犯因果关系的判断上,掺入作为义务要素,反而会导致因果关系的主观化,违反因果关系的一般理解。按照我国刑法学的通说,因果关系是现象之间引起和被引起的一种客观联系,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在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上,只能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不能主观武断或者单凭以往的经验去判断,更不能以社会一般人或者其他人对危害结果发生有无预见或者能否预见为标准。(20)换言之,因果关系具有客观性,其判断必须依据客观事实进行。但若说在不作为因果关系的判断上要考虑作为义务的话,便会使得因果关系的客观特征丧失殆尽。如在孩子落水,包括孩子父亲在内的众人围观,但无人伸出援手,导致孩子溺水死亡的场合,按照上述理解的话,只有孩子父亲的不救助行为才和孩子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而其他围观者则没有。但在当时,孩子父亲和其他围观者的表现,在现象上没有任何差别,如何能分别出孩子父亲和其他人在因果关系上的差别呢?况且,作为义务并不是在客观上能够显现于外的可视性因素,有作为义务的人和没有作为义务的人,在侵害或者威胁法益的客观表现上,并无任何差别,只是在谁要承担责任即归责上有所不同而已。 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考虑作为义务的一个可能恶果是,导致不作为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模糊不清。因为,作为义务即当为或者不当为某种行为,本身就是一个难以被客观化的规范概念,在不同国家理解不同,即便是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或者不同历史时期,看法也不一致。正如日本学者前田雅英教授所说,在共同体意识强烈的地方,不作为犯的处罚范围就广泛,而在重视个人自由的社会,个人被赋予的作为义务范围就很窄。(21)这种见解,在我国有关“先行行为”是否作为义务来源,其内涵如何,外延多大的探讨中,能够得到充分的印证。(22)其也是在不作为犯因果关系的判断上考虑作为义务,必然会导致因果关系判断上的不确定性的体现。 (二)“期待说”及其评述 因为上述问题的存在,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从不作为自身的角度来探讨不作为的因果关系。如认为“不作为的原因力,在于它应该阻止、能够阻止而未阻止事物向危险方向发展,从而引起危害结果发生”, (23)“不作为的原因力在于它破坏了阻止危害结果出现的内、外因平衡关系,使得本来不会发生的有害于社会的某种因果经过得以顺利完成”的见解,(24)就是其体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引进德、日流行的以“期待说”为基础的“假定因果关系”的判断方式,即“如果行为人实施该被期待的行为,极有可能不发生该结果的场合,可以说该不作为和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25) 这种通过“添加期待行为”的因果关系判断方式,和传统因果关系判断方式之间存在较大差别。具体来说,按照传统理解,作为犯的因果关系是事实上的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属于存在论的范畴,而上述期待说之下的因果关系则是观念上、思考上的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准确地说是“疑似因果关系”。因此,在以作为犯的条款对具备这种“疑似因果关系”的不作为犯进行处罚时,难免会产生以下疑虑: 一是和作为犯之间难以平衡。众所周知,在作为犯因果关系的判断上,正如所谓死刑犯的教学案例中所言,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得添加现实并不存在的假定事实。(26)但是,不作为的场合却恰好相反,添加“被期待的”假定事实属于理所当然。作为场合之所以禁止添加假定事实,目的在于防止其因果关系成为思考、理论上的结合关系,但不作为的场合则反其道而行之。这表明,不作为的因果关系本来就是思考、理论上的存在。“期待说”的最大意义恐怕就在于此。但是,将因果关系完全不同的两种行为适用同一种犯罪构成,难道没有问题吗?让人生疑。 二是有自欺欺人之嫌。本来,按照条件关系公式,行为只有在符合“没有前行为,就没有后结果”公式的场合,才能说明其和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判断不作为是不是引起结果的原因,只有在上述因果关系的判断实施完毕之后,才能得出结论。但在“期待说”中,由于所添加的内容即“被期待的行为”就是“能够防止结果的作为”,使得这个工作在套用条件公式之前的确定添加内容阶段即已完成。既然如此,何必又要再进行一次“没有前被期待的作为,就没有后结果”的条件分析呢?这不是在自欺欺人吗? 三是导致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未遂犯无法认定。刑法学中考虑因果关系,目的是为区分结果犯的既、未遂形态提供依据。行为和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的,成立既遂犯,否则就是未遂犯。按照“期待说”,并非任何不为“被期待”作为的行为都能构成不作为,只有不为“极有可能”(“十之八九”)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作为才能构成不作为。如此说来,“期待说”不仅与因果关系的判断有关,同时也与不作为自身存在与否的判断有关。但这种做法必然会引起不作为犯和作为犯在未遂形态判断上的失衡。具体来说,作为的场合,即便是发生结果可能性较低的行为(如用质量低劣的自制手枪向他人射击、用没有达到致死剂量的毒物杀人),也是实行行为,能够成立未遂犯;而在不作为的场合,如果所未为的行为不是“极有可能”(“十之八九”)引起危害结果行为的话,则说不上是实行行为,根本不能成立犯罪,更不用说是未遂犯了。 由此看来,尽管以不作为的手段实现作为犯的犯罪构成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并且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概念也已经被广泛认可,但在以作为犯特别是作为形式的结果犯的基本观念对其内部构造进行剖析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破绽百出、不堪一击。有关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的探讨,应当另辟蹊径。 三、作为义务论的实体及其不足 (一)概说 在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认定上,仅仅探讨不作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还不够,毕竟,即便说不作为和结果之间存在观念上的因果关系,也不能像作为的场合一样,马上就能以作为犯的条款对该不作为进行处罚。因为,“不救助溺水儿童的行为和将儿童推入水中的行为不能同等看待”,(27)否则,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范围就会无限扩大。就上述不救助落水者的情形而言,一个公认的观念是,并非任何人的不救助行为都会成为处罚对象,只有和落水者之间存在某种特殊关系,使行为人处于保证结果不发生的地位,即具有救助落水者的义务时,其不救助行为才能成为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28) (二)形式义务论 那么,何种情况下,可以说不救助者和落水者之间存在某种特殊关系呢?这就是作为义务来源问题。对此,传统学说认为其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二是职务或者业务上的要求,三是合同行为、自愿承担行为等法律行为所引起的义务,四是先行行为的要求。(29)并且,上述义务必须具有法律上的依据,而不能仅是伦理上的要求。(30)这种明文列举作为义务来源的方式,以形式框架存在,其范围和内容一目了然,故被称为“形式说”。其目的在于严格区分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阻止以实质性判断为借口而扩大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处罚范围。但这种形式地列举作为义务来源的方式本身,从一开始就存在致命的缺陷: 首先,难以说明刑罚处罚的理由。即上述形式义务来源几乎均为刑法之外的法律要求,即便违反了该要求,也只能依照相应法律当中所规定的罚则进行处罚,何以能够对其进行刑法处罚,理由不明。 其次,难以实现其初衷。“形式说”,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在形式上明确作为义务来源的方式划定不作为犯的成立范围,但将来自于习惯法要求的先行行为等作为义务来源,使得其在一开始就陷入了自我矛盾的尴尬境地。在其后的发展当中,“形式说”又进一步衍生出了如所有人、管理人、监护人的地位;交易上的诚实信用义务;紧密生活共同体、特定场合下的道德义务等作为义务来源。(31)将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义务来源或许还会继续增加下去。但这种无限列举的做法显然超出了“形式说”的初衷,使得其所引以为傲的长处大打折扣。 最后,无法限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处罚范围。如按照我国《婚姻法》第15条的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但是,母亲不尽抚养子女义务,将婴儿抛弃的行为,并不马上构成故意杀人罪;反过来,在子女对父母不尽赡养义务,即便因此而造成父母死亡的,也并不马上构成故意杀人罪,而是构成遗弃罪(中国《刑法》第261条)。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形式义务论又进行了一些修正,认为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除了作为义务之外,还要求行为人违反义务行为所生侵害在事实上与作为手段所生侵害具有同等价值,这就是所谓“等价性”的要求。(32)增加这一要件,毫无疑问地会限缩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处罚范围,但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因为,“等价性”只是一种抽象的价值要求,其和作为义务是什么关系,如何判断,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不仅不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有雪上加霜之效,使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判断标准更加难以确定。 (三)实质义务论 由于以上原因,从上世纪末开始,我国学者就开始借鉴国外,主要是日本的相关学说,基于不作为和作为之间所存在的结构性差异,以不作为和作为必须等价为前提,探求行为人的不作为具备什么样的事实特征,就可以看做为作为的立场出发,将作为义务的内容具体化。这种将作为义务从规范具体化为客观事实的研究方法,被称为“实质义务论”。(33)实质义务论的内容多样,就我国当今的情形而言,其中的代表性见解有以下几种:(34) 一是“支配行为说”。认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应当从与其对应的作为犯的不作为义务具有等价性的原则出发,用更加实质的标准来确定。这个实质标准是,行为人为防止结果的发生而自愿实施了具有支配力的行为。其中,所谓自愿行为,必须出于防止结果发生的目的;所谓具有支配力,就是控制了因果发生的进程。(35) 和传统学说相比,“支配行为说”的最显著特点是,强调不作为人和保护法益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只有在不作为人意图以客观的事实因素,即行为人自愿实施了防止结果发生的支配行为,之后又放弃不干为中心内容来认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条件,而不是仅倚重法令、合同、先行行为等规范要素。按照“支配行为说”,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行为人是否具有法定或者合同约定义务,是否具有先行行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是否具有“为防止结果的发生而自愿实施了具有支配力的行为”,即强调为防止结果发生而实施事实支配行为。因此,自始至终就没有开始救人行为的肇事者因逃逸而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场合,只要肇事者不是在开始救人之后又中途放弃,即便说其具有先行行为的作为义务,也不会因此而成立不作为杀人。同样,在民法上具有抚养孩子义务的亲生母亲,在孩子出生之后就没有实施过喂奶等照顾行为的场合,只要没有开始喂奶等抚养孩子的行为,也不成立不作为杀人。(36)换言之,行为人即便具有形式上的作为义务,但只要没有开始防止结果发生的支配行为,就不可能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 在依据和被害法益之间密切关系,要求行为人只有在出于救助意思建立了事实上的法益维持关系时,才能说具有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一点上,可以看出支配行为说与日本学者堀内捷三教授所提倡的“事实承担说”(37)之间的相似之处。也正因如此,批判意见认为,“支配行为说”可能缩小不作为犯的成立范围。因为,上述观点均强调支配或者承担行为的目的性即“具有防止结果发生的目的”,但“我们看不出交通事故中的肇事者基于救助的意思而将被害人搬进车中之后又产生杀意将其弃置在人迹罕至的场合,与肇事者非基于救助意思而是直接基于逃避追究之意图将被害人搬进车内另移至他处,在结论上应当有所不同”。(38) 确实,在作为义务的判断上,加入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可能会引起行为性质判断上的不确定性,产生同罪异罚的效果。但是,撇开这一点不论,从该学说的整体宗旨来看,其在我国学界开创了一种与形式义务论不同的作为义务探讨路径。虽然传统的形式义务论也主张,自愿承担行为是作为义务来源,但其中所体现的是民法上的“无因管理”制度中所蕴含的“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的社会伦理要求,“支配行为说”虽然也体现了这一伦理要求,但这种要求是通过将无因管理者在管理他人事务之后的事实态度、法益侵害结果联系在一起来实现的,可以说,其是重视客观事实因素的作为义务论,属于实质义务论的一种表现形式。 “支配行为说”的最基本特征是,强调行为人对是否发生侵害结果,具有事实上的支配。但这种事实支配是否仅限于行为人有为防止发生结果而中途介入面向结果的因果进程的场合,则值得怀疑。事实上,行为人完全可以通过先实施导致有结果危险的先行行为,之后不让他人介入的方式来支配面向结果的因果发展。同时,这种理解,可能会将很多传统的不真正不作为犯类型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如我国历来的学说均将不小心点燃物品,本来可以扑灭,但行为人基于某种原因而逃离现场,结果酿成熊熊大火,造成人员死伤或者财产损失的场合,以不作为的放火罪处理,(39)但按照上述支配行为说,这种场合难以构成放火罪。同样,在不照看处于假死状态的初生婴儿的场合,因为父母没有自愿实施具有支配力的行为,恐怕也难以认定为不作为的杀人。这样,显然会缩小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处罚范围。 二是“排他支配说”。这是我国目前的通说。其认为,为保证不作为和作为的等价性,不作为人不仅要掌握导致结果发生的因果流向,而且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具体、排他地支配引起法益侵害结果的因果关系的发展方向。按照这种观点,遗弃婴儿和老人(神志不清、行动困难的老人)是构成遗弃罪还是故意杀人罪,要具体分析,如将上述被害人遗弃在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如车站、别人家门口等),便于及时得到救助的,仍然应当以遗弃罪论处;如果将上述被害人遗弃在野兽出没的深山偏野或者很少有人发现的冰天雪地,便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40) 和“支配行为说”一样,“排他支配说”也是意图从事实因素(遗弃行为、对象没有自我保护或者自我生存能力、危险境地等)出发,对不履行义务行为是否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标准加以明确。不仅如此,“排他支配说”甚至比“支配行为说”提出的条件更为苛刻,即对导致结果发生的因果流向的把握必须达到排他的程度。如就行为人遗弃婴儿和老人的行为而言,按照“支配行为说”,或许只要有遗弃行为就足够,但按照“排他支配说”,行为人只有遗弃行为还不够,还必须是遗弃在“野兽出没的深山偏野或者很少有人发现的冰天雪地”,否则就只能构成作为真正不作为犯的遗弃,而不能构成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杀人。换言之,和“支配行为说”相比,“排他支配说”更加强调行为人对侵害法益的因果流向的实际把握。尽管如此,对因果关系的支配是作为犯的特征,虽说是不作为犯中的排他支配,但只要没有实施积极的排除他人的行为,所谓排他支配,实际上还是属于对面向结果的因果关系的支配,关注的也还是行为人和保护法益之间的紧密关系,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排他支配说”和“支配行为说”之间,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正因如此,上述对“支配行为说”的质疑对“排他支配说”也同样适用。而且,将神志不清、行动困难的老人遗弃在野兽出没的深山僻野或者少有人烟的冰天雪地的行为,到底是作为还是不作为,恐怕还难说。因为,神志不清、行动困难的老人,没有自我生存和保护能力,其生存只能依靠其他人的帮助。通常情况下,将这种人置于野兽出没的深山僻野或者少有人烟的冰天雪地,正如将人推入火海或者深渊一样,实际上是将其置于死地,属于积极主动引起死亡结果的作为,怎么能说其是利用或者放任死亡结果的不作为呢?令人不解。 三是“先行行为说”。这是我国近年来流行的一种有力观点。其认为,作为是行为人主动引起法益侵害,而不作为是利用或者放任已经存在的能够侵害法益的客观事实,能够弥补此二者之间的结构性差异的,是行为人在不作为之前的先行行为,因此,先行行为是认定实质义务论的关键。(41)其中,从“先行行为说”提出的时间先后,可以分为旧、新两种不同的见解:“旧先行行为说”实际上是日本的“实质原因设定理论”(42)在我国的翻版,认为只有基于行为人自己故意或者过失的先前行为导致法益面临危险的不作为,才能作为等价值性判断的前提资料。(43)“新先行行为说”的主要观念来自德国,认为“使刑法保护的具体法益面临紧迫危险,是先行行为成为作为义务来源的实质根据”,(44)“在先行行为具有引起损害结果的潜在风险,这种潜在风险继续发展,在损害结果中实现——即先行行为所包括的潜在风险发展过程中没有其他异常因素介入(如异常发展、被害人或者他人的行为介入等)导致原来先行行为所创设的风险被替代,形成新的风险——的场合,所引起的损害结果归责于先行行为人。”(45)新、旧学说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行为人对于其先行行为所引起的潜在危险,是不是要有排他性支配。按照“新先行行为说”,先行行为不仅要对刑法所保护的具体法益造成危险,而且还必须对该危险向实害结果的发生具有支配,(46)而“旧先行行为说”则没有这一要求。 将先行行为作为不作为义务来源,在刑法学中由来已久,但在先行行为如何成为不作为义务来源的说理上,作为上述实质义务论之一的“先行行为说”和传统形式说的理解截然不同。按照传统理解,先行行为的场合之所以能够成为不作为犯,关键是因为行为人先前的先行行为使得法益处于危险状态,按照常理,行为人有义务消除该危险状态,但其却没有消除,引起了侵害法益结果,因而要将该不履行义务的不作为作为犯罪处罚。在这里,成立犯罪的关键,是行为人没有履行消除危险的义务。相反地,按照上述“先行行为说”,先行行为的场合之所以成为不作为犯,不完全是因为行为人没有履行消除危险的义务,更主要的是因为行为人“故意或者过失的先前行为导致法益面临的危险”或者说“先行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具体法益造成的危险”变为了现实。换言之,上述“先行行为说”不是基于习惯或者说一般道理的约定俗成,主张先行行为人具有作为义务,而是从因果引起的角度出发,认为先行行为自身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其可以补足不作为自身没有原因力的缺陷,从而实现不作为与作为之间的等价。如此说来,此处的“先行行为说”与传统理解之间尽管在用语上相同,但内容却相去甚远:其将不真正不作为犯认定的重心从先行行为之后的不履行义务行为转移到先前的“先前行为”自身上去了。从消除不作为和作为之间的结构性差异的角度来看,上述实质的“先行行为说”是有其道理的。在实质的“先行行为说”看来,不作为和作为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只能通过事实上的同置来弥补,因此,强调先行行为自身具有自然意义上的“引起性”,便成为理所当然。而且,这种先行行为的危险可以以其自身所蕴含的侵害法益危险这种客观事实加以判断,而不必依赖于其后的“应当如此”的规范义务进行价值判断。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实质的“先行行为说”和前述的“支配行为说”、“排他支配说”具有相通之处。 但是,这种“先行行为说”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如按照“旧先行行为说”,过失引起交通事故之后,行为人只要逃离现场,就一律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此类推,在过失犯或者结果加重犯的场合,行为人只要对被害人不予以救助,马上就要转化为故意的作为犯;而且,教唆犯和帮助犯也马上要转化为作为形式的正犯,这明显扩大了不作为犯的处罚范围。为了避免这一问题,“新先行行为说”提出了“行为人对危险向实害发生的原因具有支配”的限定条件。认为甲在高速公路上撞伤他人时,交通警察刚好就在身边,此时应当由警察将伤者送往医院抢救。(47)但即便如此,在过失犯或者结果加重犯的场合,行为人只要对被害人不予以救助,马上就要转化为故意的作为犯之类的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同时,行为人中途介入并支配面向法益侵害结果的因果进程的场合,“先行行为说”也难以说明。 (四)小结 综上所述,关于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条件,尽管还存在不少问题,但将历来倚重规范价值判断的“违反作为义务”具体化为“支配行为”、“排他支配行为”、“先行行为”等可视的客观事实因素,在此基础上明确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条件和处罚范围的作法,已是大势所趋。而且,就我国目前的研究来看,尽管关注点不同,名称各异,但它们都有一个相同特点,即将不履行作为义务的行为转化为“引起”或者“支配”侵害法益结果的客观事实,以消除作为是引起因果流向,而不作为只是放任因果流向的结构性差异,从而实现二者之间的等价。 如就“先行行为说”而言,其实际上是意图通过将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认定重心从后续的不履行义务行为,转移到先前的先行行为上去的方法,将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范围限定于行为人亲自实施了具有法益侵害危险的先行行为并对该先行行为所引起的危险具有支配的场合;就“支配行为说”而言,其所表达的是: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只限于行为人以实际行动承担起对正面临侵害危险的被害法益的保护,使其处于安定状态之后,又中止或者放弃该承担行为的场合,换言之,只有承担者具有放弃或者中止法益保护的场合,才能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而“排他支配说”则主张,只有一开始就排他、具体地支配了引起法益侵害结果的因果关系的行为,才能构成不真正不作为犯。 上述意图通过可视的、具体的事实因素来说明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条件和处罚范围的做法,同传统的以违反作为义务为中心的不真正不作为犯论相比,尽管名义上仍维持了不履行作为义务的外形,但实际上却看重不履行义务行为当中所存在的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换言之,表面上维持了规范论的研究范畴,实际上却是在寻找因果论的解决路径。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做法,在维持不真正不作为犯论的理论连贯性的同时,也在突破纯粹以规范要素来判断作为义务的底线,追求不真正不作为犯认定上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值得提倡。但其问题也很明显:一方面,由于上述见解仍在采用不作为犯的框架,探讨视角也仍局限在违反作为义务和不作为上,没有突破不真正不作为犯论本身的一些价值预设和基本观念,因此,理论上难免有各种各样的难以自圆其说之处;另一方面,单凭上述某一种见解,均难以对历来要以不真正不作为犯论解决的场景(如母亲不给孩子喂奶将其饿死、父亲看见自己的儿子在水中挣扎而不救助致使死亡的、行为人不小心点燃物品之后不采取任何措施而逃走引起火灾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四、本文的观点——“排他支配设定说”及其展开 本文认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的实质根据在于,行为人主动设定了对法益的排他性支配。主动将被害人置于他人难以救助的状态,而后放弃救助的,或者不小心引起火情之后,能够而且只有其能够扑灭而不扑灭,任其燃烧,造成火灾的,都是要和作为犯同等评价的不真正不作为犯。我自己将这种见解称为“排他支配设定说”。 如前所述,作为的场合,行为人设定或者引起了面向结果的因果流向,这就意味着,作为是行为人引起了侵害法益结果的原因,与此相应,在先前已经存在面向侵害法益结果的因果流向的不作为的场合,尽管行为人不可能成为该因果经过的最初引起者或者设定者,但完全可以通过中途介入而掌控因果关系的发展进程,左右结果发生方向,从而取得和作为犯场合同样的效果。具体来说,医生单纯不履行“救死扶伤”义务致使病人死亡的场合,导致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还是病人自身的疾病,而不是医生的不作为,因此,医生的不作为可以构成渎职,却不能构成杀人。但是,在医生已经开始接手救治病人的场合,就意味着排除了其他人救助病人的可能性,病人的生死已经现实地依赖于具体接手的医生了。在从当时的医学水平和医疗条件上看,该种类型的疾病能够被有效控制的场合,“接手”即意味着则该病人已经转危为安,不再面临生命危险的紧迫状态了。在此过程中,若医生中间放弃或者中止医疗行为,则意味着被控制的安定状态不复存在,病人生命法益再次陷入了不安定。这种中间放弃或者中止的行为,在排除了病人获得他人救助的可能性的具体条件下,比医生单纯的不接手治疗行为的危害性更大,足以被评价为剥夺病人生命的杀人行为。同样,行为人在交通肇事之后,仅仅是逃逸的场合,即便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也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48)而只有在采取其他行为,使得被害人的处境更加危险,如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的场合,才能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49) 但是,对法益的排他性支配的主动设定,并不限于行为人通过中途介入而掌控因果关系的发展进程的场合(“支配行为说”),行为人亲自设定面向结果的危险,并对该危险的流向进行支配的场合(“新先行行为说”),也能实现。因为,正如前面反复强调的,作为是行为人引起并且操纵、支配面向法益侵害的因果关系;而不真正不作为则只是行为人利用、放任已经存在的面向法益侵害的因果关系而已,这样说来,不真正不作为和作为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主要在于行为人与引起结果的原因力之间的关系不同。从物理的角度看,不作为没有原因力,即该不作为本身并没有设定原因;相反地,在作为的场合,作为具有原因力,行为人是原因的主体。因此,要填补不作为和作为之间的空隙,使其与作为犯在构成要件上等价,首先必须考虑行为人是否设定了面向法益侵害的因果关系(原因设定)。但是,原因设定只是导致了因果关系的起源,在结果犯的场合,从原因引起到实现实害结果之间,还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之中,如果有其他因素介入,最终还是不能说该结果的引起是由当初的原因所引起的,难以成立结果犯。因此,成立作为的结果犯,行为人不仅要在结果发生的原因上有贡献,还必须保证该原因按照自己的预料在实害结果当中顺利实现(即原因支配)。如此说来,成立作为犯,行为人不仅要引起发生结果的原因力,而且还必须支配该原因力的发展过程。甚至可以说,“新先行行为说”实际上是“排他支配设定说”的一种表现形式。 总之,只有在行为人主动设定了对法益的排他性支配时,才可以消除不作为和作为之间的结构性差异,进而将该不履行作为义务的行为视为作为,按照作为犯的条款处罚。这种排他支配的设定,既可以通过行为人中途介入面向结果的因果进程的方式,也可以通过行为人制造并支配面向结果的潜在危险的方式。在采用中途介入的方式时,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防止结果发生的目的,只要行为人主动介入已经存在的面向结果的因果进程并达到让他人难以染指的程度即可;在采用先行行为的方式时,行为人仅仅是实施了导致法益面临危险的先行行为还不够,还必须维持该侵害法益危险最终变为现实侵害结果。 以下,依照上述见解,对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几种所谓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情形进行分析验证: (一)见危不救的场合 所谓见危不救的场合,正如丈夫见到因病痛折磨而自杀的妻子生命垂危却不救助,母亲看着不慎跌入池塘的孩子在水中挣扎却无动于衷的场合一样,是指被害人(多半是由于自己的原因)正面临生命、身体上的危险,另一方即行为人能救助却不救助,引起死亡结果的场合,其常见于夫妻、恋人以及父母子女等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对此,我国的司法实践常以不救助的一方具有法定或者道义的救助义务为由,将该不救助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这一点已在本文的开头部分进行说明。但是,从本文的立场来看,这种判决值得商榷。理由如下: 第一,上述场合下,被害人的死亡结果,都是由其自主选择或者自己的过失行为所导致的,并非行为人因果设定行为所导致的。尽管从现象上看,被害人自杀或者落水,并非与不救助的一方完全无关,不救助的一方也具有一定过错,但从日常生活的经验来看,该种程度的过错(如夫妻吵架、恋人分手、欠债不还或者父母疏于看护等)并不足以导致他人自杀,难以将其作为导致他人死亡的原因设定。 第二,和被害人自杀有关的过错,要构成刑法上的犯罪,必须满足一定条件。从域外刑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和他人自杀有关的行为构成犯罪,至少必须达到“教唆”(即让没有自杀意思的人产生自杀念头)、“帮助”(即让有自杀意思的人更加强化该种意思或者为他人自杀提供物质条件)的程度,否则就不可能构成犯罪。(50)“见死不救”行为,从类型性的角度来看,显然没有达到教唆、帮助的程度,因此,将其作为比自杀关联犯罪程度更高的故意杀人罪看待,并不妥当。 第三,日常生活中,共同生活的人群之内,一定程度的争吵和冲突是常态化的存在,即便是夫妻之间、恋人之间、父母子女或者债权债务人之间也在所难免。如果说具有上述关系的人之间所发生的见死不救行为,一律构成故意杀人罪,可能会使人们因为时刻担心不知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遇到特定人员在自己面前自杀而陷入恐惧不安当中,从而引起更大的弊端。 当然,说见危不救行为不构成杀人,并不意味着其也不构成其他犯罪。就上述特定关系人之间见危不救的情形而言,在夫妻、父母子女之间,情节恶劣的场合,可以考虑构成《刑法》第261条规定的遗弃罪;恋人之间,考虑其共同生活的时间、交往的密切程度,可以已经形成事实婚姻为由,比照《刑法》第261条规定的遗弃罪处罚;(51)但就因讨债不还而自杀的情形而言,实在是超乎人们的预想程度,难以对不救助者追究刑事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以下几种见危不救行为属于作为,并非不作为: 一是在他人处于亢奋状态时,激起或者强化他人的自杀情绪,造成他人自杀身亡结果的场合。如夫妻吵架,妻子抱怨自己活在世上没有多大意思。丈夫闻言,便打开卧室东侧的窗户对妻子说:“你如果要死,就从这里跳下去。”妻子一气之下,果然从打开的窗户跳下,当场死亡的场合就是如此。因为,丈夫在妻子处于失去理性的亢奋状态下,明知自己的上述刺激行为可能造成妻子自杀的结果,却故意以言语刺激,强化其自杀的意思,且打开窗户,为他人的自杀提供方便,最终造成了妻子自杀的严重后果。丈夫诱发和帮助妻子自杀的行为,实质上是教唆、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符合我国《刑法》第232条所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只是,考虑到该行为本质上属于介入他人的自杀行为,并非行为人亲自动手的杀人行为,因此,在处罚上可以作为“情节较轻”的杀人行为处理。 二是在他人生命处于危险状态的时候,阻止他人救助,以致他人身亡的场合。如在男女恋爱期间,男方提出分手,女方不同意而在男方家里服毒,意图自杀。在女方药性发作昏迷,女方的姐姐等人闻讯赶来抢救时,男方怕女方已服毒的事实被发现,竟对来人谎称:“她感冒了,喝醉了”,并极力阻止,不让抢救。最终,女方因抢救不及时(当时及时送医的话,是可以抢救过来的),于次日凌晨4时死亡的案件中,男方隐瞒女方服毒事实并阻止抢救的行为,应当看作为杀人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已经不是简单地利用已经存在的因果关系的不作为,而是在以隐瞒真相、阻止救助的实际行动,让本可趋于安定的法益状态恶化,属于引起他人死亡或者说让他人死亡结果提前到来的作为。 三是在他人面临人身侵害而向行为人求助,行为人不仅不提供帮助,反而让被害人的处境更加不利的场合。如在著名的“冷漠出租车司机案”中,当出租车内的女乘客正遭受另一男乘客的暴力侵害时,女乘客向被告人即出租车司机求救,要求其停车。出租车司机不仅不停车,反而听从犯人的要求,绕道行驶,本来10分钟即可到达的路程,结果开了30分钟,从而使犯人行为得逞的案件中,法院认为,出租车司机的“绕道行为”(作为)客观上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提供了便利,因此判定出租车司机构成强奸罪。(52) (二)先行行为的场合 所谓先行行为的场合,正如行为人不小心引起火情,但放任不管,结果造成火灾,酿成重大损害的场合;或者不小心让他人受伤,能够救助而不救助,结果导致他人死亡的场合;或者不小心将他人锁在图书馆之后,明知此事但仍不开锁,导致他人在图书馆里被关闭了一夜的场合一样,是指行为人由于自己的原因导致法益处于危险状态,能排除而不排除,结果引起重大损害的情形。这种场合下,行为人是不是应当构成不真正不作为犯,按照放火罪、故意杀人罪之类的作为犯的条款处罚?成为问题。 上述情形,按照“支配行为说”,恐怕是不能构成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因为,在火情发生或者他人受伤之后,行为人并没有为防止结果的发生而自愿实施具有支配力的行为,没有对导致结果的因果关系形成支配。但是,按照“先行行为说”,上述场合,都会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因为,引起火情和导致他人受伤,都属于行为人的先行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具体利益造成的危险”,当时,没有其他因素的介入,行为人对该危险的明显增加具有排他性支配,因此,在该危险最终演变为实害结果时,可以说,行为人的不灭火或者不救助行为和放火罪、故意杀人罪的作为行为等价,构成不真正不作为犯。 从本文所主张的“行为人亲自设定了对法益的排他性支配”包括行为人亲自设定面向结果的危险,并对该危险的流向进行支配的场合的角度来看,对上述情形原则上也是持肯定态度。特别是有关火灾这种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的场合,《刑法》只是规定有放火和失火两种情形,而没有其他选择。日常生活中,行为人不小心引发火情的情况非常常见,当时的情形下,只要稍微努力,就可以控制住。但行为人出于各种企图(如获取保险金、隐匿罪迹),有意利用或者放任该已经产生的火情,结果造成火灾,其社会危害性极大,纯粹以失火罪来处理,显然不足以评价其违法性或者说社会危害性。这种场合下,从行为人自己设定了火灾的起因(原因设定),并且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扑灭而不扑灭,却有意利用或者放任其发展,并最终造成人员死伤(原因支配)的过程来看,应当说,其和放火行为在价值上没有两样,因此,完全可以评价为不作为的放火。(53)同样,在行为人明知他人被关闭在图书馆,仍不打开的场合,也可以同样理解。这种场合,由于行为人不小心,将他人关闭在图书馆(原因设定),其手上有钥匙,能够轻易地打开门锁,但却不为该行为,导致了他人被关一天一夜(原因支配),因此,在行为性质上可以和非法拘禁罪同等看待,完全可以评价为不作为的非法拘禁。 但在行为人不小心让他人受伤,能够救助而不救助,结果导致他人死亡的场合,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说行为人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情况则比较复杂。因为,对这种类型的危害行为的评价,不仅涉及分则当中的故意伤害罪(《刑法》第234条)和故意杀人罪(《刑法》第234条),其还涉及刑法总则当中有关中止犯的相关规定(《刑法》第24条),换言之,其不仅是一个理论解释问题,而是涉及多大程度上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 按照“先行行为说”,作为引起侵害法益危险的先行行为的范围极为广泛,不仅包括一般违法行为,也包括故意、过失的犯罪行为,只要是创设法所不允许的风险的行为,都包括在内。(54)但是,果真如此的话,则批判意见所说的,依此类推,在过失犯或者结果加重犯的场合,行为人只要对被害人不予以救助,马上就要转化为故意的作为犯。而且,教唆犯和帮助犯也马上要转化为作为形式的正犯,这明显扩大了不作为犯的处罚范围的批判该如何回应,确实是个难题。 同时,将故意犯罪也列为作为义务来源的先行行为,问题更大。从罪刑法定原则的立场来看,故意犯罪行为是不可能作为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的。因为,一方面,从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故意犯的场合,立法者本来就没有指望行为人在实施加害行为之后,还能够主动实施防止侵害结果发生的行为。行为人主动实施该防果行为并有效的话,就要构成《刑法》中所规定的犯罪中止,受到“减免处罚”的奖励。换言之,中止犯规定的存在表明,现行《刑法》并没有赋予行为人防止侵害结果发生的义务;另一方面,正如故意伤害他人之后,不救助而导致他人死亡的,构成故意伤害(致死)罪,要被加重处罚一样,行为人所不阻止的损害后果通常包含在其先前的作为加害行为之中,只要评价其先前的犯罪行为,就足以评价其后所引起的行为不法与结果不法,没有必要再单独考虑其后的不作为行为。(55) 因此,虽说理论上可以肯定犯罪行为能够成为先行行为,并以此为根据而追究行为人的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刑事责任,但在其应用上必须结合刑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在先行行为所内涵的危险实现能够为先行行为的行为不法和结果不法所包括,就可以说该行为的危险已被先行的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所“用尽”,没有必要再将该犯罪行为视为先行行为以评价相应的不作为。(56)在理论探讨和刑法规定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当优先考虑刑法规定,绝对不能以牺牲罪刑法定原则为代价,换取对法益的绝对保护。 (三)遗弃婴幼儿、老年人、残疾人的场合 婴幼儿、老年人、残疾人等由于年龄或者身体的原因,没有自我生存或者自我保护能力,或者该种能力较弱,其生死或者日常生活严重地依赖于他人,因此,其在理论上被称为“脆弱法益”。对“脆弱法益”的保护,一般来说,均具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如关于婴幼儿,我国《婚姻法》第21条明确规定,禁止溺婴、弃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关于老年人,我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3条规定,禁止歧视、侮辱、虐待或者遗弃老年人;关于残疾人,我国《残疾人保障法》第9条规定,禁止对残疾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残疾人。问题是,不遵守上述法律规定,不尽赡养或者抚养义务,遗弃幼儿、老年人、残疾人的,是不是一律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 从本文所主张的“只有在行为人主动设定了对法益的排他性支配时,才能按照作为犯的条款处罚”的见解来看,对上述脆弱法益不尽抚养、赡养义务的行为,若要作为故意杀人罪处罚,仅仅是不履行义务还不够,行为人还必须具有进一步的、具体威胁、侵害其生命法益的行为。如母亲有意将孩子生在厕所便池里;交通肇事者将被害人转移到路边难以被人发现的草丛里;家人将神志不清、行动不便的老人带至野兽出没的深山偏野或者少有人烟的冰天雪地等。这些行为看似不履行法定作为义务的真正不作为,但是,刚出生的婴儿或者年龄尚小的幼儿,身体发育还不成熟,自我生存能力很脆弱,即便是正常环境下,如果没有包括父母在内的其他人的照料,也难以存活,更不用说将其放置在一个臭气熏天的便池里,属于行为人亲自设定了面向法益侵害结果的因果进程,并对其进行排他支配的情形。这种做法,无疑加速了幼儿生命终期的提前来临,和掐死、毒杀等作为方式的杀人行为并无二致,属于不真正不作为。(57) 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场合也是如此。依照我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58)以及有关司法解释,交通肇事后,放任被害人死亡的,构成交通肇事罪,但要加重其处罚。但相关司法解释规定,(59)交通肇事后,行为人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藏匿或者遗弃”的,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因为,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藏匿或者遗弃”的行为,实际上行为人亲自设定了面向法益侵害结果的因果进程,并对其进行排他支配的情形。被害人在被转移到路边难以被人发现的草丛中的行为以后,被他人发现救助的可能性就被剥夺,使其落入了必死的境地。这种转移行为和轧死被害人的杀人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样,神志不清、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带至野兽出没的深山偏野或者少有人烟的冰天雪地,也是让其陷入了生存的绝境,属于置之于死地的行为,因此,和作为具有等价性。 如此说来,遗弃婴幼儿、老年人、残疾人等脆弱法益的行为,虽说在形式上属于不履行作为义务的真正不作为,但由于其设定并具体支配了面向法益侵害的因果进程,促进了被害人生命法益的恶化,因此,属于不真正不作为,对其应适用作为犯条款,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但要注意的是,这种遗弃行为,只能发生在行为人主动承担了对婴幼儿、老年人、残疾人的保护的场合,在被动地处于对上述人员具有承担保护的场合,由于不属于“行为人主动设定了对法益的排他性支配”,因此,不能构成不作为的作为犯。据此,可以说,学界曾经热议的“出租车司机遗弃病人案”(60)中,出租车司机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该案情是这样的:洪某驾驶出租车在大街上揽客,何某将一大量失血并已昏迷的老人抱上车,说是自己撞伤的,要求洪某驱车前往医院抢救。当车行驶10分钟之后,何某要求停车,找借口离开。洪某等候30分钟后,见已经到了深夜,就怀疑何某已经逃逸,便将重伤老人弃于附近大街。第二天交警发现老人尸体,经法医鉴定是失血过多而死亡。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何某和洪某提起公诉,法院最后对何某作了故意杀人的有罪判决,宣布洪某无罪。我认为,法院的判决是妥当的。在上述案件当中,就出租车司机洪某的行为而言,尽管被害人身在其车厢之内,其在事实上对于被害人的生死具有排他性支配,但是,这种排他性支配的取得并不是基于洪某本人的意愿而形成的,而是由于乘客何某带人上车这种极为偶然的原因而形成的,实际上,就像是自己的院子里突然有一个受伤的人闯进来了一样。在本案当中,出租车司机在法律上并没有救死扶伤的义务,同时,被害人所处生命垂危的危险状态也不是出租车司机本人的先前行为所造成的。因此,本案当中,出租车司机的行为尽管在道义上值得强烈谴责,但是,和自己主动剥夺他人生命的杀人行为相去甚远,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不真正不作为犯论的核心,说到底,是保护法益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偏重保护法益的话,便会说所有不利于法益保护的行为都值得处罚,但强调罪刑法定原则的话,则会得出只有符合刑法规定类型的侵害法益行为才能进入刑法处罚范围的结论。 就以不作为方式实现作为犯的构成要件的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情形而言,尽管在行为方式上,其是不作为,但由于最终是按照结果犯的条款来处罚的,因此,该不作为是如何引起结果的因果关系的判断就必不可少。但现行的学说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仍显薄弱,因此,在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研究上,规范的作为义务论反而成为探讨中心。只是,这种研究方式不仅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还会导致和法益保护原则之间的紧张,因此,在实质义务论的名义之下,有关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研究最终还是回到了对不履行义务行为当中事实上存在的引起和被引起关系的探讨。 作为是引起因果关系,而不作为是利用因果关系,二者之间的这种结构性差别,使得在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上,必须以消除该种差别,实现二者之间的等价为出发点。而这种结构性差别的消除,只有在行为人主动设定了对法益的排他支配时,才能实现。这种排他支配的设定,既可以通过行为人的中途介入面向结果的因果进程的方式,也可以表现为行为人制造并支配面向结果的潜在危险的方式。 ①所谓不真正不作为犯,是以不作为的方式实现作为犯的犯罪构成,并按照作为犯的条款处理的犯罪类型,通常表现为杀人、放火之类的结果犯。就不真正不作为犯来说,也存在着举动犯和结果犯的区别,但实际上,讨论的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情形,几乎都是结果犯。参见(日)松宫孝明:《刑法总论讲义》(第4版补正版),钱叶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页85。 ②参见许成磊:《不纯正不作为犯理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页337以下。 ③(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22;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页68。 ④具体内容参见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1995)南刑终字第002号刑事裁定书。原案情为:某日晚,被告人宋某某同其妻李某生气,李要上吊,宋喊来邻居叶某某进行劝解,叶走后二人又吵骂撕打,后李寻找自缢工具时,宋意识到李要自缢却无动于衷,放任不管。直到宋听到凳子响声时,才起身过去,但其仍未采取有效措施或呼喊近邻,而是离开现场到一里以外的父母家中去告知自己父母,待其家人赶到时李某已无法挽救。 ⑤具体内容参见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金中刑终字第90号刑事裁定书。原案情为:李某某和被害人项某某(女)相识并相恋,不久项某某怀孕。同年6月,李某某提出分手,并要项去医院做流产手术。项不同意,几次欲跳楼自杀。同年9月5日中午,李某某回到宿舍,见项在房里,便发生争吵。项喝下了事先准备好的一瓶敌敌畏。此时,李不但没有及时救人,反而一走了之。临走时怕被人知道,还将房门锁上。当天下午,项被人发现送往医院,但救治无效死亡。 ⑥具体内容参见:“老汉索帐无果撞墙丧命”,载《扬州晚报》2007年7月22日,第6版。原案情为:在追帐人李老汉索钱无果以寻死撞墙要挟,而债务人赵某不仅不主动劝阻,反而拂袖离去,导致李老汉失血过多死亡。 ⑦参见:“深圳联防队员毒打强奸女子一小时其夫躲杂物间不敢出声”,资料来源:http://www.s1979.com/shenzhen/201111/0820378708.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6月30日。原案情为:被告人联防队员杨某某手持钢管、警棍闯进被害人王某的家中,一通乱砸后,对她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强奸。她的丈夫杨某则躲在几米外,不敢做声,眼睁睁看着妻子遭此横祸,一个小时后才悄悄报警。虽然身为丈夫杨某某,却没敢挺身而出制止恶行,也没有冲出门外呼救(社区警务室就在几米开外)。 ⑧参见高艳东:“肖志军案中的刑法难题和价值取向——不作为、因果关系与间接故意之新界”,《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⑨本案案情如下:2007年11月21日,怀孕9个月的李丽云因呼吸困难被“丈夫”肖志军(二人尚未登记结婚)送到北京朝阳医院京西分院治疗。医院建议进行剖腹产手术,但肖志军无视医生的百般劝说,坚决不同意实施剖腹产手术,并在手术通知单上写下“坚持用药治疗,坚持不做剖腹手术,后果自负。”最终,李丽云和腹中的孩子当天双双身亡。2008年1月24日,李丽云的父母提起民事诉讼,将朝阳医院和肖志军告上法院,索赔死亡赔偿金等,后又撤回对肖志军的起诉,并将索赔数额增加至121万元。2009年12月,北京朝阳法院驳回李丽云父母121万元的索赔请求。鉴于朝阳医院同意给付一定经济补偿,法院酌定数额为10万元。资料来源:“孕妇李丽云死亡案一审宣判,无因果关系医院不担责”,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_article/content/2009-12/19/content_2007593.htm?node=6848,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0月18日。 ⑩(日)井田良:“不真正不作为犯”,载《现代刑事法》第1卷第3号,页93。 (11)松宫孝明,见前注①,页84。 (12)以上学说的概括和总结,参见(日)日高义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理论》,庆应通信出版社1979年版,页21-22;李光灿、张文、龚明礼著:《刑法因果关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页194-196;黎宏:《不作为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6-7;许成磊,见前注②,页197-201。 (13)参见刘焕文:“罪与非罪的界限”,《江西大学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1期。 (14)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页131。 (15)参见陈忠槐:“论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法学研究》1988年第1期。 (16)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页85;冯军、肖中华主编:《刑法总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238;周光权:《刑法总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101。周教授认为,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带有规范上假定的关系:如果行为人履行特定义务,结果“十之八九”的场合,可以肯定不作为的因果关系。但罕见地也存在反对观点,认为引起危害结果的不作为不只是有作为义务的人所实施的不作为。参见肖中华:《犯罪构成及其关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382。 (17)许成磊,见前注②,页221-222。 (18)主张不作为有无因果力的判断必须考虑作为义务的学者中,只有周光权教授采用了与德日类似的三阶层的犯罪构成体系。 (19)这一点,在我国特别要强调。因为,和我国台湾地区“刑法”不同,我国《刑法》没有在刑法总则中设置作为扩张处罚事由的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规定。在不具有这种特别规定的场合,之所以能够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并不是要对处罚作为犯的条款进行扩张之后,肯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而是因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符合了相应的处罚规定本身而成为处罚对象。正因如此,在不作为与作为的等价性的判断上,必须非常严格。 (20)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页100。 (21)(日)大谷实VS(日)前田雅英:“精彩刑法(第3回):不作为犯”,载《法学教室》1996年第195号,页30以下。 (22)如先行行为能否为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理论界有“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之分。肯定说认为,既然违法行为都可以是先行行为,那么,否定犯罪行为是先行行为,于情理不合,也不利于司法实践。参见高铭暄主编:《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118、119。相反地,否定论者认为,先行行为不应包括犯罪行为,无论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都不另负防止结果的义务,主张行为人实施犯罪后,有义务承担刑事责任,没有义务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否则,就会使绝大多数犯罪从一罪变为数罪。参见于改之:“不作为犯罪中先行行为的本质及其产生作为义务的条件——兼论刑法第133条‘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立法意蕴’”,《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5期。折中说认为,不能一概否认犯罪行为成为先行行为的可能性,但必须明确其作为先行行为的性质,否则,就可能出现否定说所说的一行为变数行为,出现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情形。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可以是过失犯罪行为,但不包括故意犯罪行为。徐跃飞:“论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时代法学》2006年第2期。或者说犯罪行为是否先行行为,基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应以行为人所放任发生的危害结果是否能为前罪的犯罪构成(包括加重构成)所包括作为区分标准:能包括的,没有作为义务,依据前罪的法定刑幅度定罪处罚即可;超出前罪犯罪构成范围而触犯更为严重犯罪,则具有作为义务。赵秉志:“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应采四来源说——解析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根据之争”,载《检察日报》2004年5月20日,第6版。 (23)高铭暄、马克昌主编,见前注(20),页103。 (24)黎宏,见前注(12),页85。 (25)周光权,见前注(16),页101。周教授主张,在行为人履行特定义务,“十之八九”不会发生危害后果的场合,可以肯定不作为和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许成磊,见前注②,页234。许博士认为,对一般人来说,“行为人如果采取积极措施能够避免结果发生的几率”如果达到“60%以上”,而行为人没有采取积极的救助措施,以致造成结果发生的,就可以肯定不作为因果关系的成立。 (26)因为,“因果关系,是实际存在的行为和实际存在的结果之间的关系,是实际存在的情形,因此,其判断,只能就实际存在的事实而进行”,否则,会推导出很荒谬的结论来。如在课堂上经常列举的“死刑犯案件”中,会得出即使被害人的父亲不突然冲出来杀死死刑犯,行刑人也会开枪打死死刑犯,因此,被害人的父亲的行为和死刑犯的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结论。但这显然很荒谬。具体参见(日)大谷实著:《刑法讲义总论》(新版第2版),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200。 (27)同上注,页128。 (28)松宫孝明,见前注①,页67;(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2版),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79;高铭暄、马克昌,见前注(20),页86。其中写道:“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的特定义务,是成立不作为的前提条件。如果行为人没有这种特定义务,则不能构成刑法中的不作为”。 (29)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543-545。形式说,根据各个学者的理解不同,所归纳的类型也不一致。在我国,早期“三来源说”认为,不作为的义务来源为法律规定、职务或者业务要求、先行行为。参见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页99。现在也有人提倡“五来源说”,除了上述法律上的明文规定、职务和业务要求、先行行为以及自愿承担行为之外,还认为,“特殊场合下,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要求履行的特定义务”也是作为义务的来源。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171-172。 (30)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页99。 (31)参见许成磊,见前注②,页258。 (32)熊选国:《刑法中行为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页164。 (33)冯军:《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页45-48;黎宏,见前注(12),页157。 (34)除了以下所列举的观点之外,还有兼具实质性内容的“综合说”。认为在研究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时,必须考察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事实因素,即行为人对危害结果发生的因果关系能现实地具体支配;二是规范因素,即法令、法律行为,职务或业务上的职责等通常意义上的作为义务发生根据。参见黎宏,同上注,页166-167。这种观点也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认为“以支配理论为中心,建立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作为义务论是比较妥当的见解”。参见许成磊,见前注②,页337。但是,作为这种见解的始作俑者,我现在已经不再主张这种观点。因为,在事实因素和规范因素不一致的场合,行为人是不是具有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难以判断,反而会使简单问题复杂化。因此,我现在也主张在不真正不作为义务的判断上,只考虑事实因素,即从不作为人和结果的关系中来探讨作为义务,也就是从结果的发生原因中推断不作为人的作为义务。参见黎宏:《刑法总论问题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145。只是,什么场合下,可以说行为人实际控制了因果关系的发展流向,尚没有得出让自己满意的结论。 (35)冯军,见前注(33),页45-48。 (36)同上注,页45-48。 (37)这种见解认为,从不作为人和被害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规范的观点来理解作为义务的实体的话,最终就会归结到根据社会伦理这种一般条款进行判断的问题上,难以阻止不真正不作为犯问题判断上的伦理化趋势,因此,不作为人和结果的关系,即“面临危险的法益和不作为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事实要素(事实上的承担行为)”应当受到重视。具体来说,在考虑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的时候,必须考虑以下因素:①开始结果条件行为,即开始实施意图维持、继续法益的行为,如开始给婴儿喂食,开始救助交通肇事的受害人;②不作为人反复、继续该种事实上的承担行为;③在保护法益(不发生结果)方面,行为人具有排他性,将因果关系的发展进程控制在自己手中。参见(日)堀内捷三:《不作为犯论》,青林书院新社1978版,页249以下。 (38)许成磊,见前注②,页336。 (39)理论见解,参见高铭暄、马克昌,见前注(20),页399;苏惠渔主编:《刑法学》(第五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页256。 (40)马克昌主编:《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页515。 (41)何荣功:“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构造与等价值的判断”,《法学评论》2010年第1期。 (42)日本学者日高义博教授在其1978年所出版的《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理论》(庆应通信股份公司1978年版)一书中,提出为克服作为和不作为存在构造上的差别,必须有“不作为者的原因设定行为”,即不作为者在该不作为成立之前,必须自己设定倾向法益侵害的因果关系,它是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等价值性的判断标准。这种“原因设定行为”,实际上就是历来所说的“先行行为”。在日本,对这种“原因设定行为”说的批判是,使更多的故意犯、过失犯得以转化为不真正不作为犯。换言之,凡因故意、过失而伤害他人者,只要未予救助最终死亡,根据该先行行为便可以轻易地认定为不作为的杀人,如单纯的肇事逃逸也可以直接构成不作为的杀人。这是对其根本性的疑问。以上批判,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第2版),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页104。 (43)何荣功,见前注(41)。 (44)张明楷:“不作为犯中的先行行为”,《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 (45)王莹:“论犯罪行为人的先行行为保证人地位”,《法学家》2013年第2期。 (46)王莹,同上注,页122;张明楷,见前注(44)。 (47)张明楷,见前注(44)。 (48)我国《刑法》第133条对这种情形,仍然规定为交通肇事罪,只是加重其处罚而已。 (49)参见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 (50)参见《日本刑法》第202条。该条规定,教唆或者帮助他人自杀,或者受他人嘱托或者得到他人的承诺而杀之的,处6个月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监禁;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275条规定也规定,教唆或者帮助他人使之自杀,或受其嘱托或得其承诺而杀之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项之未遂犯罚之。谋为同死而犯第一项之罪者,得免除其刑。此外,《奥地利刑法》第78条、《西班牙刑法》第143条、《意大利刑法》第580条、《法国刑法》第223-13条等均将参与自杀的行为全部或者部分作为犯罪加以明文规定。 (51)李立众:“事实婚姻中的遗弃行为能否认定遗弃罪”,《人民检察》2008年第1期。 (52)参见:“‘冷漠的哥’坐视车内15岁少女被强暴获刑两年”,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fz/2011/05-20/305664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0月18日。,应当说,法院的这种判断固然不错,但说理上略嫌不足。因为,其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即出租车司机在犯罪嫌疑人强暴被害人的过程中,始终驾驶车辆,其持续的让车辆处于行驶状态的行为,使得犯罪行为处于一种难以被他人发觉和阻止的封闭状态,进一步恶化了被害人所面临的危险。这也应当成为认定出租车司机构成强奸罪的帮助犯的依据。 (53)当然,要注意的是,构成不作为放火的,仅限于行为人自己引起了火情的场合。在起火的原因是雷击或者第三人用火的场合,即便行为人看到了火势而任其发展,见危不救的场合,由于其没有设定起火原因,因此,无论如何,不构成不作为的放火。 (54)王莹:“先行行为作为义务之理论系谱归整及其界定”,《中外法学》2013年第2期。王莹博士认为,过失犯罪可以成为先行行为引发作为义务,并举例说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行为人在发生责任事故后,“故意隐匿重伤的被害人以防止其被救治或者阻止他人救助而致其死亡的”,应对死亡后果承担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责任。参见王莹:“论犯罪行为人的先行行为保证人地位”,《法学家》2013年第2期。但在本文看来,重大责任事故发生之后,“故意隐匿重伤的被害人以防止其被救治或者阻止他人救助”,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场合,致使被害人死亡的,由于存在行为人之后所实施的“故意隐匿重伤的被害人”以及“阻止他人救助”行为,因此,将行为人的行为评价为作为也并无不可。犯罪行为应当尽量排除在作为作为义务来源的先行行为之外。 (55)将故意犯罪作为先行行为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不将故意犯罪行为作为先行行为,就无法处罚事后的不救助行为的共犯。如在甲以杀人故意将被害人乙砍成重伤,随后,甲看到乙躺在血泊中的痛苦表情,顿生悔意,打算立即叫救护车。此时,无关的第三人丙极力劝阻甲,唆使其放弃救助的念头,乙最终因失血过多而死亡的案例中,有学者认为,只有认定甲的故意杀人行为产生了救助义务,其后来的不作为也属于杀人行为,才能认定丙的行为成立不作为杀人的教唆犯。参见张明楷,见前注(44);王莹,见前注(45)。确实,将故意犯罪作为先行行为,对于处罚事后不救助行为的共犯来说,具有实际意义。但仅因为此而不惜违反现行《刑法》中中止犯的相关规定宗旨,不仅有小题大做之嫌,而且还会引起不良后果。详言之,如A以杀人故意将乙砍成重伤后离开。无关的B经过此地,准备救助乙。C劝阻B别管闲事,结果乙死亡。上述案例当中,C的行为,从外观和产生的实际效果来看,和前述案例中丙完全一样。在前一案例中,丙要受罚,而在后一案例中,C却不受任何处罚。从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而不是其他的角度来看,完全相同的侵害法益行为,法律后果却迥异,对于故意杀人罪这种不以行为人具有特定身份为成立要件的犯罪来说,难免会让人觉得有些怪异。特别是在A杀乙之后离开,于心不忍,意欲返回救助,不知情的C劝阻,A便离开;后路过此地的无关者B看见地上躺着的乙,顿生恻隐之心,准备救助,但也被C劝阻离开的场合,两相比较,就会看出,C之所以要受到处罚,仅仅是因为运气不好——不认识谁是杀人者。这种做法,不是在追究偶然责任吗?同时,以无法处罚上述情形中的丙为由,说明先前的故意伤害行为属于作为义务来源的见解,在方法论上有循环论证之嫌。即,待证问题是甲的犯罪行为是否先前行为,但在证明过程上,一方面说,如果甲的行为不是先前行为,就无法处罚丙;另一方面又称,因为能够合理地处罚丙,所以甲的伤害行为是先前行为。二者在互为因果、循环论证。这样考虑的结果是,行为人自身的刑事责任取决于与其之外的其他人的行为,如就上例而言,本来,行为人甲的行为就是一个故意伤害致死的行为,但由于要追究其之外的丙的刑事责任,因此,不得不将其行为升格为故意杀人。这岂不是违反个人责任原则吗? (56)王莹,见前注(45)。在这一点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许玉秀教授的见解,值得考虑。她认为,如前行为是故意的作为时,对后面的不救助行为产生的结果,所侵犯的法益不同的,按照结果加重犯处理,侵犯法益相同的,按前一行为的既遂犯处理即可。确实无法解决的,只能通过立法的方式。上述内容参见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页693以下。 (57)我国的司法实践也是这么理解的,只是将这种行为认定为不作为的杀人行为而已。如在最近轰动一时的“南京饿死女童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人乐燕身为两位女儿的生母,对女儿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明知两年幼的女儿无人抚养照料,其不尽抚养义务必将会导致两被害人因缺少食物和饮水而死亡,但却仍然将两被害人置于封闭房间内,仅留少量食物和饮水,离家长达一个多月,不回家抚养照料两被害人,在外沉溺于吸食毒品、打游戏机和上网,从而导致两被害人因无人照料饥渴而死。乐燕主观上具有放任被害人死亡的间接故意,客观上造成两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因此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具体参见“南京饿死女童案宣判被告人因故意杀人罪判无期”,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fz/2013/09-18/5300339.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0月18日。 (58)我国现行《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需要说明的是,从我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来看,似乎不认可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可以成立不作为杀人。但是,从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来看,应当说,这种理解是没有道理的。按照我国最高法院的前述“解释”,交通肇事罪,只有在造成一定人数的人员死伤的场合,才能成立。在交通肇事造成1人死亡的场合,可能会有逃逸行为,但是,不可能具有“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结果,所以,这种情形应当排除在外;在造成3人以上重伤的场合,可以出现肇事者“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这种情况下,因为肇事者有逃逸行为,所以,应当在“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范围内酌定量刑。同时,又因为行为人的“逃逸致人死亡”行为成立故意杀人罪。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构成“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罪,应当在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范围之内酌定量刑。这种场合,即便对行为人都选择各个犯罪的法定刑幅度之内的最高刑,最多也只能在10到17年的有期徒刑范围之内,选择宣告刑。这和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在“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范围内选择刑罚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另一种可能是,将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作为“情节一般”的故意杀人罪,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范围内量定刑罚,然后再和具有逃逸情节的交通肇事罪实行并罚。这种场合下,对行为人的处罚,显然会很高,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场合就不用说了,在判处有期徒刑的场合,最高可达20年。但是,总体上看,本质上属于过失致人死亡的交通肇事行为,结果却被处以如此重的刑罚,这无论如何也是叫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因此,《刑法》第133条避开了争议巨大的交通肇事后逃逸是不是构成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争议,而笼统地规定为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交通肇事罪,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但这并意味着,现行《刑法》不认可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可能成立不作为杀人的见解。 (59)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条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藏匿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当分别依照《刑法》第232条、第234条第2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60)具体案情介绍以及讨论分析,参见杨兴培、李芬芳:“见死不救旁观者是否构成犯罪及救助义务探析——以一起‘出租车司机弃置伤者致其死亡案’为切入点”,《东方法学》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