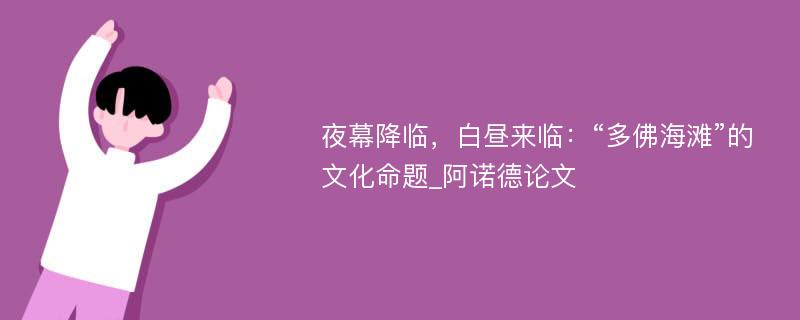
夜尽了,昼将至:《多佛海滩》的文化命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佛论文,尽了论文,命题论文,将至论文,海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的诗歌作品中,《多佛海滩》(“Dover Beach”,1867)是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一首。国内外对该诗的研究热情似乎从未消退过。以我国为例,过去十年里涉及该诗的研究成果就不下十余种,大都把兴奋点集中在“阿诺德的悲观”这一话题上,而对《多佛海滩》的文化命题未能深究。可以说,新近的研究依然沿袭了当年吴宓先生如下评论所遵循的思路:“安诺德深罹忧患而坚抱悲观,然生平奉行古学派之旨训,以自暴其郁愁为耻,故为文时深自敛抑,含蓄不露。所作者光明俊爽,多怡悦自得之意,无激切悲伤之音。惟作诗时,则情不自制,忧思劳愁,倾泻以出。”①当今学界大都沿着这条思路,认定阿诺德是借《多佛海滩》倾泻悲情,可以说是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例如,《英国19世纪文学史》对《多佛海滩》作了这样的解读:“信仰和怀疑、希望和绝望之间的斗争是阿诺德忧郁的源头,也是他对他的时代做出极端悲观的描述的原因。”②
《多佛海滩》仅仅是倾泻悲情吗?依笔者之见,如果我们细细揣摩该诗的两组中心意象,即“海潮”意象和“夜战”意象并顺势挖出其背后的文化命题,就不会简单地给阿诺德贴上“绝望”的标签。
在分析“海潮”意象和“夜战”这两个意象之前,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下“悲观主义”这个概念。在西方文学中,“悲观主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消极的概念,因而不能简单地跟“沮丧绝望”和“灰暗色调”画等号。尼采就曾经这样发问:“悲观主义一定是衰退和堕落的标志吗?一定是失败的标志吗?一定是疲惫而羸弱的本能的标志吗?”③他还提倡“一种有力量的悲观主义(pessimism of strength)”。④我们不妨借用尼采的口吻提问:《多佛海滩》是否也传达了一种有力量的悲观主义呢?当它与文化命题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是否尤其如此?
一、潮起潮落为哪般?
“绝望论”往往依据诗中关于海潮的描写,引用得最多的是下面这一诗节:
信仰之海
也曾有过满潮,像一根灿烂的腰带
把全球的海岸围绕。
但如今我只听得
它那忧伤的退潮的咆哮久久不息,
它退向夜风的呼吸,
退过世界广阔阴沉的边界,
只留下一滩光秃秃的卵石。⑤
确实,此处“信仰的海洋已经退潮”,⑥使得许多学者都从中找到了阿诺德“悲观”的原因。安德森(Warren D.Anderson)就曾经根据诗中“潮水起伏循环的意象”,强调“这首诗因其悲观主义而独步一时”,⑦而对其“悲观主义”的内涵则未作深入的分析,对“海潮”意象的其他含义更没有顾及。伊莎贝尔·阿姆斯特朗(Isobel Armstrong)也认为,阿诺德“哀叹基督教神话的消失,就像《多佛海滩》中‘信仰之海’退潮那样”。⑧今年刚问世的《剑桥英国文学指南:1830-1914》(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1830-1914,2010)中的一篇文章,也仅仅指出“《多佛海滩》讨论的是退潮的‘信仰之海’”。⑨不能否认,诗中的“海潮”意象的确是指涉“信仰之海”的退潮,指涉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科技发展给宗教信仰带来的打击,但是众所周知,文学意象的意蕴远非一对一的指涉关系所能涵盖的,这里的海潮也不例外。
“海潮”意象在诗中出现过多次。除了上举引文以外,它还分别出现在第二和第三小节。在第三小节中,我们看到(同时也听到)“索福克勒斯很久以前/在爱琴海边听到的/引起他内心共鸣的人类苦难的/浑浊的潮落潮起……”(Sophocles long ago/Heard it on the Aegean,and it brought/Into his mind the turbid ebb and flow/Of human misery…)⑩在第二小节中,我们看到海浪“涌起,停息,再涌起”(Begin,and cease,and then again begin)。以笔者之见,这反复出现的潮起潮落,不光在哀叹“信仰之海”的退潮,更重要的是意味着维多利亚思想史上的一次范式转换。
这次范式转换的端倪表现为隐喻转换,即从“钟摆”或“车轮”的隐喻向“潮汐”的隐喻转换——先前用“钟摆”或“车轮”来形容人类社会的总体进程,此时则改为用“潮汐”来形容。奥尔悌克(Richard D.Altick)曾经对此有过这样的叙述:在维多利亚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包括阿诺德)开始把社会历史的变迁比作“潮落与潮涨、命题与反题、腐败-死亡-新生的循环轮回,而这在先前则被比作钟摆或车轮,后者的运行方向非左即右,非上即下,因而用以判断人事时,其寓意总是非好即坏,两者只能取其一”。(11)笔者认为,这一隐喻的转换,其实意味着向当时“进步”话语的挑战:19世纪,流行着一种令无数英国人陶醉的进步观;英国因其工业、科技和军事上的实力而成为世界霸主,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等人大肆传播“进步”学说,致使许多人抱有一种“认进步为不绝的和必然的事情之信仰”,(12)尤其是许多资本家“把自己的好运气看作自然规律,并且认为这种好运气会永远延续下去”。(13)支撑这种进步观的就是以“钟摆”——更确切地说,是以“直线”——为核心隐喻的思维范式。英国举国上下,无不痴迷于一种宏伟的构想,即人类社会因财富的无限增长而直线式地、无止境地朝着幸福状态进步。当此之际,阿诺德的“潮汐”隐喻对所有做着这一美梦的人来说,不啻为当头棒喝。
在当时社会,在“潮汐”隐喻崛起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大发现”:通过对出土文物和史前洞穴的研究,当时的考古学家们发现,以往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并非遵循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直线发展轨道,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众多文明几度兴盛,几度衰亡,就像海潮的起伏波动。这一发现,对当时踌躇满志的英国人来说,几乎是颠覆性的,因为他们引以为荣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远非最早的伟大文明,无论是在此之前,还是在此同时,都出现过成就堪与比肩的其他文明,出现的地点不仅在地中海周围和近东,而且在亚洲和中美洲。这些文明个个都一落千丈了”。(14)这一史实对把英国吹嘘为“有史以来最伟大最高度文明的民族”(15)的麦考莱等人构成了极大的讽刺,也使阿诺德的“海潮”意象具备了深厚的意蕴。对此,奥尔悌克有过如下评论:“阿诺德的《多佛海滩》中的‘潮落潮起’意象是一个特别合适的象征,它象征着那些较为敏感的维多利亚人的一种意识,即每一英里的进步,都很可能会有一英里的退步来抵消它。”(16)当然,我们不必完全同意奥尔悌克的说法,因为凡是象征,都具有多义性,“海潮”意象完全可以不局限于“进步”和“退步”相抵消的含义。然而,向“进步”话语提出质疑,这无疑是“海潮”意象的蕴涵中极其重要的部分。
《多佛海滩》全诗的内容和行文节奏都可以用一涨一落的海潮来形容。仅以诗歌的首节和末节为例:两者之间的互动和对比恰似潮水的涌起和低落。首节是宁静而甜美的梦幻开局:
今夜大海平静,
潮水正满,月色朗朗,
临照海峡,——法国海岸上
微光渐隐,而英国的峭壁高竖,
在宁静的海湾里显出巨大模糊的身影。
到窗边来吧,晚风多么甜!
末节则揭示这一切全是虚幻的表象:
啊,爱人,愿我们
彼此真诚!因为世界虽然
展开在我们面前如梦幻的国度,
那么多彩、美丽而新鲜,
实际上却没有欢乐,没有爱和光明,
没有肯定,没有和平,没有对痛苦的救助;
两相对比,分明是潮水的一涨一落:首节中是朗朗的月色、宁静的海湾、甜美的晚风和满满的潮水,其美妙已经不言自喻;可是末节笔锋突转,指出在“多彩、美丽而新鲜”的背后,实际上“没有爱和光明”,甚至连“对痛苦的救助”都没有,这跟潮水的低落又十分合拍。
在这潮涨潮落的节奏中,我们似乎可以听到对如下文化命题的追问: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幸福?什么叫有质量的生活?奥尔悌克曾经指出,人民大众的生活质量问题,在维多利亚时代首次成了“文化”命题:
在维多利亚时代,人民大众的生活质量第一次成了紧迫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关注。由工业化及其相关的社会发展造成的巨变促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社会该怎样改造并装备自己,才能给社会成员带来最大的内心满足,帮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有人认识到,英格兰希望建成的美好社会有赖于某种叫做“文化”的东西。“文化”一词在19世纪上半叶经历的这种意义上的演变,表明社会思想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观念。(17)
《多佛海滩》中的潮汐似乎正好跟这生活质量有关:首节中貌似甜美的海景恰好与维多利亚社会的表面繁荣暗合,而末节潮水的低落则表明维多利亚式的文明并非真正的进步,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幸福,并没有提供品质良好的生活。诚然,得益于工业革命和军事掠夺,19世纪中期英国的GDP和贸易总量远在其他国家之上:它的工业生产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铁和煤的产量占世界的二分之一,贸易总额占世界的四分之一;而且,“英国商船的吨位高居各国首位。伦敦成为世界唯一的金融中心”。(18)然而,这一切只是《多佛海滩》首节中表面的甜美,其本身不能构成欢乐、爱和光明,因而不能给人民大众带来内心的满足,不能让他们全面施展自己的才能并展示自己的禀赋,也就是不能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当然,把上述一切当作进步、幸福和高品质生活的维多利亚人不在少数,他们自信满满,就像《多佛海滩》首节中的“潮水正满”。正因为如此,阿诺德要用末节中的无情潮水冲走那表面的繁荣。这潮水卷走了“多彩、美丽而新鲜”的“梦幻国度”,同时也卷走了那自欺欺人的“进步”话语。从这一角度看,“海潮”意象何尝不具有积极意义?
“海潮”意象的积极意义还由索福克勒斯这一形象得到了加强。我们在前文中已经引用以下诗行:“索福克勒斯很久以前/在爱琴海边听到的/引起他内心共鸣的人类苦难的/浑浊的潮落潮起……”此处,我们在字面上看到和听到的虽然只是“人类苦难”,但是海潮的旋律把索福克勒斯所代表的希腊精神(19)烘托到了全诗的顶点。就在阿诺德和索福克勒斯一起聆听的那一刻,时空的超越得以完成,世界的完整图景得以观照,就像尼采在谈论“悲剧文化”时所说:
这种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是,智慧取代科学成为最高目的,它不受科学的引诱干扰,以坚定的目光凝视世界的完整图景,以亲切的爱意努力把世界的永恒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来把握。(20)
除了把握痛苦以外,索福克勒斯及其希腊与悲剧精神还强烈地暗示着一种形而上的慰藉以及坚不可摧的生命和欢乐。这一点也不妨用尼采的话来说明:“每部真正的悲剧都用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之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和充满欢乐的。”(21)这生命,这欢乐,是否也奏响在海浪与索福克勒斯组成的交响曲中呢?
二、夜尽了,昼将始
“绝望论”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诗中的“夜战”意象。“夜战”的伏笔早在首节中就已埋下:“……那一条长长的浪花线/传来磨牙般的喧声。”在本文上一小节开端处所引的那几行诗句中,“退潮的咆哮”、“夜风的呼吸”和“广阔阴沉的边界”也都预示着一场“夜战”的来临。终于,在诗歌的最后三行里,“夜战”意象达到了高潮:
我们犹如处在黑暗的旷野,
斗争和逃跑构成一片混乱与惊怖,
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互相冲突。
全诗在“混乱”与“惊怖”的夜战中结束,这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印证了阿诺德的“悲观绝望”。然而,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本文上一小节的分析已经表明,《多佛海滩》的背后有一个文化批评的语境。所以诗中“夜战”的意象,也必须放在这一语境中来审视,必须结合“海潮”意象来审视,还必须结合该诗与阿诺德其他作品的互文关系来审视。
要理解“夜战”意象的含义,首先要弄明白上引诗行中“无知的军队”的意思。对此,中外评论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最典型的要数下面这一解释:“‘无知的军队’是指1848年的欧洲革命和法国军队1849年对罗马城的围攻,但是它也指意识形态的冲突。”(22)跟这种解释相比,阿姆斯特朗的解释更令人信服。她认为此处的掌故至少有二:一指修昔底德笔下的埃皮波莱战役(the battle of Epipolae),二指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于1839年的一次布道中提及的当时思想界的论战。在修昔底德所记载的那场战役中,雅典人因黑夜而分不清敌我,结果互相厮杀,不过这对《多佛海滩》来说,只起到了形容作用。跟本文所说的文化命题更加相关的是纽曼的那段话:
……论战没有在天国主人们……和邪恶势力之间进行……而是变成了一种夜战(按:黑体为笔者所加),敌友无法分辨,人人只为自己而战。(23)
令阿姆斯特朗特别感兴趣的是,纽曼此处“惊人地搬用了经济学那咄咄逼人的语言以及热衷于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者惯用的语言,来描述他所处时代的精神生活”。(24)阿姆斯特朗的观察确实非常敏锐:阿诺德笔下“无知的军队”原来是以当时走红的政治经济学(“进步”话语的一部分)为武器、狂热地从事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
值得注意的是,纽曼和他所批判的自由主义同样出现于阿诺德的另一经典之作《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
纽曼博士所看到的自由主义、这个让牛津运动折损的自由主义究竟为何物?它其实是伟大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这自由主义所信奉的基本信条,从政治上说是1832年的国会选举改革以及地方自治;在社会领域,是自由贸易,无制约的竞争,办工业发大财;在宗教上,就是“力陈异见,固守新教”。(25)
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阿诺德明确地把自由主义者称为文化的“敌人”,因为后者只专注于“办工业发大财”,这种“某一种能力过度发展,而其他能力则停滞不前的状况,不符合文化所构想的完美”。(第11页)
跟《多佛海滩》末节海潮低落和远退一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的“无知大军”及其“自由主义蔚为大观了”,而“牛津运动夭折了,败阵了,四处的海面都漂浮着我们的残骸”。(第24页)问题是:阿诺德沮丧了吗?绝望了吗?我们的回答是——
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他没有。反而,他认为牛津运动虽败犹荣:
我们对优美温雅的热爱,对丑陋粗鄙的憎恶,我们的这般情怀,才是我们靠拢许多失败了的事业、也是我们反对那么多成功了的运动的根本原因。这感情是虔诚的,它从来没有被整个地摧垮,它虽败犹荣……我们已于不知不觉中对国人的思想产生了影响,我们培育起的感情洪流冲蚀和削弱了对手们似已占领的阵地,我们保持着同未来的沟通联系。(第24-25页)
而且确信最终会取得胜利:
纽曼博士的牛津运动培育的感情洪流,这运动所滋养的追求美与雅的愿望,它所表露的对中产阶级自由主义之苛刻庸俗的反感厌恶,它那照得中产阶级新教教义的丑恶怪诞无处遁迹的强光——在引发秘密的不满大潮,从而暗中损毁30年来自信的自由主义的地基、为之突然崩塌和被取而代之铺平道路的过程中,所有这些起了多大的作用,谁可以予以评说?牛津的美与雅的情操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取胜的,而且还会继续长期地取胜!(第25页)
在《多佛海滩》中,他也没有。虽然全诗在“混乱”与“惊怖”的夜战中结束,但是海潮背后的文化洪流,是否也跟《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的“感情洪流”一样,“于不知不觉中……冲蚀和削弱了”“无知大军”“似已占领的阵地”呢?我们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多佛海滩》末节中的潮水象征着对表面繁华的冲击,对“进步”话语——也就是“无知大军”所信奉的话语——的冲击。我们前面还提到,无论从诗歌的内容来看,还是从节奏形式来看,首节和末节的互动都宛若海潮的一涨一落:首节如潮涨,末节如潮落。“无知的军队”,还有那“混乱”、“惊怖”的夜战,都将随着落潮被卷走,其中岂无深意?
诗歌中还有一个细节不能不提:全诗最后以“黑夜”(night)一词结尾——“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互相冲突”这一诗行的原文为“Where ignorant armies clash by night”。乍一看去,用“黑夜”来压轴,这好像是悲凉到了极点,然而,我们似乎可以从中读出另一层意思:night一词放在诗的尽头,难道这不意味着黑夜已经走到了尽头?
借用语言学中的概念,我们可以把“黑夜”及其所占的位置看成一种“型式化”(patterning)。它是语篇凸显的部分,是语篇前景化的部分,用以突出语篇要传达的主要信息,或者说为我们探索主题提供基础。(26)那么,“黑夜”的“型式化”究竟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信息呢?依笔者之见,它提供了积极的信息。黑夜被推向极致,这恰恰反衬了对光明的呼唤。在诗中,光明的确还未到来——“光明”(light)一词分别出现在首节和末节(我们前面已经引用了译文),第一次它微微闪动,便渐渐隐退:…on the French coast the light/Gleams and is gone…;第二次干脆以缺席的身份出现:Hath really neither joy,nor love,nor light。惟其如此,更显诗中对它的期盼。应该说,“光明”在诗中也构成了一种“型式化”,它与“黑夜”的型式化两相呼应,似乎在传递着这样的信息:黑夜到头了,光明还会远吗?由此,我们不由得会想到雪莱当年洒下的诗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在两者之间画等号——阿诺德不是雪莱那种类型的乐观主义者。在一篇专论中,阿诺德曾经称雪莱为“美丽而无效的天使,徒劳地在虚无中拍打着发光的翅膀”。(27)也许,我们可以把阿诺德划入悲观主义的范畴,但是他所信奉的至少是尼采所说的“有力量的悲观主义”。(参见本文的引言部分)这种力量来自他的执著和勇敢。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曾经把海涅跟雪莱和拜伦等人相比较,并指出海涅比后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真正地融入歌德所代表的“现代精神”(the modern spirit),即“跟非利士主义(28)展开生死搏斗”。(29)海涅也许没有像雪莱那样乐观,甚至有些悲观,但是在阿诺德的眼里,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解放战争中的勇敢战士”。(30)阿诺德之所以赞扬海涅,是因为他身处茫茫黑夜,却永不放弃对光明的追求。在《多佛海滩》中,阿诺德呼唤的也是这种精神。
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光明与黑夜之间的关系也极其相似。该书的第一章以“美好与光明”为题,其呼唤光明的热情跃然纸上,但是它同时又承认光明的缺席:“长期以来,光明无以穿越,我们头上无光,于是也就无从谈起使行动适应于光明了。”(第8-9页)不过,光明尚未来到,并不意味着不会来到。“美好与光明”的结束语借用了圣奥古斯丁的语录,来点明“夜”与“昼”之间的辩证关系:
我们不会让你独自保留创世的秘密,如你在开辟天地、分出光暗之前所做的那样;让你的放置天空的神灵之子发出光来,普照大地,分出昼与夜,宣告时光的流转;因为旧的秩序过去了,新的秩序已出现;夜尽了,昼将始;你派耕者去收获他人播种的庄稼;你派出新的耕者劳作在新的播种季节,而收获时节尚未到来;你这样做的时候,是为岁月赐大福了。(第32页)
这段话中最让人回味的是“夜尽了,昼将始”这一句。这难道不是与《多佛海滩》中的“潮落潮起”、“黑夜”与“光明”形成了呼应吗?
还须说明的是,阿诺德追求“文化之光”,但是并不过于急切。他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对“文化”和“行善的热情”作了如下区别:
行善的热情很容易过于急切……它迫不及待地要披挂上阵;这种热情又很容易将自己的构想和计划当成行动的基础,而因为这些构想是当前发展阶段的产物,故具有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不完善、不成熟之处。文化同行善的热情之区别,就在于文化既具有行善的热情,也具有科学的热情……因此即便是为了纠错解惑和排忧解难的伟大目标,它也不会急于在思考之前就采取行动、着手规划;它会牢记,如果我们不了解该做什么以及怎样做,那么行动和规划就没有多大用处。(第8页)
这也许是《多佛海滩》中没有出现“披挂上阵”的“光明战士”的原因。为此阿诺德曾备受指责,被说成“选择了逃避和哀叹”。(31)不仅如此,“阿诺德的诗歌……作为一个病态社会的病态心灵的记录,的确反映了维多利亚社会的心绪走向和发展主线。……但是,作为一个诗人,他仅仅反映这个现实,并没有试图为这个病态寻求一个良方。他把这个任务和使命推迟到了后期,推迟到了他完全放下了诗歌创作的笔之后。”(32)这种说法不那么准确。如前文所说,《多佛海滩》的潮水意味着对“进步”话语的冲击,这显然是寻求良方的努力的一部分。诗中没有匆忙披挂上阵的战士,却不乏催人深思的浪潮,这未尝不是采取行动、着手规划前的准备。阿诺德的其他不少诗歌也是如此。在《海涅之墓》中,他奉劝国人不要“整天愚蠢地奔忙,/全为那机械的商务,却让/荣誉、天赋和欢乐/逐渐从生命中消亡”。(33)在《吉卜赛学者》中,主人公虽然暂时远离尘嚣,却有一个远大的抱负,即“在学成之后,向世人传授艺术的奥秘”。(34)这一切都反映了阿诺德一以贯之的文化思想:在行动之前,先要有思想的高扬;可以不要惊天动地的业绩,却不可以不期待“在未来结出果实”。(35)
让我们再回到前面有关牛津运动的那段引文:阿诺德于失败的牛津运动中看到了一种“照得……丑恶怪诞无处遁迹的强光”,这是一种文化之光,它正在“引发秘密的不满大潮”。这强光,这大潮,是否也孕育在《多佛海滩》中呢?
潮落了,潮将起。夜尽了,昼将至。
注释:
①吴宓:《吴宓诗集》,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65页。
②钱青:《英国19世纪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179页。
③Friedrich Nietzsche,"An Attempt at Self-Criticism",in Oscar Levy,ed.,The Birth of Tagedy or Hellenism and Pessimism,The Compile Works of Friedrich Nietzsche,Vol.3,translated by WM.A.Haussmann(Edinburgh:T.N.Foulis,1910)1-19,2.
④Friedrich Nietzsche,"An Attempt at Self-Criticism",in Oscar Levy,ed.,The Birth of Tagedy or Hellenism and Pessimism,The Compile Works of Friedrich Nietzsche,Vol.3,translated by WM.A.Haussmann,2.
⑤阿诺德:《多佛海滩》,载《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飞白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4页。
⑥钱青:《英国19世纪文学史》,第179页。
⑦Warren D.Anderson,Matthew Arnold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1)70.
⑧Isobel Armstrong,Victorian Poetry:Poetry,Poetics and Polit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173.
⑨Andrew Sanders,"Writing and religion",in Joanne Shattock,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1830-191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205-221,217.
⑩Matthew Arnold,"Dover Beach",in Beverly Lawn,ed.,Literature:150 Masterpieces of Fiction,Poetry and Drama 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0)392-393,392.
(11)Richard D.Altick,Victorian People and Ideas(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and Company,1973)110-111.
(12)罗伯特·路威:《文明与野蛮》,吕叔湘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73页。
(13)A.L.Morton,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London:Lawrence & Wishart and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9)398-406.
(14)Richard D.Altick,Victorian People and Ideas,111.
(15)转引自Walter E.Houghton,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1830-1870(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39.
(16)Richard D.Altick,Victorian People and Ideas,111.
(17)Richard D.Altick,Victorian People and Ideas,238.
(18)余开祥:《西欧各国经济》,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87页。
(19)阿诺德十分推崇希腊精神(Hellenism),他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曾专辟一章来阐述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
(20)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78页。
(21)尼采:《悲剧的诞生》,第28页。
(22)钱青:《英国19世纪文学史》,第177页。
(23)转引自Isobel Armstrong,Victorian Poetry:Poetry,Poetics and Politics,175.
(24)Isobel Armstrong,Victorian Poetry:Poetry,Poetics and Politics,175
(25)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韩敏中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4页。后文凡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
(26)任绍曾:《语篇中语言型式化的意义》,载《外国语》,2000年第2期,第110-116页。
(27)Matthew Arnold,"Shelley",in S.R.Littlewood,ed.,Essays in Criticism:Second Series(London:Macmillan & Co.Limited,1951)121-147,147.
(28)阿诺德在许多作品中都用了“非利士人”(Philistines)一语来指称中产阶级,并且把后者的信念、主张和价值观统称为“非利士主义”(Philistinism)。
(29)Matthew Arnold,"Heinrich Heine",in R.H.Super,ed.,Lectures and Essays in Criticism(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2)107-111.
(30)Matthew Arnold,"Heinrich Heine",in R.H.Super,ed.,Lectures and Essays in Criticism,107.
(31)钱青:《英国19世纪文学史》,第180页。
(32)钱青:《英国19世纪文学史》,第181页。
(33)Matthew Arnold,"Heine's Grave",in Kenneth Allott,ed.,The Poems of Matthew Arnold(London:Longmans,1965)472-473.
(34)Matthew Arnold,"The Scholar-Gipsy",in Kenneth Allott,ed.,The Poems of Matthew Arnold,339.
(35)刘意青:《评阿诺德“去个人好恶”的文学批评原则》,载《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11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