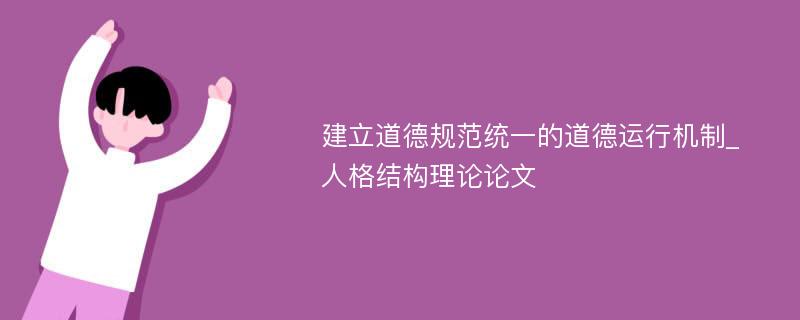
建立德性与规范相统一的道德运行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性论文,运行机制论文,相统一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德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方面,它同时又与道德行为相联系:道德教育总是以行为为指向,并通过道德行为而得到具体的落实和确证。这里,主要从德性与规范的相互关系上,对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教育及道德行为机制作一考察。
道德行为在本于德性的同时,又受到普遍规范的制约。德性以主体为承担者,并相应地首先涉及人的存在;相形之下,规范并非定格于主体;作为普遍的行为准则,它更多地具有外在并超越特定主体的特点。然而,尽管德性与规范各自呈现出和主体存在的不同关系,但二者并非彼此悬隔。
德性往往以人格为其整体的存在形态。历史地看,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都存在着理想的人格典范。从中国古代的圣人(尧、舜、禹等等),到古希腊史诗中的英雄(俄底修斯、赫克托耳等等),都曾被视为理想的人格范型。这些理想的人格尽管常常与神话传说等等纠缠在一起,但同时又汇聚了多方面的道德品格,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德性的化身。作为德性的具体化,理想的人格首先折射了一定时期的历史需要,尧以禅让(让位于既贤且德的舜而非传位于尧之子)展示了重天下甚于重一家的群体关怀意识,而群体关怀则是维系社会稳定和有序化所必需的;禹在传说的治水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则反映了与天奋斗、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所必需具备的品格。同样,古希腊史诗中的英雄所表现出来的勇猛无畏,也体现了在氏族部落之间战争频繁的历史时期,骁勇善战、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已成为生存的重要精神因素。略去其中渗入的神话传说成分,我们不难看到历史中的理想人格与历史需要本身之间的联系;不妨说,理想人格内含的德性,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历史的选择:正是合乎历史需要的主体品格,在历史演进过程不断得到确认和肯定,并逐渐凝结、汇凑于历史中的理想人格。
德性在理想人格中的具体化,从一个方面为规范的形成提供了前提。规范既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需要,又体现了普遍的道德理想;这种理想以现实的社会存在为根据,同时又在圣人、英雄等理想人格中取得了具体的形态。相对于比较自觉的观念系统,与人的具体存在融合为一的理想人格似乎具有某种本体论的优先性:在抽象的行为规范出现以前,理想的人格往往已作为历史中的现实而存在;规范系统本身在一定意义亦以历史中的理想人格为其重要的本源。事实上,理想的人格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完美的存在范型,这种范型对一般的社会成员具有定向与范导的意义,观念化的规范系统在相当程度上亦可理解为对这种范型的概括、提升。埃尔德曼认为,“品格的善在逻辑上更为基本”,“在道德生活中,规则是后起的。”(H Alderman:By Virtue of Virtue,Virtue Ethics)这一看法似乎已有见于此。
当然,对德性在现实人格中体现出来的本源性,不能作片面的理解。从人的存在在历史中的优先性来考察,作为德性统一形态的人格确乎具有本源或基础的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德性完全超然于规范。历史地看,社会发展的每一时期往往存在着与该时期的社会状况相适应的行为规范,这些规范最初也许不一定取得系统的、自觉的形态,而更多地表现为某种风俗、习惯、礼仪、禁忌等等,但它在一定时期却作为影响人们行为的实际制约因素而起着规范或准规范的作用。文明早期的理想人格固然作为历史中的现实存在而为规范提供了依据,但他们本身亦受到了当时价值原则及体现这种价值原则的社会风尚的影响,古希腊英雄的无畏精神,多少折射了当时尚武的社会价值取向;传说中的禹在治水时的自我献身品格,则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对有限的时期,集体力量及集体价值的优先性。事实上,历史中的理想人格取得如此这般的形态,也包含了某种塑造或再创造的作用:人们往往是根据自己所理解的价值原则及与之一致的规范,确认或突出理想人格的德性;在理想人格之后总是可以看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价值取向及相应的规范原则。不管是就其本然形态而言,还是从它被塑造或再创造这一面看,历史中的理想人格都难以和一定的规范系统截然相分。
综而论之,德性通过凝化为人格而构成了规范的现实根据之一,规范则从社会价值趋向等方面制约着理想人格的形成与塑造,二者呈现为某种互为前提的关系。如果仅仅从静态的观点看,往往容易引出单向决定的结论,惟有着眼于历史过程,才能把握二者的真实关系:正是在历史实践的过程中,德性与规范展开为一种互动关系并不断达到具体的统一。
以上所涉及的,主要是德性与规范关系的历史之维。从逻辑的层面看,规范作为普遍的行为准则,总是超越于具体的个体,而道德行为则以个体为承担者,如何使普遍的规范化为个体的具体行为?这一问题涉及了德性与规范更内在的关系。
道德实践中的为善避恶,以善恶的分辨为逻辑前提,而善恶的分辨则表现为一个道德认识(知)的过程。道德认识意义上的“知”,虽然不同于事实的认知,但就其以善恶的分辨、人伦关系的把握、规范的理解等为内容而言,似乎亦近于对“是什么”的探讨:以善恶之知而言,知善知恶所解决的,仍不外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问题。从逻辑上看,关于是什么的认识,与应当做什么的行为要求之间,并不存在蕴含的关系。如所周知,休谟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仅仅从“是”之中,难以推出“应当”。休谟由此将事实认知与价值评价截然分离,无疑有其问题,因为在善的认定中,也已包含了认知的内容。不过,即使以价值确认而言,它固然通过肯定什么是善而为行为的规范提供了根据,但懂得什么是善并不意味着作出行善的承诺:在知其善与行其善之间,存在着某种逻辑的距离。
规范内含着应当,以善的认定为根据,规范无疑涉及善恶的分辨:在肯定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的同时,它也确认了何者为善,何者为恶。然而,规范作为普遍的当然之则,总是具有超越并外在于个体的一面,它固然神圣而崇高,但在外在的形态下,却未必能为个体所自觉接受,并化为个体的具体行为。同时,规范作为普遍的律令,对个体来说往往具有他律的特点,仅仅以规范来约束个体,也使行为难以完全避免他律性。
如何由知其善走向行其善?如果换一种提问的方式, 也就是:如何担保普遍的规范在道德实践中的有效性?这里无疑应当对德性予以特别的关注。个体的社会化往往伴随着化天性为德性的过程,德性从一个方面使人由自然意义上的存在,成为社会的存在,并进而提升为道德的主体。规范作为普遍的律令,具有无人格的特点,相对于此,德性更多地体现于个体的内在品格。作为内在的道德品格,德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规范的内化。通过环境的影响、教育的引导,以及理性的体认、情感的认同和自愿的接受,外在的规范逐渐融合于自我的内在道德意识,后者又在道德实践中凝而为稳定的德性。与规范主要表现为社会对个体的外在要求有所不同,德性在行为中往往具体化为个体自身道德意识的内在呼唤。较之规范,德性与个体的存在有着更为切近的联系:它作为知情意的统一而凝化于自我的人格,并在本质上呈现为个体存在的内在形态。当行为出于德性时,个体并不表现为对外在社会要求的被动遵从,而是展示为自身的一种存在方式。在德性的形式下,知当然与行当然开始相互接近:作为同一主体的不同存在形态,知当然与行当然获得了内在的统一性。
从规范与行为者的关系看,规范在形式上表现为“你应当”(You ought to)之类的社会约束。相对于此,德性则首先以“我应当”(I ought to)为约束的形式。对行为者来说,“你应当”似乎呈现为某种外在的命令,“我应当”则源于行为者的自我要求,后者乃是基于向善的意愿、善恶的辨析与认定、好善恶恶的情感认同等精神定势,它可以看作是内在德性结构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你应当”的形式下,行为者是被要求、被作用的对象,在“我应当”的形式下,行为者则呈现为主体。仅仅停留在“你应当”之类的命令关系中,行为显然很难完全摆脱他律的性质,惟有化“你应当”为“我应当”,才能扬弃行为的他律性,并进而走向自律的道德。(注:需要指出的是,超越“你应当”,并不意味着消解规范的作用,毋宁说,它所侧重的是规范作用方式的转换。事实上,在“我应当”的自我要求形式中,同样蕴含着规范的制约。详见后文。)
通过化外在规范为内在德性,普遍规范在道德实践中的有效性,显然也获得了某种担保。康德曾指出,德性是一种抑制非道德因素的坚韧力量,其意义之一在于控制各种感性的倾向(inclination)。[1](pp.38、49—50) 所谓抑制非道德的因素,意味着排除各种干扰,使道德律能够更自觉地得到贯彻。康德的这一思想体现了其注重义务及理性原则的倾向。尽管如前所述,康德对德性的理解存在着某种超验化的趋向,但以上看法同时亦从一个侧面注意到了德性在担保规范有效运作方面的作用。康德在伦理学史上以坚持义务论立场而著称,他对德性作用的肯定,既表现了哲学家思想的复杂性,也从一个方面表明德性对道德实践的不可或缺性:即使义务论者,也无法完全忽视德性的作用。
从逻辑上看,行为者对道德规范的遵循,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他具有追求善或认同善的趋向,换言之,他愿意并选择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种向善的取向,可以看作是行为者的内在承诺;惟有作出了这种承诺,道德规范才对他具有约束力。对一个无向善意愿、与社会为敌的个体来说,由于缺乏向善的自我承诺,道德规范对他便没有任何意义,他绝不会因行为不合乎规范而感到内疚或自我谴责。当P·福特肯定道德也具有假言命令的意义时,她似乎已注意到这一关系。[2] 在引申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就规范的遵循要以向善的承诺为前提而言,道德系统呈现某种假言的性质,其逻辑形式可以概括为:如果你选择或承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那么,你就应当遵循道德的规范。按其实质,向善的取向体现的是德性所内含的精神定势,从而,德性的形成亦相应地构成了规范得以确认和贯彻的逻辑前提。
当然,肯定德性为规范提供现实的担保,并不意味着否定规范本身的一般制约作用。德性作为统一的精神结构,总是包含着普遍性的规定,这种规定显然难以离开对规范的自觉认同。事实上,德性的形成过程,往往与按规范塑造自我的过程相联系;一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规范体系,既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也影响着人格的取向。李觏曾指出:“导民以学,节民以礼,而性成矣。”[3](p.66) 礼既有制度之意,又泛指一般的规范;性则指与天性相对的德性。“导民以学,节民以礼”,意味着引导人们自觉地接受、认同普遍的规范,并以此约束自己;“性成”则是由此而使天性提升到德性。张载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强调“凡未成性,须礼以持之”,[4](p.264)“故知礼成性而道义出”[4](p.37)。这里所肯定的,亦为“知礼”(把握规范系统)与成性(从天性到德性的转换)之间的统一性。对规范的这种认同,同时亦有助于避免德性向自我中心的衍化。亚里士多德曾把公正与合乎法(lawful)联系起来,而公正又被理解为“一种完全的德性”,从而,公正与合乎法(lawful)的沟通,也意味着德性与法的联系。[5]“法”是一种强制性的规范,尽管它不同于道德律,但在规范性上,与道德领域的当然之则又有相通之处;而以“法”来解释德性,则从一个方面确认了德性与规范之间的联系。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史上被视为德性论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对德性与规范的沟通,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在理论上的多向度性,但同时亦表明德性与规范并非简单地相互排斥。
广而言之,社会的凝聚和秩序的维系需要一般的规范,行为要达到最低限度的正当性,也离不开普遍的当然之则。一般的规范既对行为具有普遍的范导意义,又为行为的评价提供了基本的准则,它在道德实践中往往更接近可操作的层面,因而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德性的形成总是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相对于明其规范,成其德性似乎是一种更高的要求;就行为而言,较之对规范的依循,出乎德性也无疑是一种更不易达到的境界。由此而视之,遵循规范似乎应当成为基本的、初始的要求。不过,无论从个体抑或社会的角度看,停留于依循外在规范这样一个“底线”的层面显然是不够的,这不仅在于仅此难以达到完善的道德关系,而且如前所述,当规范仅仅以外在的形式存在时,其现实的作用本身往往缺乏内在的担保。总之,行为的普遍指向与评价的普遍准则离不开一般的规范,而规范的现实有效性又与德性联系在一起。
德性与规范的统一,在规范与德性的一致中也得到了具体的展现。从历史上看,传统的规范与传统的德性往往存在着某种对应性,以儒家而言,其核心的道德理念具体表现为仁、义、礼、智、信等等,作为行为的要求、评价的准则,这些道德理念无疑具有规范的意义;所谓“为仁”、“行义”,即意味着在实践过程遵循仁、义的原则。但在儒家的道德系统中,仁、义等等同时又被理解为内在的德性和品格,所谓“仁者”,便是指具有“仁”这种德性或品格的主体。在“仁”的规范下,通过“为仁”的道德实践逐渐形成内在的德性,又以“仁”的德性为根据而展开为善去恶的道德工夫;在实践的过程中,作为规范的“仁”与作为德性的“仁”融合为一。同样,在西方伦理传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正义,也既表现为普遍的规范,又是主体的美德。
从性质上看,德性总是包含着善的倾向,无论是具体的德性,抑或整体的人格,德性都表现出向善的定势。以仁而言,具有“仁”的品格,意味着将他人视为目的,以仁爱的精神对待他人。这种向善的定势无疑显示了正面的价值意义。然而,内含善的趋向,还只是表明具有走向善的可能,它并不意味着达到现实的善。在某些情况下,德性的具体规定往往亦有导向负面结果的可能。如“仁”本来具有善的向度,但如果以“仁”的精神对待危害社会、与人民为敌者,则很难真正视为善举。要使善的趋向化为善的现实,避免德性的异化,便既应肯定德性的整体性,注重行善趋向与知善过程(包括善恶分辨、情景分析等等)的统一,也应肯定社会规范的指导、调节意义,以普遍的原则引导德性的作用方向。这里同样展示了德性与规范之间的相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