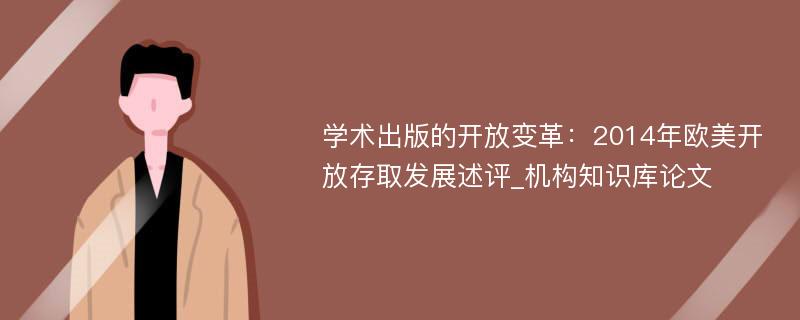
学术出版的开放变局:2014年欧美开放获取发展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局论文,学术论文,欧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强制性开放获取政策(Open Access Mandates)被西方主流科研机构广泛采用,学术内容的开放交流成为大势所趋。在总共1.14亿在线英文学术文献中,已有超过2700万是开放获取(Open Access,简称OA)的,占24%[1];据估计,到2016年,将有超过一半的学术论文实现OA。可以说,学术出版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开放变局。2014年,无论出版商主导的OA期刊出版,还是图书馆学术机构主导的开放知识库,都在积极进行创新探索。新学术出版模式与OA平台层出不穷,各方深层合作整合日益普遍,在权利结构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也日趋激烈。虽然从政策层面讲,开放获取已成为科研群体与政府的共识,但在学术出版实践中,仍然充满阻力和不确定性。人人都知道OA好,问题是怎样实现它——这是目前欧美OA转型现状的真实写照。 如何实现学术出版产业的开放转型?如何建立基于开放内容的新商业模式?如何确保学术传播体系的可持续性?如何平衡出版商、学者、图书馆、科研机构和公众的利益?围绕上述议题,本文从开放获取政策、OA期刊出版和开放机构知识库三个方面对2014年欧美发展动态进行梳理,并针对我国学术出版现状提出相关建议。 1 开放获取政策:知识开放是大势所趋 开放获取的目的,是让经过同行评议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通过互联网对每一个读者免费开放,并允许读者非营利性使用,甚至重新演绎。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学术传播中,OA论文具有引用优势(citation advantages),即获得比同类非OA论文更多的引用;此外,OA论文在教育、科普、公共政策等方面也更具应用潜力与影响力。目前,全球大部分有影响的研究型大学,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国的国家科研基金以及一部分私人科研基金,都已采用强制性开放获取政策,要求其资助的学术研究所发表的出版物对公众免费开放。2014年,强制性OA政策的涵盖领域更广,规定更细化,强制力度也更强。开放获取时滞(embargo period)成为政策焦点之一。通常OA政策允许12个月的开放获取时滞,以确保期刊出版商的订阅市场和商业利益,但这却造成了学术成果传播的滞后。2014年世界多个著名学术团体联合签署声明,要求取消OA时滞,实现学术论文的立即开放获取。签名机构包括学术出版与学术资源联盟(SPARC)、欧洲学术图书馆协会(LIBER)、开放获取知识库联盟(COAR)以及中国国家科学图书馆,等等。盖茨基金会近日也宣布,自2017年起,对其资助研究所发表的论文,不再允许12个月的开放获取时滞。 现行科研评估体系以期刊论文为基础,尤其依赖出版商建立的引证计量体系,比如引用率和期刊影响因子。这一评估体系为学术出版产业提供了政策红利;但是,单纯以引用率来衡量学术研究影响力的方法一直饱受争议,其局限性在OA时代越发明显。改革学术评估体系的呼声在欧美变得越来越强,新举措也不断推出。比如,英国研究委员会要求基金申请者提供构建“多元影响力”的方案,以“确保研究的潜在受益人有机会获益”。多元影响力包括对相关群体、社会大众和公共政策的影响,而不仅仅是论文引用率。澳洲医学研究委员会(NHMRC)2014年4月发表了一份声明,更直白地表述了科研基金对研究成果评估的改革思路:评估优先权要从期刊影响因子转向单篇论文的引用数,甚至替代计量指标(altmetrics)①;科研成果不但包括期刊论文,还有其他学术传播方式,比如报告、多媒体作品等。客观讲,上述政策革新尚不足以撼动现行评估体系的主导地位。不过,这些改革举措以及新型学术影响力计量指标的发展,会使学术评估走向更多元化的时代。这有助于建立可持续性的OA学术出版生态。 开放科学是欧美科研政策的新焦点。欧盟推出了雄心勃勃的Horizon 2020规划,计划投入800亿欧元预算,打造基于数字开放理念的科研创新体系。开放数据是当下热点,欧盟已经要求其资助科研项目的研究数据对公众开放;一些世界级的学术机构,比如欧洲核子研究理事会(CERN)开始构建开放数据存储库;学术出版商如PLoS和Nature也开始尝试科研试验数据出版。无论开放科学,还是OA政策,都将青年一代研究者视为未来主导力量。比如,欧盟推出了FOSTER②项目,旨在对欧洲青年学者进行开放获取、开放数据和开放科学的培训;2014年国际开放获取周以“开放一代”为主题。年轻一代学者成长于开放网络环境,在Facebook、Google、Twitter等熏陶下长大,心里更认同开放理念。虽然现行商业出版和评估体系会造成短期障碍,年轻一代还是拥有巨大潜力与能量去推动转型,实践和推广开放科学与新型学术传播。总体讲,开放获取政策反映了欧美学界、科研基金和政府的共识,正成为学术出版产业变革与转型的推动力量。 2 学术出版产业的开放转型 开放获取在欧美一直有“金色”和“绿色”两大路径。简单讲,“金色”OA指由出版商主导的、通过各类OA期刊来实现学术内容免费开放的路径。自然、施普林格、威利、爱思唯尔和泰勒·弗兰西斯等传统学术出版巨头是“金色”OA的主导力量之一。它们在OA领域早有布局,也都形成了一定规模。施普林格是目前OA出版收入排行第一的实体,到2014年为止,施普林格通过旗下的两大OA平台BioMed Central和Springer Open总共发表了20万篇OA论文[2]。施普林格最近宣布,对其出版的OA内容采用知识共享(CC-BY-NC)授权模式,这比传统版权更符合数字出版和开放科学的大环境。 对出版巨头而言,OA收入所占比重仅在10%左右,其商业体系仍然依赖付费订阅。顶级学术期刊对OA态度多比较谨慎,一般采用混合(Hybrid)模式试水:一方面保持付费内容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允许少部分文章通过作者付费实现开放获取。2014年底自然出版集团启动的一项OA试验颇具突破性——读者可以使用readcube软件免费在线阅读包括《自然遗传》《自然医学》等在内的48种期刊的论文全文,但不能下载、复制和打印。自然出版集团希望通过这种有限开放获取,一方面保持对机构订阅市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最大限度扩大论文的读者、提高引用率。对大牌期刊来说,由于较高的质量和声誉,其订阅市场和稿源一直非常稳定;但长远来说,由于OA的引用优势,封闭内容对学术期刊而言等同自杀——这会减少引用、降低期刊影响因子,最终损害期刊的声誉和订阅市场。这是《自然》尝试有限OA的原因所在,估计其他几家顶尖学术出版商也会效法。 在线平台和新型期刊是学术出版巨头的主要OA试验田。《自然》在2014年将旗下的在线期刊平台Nature Communications转换为完全OA,停用付费内容模式;Palgrave在年初上线了类似的Palgrave Communications平台,同样靠收取作者出版费运营。2014年,新OA期刊创刊的消息不绝于耳,这些依靠知名品牌创办的新期刊多面向新兴研究领域和交叉学科,成为不折不扣的新市场开拓者和新模式试验者。此外,对原有付费期刊进行开放转型也是策略之一。2014年,爱思唯尔有7种知名刊物宣布转型为OA,De Gruyter Open转换了8种付费期刊,并在OA后扩大出版规模,打造大型OA在线期刊(mega journals)。随着OA期刊数量的增长,出版巨头正在依托传统品牌优势构建OA期刊群。目前以期刊群形式上线的Sage Open、Routledge Open等充分发挥了出版巨头的规模优势,OA内容与付费内容共存于一个数据平台,读者不但可以阅读高质量的OA论文,同时可以使用各种信息服务,这为读者带来便利,也为出版商平台带来流量、用户和商业机遇。 以PLoS和PeerJ为代表的在线OA出版商是另外一大势力。这些数字在线平台在OA领域一直风光无限——引领创新潮流,尽享新市场带来的商业利益。相比传统出版巨头,这些在线OA平台在产业进化中扮演着颠覆性创新者的角色。从PloS ONE的轻触同行评议(Light Touch Peer Review)到Peer J的99美元终身OA出版套餐,都为学术出版产业引入了新思路,开拓了新市场,也解决了一些结构性问题。但是近几年,这些OA数字先行者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随着传统出版巨头入局以及大量新OA期刊的兴起,PLoS的竞争优势在减弱。2013年PLoS影响因子下滑;2014年上半年,PLoS刊文数量首次出现了20%的大幅下降,按照其单篇出版费计算,PLoS收入减少了近100万美元[3]。这些产业信号预示着OA出版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欧美学术出版产业的行业集中度很高,但仍有大量的中小规模出版机构活跃在各学科领域,尤其是学术协会(Learned Society)期刊。汹涌而来的OA浪潮,日益成为出版巨头、顶级大学和科研基金的博弈游戏,将中小学术出版商置于尴尬困境。2014年发表在Scholarly Kitchen的一篇博客文章,道出了学术协会期刊的潜在危机。多数欧美学术协会在经济上依靠期刊订阅收入和会员费,尤其以期刊订阅收入为主要来源。OA理念无疑是学界共识,但OA实现路径应该多元,不能一刀切(即西方所言的one size fits all)。目前强制性OA政策把这些依赖订阅收入的中小期刊置于两难窘境:要么收取高昂OA出版费,要么难以为继。 近几年大量涌现的OA新期刊正成为另一大势力,尤其是由学者和学术机构兴办的新刊物。在欧美,学术期刊出版手续极为简单,开源软件的技术支持也比较完善,OA浪潮激发了很多学者的办刊热情,这些因素使在线OA新期刊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增长。开放获取期刊数据库DOAJ已总共收录了超过1万种OA期刊——这仅仅是经过质量审核筛选的期刊数;仅2014年3月至8月期间,DOAJ就新增187种OA期刊,另有140个申请因材料不足等原因遭拒[4]——OA期刊的增长速度可见一斑。 这些“草根”OA新期刊为过度商业化、体制僵化的学术出版业注入了创新元素和活力。正如一位学者在博客中写道:“我们相信,一个学者设计、图书馆支持、坚持原则并可持续发展的OA出版模式能够建立起来。”[5]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的学术评估机构,对高水平OA新期刊持积极支持的态度。澳大利亚2015年研究绩效评估(ERA)的期刊数据库中,增添了很多OA新期刊,大部分甚至还没有影响因子或引证数据。这无疑有助于新学术出版模式的健康成长。大量中小OA期刊的出现,也使数字内容整合成为产业创新点。创业企业Paperity适时推出了跨学科的OA期刊论文整合服务,提供一站式的、实时更新的OA文献搜索接入平台。这类平台可能会成为OA时代的内容入口。 总体来看,“金色”OA的商业模式仍依赖作者支付OA出版费(Article Process Charges,APC)。虽然学术机构出版的OA期刊在努力降低出版费,但商业出版商正在把OA变为新的摇钱树。目前高价OA期刊每篇文章平均收费超过5 000美元[6]。《自然》主编Campbell称,如果《自然》《科学》和《细胞》这样的顶级期刊开始收取OA出版费,那么每篇至少要1万美元[7]。英国是为数不多的、选择“金色”路径实现OA转型的国家。一项基于23家英国学术机构的调查显示,截至2014年3月,这些机构总共为5 142篇论文支付了超过8 600万英镑的OA出版费,平均每篇1 673英镑[8];著名科研基金Wellcome Trust在2012-2013年度为2 126篇文章支付了390万英镑的OA费用,平均每篇1 821英镑[9]。这给很多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造成了预算难题:一方面期刊订阅费用没有显著减少;另一方面,学者的OA出版费支出日渐增加。有人戏言,OA之前,有人穷得读不起好文章;实行“金色”OA后,有人穷得发不起文章。 OA期刊出版的另一个问题是质量下滑及低质期刊泛滥。为了与传统期刊竞争,OA新期刊往往承诺更快的出版速度和更宽松的同行评议。比如,欧洲呼吸研究协会与斯坦福大学High Wire出版社今年新推出了OA期刊,其编辑思路强调:“在编辑把关和同行评议中,本刊只注重研究方法、数据采集和整体逻辑的严谨合理,不会对文章学术价值和影响力作主观判断,并以此拒稿——这些应该留待读者去决定。”该刊还承诺在接受稿件后3星期内出版。这些举措虽有革新之意,却不禁让人对质量担忧。2014年先后有多起OA质量丑闻被曝光。比如,哈佛大学的科学记者John Bohannon将一篇伪劣论文投稿于OA期刊,有157家接受出版。自然出版集团对一些经过同行评议的学术会议论文集进行质量抽查,发现122篇造假论文被堂而皇之地出版。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存在质量问题的OA出版物很多甚至来自于学术出版巨头。2014年开放获取出版协会(OASPA)因此重新审核Sage和Springer的会员资格。当然,正如Richard Stone所言,这种“钓鱼”试验,放在传统期刊恐怕会得到类似的结果。随着论文出版量迅猛增长,学术出版资源——尤其是专家审稿人的数量——难以维系高水平的同行评议。这是目前整个学术出版体系面临的问题[10]。 3 开放机构知识库的升级与整合 与出版商主导的“金色”OA并存的,是由学术机构、图书馆以及学者主导的“绿色”OA——科研人员依然在传统(付费内容)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但是将经过同行评议的终稿上传于各种机构知识库,供读者免费阅读。“绿色”OA的初衷,是在不改变现行学术期刊订阅模式的前提下,通过学者自存储实现研究成果的开放获取。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成本较低;同时,依然保持出版商为读者服务的商业模式,避免出版商为赚OA出版费而降低质量。据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已公布OA政策的国家中,48个选择了通过机构知识库——也就是“绿色”路径——来实现开放获取;14个介于二者之间;只有英国明确选择了“金色”路径,但英国政府也作了政策修订。这种压倒性的政策支持,极大促进了机构知识库在西方的发展。根据OpenDOAR的数据,全球机构库的数量从2006年的300多家,猛增到目前超过2 700家——这仅是具有质量保障的正规机构库的数量。机构知识库的内容资源不仅包括OA学术论文,还有研究数据、教学资料、会议演讲、多媒体素材等。很多机构库的职能已超越资源平台,逐步发展为网络开放出版平台;很多大学甚至把机构库作为推广大学品牌、进行高等教育市场营销的工具。 近几年,西方机构知识库发展重点已从扩大资源规模转向提升资源整合能力和使用效率。一直以来,各大学科研机构的知识库各自为战,造成“绿色”OA资源分布分散,多数呈信息孤岛状态。另一方面,由于资金投入和技术实力局限,机构知识库缺乏类似商业数据库的信息服务,这不但给读者造成不便,也降低了学者上传分享文献的效率。欧美机构库正在从多方入手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比如,增强不同机构库之间基于API的互操作,加强与机构内研究教学管理系统(RMS和LMS)的整合,实现与文献及学者信息识别系统(比如ORCID和DOI)的信息共享,利用数据文本挖掘等技术提升检索效率,以及构建知识社群,等等。 美国OA体系有两大主导势力:以出版商联盟为基础的CHORUS和美国科研图书馆协会领导的SHARE。2014年SHARE的年度发展计划中,提出了“机构知识库生态”的概念,并推出了一个具体实施项目——主要内容包括OA资源注册、OA资源发现和内容整合3大部分。该项目试图实现对机构库OA资源网络传播的系统追踪,以提升用户搜索学术资源的效率,提升机构库OA内容的可见度,并计量其影响力。与此同时,通过深度内容整合和机构库互操作,增强信息服务能力。另一个OA资源整合的例子则从“小”方面入手,通过提升学者个人的开放资源使用效率,来促进OA发展——它是一群大学生在2013年底创立的“开放获取按钮”(Open Access Button)。读者如果发现一篇感兴趣的付费论文,可以通过“开放获取按钮”,在谷歌学者、OA期刊平台、机构库和各种社交媒体中搜索该论文可能存在的OA版本。在2014年国际开放获取周期间,“开放获取按钮”推出了升级版,并借机向全世界推广。其独创性的用户界面和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获得广泛好评,成为备受关注的OA新兴力量。 出版巨头培生曾放出豪言“出版商就是教育者”(publisher as educator)。今天,开放机构知识库的迅猛发展让教育科研机构有机会成为“开放出版商”。这一发展趋势,一方面将给学术出版产业带来巨大创新空间和活力,也将强烈冲击传统学术出版生态,甚至可能边缘化商业出版在学术传播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机构知识库与出版商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合作共赢空间。二者是竞合关系,而且合作实践正在升级:比如,一些出版商允许作者在OA时滞期后,将论文的正式版本(record version)存储于机构库——以往作者只能在机构库发布未经编辑加工的终稿(accepted manuscript);很多机构库也开始设立出版商数据库链接,将处于OA时滞期、暂时无法免费阅读的论文链入付费页面。 4 结语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开放获取在欧美已经从理想主义新方案演进为学术传播实践的主导模式之一。虽不乏颠覆创新和争论博弈,总体上讲,开放获取所引领的是学术出版改良(evolution),而不是革命(revolution)。欧美出版商、图书馆、学界、科研机构与政府一直在寻求协作共赢以及最具效率的OA转型路径。2014年的OA实践创新体现了这种务实精神。很多欧美经验模式值得中国OA界研究借鉴。 中国中科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2014年发布了类似欧美的强制性OA政策,这是中国OA发展的里程碑。但是学界、出版业、政府和公众达成广泛共识尚需时日,在实践中大规模实现OA仍不乏阻力。中国学术出版业长期以来受益于垄断体制和政策红利(尤其是论文导向的学术评价政策),坐享稳定丰厚的经济收益。但在全球出版业数字升级、知识走向开放交流的大环境下,中国学术出版面临着比欧美更严峻的转型挑战。开放转型的成败不但事关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也直接关系到国内学术出版市场的份额——多数国内一流研究成果已不在中文期刊发表论文。中国是世界上公共科研基金投入最多的国家之一,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向知识型、创新型经济转型。开放获取和开放知识所带来的科研活力、科研透明度以及公众科学参与至关重要。中国学术出版界需要了解欧美OA的发展,积极融入全球学术出版体系,发现差距,寻找机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升国内出版业的运营能力,以面对数字化、全球化和开放化的新型知识环境。 ①altmetrics,通过对学术论文的下载次数、社交媒体转载次数、个人图书馆保存次数等非引用率指标,来计量单篇学术论文的影响力。 ②英文名称为:Facilitate Open Science Training for European Research,FO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