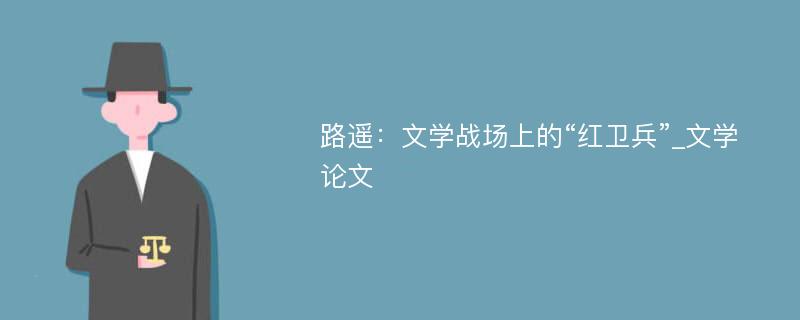
路遥:文学战场上的“红卫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卫兵论文,路遥论文,战场上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7)02-0012-09
1992年,路遥突然撒手人间,把自己塑造成一位视文学为生命、呕心沥血、英年早逝的伟大作家,获得了人们的巨大崇敬和高度赞叹,也在无形之中提高了其作品的地位和价值。十多年过去了,为文学呕心沥血、励精图治的路遥形象一直遮蔽着我们去更深入地探索路遥的创作心理、人生经历及其性格中的某些缺陷,似乎如果我们揭示了路遥其人其文的某些缺陷就是对这位以生命换来文学的作家的不恭、不敬。我非常尊敬路遥,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接触路遥的作品时就被他的作品深深打动,然而,当我重新阅读路遥的作品时,竟发现自己的阅读感受和十多年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感动我的、让我心痛的那些苦难、艰辛、崇高、伟大、英雄气概、受难精神竟引起了我的一丝反感,并由此心生警惕,从中读出了作者的某种矫情、夸张、偏执和狂热。这种差异,使我产生了重读路遥所有作品的愿望,想从中找出路遥其人其文中所隐藏的至今还秘而未揭的某种东西。
路遥的身份无疑是复杂的:知青、农民、红卫兵。他是知青,但是很少有人把他看作知青作家,因为他是回乡知青,回乡知青在身份上其实是农民,不过多读了几年书而已;在1966年到1969年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他是延川县红极一时的红卫兵头头,靠着横扫千军的勇谋夺到了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职位。在对路遥的研究中,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到路遥作为“农民”或者“农民的儿子”这一身份对创作的影响,而忽视了红卫兵这一身份对路遥精神气质和文学创作的重大影响。而路遥本人,对自己的红卫兵身份也讳莫如深,他几乎从未提及这段时期的经历①。与此对照的是,路遥极力张扬自己作为“陕北农民的儿子”这一身份。一扬一抑、彰显与回避,其中是否包含着路遥某种程度上的掩饰呢?抑或他主观上觉得造反经历应该彻底抛弃?
(一)“红卫兵”经历与选择文学的无奈
1966年,原名王卫国的路遥在延川中学初中毕业,由于“文革”的爆发,升学毫无指望,惟一的出路只能是回乡当个农民。但是对于农村青年来说,回乡务农是痛苦的选择,尤其是对路遥这么赤贫的家庭。为了读书七岁离开亲生父母过继给他人,养母靠着乞讨供养他上中学,这一切当然是希望路遥能够谋得一个公家人的身份,脱离农村进入城镇。就像《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路遥极度不愿意回到土地上务农。但是突然,时代为路遥提供了一条比读书升学更加快捷、轻松的道路,只要敢于造反,敢于冲锋陷阵,就可以前途无量。于是,路遥狂热地投入到滚滚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在中学时代,路遥是一位特别的、有才能的学生,但是算不上好学生。他的功课平平,不但对数理化不感兴趣,语文功课也并不认真学习,倒是热衷于到县文化馆看报纸,热衷于国家政治、时事新闻。由于班主任偏爱他在作文、讲演方面的才能,因此对他比较宽容[1]。“文革”开始后,路遥在讲演、作文方面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助他在“文革”中一举成名。“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他满怀激情地投入了那场史无前例的造反斗争,上大会,念批判稿,博得阵阵掌声;登高墙,贴大字报,引来簇簇观众;挥拳头,高呼口号,‘九种人’闻风丧胆。他以‘王天笑’的笔名,着意写过一些引起轰动的大字报和大批判文章,同学们自愧弗如,终于熬成本班红卫兵组织‘井冈山’的山大王。延川中学师生分化成两大派,他又以出众的组织能力一跃而为本派的首领,全县革命群众分裂为两大阵营,他又扶摇直上,被推举为本阵营的领袖,晋升为‘军长’。”[2] 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初中生一步步走上全县红卫兵头头,既需要组织、演讲、写作多方面的才能,也需要勇猛、狂热、强烈的造反精神。也许路遥在“文革”中的狂热是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但是谋取个人的功利可能是更大的驱动力。张志忠在分析近年文艺作品中的红卫兵形象时,精辟地指出:“我们都习惯于认定红卫兵运动的参加者,是一群纯洁而天真的青少年,是出于无私忘我的革命激情,而投身于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但是,在阅读中,却常常让我感到,‘文革’初期对立的学生和红卫兵们,在看似冠冕堂皇的革命动机后面,是有着利益驱动原则的”,这种利益既包括物质上的实际获得,也包括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理优势[3]。
根据《延川县志》[4] 的记载,“文革”期间延川县红卫兵组织之间的派系斗争非常激烈。从“文革”开始到1966年年底,全县一共建立了一千多个红卫兵组织,遍及全县各城镇、乡村。到1967年上半年,大辩论逐渐使观点相同、意见相投的队与队互相联合,形成观点相异的两大派系,“延川地区毛泽东思想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延总司”或“司令部”)与“延川县红色造反第四野战军”(简称“红四野”或“四野”)。随着两派意见的分歧,矛盾激化,两派由唇枪舌剑,发展到拳头砖头相击,继而开始荷枪实弹的“武斗”。路遥正是“红四野”的头头,带领着“红四野”武斗队的12个支队,先后和“延总司”进行了9次派性斗争,并组织了多次抢劫,“红四野”在武斗中死伤人员近三十名。关于“文革”初期的这一段武斗生活,路遥在《惊心动魄的一幕》中加以展现,这也是路遥表现“文革”红卫兵经历的惟一作品。小说副标题为“一九六七年纪事”,具有很强的纪实性,基本上是延川县两派之间武斗情况的真实展现。对这篇小说,我感兴趣的是作者对待“文革”造反派头头的态度。发生武斗的两派“红总”与“红指”,其头头们参加造反都不是为了神圣的理想,而是出于个人的私利目的,或者为了个人的报复,或者为了自保,或者出于政治投机,完全是一场利益的角逐和争夺。虽然除了周小全之外,他们的身份都算不上红卫兵,但是作为造反派头头,路遥在作品中对他们造反动机的解释显示了路遥对造反组织的认识。那的确是一场利益的角逐。
在这场利益的角逐中,路遥先是尝到了成功的滋味,而后彻底失败。这段大起大落的生活经历给路遥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不可否认,在路遥性格中,家境的极端贫穷给路遥所带来的自卑、伤害和屈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路遥的朋友李天芳在悼念路遥的文章中说:“不管日后人们将怎样评说路遥,也不管学者和评家将怎样研究他的人生和作品,在我看来,路遥拼力搏击的一生中,潜意识里一直有个支撑点,那就是要完全彻底地摆脱苦难和贫穷的童年带给他的诸多屈辱和阴影,但最终他也未能完全如愿。”[5] 64-65贫穷给一个人所带来的伤害往往超出我们的意料。陕西作家高建群先生曾在《关于路遥的二三事》一文中转述了他听到的一件路遥少年时代的事情,这件事情可能有些艺术加工,不一定完全真实。
庭长说,路遥通常总没有吃的,看见谁手里有个馍馍,于是一把夺过来,待那同学来抢时,路遥就给馍上吐两口唾沫,同学见状,放弃了,于是路遥便就着自己的唾沫,将这半个黑白馒头吞下。
庭长说,班上有一个同学,家境好一点,口袋里时常有馍吃,于是就用这馍逗路遥。他说:“王卫国同学,你学两声狗叫,我将这馍给你吃!”路遥于是学两声狗叫,这同学又说:“我将这馍掰成蛋儿,往空里扔,你用嘴接!”路遥又答应了。于是,在延川县立中学的操场上,便演出了这一幕,一个人不停地向空中扔着馍蛋儿,一个人用嘴去接,接一次学两声狗叫②。
现在没有确切的资料证明路遥在“文革”时期的造反中究竟有多么疯狂和狠毒,从他在造反派中地位的扶摇直上来看,他应该是造反精神极强。这种造反精神与他因贫穷而受到的屈辱和人格践踏显然有着紧密的关系。对路遥而言,童年的屈辱记忆和青年时期的红卫兵造反生涯二者相互影响,相随相生。“文革”初期的“造反有理”的确给路遥带来了希望和命运的转折,他抓住了这样一次机会,奋力拼搏,也的确风光了两三年,但是“好运”转瞬即逝,在变幻莫测的政治斗争中路遥跌向了更深的深渊。1969年“九大”之后,“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路遥由于“文革”初期的种种过激的武斗行为与迫害革命领导干部的行为,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中被罢免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并于1969年年底被彻底赶回老家郭家沟村务农。
路遥正是在政治道路完全被堵死的情况下才转而进行文学创作的,试图用文学打拼出一条人生的新道路。文学,成为他开辟的一个新战场,等着他在文学的战场上展开一轮新的厮杀与追逐。“文革”时期,写作是知识青年改变个人命运的一种常见方式。路遥从事写作,是经过慎重思考、权衡利弊后的选择。“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王卫国来往于县里上层人物之间,有缘结识了延川几位众所公认的‘智多星’,他们很会审时度势,能言善辩,立足于王卫国眼下的处境,民办教师和贫宣队员,都非长久之计。他读的书多,笔杆子利索,文有新意,搞写作,只要肯下功夫,或可有成,舍此别无他途。”[2] 路遥后来回忆这一段时期的文学经历:“就我自己来说,觉得好像又一次开始面对纯朴的生活,进入到一种渴望已久的人情的氛围里,变硬了的心肠开始软化了,僵直了的脑筋开始灵活了,甚至使自己面对过去几年不正常的生活感到了一种真正的羞愧”,“艺术用它巨大的魅力改变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我深深感谢亲爱的《山花》的,正是这一点”[6] 350。在给曹谷溪的诗集《我的陕北》作序时,路遥用同样的论调写道,是“文学”这个“久违了的字眼”让他和曹谷溪由“文革”初期的相互敌视结成了朋友,“共同的爱好使我们抛弃了派别的偏见,一起热心地投入到一个清风习习的新天地里,忘却了那场多年做不完的噩梦”[7]。在路遥的表述中,文学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甚至改变了个人的性情与思想,此种表述有真实的成分,但是也有遮掩。路遥从事文学其实是别无选择,出人头地的意识远远强于对文学的爱好,文学更多的是一块改变身份的跳板,而不是为了陶冶性情。如果可能的话,路遥更愿意做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不过以他底层的身份难以进入权力阶层,即使在“文革”这样的非常态社会里,路遥眼看要一步步青云直上,最后还是被赶了下去。这多少刺痛着路遥的心!这种政治仕途的无望所带来的刺痛可以说一直潜伏在路遥内心深处,即使“文学”这个神奇的药方,也不能抚平路遥心底的伤痛。从一些细节中也可以看出路遥对那段造反生涯还是念念不忘的。路遥在写作之初给自己取的笔名是“缨依红”,从字面上看显然还有怀念红卫兵时代之意[8] 209-210。1974年路遥与金谷合写了长篇政治抒情诗《红卫兵之歌》,发表于《陕西文艺》(1974年第4期)。全诗分为六节,长达580行,为红卫兵高唱赞歌,其气魄可以与“文革”后期名重一时的《理想之歌》相媲美。在这首诗里,看不出路遥对政治的冷漠,相反倒是一腔热情。《惊心动魄的一幕》是路遥惟一一篇写自己造反经历的作品。但是路遥在这部作品中对自己昔日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实质性的反思,反而对自己的行为作了某种辩解。作者对各位造反派头头作了否定性的描写,甚至对金国龙、段国斌有明显的丑化和漫画,周小全是惟一的例外。从周小全的学生身份以及最终的思想转变来看,周小全这个人物有作者的影子。作者把周小全和其他丧心病狂的造反派头头区别开来,其中包含着作者对自己曾有的某些行为所作的潜在辩解。周小全在退出“红总”时说“运动初期,我起来造反,这我现在不后悔”[9] 100,是否也可以看作路遥对自己红卫兵经历的态度呢?
1969年路遥返回农村,在郭家沟做了一名地道的农民,幸运的是,很快路遥就做了民办教师,摆脱了土地上的辛勤劳作,1970年开始写作③。从公社大队的黑板报到县级刊物《延川文化》、自编文艺小报《山花》、自编诗集《延安山花》,再到地区的《延安报》、省级的《陕西文艺》,一步步闯出自己的文学道路。到“文革”结束,路遥的创作在陕西小有名气,并且前途被普遍看好。路遥最初从事创作是从写诗开始的,大约在1973年前后路遥开始转向小说创作。从1970年到“文革”结束,路遥的创作与其他知青相比,算得上丰收。路遥在这个阶段的创作不但数量丰富,在质量上也相对较好。他的创作当然摆脱不了“文革”时期的语言、表达方式、写作套路及思想认识上的局限,但是路遥创作的最大优点是生活实感强。在“文革”常见话语下,可以感受到生动活泼的生活气息和陕北高原所特有的泥土气息。比如诗歌《进了刘家峡》:
进了刘家峡,/把人眼看花!/看了东山大寨田,/又看南沟大水坝,/西梁梯田水哗哗,/果林罩了北山坬!/十里长渠一根藤,/水库就像“串串瓜”……进村问大妈,/支书这阵可在家?/大妈笑哈哈,/手指前川忙回答:/庄稼长势催人忙啊,/家里哪能留住他!/刚才碗一丢,/又去锄庄稼。/玉米林林里找到了他……
虽然最后支书的话不过是在重复“文革”时期报纸杂志上千篇一律的论调,但是诗人寻找支书的过程描写得很生动、形象,拨开一湾“打锣锤”、闪过一滩好棉花、穿渠过坝来到玉米林林里,农忙时分人们劳作的景象、田里长势喜人的庄稼,农民虽忙但是眼看丰收时的喜悦心情,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路遥在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除了《红卫兵之歌》外,都能紧贴农村生活现实,因而在“文革”时期算是比较好的作品。路遥的小说、散文也是如此,尤其是《优胜红旗》,是一篇难得的好作品。《优胜红旗》是路遥的第一篇小说,最初发表在《山花》第七期上。1973年《陕西文艺》(原《延河》文学月刊)复刊时,编辑贺抒玉、问彬慕名《山花》来到延川组稿,曹谷溪向她俩推荐了路遥的《优胜红旗》。读过小说,两位女作家十分惊喜,“小说写的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个小故事,文笔清通,有生活气息,故事也颇具意味”[10] 36,于是登在《陕西文艺》复刊号上。《优胜红旗》是路遥的第一篇小说,也是“文革”期间最出色的一篇。虽然小说免不了鼓吹农业学大寨的政治口号,但是全文对政治因素还是比较淡化,尤其是没有为了追求“文革”时期所谓的“深度”,硬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上扯。小说塑造的人物石大伯和二喜都比较真实可信,石大伯作为在土地上干了几十年的老农民,沉稳、厚重,就像他手中的那把沉甸甸的铁锹,二喜是一匹初生牛犊,有后生们的那股子虎劲,但是缺乏经验,过分看重名誉,因此造成工作中的失误。比较而言,路遥后来创作的《父子俩》、《银花灿灿》、《灯火闪闪》等作品政治性因素越来越浓,反倒失去了最初习作中的那种生活实感和泥土气息。
总的来看,路遥在“文革”后期的创作还处于练笔阶段,而从事创作的动机也有很强的功利性,把写作作为一块从农村进入城市的跳板。实际上,写作也的确成功地完成了跳板的作用,在好友曹谷溪的帮助下,路遥凭借创作在延川县政工组混饭吃,后来又因为创作上的才能进入了延安大学中文系,从此彻底改变了他的农民身份,真正进入了城市。因为路遥曾经是造反派头头,因此学校都不愿接受这种政治上有问题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就拒绝接受路遥,后来才转到延安大学,但是延安大学也有同样的政治顾虑。眼见路遥是上不成大学了,延川县文教局长带上一沓子《山花》与延安大学的招生同志恳谈,延川县委书记也亲自出马,频频出入延安大学去做工作。也许路遥的确有超出普通人的才能,从大队、公社、文教局到县委,一帆风顺、闯关斩将,甚至县文教局长、县委书记为了他上大学也不惜劳累奔波,亲自奔走,不过从中也可看出路遥善于人际交往,善于和大大小小的官员打交道。“文革”结束之际,路遥大学毕业来到了《延河》④ 编辑部,文学成了他今后必走的人生道路。
(二)“红卫兵经历”对作家心理及文学创作的影响
“文革”期间的造反尽管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这段经历对路遥的精神气质、性情、心理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让路遥形成了一生都无法割舍的英雄情结。高建群在悼念路遥的文章中说:“在这个地球偏僻的一隅,生活着一群有些奇特的人们。他们固执。他们天真善良。他们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他们自命不凡以至目空天下。他们大约有些神经质。他们世世代代做着英雄梦想,并且用自身去创造传说。他们是斯巴达克和唐吉诃德性格的奇妙结合。他们是生活在这块高原的最后的骑士,尽管胯下的坐骑已经在两千多年前走失,他们把死亡叫作‘上山’,把出生叫作‘落草’,把生存过程本身叫作‘受苦’。”[11] 111虽然高建群的分析侧重于陕北高原对人的精神气质的影响,但是这段话用在路遥身上太贴切不过了。在关于路遥的众多文章中,高建群先生对路遥的分析最深刻,尽管作为朋友他对路遥的描述有时候需要回避、闪烁其词,但是在行文中仍然能读出对路遥人格和某些行为的微词。路遥的英雄梦想可能与黄土高原有关,但是与红卫兵时代的经历有更直接的、更重要的关系。路遥的英雄情结可以具体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受难情结、政治情结和绝望意识。
第一,受难情结。因为贫穷,路遥青少年时期有源源不断的苦难资源。他从小饱受饥饿、贫穷,为了读书七岁离开亲生父母、遭人嘲弄、受到各种各样的屈辱。人在苦难中,应该勇敢地承受,这是无可非议的。路遥从中学时代,已经开始试图把自己所受的苦难用一种崇高的、伟大的话语进行阐释。如果像猪狗一样地承受苦难,这样的苦难是毫无意义的,必须把苦难转化成一种资本,转化为精神上的优越,从而获得心理优势。“中学时代,路遥已对文学作品产生了浓厚兴趣,那时,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毁灭》、《铁流》等书籍,还不是为了创作,主要是把自己锻炼成意志坚强的人。”[6] 348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英雄、硬汉,他们把苦难当成一种享受,甚至当生活中缺少苦难时,人为地制造出一些苦难,以便磨炼自己的意志,把脆弱的心变得坚强,把人们之间的温情变得冷酷。路遥在中学时代还模仿过少年毛泽东的行为,“记得十几岁时,就曾在暴雨雷电中一个人爬上山让瓢泼大雨淋过自己,雷声和闪电几乎就在咫尺之间;也曾冒险从山顶几乎不择道路地狼奔豕突蹿冲下来,以锻炼在危难瞬间思维和行动的敏捷与协调,或者说选择生存的本领。”[12] 72显然,路遥在造反之前已经具备了造反所需的心理素质,加上路遥文字上、讲演上的才能,自然会在“文革”造反中一马领先,曾经受过的种种苦难如今都得到了回报,苦难真的转化成了一种令人自傲的、自我满足的资本。苦难的神圣化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路遥的受难情结也于此形成。路遥把自己的苦难理想化、崇高化、圣洁化,那种崇高的受难精神可能掩盖了现实生活中他在苦难面前的屈从。例如,《在困难的日子里》一文是描写路遥中学时代的饥饿经历。面对饥饿,马建强宁可饿死,也不愿受到侮辱。
有一天,我们全班在校园后边的山上劳动,他(周文明)竟然当着周围几个女同学的面,把他啃了一口的一个混合面馒头硬往我手里塞,那神情就像一个阔佬耍弄一个叫花子。
这侮辱太放肆了,我感觉浑身的血都往头上涌来。我沉默地接过这块肮脏的施舍品,猛一下把它远远地甩在了一个臭水坑里![13] 111
如果吃他人啃了一口的馒头就是不能容忍的侮辱的话,那么在操场上装狗叫、模仿狗跳起来接食的动作该如何呢?人毕竟不是神,承受苦难的能力也是有限度的,面对苦难的英雄气概只是一种想象,现实生活中往往只能屈从。路遥把苦难神圣化、崇高化的同时,也阻挡了他对自己人格心理的真诚解剖,作品中的人物被洗涤得过分干净,反倒显得不真实。因此我更偏爱《人生》、偏爱性格有缺陷的高加林,而不太喜欢《平凡的世界》中“高大全”的孙少平。
如果说人面对无法摆脱的苦难时,用一种崇高的理想来激励自己是正常的话,那么路遥在“新时期”生活安定之后,故意制造生活中的苦难就有些做作和矫情了。看看路遥在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的一些表述:“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12] 12“写这部书我已抱定吃苦牺牲的精神,一开始就到一个舒适的环境去工作不符合我的心意。煤矿生活条件差一些,艰苦一些,这和我精神上的要求是一致的。我既然要拼命完成此生的一桩夙愿,起先就应该投身于艰苦之中。实行如此繁难的使命,不能对自己有丝毫的怜悯之心。要排斥舒适,要斩断温柔,只有在暴风雨中才可能有豪迈的飞翔;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有可能弹拨出绝响。”[12] 34当他在写作第二部初稿时,因体力不支,在锻炼时竟然不顾自己身体的实际情况再次模仿少年毛泽东[12] 72。与其说是为了锻炼身体,不如说是为了从模仿伟人的行为中获得一种心理优势,从人为制造的苦难中给自己增添信心。作家写作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是只有路遥最苦,仿佛全世界的苦都加在了他一个人身上。“我看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比我聪敏。我常暗自噙着泪水,一再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12] 33路遥大约从这句自我反问中得到了最大的心理满足,“我”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相对立,所有的人都在聪敏地活着,而只有“我”却像一个弱智,但是恰恰是“我”才有资格噙着泪水,透过泪水,路遥一定看见了自我成为英雄的幻影。表面上看,路遥生活上的种种艰辛,是由于他不善于生活、不拘小节、放任自流所造成的,实际上潜意识里是路遥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认同和自我满足。他相信惟有苦难才能带来辉煌,有意识地把自己弄得痛苦不堪,从中获得英雄的幻觉。
为了成为一个英雄而自觉承受苦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受虐意识,偏执、狂热。路遥的这种性格有时候会投身到作品中的一些人物身上,做出一些不合理性的偏执和狂热的行为。例如《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润叶,作者把她塑造成外表柔嫩、骨子里坚韧、在关键时刻默默承受苦难挑起重担的正面人物形象,但是这个人物性格中不能不说有某种偏执。作品中的金波在爱情上的表现更是偏执得离奇,即使作为理想,那种语言不通、从未谋面、仅凭一首民歌就生死不渝的爱情也有些失真。从整部小说来看,这个情节也不符合金波的性格发展。这种人物性格的偏执是路遥性格中某些因素的自然流露。
第二,政治情结。路遥在19岁就尝到了做官的妙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时,王卫国被协商成副主任,坐在城内井滩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俯视高举领袖像和标语牌的芸芸众生,听着震耳欲聋的山呼万岁声,他踌躇满志,颇有点春风得意,革命原来是这么回事”[2]。这的确是风光无限好。据说路遥在“文革”结束后在担任陕西省文联主席期间,在文联大院里进进出出,勇猛而好战,令他的对手们闻风丧胆。路遥的不少朋友都认为路遥的精神气质更适合做政治家,而不是文学家。路遥本人也是在政治仕途完全被堵死的情况下才从事文学创作的,但是他本人一生都没有放弃政治,在作品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由于路遥在造反时具有强烈地改变个人身份的目的,因此他的政治情结的核心是为官,他所认同的价值中含有明显的官本位的陈腐思想。
且不说路遥在《平凡的世界》大段引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官方报纸的社论,也不说对村级、大队级、县级、地区级、省级、中央级等各级官员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描写,仅选择看起来与政治、为官最没有关系的孙家三兄妹的爱情来分析。《平凡的世界》中,爱情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孙少安、孙少平、孙兰香,每一个人都处在一个爱情的三角关系之中,孙少平作为全书的第一号主角,更是被置于三个爱情三角之中。在孙少安—田润叶—李向前这个爱情三角中,争夺的核心是田润叶,孙少安作为家贫的农民,很轻易地就战胜了干部子弟李向前,让田润叶爱得死去活来。孙少平的第一个爱情三角是孙少平—郝红梅—顾养民,虽然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孙少平以失败而告终,但这只是一个开端,为了让故事发展得更曲折的一个小插曲。孙少平的第二个爱情三角是孙少平—田晓霞—高朗,孙少平先是作为一个居无定所的揽工汉、后是谁都看不上眼的煤矿工人,战胜了省报记者、父亲是副省长、爷爷是中纪委常委的高朗。爱上孙少平的田晓霞是大学生、省报记者,父亲是地委书记。孙少平的第三个爱情三角是孙少平—金秀—顾养民,金秀是医学大学生,和顾养民已经建立了稳定的恋爱关系,顾养民此时已经是医学研究生,各方面条件非常优秀,以致令女友金秀感到其过分完美成为了一个缺点,使得金秀最后弃顾而爱上孙。孙兰香的爱情三角孙兰香—吴仲平—高敏同样如此。在这一个又一个的爱情三角中,孙少安、孙少平、孙兰香都是以弱势地位战胜高官显贵的公子千金,他们的每一个竞争对手,必然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出身名门、官宦之家,本人也出类拔萃,但孙氏三兄妹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当然现实生活中贫民百姓与高干子女之间也时有爱情发生,但是路遥把所有的爱情都这样安排,不能不说有些牵强和一厢情愿,其中透露出的是路遥对高官显贵的认可和渴望。有趣的是,孙氏三兄妹的爱恋者和竞争者的父亲无一例外都是官场上的高官大官,而不是金钱上的富有。看来路遥更看重的是社会地位、社会身份,而不是财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当田福堂得知女儿润叶和女婿李向前婚姻关系十分糟糕、而孙少安成为村里的冒尖户时,仍然不后悔当初阻止女儿与孙少安之间的恋情。在他看来,女儿女婿关系糟糕是一回事,孙少安和润叶的关系又是另一回事,李向前毕竟是公家人、城里人,这种身份才配得上润叶,孙少安再强,也是农民,即使发家致富,他的农民身份决定了他永远处于弱势地位。孙少平也不太看得上哥哥的奋斗,即使哥哥成了村里的首富,他也不愿意走哥哥那条道路,宁愿当个煤矿工人,也不愿做农村财大气粗的个体户,原因何在?关键在于孙少安的身份永远只能是农民,首富又怎样,首富也抵不过煤矿工人的公家人身份。因此在看来最没有政治的爱情里,其实包含着最大的政治,路遥个人的价值认同和人生取向也从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路遥的政治情结不仅表现在价值取向上的官本位思想,同时作为一种心理情结也直接影响到路遥的文学创作观念。路遥渴望自己的一生能够建功立业、功勋卓著,但是现实生活偏偏不给他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于是路遥只好在文学的虚拟世界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这表现在路遥在写作上的“大书”情结。“我决定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在我的想象中,未来的这部书如果不是此生我最满意的作品,也起码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作品。”[12] 8这部书,“三部,六卷,一百万字。作品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七五年初到一九八五年初,为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人物可能要近百人左右。”[12] 12但是路遥所理解的“大书”似乎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史诗般巨著”,更侧重于规模上的宏大和字数的庞大。路遥对于规模有一种近乎疯狂的追求,数量能给他带来巨大的亢奋和狂热。
工作进展已经在量上表现了出来。这方面确定的第一个目标是突破十三万字。这是《人生》的字数,迄今为止自己最高的横杆。突破这个数字带有象征意义……
十三万字的数量终于突破。兴奋产生了庄严。庄严又使人趋于平静。
这是一个小小的征服。接下来,脚步已经开始变得豪迈了一些。最少在表象上看,下一步将从自己写作史上的一个新的起点出发了。
下一个数量上的目标是越过这一部的二分之一处。
这个目标再有几万字即可达到,但这是在创造新的记录,情绪为之而亢奋。[12] 39
路遥把自己想象成驰骋风云的英雄人物,在三部六卷一百万字的广阔战场里,带领着近百人冲锋上阵,在文学的战场上实现自己“维特时期”的许多梦想,再现造反时代的叱咤风云。尽管对规模的狂热和硬性规定,损坏了作品的艺术性。在现实生活中不可实现的梦想,在文学中得到想象性的满足。
第三,绝望意识。造反生涯的短暂辉煌和之后的彻底穷途末路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形成了路遥一生都无法摆脱的绝望意识。那种绝望是无法代替、无法排解的,因此在路遥最辉煌的时候,涌上心头的恰恰是抑止不住的悲伤。陈泽顺先生回忆路遥在《人生》得了大奖、全国轰动时,竟然歪倒在椅子上“觉得没意思”。他常有一种危机感,惧怕所得到的一切是一个吹出来的五彩肥皂泡,转眼之间就会破碎得无影无踪。因为19岁那年炫人眼目的肥皂泡陡然破碎,给了他太强的刺激和恐惧。因此,路遥每每在人生的辉煌时,看见的不是鲜花和红地毯,而是令人粉身碎骨的深渊。他拼命写作,残酷地对待自己,为了把人生的辉煌尽可能拉长、再拉长。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源于他二十岁左右的一个梦想,“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12] 7“维特时期”曾经有过多种梦想,惟有写一本规模巨大的书这个梦想鲜活地来到路遥心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契机,《人生》获得了巨大成功,有人断言这是路遥人生的最高度、事业的顶点。这意味着路遥将在《人生》的极度辉煌之后,风光不再,因此经过无数个焦虑而失眠的夜晚,那个尘封已久的梦想出现了,为了二度辉煌,路遥投入到《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中。因为绝望,路遥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注定了他的人生会打上悲剧的色彩,也注定了他一生的沉重。
在作品之中,作者对自己心爱的主人公的失败有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敏感。孙少平在中学时代,被郝红梅所抛弃,作者对于这段经历耿耿于怀,以致不顾情节的发展逻辑,文至最后居然让金秀爱上了孙少平。这实在让人感到突兀,也看不出情节如此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惟一的理由是金秀作为顾养民的女友,作者让她离开顾养民选择孙少平,是为了报当年顾养民横刀夺爱、抢走郝红梅的一箭之仇。甚至连郝红梅,作者也没有轻易放过,先是因为偷手绢事发被顾养民抛弃,后又远嫁他乡而新婚丈夫猝然去世,最后才在各方面都十分平平的田润生那里找到归宿。表面上看,郝红梅的厄运是因为个人道德上的缺失,因偷盗而失去一切,实际上她的厄运之根本在抛弃孙少平这一行为,为了惩治这一行为,为了平息孙少平被抛弃的愤怒,她是非偷手绢不可了。作者那么急于为孙少平“报仇雪恨”,其实是为了给自己年轻时的一段恋情做一个了解,也是为了平息那段恋情给自己带来的极大伤害。1969年,路遥在人生最为辉煌的时刻与北京知青林红⑤ 展开了他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恋情。路遥一生都没有走出这段恋情所带来的幸福与阴影。1970年延川县招工,路遥争取到了一个指标,但是他把这个名额转给了林红。林红进厂后不久便和路遥分手,爱上了一位支工的解放军下级官员⑥。对于这段失败的爱情,路遥曾对朋友高建群做过交代,说林红曾在《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奖后抱着忏悔去找过他,但是高建群很怀疑这个再次相遇的故事“真实的成分有多大”[11] 105-106。林红离开路遥,很重要的原因是路遥的县革委会副主任被停职,返回家乡做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林红的选择相似于郝红梅在孙少平和顾养民之间所做的选择。我也很怀疑路遥所讲述的再遇部分的真实性,路遥把这次相遇放在他小说获奖之后,也就是他再次成功之后⑦,其中颇有意味。林红当初因为路遥的失落而离开,又因路遥的成功而主动回来,那种后悔、遗憾和自责大约让路遥很满足。林红的离开对路遥的一生有重要影响,如果说路遥因为革委会副主任被停职已经痛不欲生的话,那么林红的离开,无疑是加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路遥,也才会造成路遥内心深处的彻底绝望。这种绝望,表现为对成功的极度渴望和永不满足,对失败近乎神经质的敏感和拒斥。
路遥的绝望意识和极度渴望成功的心理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的结合使得路遥的作品既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矛盾,又掩盖这些矛盾。城乡之间的矛盾冲突是路遥作品的核心主题。路遥的作品非常真实地展现了农村青年进入城市的种种艰辛、渴求、痛苦、煎熬。农村青年所面临的种种艰辛和痛苦是由国家不合理的城乡户籍制度所造成的,高加林的悲剧本来是一个社会问题,但作者最后把它处理成了一个道德问题,高加林的失败是因为他“卖了良心”,道德上有了缺陷。虽然作者也指出了社会的不合理:“社会也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真正廓清生活中无数不合理的东西,让阳光照亮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使那些徘徊在生活十字路口的年轻人走向正轨,让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让他们的理想得以实现。”[14] 346但是对社会的温和指责被对高加林道德上的强烈谴责所掩盖,尤其是德顺大爷——从黄土地上树立起来的道德完人——在高加林回村的路口对高加林的那一番人生道德的教导,完全把社会悲剧变成了道德悲剧。因此高加林才会在最后“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叫喊了一声:‘我的亲人哪……’”[14] 361《人生》发表后,有评论家将高加林和于连·索黑尔进行比较,认为二者都是个人主义的奋斗者。其实在《人生》中路遥借黄亚萍之口就评价高加林有点像保尔·柯察金,更像于连·索黑尔⑧。但是当批评家真的把高加林和于连相提并论时,路遥感到愤怒,也有些惊慌、不安、紧张。毕竟高加林不同于于连,当于连站在绞刑架上对社会发出强烈控诉的时候,高加林则按照路遥的旨意匍匐在了道德楷模德顺大爷的脚下,匍匐在黄土地上。高加林由对社会的控诉转变为对道德的膜拜,这其实是路遥向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屈从与取媚。路遥非常清楚像高加林这样的个人奋斗主义者在社会主义中国是完全没有出路的,必然会遭到主流话语的猛烈批判。如果高加林最后也像于连一样,站在黄土高原上控诉国家制度的不合理,那么迎接《人生》的就不是鲜花与红地毯,而是被围剿的命运,就像《假如我是真的》这类作品一样。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路遥对城乡之间的社会不合理认识得非常清楚。“我国不幸的农村问题是历史形成的;是古老中国和现当代历史形成的……这个责任应由历史承担,而不能归罪于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简单地说,难道他们不愿意像城里人一样生活得更好一些吗?命运如果把他们降生在城市而把现在的城里人安排到农村,事实又将会怎样?”[12] 66-67这段话写于1992年,但是这是路遥写作《人生》时已经形成的认识,只是因为忙于写作《平凡的世界》没有精力和评论家辩论[12] 63-64。也就是说,路遥很清楚高加林的悲剧所在,但是他没有直率地写出来。高加林最后回到黄土地是必然的,作者遵循生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写出了这个必然性,正是作者的伟大之处,但是作者把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转化为没有政治危险的道德原因,则显示了作者向国家权力的屈服,也大大降低了作品的现实力度,于是路遥和司汤达式的伟大作家擦肩而过了。《人生》获得巨大成功之后,路遥产生了文学大家的幻觉,自觉地担负起了一个文学大家应负的社会责任,把高加林身上不光彩的因素淘净,《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一个个都完美无缺、道德高尚,为我们普通人指方向、立榜样。路遥向主流意识形态靠得更近了,作品也取得了更大的社会成功,但是作为艺术品,《平凡的世界》比《人生》逊色很多。渴望现世成功的心理阻挡了路遥向伟大作家行列迈进的脚步。
总之,造反经历对路遥的精神气质、心理性情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并直接影响到路遥的文学创作。可惜路遥英年早逝,如果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在《平凡的世界》之后他的创作会怎样呢?从他已有的创作来看,他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路遥在“新时期”的整个创作都指向最终的目标《平凡的世界》,早在1987年李星就撰写了很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无法回避的选择》[15],指出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是必然的选择,是他创作路数的必然发展。路遥自己也看到自己创作道路的尽头,去世前不久,他亲自编选了《路遥文集》,“以此与他的青年时代告别,以后他的作品不可能再写那些人物了,以后得重新开始。”[10] 48因为他的早逝,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重新开始的创作会是什么样。高建群在路遥去世后,做过一种设想:“路遥本身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也许,他的本身,比他小说中的任何人物都更精彩、更复杂和更具有文学的独特性,可惜,他英年早逝,没有可能再去表现这一切了。这是整个人类的损失!人类整体利益的损失!我曾经多次给路遥说过,我说,如果让你经受一次大的打击,脱离现在的生活轨道,而走向内心反省,一定会有比《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更为精彩的伟大作品出现的。”[11] 107-108高建群对路遥的确有着深刻的认识。表面上看,路遥的作品有很强的自传色彩,实际上路遥从未真正打开过他自己,一直在有意回避着那个真实的自我。“人们都知道,路遥是一位很少敞开心怀叙述他内心一切的一位面部表情冷峻、极少言语的作家。他的欢乐和悲伤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朋友才能知道,在别人看来他仿佛是一个谜。”[16] 11路遥还未来得及反省自我的人生,也未来得及反省自己年轻时的种种行为,就带着面纱永远离开了我们。也许这对路遥是最好的结局,他内心深处的自卑、脆弱、敏感未必能承受痛苦的自我反省。
注释:
①路遥逝世后,他的生前好友在悼念文章中偶尔会提及路遥对他们讲述自己的造反经历,但都是在“文革”期间,如:董墨在《灿烂而短促的闪耀——痛悼路遥》。至今还没有发现路遥到了“新时期”之后,重提红卫兵造反经历,无论是表诸于文字还是对朋友的口头讲述。因此,路遥在“文革”时期的红卫兵经历,现在可查的资料很少,高歌的《困难的日子纪事——上大学前的路遥》和晓雷《男儿有泪——路遥和谷溪》以及路遥本人的文学作品《惊心动魄的一幕》为我们提供了只鳞片爪的记忆。
②这篇文章发表于《教师报》(1996年3月17日第四版).但是,路遥生前的挚友曹谷溪先生2005年10月11日给笔者的来信中称,高的这篇文章“完全是凭空杜撰。我亲自访问了文中提到的所有人……他们都矢口否认与高交谈过这样的故事”。关于这“二三事”是否真的发生过,现在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了。笔者认为,即使这些事情经过了加工、甚至是“凭空杜撰”,对本文的论点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毕竟路遥自己亲笔所写的作品、创作随笔是无法更改的。
③诗歌方面有:自编诗集《延安山花》收录路遥的诗歌《进了刘家峡》、《电焊工》、《老汉走着就想跑》、《塞上柳》,路遥和曹谷溪合写的诗歌《灯》、《当年“八路”延安来》,以及署名“鲁元”的《山村女教师》和“雨园”的《农村销货员》,一共有8首;在《山花》上发表的有《赞歌献给毛主席》、《桦树皮书包》、《老锻工》、《今日毛乌素》等;1972年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编选的诗集《山丹丹花开》,收录了路遥的诗歌《车过南京桥》、《塞上柳》、《当年的“小八路”回延安》(与曹谷溪合写)三首;1974年《延安山花》再版时,增补了路遥的《老汉一辈子爱唱歌》;在省级刊物《陕西文艺》上发表与曹谷溪合写的诗歌《歌儿伴着车轮飞》(1973年11月,总第3期)、《红卫兵之歌》(1974年第4期,总第7期)。2000年由广州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路遥全集》“短篇小说、剧本、诗歌”一卷中收录路遥的诗歌11首,显然是不全的。小说方面有:在《山花》上发表《优胜红旗》(第七期)、《基石》(第十五期)、《代理队长》(第十八期)等;在《陕西文艺》上发表有《优胜红旗》(1973年7月创刊号)、《父子俩》(1976年第2期)。散文方面有:在《陕西文艺》上发表《银花灿灿》(1974年5期)、《灯火闪闪》(1975年1期)、《不冻结的土地》(1975年5期)、《吴堡行》(与李知、董墨合写,1976年第1期)。剧本方面有:1972年与陶正合写大型歌剧《蟠龙坝》、与闻频合写大型歌剧《第九支队》,并经排练后上台演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通讯报道等。
④《延河》是陕西省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文革”前为《延河》,“文革”时期复刊时更名为《陕西文艺》,“文革”结束后恢复原名《延河》。
⑤关于路遥的初恋女友,大多数回忆文章说她叫林红,惟有晓雷的《男儿有泪》说她叫林琼。
⑥路遥的这段初恋可以参见高歌《困难的日子纪事》和晓雷的《男儿有泪》。
⑦这次谈话是在路遥刚刚写完《人生》的时候,《惊心动魄的一幕》是路遥那时最引以为傲的成绩。
⑧有意思的是,当路遥病入膏肓,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蜷成一团时,让看望他的朋友高建群想起了《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在狱中的最后情景。(参见[11],1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