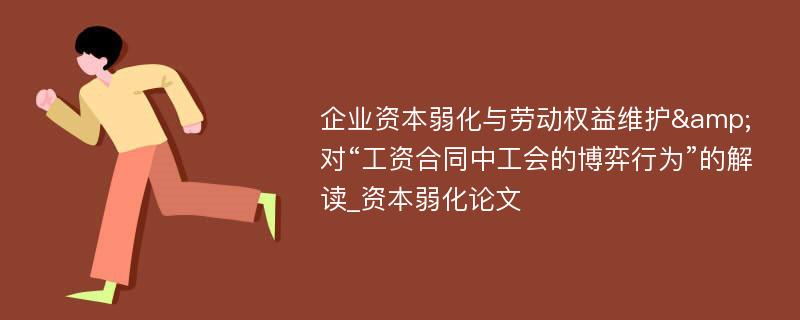
企业“资本弱化”与劳工权益的维护——兼释“工会在工资合约中的博弈行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工论文,合约论文,工会论文,权益论文,工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6;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6-0089-06
资本弱化(Thin Capitalization),亦称资本隐藏、股份隐藏或收益抽取,是企业股东为了少纳税或其他目的,以贷款方式替代募股方式进行的投资或者融资(孙少岩,李响,2006)。按照经合组织(OECD)的解释,只要企业的权益资本小于债务资本,股东的资本弱化行为就存在。由于与债务资本相关的利息费用具有“税盾效应”(Taxshield)①,资本弱化问题由此产生。为规制资本弱化对一国税基的侵蚀,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税收制度对资本弱化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②。事实上,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资本弱化问题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很多外资企业“亏而不倒、越亏越大”现象与资本弱化问题不无关系③。
一般认为,劳工工资合约体现企业劳动者的核心权益,是劳工或其“代言人”—工会与资方或其代表—管理层就劳动报酬所进行的约定。理论上,劳工工资合约与企业绩效密切相关。“会计数据”作为规制公司合约的重要依据(付蕴英,2004),已经成为检验企业绩效的“代名词”,并在工资集体谈判中被广泛应用(任小平,2008)。因此,资本弱化问题影响的不仅仅是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税收合约,也必然会影响到劳工与企业之间的工资合约。而本文的意图是,以资本弱化下的劳工权益受损为逻辑起点,从劳工权益“代言人”——工会的视角,分析工会在劳工工资合约中的博弈行为,并探究性的提出劳工权益维护的因应策略。
一、资本弱化下的劳工权益受损逻辑
企业是一个合约集(nexus of contracts),股东、债权人、政府和劳工(工会)是公司重要的合约主体。劳工工资合约作为企业重要合约之一,在劳资双方的工资谈判中,无疑会考察企业的财务绩效,“工效挂钩”正是这样的例证。当财务绩效成为工资合约的决定变量时,理性的资方(股东)有动机让工会知晓的是低财务绩效的会计数据,而资本弱化行为有助于其动机的实现。因此,资本弱化下的劳工权益受损逻辑图景就是:
在注册资本审批制度下,股东根据需要确定企业经营所需总资本的同时,根据企业所在地的法律制度,最大限度加大债务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④。和股东投入权益资本所不同的是,较多的债务资本可以给股东带来三方面的隐性收益:(1)因债务资本利息的税前列支而节约的税负支出;(2)与债务资本相关的利息费用可以降低企业财务绩效,从而降低与财务绩效挂钩的合约标准,而劳工工资合约也与此相关;(3)在公司责任有限制的情况下,如果股东投资的企业经营不善,按照法律的规定承担的责任仅以出资额为限,而低的权益资本无疑可以实现这一目的。所以,在现实的工资谈判中,当工会代表劳工表达工资增长诉求时,资方一般会以财务绩效水平不佳予以婉拒。
和股东直接主导下的资本弱化所不同的是,“两权分离”下的管理层作为股东财产的受托经营者,自身也会与股东之间形成合约(即管理层的激励合约)。一般情况下,管理层的激励合约与企业财务绩效也是相关的。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管理层是否有动机支持股东资本弱化行为呢?或与此相反,作为受托人的管理层是否有动机与劳工合谋取得最佳的财务绩效以实现各自的最优合约呢?
从现实的层面考察,股东的风险偏好无疑是诱使其投资动机的重要因素。但是,股东能否把风险偏好转换为现实投资行动的关键是其预期的合约收益能否弥补其所承受的风险。当股东的合约收益超过其承担的风险成本时,其投资的动机就能实现,基于股东投资行为的企业组织得以诞生。当股东的投资偏好付诸实施后,剩下的问题是谁将对股东的合约收益负责?
理论上,股东亲自打理自己所出资的企业是一种比较理性的选择。但受股东自身的经营能力的限制,绝大部分股东又不得不将所投资的企业交给具有专业经验的人或团队进行管理,尤其是在企业规模扩大、资本大众化成为现实后,专门负责企业经营管理的管理层(职业经理人)由此诞生。管理层的主要任务是:(1)对外,在以合约的方式获取一定的授权后,对利益相关者(如股东、债权人等)的合约收益承担责任,并取得约定的合约收益;(2)对内,则以权威命令等手段,动用一切资源,组织实施有效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
当管理层被授权经营企业后,股东为防范管理层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所可能带来的合约损失,必然有动机将自身合约收益压力传递给管理层,并与管理层签署有压力的激励性合约。当管理层承受这种压力的时候,自然会将这种压力在企业内部以“领导者”的身份予以传递和分解,而劳工就成了这一行为的直接承受者。
因此,管理层基于自身合约收益的考量,存在与股东合谋压低企业财务绩效的动机,而动机转化为行动的两个基本条件就是:(1)管理层主导下的劳工工资合约不会导致劳工的抗争;(2)管理层可以从与股东合谋下的低财务绩效中取得“补偿”。现实当中,当工会代表劳工提出较高的工资合约要求时,管理层与股东在立场上的高度一致,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管理层通常从压低劳工工资中获益。对股东主导下的资本弱化行为,管理层也乐观其成,尤其是当管理层的合约收益中包括部分长期性激励(如股权激励、期权激励)时,更有动机在最有利的时候对潜在的财务绩效集中释放,以最大限度获取收益。
所以,资本弱化问题侵害的不仅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税收合约,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对弱势劳工群体的工资合约侵害也同样存在。即使是在“两权分离”下,管理层基于自身合约收益的考量,也不会在劳工工资合约方面与工会合谋,除非管理层的利益与劳工利益高度一致,而这在现实当中很难成为普遍现象⑤。在资本话语权空前强大的背景下,劳工权益的被侵害不仅有资本权益优先的制度性偏好,而且也有包括资本弱化在内的隐性侵害,这在外资企业中可能更为明显⑥。
二、资本弱化下的工会博弈行为分析
工会当以劳工权益为首要责任。没有强大的劳工运动,就没有强大的中产阶层(奥巴马,2009)。在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关系市场化演变的事实表明,劳工权益“被侵害”⑦已经是一个普遍事实,曾经的“主人翁”身份在现实的语境中更多地被社会解读为一种“政治符号”,而劳资冲突并未因“政治符号”的存在而忽略对自身经济权益的诉求,经济权益的缺失已经成为劳资冲突的主要因素,而社会的观察往往认为是劳工“话语权”的缺失并将问题归咎于中国工会的“三不行为”(不作为、不能为和不愿为),但这种无谓的诘难并未改变中国工会应将表达和维护职工权益作为一切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制度主张。集体谈判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工会代表劳工向资方主张权益的基本制度,在我国的实践中也得到了大力的推行。在此次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工会率先倡导并大力实施的“共同约定行动”之所以能够得到“劳、资、政”(劳工、企业和政府)的大力支出,重要的因素就是规定所有涉及劳工权益的行为,尤其是经济权益,必须以集体谈判的方式共同决定。和西方工会在劳工工资合约博弈行为所不同的是,中国工会独有的“双重受托责任”一直是在寻求劳工权益和与资本利益的和谐共赢(任小平,许晓军,2009),即使在“资本弱化”这一事实下,中国工会也是初衷未改。
(一)“合则两利、败则两伤”是决定工会博弈行为的基本准则
就性质划分而言,博弈论(game theory)往往被区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两大类(纳什,1951),而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无疑是实现劳工利益的基本前提。但能否实现的基本条件就是:对参与博弈的主体而言,合作博弈的收益应大于非合作博弈的收益。
在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劳资谈判中的对抗之所以频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的劳工制度承认工会的集体行动权(即“罢工权”),并且也认为只有通过劳工的集体行动,才能让资方迫于压力重回谈判桌并最大限度接受工会的主张。由于国情不同,中国的劳工制度对工会的“集体行动权”没有明确的说法,对事实上采取非合作博弈的“集体行动”⑧也偏好用“群体性事件”予以表述,并借政府之手予以解决。可以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合作博弈是工会的最佳选择,即使存在着“资本弱化”对职工权益的侵害,“合则两利、败则两伤”仍然是决定工会博弈行为的基本准则。这是因为:(1)工会在劳资谈判中很难发现“资本弱化”的事证,即使发现,也很难理清这一行为对工资合约的具体影响,即使能够厘清,与之相关的成本也是工会不能承受之重;(2)不管谈判结果如何,代表劳工谈判的工会代表的风险要比劳工群体的风险要大,因为工会代表的“饭碗”是由资方决定,现实当中也不乏因维护职工权益而遭受资方“不公正待遇”的案例;(3)国家关于资本权益优先的制度安排使工会很难背离这一制度偏好,尤其是在“引资发展”的大背景下,工会任何的不合作行为将被冠以“本位主义”的帽子而备受责难。因此,在劳工工资合约的博弈中,中国工会在制度上不具备非合作博弈的空间,即使在合作博弈的基本条件丧失时,中国工会仍然会坚守“合则两利、败则两伤”的博弈准则,并以此为基础,决定具体的博弈行为。
(二)以“数据说话”为核心的“柔性诉求”是工会现实可选的理性博弈策略
信息的完备程度决定合约的完备程度。就工资合约而言,与之相关的企业绩效信息是否充分将直接影响到劳工的工资合约。劳资谈判中,资方的信息优势是明显的,尤其是与工资合约有关的信息,资方几乎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信息垄断。但在“合则两利、败则两伤”的基本准则下,工会明知处于信息劣势,但仍希望用“数据”来支撑自身的谈判诉求,并以此期望资方做出让步。在工会无法知晓所在企业真实财务绩效的情况下,工会可供选择的路径就是大量的与所在企业相关的行业、地区甚至政府的非刚性规定(如工资指导线)等数据作为博弈的依据。当工会收集的这些数据足以让资方知晓工会的“良苦用心”时,理性的资方也会做出适度的让步来部分满足工会的诉求。而现实当中的两个小案例可以窥见一斑⑨。
案例一:某企业组建工会后,按照制度要求寻求与管理层就职工工资问题进行谈判,并不断要求管理层坐下来与工会就工资问题进行协商,但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管理层仍然以各种理由婉拒工会的谈判要求。在工会“持之以恒、软磨硬泡”下被逼无奈的管理层提出,只要工会能够找出企业绩效改善的信息,就和工会进行谈判。随后,工会依靠工人拿出了大量的生产数据,并将模拟后的企业绩效提供给管理层,当管理层看到数据后,在惊讶的同时也最终同意了工会的谈判要求,并最终达成当年员工工资增长8%的协议。
案例二:某跨国公司,1997年成立,到2002年仍然累计亏损近2个亿,但在此期间,该跨国公司在中国三地扩建了三个新工厂。2002年,工会提出工资增长20%的谈判诉求,管理层坚决回绝并单方决定当年工资零增长。为迫使管理层同意工资谈判并实现增资目标,该企业工会围绕人均产值、人均利税、人均工资等指标,收集与企业相关的行业、地区和同一地区同类型外资企业的相关数据近3 000个,并将本企业的相关数据与之比较后提交管理层。尽管管理层质疑工会数据的公信力,但在基本事实面前也迫不得已和工会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增资10.52%的协议。
案例一是有“数据”才谈,而案例二则要有“好数据才谈”。上述个案或许不具备学术研究上的一般意义,但个案中的观察也足以描述中国工会在劳工工资合约谈判中的“柔性诉求”,而“数据说话”无疑是重要的,以“数据说话”为核心的“柔性诉求”是工会现实可选的理性博弈策略。
事实上,在案例二中,工会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指出了资方的“资本弱化”行为,也发现资方尽管亏损,但个别股东因“资本弱化”行为的获利已经超过权益资本的3倍。工会虽然也认同资方的“资本弱化”行为并不违背法律规定,但事实上是该行为影响到了企业绩效,并进而影响到员工的工资合约。可以想象,在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下,没有大量数据支撑的“柔性诉求”,劳工工资合约的实现将何其艰难。
(三)巧用“压力机制”,促使资方让步是中国工会实现博弈目标的保障
工会代表劳工进行工资谈判是一种集体行为。在资强劳弱的现实下,工会能否抑制资本的强势需要有一定的行为能力和策略手段。实践中,尽管工会认为没有集体行动权的集体谈判无异于“集体行乞”,但仍然希望按照“合则两利、败则两伤”的博弈准则并付诸在“数据说话”的“柔性诉求”中实施具体的博弈行为。如果资方在有能力的情况下一味拒绝与工会合作,中国工会实现合作博弈目标的手段就是巧用“压力机制”。和法律认可的“罢工“这一集体行动权不同的是,该“压力机制”的核心是在内部出现“消极怠工”和在外部寻求“制度救济”相结合的一种博弈策略。在中国独有的国情下,这一压力机制具有现实基础,尤其是中国工会所独有的“双重受托责任”,使其较为容易获得外部的制度救济,包括政府的指令和上级工会的帮助,而中国独有的商业生态也决定资方不敢忽视工会寻求“制度救济”而产生的社会压力。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促使劳资谈判制度的建立,将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纳入评选和谐劳动关系企业的核心内容,而被评为和谐劳动关系的企业,其产品在进出口方面将享受快速通关甚至免检免验的待遇。对视时间如金钱的企业而言,这一对集体谈判的“制度救济”在某种意义上比单独的集体行动权可能更为有效。
三、资本弱化下的劳工权益维护
劳动关系的实质是经济利益关系,在我国现实的劳资纠纷中,绝大部分与劳工经济权益受损有关。来自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数据也表明,当企业发生集体劳动争议及群体性事件时,61%的职工表示“有可能参加”⑩。这说明,劳动关系领域所累计的社会风险在不断加大,在资本弱化行为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加大劳工权益维护不仅是工会的应尽之责,而且也应从社会层面提出因应之策,为建立劳动关系和谐基础上的社会和谐创造必要条件。
(一)制度层面高度重视资本弱化行为对劳工权益的不利影响并予以有效规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关系的市场化趋势基本形成,基于劳动合约的劳资自治是市场化劳动关系调整的基本方式,劳资权利的对等是实现劳资自治的基本要求。在资本稀缺大背景下所推行的改革路径,一些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较为容忍资方的资本弱化行为,对外商投资企业尤为宽容。为控制这一行为的不利影响,现有法规更多的是从保护国家税收和债权人利益的角度来进行规制(11),而劳工利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在与劳工经济权益密切相关的工资合约中,现有的制度设计仅仅寄希望于“劳资自治”的工资谈判方式予以解决,这无疑将本就弱势的劳工群体推向了“自生自灭”的窘境。股东主导下的资本弱化行为,受损的不仅仅是国民的税收财富,也不利于劳工权益的实现,还有可能诱发劳工群体的潜在性抗争。因此,从制度普适性的角度,也应将劳工权益的维护纳入制度规制的范围,在国家层面的劳动关系游戏规则中加入资本弱化下的劳工权益保护条款,当务之急是要允许工会比照税法调整后的企业绩效作为工资合约的要价标准,或者以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的固化比例来抑制股东的资本弱化行为,在实现税收合约保护的同时保护劳工权益。
(二)提升集体谈判制度在劳工权益维护方面的实质性效果
集体谈判制度在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成为劳资自治的一项重要制度。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集体谈判制度尚未落实,往往处于“有形式、无内容”的尴尬境地(12)。因此,如何发挥集体谈判在劳工权益维护方面的应有作用,已经成为包括劳工群体在内的社会期望。
“合则两利、败则两伤”作为工会博弈的基本准则应该提倡,以“数据说话”为基础的“柔性诉求”也应予以鼓励,但由此产生的谈判成本也可能抑制工会主动维护劳工权益的积极性,而工会在现阶段巧用的“压力机制”也仅仅能有限保障工会博弈目标的实现。就我国市场化劳动关系的现状而言,将劳动关系的调整完全寄托于现有的“压力机制”也不现实,集体行动权作为提升劳动者谈判能力的重要手段,在未来的政策选择中可能更为重要。当然,基于中国特有的国情考虑,制度层面的集体行动权必须是一种有限的、可操作和可约束的权利。就当前的现实而言,比较有效的做法就是在政府的主导下,从制度层面完善与集体谈判相关的信息披露制度,使工会的工资协商有据可依。
(三)不断彰显工会在劳工权益维护中的应有功能
只要工会主动作为,在劳工权益维护方面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但从社会观察的大量事实却发现,工会在市场化劳动关系中的应有功能彰显不足,多数企业工会在劳工权益维护方面与社会期望差异较大,这或许是劳工群体对工会认知度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工会作为维持劳动条件或改善生活状况为目的的永久性团体(Sidney and Beatricd Webb,1920),要“把表达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胡锦涛,2008);为此,“要把更多的资源和手段赋予工会组织”(习近平,2008)。由此看来,工会不仅需要从制度层面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手段,而且在实践层面不断累积与资方谈判的博弈经验。就本文所关注的主题而言,工会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源头参与劳工权益的维护:(1)企业层面,应在企业成立之初的有关公司章程或协议中,征求工会的意见,并将工会的关注纳入其中,而这一工作将有赖于上级工会的主动作为;(2)宏观层面,国家在出台与劳工权益相关的经济政策时,应充分征求工会的意见,并将工会在微观层面的关注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制度规则。
综上所述,理性经济人的股东所主导的资本弱化行为尽管无可厚非,但对劳工工资合约的侵蚀逻辑是客观存在的,在实践中也已显现。在劳动关系领域抑制资本弱化行为对劳工权益的影响,既需要作为劳工权益代表者的工会有效运用博弈策略,同时需要在制度层面上对资本弱化行为进行规制,以促进劳工权益的实现。
收稿日期:2009-07-20
注释:
①“税盾效应”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费朗哥·莫迪格里安尼和默顿·米勒在研究现代资本结构时提出的一个避税理论。主要的意思是指,当债务成本(如借款利息)在税前列支时,股东同样的投入资本可以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
②如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第46条规定,“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21号)也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不超过规定比例和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计算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不得在发生当期和以后年度扣除”。
③据统计,2003年,外企在中国平均亏损达51%至55%,年亏损金额逾1200亿元。另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5月23日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1-4月份,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利润(1075亿元)下降幅度为3.5%。对此,国家税务局官员认为,亏损企业2/3属于非经营性的原因,意在避税。保守估计,我国一年流失的外资企业税收已达300亿元(引自: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3700039.html,《2/3外资企业亏损之意在避税》。
④该比重的会计语言是“资产负债率”,即一定的资产总额中负债比中有多大,理论上而言,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财务风险越大,但只要企业的资本收益率高于债务资金利息率,债务资金对股东自有投资收益具有放大效应,即积极的“财务杠杆”效应,如果资本收益率低于债务资金利息率,可能造成消极的“财务杠杆”效应,现实生活中的“借鸡生蛋”或“鸡飞蛋打”正是这一理论的通俗演绎。
⑤在国有企业中,我们可能观察到的现象是:劳工(工会)与管理层合谋,向国有企业的监管机构(如国资委)报告较好的财务绩效。而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1)和管理层比较,国有企业的监管机构无疑具有明显的信息劣势,尽管这种信息劣势可以通过加大信息监督成本的方式予以弥补,但由于监管机构人员本身的自利性可能并没有让相关的监督措施得到严格执行;(2)尽管监管机构也希望将管理层的合约收益与股东受益进行“捆绑”,但这种“捆绑”的期限无疑是较短的(以中央企业为例,任期考核也仅仅只有3年);(3)国有企业可能是特例,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和劳工(职工)在利益方面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既是国有资本的属性决定,也是意识形态决定的结果。所以,我们观察到的国有企业现象并不能否定文中提出的管理层与股东合谋侵害劳工工资合约的判断,换句话说,国有企业股东的非完全经济人属性,决定了管理层可能与劳工在合约收益方面达成某种程度的一致。
⑥支持这一判断的基本理由是,在我国的对外开放中,各级政府对外资需求的冲动十分强烈,并以超国民待遇的方式对外资进行招揽。而劳工权益无疑是超国民待遇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个别地方甚至在引资过程中承诺可以不执行最低工资制度。
⑦此处所言的“被侵害”有两层含义:一是“资强劳弱”的社会现实使得劳工群体只能被侵害,当然这种侵害必须以劳工现实可接受、将来不抗争为前提;二是资本权益优先的制度性偏好使得劳工权益不得不接受资本“貌似合法”的合约安排,如保护劳工权益的最低工资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资方“婉拒”劳工共享企业绩效的“挡箭牌”。
⑧当然,这些事实上的集体行动鲜有工会牵头或者组织,因此,我们更习惯用“职工权益自救”这一中性术语予以表述(参见:任小平,许晓军.《职工权益自救与工会维权策略:基于“盐田国际”罢工事件的观察》.《学海》,2008年第四期)。
⑨此两个个案并非杜撰,是2009年3月份笔者去沿海某省调研时发现,调研的动因源于该两个企业在工资谈判方面曾经被CCTV报道过,作为观察工会博弈行为的样本,应该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⑩引自:《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专辑》,《工运研究》,2008年第9期,p15。
(11)相关规定在《公司法》、《税法》甚至《会计准则》中都有体现,如2005年《公司法》第20条第1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即揭开公司面纱制度;财政部在2006年发布的关于母公司股权投资减值的处理中,也将原来规定的减计到零修改为:如果母公司事实上承担对子公司的责任,可以对长期借款继续提取减值准备。
(12)全国总工会的调查的数据表明,45.6%的职工表示不知道本单位是否有集体合同,48.5%的职工不知道集体合同能否发挥作用,38.5%的职工不知道本单位是否开展了工资集体谈判。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的集体谈判制度与劳工的现实期望差距较大,尤其是“运动式”的集体合同签订方式,很难真正维护劳工权益(引自:《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专辑》,《工运研究》,2008年第9期,p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