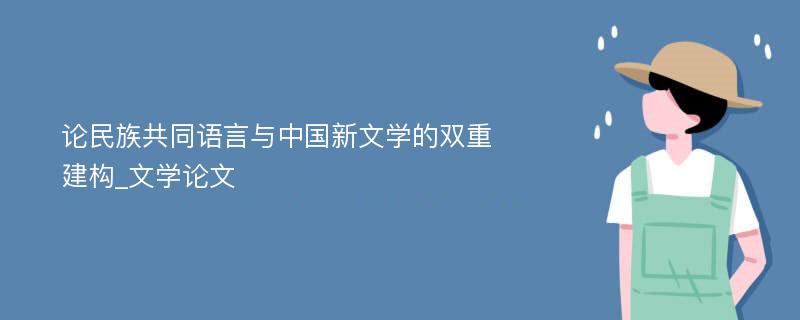
论民族共同语和新中国文学的双重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同语论文,新中国论文,民族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共同语想象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意义早已被安德森揭示出来①。而柄谷行人则通过研究日本现代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分析日本民族国家建制与日本现代文学之间的勾连②。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本文从民族共同语建构这一新的视角,研究新中国民族共同语和文学书写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追溯其历史起源,重新思考新中国文学是如何发生和如何被建构的。值得指出的是,和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国家共同语的想象和建构不同,现代中国所谋求的现代民族国家独立自主不是臣属国对宗主国的离散,而是和现代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国家的自我更新和重构。但即便如此,文学书写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民族共同语想象和拟构与民族国家的自我更新和重构中。
一
现代中国,民族共同语想象、拟构与白话文革命之间的关系被明确地揭示出来并且进行系统阐释的应该是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其副题“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标志着从晚清开始分头进行的以口语为基础的“新文体”革命和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官话”推广在此合流。这是新中国民族共同语和文学书写双重建构的现代起源。在整个民族共同语建构框架里,目标“言文一致”的“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致力于现代汉语书面语由“文言”向“白话”的语言的现代性转换。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现代文学革命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民族共同语想象和拟构的任务。胡适认为:“标准国语不是靠国音字母或国音字典定出来的。凡是标准国语必须是‘文学的国语’,就是那有文学价值的国语。国语的标准是伟大的文学家定出来的,绝不是教育部的公告定得出来的。”③胡适希望“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现在的问题是,在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国语”还处在想象和拟构时,凭借什么去实现更高层次上的“文学的国语”?胡适认为:“我们尽量采用《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用的,便不用它;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法,绝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绝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而“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④。钱玄同认为,有时“非用方言不能传神,不但方言,就是外来语,也采用”⑤。傅斯年也认为,一方面“乞灵说话”⑥;同时可以“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法(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⑦。
在世界语言学史上,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往往和民族意识觉醒、民族国家形成联系在一起。地方性语言(方言)与宰制它的权威语言对抗而形成民族共同语。而现代中国语言的状况则是“书”同“言”殊,因此“新文学的白话”从来不是局限于某一个地方性的方言。从一开始,作为“国语的文学”语源的“白话”就纠缠着雅与俗、文言与白话、本土化与欧化、知识分子与大众,以及方言、土语的地方性和共同性等等许多有时相互补充,有时却相互冲突的语言因素。因而一个作家一旦进入白话文的书写场域,他所运用的“白话”,他想象中的“国语”就难以避免“语出多源”。这一方面,固然为共同性的“国语”建构提供了多重想象的空间;另一方面,也为“国语”同一性的达成带来困难。胡适等人的文学实践也证明,语源本身的“杂糅”,“各人所用的白话不能相同,方言不能尽祛”⑧,使得“国语的文学”的尝试,最后得到的“文学的国语”只能是一种“杂糅”的“国语”。
这种“杂糅”的“文学的国语”在一九三○年代初被瞿秋白批评为“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⑨。而“杂糅的国语”显然不能担负“中国的标准国语”的民族共同语建构的任务。胡适等人希望通过“国语的文学”的尝试,锻造“文学的国语”,在与“文言”的对抗中把现代汉语“白话”的可能性充分地呈现出来,实现“国语”和“文学”的同构和双赢。其结果是,他们以否定文言文“言文疏离”,追求白话文“言文一致”为目标,最终又事实上造成新的“言文疏离”,导致“白话”和“国语”之间更深刻的断裂。尽管如此,胡适等人的“国语文学”运动毕竟建设性地、多向度地为“国语”建构拓展了新境。民族共同语的想象、拟构和生成不是仅仅依赖语言专家凭借体制的权威来制定和推行,而必须参与进文学书写。在文学的生产和传播中,民族共同语被锻造、接受和认同。
如果时代能够给胡适等人充裕的时间,他们能不能在反复书写中,祛除芜杂,锻造出“文学的国语”?但时代没有给予他们这样的机会。随后的一九三○年代,是一个“需要黑面包”,而不是“埋头制造细饼干”⑩的时代。“制作大众文艺化的文艺”(11)的现实使命,使瞿秋白等人把“用什么话写”作为“普洛大众文艺的一切问题的根本问题”。他们从“白话”的语源上对“国语文学”所依凭的语源进行清理和澄清,重新思考“言”与“文”的关系,提出“要用现代话来写,要用读出来可以听得懂的话来写”(12)。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决议指出:“作品的文字组织,必须简明易懂,必须用工人农民所听得懂以及接近的语言文字,在必要时容许使用方言。因此作家必须竭力排除知识分子的句法,而去研究工农大众言语的表现法。当然,我们并不以学得这个简单的表现为止境,我们更富有创造新的言语表现法的使命,以丰富提高工人农民言语的表现。”(13)同样是“乞灵说话”,此时的“说话”已经被明确到对“工农大众言语”的汲取和提高之上。在随后一九三四年的“大众语”问题的讨论中。“大众语”的倡导者进一步认为,“大众语”“不但和僵尸式的文言不相容,同时也不能和现下的所谓白话与国语妥协”。真正的“大众语”应该“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14)。“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也当然地被置换成“大众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大众语”。同样“标准的大众语,似乎还得靠将来大众语文学的作品来规定”(15)。
毫无疑问,普罗文艺运动的文艺语言大众化和“大众语”倡导,是现代中国语言变革和白话文学的大众化、底层化和普通化运动。它确立了被赋予特定意识形态内容的语言同一性和文艺大众化的“大众标准”和“大众方向”,将现代语言和白话文学的变革从“知识分子一个阶层”的东西推进、扩展到“普遍的大众”阶层。从积极意义看:第一,它一定程度上矫正了五四所行“白话”,“文言、白话的混用现象”,“外文词的异译、句式的欧化”(16)等非普通化的语源杂糅现象,使白话文的语言实践归结到“乞灵说话”。在“随着大众生活的进展而进展”的“大众语”运用中“创造新的言语”。第二,共同语建构是一个回环往复的过程。“大众语”源于广阔的底层社会,从大众和底层汲取语言资源,又通过大众文艺的阅读、渗透和沉潜,回到广泛的社会底层,为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社会成员围绕“大众文艺活动”,广泛地参与到共同语建构的语言实践,有利于民族共同语建构完成之后的推广和普及。
但也应该看到,由于一九三○年代左翼特定的意识形态历史语境,对“工农大众言语”和“大众语”的片面强调,忽视了语言的独立性和语言生态的多样性,不利于民族共同语丰富性的实现。从文学书写的角度进而也制约了文学多样化的语言表达。而且,当“乞灵说话”的“说话”被置换成“工农大众言语”或者“大众语”之后,原来还不明显的语言的地方性和行业性问题成为一个不得不正视,但事实上在一九三○年代却没有能解决的问题。“工农大众言语”之“言”、“大众语”之“语”本身客观存在着地方性的方言和行业性的行话,即便达成“言文一致”,书面语之“文”也必然存在地方性和行业性的印记,并不能兑现超越地域和阶层的民族共同语的同一性。而且,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文艺语言大众化”和“大众语”的倡导者还不能有效地将“工农大众言语”或者“大众语”转换成“文艺作品的语言”。即使赞同“大众语”的作家也不得不重新拾起“国语运动”中的减法和加法,减去方言中“太僻的土语”,加上“欧化”语文的“新字眼,新语法”(17)。但即使如此,一九三○年代文艺语言大众化和“大众语”的语言理论和实践,从“大众”中间找寻和挖掘正在生长的“活”的语言资源,不失是一条能够顾及乡土中国辽阔的底层社会,最大可能弥合“言文疏离”的道路。其中仍然存在的“言”与“言”的差异,到一九四○年代毛泽东的新语言计划倡导“人民的语言”阶段,经过赵树理等人成功的“大众语文学”实践将最终被解决。
二
始于一九三○年代末的“抗战文艺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论争,承一九三○年代的文艺语言大众化和“大众语”运动。在这两场论争中,民族共同语建构中的一些核心问题,像民族共同语的源泉、方言和国语的关系、语言的地方性和共同性的转换、文学和语言如何在互构中实现大众化等问题都或多或少地被涉及到。所以有人认为,一九四○年代“大众化通俗化的工作,最主要的是语言问题”(18)。在他们的视野里,发端于五四时期的“国语运动”由于和大众的脱节,并没有渗透到广阔的底层社会,成为真正意义的全民意义“民族共同语”。更有极端者,质疑“北京官话”作为“准民族共同语”的合法性。当时就有人认为:“真正的国语在哪里呢?可以说现在还没有,还要在各地的方言统一的过程中成长起来。”(19)“各地的方言统一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民族共同语想象和拟构,是地方性方言自主性的择选和趋同。在“抗战文艺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论争中,继一九三○年代“大众的发现”,方言的意义被充分揭示出来。“中国语言文字的出路,是要到方言里去想办法的。”(20)“由高度的多元的发展(方言文化、方言文艺运动)争取一元的统一(未来的民族统一语文和国民文艺)。”(21)与此同时,在华南等非北方方言地区,方言文学的创作也被尝试着实践着。他们认为,“以纯粹的土语写成文学,专供本地的人阅读,这些本地文学的提倡,一定可以发现许多土生的天才。这些作品,我想在将来的文艺运动上,是必然地要起决定的作用的。”(22)
方言的重新肯定和方言文学的倡导和实践,对一九四○年代“大众语”进一步细化,使局限在知识层的民族共同语的想象和拟构与更广阔的底层社会和更丰富的地方语言资源发生关联。从理想状态看,也许确实可以通过“方言的文学”锻造出“文学的方言”,进而将“文学的方言”提升到民族共同语层次。但如果真的依靠方言和方言之间的自主择选和趋同,民族共同语的生成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于不同政治区域分而治之的现实使方言自主性择选和趋同的思路部分地获得了展开的理论话语空间。而且因为救亡和战争动员的需要,也现实地需要给予方言文学以自己的生存空间。在一九四○年代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明明是偏离“共同语”的“方言文学”却被鼓励和提倡。值得注意的是,对方言和方言文学的极端强调必然会导向瓦解民族语言同一性。当时就有人认为:“大众语可以理解做国语——官话——的反面。里面包含方言与俗语。前者是地方性的,后者是阶层性……”(23)而民族语言共同语的建构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部分。对民族语言同一性的瓦解进而有可能会走向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离散。
和地方性方言自主性择选和趋同而成为“民族共同语”的思路不同,毛泽东在解放区提出的新语言计划试图借助政党意志自上而下的想象、阐释,进而在文学和语言的双重建构实践中生成语言的同一性和实现文学的一体化。事实上,从世界范围观察,几乎没有一个民族共同语的建构完全凭借地方性方言自主性的择选和趋同。往往“有时候是选择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的方言,有时候是选择政治集权和中央统治所在地的方言,有时候是宫廷把自己的语言强加给国家。”(24)同样,现代中国“在寻求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普遍的民族语言和超越地方性的艺术形式始终是形成文化同一性的主要形式。”(25)
延安整风,语言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提出来。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题为《反对党八股》的讲演。这是延安整风运动中整顿学风的纲领性文件。毛泽东指出:“党八股也就是洋八股。……我们为什么叫它党八股呢?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26)在随后不久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的讲话再次从政治立场谈到语言和文艺大众化关系的问题。“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27)应该说,以“人民的语言”为核心的毛泽东新语言计划更多的基于政治建构策略和思想统一的考虑,还不是有意识的民族共同语设计,当然更不可能提供具体的民族共同语设计方案。语源集中到“人民的语言”之“言”必然会导致文学书写语言之“文”在政治规范牵引下的趋近,为民族共同语的建构提供基础。
在各解放区,毛泽东的新语言计划很快进入到实践层面。应该指出的,这个过程中包含着语言的提高和发展内容。“不是迎合大众,而是提高大众”(28)。在提高中,发展“人民的语言”,推动语言的当代变革。他们认为:“新文学却很少有人对现存白话,也即是新文艺现在所用的一种新的民族形式作过慎重选择和挑剔清洗的工作,使它更臻完善,更能成为文学的语言。”(29)新文学没有做的“慎重选择和挑剔清洗的工作”,现在由解放区的作家去做了。解放区的文学书写所运用的文学语言一开始就汲取着大众丰富的语言资源。从底层中来,经过甄别、加工、清洗,进而锻造出新的“文学的语言”,再通过文学阅读回到底层。经过这个过程,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采用了许多从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新的语言”,“在他的作品中,他几乎很少用方言、土语、歇后语这些”(30)。其结果是,“不仅每个人物的口白适如其分,便是全体的叙述文都是平明简洁的口头语,脱尽了五四以来欧化体的新文言的臭味”(31)。赵树理在群众的、普通的、对话的语言同一性和审美的、艺术的和独创的语言个人性之间寻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实现了文学书写和语言实践的双重建构。
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对中国共产党文学想象和语言计划的顺应和认同使文学书写一体化的完成,通过广泛的阅读和传播客观上实现了知识阶层和大众贯通的一体化语言认同。毛泽东的新语言计划经过阐释,在实践中被转换和安置,它的成功必然会在新中国产生后效。因此,“延安整风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是一次整顿言说和写作的运动,一次建立整齐划一的具有高度纪律性的言说和写作秩序的运动”(32)。很多语言学家把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归功于一九五○年代后开展的推广“普通话”运动,认为这一运动最大成绩是为全民族确立了典范的现代白话文和普通话,使口语和书面语都有了一种民族共同语为依据。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错。但是语言学家们似乎忽视了在毛泽东的新语言计划影响下,赵树理等解放区作家文学实践所达成的真正意义上的“言文一致”。“大众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大众语”事实上已经在解放区这个特定的政治区域成为现实的存在。这在中国现代语言和白话文学变革史上是一件富有意义的大事。
毋庸讳言,解放区新语言计划、“为工农兵”文学实践和政治权威之间存在着彼此借力的默契,是在特定的政治建构中完成语言同一性和文学一体化的双重建构。这个范式同样被新中国所因袭。早在一九三○年代初就有人指出,大规模制作大众化的文艺,“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33)。文艺如此,和文艺存在互构的语言变革当然也是如此。延安解放区,毛泽东开展的新语言计划,无论是语言想象、制度设计,还是路径选择以及运用于文学的语言策略和实践等,无不借“政治之力的帮助”而得以实施。在现代民族共同语想象和拟构的过程中,虽然从晚清开始就有体制的介入,但实际上直到一九四○年代解放区和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才真正意义上结束了现代中国政治涣散、无序的局面,也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借助体制的力量进行广泛的动员,完成包括民族共同语构建在内的民族国家的构建。因此,相比较于未来更大规模的新中国民族共同语和文学建构,解放区的新语言计划和文学实践只能说是一个预演。
三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在延安解放区实验的新语言计划可以在现代民族国家框架里借助政党和国家力量在更大范围内推行。首先是目标规划、机构设置、制度设计和舆论动员。一九四九年十月,与新中国成立同时,“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组成。这个协会,一九五二年二月合并于国家机关,就是政务院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十月,依照国务院组织法,列为直辖机构之一,改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曾给当时的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写信,提出起草一个中央文件来纠正写电报的缺点的问题。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为贯彻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有关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社论”明确了语言在政治建构中的重要意义,“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关乎“政治的纯洁和健康”,“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在今天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34)。应该说,经过一九三○年代的和一九四○年代的“去知识分子化”的语源净化和语言清洗,现代汉语书面语至少在中国共产党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区域被一定程度地“纯洁和健康”,合于政治规范。但一九四○年代特定的历史语境,使得方言、土语这些潜在的瓦解民族共同语同一性的地方性力量也得到充分发展。在初步完成了民族国家统一的新的历史语境中,作为民族共同体想象重要部分的民族共同语必然会对方言和土语进行清洗。“社论”批评有些人:“不但不重视和不肯好好研究祖国的语言,相反地不加选择地滥用文言、土语和外来语,而且故意‘创造’一些仅仅一个小圈子才能懂得的各种词。”(35)土语被与文言和外来语相提并论成为新时代语言纯洁的污染源。事实上,文言和外来语经过多次现代语言变革的清洗,影响力已经被削弱得不足以成为抗拒的力量。而经过一九四○年代战时的片面繁荣,方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事实上成为民族共同语同一性最大的障碍。
“社论”发表之前,语言学家和作家已经就方言和民族共同语关系的问题展开了论争。一九五一年三月《文艺报》就《文艺学习》一九五○年八月发表的邢公畹的《谈“方言文学”》开展讨论。邢公畹认为:“‘方言文学’这个口号不是引导我们向前看,而是引导我们向后看的东西;不是引导着我们走向统一,而是引导着我们走向分裂的东西。”(36)讨论中,大量运用方言土语的作家周立波认为:“在创作中应当继续大量地采用各地的方言,继续地大量地使用地方性的土语。要是不采用在人民的口头上今天反复使用的,适宜于表现实际生活的地方性的土话,我们的创作就不会精彩,而统一的民族语言也将不过是空谈,更不会有什么‘发展’。”(37)随后四月出版的《文艺报》第十二期发表了邢公畹的辩论文章,指出周立波混淆了“语言”和“文体”。认为周立波讨论的“方言”是把“方言”引入创作的“文体”因素,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言”。但《文艺报》没有把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深入探讨下去。一定程度上,从一开始讨论,《文艺报》的结果就是预设。不然,就不能理解为什么问题刚刚展开,《文艺报》就以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争取语文的纯洁》置于双方第二次争论的一组文章之前,而草草地结束了争论。一定意义上,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立场也是《文艺报》的立场。显然,这场争论的目的不是为方言赢得更多生存空间,而是敦促方言的尽快退场。
与此同时,民族共同语想象最为重要的共同语标准也在探讨中。“以北京语音为基础语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新中国民族共同语拟构在这方面继承了晚清以来“国语”研究的遗产。但民族共同语的语法规范“典范的白话文著作”则需要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进行再择选。
丁声树等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虽然到一九六○年十二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38),但本书的初稿是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在《中国语文》月刊一九五二年七月号至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号连续发表的《语法讲话》。该书使用例句注明作者的共六十二人。引用例句条数按从多到少顺序排列:老舍二百八十八条,赵树理二百五十五条,毛泽东二百三十三条,杨朔一百五十五条,袁静一百三十六条,鲁迅一百二十七条,曹禺八十七条,杜鹏程三十二条,周立波十九条,丁西林十八条,欧阳山十一条,巴金、叶圣陶、高玉宝、王向立七条,卢耀武六条,马烽、刘白羽、矫福纯五条,茅盾、朱自清、崔八娃、马烽和西戎四条,王希坚、魏连珍三条,冰心、萧红、孙犁、王愿坚、康濯、何永鳌、萧高嵩、西虹、韶华两条,郭沫若、阳翰笙、安子文、李准、杨尚武、洪灵菲、周恩来、薄一波、峻青、蓝光、萧平、张仲明、田流、吴梦起、陶怡、曹克英、鲁彦周、黄文俞、王西彦、韩旭、闻捷、胡考、白原、任美锷、许寿裳、梅阡、《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一条。
语言的诸种要素中,修辞是体现语言文学性,衡量作家对母语把握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从修辞的角度去择选“典范”,肯定会和语法角度的择选存在差异。一九五三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张志公的《修辞概要》涉及例句注明作者的共三十七人(39)。引用例句条数按从多到少顺序排列:鲁迅五十条,老舍四十三条,丁玲三十八条,赵树理二十五条,周立波二十四条,袁静和孔厥二十条,毛泽东十六条,巴金、朱自清九条,茅盾八条,欧阳山七条,郭沫若、田间六条,叶圣陶、张天翼五条,闻一多、李季、孙犁、西戎和马烽、李株三条,曹禺、周扬、艾青、杨朔两条,宋文茂、胡乔木、徐光耀、萧殷、刘少奇、夏衍、冯至、黄药眠、董迺相、贾芝、臧克家一条。引用例句涉及作品篇目最多的是鲁迅,共二十一篇。引用次数超过二十条的作品分别是《暴风骤雨》二十三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新儿女英雄传》二十条,均为解放区的代表作,其中前两部获斯大林文艺奖。
两本著作的例句选择值得思考的东西很多。比如,如果不是从一九三○年代末以后毛泽东对鲁迅的不断经典化,语言欧化的鲁迅能够进入这个名单吗?而且从语法和修辞的不同角度,鲁迅的位置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比如毛泽东进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之列对新中国文学书写在语言方面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比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为何在两部书中都集体失踪?比如以方言彰显写作特色的周立波为何同时出现在两部著作,而且《暴风骤雨》竟然是引用最多的作品?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共同语建构中提出,什么是“典范的白话文著作”,其中隐含的是文学史叙述和经典化的问题。这当然是新中国文学建构中的重要问题。从这两组名单中明显看到新中国文学在确立自己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同时,重述现代文学谱系的企图。在新中国民族共同语构建的视阈下,现代文学史被重新叙述。而这样的叙述将会通过民族共同语的推广和普及被认同。凭借民族共同语建构,老舍由于他的方言优势在这个谱系中地位姑且不论。鲁迅、毛泽东、作为新中国文学直接源头的解放区文学和正在生成的当代文学权威性被确认。鲁迅被放置到和解放区文学、新中国文学,甚至是毛泽东一个文学谱系上被再认和识别。语言视角使这样的文学史描述自有其合理性。
新中国民族共同语的拟构对主流意识形态充满妥协,但又试图在主流意识形态容忍的限度中,尊重语言自身的规律。比如关于毛泽东,虽然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早在一九四○年代就有人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是中国当代造诣到最高境地的文章。”(40)但两部著作引用的条数,毛泽东都不是最多的。张志公著作,鲁迅成为引用条数和涉及作品数最多的作家。无疑,这种在鲁迅同时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集体消失难以避免的政治语境中,以鲁迅自身的丰富性来弥补这种集体消失所带来的民族共同语的缺失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明智的语言策略。还是张志公著作,引用超过十条的七人中,有四人的方言区域非北方语系。这四人虽然都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推举或者容忍的,但非北方方言的地方性肯定会遗存在他们的写作中,从而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民族共同语的语源。如果把这两部当时很有影响的语言普及著作和同时代文学史著作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他们之间存在明显的趋同和共构。新中国民族共同语建构是一场空前的革命,而它引动文学经典的再认识又是一场新的文学革命。借助推广民族共同语的国家行为,经过新中国重构后的现代文学能够迅速地渗透到民间低层社会。
与典范确立同时进行的是理论清理。新中国成立后是对胡适的语言学观一边倒的批判。在这场“倒胡”潮流中语言学界的魏建功、殷德厚和文学界的何其芳、黄药眠等人都先后发表了重要的论文(41)。他们以新的政治意识形态为尺度,质疑和拆解胡适在现代汉语变革史中的权威性,全面清算胡适的语言观。在这些特定政治语境下的有意误读中,胡适“为白话文学伪造了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家谱”(42),“语言只是某几个文学家或者是某个文学家造的,当时的白话只来源于过去的书面语”(43),“看不到人民,想不到文学语言的源泉在人民大众”(44),这必然导致对文学革命与现代白话文运动的作为民族共同语建构的历史起源的质疑和拆解。既然“文学语言的源泉在人民大众”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工农大众言语-大众语-人民的语言-民族共同语的现代语言发展谱系的历史建构自然也获得合法性和权威性。而这个民族共同语建构的历史谱系和“典范的白话文著作”遴选过程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集体失踪相互印证。
新中国民族共同语最后的完型和确立要到一九五五年十月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此次会议形成的决议被“政治的强力”合法化、权威化。一九五五年十月,《人民日报》再次以“社论”的形式对“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的内容在政治和语言两方面的合法性予以确认。一九五六年二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民族共同语进入自上而下的全民共同语认同阶段。置身在新时代的语言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显然都意识到民族语言同一性的大势。新中国民族共同语建构以民族语言的同一性为目标,同时也把和语言关系最密切的作家个人书写的同一性完成了。政治立场和语言立场叠合,几乎成为新中国作家的集体认同。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在《文艺报》举办文风座谈会,老舍、臧克家、赵树理、冰心、叶圣陶、宗白华、王瑶、郭小川和陈白尘等二十二位知名作家、诗人、戏剧家、文艺理论家和文学史专家参加。座谈会上大家达成共识:“语言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普及的、通俗的,就是用普通的能说明白一切的,不论多么高深的道理都能用浅显的语言说明白的”(45)。民族共同语建构完成后,以“说明白”为共同性标准来规范文学,且获得作家的广泛认同,这标志着文学语言一体化的建构也已经实现。
从观念认同到创作实践中对民族共同语的自觉选择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尤其是非民族共同语基础音系的作家。因为他们这样的选择不仅仅意味着一种语言技术,而是言说和话语方式的转换。新中国成立前后,作家创作的转型以及一部分作家在转型过程中,中断自己的写作,文学史研究曾经给出过许多解释。那么,从民族共同语建构的角度看,方言运用过程中生成的地方性和个人化话语空间逐渐逼仄,是不是导致作家创作终止的原因呢?比如沙汀,在现代文学格局中,沙汀是以“善用俚语”(46),善用“活生生的土话”(47)彰显他个人化的“四川地方性”的。但新中国成立后,那个现代文学史上的“地方性”的四川和“个人化”的沙汀一齐消失了。和沙汀相比,周立波的方言腔更为突出,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却能被时代有限度地容忍,保持着持续的写作,而且“地方性”和“个人性”也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茅盾在一九六○年第三次“文代会”报告中指出:“作者好用方言,意在加浓地方色彩,但从《山乡巨变》正续篇看来……太多的方言反而成了累赘。”(48)实际上,和《山乡巨变》相比,《暴风骤雨》充满了更多的方言土话,但作为解放区文学的重要收获,其经典性被“斯大林文艺奖”所巩固。而《山乡巨变》虽然也有肯定性的个人评价(49),但主流意识形态对它却充满微词。《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两部小说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生成史和评价史,正揭示了对待方言问题上从解放区到新中国政治策略的微妙调整。在创作《暴风骤雨》之前,一九四三年,周立波起初心理上“以为只有北方人才适宜于写北方”(50),而《暴风骤雨》则是南人操北腔,知识分子用土语。成为知识分子改造自己,实践毛泽东新语言计划的成功尝试。因而,即使这部小说方言运用得很“隔”,但由于“政治正确”保证了它顺畅地被经典化,并且在接收的过程中把其中的方言因素强调出来。而写《山乡巨变》的周立波,从《暴风骤雨》的北方回到他最熟悉方言的南方故乡,在方言、土语的运用上完全摈弃了《暴风骤雨》中的“异乡人”的“隔”,而且在新中国民族共同语建构的时代语境下,周立波也作出了很多妥协和迁就。但即使作出了这样的努力,《山乡巨变》仍然成了一部在他所处时代的问题之作。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山乡巨变》不只是“群众语言和夹杂近于欧化的知识分子腔调”(51),更重要的是周立波要在方言、“欧化的知识分子腔调”和民族共同语之间寻找个人性和地方性的书写空间。方言、“欧化的知识分子腔调”在共同语的压抑下,不但没有臣服,相反却和它从容地周旋,甚至是反制。这样的背离,在一个以追求同一性为目标的时代是不能被容许的。
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于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重要内容的文学革命之中,五四初期的这场语言革命对现代文学形式的产生和发展也就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中国现代文学是这场语言革命的产物,同时它也必然地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语言革命的后果。
首先,新中国民族共同语建构是共同语同一性和文学书写语言一体化的双重建构,是一场追求“言”与“言”、“文”与“文”、“言”与“文”一致的纯洁化运动。现代中国,民族共同语的想象和建构过程中,明显存在向“乞灵说话”的“说话”靠拢后,经由“工农大众言语-大众语-人民的语言-民族共同语”,最终在新中国完成民族共同语同一性和文学书写语言一体化的双重建构的历史线索。胡适等人的语言和文学革命所缠绕的现代汉语变革的目标追求和效果指向与文学语言的本体要求、“国语”想象共同性与“白话文”书写个人性、“言”与“文”、欧化与本土化、知识阶层与底层大众、文学书写、语言研究个体实践与体制等等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国语”和“白话文”的双重建构从一开始就存在许多歧异。一九三○年代“普洛文艺”和“大众语”、一九四○年代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论争中的语言实践,试图通过知识阶层和大众之间语言共同体缔约来消除歧异,但还是没有能够解决“言”与“言”不一的问题。和这些语言变革实践不同的是,解放区的新语言计划在有效的政策和制度保障下,在规定的政治立场下,推动知识分子沉入民间,融入大众。文学书写成为制度框架下规定了方向和路径的“写大众”和“为大众写”。纯洁化,对人民大众语言源泉的片面强调可能使同一性和一体化的缔结和实现相对容易,但它是以损失民族语言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为代价的。
第二,从文学和语言不同的发展规律看,民族共同语和文学书写之间的互构,并不必然导向共同语同一性实现之后文学书写的语言一体化。文学书写应该是一个民族语言活动中最具有实验性、探险性的部分,它不断拓展民族语言的疆域,推动民族共同语在动态中不断生成新的同一性。借文学“新民”、“立人”和“救亡”,倡导“文艺的大众化”和“文学为工农兵服务”,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建构都需要追求文学语言的大众化、普通化和文学书写的一体化。从解放区到新中国文学,语言和文学的纯洁化运动展开,并被赋予政治意识形态内容,文学书写中为语言预留的实验和探索的空间越来越窄,以至于发展到对共同语同一性的完全顺应。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成为重要的规范力量。它不仅仅很快完成了解放区文学和语言大众化的互构,而且在新中国成立短短五六年时间,就迅速完成了汉语规范化,并通过国家动员机制推广普通话,基本实现民族共同语的建构。而建构完成的民族共同语转而成为规范文学书写的前提和现实基础,决定新中国不同的文学体裁和文学样式的形式发展,导致了新中国文学文体特征和文学文体风格的趋同。从此,方言文学、文言文学和欧化体的文学尝试在新中国文学中彻底丧失合法性。
第三,在民族共同语的建构过程中,作家必然自觉地对语言同一性存在顺应和偏离。从新中国文学的现实看,通过汉语规范化和普通话的推广,新中国在“言”的逐步趋同前提下规范个人书写之“文”,实现真正意义上“言文一致”基础上的文学语言一体化。这中间虽然依然存在着有限度的反抗,但这样的声音在同一性和一体化的大势中显得很微弱。一九五○年代就有人质疑:“拿推广普通话的理由,反对和非难作家的采用方言”,“忽略了作家也提炼语言丰富普通话的责任”(52)。事实上,民族共同语和个人书写之间的紧张甚至对抗是每一个时代和民族都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多方言的中国表现得更为激烈。新中国民族共同语建构在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中迅速地完成,其实一些问题并没有被充分展开就给出了答案。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对语言立场、文学立场和政治立场同一性的强调,可能会暂时把这样的紧张和对抗遮蔽、悬搁和压抑,但一旦我们意识到语言问题、文学问题有着和政治问题不同的独立性,并给予这种独立性充分的表达空间,原来遮蔽、悬搁和压抑的问题迟早要被揭示出来。
注释:
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②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③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2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④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31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⑤⑧钱玄同:《尝试集·序》,《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05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⑥⑦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19、223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⑨(12)史铁儿(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第38、37-4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⑩沈端先(夏衍):《所谓大众化问题》,《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第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11)王独清:《要制作大众化文艺》,《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第1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13)《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14)陈望道:《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第21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15)陈子展:《文言-白话-大众语》,《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第20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16)高天如:《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第14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17)鲁迅:《答曹聚仁先生》,《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第325-326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18)周文:《文化大众化实践当中的意见》,《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二),第139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19)齐同:《大众文谈》,《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二编)(理论论争·第一集),第10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20)严辰:《关于诗歌大众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二),第1376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21)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的实际意义》,《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二编)(理论论争·第一集),第44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22)黄药眠:《中国化和大众化》,《黄药眠美学文学论集》,第177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3)南桌:《关于“文艺大众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二编)(理论论争·第一集),第3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24)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7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5)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学人》(第十辑),第304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26)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7)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0-8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8)周文:《文化大众化实践当中的意见》,《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二),第1386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29)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二),第134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30)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二),第1676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31)郭沫若:《读了〈李家庄的变迁〉》,《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二),第168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32)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花城》1998年第5期。
(33)鲁迅:《文艺的大众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第18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34)《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
(35)《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36)《文艺报》1951年第10期。
(37)《文艺报》1951年第12期。
(38)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39)张志公(环一):《修辞概要》,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
(40)杨献珍:《数一数我们的家当》,《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一),第45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41)魏建功:《胡适“文学语言”观点批判》,《“文学语言”问题讨论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殷德厚:《批判胡适反动的语言学观点》,《鲁迅与现代汉语文学语言·附录》,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何其芳:《胡适文学史观点批判》,《人民文学》1955年第5期;黄药眠:《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黄药眠文艺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42)何其芳:《胡适文学史观点批判》,《人民文学》1955年第5期。
(43)殷德厚:《批判胡适反动的语言学观点》,《鲁迅与现代汉语文学语言·附录》,第63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44)魏建功:《胡适“文学语言”观点批判》,《“文学语言”问题讨论集》,第56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45)老舍:《反对八股腔,文风要解放!》,《文艺报》,1958年第4期。
(46)(47)金葵:《沙汀研究专集》,第228、161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
(48)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人民文学》1960年第8期。
(49)王西彦:《读〈山乡巨变〉》,《人民文学》1958第7期。
(50)(51)周立波:《后悔与前瞻》,《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一),第44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52)王西彦:《读〈山乡巨变〉》,《人民文学》1958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