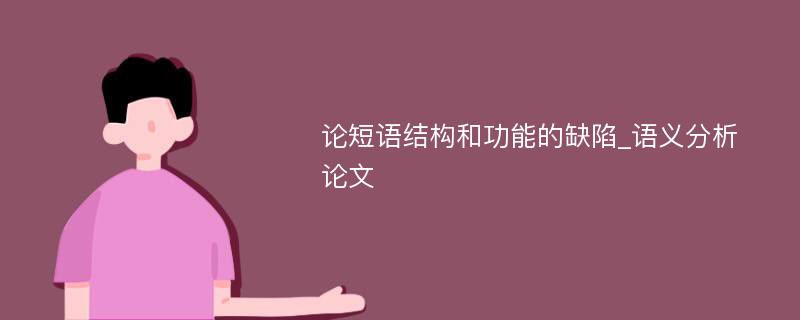
论词组结构功能的虚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组论文,结构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虚化是人类语言演变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虚化可以是词义的由实变虚,也可以是语义功能的由实变虚,词义和语义功能的虚化实际上也就是语言演变中的语法化现象,其在语言的演变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来,语言学家对语法化理论的研究颇为重视,汉语语法化现象的理论探讨则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注:参阅刘坚等《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汉语中词的虚化现象前哲时贤已有论及,而有关汉语词组结构功能的虚化现象则尚欠研讨,本文拟就此略加论述,冀俾益于进一步深入探讨人类语言演变中普遍存在的语法化现象。
一、词组演变为词的词汇语法化
汉语复音词往往是由两个单音词的临时组合而逐渐固定下来的,其最初尚是一个词组,搭配灵活,单音词与单音词之间可以自由搭配,其各自所表示的词义在由其组合成的词组中有所虚化。随着两个单音词之间的搭配关系逐渐固定,这两个单音词也就由临时组合的词组凝固成一个词,由其组合成的词组的词组义在其各自原来表示的具体义基础上进一步抽象虚化,从而形成了由其所组成的复音词的词义。一般来说,单音词大多数是多义的,而由它们组成的复音词大多数是单义的,因而,单音词组合的词组凝固成复音词,实际上也就是多义的单音词抽象虚化成为单义的复音词,即由多义虚化为单义的词汇意义演变,同时也可看作是由词组虚化为词的一种词汇语法化现象。
汉语并列结构词组在凝固成词的过程中,两个单音词各自所含词义虚化的程度不一,如果凝合成词后其中一个单音词词义完全虚化,失去了其原有的词义,仅仅作为另一个单音词的陪衬,这就形成了偏义复词。如“睡觉”本是“睡”和“觉”(古岳切,音jue)两个单音词组成的词组,直至晚唐五代仍表“睡醒”的意思,尚未凝固成词(注:参阅王锳《关于“睡觉”成词的年代》,《中国语文》1997年第4期。)。如:
(1)至年十五,偶因抱疾,梦神人与药,睡觉顿愈。(《祖堂集》卷十)
演变至宋代,“睡觉”这一词组中“觉”的词义已完全消失,虚化为构成表示“睡眠”义的并列复音词的一种语法功能上的构词成份,读音也念成古孝切,今音jiao,从而凝固成一个偏义复音词。如:
(2)续生向夕来卧,冬日飞霜着体,睡觉则汗气冲发。(《太平广记》卷三八《续生》)
随着“觉”词义的虚化,“觉”也由表“醒悟”义的动词虚化为表示“睡一觉”的动量词,如:
(3)唐庄宗时,有进六目龟者,敬新磨献口号云“不要闹!不要闹!听取龟儿口号:‘六只眼儿,睡一觉抵别人三觉’。”(《游宦纪闻》卷二)
又如“缓”与“急”组成偏义复词,其词义偏在“急”,“缓”原有的单音词词义在与“急”组合成词组并进而凝固成词的过程中已消失。如:
(4)缓急人所时有也。(《史记·游侠传》)(5)缓急无可使者。(同上《仓公传》)
偏义复词的词义已不是两个单音词意义的简单相加,也不是两个单音词组合而成的词组义,而是以其中一个单音词的原来意义作为复音词的词义,另一个单音词原有的词汇意义则虚化为一种构词成份的语法意义,实际上也就是两个单音词组合而成的词组虚化为一个复音词,即由一个单音词的词汇意义与另一个单音词作为构词成份的语法意义组合成一个偏义复词。
二、词组演变为虚词的词汇语法化
汉语中的复音词往往是由词组演变而成,汉语中的复音虚词往往也先由词组演为成词,继而进一步演变为虚词,其由词组演变为复音虚词同样也是一种词汇语法化现象。比较典型的例子为现代汉语中表示反诘语气的复音虚词“不成”。(注:参阅钟兆华《“不成”词性的转移》和拙文《也谈“不成”词性的转移》,载《中国语文》1991年第4期和1993年第5期。)
“不成”在唐代以前尚是一个松散的偏正词组,表示各种否定的动作和状态。如:
(6)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
随着表示否定的“不”与表示被否定的“成”这两个单音词之间的搭配关系的逐渐固定,这两个单音词也就由临时组合的词组凝固成一个词,类似于“不朽”、“不良”等,表示“不能”、“不行”义。由于其在句中经常作为修饰补充成份依附在中心动词的前面或后面,这种语法位置导致其词义的进一步抽象虚化,发展至唐代而有“未曾”、“未能”的意思。如:
(7)汨汨避群盗,悠悠经十年,不成向南国,复作游西川。(杜甫《自阆州领妻子却蜀山行》)
同时,随着其在句中所表示的否定语气的不断加强而产生了表示反诘的语气,从而导致其原有的词汇意义虚化而消失,于是产生了“岂能”、“难道”的意思。从汉语典籍记载的语言事实来看,“不成”在宋代已经由词汇单位语法化为一个反诘副词。如:
(8)今观儒臣自有一般气象,武臣自有一般气象,贵戚自有一般气象,不成生来便是如此!(《二程语录》卷十一)
语法化可以是一个词组结构演变成一个词,也可以是一个实词演变成一个虚词;可以是一个具有实实在在词汇意义的语言成份也可以是一个较虚的语言成份演变成一个较虚的语言成份演变成一个更虚的语言成份。汉语中语气副词和语气助词都是表示语气的,其区别只是在句中位置的不同而已。语气副词“不成”作为谓语动词的修饰成份,最初的位置是在动词之前,也就是处在句中的位置。如:
(9)因论三国形势,曰:“曹操合下便知据河北可以为取天下之资。既被袁绍先说了,他又不成出其下,故为大言以诳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
由于汉语句子中的主语经常承前省略,副词“不成”就经常处在省略主语的句子的句首,如前所举例(8)就可据上文补出主语“这些人”来。“不成”经常处在省略主语的句子中的句首,使其在句中的位置从形式上看既可在句中,也可在句首,而其所表示的“岂能”、“难道”的语义在反诘的语境中也进一步虚化,导致其由修饰谓语动词而扩大为修饰全句的一种语气,这样就使“不成”在句中的位置前移至句首,既不仅可处在谓语动词前,而且也可以处在主语名词前。如:
(10)不成杀人者亦止令出金而免!(《朱子语类》卷七十八)
语气词就是在句子基本意义的基础上表示某种语气的虚词,它的有无对句子结构没有很大的影响,因而在句中的位置显得比较灵活。“不成”由修饰谓语动词演变为修饰全句,其语法功能也更为虚化,其较虚的词汇意义则进一步抽象化,形成一种缺乏具体意义而纯粹表示反诘的语气。这种反诘语气的不断强化促使其在句中的位置更加趋于灵活,以致其也可以置于句末来补足强调反诘的语气,这就使其由语气副词语法化为一个语气助词。如:
(11)既来了,怕他回去了不成?(《王粲登楼》第三折)
词汇语法化往往是几百上千年逐渐演变的一个复杂过程,“不成”由偏正词组演变为语气助词可以说是汉语词组语法化的一个典型。
三、动宾词组结构功能的虚化
汉语中动宾词组的搭配不仅要求意义上相通,事理上相合,而且要求符合语言习惯。动宾词组中“养病”、“开刀”、“跳水”、“等门”、“叫门”、“问候”、“报幕”、“报关”、“抢手”、“拉肚子”、“吃馆子”、“看医生”、“走亲戚”、“吃盆子”、“喝小杯”、“恢复疲劳”、“打扫卫生”之类的说法,按照语法上动宾支配关系来分析,显然搭配不当,不合事理逻辑。语言学界对这些词组的看法颇多,有的认为“语言不等于逻辑”,“语言这东西是约定俗成的”;有的认为“从修辞的角度来看,无非是故意用逻辑事理上的明显不通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有的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动宾关系,“动词对于宾语含有‘为宾语怎样’的意思,宾语是动作的目的原因”;有的认为这些词组中动词后面的名词不是宾语,而是表示动作目的原因的补语;等等。(注:见黄河清《短论三则》、程观林《逻辑乎?语法乎?修辞乎?》等,《语文建设通讯》第28期和第33期(1991)。)
汉语中这类词组从形式上看实属动宾结构,从语义上看则隐含有不同的关系,因而用模仿印欧语言建立起来的语法体系来分析,自然显得不伦不类,捉襟见肘。诚如吕叔湘先生所指出,这种“动词和宾语的关系确实是说不完的”,“在表示动作和事物的关系上,几乎全赖‘意会’,不靠‘言传’。”(注:见吕叔湘《语文常谈》,三联书店1980年版60~61页。)这类词组中的动宾关系虽可称为特殊的动宾关系,而实际上是在动宾的形式下演绎着各种不同的语义关系,其中的宾语功能已经虚化。
启功先生曾经指出,“各民族的语言结构,都有各自的规律,其规律并不是谁给硬定的,而是若干人、若干代相沿相袭而成的习惯”。(注:见启功《有关文言文中的一些现象、困难和设想》,《北京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汉语和印欧语的语言结构不同,各有各的规律。印欧语以“句”为本位,以词为句法结构的基本单位。一个句子必须有一个主语和一个谓语,主谓之间受一致关系制约。印欧语的词有明确的功能,其出现在什么位置受到主谓一致关系和谓宾支配关系的制约。汉语的词是由表义的汉字体现的,而汉字“作为中国人观念中的一个‘中心主题’”(注:见赵元任《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载《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248页。)在汉语句子中具有灵活多变的功能,不受统一的形式规则的支配,只要字与字间表达的词义互有关联,符合交际搭配的习惯,就可以组成词句。(注:参阅徐通锵《“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世界汉语教学》1994年第2期。)
印欧语言的句法分为词位句法(lexemic syntax)和义位句法(sememic syntax)两层。由一致关系支配的主谓结构以及和这种结构相适应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的划分属于词位句法的范围;句子中语义分类等级对义位结合的规定属于义位句法的范围。词的组合能不能成为一个句子,由其是不是一种由一致关系支配的主谓结构决定,这属于词位句法,是一种表层结构。词的义位结合哪些是允许的,哪些是不允许的,这属于义位句法,是一种深层结构。汉语的句法结构没有和印欧语词汇结构相当的那种表层结构,而大体上与印欧语的义位句法相当,因而决定汉语句子的构成的因素不是由一致关系支配的主谓结构之类的语言规则,而是语境、说—听双方的交际意图和语序之类的语言规则。汉语表层的结构框架是一种相对开放的“话题—说明”(topic-comment)结构。汉语句子的组成往往根据一个事件或一个话题的标准来确定,故赵元任先生认为,“在汉语里,把主语、谓语当作话题和说明来看待,比较合适”。(注:见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印欧语言的“谓语”和“主语”受一致关系控制,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彼此依存,不可或缺,词与词之间环环相扣,互相制约,因而语境、说—听双方的交际意图往往无法直接参与句子的构造。汉语中“说明”和“话题”的关系由话题控制,语境、说—听双方的交际意图往往可以随字所表达的词义之间的关系隐含入句子的结构,这样就可以省略某些原来具有相互选择限制的成份,因而句子各成份之间的联系显得很松散,表面上看不出相互的选择限制关系。如:
(12)他(买的货)是五元钱,你(买的货)是八元钱。(13)你(的水仙花)要死了来找我。
(14)你们(学的)是外国文学,我(教的)是中国文学。(15)我的衬衫破了,你(的衬衫)没破。
(16)(你的)被头冷吗?(17)老二,(饭)烧焦了。
这些句子即使省略掉括号内的成份也照样符合汉语的语言规律。又如“学习文件”,可以是“学习的文件”,也可以是“学习某一文件”;“气他们”,可以是“因他们而生气”,也可以是“使他们生气”。这些句子语言形式上虽然相同,但是由于话题的不同却可以构成两种不同的语义结构。汉语中“说明”和“话题”之间的关系虽然相当松散,但却不影响信息的交流,其原因就在于有语境的提示和辅助,有说—听双方在交际意图上的相互配合。人在语言交际活动中从来就不是被动的,汉语句子的构成符合人的语言交际心理。事实上人们不仅能根据语境的规定和提示恰当地调整语言结构,而且也能主动地调整语言结构来规定和创造具体交际中一定的语境。(注:语言交际心理可从语用角度进一步探讨,限于篇幅,拙文未予展开。)
汉语的句子由于是这些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形成了不同于印欧语言的一系列特点。在汉语的“话题—说明”结构框架中,“话题”必须有定,不然交际就没有了主题,说—听双方也就无法配合;而由于有语境的补充和提示,有定性的话题有时也可以省略。汉语语言形式的外部变化较少,因而语境中隐含的语义关系成为语言结构的一种联系手段,同一外在形式往往可以虚化成不同的语义关系,不同的语义内容又能组成不同的结构形式。这也就是汉语自身特有的语言结构规律。同样是动宾结构,由于语境所隐含的语义关系不同(支配、原因、对待、工具、范围、状态、处所、给予等),致使其语义特征有所不同。因此,结合汉语的实际,用“话题—说明”的关系来分析识别语境中隐含的语义关系,汉语中这类“在表示动作和事物的关系上,几乎全赖‘意会’”(注:见吕叔湘《语文常谈》,三联书店1980年版60~61页。)的特殊动宾关系的语义结构也就显现出来了。如“养病”为“因病而养”、“开刀”为“用刀动手术”、“跳水”为“跳到水里”、“等门”为“等着替人开门”、“叫门”为“叫人开门”、“问路”为“向人问路”、“报幕”为“在开演时报告(节目)”、“报关”为“向海关申报”、“抢手”为“用手抢”、“拉肚子”为“肚子泻”、“吃馆子”为“上饭店吃”、“看医生”为“请医生诊治”、“走亲戚”为“到亲戚家探访”、“吃盆子”为“把盆子里的剩菜吃光”、“喝小杯”为“用小容量的酒杯喝”,而词义上是“平复疲劳”的“恢复疲劳”在一定语境中亦可解释为“从疲劳中恢复”,“打扫卫生”则为“为卫生而打扫”等。
汉语中这类语法现象的语义形式与其外部形式并不一致。这种同一外部形式下可能出现的各种语义结构也可以用重新分析(reanalysis)的方法来说明解释。重新分析是一种认知行为,Langacker给重新分析作的定义是:没有改变表层表达形式的结构变化,一个可分析为(A,B),C的结构,经过重新分析后,变成了A,(B,C)。Bernd Heine等在《虚化论》(Grammaticalization-A Conceptual Framwork)一书中曾用此理论来分析英语at the back of the mountain中的back。"back"愿意为背,它是一个名词,而且是名词短语the back of the mountain的中心词,但重新分析后,"back"的意思虚化为“后面”,at the back of被解释为一个介词结构。(注:参阅孙朝奋《〈虚化论〉评介》,《国外语言学》1994年第4期。)太田辰夫先生在《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中曾用此理论来解释汉语被字句的产生。刘坚等先生亦曾用此理论分析“把+名词+及物动词”由连动式到处置式的变化。(注:参阅刘坚等《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在汉语中“话题—说明”结构框架中,虽然词汇句法位置和组合关系(即外部形式)没有改变,但由于在语境的作用下,词义和词的组合结构功能等抽象而虚化了,其表达语义的结构功能得到了调整,表支配关系的动宾结构倾向于虚化为表其他关系的类似于动补的结构,因而,那些看似不合事理逻辑的动宾关系也可看作汉语中构词成份语法功能的虚化现象,正是这种语法功能的表达范围逐步增加较虚成份的进一步语法化使句子结构的语义关系产生了变化。重新分析的作用就是从认知的角度把词义结构的抽象虚化和功能调整的变化形式表现出来。通过重新分析,同样也能揭示汉语在表示动作和事物的关系上隐含的几乎全赖“意会”的特殊动宾关系的语义结构。如前文所述“养病”隐含的语义结构即为“因病而养”,“打扫卫生”隐含的语义结构则为“为卫生而打扫”等。
我国早在宋代已注意到语言中的虚化现象,认为虚实动静相依,构成矛盾对立的统一体,这是宇宙万物皆然的客观规律,汉语真实地反映了这个客观规律。汉语中的虚和实看上去似乎是矛盾的,但凭借一定的语境,虚实可以互相转化,语法形式和语义内容也可以互相转化。(注:参阅清·袁仁林《虚学说》。)西方语言学家在十九世纪也注意到语言中的虚化现象,Erzy Kurylowic 的说法代表了关于虚化现象的一种普遍观点,即认为“虚化就是一个语素的使用范围逐步增加较虚的成份和演变成一个较虚的语素,或者是从一个不太虚的语素变成一个更虚的语素,如一个派生语素变成一个曲折语素”。(注:参阅Bernd Heine等《虚化论》(Grammaticalization-A Concceptual Framework),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根据汉语中这些动宾关系的虚化现象,我们还可以说,虚化还是一种语法功能的表达范围逐步增加较虚的成份和演变成一种较虚的语法功能。
Elizabeth Traugott曾提出语义的虚化是一种“主观化”现象(subjectification),这也许颇有启发意义。她说:“在虚化过程中语义的演变,往往是某一功能/语义,在上下文的影响下,由命题(propositional)的功能,变成语言表现上(expressive)的功能”。也就是说“语义变成不再指较客观的语境,而指较主观的(包括说话人的观点),不再用作表述事物,而用作满足话语结构的需要”。(注:参阅孙朝奋《〈虚化论〉评介》,《国外语言学》1994年第4期。)虚化是由认知学的一些因素造成的,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概念转换。实际上虚化也就是一种抽象化(generalization)的演变,这种抽象化一方面使某一语素或语法功能显得缺乏原有的较为具体的意义,一方面也使得其应用的范围变得更加广泛,从而具有语言表现上的功能。
汉语中的虚化现象表现在词句的各个层面上,不仅表现在语法形式上,而且往往涉及同一语法形式下不同的语义内容形成的不同结构关系,甚至还涉及到句子的语义或功能。如“有空来我家坐坐”,实际的语意可能只是一句礼节性的客套话。又如甲请乙吃饭,乙回答:“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呢?”表面上似乎是拒绝的语义虚化为表示客气的功能。如果乙回答:“啊,太不巧了,我另外有个约会,改天再说吧?”表面上建议改天再说的语义实际上可能虚化为表示客气地拒绝的功能。由此可以看到汉语语言结构规律注重字面意思下的语义内容的特点,同时也可以看到虚化在语言演变和运用中的重要功能。
汉语中的虚化现象涉及的因素较多,因而尚有待于从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上进行系统的深入研究,从而揭示其在人类语言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价值,笔者不揣谫陋,谨就此略陈一得之见正于方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