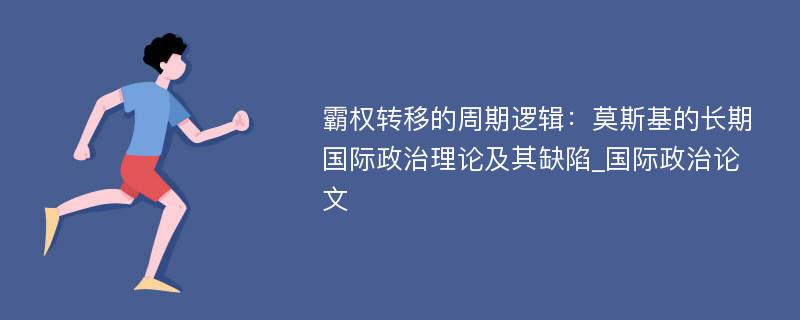
霸权转移的周期逻辑——莫德尔斯基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及其缺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期论文,霸权论文,斯基论文,德尔论文,缺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6-9550(2007)12-0024-09
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有一种影响深远的探讨循环式的大国兴起以及由此引发全球性霸权战争现象的思想流派。如亨利·基辛格在《大外交》篇首即称:“仿佛是根据某种自然法则,每一个世纪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智识与道德动力的强国依其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①美国学者乔治·莫德尔斯基将这种史学家感悟到的列强兴衰更替现象彻底理论化,提出了国际政治发展的长周期理论。此论一出,立即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但是,这个高度宏观的理论果真能在解释纷繁芜杂的现实国际政治中,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发展方面让人信服吗?本文意在通过对近代以降的国际政治史实的考察和借助国际关系基本理论来检验莫德尔斯基的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并期望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 莫德尔斯基长周期理论的内涵
莫德尔斯基的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是以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国际政治史特别是西方国际政治史为基础,借助社会学理论中的体系分析方法和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发展长周期理论,构建的一个高度简约的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
首先,莫德尔斯基借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社会体系理论来证明世界政治体系需要一个领导者。帕森斯认为“社会体系是由国家以及参与体系运动的单元之间的社会互动过程构成的”。②他把现代社会体系按功能划分为四个次体系,即经济体系(economy)、政治体系(polity)、社会共同体(societal community)和维持模式(pattern maintenance)。③莫德尔斯基的研究焦点放在帕森斯现代社会体系的政治层面。他把全球政治体系(global polity)定义为“按功能划分的、涉及明确问题范畴的一组特定关系,那些体系的参与者在全球层面上采取有组织的集体行动。”④它由四个部分构成:“(1)世界性强国和挑战国之间的关系;(2)全球政治体系既与(起支配作用的)全球体系和世界体系共存,也与由全球经济、共同体和文化构成的(起协调作用的)的次体系共存;(3)维持全球政治体系运转的调节性机制(regulatory mechanism);(4)解释全球政治体系演变的发展性机制(developmental mechanism)。”⑤莫德尔斯基认为,和国家层面的政治体系及地方层面的政治体系一样,世界政治体系需要一个领导者来维持其运转,体系领导者和挑战国之间的关系是核心。在这一意义上说,全球政治体系是由政治行为(politiking)和政策(policy)两部分组成的,前者指竞争体系的领导权,后者指体系领导者为集体目的而追求的目标以及追求这一目标的方式。竞争体系领导权成功的国家成为“世界强国”,体系秩序遂由其支配。
其次,莫德尔斯基以社会学理论和人类历史经验来证明国际政治领域丛林法则的普遍性。尽管莫德尔斯基强调“长周期并非是战争周期,而是通过全球性战争的调节而形成的一种政治进程”,⑥但是该理论还是把国际体系演进的动力归结为战争,就如生物学家把自然界物种起源与发展的动力归结于“自然选择”一样,长周期理论把全球性战争看做是国际体系发展的“社会选择”。⑦他认为国际体系转换的主要方式是全球性战争,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以来的世界领导者无一不是从战争中脱颖而出的。⑧
再次,长周期理论把经受住霸权战争考验的国家定义为“世界领导者”。不过,并非每一个大国都有机会问鼎“世界领导者”的独尊地位,世界领导者必须具备如下四个要素:地理上须是岛国或半岛国家;国内政治稳定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上领先;拥有强大的海军,能在全球范围内运用自己的力量。⑨在这四个要素中,莫德尔斯基特别强调地缘位置和海军力量的重要性。莫德尔斯基认为近代世界历史上出现的四个“世界领导者”均是海岛或半岛型国家:葡萄牙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一角,在欧洲大陆上没有特别利益;荷兰在地理位置上虽不是典型的半岛国家,却也类似于半岛的海洋国家;英国在地理上完全是一个岛屿国家;美国则是一个大陆型的“海岛”国家,其地缘位置之与欧亚大陆犹如英国之与欧洲大陆。
最后,莫德尔斯基把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发展长周期理论和埃尔文·拉斯佐罗(Ervin Laszlo)的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在理论上论证世界领导权是以周期的形式更迭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就对长期经济景气变化进行研究,提出了经济发展长周期理论。该理论把一个经济长周期分为繁荣-衰退-恐慌-回复四个阶段。康德拉季耶夫在研究中还发现,经济长期上升时期通常处于战争及国内社会动荡最为多发和最为激烈的时期。⑩莫德尔斯基的长周期理论对每个周期的阶段划分与康氏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他把世界领导国的成长与衰败阶段划分为全球性战争阶段、世界性强国出现阶段、合法性丧失阶段和权力分散阶段。这四个阶段的运动过程构成了莫德尔斯基所说的特定周期的阶段性运动(phrase movement)。(11)在这四个阶段中,第一、第二阶段对秩序的需求(preference for order)最高,第三、第四阶段由于处于领导国地位确立后的稳定期,对秩序的需求相对较低。但就秩序的可行性(availability of order)而言,由于第二、三阶段处于世界性强国的支配之下,国际秩序比较稳定。(12)对秩序的需求反映了体系阶段性演化的功能,而秩序的可行性则体现了世界性领导国对体系演变起到的主导性作用。
在国际政治发展的动力方面,莫德尔斯基还借鉴了拉斯佐罗的社会学理论。拉斯佐罗的理论认为所有社会体系都由调节性机制(regulatory mechanism)和发展性机制(developmental mechanism)组成,二者构成一个反馈系统,即系统输出部分将其所获得的信息重新输入系统,对系统的运转进行修正。在这个反馈系统中,调节机制或控制进程构成负反馈,供暖系统中的温度计是负反馈系统的典型;发展机制或增长过程构成正反馈,人口或经济增长是正反馈进程的典型。(13)莫德尔斯基把上述两套机制引入全球政治体系,用调节机制解释体系的稳定性,发展机制则解释体系的变迁,二者形成一个反馈系统。在这套反馈系统的作用下,全球政治体系以周期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种周期既表现为世界领导者主导国际体系必经的几个过程,也表现为世界领导者的更迭。
简言之,莫德尔斯基的长周期理论由如下四个命题组成:(1)世界政治体系需要一个领导者;(2)世界领导者均脱颖于全球性战争,但“挑战者”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取代旧的世界领导者的国家往往是被取代国的伙伴或盟友;(3)有资格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均是海权国家;(4)国际政治演变的模式是“循环的”,世界性领导者主导国际体系的周期约为100~120年。从形式上看,莫德尔斯基对近五个世纪以来国际政治发展的梳理颇似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原因的总结,(14)具有极强的解释力。但学术研究不能满足于大而化之,而需进行细致研究,以考察其是否与国际政治发展的历史相契合以及其预测力。
二 世界政治体系是否需要一个领导者?
作为“美国理论”的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对所谓“世界领导权”及其稳定世界秩序的功能情有独钟。不过,为掩饰其为霸权进行辩护的色彩,他还将长周期理论与以吉尔平为代表的霸权稳定理论做了如下比较(见表1):
表1 霸权稳定理论和长周期理论比较(15)
霸权稳定理论 长周期视角
核心概念是霸权 核心关系是领导者与挑战者
之间的关系
霸权是物质资源方面占有 领导权是为解决全球问题而
优势产生的供给与需求的产物
两个相关事例分别指19相关案例除了19世纪的英国
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和20世纪的美国外,还包括
美国18世纪的英国、荷兰和葡萄牙
霸权创造国际秩序,其中 世界领导权解决全球政治问
包括国际机制题
需要霸权来维持国际秩
序,包括经济秩序
霸权创造自由贸易领导权和自由贸易之间的关
系是可变的,演化趋势是减少
垄断
为证明所谓世界领导权的合理性,莫德尔斯基给出了两点论据:
第一,该理论认为全球政治体系本身需要一个领导者,就如一个公共部门需要一个部门首长一样。(16)莫德尔斯基的这一比喻貌似合理,实为不妥。国内政治的某一公共部门实际上还受到其他部门的制约,比如行政权要受到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制约。因此,公职部门需要一个首长来管理本部门的事务并不意味着本质上以“自助”为特征的无政府社会也需要一个世界领导者来管理世界事务。
第二,他极力强调“世界领导者”所谓仁慈的一面,把国际体系的支配国称为“世界领导者(world leader)”,而非“霸权国家(hegemon)”,意在强调世界领导者在稳定国际秩序方面具有合法性。(17)长周期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世界领导者并非只是享受独尊地位带来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充分安全(surplus security),还要履行义务,为体系提供有利于维持秩序的“公共产品”。在他看来,世界领导者不同于霸权国是因为后者更强调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方面,而忽视领导权必须解决的全球性问题。(18)而霸权国的典型特征则是过度依赖武力优势,行为傲慢,并以帝国主义方式获取领土,但对国际体系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普遍性问题却兴趣索然,无意解决之。(19)世界领导者与霸权国大不相同,因为全球政治体系不同于帝国体系,前者可以看做是为获得共同利益或生产公共物品在全球层面上采取的集体行动,也就是帕森斯所说的“对集体目标的集体追求”。(20)因此世界领导者尽管拥有压倒性优势,占据着支配性地位,但它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各大陆、海洋甚至太空之间的远程互动,(21)维持国际政治秩序和维护开放的自由贸易体制等,而非压制别国的独立自主权。
尽管莫德尔斯基不承认,但从严格意义上讲,他创造的“世界领导者”概念其实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霸权”,或许更接近于时下美国风头正健的新保守派学者克里斯托尔等人所鼓吹的“仁慈的霸权”。(22)国际政治中的霸权与国内政治中统治集团对被统治集团的“霸权”并无天壤之别,都有强制性的一面和意识形态的一面,亦即葛兰西所说的“支配”及“知识和道德上的领导”。(23)克里斯托尔把美国看成是一个“受人之邀的帝国”和“仁慈的霸权”,而这恰是莫德尔斯基心目中完美的世界领导者形象。
但是,我们真能指望所谓的“世界领导者”为国际体系提供“公共产品”而不谋私利吗?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剑桥世界近代史》的编者阿克顿勋爵曾有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要想抑制腐败,唯一手段只能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在国家间关系方面也是如此。他在《近代史演说集》中认为处于霸权地位的国家,无论其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制度如何,不能指望这样的国家会奉行自我克制的政策,而只能靠与之抗衡的力量。(24)法国神学家、康布雷大主教弗朗索瓦·费内隆(Francois Fénélon)也从以权力制约权力的角度出发,警告人们“切不可指望一个超级强国会严守中庸之道,奢望它会将自己的强大摒弃不用而仅想得到它在最衰弱的情况下也能得到的东西……所有这些都不能允许人们相信:一个能够征服其他民族的民族会永久地按兵不动”。(25)秩序固然是国际社会存在的最重要的价值之一,但是,所有的历史事实都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指望一个实力超群的霸权国维持的秩序最终只能是监狱里的秩序。
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还证明,不受霸权国操纵的国际体系是人类群体保持独立、多样性和有效竞争的最终条件。在这方面西方先哲们是有共识的。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和《永久和平论》中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竞争乃至竞争的最激烈形式——战争可以促进“大自然的节约原则”。(26)亚当·斯密曾对工商业民族尚武精神的退化深表忧虑,他认为,“哪怕在社会的防御上已用不着人民的尚武精神,但为了防止怯懦必然会引起的这种精神上的残废、畸形及丑怪在人民中间蔓延传播,政府仍应加以最切实的注意。这好像癞病及其他讨厌的、令人不愉快的疾病,虽不会致死,或没有危险,但为防止在大多数人民中间传播,政府仍应加以最切实的注意……有效地保持这种尚武精神”。(27)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战争不应看成一种绝对罪恶和纯粹外在的偶然性。”(28)从人类的道德良知角度来看,这种不受霸主支配的国际体系是冷酷粗暴,甚至是血腥的,但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大背景看,这种体系又是必要的,这就如冷酷的市场体制是我们的最佳经济制度一样。谁试图以某一世界性强国——无论这个强国是霸权国还是所谓“世界领导者”——支配国际体系来消除国际政治中的动荡与冲突,就如试图用全盘计划来消除市场中的不公正一样,其结果总会走向反面,也决不可能成功。
三 未来国际体系转变会遵循全球性战争模式吗?
莫德尔斯基长周期理论的第二个命题是世界领导者均脱颖于全球性战争。为证明自己的命题,莫德尔斯基列举了近代以来发生的五次大规模战争及每次战争的后果。这五轮战争如表2所示:
表2 莫德尔斯基的五次全球性战争及其胜利者(29)
战争中产生的
周期周期大致时段
世界领导者
全球性战争
周期一 1518~1608年 葡萄牙意大利战争
(1494~1517年)
周期二 1609~1713年 尼德兰联合省 西班牙战争
(1581~1608年)
周期三 1714~1815年 英国 对法战争
(1688~1713年)
周期四 1816~1945年 英国 对法战争
(1792~1815年)
周期五 1946~美国 对德战争(1914~1918
年;1939~1945年)
这里且不论莫德尔斯基在这里给出的上述五个周期是否准确,就他所称的五场全球性战争而言,似有不妥之处。就范围来说,只有对德战争,即其意指的两次世界大战具有全球性质,其他的四场战争均为地区性或局部性战争:1494年爆发的由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引起的意大利战争仅限于地中海的若干国家参战,更重要的是,葡萄牙并非是意大利战争的主要参战国,因此谈不上葡萄牙赢得了意大利战争。1581~1608年间发生的西班牙战争主要内容是尼德兰联合省寻求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出来,全无争霸色彩,反倒是莫德尔斯基为自圆其说而有意忽略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为公认的霸权战争。1688~1713年欧洲爆发的针对路易十四大陆霸权的战争同样谈不上是全球性冲突,甚至谈不上是全欧洲冲突,因为同时期欧洲还爆发了另外一场大战,即俄罗斯和瑞典之间的北方大战。1792年至1815年的对法战争将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战争,无疑具有全欧性质,但战争的最大的受益者是沙皇俄国,而非英国。战后的俄罗斯是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等大陆国家恐惧的对象,也是英国嫉妒的目标。可见,莫德尔斯基的“世界领导者”概念有必要做出适当修正,改称为“体系领导者”似乎更为合理;“全球性战争”也要相应改称为“体系性战争”。唯有如此,才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五个世纪的近代国际政治发展史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如果说长周期理论把体系领导者误解为世界领导者,把体系战争误解为全球性战争,只是瑕疵,无伤大体,那么把未来国际体系的转变模式依然建立在全球性战争的基础之上就是硬伤了。(30)当然,就传统国际政治现实而言,把战争作为霸权国检验标准的思想有其合理之处。泰勒梳理了1848~1918年的欧洲争霸史后给霸权国下了一个值得深味的定义:“大国,正如其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是谋求权力的组织,亦即最终诉诸战争的组织。它们或许还有其他目的——其居民的福利或者统治者的荣耀,但是对它们作为强国最基本的考验是看其是否有能力进行战争。”(31)德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在《论列强》一文中也认为,霸权国就是必须能抗击所有的其他强国——即使在后者联合起来的情况下也不会被打垮的国家。(32)但是,任何政治现象都是其时代的产物。随着核武器的出现、战争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人类的毁灭能力正以惊人的几何级数增长。与此同时,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若再仅以军事力量和战争能力作为衡量大国的标准,可能失之准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的军事技术取得飞速进展。据有关专家研究,冷兵器时代剑和长矛的杀伤力理论指数为23,而一百万吨级高空爆炸核弹的杀伤力理论指数则猛增至695385000。(33)由此可见,随着战争技术的发展,战争成本越来越高昂,以至于战争已成为只有穷国和落后国家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大国之间已不敢轻言战事。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一次会晤中宣称核战争中没有赢家,大国不可再战。(34)此话虽为示好之辞,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技术发展的现实和普通民众的心声。若根据莫德尔斯基长周期理论预测下一轮全球性战争,无异于预测何时实现康德所言的“坟墓上的永久和平”。
此外,当代最典型的特征是全球化,不仅是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而且是生产的全球化。全球化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具有潜在的革命性意义。就如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一本有关全球化意义的书中所指出的,当前时代国际体系变革的动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多依赖过去而且单纯依赖过去预测未来”的方法已不再可行,因为全球化已成为“塑造每个国家内政与外交的全面支配性国际体系。”(35)不管你是否赞同弗里德曼的观点,从宏观外交史的角度考察国际社会,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当前“世界各国仍在相互竞争,但今天的游戏不同于1900年对殖民地的争夺。如今它们追求的是社会和经济目标。为此国与国之间需要相互合作并遵守国际规则……(现在的世界主要大国)往往通过国际组织,而不是用炮舰寻求自己的利益”。(36)
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大趋势使爆发全球性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不会发生变化。恰恰相反,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将更加凸显出来。现代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将随之由平衡转向失衡并最终发生更迭,但这种更迭或演变大概不会再遵循长周期理论依据人类经验构建的全球性战争的传统模式,而是和平变更或在小规模、低烈度战争的模式下实现国际体系变更,毕竟国家的生存利益是至高无上的。
四世界性大国必定是海权国家吗?
如前文所述,莫德尔斯基注意到他所列举的世界领导者均为岛屿国家或半岛国家,因而特别强调地缘位置和海军力量对世界性大国的重要性。
政治地理位置与国家兴起之间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法国著名外交家朱尔·康邦曾在上世纪30年AI写作过一部有关大国外交政策的论著。康邦在书中指出,“一国的地理位置是决定其外交政策的首要因素,也是它为什么必须有一项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因。”(37)不过,莫德尔斯基太过于机械地理解地缘政治因素,他只看到国家的地理位置基本不变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地缘政治和一国的地缘战略地位动态变化的一面。国际关系史表明,由于某项技术创新或重大政治事变,地缘战略关系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例如,在铁路网形成之前,德国由于缺少天然屏障成为“死地”。但铁路网建成后,德国一跃成为“四出之地”。同样是德国,在1871年统一前,由于政治分裂,德意志各公国竞相媚外,法、俄、英等国借机干涉德国内政。有学者把德国统一前饱受的这些凌辱归因于“倒霉的地理位置”。(38)德国统一后,开始轮到它的邻邦,尤其是法国抱怨自己的地理位置倒霉了。由此可见,地缘政治因素实非一成不变。
在地缘政治理念方面,莫德尔斯基属于坚定的“海权主义者”。他认为,在全球性战争时期,海权履行了如下四个功能:首先是“控制海洋”的功能。在第一次大战期间,英国的海军力量在北海抑制住了德国的海上力量,使其不敢妄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对日本的海上力量给予致命性打击。其次,海权可以保障国内基地免遭打击和入侵而使对手的国内基地受到直接打击,后者为海权的“力量投射”功能。拿破仑战争期间,特拉法加尔海角(Trafalgar)一役让法国直接入侵英国的计划灰飞烟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的海上力量使纳粹德国无法直接登陆英国,而盟国的两栖部队却能成功实施诺曼底大登陆。再次,海权可以保障自身及其盟国在战时交通顺畅、贸易如常,同时切断对手的交通和贸易线路。最后,确保与核心盟国之间有效联系。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的海上力量保住了两国之间在北大西洋上的生命线,并经过摩尔曼斯克支援苏联。与之相比,德日两个钢铁盟友之间的联系在美英海上力量的联合阻击下几乎荡然无存。全球性战争结束后,世界领导者还要利用海权来维护有利于它的国际政治秩序,不给挑战者控制海洋的机会。(39)总之,莫德尔斯基认定海权在全球性战争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世界领导权的变化与海上力量的转移息息相关。(40)所以,出于海权的考虑,他把葡萄牙而非学术界近乎公认的西班牙作为现代世界体系出现后的第一个霸权国或“世界领导者”。(41)
不可否认,对一个世界性大国来说,面向海洋发展是前提条件,因为海权相对于陆权具有的优势来自于这样一个地理事实:毕竟地球表面3/4由水域覆盖。(42)可能也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43)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完全同意莫德尔斯基对海权的过度强调。首先,与其强调海权的重要意义,不如强调综合国力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海上力量建设是所有军兵种中最为昂贵的,也是科技含量较高的军种。如果综合国力尤其是国内经济基础薄弱的话,把大笔的资金投入海上力量建设无异于是一场灾难。其次,海上力量的强大也未必就等于胜券在握。荷兰海上力量强盛时期,其海军力量相当于英、法两国的总和,但其陆上力量却远逊于法国。1672年,路易十四发动对荷战争,横扫荷兰,直逼阿姆斯特丹。荷兰利用地势低洼的条件掘堤放水,方免亡国之运。晚清时代,中国的海军力量并不弱于邻国日本,但北洋水师还是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亡。再次,军事力量的发展要着眼于本国面临的安全威胁,而非机械地套用海权、陆权或空权理论。类似于英国这样的岛国需要拥有强大的海军保护自己的海岸线;美国虽为大陆型国家,但其两面向洋,又无强邻,所以也以发展强大的海军为主;拥有广阔大陆腹地的中国和俄罗斯因陆上边界漫长,始终要拥有庞大的陆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随着技术发展和高速铁路及高速公路网的建成,陆上力量的机动性将大大提高,这将进一步削弱海权的重要性,并且可能出现保罗·肯尼迪在《英国海军霸主地位的兴衰》一书所指出的那样,不能排除大陆国家统治海洋国家的局面。(44)
五世界政治体系演变规律是循环的还是螺旋式上升的?
莫德尔斯基长周期理论的最大特色莫过于世界领导权的往复更替。他把地理大发现之后五个世纪的国际政治史划分为五个周期,分别是葡萄牙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Ⅰ、Ⅱ)和美国周期,每个周期的时间跨度约为100~120年。(45)
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以降,欧洲国家间的战争摆脱了地方性,具有争霸性质。欧洲国家间关系遂逐渐发展成为单一的政治体系,它在国际法和势力均衡——“在国家之间、应该说是国家之上发挥作用的法律以及在国家之间、或应说国家之上发挥作用的权力”(46)——的双重作用下,演出着一幕幕大国兴衰的悲喜剧。长周期理论的世界领导权循环模型犹如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让人对霸权更迭一目了然。但问题也出在这里,它只让读者看到不同领导权周期间相同的一面,而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差异。从历史角度考察,英国霸权与荷兰霸权不同,而美国霸权与英国霸权又有很大的差异。与其说国际政治演变的基本规律是循环的,倒不如说是螺旋式上升的。
自1659年西班牙在“比利牛斯条约”上画押服输后,荷兰凭借其海上实力和贸易优势成为欧洲霸主。但正如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布罗代尔所言,荷兰霸权是一个分水岭,“它处在经济霸权的两个连续阶段之间:一方面是城市的时代,另一方面是现代领土国家和民族经济的时代”。(47)荷兰霸权的基础是商业和金融业。它在战争期间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对被战争长期困扰的欧洲国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欧洲的参战各国都急赴荷兰争取贷款。“到18世纪60年代,所有欧洲国家都排着队,等候在荷兰放款人的办公室前: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萨克森选侯、巴伐利亚选侯,到再三举债的丹麦国王以及瑞典国王、俄国的叶卡特琳娜二世、法国国王,甚至还有汉堡市”。(48)
英国在18世纪中期取代荷兰成为欧洲体系的领导者。虽然荷、英两个霸权国的基础都是以宗主国领土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但是荷兰缺乏工业和帝国的后盾,而英国不但是商业中心,还是工业中心,是一个机械化了的商业运输和生产体系。通过对外拓殖,英国控制了大片殖民地以及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交通要道。所以,英国霸权特别是19世纪的英国霸权是以与17世纪荷兰霸权完全不同的方式建构的,它赋予英国霸权更广泛、更复杂的结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专家卡尔·博兰尼认为,在荷兰霸权时期,欧洲的国际体系是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体系,也就是说,这个体系中没有中心统治者;而在英国霸权时期,通过维也纳会议重新建立的国际体系,已不再是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体系。在这个新体系中,欧洲力量均衡已成为英国支配体系的非正式工具——它们把力量均衡视为政策,而非体系。(49)
国际关系史学界普遍认为,英国霸权的衰落源自德国的挑战。但从更深层的原因看,英国霸权是毁于工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传播。工业主义的传播导致英国失去世界工场的地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西利(J.R.Seeley)早在1883年就预见到运输革命和战争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战略地理”。他指出,如果英国不能把殖民帝国转变为“更大的不列颠”,美国和俄国由于其辽阔的疆域,一旦它们的潜力因“蒸汽机和电力”以及铁路网而得到充分的发挥,将使英国沦为“不安全、不重要、第二流”行列的国家。(50)而帝国主义的传播“让列强发现自己愈加依赖于一个逐渐不可信赖的世界经济体,因此它们倾向于帝国主义,随时准备闭关自守。”(51)19世纪90年代流行的“新海军至上主义”尤其摧毁了英国的海洋霸权。1902年以后,英国和德国之间展开的海军竞赛迫使英国实施战略收缩。英国不得不放弃传统的海洋政策,寻求同其他区域性海上力量,如美国、法国和日本结盟,重新回归到欧洲均势体系之中。英吉利海峡不能再为英国提供孤立,而大西洋依然可让美国保持孤立。更重要的是,随着交通和通讯手段的不断革新,空间的屏障陆续被克服,从商业和军事的角度看,美国遥居欧亚大陆之外不再是缺陷了。“确实,随着太平洋区域开始作为大西洋的经济对手出现,美国的地位中心化了——它是一个洲级规模的岛屿,可以不受限制地到达世界两大洋”。(52)与美国相比,作为帝国的英国虽也有庞大的领土,但它分散于全球,在整合程度上难望美国项背。从霸权建立的形式上看,美英两国也迥然相异。英国的霸权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它掌握欧洲的力量均衡,强化自己作为贸易中心的地位。而美国则相反,它的霸权是自上而下建立的,它采取有意识的行动,一方面抢在欧洲力量均衡最后崩溃所造成的动荡之前建立一个国际性组织机构;另一方面,美国则依赖自由贸易原则,把美国经济与西方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在一起。
因此,纵观国际关系史中世界领导国家或霸权国家的更替演变,我们发现,在工业化和技术发展的双重推动下,每一轮斗争都改变了前一个国际体系出现的空间格局,使霸权沿着螺旋式的轨迹上升,为新力量进一步向东或向西迁移创造条件,并最终把以欧洲为中心的主权国家体系推广到全球。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德里奥指出:“西方的力量均衡之所以能够保持,只是因为新的平衡力量一次次从其边缘出现,与追求霸权的力量相对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欧洲不断转移的力量……出人意料地转回到它们来的地方……旧日小国家的多元体系在年轻的巨人面前完全黯然失色,它向年轻的力量寻求援助……囊括欧洲场景的旧框架于是……破碎了。日益狭小的舞台不再是小国多元体系兵强马壮的演出场地,它的重要性也已经丧失,被纳入更广阔的舞台之中。两个世界巨人都是各自舞台的主角……但是旧日欧洲的趋势被弃之一旁,统一的全球新趋势取而代之”。(53)
随着霸权基础质的飞跃,在一个自治的军事结构多元复合体中,国家间力量斗争的费用急剧攀升,采用的方式也将更具毁灭性,传统的欧洲力量均衡的趋势难以再现,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军事力量集中化的趋势。可以预见,随着斗争中军事装备的规模及技术含量、资本含量越来越高,渴望成为或能够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国家将越来越少。
六 结论
通过对五个世纪以来国际政治发展史中一些重大问题的探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莫德尔斯基国际政治长周期的四个主要命题均存在瑕疵,甚至重大错误。特别是随着人类军事技术领域的革命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莫德尔斯基长周期理论引以自傲的预测功能已大大弱化。如果再以长周期理论的视角来解读中国崛起的前景及其与当前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走向,难免会误入歧途。中国虽不是莫德尔斯基属意的海洋国家,但作为地理构造自成一体的、具有洲级规模的海陆复合型国家,兼有陆上资源的丰富性和海洋交通的通达性双重优势,其崛起不可遏止。此外,与历史上的法国和德意志第二帝国不同,崛起中的中国的国际战略理念是倡导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赞同并符合历史潮流的世界多极化,(54)而非要取代美国主导国际体系。当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向海洋国家的转型,美国及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战略家所担心的中国海上力量的崛起势所必然,但是中国周边列强环伺的战略态势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盲目追求海权。更何况,中国海权崛起的时代大背景是全球化,而不是殖民争夺时代。诚如倪乐雄先生所言:“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个史无前例的新因素……有可能将现代海权观念导向崭新的思路,既然未来每个国家的生存依赖全球经济一体化体系,那么所有国家的军事努力、包括海权战略都将殊途同归,指向同一个目标——维护世界经济的一体化,那是个划时代的时刻,它将意味着人类已不可逆转地走向永久和平,也意味着马汉的‘海权论’即将退出历史舞台。”(55)这句话也可算是他对莫德尔斯基长周期理论核心命题的批判和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所做的一个恰当的时代背景注解。
注释:
①Henry 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4,p.17.这种国际政治发展的循环观点被一些学者称为霸权转移的周期逻辑。用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约翰·加迪斯比较通俗的话说,这种逻辑“认为虽然时间一往无前,历史进程却可重复,以圆圈来比喻历史的发展要比用箭头比喻历史的发展更为贴切。从这个角度看,未来会不时地重复过去,即便它不一定是精确地重复过去。研究者可通过感悟历史循环的频率、幅度及其含义来预测未来”。参见John L.Gadd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Sean M.Lynn - Jones and Steven E.Miller,eds.,The Cold War and After:Prospects for Peace,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3,p.364。
②Talcott Parsons,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71,p.7.
③相关介绍可参见[美]安东尼·奥罗姆著,张华青等译:《政治社会学:主体政治的社会剖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④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7,p.7.
⑤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p.12.
⑥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p.93.
⑦相关论述参见George Modelski,"Evolutionary Paradigm for Glob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No.3,September 1996。
⑧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Thompson,"Testing Cobweb Models of the Long Cycles," in George Modelski,ed.,Exploring Long Cycles,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87,p.87.
⑨相关总结参见Shumpei Kumon,"The Theory of Long Cycles Examined," in George Modelski,ed.,Exploring Long Cycles,pp.60-61 。
⑩参见Nikolai Kondratieff,The Long Wave,New York:Richardson and Snyder,1984;对康德拉季耶夫经济长周期理论的简要评述可参见Richard Rosecrance,"Long Cycl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1,Nol.2,1987。
(11)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p.31.
(12)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p.31.
(13)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p.29.
(14)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在于“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参见[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9页。
(15)George Modelski,Exploring Long Cycles,p.13.
(16)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p.13.
(17)莫德尔斯基的这一观点与美国另一位著名国际关系研究专家罗伯特·杰维斯相类似,只是后者所使用的概念为“优势(primacy)”。参见Robert Jervis,"International Primacy:Is the Game Worth the Candie?" in Sean M.Lynn -Jones and Steven E.Miller,eds.,The Cold War and After :Prospects for Peace。
(18)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p.17.
(19)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pp.17 - 18.
(20)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Testing Cobweb Models of the Long Cycle," in George Modelski,ed.,Exploring Long Cycles,p.85.
(21)William R.Thompson,On Global War:Historical - Structural Approaches to World Politics,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88,p.45.
(22)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Toward a Neo- Reaganite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Vol.75,No.4,1996.
(23)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1,pp.57-58.
(24)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p.111.
(25)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p.111.
(26)参见[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另参见Immanuel Kant,Perpetual Peace:A Philosophical Essay,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1903,英译者长篇序言。
(27)[英]亚当·斯密著,王亚南等译:《国富论》(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44页。
(28)[德]黑格尔著,范扬等译:《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40页。
(29)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Testing Cobweb Models of the Long Cycles," in George Modelski,ed.,Exploring Long Cycles,p.87.
(30)长周期理论把2000~2030年间的挑战国确定为苏联,参见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p.40 。
(31)A.J.P.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 -1918,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p.xxiv.
(32)Leopold von Ranke,"On Great Powers",in Leopold von Rank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Indianapolis:The Bobbs- Merrill Company,Inc.,1973,p.86.
(33)[美]T.N.杜普伊著,李志华等译:《武器和战争的演变》,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117页。
(34)Karl Kaysen,"Is War Obsolete? " in Sean M.Lynn - Jones and Steven E.Miller,eds.,The Cold War and After:Prospects for Peace,p.81.
(35)Thomas L.Friedman,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99,p.7.
(36)[美]帕斯特主编,胡利平等译:《世纪之旅:世界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第2页。
(37)Jules Camb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France," i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ed.,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owers,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35,p.3.
(38)帕斯特主编:《世纪之旅:世界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第98页。
(39)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Thompson,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1494 - 1993,Sea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8,pp.11 - 13.
(40)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Thompson,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1494 - 1993 ,pp.16 - 17.
(41)保罗·肯尼迪把西班牙作为第一个世界性大国。参见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New York:Vintage Books,1987,chapter 2。
(42)[美]阿尔弗雷德·塞尔·马汉著,范祥涛译:《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2页。此引文参见弗朗西斯·塞姆帕为该书所写的学报版引言。
(43)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
(44)参见朱听昌:《西方地缘战略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45)具体模型参见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p.40。
(46)Leo Gross,"The Peace of Westphalia,1648 - 1948 ," in R.A.Falk and W.H. Hanrieder,eds.,International Law and Organization,Philadelphia:Lippincott,1968,pp.54 - 55.
(47)Fernand 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Fifteenth - Eighteenth Century: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4,p.175.
(48)Fernand Bran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Fifteenth - Eighteenth Century: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pp.246- 247.
(49)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57,pp.259 - 262.
(50)参见[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张广勇等译:《当代史导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
(51)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p.217.
(52)Joshua Goldstein and David Rapkin,"After Insularity:Hegemony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 Futures,Vol.23,No.9,1991,p.946.
(53)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the Politics of Power in Europe,1494-1945,London:Chatto & Windus,1963,pp.264-266.
(54)对于世界的多极化趋势,美国的一些国际关系专家有着深刻认识。参见Christopher 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in Sean M.Lynn -Jones and Steven E.Miller,eds.,The Cold War and After:Prospects for Peace.
(55)倪乐雄:《海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8期。
标签:国际政治论文; 莫德尔论文; 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国际秩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