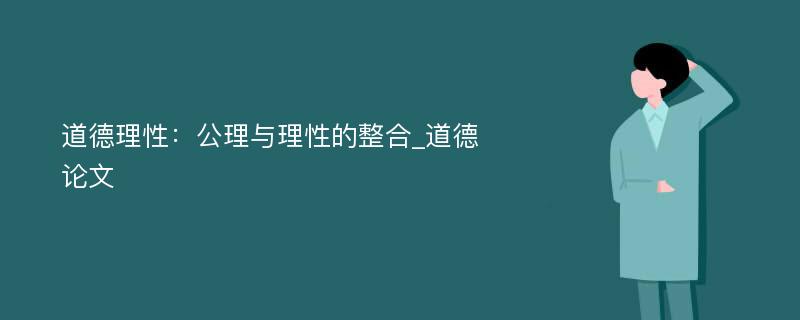
道德理性:公理与情理的融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理论文,情理论文,理性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道德上的公理:公共价值而不只是公共规范
道德是讲理的,它对应该做的事情必须给出强理由,它体现的是事理之当然。我们看到,道德与现实的社会伦理关系的特点密切相关,比如古代的民主制、专制君主制、寡头制等,就决定了在这些社会中伦理关系有各自不同特点。由于其伦理关系的特点不同,它们推行的道德价值也就不同。从社会关系来看,中国古代社会就是以血缘亲情为原则的宗法制社会,而在古希腊时期,对于社会政治—伦理关系性质的定位就引起过争论,比如是把平民看作是一个享有政治权利的城邦中的人,还是只看作需要统治的一群人的集合,这些都会直接影响社会的伦理关系——道德的说理基础。在一种宗法社会,它的伦理原则是以家庭亲情为核心和原型的一种放大和外推,其实质是服从家庭中情感的利他原则,在本质上,人们的地位是不对等的,外推为政治伦理原则则是忠君、从上,维护等级秩序;而在古希腊城邦制度中,如果把人们只看作需要统治的人群,那么,就是一种绝对的君主制度(如斯巴达),而如果把平民看作是享有平等政治权利的人,那么,就会建立一种民主制的城邦政治体系,塑造一种平等的社会伦理关系(如雅典)。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逐渐进入一个经济时代,经济日益市场化、社会化,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日趋平等,在国家政权的主持下,有步骤地让市民社会得以发育完善。市民社会服从的是利益的利己原则,它的伦理关系的特点是人们成了独立的利益主体,也就是说成了自由、平等的个人。这是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最深刻的变革,它对宗法纽带的冲击是最有力的,也是最有效的,同时对改革开放前完全隶属于政治国家的中国社会也是一种解放。因此,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自由、平等的伦理关系是我们道德思考的基础。道德的最基本功能是保卫这种新型的伦理关系,它要求对制度进行设计,道德将给出制度的合理性的价值基础,这种制度设计也许是宏观的、长程的,但在道理上却必须是严格的、甚至是斤斤计较的,因为它对整个制度的道德基础负责。所以,它必须采取一种非个人的,俯瞰式的视角,这样推论出来的就是一种公共的道理,简称“公理。”
之所以需要“公理”,是因为人们生存的社会性,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道德公理系统。公理是保证社会的健全存在和运作的最普遍、最基本的道德价值。从当代社会制度的角度上说,这种公理有哪些要点呢?(1)它实际上是社会本位性的,也就是说,公理是一种社会伦理、公共伦理,即从社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个人得到发展和完善这一前提出发来建构人们的应然规则,这是公理的形式规定;(2)每个人的最基本的社会权利是平等的,比如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机会、自尊的基础等都应该是平等的(注:参见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在正常情况下,反对任何一个人、任何势力对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侵害。这是一切社会公共道德规范的价值之源。这两条是只有在社会日益平等自由的时代才能讲的道理,而在宗法等级制度和官本位的社会中是不能讲这个道理的,同样,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中,更不能讲这个道理。在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中,国家之所以需要并且要强大,是因为要建立社会的秩序,保卫人们的自由和平等。因为市民社会本身由于其利益的利己原则,凭其自身要达到的均衡、建立秩序是要经过痛苦而漫长的过程的,并且要付出很大代价,所以,国家有维护和优化社会秩序的任务。在国家与社会相对独立的情形下,实际上一方面要让社会成员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自由地交往而演化成一种合理秩序,但同时,国家要负起保卫社会、指导社会的职责,它运用的最高手段是法律,其次是社会管理,而且,社会的知识阶层和先进分子则要成为社会的良知,为法律的合理性给出道德价值基础,并对市民社会给以道德追求方面的指导。因为市民社会虽然是独立的,但它在伦理上却是不自足的。
其实,以往的伦理学家也探讨道德的公理,但似乎都把讲理的基础错置了。它们的典型表述是由康德所作出的,即所谓的“可普遍化原则”。所谓公理,实际上是指人人应该遵循的道理、价值。但是,康德的可普遍化原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想通过使个人的主观准则能成为客观的道德法则来实现的,即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这一点去做,社会的体系就能存在下去。他认为,这要通过使用自己的理性推理能力才能达到。这种自我中心的伦理观点是有问题的,康德也意识到了。比如说,“除我之外,把每个人都作手段”(注: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这样一条准则并无前后不一之处,但这不是道德的,所以,他们加了一个限制即“人是目的”。但是在一种社会服务的体系中,人们不可能只是目的,而不同时又是手段。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康德只是在主观理性的范围内转圈子。我们认为,问题的根本不在于设计什么样的规范是人们都应该遵守的,而是应该弄明白什么样的价值是人们都必须保卫和体现的。所以,重要的不是把所谓“推己及人”作为道德的最高规范,而是你的准则要体现什么样的道德价值:你是出于偏狭的个人私欲呢,还是出于对社会生活规则的深刻领悟、内化了社会生活的普遍本质而作出此行为的。由“社会存在的目的”这个视角推理出来的行为规范,则是经得起康德的“可普遍化原则”的检验的。
这里思考一下以往一些著名的对道德规范的表述,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爱人如己”(注:这是基督教道德的“金规”,见《圣经·新约》中的《马太福音》第22章第39节,中国基督教协会1994年印发。)、“人所不欲,勿施于人”(注:参见赵汀阳《“我们”与“他们”》,载《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等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孔子说的“恕道”,它通过将心比心而推己及人,从自己不想受到的对待出发来限制自己不要把此种对待加于他人,它的否定性表述,确实能限制我们的任性,也就是说,它要求我们在一定范围内不作为。这当然有减少作恶的作用,表明孔子在道德问题上确实非常谨慎。但是这并没有指明应如何行善;不过他还有一个肯定的原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实际上这是一种积极助人的原则。但是以这种原则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仍有可能会以自己的意思来强加于他人,因为你心目中的“立”、“达”,并不一定是别人想要的,别人可能会有与你不同的志趣,这就是日常生活中时常出现的“好心办错事”现象的由来。其关键仍在于它的自我中心立场。一个人再聪明,再善解人意,也不能完全了解别人,你的想法和感受本身就会带有主观性,所以,你自己的主观准则是不可能成为完全客观的法则的。在这个问题上认真推究,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们要寻找的是明确的、一丝不苟的公理。
于是,学术界有人指出,真正的道德原则应该是“人所不欲,勿施于人”。诚然,这是超出自我中心的努力,其目的是还个人以绝对的自由、自我决定权,人们要对他人做什么,必须经过他人的同意,他人不同意的事,绝不要施加于他。但是,这实际上是把中心移到了自己以外的他人身上。这个道德原则的主观性仍然存在,而且有可能导致无政府主义。而耶稣“爱人如己”的伦理命令则是需要在爱上帝的原则下来实现的,它的哲学基础是众人一体,不能与任何生命相分隔、对立,因而要爱一切人,包括自己的仇敌。但这是上帝之眼的角度,这是神的道理,而不是人的道理。
在我们看来,这些公理的表达的根本问题在于,都是把视野放在个人对个人的关系之上,或放在超越于人类的上帝之上,而遗忘了个人生活的背景,即社会存在的目的。社会存在的目的是普遍的,因而它从根本上是超个人的,是客观的,是公理的基础,只有它,才能对所有的个人进行有公理意义的道德限制和提升。
我们既要讲“人的道理”,又要超越个人的观点,于是,就只有社会的观点。它本身有着时代性,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社会存在有着不同的目的,即价值理念。但是,我们身处的时代是我们生活的最高背景,我们只能以此来推导道德的公理,这就是我们生存的历史性之所在。我们能找到的绝对性,实际上只能是现实的、相对的绝对性。在一个人们社会、经济地位日趋平等的社会中,道德公理的根本之点就是:尊重他人为一个人,一个自由、平等的人,一个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人,一个参与组成社会并提供了社会合作的人。这是我们时代的公理的绝对基础,也是限制个人任性的最高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要借助政权的力量来强制执行其基本的法律规范。规范本身并没有不经批判就有的价值,它们的价值基础必须经得起道德理性的批判,或者说,它们应该以正当的道德价值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讲,道德理性就是一种价值理性,它指导着一切工具理性、操作理性。如果说,国家法律和管理的规范是社会的管理技术系统,那么,它们必须以道德价值为基础。正是在这个层次上,道德理性执行着社会批判功能。
我们可以看出,公理其实是指维持社会交往秩序的基本的、公共的原理,它的合理性就表现在每个人都要保卫并享有它。需要指出的是,以往人们都认为公理是一些规范,即人人都应遵守的行为规则。然而,在道德上,规范必须以最基本的价值为基础,也就是说,规范不是最本质的东西。实际上,我们根本无法设定一些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必须执行的普遍的道德规范,如果有,这样的规范一定会有惊人的反例,比如“不许撒谎”之类的绝对命令,而对追杀好人的坏人说谎就是一种道德选择。所以,我们应该在基本价值的引导下,为保卫并体现这种人人都要争取的基本价值,而采取恰当合宜的行为,对各种具体的情形进行道德的判断。正是因为我们要保卫和体现一些基本的、宝贵的价值,所以我们才有必要对规范作有变通的遵守,这种变通实际上不是规范的例外,而是对规范的成全。诚然,价值应该具体化为规范,但是,规范不能遗忘价值,而必须时刻受到价值的引导。所以,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并不是完全按照规范去做,因为规范的形式特点,不可能完全帮助人们决疑解惑。这需要人们诉诸自己道德的判断,判断怎样做才能体现价值。任何一个只把遵守规范看作是道德行为的人,是不需要也不可能有这种具体的道德判断力的。道德问题确实不只是一个规范问题,而更根本的则是一个价值问题、合理性问题。大而言之,道德要为一种制度奠定一种价值基础。比如说,一个制度的最基本的价值就是公正、正义,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正义、公正的价值蕴涵就不尽相同,比如柏拉图的“界域公正(不同社会等级各尽其责,绝不越位,相互和谐)”和亚里士多德的“分配公正、惩罚性公正、交易公正”的不同思路,现代则有诺齐克与罗尔斯的正义观之争。有什么样的正义观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设计,或者反过来说,一个人认为社会现行制度有着什么样的根本特征,就会有什么样的对正义价值的思考。即使在基本原则相似的前提下,对正义价值的细节和实现方式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伦理学在这方面谨慎思考。
二、道德上的情理:情感的普遍化
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思考其公理性的价值基础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是伦理学的全部任务,也不是道德理性的全部功能。道德理性还有一项更根本的功能——对人的精神进行塑造,在这个问题上,是理性返指于人自身、道德主体,也就是说,要让人的情感、感受、意愿、欲望、意志等等与理智相融渗,从而具备理智的普遍性,即得到普遍化,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情感欲望的普遍化。
所谓道德,就是指行为的善恶。而行为又是一个人的整体精神的外在化。所以,道德从根本上与人的精神相关联。人的理智诚然可以认识、推理许多东西,但是,没有情感的普遍化与之相适应、协调,也是不能化为行动的。即使是公理,一些基本的、公共的道理,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也是难以遵守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人的情感没有得到普遍化,而又迫于道德律令的威慑,就只能体现为“义务命令你去做的事,你就深恶痛绝地去做。”(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7页。)之类的情和理的二歧化。所以,要很好地执行公理,也要求人的情感得到较好的教化。而且,公理的考量,本来就含有一种伟大的人道情怀,因为它要维护人的自由、平等。情感受到教化,就是情感具备了理智的特点,变得普遍了,这就是融渗在情感之中的理性,我把它简称为“情理”。
情理又指人与人的情感相沟通,其关键在于一个人的情感是指向他人、社会的,有着向他人敞开的结构,有热爱社会的指向,因而能自尊而尊人。情感之理就表现为理智的普遍性与情感感受、欲望相互化通,这样,理智也有了生命情感的感受性,而情感欲望也有了理智性,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道德选择是“或者就是有欲望的理智,或者就是有思考的欲望”(注:《亚里士多德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页。)。这样的情感欲望就变得深厚、和畅、宽裕,与未受教化状态的情感欲望相比,后者则是狭隘、窄薄、只顾一己私欲满足而盲目冲动的。所以,情理的普遍性就表现在自己的情感变得普遍、优美而高尚,表明这个人成了一个普遍的现实个体,因为他内化了社会生活的普遍本质。他的情感感受、欲望,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也是可以存在的、值得赞赏的,而那种未受教化的情感欲望,则只有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才能存在,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则会自我取消。打一个比方说,一件乱涂乱画的作品就只是个人任性的表现,它是不可能持存的,而一件有着优美形式的画作,就是别人也能欣赏的,并有给别人以鼓励、振奋精神、净化灵魂、提升情感的作用。在道德上也是如此,一个人如果面对各种情境都能情感合度、行为合宜,这就是让人称赞的品质,而道德上的任性行为是不能持存的。
所以,考察情理的角度之一就是精神受到塑造即德性培养的问题。一个情感得到普遍化即融会了理智成分的人,其精神气质是与社会普遍的道德原则相应的,他能更好地禀有一种热爱社会、尊重他人的情怀,因为公理的道德价值基础就是普遍的。这是一个普遍实行法治的社会所要求的心灵情感品质。相比较而言,受到宗法血缘情感纽带束缚的人,如果不冲破这种束缚而具备公民的意识,那是难以拥有这种普遍情怀的,而那种情感偏私狭隘的人,则更是不能具备这种情怀的。
如果抽象地谈论情理的普遍性,那么,一个人只要其情感有着指向他人的结构,就意味着去除了情感的狭隘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血缘亲情的情感利他原则也是可以培养一种普遍情感的,这就是中国古代儒家如此重视“孝悌”,并把“孝悌”看作“仁之本”的根本原因。同时,“孝悌”也可以扩展自己的范围,因为大家都有父兄,并可与政治等级相类比。“忠”“孝”相连,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制度的性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伦理的根本缺陷。它可以培养那种以血缘情感为基础的普遍情感,但是它从本质上是不普遍的,因为它为宗法纽带所限制,奉行爱有差等的差序格局的情感联系方式。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情感仍然可能要进入、影响公共生活的行事方式,从而造成在公共事务上的人情偏私性,并进入权力结构和社会管理中,极大地损害社会公正。在走向现代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必须破除这种宗法意识的残余,树立以平等和自由为核心的公民意识和社会公正感。
一般来说,在最深的层面上,塑造普遍性的情感,可以用有着优美情感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来陶冶人们的情感气质,因为这些作品体现着人类情感的普遍范例,可以使人们的情感得到某种程度的普遍化;也可利用人类的数理成就、哲学和人文科学成就来培养人们精审的判断力,形成严谨思考的智力习惯,或通过严格、艰苦的训练来培养坚强的意志。这就是一般性的精神教化过程,它培养的是情理的普遍性,是深厚的道德德性。但是,如果没有社会现实的伦理关系和社会活动的哺育,是不能成为坚定的、现实的德性的。中国古代社会就把这种一般德性培育与古代宗法社会制度的等级性的公理结合起来,比如说,德性培育从属于“亲亲”、“尊尊”之类的社会公理。因此,我们应该把这种情理和德性与现代社会的道德公理融通起来,使之水乳交融,从而培养一种现实的德性。在现代社会中,那种只顾个人私欲满足的人,其情感是封闭而狭隘的,不能具备社会平等和正义的观念和情感。一个人情感偏狭,那是直接违背社会存在的目的的。任人唯亲、行贿、走后门、坑蒙拐骗等等都是源于情感空间的逼仄和正义感的缺乏。
考察情理的角度之二是人伦关系。在这方面,情理就是平等的人们之间的情感沟通,就是人们情感需要的满足方式。人是一种情感的动物,需要自尊和受人尊重,需要友爱之情的对待,同时,人们也有尊重他人、友爱他人的需要,因为在本质的意义上,人是从对方身上来发现自己的。另外,人际的情感沟通、和睦、有创造活力的人文环境都是我们所期望的。现代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有两方面的特点:第一个方面,由于利益的分立,出现了独立的利益主体,实利的追求、计较,会造成人际的冷漠,甚至可能会只讲求一种形式的公正,这种情况会给人际的情理联系带来极大的损害。人人互不关心,情感麻木,彼此冷漠以待,丧失了人情之通感的能力,这表现为社会生活意义的缺失。于是,国家法律也要来对形式公平进行干预,比如那些显失公平(实质公平)的高利贷合同,以及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式的残酷等等,看上去都是借贷双方自愿、平等的契约关系,但实际上都是由于失去了情理沟通的指向,以形式公正来危害他人。在这方面,法律在道理上必须考虑到情理因素,比如在人际交往中,不能以人身和生命做抵押。如果社会容许这样的行为,就只能证明这个社会本质上的不公正。所以,在协调人际关系时,也必须让公理与情理相融通。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独立的利益主体的出现,于是,以人际尊重、合作和情感之沟通来塑造个人的精神就显得更为必要。在现代社会,与他人的情感沟通由于不能借助自爱和血缘亲情等自然情感作为基础,只能以一种哲学的理由为基础,那就是社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能更好地塑造人们的精神。传统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路,推广到现代社会公共生活中,其意思很难说是健全的,因为在其视野中,“吾老”和“吾幼”总是有着优先位置的,这在乡土的风俗型社会中是可行的,但是在法理型的社会中是行不通的,因为它在道理上有欠缺。本来,独立、平等的个人在本质上是可以导致对社会公正的认同,更应该情感相通、合作,来达到增强自己力量和塑造自己精神的目的,可以培养一种典型的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的情意相通的能力,这样,就可以突破个人狭窄的眼界,使情感不再狭隘,而变得宽广深厚。因为平等独立的个人之间虽然容易产生对抗、利益竞争,但是也容易产生尊重对方的情感。这就如赛场上的对手所能达到的相互尊重和敬重,是人生的一种很高的境界,只有这样的情感和行为,才是令人由衷赞赏、钦慕的品质。所以,现代社会中的互敬、互爱、自尊尊人、情意相通是从社会生活的普遍本质中引申出来的。在这方面,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就是要注意不能把宗法社会中的血缘自然情感之理由,扩展到现代法理型的社会生活中,更不能被狭隘的实利计较封闭了自己情感的向他人、社会敞开的结构指向,所以,我们更应该把情理与现代社会的道德公理融通起来。
总之,道德理性本来就应该有公理和情理两个部分,它们本应该融合化通起来。由于历史的原因,一说情理,就会令人想起传统社会的血缘亲情及其扩展,而一说公理,就会让人感到是完全不讲情意的。这就要求我们从社会现实生活出发,界定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公理和情理的新特点,揭示它们相互融通的存在状态及其在保卫社会成员的自由平等、和睦人际、塑造人们的情感气质和德性等方面的巨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