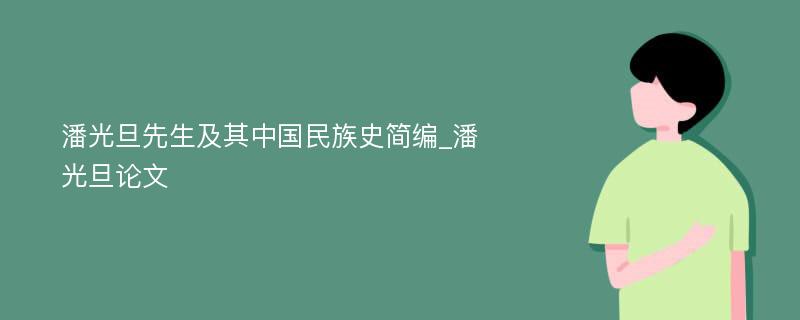
潘光旦先生和他的《中国民族史料汇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中国论文,民族论文,潘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12月,我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回北京探亲,到中央民族学院教职工宿舍去看望费孝通先生,费先生直截了当地问我:“你能不能回来整理潘先生的遗稿?”并且专门谈到我父亲潘光旦(注:潘光旦(1899—1967年),江苏宝山人,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和教育家。)所摘录的民族资料卡片。不久我就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开始收集父亲的遗稿。1967年父亲去世时,在北京大学工作的两个姐姐乃穗、乃穆都身处逆境,无法妥善保存父亲的遗物,因此决定将他的全部藏书、资料赠送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这时我最先找到的是父亲的卡片柜,它被精心地保存在图书馆吴丰培老先生的工作室里,吴先生和父亲在爱书、读书方面存有很多共识,他了解这些卡片的意义和价值,让我尽快找回空缺的一个抽屉,并认真地清点一下。随后,我仔细看了柜中全部卡片,同时抄写了一个目录。这里最主要的是民族史料方面的卡片,如阅读《二十五史》后摘录的卡片、研究土家族问题所积累的卡片、研究中国犹太人的历史所积累的卡片,其它还有父亲藏书目录卡片等等约万张。
在讨论如何整理民族史料卡片时,费先生谈到自五六十年代以来他和父亲经常讨论民族研究方面的问题,他了解父亲摘编民族史料卡片的思路和想法,他希望自己有时间来做这件事,他认为不了解情况的人很难进行这项工作。他也曾想到请吴丰培先生来帮助进行,后来我首先着手整理的是父亲关于中国开封犹太人的遗稿。直到2001年乃穆、乃和所编14卷本的《潘光旦文集》全部出版之后,我们才有机会整理有关的民族史料卡片。从父亲幸存的日记(注:《晚期日记》,《潘光旦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617页。)中了解到,他从1959年开始阅读《二十五史》,对民族史料加以圈点,至1961年10月23日全部阅讫。其中《史记》阅读了3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各2遍,其他1遍。又因《南史》,《北史》前阅本已出版,又重阅一遍,再加圈点,至1962年3月23日完成。紧接着阅读圈点《资治通鉴》,从同年3月24日开始至该年9月9日阅完全书。自1962年5月开始摘录《史记》中有关民族史料,做成资料卡片,至当年9月止。现存卡片425张。1963年3月至5月间,摘录了《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汲冢周书》、《竹书纪年》几种书,共存卡片796张。其中《春秋左传》的资料对比了顾栋高著《春秋大事表》中的《四裔表》,对顾著也作了一些摘录。《资治通鉴》民族史料的摘录做于1963年9月至12月之间,但只摘录到第二十二卷,现存卡片201张。以上《史记》及《资治通鉴》之卡片各为一套,而《春秋左传》等5书则混编为一套。
1963年5月29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副主任傅乐焕教授来访,与父亲谈录登《明史》中民族资料事,以配合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工作。父亲当即表示同意,并于5月30日开始进行摘录。由于这种摘录往往要结合辨识,所以难以请助手代为摘录,次定由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请王兴泰先生同步抄录副本,以便提供他人使用。至1964年12月12日全书摘录完毕,现存资料卡共839张。这份资料当时对《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起到有益作用。傅先生曾和父亲讨论过编印成史料长编的事。惜经费问题不能解决,王兴泰的抄录工作未能全部完成,至1965年6月28日终止。其后傅先生竟于1966年5月不幸去世。“文革”过去,此抄录副本也不知下落。
上述4套卡片,每套卡片前有“总录”部分,其后按民族分类,以族类名称的拼音排序,每张卡片左上角列有片目,右上角以红笔标出所摘书名。每条资料写明所出卷数或章节。每张卡片上抄写资料一条至数条。父亲除摘录了各书正文及部分注释外,在一些资料条文之下还加有署名光旦的按语,表达自己的看法及研究心得等。《二十五史》其它部分虽有圈点,但因父亲遭文革劫难,不幸去世,未能摘编成卡片,现已无法按其意图进行编辑,实为憾事。
那么父亲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来进行这件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耗时费日的重头工作”呢?1957年他被错划右派之后,在民院有几年没有固定的单位,直到1961年10月才分配到历史系去工作。此时是游离于临时分配的集体任务之中,如《辞海》编纂工作、边界资料工作等等。1957年之前他所承担的研究计划,土家族的研究原拟再作补篇,现既以土家问题而获罪,至少暂时不可能再写作,对畲族的研究论文(1961年《从徐戎到畲族》,已佚)也完成了,正可在此时按自己的意愿进行此项工作,但也只能是在被分配的临时任务、许多会议和政治学习之余见缝插针式地进行。
这项工作不是一项单纯的资料工作,而是一项有关中国民族史的庞大研究的基础步骤。费孝通先生1981年和1985年两次谈到父亲对苗、瑶、畲民族关系的一段设想。他说:“这段设想的酝酿,始于潘先生和我一起在1952年调来中央民族学院之后和1957年之前的一段时期。”这段设想是:“我们可以从徐、舒、畲一系列的地名和族名中推想出一条民族迁移的路线。很可能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东夷中靠西南的一支的族名就是徐。他们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现在还留下徐州这个地名。从这一时期的文献中也可看到这块地区被居民称作舒。潘先生从瑶、畲的盘瓠传说联系到徐偃王的记载,认为瑶族中的过山榜有它的历史背景,只是后来加以神话化罢了。这一批人,后来向长江流域移动,进人南岭山脉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瑶,而从南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里和汉族结合的那一部分可能是畲,另外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可能就是苗。”(注:《潘光旦先生关于畲族历史问题的设想》,《费孝通文集》,第10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393页。)费先生认为这种设想的重要性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宏观的整体观点,它指出了我们中国各族人民在历史上是不断流动的,而这些流动有其总的趋势。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里,总的说来是北方民族的南下和西进,中原民族的向南移动,沿海民族的人海和南北分移,向南移的又向西越出现在的国境。这一盘棋如果看清楚了,我们现在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也就容易说明了(注:《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费孝通文集》,第8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293页。)。他还特别提出:潘先生对于我国各民族历史的研究,一向不主张孤立地研究某一民族的历史。他在研究了土家和古代巴人之后,在1955年发表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一文中明确地说:“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上绝大部分的巴人,今日湘西北‘土家’人的一部分祖先也不例外,在发展的过程中,变成了各种不同程度的汉人,终于和汉人完全一样,成了汉人的组成部分……因此,这种历史研究又必须与汉族,乃至全部中华人民的大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个总问题密切地结合起来进行,至少第一步也应该不断地互相参照着进行,才有希望把头绪整理出来,孤立地搞是绝对不行的。在祖国漫长的几千年的历史里,这样的一个族类之间接触、交流与融合的过程是从没有间断过地进行着、发展着,我们现在还在这过程之中。从人文学的方面来看,也不妨说,这过程就是祖国的历史。”从这一点认识出发,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就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发展,从宏观方面发展就是拾起中华民族形成过程这个课题进行研究。研究各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向微观方面发展的研究工作(注:《潘光旦先生关于畲族历史问题的设想》,《费孝通文集》,第10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393页。)。父亲对土家族、畲族历史的研究即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摘编《二十五史》等文献中民族史料卡片工作也同样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在具体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不断扩充、加深认识。他的头脑中,始终存在着一幅我国各民族在历史时期中的发展、变化、流动迁徙和中华民族形成、民族关系变迁的一个整体画面。如1956年父亲和张祖道等一同到川鄂进行土家族调查的途中,为了让他们了解“土家”和“巴”所处的位置,曾通俗地为他们勾勒了一幅中国古代各民族迁徙流动的大画面(注:《随潘光旦师川鄂“土家”行日记》,彭振坤主编,《历史的记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6—27页。)。
因此在摘录了先秦民族史料之后,1963年父亲曾向历史系表示自己可以试讲“先秦民族形势鸟瞰”专题课,又说:“前途逐年扩充补缀,二三年后或可发展成为比较完整之课目也。”
父亲在民族史料卡片中写了一些按语,记载了心得、看法,以下谈谈他曾经关注和探索的一些问题:
1.关于“华”、“夏”、“诸华”、“诸夏”的名称。
他在1962年10月的日记中说,民院有人来“商检《太炎遗书》中的文录,供‘中华民族’一词目讨论时参考。此词目本我所属稿,其部分资料即出章氏之《中华民国解》一文,去年讨论时始终未约我参加,今日亦只向我索此来源,去年同时我曾建议加列‘夏’(诸夏)、‘华(诸华)’二词目,而不仅列‘华夏’,且曾送去所拟释文稿,亦未见采纳或其它下文,——甚所不解也。”
1963年摘录卡片中,他注意到《汲冢周书》卷八《史记》篇中所记穆王命左史戎夫集古诸侯败亡之经验,“华氏以亡”,他说这个华氏与夏后、殷商并列,并在夏、殷之前,或与后之称“诸华”有涉。是则“华”之称犹在“夏”之前矣。此前所未喻。接着又看到“西夏以亡”,他说:“是夏后氏以前尚有夏,与陶唐氏同时,与上文所叙‘华氏’可能同时,或更早,是则华夏二字究孰为首出,尚不易论定也。”以后他说:“单称夏,而不称诸夏,《战国策》不一见。是亦说明诸夏已日归于统一矣。”
《明史》中他又摘录了“华”(卷一九九《郑晓传》)、“中华人”(卷三二二《日本传》)两条,这个称呼都是相对日本而言的。所以他写按语说:对国外用“华”,对国内诸少数民族言,则往往用“汉”。《明史》言“番汉”、“夷汉”之处不一而足。关于“汉”之一词,率不列片,此处华人之称似尚属仅见,并于以见“汉”、“华”二词之用法,在当时已有内外大小之别。今“汉族”与“中华民族”之区别,已于此见之矣。他又说:唯以语言论,“华”字之用法似始终等于“汉”,曰“华言”者,汉语也,然似未见有用“汉语”一词者,例如,卷二○○,《刘清源传》(附《詹荣传》后)云:“那颜者,华言大人也。”
2.关于秦起于戎。
他根据《史记·秦本纪》画出秦之先世世系图,说明秦和戎有密切的关系:“大抵自胥轩前一二代至秦嬴时,前后约十代,与戎合,此后分异。”申侯称胥轩是戎,所娶骊山之女为骊戎。秦之先世从事牧业。他说:“同起戎狄之人,周以农,而秦则以牧。”他推测秦出于犬戎,或其先主要成分之一为犬戎。理由是《秦本记》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祭祀的时候,以狗血御蛊,就是把狗血当做最神圣有效的东西。并且,太史公说“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按应作氏),有徐氏……”,徐和徐偃王的徐不能无涉,而徐偃之后是以“鹄仓龙犬”为祖的。他写下:“姑书存此说,续加考证。”
3.关于山东半岛是远古各民族迁徙的汇合点和转运站。
《史记·封禅书》载秦始皇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的第七神是主日之神,所祠之山为成山,注,成山在东莱不夜。这个“不夜”他认为可能和越的自称有关。越之先自西而东,散布东海岸全部,故北有“夫馀”,中有“不夜”,南有“武夷”、“番禺”。他推测齐境的“不夜”是从东北渡海而来,先到成山。百越从东海岸再向南海岸移动。而山东半岛是远古各民族自西徂东、自北徂南的汇合点与转运站。
他推测“不齐”与巴人自称有关,巴人自西来,故有天齐之神(八神之第一);苗人自北来,来故有蚩尤主兵之神(八神之第三);越人自东北来,故有“不夜”主日之神(八神之第七);八神之第二即地主神,所祠的山为泰山,有可能为傣人先辈的贡献。
4.关于畲为徐后。
1961年前他写过一篇《从徐戎到畲族》的论文(已佚),认为畲族的先人是徐戎。1962年1月访问福州时,特别请林仲易先生带他去看小巷中民间旧所广泛信仰的“泗洲佛”。在这些卡片中他仍然关注着这个问题,摘录了有关的史料。如徐偃王的故事,他说:“徐偃之亡,一说周穆,再说楚文,明其为民间传说,然传说亦必有其事实根据,而此事实之发生必甚早,周穆或周穆之前,但不能早于《费誓》之年代耳。”因为《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说伯禽作《费誓》,平徐戎,定鲁。”“徐偃之亡无论其时代为周穆,抑为楚文,要不等于徐之灭,特其国境、从属之国、影响,大见削弱耳。”以后,他认为有许多徐偃王的遗迹,如“徐侯山之徐侯疑与偃王有涉,两浙多徐偃遗迹,全系江淮三十六国人渡江携与俱来者……此殆一例也。”又认为闽中又一民间迷信“泗洲佛”也是徐偃王的遗迹。他从一系列的地名也看出“畲为徐后”。他说:“徐、舒、邻、佘、畲等皆同类字,代表同一事物,一个人群,字音、字形前后均相联属,畲为徐后,相绳一脉,不可诬也。”
5.关于“龙泉山寇”。
1965年11月他到井冈山访问时,悟出《明史》资料中所谓“龙泉山寇”之“山”,即井冈山无疑。理由是:(1)龙泉即清代以来之遂川,此次访问虽不经遂川县治,然井冈中心及迤东境地原属遂川;(2)井冈山,旧日舆地之书率不详,显为汉人所不甚涉足之地,他说此点须再续加考定;(3)井冈景色之美,实不在庐山之下,今其地竟无一处僧寺道观,亦不见有坟山,与其它名山迥然不同;(4)井冈山极少荒山秃岭,竹木之盛,得未曾有,其间尚闻有些原始森林;(5)井冈山土语甚特别,甚至江西人亦全不懂,此说明其间或有部分非汉语之基础成分。他说:有此五端,可知“龙泉山寇”者即居于井冈山及其周匝山区之瑶族耳。“山寇”为畲族、瑶族之先之通称,东汉以还之史书皆载之,此固不待多事说明者。瑶族在历史上长期以来分布在赣、湘、粤、桂四省毗连地区,以江西论,小镇压不计,明代大镇压至少有三次,王守仁曾对桷岗、三利、左溪等地大围剿。大抵“龙泉山寇”受镇压后,瑶族散布地区更趋压缩,而只能限于上犹一隅,到王守仁分上犹设崇义县,则幸存者非汉化即退两粤北境,而更集中于九连山区矣。“此论而确,则可知井冈所以成为当代革命之策源地,兄弟民族亦间接有其一分力量也”。“姑存此一说,容前途纠正或充实”。
潘光旦先生摘录民族史料的工作始于1960年代,但没有全部完成。在费孝通先生的关心支持下,近日,由潘光旦编著,潘乃穆、潘乃和、石炎声、王庆恩整理的《中国民族史料汇编》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三册100余万字,汉代以前一册已发行,明史部分待出)。它的出版一方面为完成父亲和傅乐焕先生等前辈学者的遗愿,一方面对民族史研究者还会有一些参考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