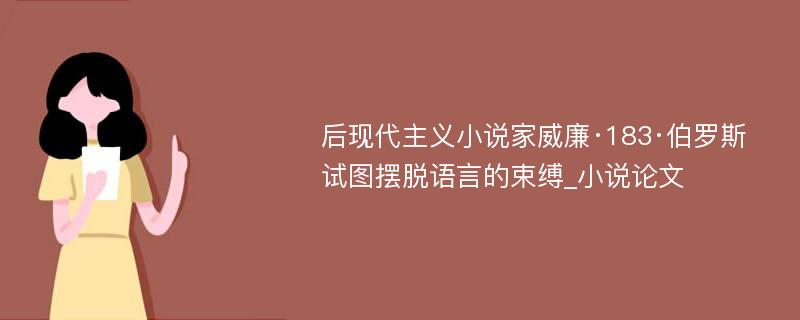
一位力图摆脱语言羁绊的后现代派小说家——威廉#183;巴勒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派论文,小说家论文,羁绊论文,威廉论文,勒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威廉·S·巴勒斯(William S.Burroughs.1914—1997)的名字往往被人与“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杰克·克鲁亚克、艾伦·金斯伯格等人联系在一起。然而与“垮掉的一代”的写作不同,巴勒斯的创作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克鲁亚克强调“自发性创作”,金斯伯格以诗歌为主要形式对社会进行批判,而巴勒斯却跟许多后现代小说家一样关注着语言本身,并由此引发对社会与人类的更为深刻的人文思索。他认为,在文学创作中只有对语言进行解构才能真正达到精神上反控制(decontrol)的目的,因为“语言本身就是谎言”。(注:Jennie Skerl & Robin Lydenberg ed.,William S.Burroughs At the Front(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24.) 巴勒斯被誉为美国后现代主义创作的先驱之一,作品颇丰,其代表作品有:具有浓厚自传色彩的《贩毒者》(1953)、在美国招惹审判风波的《赤裸的午餐》(巴黎,1959;纽约,1962)、60年代使用剪裁手法的实验三部曲《软机器》(巴黎,1961)、《爆炸的票》(巴黎,1962)、《新星快车》(纽约,1964)、70年代的《野孩子》、《终结者》、《圣人港》及80年代的另一三部曲《红色夜幕下的城市》、《死路之处》、《西部土地》等等。其中,《赤裸的午餐》最为人所知。除了文学创作以外,他还举办过个人画展,也曾与人合作拍过电影,灌制过CD。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其祖父是美国第一台加算机的发明者,母亲是南北战争中南方著名将领罗伯特·李的嫡系后裔。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他,生性内向、少言而敏感,却对枪支和毒品有着不可抑制的好奇心。1944年他因携带毒品在纽约被捕,1947年在得克萨斯因酒后驾车与公共场合猥亵罪再次被捕,1951年在墨西哥因亲手枪杀了自己的妻子琼再次入狱。同时,他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同性恋者。巴勒斯是个在当时引起争议的人物。
代表作《赤裸的午餐》同样是一部令人争议的作品。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做区际城(Interzone)的地方,它充满了敌对和压制,各种势力展开激烈的竞争,争相操纵人的心理。作品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地狱般的世界,这里泛滥着性交、海洛因与各种可怕的病毒。在这个魔窟里,漂移着活在恶臭污秽中的一群变形的人类。《赤裸的午餐》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人间地狱。因为该作品涉及诸多忌讳话题,由此引发了1965年马萨诸塞州最高法庭的审判,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和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都到波士顿法庭上为此书做激烈辩护,致使法庭最终否定了该书为淫秽小说一说。
短篇小说《寒春新闻》和《走在你身边的第三者是谁?》均译自旧金山城市之光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巴勒斯档案》(The Burroughs File),其中《寒春新闻》最初出现在1965年密歇根的一家名为The Spero杂志的第一期上,而后在多家杂志登载;《走在你身边的第三者是谁?》写于1964年,首先在纽约的《艺术与文学》杂志上面世。这两个短篇均创作于60年代,当时的巴勒斯正热衷于和他的密友、画家布罗·吉辛(Brion Gysin)利用“剪裁法”(cut-up)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上面提及的科幻三部曲《软机器》、《爆炸的票》和《新星快车》便是巴勒斯在这一时期对该手法持有饱满热情的产物。选取的这两篇短篇均显著带有该手法的特色。“剪裁法”并非巴勒斯与吉辛首创,在现代派作家T.S.艾略特的《荒原》、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与法国达达主义诗人查拉(Tristan Tzara)的创作中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意象并置的创作手法,然而,这些只是作者此时此地为了表达作品意义的一种灵光闪现,相对于现代派的主要创作手法如意识流来讲,其分量轻之又轻。可是,当这一手法到了巴勒斯与吉辛的手上后,他们将它广泛地运用到通俗文化和现代文学的意象中来,使其成为一种有力的艺术工具。
“剪裁法”实质上就是蒙太奇的手法,它始于绘画,后来被应用在文学创作上。1959年9月的一天,吉辛在房间里试图作画,他用剪刀剪画板时,将下面用来保护桌面的几张《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最上面一页剪去了狭长的一条,他发现被剪掉的那部分与下页的同一行在意义上产生了有趣的组合,于是他又将这不完整的一页与下面的每一页拼接,结果令人兴奋。当巴勒斯一周后从外面回来时,吉辛兴奋地向他展示了自己的发现。于是,两人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将这一手法广泛地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来。巴勒斯认为这一手法符合我们意识的真实情况。他举例说:如果你在街道上行走,之后记录下所看到的事物,你肯定会大吃一惊。一些表面上看起来连贯和流畅的事物实际上却是支离破碎的意象并置:一束电焊的火花,一阵音乐,一个标志牌,一股飘来的香味……这一切被我们训练有素的大脑赋予了某种“秩序”,加工成了具有连续性的线性叙述文字,如影片画面一般讲述着一个完整的故事。在完成这一过程中,文字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巴勒斯认为文字是实现控制的主要帮凶,“建议是文字,劝说是文字,命令是文字。没有文字,控制的机器就无法运转。”(注:Barry Miles,William Burroughs El Hombre Invisible ( London:Virgin Books Ltd,2002) ,p.134.) 我们的思维被语言控制着,不是我们在使用语言,而是语言在使用我们。“词语原本是个健康的神经细胞,现在却变成了寄生的有机体,不断地侵入与破坏神经中枢。”(注:Jennie Skerl & Robin Lydenberg ed.,William S.Burroughs At the Front,p.56.) 人类沦为语言的奴隶,而对控制者惟一的抵制途径就是消灭其实现控制的工具——语言。“剪裁法”通过对支离破碎的意象的不断并置展现了一个没有逻辑没有理性的无序世界,而这恰恰是我们意识的真实图景,这便是作者想向读者传达的信息。这样,作家和读者最终从传统的语法和句法中被解放了出来。在这个混沌的世界里,巴勒斯向我们展示语言是多么地苍白无力。“任何人,只要有一把剪刀就能成为诗人。”(注:William Burroughs El Hombre Invisible,p.128.)
短篇小说《寒春新闻》正是巴勒斯剪出来的作品。作品中出现的人物有马丁、阿奇、克莱姆、管道工、内地的悲伤侍者、警察、不知名的年轻人、男妓、“我”和“他”。小说的开始似乎要讲述一个连贯的故事,马丁骑着马来到了名叫蓝色交汇处的地方,他喝完一杯威士忌后向酒保要了一间房间住了下来。而后讲述的是阿奇带领一伙人向马丁索要其丢失的马匹,因为克莱姆看到他在寒春卖掉了一些牲口。马丁对此一言不发。小说从一开始便突出了一种极为安静的氛围。在“对勘测线的多年等待”一节中,剪刀的痕迹随处可见,毫无关系的意象像走马灯一样转动:马丁、手枪、战士、管道工、一个名叫克里科的人、死亡之星、起风的街道、枯死的树叶、撕裂的天空、一只遥远的手……惟一让人联想到前面故事的句子是:“为什么告诉我,阿奇?”但是说话人由马丁已变成了枯死的树叶;“我没看到你”的字语也再次出现;香烟的烟晕也同样飘浮着。随后的“内地的悲伤侍者”一节继续了上一节的写作风格,安静的杂货店、铺着鹅卵石的街道、风中的湖、内地的悲伤侍者、老人、年轻人、警察与男妓,重复出现的意象有爆炸的星球、一只遥远的手和“安妮·劳瑞”曲子。值得注意的是整篇小说中表示颜色的词语:夕阳就像浓浓的蓝色灰尘似的从山上落下来;沉默凝重、幽蓝;夕阳下他灰色的眼睛折射出一股冷酷;淡蓝色夏日的天空;模糊的黄色肋骨;银色的灰烬;苍白的枪支;风中的湖宛若一张被撕碎的银色的纸;白色,白色,白色,一束眩目的白色;银色鬼魅;黑色和银色交织的天空;白色的海堤墙。蓝色、灰色、白色、黑色与银色均为冷色调,其反复出现加重了小说蓄意营造的一种空寂贫瘠的虚无氛围,内容与形式的契合走到了彻底颠覆的极限。作者天马行空地游走于各种意象组成的世界里,把希冀从作品中寻求意义的读者带入了一个令其不知所措的领域。
1961年金斯伯格与格里戈里·柯索(Gregory Corso)为某杂志对巴勒斯进行了一次专访,当金斯伯格问及该采取什么步骤才能使意识摆脱控制获得解放时,他回答说,首先是沉默,我们要使自己远离文字,为了做到这一点,可以用其他表达方式来取代词语与概念,比如颜色。可以将词语转换成颜色,用颜色来表达意义。换句话说,人类必须远离语言形式来获得意识。接着,科索问道,具体该如何采取这一步骤呢?巴勒斯回答说这正是目前他在做的。第一步要脱掉旧的盔甲,因为文字已经深入到你的内心……(注:William Burroughs El Hombre Invisible,p.135.) 不知所措的读者在碰到类似《寒春新闻》等小说时,判断力的标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思维惯式失去意义,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话语来描述:“元叙述”被彻底地颠覆,总体性随之丧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该如何正确认识这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创作呢?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创作的合法性何在呢?有趣的是,巴勒斯的创作实践与著名的后现代批评家让-弗·利奥塔的理论不谋而合。关于语言,利奥塔特别欣赏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游戏”概念的描述,不同的话语类型就像是不同的“语言游戏”,各自遵循着不同的游戏规则。随着总体性的丧失,利奥塔指出:“大多数人都不再怀念失去的叙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堕入了蛮荒状态。拯救他们的是这么一种意识:合法性只能来自于他们自己的语言实践和交流互动中。”(注:秦喜清,《让—弗·利奥塔 独树一帜的后现代理论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第123页。) 在这种情况下,判断的标准从何而来?利奥塔认为,判断的能力不是依靠遵循某种标准,在无标准的状态下,思想呈现出开放的姿态,它可以躲避由标准带来的思想共识(consensus),由此躲避思想共识带来的总体性观念,并最终躲避总体性包含的压迫性——这正是巴勒斯孜孜以求的。利奥塔强调说,艺术不是以还原的方式模拟愿望满足过程,而是通过形象的作用达到一种解构作用,这种解构导致一种难以表述的窘境,一种辞不达意、闪烁不定的状态,在正常意识状态下不能容忍的冲动、意愿堂而皇之地进入到意识领域,艺术抛掉了和谐的、令人感到欣慰的、熟悉的东西,“以暴露那些丑的、令人不安的、陌生的、无形式的、代表着无意识混乱的那些东西”。(注:秦喜清,《让—弗·利奥塔 独树一帜的后现代理论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第66页。) 《赤裸的午餐》便曾被一位名叫约翰·温的评论家贬为一堆垃圾,根本不值再看第二眼。在利奥塔看来,这样的艺术作品已经超越了美丑的范畴。对既定形式的否定,在暴露中的追求,由于无意识混乱的本质,这种否定与暴露注定将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由此,艺术进入到表现与追求极限的层次,从而站在哲学的位置上。(注:秦喜清,《让—弗·利奥塔 独树一帜的后现代理论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第66页。) 后现代的艺术家正是站在哲学家的位置上的。
《寒春新闻》的原稿是一幅拼贴作品,所不同的是巴勒斯对其进行了再加工,也就是说,他将剪裁后的作品又做了剪裁,因此最终完成的作品是经历了冗长挑选之后的成果。可以说,意象的并置并非随意的组合,而是经过了反复实验的结果。毫无关联的意象并置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它们取代了“元叙事”的话语模式,意义尽管难以捕捉,却毫无疑问地开拓了人们的意识,呈现了意识的真实画面。尽管在创作过程中,在对意象的选择上,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作家本人的影响,但其作品所努力追求并向往的自由的确唤起我们对问题的关注与现状的反思。
《走在你身边的第三者是谁?》是巴勒斯1964年又一语言实验的作品,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剪裁法”。他注意到当人们阅读报纸上其中一栏的一篇文章时,眼睛会不由自主地看它左边和右边的栏目,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拼贴。1964年的二月他在一篇旅行笔记里采用了这种“三栏技巧”(threecolumn technique),他将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以日记的形式写成一栏,之后他将自己当时内心的感触另辟一栏;第三栏则是他的阅读摘要,引用的是他旅途中随身携带的一本书中的句子。选译的这篇文章正是采用了这种技巧,正确的阅读方式应该以栏为界,顺着一栏一直读下去,而不是跨栏阅读。在选取的这篇文章中,每栏仍都没有连贯的情节,巴勒斯式的词语频频出现,如“重新书写计划”、爆炸的星星、现在的尿壶、“悲情恶毒好男人”与暗示同性恋的“血液和粪便”等。《寒春新闻》中的意象再次出现在这里:如爆炸的星星、血液和粪便、多风的街道、白色的台阶等。在第三栏的结尾,冷色调再次出现,如柠檬色的阳光、浅蓝色的眼睛、白色台阶上的鲜血与白色踏板。这篇应用“三栏法”创作的文章与用“剪裁法”创作的《寒春新闻》之不同在于它包含了作者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的表白。在第二栏巴勒斯阐明了后现代的时间概念:“‘现在’是过去发觉的影像病毒受到现在主人牵引的那一刻。于是主人就踏着过去走出来,而当你在现在的尿壶里懵懵懂懂地到达交叉点时,主人同样也踏着现在的现在走了出去,那么就全是尿了。”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由于意识、生命、物、事件及所有的一切都在不停地流动之中,在不断地消遁之中,因此把捉这样的“现在”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时间流动的本性,每当我们说到“现在”时,这个“现在”实际上正在流去,因此我们要把捉那个本来面目的“现在”时总会感到“太晚”;而现在的进行过程又使我们内心中把握在“此时此刻”实现为物本身的那种“实体性”(entity)的规划显得过于超前。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现在”状态时,一切尚在进行中,它尚未达到实在体所具有的稳定性,它是一种尚未完成的状态。(注:《让一弗·利奥塔 独树一帜的后现代理论家》第207页。) 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不可表现性与不可确定性的认识基础。在第三栏的第四段,巴勒斯表达了对文字的观点,他这样写道:“人一开始接触的便是文字,文字是个什么东西!当然,伙计,习惯是很难改变的。人类写了50万年的RX,突然停止自然困难。但我却在医德的指引和健康委员会的干涉下,不再拘囿于文字了。”巴勒斯认为“语言本身就是谎言”。他的语言观与宇宙观是分不开的。根据一个古老的传说,白种人起源于3万年前的一次原子爆炸,制造原子的文明连同其先进技术一并被摧毁,惟一幸存下来的是生活于先进文明边缘的奴隶,他们对于先进技术一无所知,由于受到爆炸的辐射变成了白化病人。他们向四面八方迁徙,有的去了波斯、印度北部、希腊和土耳其;另外一些到了更西部的欧洲,住在了洞穴里。现在的西欧人和北美人便是这些居住在洞穴里的白化病人的后代。在洞穴里,他们染上了一种病毒,用巴勒斯的话说这是“对地球生命的极大威胁”。这一病毒即弗洛伊德所谓的“无意识”。病毒在洞穴人的后代中代代相传,从而与那些没有过洞穴经历的人种产生了天壤之别。表现在语言上,即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的区别。象形文字,无论如何去读,其象征一目了然;而表音文字如英语却不是这样。巴勒斯说:“当我们写下一些词语时,它们成为了意象,然而在我们头脑里出现的是词语的意象而非词语所象征的意象,斯坦因的话‘一支玫瑰是一支玫瑰是一支玫瑰是一支玫瑰’(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只有付诸文字才能成立;但波兰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尔兹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却说,一支玫瑰(花),不管怎么样,都不是一支玫瑰(词语)。”(a rose(flower)is,whatever it is,not a rose(word))(注:William Burroughs El Hombre Invisible,p.176.)
在索绪尔看来,构成语言符号的能指/所指间是一个任意的组合,但一经组合,两者间的联结关系就十分地稳定了,而拉康却认为能指/所指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结合,而是一种分裂,这一分裂象征地表达了无意识和语言表达间的不和谐关系,语言试图将主体置放在一系列词语中,获得稳定性,但无意识却可以引发出乎预料的转变。巴勒斯的创作游走于词语与无意识之间,他笔下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意象、支离破碎的故事情节与不断的重复正是体现了这种分裂。于他的艺术创作而讲,其艺术表现打开了一个艺术空间,敞开了一个更为广泛的意识领域,他努力使无意识成为直接通向意象与真理的途径,巴勒斯说:“只有当你学会用意象而非语言思考(thinking in images)时,(在逃脱语言的斗争中)你已经上路了。”(注:William Burroughs El Hombre Invisible,p.177.) 巴勒斯在文学创作中进行的哲学思考使我们不仅关注后现代视角下语言与人的关系,更唤起我们对政治-社会领域一体化束缚模式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