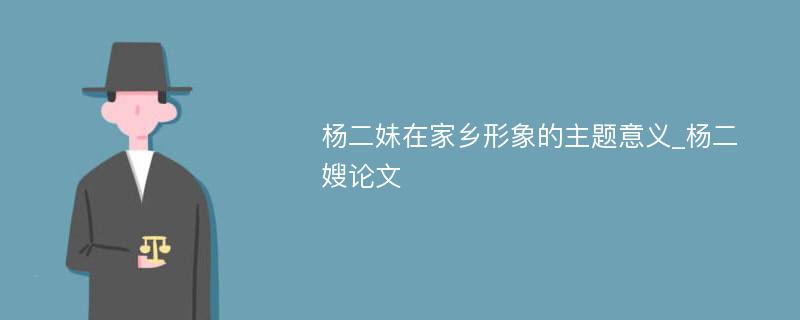
《故乡》中杨二嫂形象的主题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故乡论文,意义论文,形象论文,主题论文,中杨二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小说《故乡》是初中语文的传统教材,小说主要写了三个人物:闰土,杨二嫂和“我”。在课堂教学中,不少语文老师往往只注意对闰土这个人物的分析,却忽略对杨二嫂这一形象主题意义的开掘。
主题是通过人物形象展现的。在《故乡》这篇小说中,重点写了“我”童年时代和少年闰土的愉快的交往以及20多年后“我”回到故乡与闰土重逢的场面。通过闰土20多年前后的巨大变化,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十年中国农村破产的悲惨景象,揭示了广大农民生活痛苦的社会根源。这个主题显然是鲁迅小说的主要视角。但是,如果我们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肯定是不够的。如果说闰土的命运代表了20世纪初中国广大贫苦农民的共同命运,闰上的遭遇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的社会现实的话,那么杨二嫂这一形象则是另一群破产者——城镇小市民的代表,她的命运和遭遇,从城镇小市民的角度揭示了当时社会经济的衰败、萧条和没落,反映了社会破产的广泛性。从而,杨二嫂的形象在更深的层面上开掘了《故乡》的主题。
当年的杨二嫂,在“我”的印象里显然同20余年后重新见到的杨二嫂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从前的她,年轻美貌,“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是这个小镇上出了名的“豆腐西施”,“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而今,这位昔日的“豆腐西施”竟然变成了凸颧骨、薄嘴唇、“张着两脚,活橡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且又尖嘴利舌、自私庸俗贪利的丑老太婆!这是多么惊人的变化!与闰土的巨大变化相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小说通过这两个主要人物的巨大变化,透视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闰土的变化在小说中可以找到比较明确的答案:“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的他像一个木偶人了”。但是,促使杨二嫂产生巨大变化的原因何在呢?似乎年纪大了,“人老珠黄”是唯一的原因。上课的时候,许多学生就是这样回答的。在小说的情节表层中确实找不到更深层的理由。然而,只要我们引导学生运用自身已有的政治、历史常识深入分析,就不难知道,杨二嫂这个小市民的命运与闰土这个破产农民的命运,本来就有着内在的、必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尤其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的主要经济命脉是农村经济,农村经济的破产无异于釜底抽薪,势必导致城镇经济的破产。闰土们“拆了本”,”收成又坏”,口袋空空,杨二嫂们自然也做不了小本生意,自然也无法维持自己的生计。这样的故事,我们在《春蚕》《多收了三五斗》《林家铺子》等小说中已经不只一次看到过了。沉重的压力使闰土变成了未老先衰的木偶人,畸型的艰难生活自然也会将昔日美女杨二嫂变成“辛苦恣睢”的丑女人!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小市民都摆脱不了贫穷、破产的命运。
作为思想战士,作为先驱者,鲁迅时常感到孤军奋战的苦闷与寂寞,“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即使回到久别的故乡,这寂寞仍然像大毒蛇一样紧紧地缠住“我”。而揭示人与人之间可悲的“隔膜”,正是《故乡》主题的另一重要视角。这种可悲的“隔膜”像一道“厚障壁”隔断了“我”和少年时代的朋友闰土的心灵沟通。闰土的一声“老爷”使“我”打了个寒噤,使“我”感到“非常悲哀”。而在此之前,“我”和杨二嫂不期而遇时,杨二嫂一番尖酸刻薄的胡言乱语,对“我”来说,更是匪夷所思:
“啊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台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啊呀啊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
二十多年疲于在“辛苦辗转”中“挣命”的“我”,对于这样不讲理的胡话除了“无话可说,还能怎样呢?!当然,这种可悲的“隔膜”决不是闰土、杨二嫂和“我”之间先天就有的,我们本来是很“一气”的,比如这样的话:
“可惜正月就要过去了,闰土须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呢!”
这种“隔膜”,是旧中国特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造成的,是闰土、杨二嫂们在现实生活中饱受阶级压迫、政治统治、经济剥削的深刻反映,鲁迅在《故乡》中所表现的对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的悲哀,正是对造成这种“隔膜”的社会制度的强烈愤恨和尖锐批判。也正因为如此,闰土和杨二嫂的形象才更具有现实主义的强大穿透力。
闰土和杨二嫂无疑是一把剑的双刃,在《故乡》的主题显示上,具有同等的力度。鲁迅将找寻闰土和杨二嫂身上失去的东西的期望,寄托在新一代身上,寄托在新的时代,宏儿、水生乃至杨二嫂的后代,正是走向这个新时代的一代新人。鲁迅热切地希望他们将过上亲密友爱的新生活,并愿意为这一代新人去开辟前人尚朱走过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使成了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