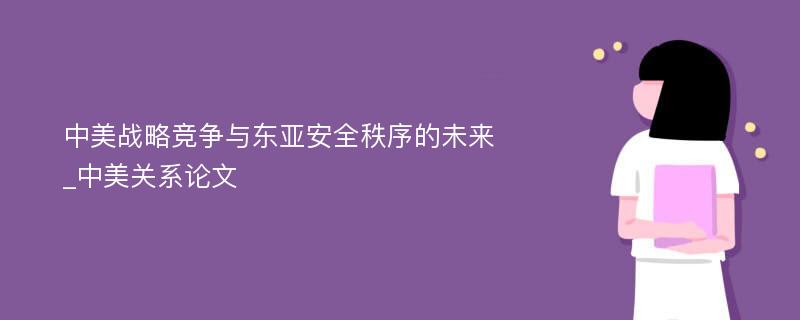
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中美论文,秩序论文,竞争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13-02-21]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3)03-0004-23
2012年是尼克松访华40周年。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冲破23年两国关系的冷战坚冰建立中美战略和解,并最终在1979年1月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40年间,中美关系的发展一直是东亚地区安全秩序调整与变化的核心变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在《论中国》一书中明确指出,“尼克松访华40年给美国外交和东亚政治带来的最大变化,不仅是使中美敌对转向中美携手,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的合作成为了东亚安全的重要基础”。①然而,40年过去了,两国彼此战略视野中的关系定位正在又一次出现历史性变化。这40年间引导中美关系变化和地区安全影响演变的最突出的变量,是两国之间实力对比缩小而出现“权力变更(power shift)”。中美之间的“权力变更”不仅导致了两国各自的政策需求与战略目标的变化,也造就了两国关系所关注的问题领域、侧重的政策手段以及未来的战略期待等都在不断地出现明显变化,逐步累积起了以往40年间中美关系中所难得一见的“结构性紧张(structural tension)”,②推动了两国关系从性质到内容的战略转型。可以肯定的是,中美关系已经演变成了某种“战略竞争关系”。东亚区域安全构造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在亚太地区究竟以什么方式进行和管理彼此之间的战略竞争以及区域内的其他国家究竟如何对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做出选择。
一 中美关系的性质正在发生第三次重大变化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关系从基本性质到彼此关注的问题领域、从互动模式到目标设置都在发生连续不断的调整和变化。自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一直到1991年冷战结束,中美关系是美国外交中的“次要问题”,中美通过战略接近来共同应对苏联的全球战略扩张是两国关系的核心内容。这20年间的中美关系可以清楚地界定为是“共同威胁驱动”的中美关系。在冷战的大背景下,逐步建立中美战略合作,暂时超越中美就政治体制、人权和发展历程等各种问题所导致的差异,是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重要特点。③即便1989年中美关系遭受了重大考验,但老布什政府很快派遣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访问北京,本着现实主义的政策理念稳定了对话关系。
1991年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让中美关系的大背景发生了重大转换。随着苏联这个“共同威胁”的消退,什么是中美关系新的战略纽带?如何重新建立在制度、价值、意识形态和外交风格等各方面都存在着显著差异的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稳定合作,如何求同存异?特别是如何面临越来越具有挑战性的台湾问题?中美双方都不得不面对彼此关系的基础和性质做出再一次调整。1993年上台的克林顿政府面临着“遏制中国”还是“交往中国”的两难。随着1995-1996年台海危机的爆发,两国关系中军事冲突的因素急剧上升,中美双方都开始寻求两国关系新的战略定位。中美关系开始成为一种“非敌非友”的关系,彼此在政治和战略层面都直接把对方视为“另类”,20世纪80年代时被掩盖的两国关系的分歧——人权和政治制度问题迅速上升为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④中美关系也迅速成为了一种“双边议题导向型”的关系: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中美是伙伴关系,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就是不愿意放弃中国市场、不愿意放弃影响中国的战略机会而设计并执行的政策;在人权领域,中美是相互的批评者和攻击者;在台湾问题上,中美更有可能是敌人。由于后冷战时代的美国抛弃了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继续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和支持促成“台独”势力兴起的台湾“民主化”进程,强调所谓美国对台海和平的义务,台湾问题使得中美陷入军事冲突的风险不断上升,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最敏感和最核心的问题。然而,由于两国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实力差距,彼此充其量只是“有限对手”。⑤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恰逢美国发生九一一事件。随后这十年的发展进程使得双方的认知和心态再度出现了重大变化。这十年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军事实力也有了明显的跃升;而美国则陷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对美国经济、金融和财政能力带来重大打击。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尽管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中国的崛起带来了“实力变更”,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在缩小。与此同时,中国发展海军、空军和战略威慑力量的步伐,中国今天媒体中充斥的民族主义情绪、按捺不住的强国意识以及媒体中的“反美主义”,再加上东海与黄海等海上领土争议所产生的持续紧张和对峙,让美国迫切地感觉到需要在安全战略上重新“定义”中国。
2011年11月,美国奥巴马政府宣布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亚太安全战略所出现的又一次重大调整。这一调整的中心内容,不仅是加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和战略存在,自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第一次在亚太地区推行军事扩张主义;更是因为美国经济、贸易对亚太市场越来越大的依赖性,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开始明确转向亚太地区,以保持美国在战略、贸易、市场和社会关系等各个领域的主导地位和战略利益。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强调美国所面临的中国挑战是“前所未有”的,美国要保证在21世纪的亚太领导地位。⑥中美关系开始超越传统的“双边议题导向型”的关系,正在变成越来越具有地缘战略、地缘经济、地缘政治竞争为导向的关系。美国认识、谋划和处理中美关系的重点已经不是放在双边议题上,而是放在了在中国周边的“投资布局”、放在了应对中国崛起的今天有可能出现的战略力量扩张和与美国争夺在亚太的影响力等诸多方面。中美之间虽然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人民币汇率、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仍然存在争议,但在双边议题上中美已经建立了超过65个各种形式、各种层次的对话机制。然而,美国涉华的重大战略关注已经转向了中国国防力量的现代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议以及中国究竟在以什么样的方式扩大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战略的存在,关注中国的崛起和在亚太地区显示和使用力量的方式是否会实质性地侵蚀美国的战略资产,或者一个崛起的中国是否会单方面争取在周边的领土争议问题上实现“中国方案”、推行对周边国家的“强制外交”,从而挑战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声望、利益和霸权。⑦在201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中国议题基本不涉及人权等问题,而更多的是讨论中国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和东亚地区安全话题。希拉里·克林顿于2013年1月30日在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发表演讲时特意强调,如果“中国不能在亚太地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美国将不会欢迎中国崛起”。⑧阿隆·弗里伯格(Aaron Friedberg)认为,中国实力地位的上升、高涨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政治体制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中国对外投送、炫耀和显示力量,中国必然意在和美国争夺在亚洲的主导权,中美“争霸”时代已经开始。⑨
中美关系性质的这一深刻转型不仅典型地体现在美国在亚太“再平衡”的战略举措上,更是生动地表现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美关系新的定义上。2012年10月23日,在美国两党总统大选举行的最后一次电视辩论中,奥巴马非常明确地表示,中国是美国的“对手(adversary)”,也是一个“潜在的合作者(potential cooperator)”。⑩美国担心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动向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性,而中国则担心美国是否在加紧“围堵中国”,并成为中国周边领土与安全争议的“幕后黑手”。(11)中美关系中战略竞争的帷幕已经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地拉开了。如何面对中美关系性质这一深刻的、历史性的变化,应该迅速成为中国政策界和学术界共同努力的长期性研究课题。
二 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定义与预测
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产生是国际体系中权力再分配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安全困境”因素深化的必然产物。(12)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即便如此,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进程以及中国对外安全利益特别是海洋安全利益的扩展,必然带来美国及亚太其他国家的疑虑、担心和不满。中美的战略竞争关系,是美国担心中国挑战美国亚太地区战略利益的产物,更是美国在亚太地区自冷战结束后一贯采取的“美国优先(primacy)”战略的必然结果。1996年美国的《东亚-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就提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心战略目标是防止出现“一个实力特别是军事和战略实力上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2006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称为美国面对的最有潜力的“战略挑战者”,2010年奥巴马政府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则直接把中国列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13)
2011年11月奥巴马政府高调宣布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美国在面对亚太区域新格局所必然采取的加大对华制衡力度、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这一全球经济与战略的“权力场(powerhouse)”中主导地位的新战略。中国在南海和东海领土争议问题上的“强势”态度、在朝核问题上对美关注的“不合作”以及中国国内对于中国崛起的“过分自信”和“急于展示肌肉”的政策趋势,加速了奥巴马政府的战略东移。(14)虽然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走建设和践行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但随着中国“体量”和“质量”的扩大以及中国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决心的上升,中国在处理区域安全紧张关系中的立场当然也越来越趋向于“中国利益”。中美关系演变为战略竞争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权力逻辑的延续,更是“霸权国家”与“崛起国家”关系中难以避免的权力内涵。中美关系开始以地缘经济、地缘战略与地缘政治为导向,是两国关系具有国际体系中“结构性关系”特征的生动体现。
中美双方国内政治所形成的知觉、认知和偏好往往对中美关系中的观念结构和政策互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一系列基于国内政治利益和政治因素所激发起的中美“战略互疑”,同样造成了中美两国在政策和战略层面竞争性一面的显著上升。(15)没有人可以忽视中美之间业已形成的强大的经贸、金融和社会联系。中美双边贸易额在2012年突破了5 000亿美元,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则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2年,中国人民币的海外结算量增加了50%。(16)全球经济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直形成了中美“双引擎模式”。两国继续发展牢固而又深入的双边经济交往与世界合作,不仅事关两国的经济增长,更事关未来全球经济的走向。然而,随着美国越来越多地关注国内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关注自身的“出口增长”和制造业复兴战略,中美经济领域内的竞争性也在不断扩大。美国越来越担心如果在经济竞争力和地区性的经济影响上被中国“超越”,美国保持亚太地区领袖地位和前沿军事存在的能力从长远来说也将难以为继。经济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也在发生“质变”,从传统的两国关系中的“稳定器”,逐步转向既合作、但又冲突和竞争的领域。(17)讨论中美在亚太区域的战略竞争关系,不能脱离两国关系的整体。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必然也是两国关系中的结构因素、国内政治因素、社会因素以及两国在全球经济结构中的市场因素的综合体现。但当前中美关系的总体趋势是,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到了需要调整战略以应对和中国的全面“战略对抗”的时候了。(18)
即便如此,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分析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不能简单参考和引述国际关系中大国对抗的历史经验,也不能单纯地着眼于军事、战略与外交关系,而是应该更多地从两国各自的战略诉求、国内政治限制因素以及东亚地缘政治的结构性特点来分析其战略竞争关系的构造、特点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从两国的战略诉求来看,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对外方针,而美国则是需要承担全球自由主义秩序主导者的角色。从国内政治角度,美国会对中国的崛起充满战略忧虑,对中国走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总是带有根深蒂固的排斥;中国正处在深刻的国内转型进程之中,“转型国家”的内在压力和矛盾常常使得中国缺乏对外交和战略主题深思熟虑的判断,外交行为的“反应性”特点较为突出。但中美双方对于维护和增强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合作方面有着明显的共识。从东亚地缘战略环境来看,美国从二战之后就一直是东亚区域秩序的霸主,美国可以较为容易地调整自己的政策以便利用同盟体系等战略资产全面增强对付中国的战略能力,而中国则长期处于富有偏见和敌意的大国、有领土争议的中小国家以及随着中国崛起对中国疑虑加深的国家包围之中。中国为了自身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发展,努力改善自身周边安全环境、稳定中国主权与领土利益的强烈需求和沉重负担,则是美国所没有的。再加上美国在军事实力、同盟体系、全球力量投送能力、战略威慑能力以及全球快速常规打击能力等诸多方面对中国所保持的绝对优势,中美在东亚战略竞争的基本目标,应该排除美国对中国采取像对待苏联那样的“遏制”政策和中国有可能采取对美全面战略“挑战”两个“极端”。(19)事实上,美国担心中国崛起是否会带来中国的“攻击性”,同样也担心区域内国家与中国的领土、安全争议激化以及同中国的对抗,从而导致区域内破坏稳定、和平与合作的“不确定因素”的上升。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曾明确提出,对美国来说,东亚未来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该地区“究竟是20世纪前半期的欧洲、还是20世纪后半期之后的欧洲”。(20)中美作为彼此都对地区稳定与繁荣负有特殊责任的国家,其战略竞争即便是“结构性”的,仍然难以演变为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对抗(great power rivaling)”,也不可能是争霸进程中的“新冷战(new cold war)”,而只能是客观反映两国实力对比、反映各自变化了的战略利益需求及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东亚安全秩序变革进程的战略竞争关系。
传统意义上的大国战略竞争所呈现的“大国对抗”模式,是一种典型的以战略扩张主义为核心的战略竞争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内容是彼此怀有敌意的大国公开地争夺战略资产和战略资源,以削弱和排斥对手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存在为战略目标。战略资产包括同盟体系、防务与战略伙伴关系、海外军事基地以及对其他国家政府的外交影响力,而战略资源则包括陆地和海洋领土、海上通道的航行自由、商业与政治存在以及经贸与市场的关联度。(21)国际关系理论通常将战略力量扩张、势力范围的圈定以及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选择——如究竟是“现状国家(status quo power)”还是“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作为评判和审定战略竞争关系的对抗度的重要指标。(22)另一历史经验所提供的大国战略竞争模式是“冷战”类型的大国争霸模式。这一模式的典型特征是两个主导型的大国各自建立并带领自己的军事同盟集团进行集团对抗,常常以地缘战略的分裂作为战略竞争的手段,以维护和保障从意识形态到市场交易体系、从大规模的海外军事部署到频频挑起“代理人战争”等方式来实现完全排他性的战略利益。但在今天这个全球化和美国主导的时代,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关系已经难以走向以地缘政治分裂、同盟重组和集团对抗为导向的战略竞争关系。(23)以往国际政治历史中常常看到的那种以“大国敌对”或者“大国争霸”为导向的战略竞争既不符合中美关系中力量对比的现实,也不符合双方在经济和贸易领土内合作共存的共同利益。
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全面加大了在亚太区域方位内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插手中国周边事务,强化军事同盟体系为基础的战略、外交与经济存在,力图“压制中国”和“看管中国”,避免中国崛起“挑战”和“侵蚀”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和影响力。两国今后很可能在亚太一些战略节点问题上形成长期僵持局面,中美彼此都无法将自身的意志和诉求单方面地强加给对方。
中美之间虽然有亚太安全磋商机制,但在亚太区域安全中的立场常常相左。中国不满奥巴马政府宣布美国在南海有“国家利益”、干涉南海事务,而美国则认为中国外交越来越“咄咄逼人(being assertive)”。美国公开要求中国和东盟集体谈判解决南海领土争议,接受东盟旨在约束中国南海行为的“南海行为准则”。美国几乎公开挑战中国在南海的“九段线”,诋毁“九段线”的法理依据,认为中国2012年设立三沙市和三沙警备区的做法,是中国谋求对南海强势扩张。(24)为了更好地在南海争议上发挥美国的作用,奥巴马政府也在努力说服美国国会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朝核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也一贯指责中国立场的“僵硬和不负责”。奥巴马政府前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B.Steinberg)认为,中美两国彼此都开始更愿意表达敌视性的看法和做法,并促成双方“围绕着今后长期的敌对关系来重新调整自己的政策,这是相当危险的”。(25)中国将在东海和黄海的领土争议中采取行动是中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必然举措。中国的立场是“不会主动挑起海上纷争”,但任何国家“不要希望中国拿主权、安全和发展等核心利益做交易”。(26)美国对于中国海上维权的解读,则是中国在利用海监船队等国家政策手段“欺负”周边其他国家,是中国寻求将战略存在扩大到东海和黄海。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情报和信息作战处副参谋长詹姆斯·法内尔(James Fanell)公开指责中国的“野心”是要击沉美国海军、控制西太平洋海域。(27)
第二,由于这些战略节点争议上的僵局长期存在,中美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甚至军事对抗的潜在爆炸点在不断扩大,彼此的威胁认知的层级在不断上升,美国在加紧采取以中国为“假想敌”和未来中美之间在东亚发生军事冲突、战区战争、甚至全面战争为预设场景的战争准备。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到2008年民进党政府下台,台湾问题被普遍认为是中美两国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最直接和最危险的“燃点”。今天,对美国的战略分析家们来说,中美有可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诱因已经从台湾问题扩大到了朝鲜半岛、东海、南海和因为美国对华抵近侦察而可能出现的彼此海上事故性的军事冲突。(28)太空和网络领域目前也是中美竞争的潜在军事冲突领域。近年来,美国国防部给国会提交的中国军力报告对中国军事力量发展和战略意图的评估日趋消极。2012年下半年,有关中国有秘密“地下核长城”的报道开始出现,甚至引起了美国国会议员的激烈反应。(29)2013年1月27日,中美两国同时进行了导弹拦截试验。2013年1月以来,美国媒体连篇累牍地爆料中国对美国主流媒体的网络攻击,也已经引起了美国对中国是否“先发制人”地进行网络战或者网络攻击报复的叫嚣。(30)《华盛顿邮报》2013年2月刊文表示,中国的网络“攻击”使得美国损失了几百亿美元,造成了对美国国家安全的直接损害。(31)
第三,美国为了指挥和调动亚太均势体系朝着“制衡中国”的方向发展,支持和纵容区域内部分国家的“修正主义路线”,将战略利益置于历史观的是非之前,亚太地区传统被压制的不安全因素迅速扩大。这又进一步挑战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导致了区域安全的持续动荡和紧张。
钓鱼岛争端的持续发酵将亚太地区三个大国——美国、中国和日本都推到了风口浪尖。日本极右翼政治人物、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2012年4月17日宣布“购岛”再到前野田政府的“国有化计划”等一系列日本举动的背后,明显存在着美国在怂恿日本“压制”中国的战略意图。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打“日本牌”,是今天中日领土争议严重恶化的重要根源之一。(32)中国是否有后继行动旨在继续从心理上“撕裂”安倍右翼政府在钓鱼岛冲突问题上不承认、不对话的强硬立场?这些疑问加剧了中日在钓鱼岛海域的危机态势,也让国际社会对中日发生即便是擦枪走火式的军事冲突忧心忡忡。美国虽然对中日钓鱼岛领土归属的争议保持中立,但对两国如何解决争议过程中的外交、甚至军事冲突不会保持中立。说服日本等盟国增强军费、发展国防力量来共同“制衡”中国,这既是美国要求盟国分担地区安全责任的需要,也是强化同盟关系的手段。2012年5月公布的“阿米蒂奇-奈报告”非常明确地表示,日本不增加军费,缺乏对中国崛起的制衡意识,造成了美日同盟的再一次“漂移”。(33)
第四,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中国的核心目标是希望在东亚赢得安全、尊重和自身合法的领土与主权利益,而美国则以影响、限制和塑造中国的行为和选择为目标。这两者能否协调和平衡,将决定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
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的重要目标除了所谓应对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之外,还要维持亚太地区继续保持符合美国意愿的稳定、避免不确定性、避免美国被迫卷入因为领土争议而产生的军事冲突。为此,美国难以主动激化与中国的对抗,也不会采取旨在全面遏制中国的战略,仍将继续把重点放在增强前沿军事存在、同盟体系的构建以及美国的外交与战略动员能力建设上,以便为中国未来的选择和战略“设限”。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根本目标是希望“重新塑造中国(reshape China)”:既给中国周围树立强大的“力量屏障”,让中国不要在海上安全和领土争议问题上轻举妄动;又能通过开放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系统,让中国按照“规则”办事,使得中国的做法符合美国的利益,让美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可以继续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受益。
然而,这两者能否保持平衡与协调的迫切挑战,是美国有可能抛弃1996年克林顿政府奉行“对华接触”以来对中国国内政治体制和政治变革的务实看法,重新寻求将改变中国政治道路作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2012年以来,美国媒体连篇累牍地持续报道中国的政治状况,揭露中国官员的家庭财产,爆料中国官场黑幕。这一系列的做法反映了在美国对华加大战略博弈背景下对于影响和引导中国变革新的冲动。美国保守派智库最近明确提议,奥巴马第二任期除了保持“再平衡”攻势之外,需要重新审视美国传统的对华“接触政策”,不再理想地认为接触政策可以逐步改变中国,而是要追求美国能够“立竿见影”看到的好处——中国出现美国所希望的变革。(34)
尽管如此,战略竞争关系并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除了中美战略性竞争之外,中美依然维持和发展着强大的经贸、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内的伙伴关系。中美关系的基调——既竞争、又合作——难以被根本改变,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不断地上升。这突出体现了中美两国“管控争议和危机”更为迫切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中美经贸、社会、文化和外交关系的强大和紧密,可以有助于两国政府和领导人妥善处理战略性竞争,却并不能实质性地遏止和降低战略竞争;(35)然而,战略竞争关系中的误导和误判,有可能给中美关系带来实质性的打击和伤害。
三 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影响东亚安全的基本方式
随着中美关系在尼克松访华40年后出现的这四点新变化,我们要有足够的心态、政策和战略的准备。中美在亚太区域内的未来战略竞争,必将带来亚太安全秩序的新变化。原来学术界通常具有的三种典型性的看法已经过时,未来的亚太安全秩序需要新的解释性理论。
传统解释东亚地区安全有三种典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与美国在亚太的前沿驻军和同盟战略,将会确保美国随时愿意承担对东亚地区的安全责任和义务。亚太地区将会继续在“霸权和平”的战略与力量框架下保持足够的稳定与和平。(36)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亚太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中美“大致的两极格局”。这一两极格局并非是中美的实力均衡,美国当然还是保有对中国绝对的战略力量优势,但是由于中国占据东亚大陆的核心位置和力量的发展,亚太的地区安全秩序可以围绕中美这两个国家的“力量类型”而形成“陆上亚洲”和“海洋亚洲”的大致均衡。换句话来说,中国将更多的是以亚洲大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力量投射区域,而将海洋留给美国和美国所主导的同盟体系来控制。为此,东亚地区安全的秩序就是中美两大国各以大陆和海洋为依托的非均衡的“两极体制”。(37)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今天的亚太地区秩序应该更多地适应亚洲区域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让亚洲内在的市场力量推动的经济区域化趋势与美国在亚太地区不可或缺的安全和安全存在相兼容,将亚太秩序组合和转型成为一个经济、贸易和各种军事与战略要素能够相互补充、但又相互独立的地区安全架构(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这一亚太地区安全架构既包括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和美国的前沿安全义务,又包括各种多边主义的地区安全对话和合作机制,例如“东盟地区论坛(ARF)”、东亚峰会(EAS)、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以及包括亚太21国国防部长、官员和学者参加的“香格里拉对话(SLD)”。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初衷,就是在美国保持地区安全事务的主导性责任与能力的前提下,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带来的合作效应,探讨亚太区域安全合作的制度化道路,以便在美国的战略力量存在之外,寻找更加具有区域特色的应对和解决区域安全争议与冲突的多边机制。(38)这种观点倾向于认为,由于历史、地理和现实的原因,亚洲“是一个危险的地区”,其安全的未来只能依靠多样化的路径,在力量均衡与多边主义的制度建设等手段中建立起系统的地区安全进程。(39)美国超强的战略和军事能力以及中国融入地区性经济与政治多边机制所产生的“压制”与“诱导”的双重效应,将会逐步推动中美两国通过与区域内其他国家的互动、协商来实现东亚安全秩序的“谈判性变革”。(40)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美关系性质的悄然变化,上述的三种观点或者三种理论都不再具有充分的解释力。例如,中日如果因为钓鱼岛问题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那么这不仅有可能把本来不愿意介入的美国“拉下水”,更可能使得整个东亚经济的一体化进程遭受重创。作为亚洲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日之间的钓鱼岛冲突升级或者危机状态迟迟无法得到平息,对美国所在地区的“霸权稳定论”是一个颠覆性的冲击。同时,在南海问题上,美国的积极介入并没有促成中国与东盟有关国家在谈判解决南海领土争议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相反,美国的插手干预助长了菲律宾等国和中国对抗的区域,反而使得今天的南海主权争议更趋复杂化。东亚安全的核心问题还是在中国崛起的现实之下,中美如何谈判形成“各自的战略疆域(strategic boundaries)”,保证双方各自核心、但又有节制的战略利益。(41)近两年来,围绕着“南千岛群岛”、“独岛”、钓鱼岛和南海诸岛发生的领土争议的尖锐化,说明东亚的安全秩序不可能形成“陆地亚洲”和“海洋亚洲”的区别,但新的“战略疆域”的共识并没有得到确立。今天,亚太地区最严峻的领土争议都发生在海上,同样表明海洋权益和海洋战略的碰撞,是当前亚太地区安全秩序主要的不稳定因素。而从领土与主权争议的冲击力来看,发生争议和冲突的这些国家,都是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受益的国家,也是亚太经济区域合作进程中的重要力量。领土争议的恶化反映出“安全”与“经济”依然是当今国际政治中两个各自独立和分立的领域。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并不必然产生安全领域内扩大与深化合作的“溢出效应”。相反,即便亚太区域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已经如此巨大,安全领域内的争议和冲突仍然不会因为经济的相互依存而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和解决。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日本安倍政府不仅11年之后再度显著增加军费,更是发起了“重返东南亚攻势”,把亚太地区变为“压制中国”的重要支柱。(42)
亚太区域安全的核心话题,是中美两国如何共处、共生、共荣,如何在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霸权战略之间找到竞争性的、但却非敌对性的互动模式。只有中美关系稳定,亚太区域安全的大局才会稳定;只有中美关系能够包容各自利益,同时又能管控差异、避免竞争演变成冲突和对抗,亚太安全秩序才能真正重新趋于稳定与持续。而要建立这样一种新的中美关系的互动模式,不仅需要时间,需要摸索,更需要一些标志性的事件来助推“新历史”的产生。目前的朝核问题、南海领土争议和钓鱼岛冲突就是对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从性质到内涵的重大考验。澳大利亚政府2012年1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非常明确地表示,中美两国在亚太区域的战略竞争是区域安全的最大忧患。(43)
未来的东亚安全秩序的核心是稳定和建设性的中美竞争与合作关系,但实现的路径却远非中美两国。包括地区内国家的战略选择在内的一系列问题究竟如何回答,既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演变,又将对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建进程发挥重大作用。
第一个问题是:亚太地区国家到底如何对待中国和美国?
以往东亚国家的“战略性套路”是不选边,现在变成经济与安全的“双轨制”,就是经济上都无法离开中国,在安全上则倒向美国。这既是一种“战略选择”,又是一种“消费行为”。当安全和经济都是公共产品的时候,大多数地区内国家进行这样的选择既反映了东亚的历史,又是为了利益的最大化。问题是这些国家的利益估算、政治选择和战略偏好究竟是什么,这对于未来的中美战略关系将产生重大影响。
在美国宣布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一方面是区域内国家纷纷表示欢迎,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或者防务与安全伙伴关系来对中国崛起采取“两面下注”的战略;另一方面,这些国家认为,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存在,不仅是依靠美国“制衡中国”的需要,也是这些国家在与中国发生安全纠纷和冲突时,它们可以更好地指望美国作为“安全保障者(security guarantor)”的干涉性保护。(4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区域内国家愿意看到中美冲突,或者愿意全心全意地绑到美国战车上与中国为敌。中国实力的上升、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出现和深化以及主权和领土争议所产生的持续紧张,只是显著加强了区域内对美国“制衡中国”的战略依赖,也确实增强了美国作为亚太地区“安全保障者”的政治地位,但并没有根本改变区域内国家同时希望和中国保持友好与合作关系的现实政策,也并不意味着亚太区域内大多数国家就愿意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在中美冲突中“选边”的战略需要。(45)然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毕竟给地区内的国家提供了利用中美战略竞争的外交和战略实利。各国究竟如何审视、判断和应对中美关系的这一新变化,如何计算自己的安全与外交利益,如何做出自身的政策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东亚究竟如何重新面对、容纳和建构包含中美竞争性战略关系在内的新变化。
未来东亚区域安全秩序究竟是稳定、动荡,还是陷入灾难性的冲突,与中美关系的性质和状态存在着直接的联系。然而,不管中美关系多么重要,中美两国都无法按照自身的意志单独来塑造地区秩序,也无法简单地由两国的实力、意志和战略选择来主导东亚区域秩序的演化,更无法单方面推动地区安全朝着自身意愿的方向发展。布热津斯基就曾指出,“东亚对于中国崛起的普遍担心给美国转身亚太提供了台阶”。(46)进入21世纪,中美两国尽管在地区安全的走向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地区安全秩序的未来已经前所未有地同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区域国家的选择和作用联系在了一起。今天,亚太地区已经出现了“两个亚洲”:“经济的亚洲”和“安全的亚洲”。前者要求尽可能地合作和深化经济区域化进程,后者则充满了不安、争议和潜在的对抗。但从长远来看,这“两个亚洲”是不可分离的。(47)“两个亚洲”的存在目前符合东亚多数国家的期待。没有同盟国的支持、美国防务伙伴的配合,没有区域内大多数国家跟着美国走,美国即便有遏制中国的意愿,也缺乏实际有效的、可持续地遏制中国的能力。同样,如果中国想要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避免美国因素的干扰,不仅需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增进中美互信,更需要让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所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得到更多的周边国家的认同、理解和配合。(48)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未来,说到底取决于两国谁更能够为亚太带来稳定、合作与繁荣。
第二个问题是:东亚安全的未来究竟能够建立什么样的新规则、新秩序?中美战略竞争究竟是有利于其他地区安全热点问题的解决,还是将带来地区现有安全利益冲突的恶化?
2012年9月以来中日钓鱼岛领土争议的升级、2013年2月12日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以及南海领土争议僵局的深化,这些事件正在将东亚地区安全秩序拉入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新变局。这一新变局的起因,表面上看是“领土争议”,但核心问题是如何面对二战后的东亚条约体系和冷战后的东亚安全秩序。美国一连串的举动,比如向东海和南海派遣航母、声称要在冲绳进驻F35战机,包括已经实施的“鱼鹰”运输机部署,说到底,只是想要继续“捂住盖子”,避免中日直接军事对抗。然而,钓鱼岛纷争再加上韩日“独岛”争议,二战后美国主导的东亚条约秩序的私利与丑陋已经“捂不住”了。(49)在东亚区域安全的这场变局中,美国是“获益者”,但同样也是“受害者”。美国获益,是因为只要中日之间摩擦不断、中日战略关系紧张,美国在东亚的主导性地位就越稳固。美国就始终能够将日本拴在自己的身边,成为美国保持和推进现有军事同盟体系、前沿驻军和在美国领导下的“霸权稳定”的最重要的帮手。但日本右翼势力配合美国积极“反华”、“制华”,以安倍为代表的保守派否定日本侵略历史的看法,必然给亚洲带来新的争论和对立。如果美国一味在“制华”问题上纵容和迁就日本的右翼势力,只会给亚洲带来新的冲突。(50)只要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利益,区域内的国家就会随之担心中国是否将寻求战略扩张,转而投靠美国以牵制中国的战略需求就越坚定。作为亚太地区秩序的主导者,美国并不乐见东亚国家“一团和气”,甚至“称兄道弟”。南海、东海的领土争议以及朝核问题的僵局,都给美国提供了在战略上牵制、甚至压制中国的战略“抓手”。(51)如果亚洲国家有能力消弭和解决内在的各种争议,东亚就会转向另外一个“变局”,一个有可能真正不再需要美国来当“老大”的格局。这是美国最不想看到的,而事实上今后很长时间内也不可能出现。(52)中美仍然在东亚安全秩序的稳定和发展中存在着无法割舍的共同利益。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自己到底准备怎么办?
面对美国的“战略东移”,我们当然需要发展自己的军事和战略能力,以便尽可能地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特别在目前美国为经济振兴和削减联邦财政赤字正在苦苦挣扎的时候,一个相对衰落的超级大国,很可能对最有希望崛起为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国家采取“预防性军事打击”和外交上恶意排挤等举动。(53)包括国防和军事力量现代化在内的战略能力建设是中国应对美国的战略竞争的重要努力。但一个国家的战略竞争能力并非简单的军事装备和国防能力,着眼于长远的战略设计、规划和执行能力以及立足于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和增强对外影响力的外交能力,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战略能力建设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外交手段的运用上,如何实现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的结合与相互协调,我们面临的自身难题太多。目前中国的周边安全和领土争议对中国外交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对外关系的争议性除了西方心态和政策之外,核心问题是中国自己有没有准备好。今天的中国变了,世界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变了,但是无论从制度到战略、从政策到心态,还是从观念到外交体制,我们的改变还跟不上。安德鲁·斯科贝尔(Andrew Scobell)的评价是“中国走向了全球,但还在原地思考(going global but thinking local)”。(54)说到底,限制中国外交更新和升级的诸多问题是中国目前治理体制的局限性。推动中国战略和外交领域能够尽快跟得上中美关系转型和发展的大趋势,至少我们必须面对今天中国转型的结构性的制度困境,推动中国战略和外交部门管理机制和运作模式的发展,是我们自身必须紧迫解决的问题。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将会实实在在地表现为两国在区域内的影响力之争。然而,中国和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是什么关系?在中国维护地区稳定和自身海洋权益、领土争议问题上,如何实现双边和多边手段的结合?如何面对来自越南、菲律宾等国“狐假虎威”、利用美国因素牵制中国的同时单方面强化在争议领土问题上的主张?中国如何在发展自身军事装备和军事作战能力的时候避免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迎头相撞,出现大规模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拿出新的答案,实现中国外交和安全战略从观念、体制、心态等诸多方面的及时调整和进步。
第四个问题是:美国在亚太“再平衡”的道路上到底会走多远?
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本身充满争议性,也助推了2011年以来东海、南海和黄海局势的动荡。“再平衡”战略无论是基本动机、战略手段的选择还是战略目标的确立,有“后伊拉克战争时代”和“后阿富汗战争时代”美国全球军事战略调整的需要,但“剑指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通过“再平衡”战略,美国给中国传递了明确的信号——对于中国想要利用美国陷入国内经济低迷谋求地区战略势力扩张的道路是行不通的,美国有能力、也有决心阻止中国有可能破坏亚太地区现状和稳定的举动。该战略也给亚太地区的其他盟友传递了明确的信号,那就是美国不会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削弱对亚太地区事务的投入和责任,也不会谋求任何形式的如“中美共治”两极体制。美国仍然是制衡中国崛起、应对亚太权力结构变更进程中最积极、最值得信赖的因素,“只有美国才有能力将不同的国家汇集到一起”。(5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宣布改变对华政策,但通过宣布新的地区安全战略,修正和调整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这就是美国对华关系上的“变轨”——不再以换取中国合作和防范中国政策的不确定作为对华政策的首要战略目标,而是以防范中国的挑战、遏止中国的战略利益扩张和支持东亚国家所谓抵御来自中国的“伤害”作为美国对华政策和东亚政策的首要战略目标。
为了进一步实施“再平衡”战略,美国将继续扩大在东亚的战略与军事优势。美国国防部正在谋划在亚太地区建立海基和陆基的导弹防御系统,这势必给中国有限的战略威慑力带来冲击。中国是否将在增加核导弹的数量和质量上做出回应,中美是否会进入新的军备竞赛,这一系列问题都还远没有答案。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Hugh White)提出,如果在中国的崛起进程中美国并不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并给予中美在地区安全管理中的适当位置,一味将中国视为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只会导致未来亚太地区秩序的灾难。(56)美国过多地依赖军事强势、刻意搅动东亚均势格局进一步向美国倾斜,挑战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也煽动了中国的民族主义。(57)即便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基于同盟关系支持日本,但日本安倍政府继续在钓鱼岛领土争议问题上拒绝与中国对话和承认日中领土争议的事实,也使美国处于非常尴尬和棘手的境地。(58)
四 中美关系与未来的东亚安全秩序
中美关系变成战略竞争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简单地埋怨美国的霸权逻辑对我们正确审视和应对这一关系无益。中美战略竞争虽然给中国保障主权、安全与发展这三大核心利益带来了新的战略压力,但通向未来的主动权依然掌握在中国手中。中国能否尽快做好准备、提升战略规划和政策应对能力,理性而又务实地规划和执行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主动、积极和建设性地塑造东亚安全的新秩序,这对重建中美两国战略互信、在竞争中增进合作、在合作中规范竞争,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是否能主动求变,加速自身观念、心态和体制的转变,正在成为塑造东亚未来安全秩序的关键因素。
首先,中美可以是战略竞争者,但中美并非注定是敌人。在迎接中美战略竞争这一新时代时,中美两国都需要深化这种“非敌”的意识和信念。这是防止中美关系造成东亚地区安全动荡、甚至出现地缘政治分裂的关键。
中美关系在本质上是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关系。这一关系的复杂性不仅仅是“主导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两国国内的竞争性政治、观念和利益因素常常让中美关系的基本性质变得模糊而又富有争议性。中美对彼此的战略动机和意图都存在着显著的疑虑。然而,中美不应该互相为敌。一个崛起的大国以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大国为敌,本身是一种战略错误。而主导性大国如果非要把崛起大国“逼成”敌人,更是时代性的错误。(59)20世纪90年代,中美在台湾和人权问题上进行对立时,中国经常告诫美国,如果美国把中国当成敌人,中国就是美国的敌人;今天,中国人需要问我们自己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把美国当成敌人,美国真的就可能是中国的敌人。问题是,中国需要制造这样的敌人吗?中美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论述,应该成为中国今天对美政策思考的中心话题。这同样也是中美两国建设和践行“新型大国关系”的意义所在。
战略竞争关系的特殊性就在于,中美两国的强力部门(例如军队和情报系统)都会依据“最坏的可能性”来准备各自的军事任务,但这并不等于两国的政府和人民需要敌对。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的社会关系是一致的。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者”关系非常普遍。有利益的竞争,就一定有猜忌和争斗,也一定有相互之间的防范。但如果把“竞争者”都当成敌人,不仅将造成恶性竞争、激化冲突,更有可能让我们自己的路也越走越窄。中美关系变成东亚地区影响力之间的竞争关系,本身是中美变化了的实力和利益的结果。但如果不坚持中美“不是敌人”的信念,这才是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真正可怕之处。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在《解释社会行为》一书中指出,“信念”常常在人类的社会行为中并不那么可靠,这是因为一是信念容易缺乏确定性,二是坚持信念常常要冒风险,但“没有信念的社会行为却更容易招致更大的风险”。(60)今天,中美在东亚一系列海上领土争议问题上的对立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两国同样有堕入直接军事冲突的巨大风险。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认为,东亚存在着出现“海上巴尔干”式的火药桶的危险。(61)
其次,在稳定和推进东亚热点问题的缓和与解决的进程中,中美既有竞争的一面,更有利益共存和互利合作的一面。中美两国能否在竞争的同时,加深两国在塑造和影响地区安全冲突性问题的缓和与解决进程中的相互协调与合作,本身对中美战略竞争关系能否得以积极引导、风险管理、避免误判和提升战略互信,将发挥关键作用。
即便中美关系中存在着越发明显的战略竞争态势,但彼此都愿意从东亚地区稳定、和平与繁荣中获益的现实,同样决定了中美在强化地区稳定、消除朝鲜半岛核扩散、阻止日本右翼政治的极端政策动向等问题上具有重要的合作利益。对于日本未来的战略动向,中美两国有必要加强合作,共同遏制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对东亚安全秩序的挑战。奥巴马政府不同意安倍政府“实行集体自卫权”、要求日本不要对中国飞机发射警告信号等行动,至少说明在阻止钓鱼岛危机升级问题上中美存在共同利益。同时,在东亚安全稳定与合作的进程中,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建设性互动至关重要。因为目前的钓鱼岛和南海争议而否认美国存在的积极意义,或者只是功利性地追求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联美反日”,都是战略上的短视行为。“太平洋足够宽广,容得下中美两国。”(62)落实这一指示的关键,是能够为今后的中美日稳定而又合作性的关系寻找新的基础和路径。简单地把美国视为中国周边各种问题背后的“幕后黑手”的心态,同样只会误导中美战略竞争。因为争议性问题而将美国越来越视为亚太地区“多余存在”的心态只会加深美国对华疑虑,被视为中国想在亚太称霸。(63)而朝核问题的解决,更是离不开中美合作。
最后,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依然还是一场相当程度上极为显著的“非对称性”的竞争。中国不仅将长期处于“被动”和“应付性”的状态,美国在亚太地区广泛的战略存在和战略力量动员能力,将使得美国长期处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反应-再反应”过程中的主动和优势地位。换句话来说,中国未来在守护自身核心利益时所采取的外交和战略推进的力度有多大,就可能在中美没有协商共识的争议点上招致美国同样力度的战略抑制。中美在亚太战略竞争的本质并不取决于彼此的军事力量对比,而是取决于彼此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和战略资源的动员能力。
这是中美之间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也是由美国作为东亚传统的主导性国家在东亚通过长期战略、军事与经济存在纽带所保持的历史、社会和价值纽带所决定的。中国作为亚太地区权力和财富格局中的“后来者”,不可能只是凭借经济影响力的扩大而取代美国的影响力,更无法短期内扭转战略竞争的被动态势和在地区安全结构中依然所处的从属性位置。从二战前、二战时期一直到二战后,数代美国人付出鲜血和生命代价所积攒起来的东亚影响力不可能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在短期内被动摇。正如新加坡资深外交官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所言,未来东西方之间应该融合。长期主导的西方应该给以中国崛起为代表的东方留出位置,但中国如果想要取代美国和西方的优势,恐怕也是幻想。(64)单纯从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出发看待中美力量对比在显著缩小的认识,事实上掩盖了中美战略能力对比依然存在着的巨大差距,只会误导未来的中美关系。从未来很长时间来看,美国在综合实力和战略能力上的对华领先优势难以有实质性的缩小。(65)更为重要的是,“过去20年中美国单极霸权的衰落,并非是伊拉克战争,而是全球范围内更加广泛的权力分化关系所造成的”。(66)即便今天美国面临着财政赤字高涨、联邦政府预算削减的事实,但也并非意味着美国未来的财政能力和国防开支将从此一蹶不振。为此,中国学术界要对中美力量对比保持清醒头脑。如果以同盟国数量作为衡量大国的战略影响力和资源动员力的标准,中美之间更是处于完全不对等的地位。美国今天在全球拥有64个同盟国,而中国只有1个。
另一方面,中国学术界更需要破除在战略竞争中“唯实力论”的迷思。未来决定中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地位的主要因素,除了力量对比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战略规划、执行和运作能力,即中国在崛起进程中应对不同的问题和挑战是否能有效化解和合理处置的能力,更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断更新自我体制、观念和政策有效性的内在更新和进步的能力。任何国家再强大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倘若无法妥善与合理地解决强大过程中遭遇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中国则无法真正实现强大。因此,相信“只要中国强大了,各种国际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要树立有限的目标,不能急于一味按照自身意愿来推进主权和领土争议以及海洋权益问题上的解决方案,更不能将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简单化为僵硬的教条主义。相反,让中美关系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注重斗争与妥协相结合、“谋势”与“谋利”相结合,中国才能真正在东亚区域安全的未来格局中赢得更多的主动。例如,中国军事装备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中国武器装备的研发、生产和制造能力仍有着漫长的道路要走。(67)与此同时,东亚地区国家都希望看到中美这两大国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可以给地区内的中小国家“腾留”出重要的战略空间,让它们能够成为中美地缘战略竞争时都不得不去“拉拢”的伙伴,有利于地区内的这些中小国家从大国那里获得更多的尊重、援助和外交资源。但地区内的大多数国家仍然期待中美合作,期待中美关系有利于地区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如果中美出现直接的军事冲突或者地缘政治的分裂,不仅将严重打击地区内的经济发展进程,更将让大多数地区内国家不得不“选边站”,这并不符合它们的实际利益。面对这一东亚区域政治的现实,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必须兼顾地区内多数国家的利益需求,必须能继续有利于东亚地区各国向往稳定、繁荣和发展的内在愿望。任何旨在为了“战胜对手”而设定的战略,必定将加剧地区安全局势的严重对立,从而最终失去区域内多数国家的支持。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Henry Kissinger,On China,New York and London:Penguin Books,2012,p.5.
②Michael Evans,"Power and Paradox:Asian Geopolitic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Orbis,Vol.55,No.1,2011,pp.85-113; David M.Lampton,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Might,Money,and Mind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
③Warren I.Cohen,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Fourth Edi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chapter 8.
④对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性质、看法和处理机制转变的深度分析,请参见Harry Harding,A Fragile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2。
⑤Jianwei Wang,Limited Adversaries:Post-Cold War Sino-American Mutual Image,New York and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⑥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November 2011,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wpisre=obinsite.
⑦Zhu Feng,"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ing toward Asia and Sino-U.S.Relations," i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Review 2012,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2012,pp.18-37.
⑧Hillary R.Clinton,"Remarks on American Leadership,"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January 31,2013.
⑨Aaron L.Friedberg,A Contest for Supremacy:China,America,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2012.
⑩James Wong,"Obama Reveals His Warning o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24,2012.
(11)有关近年来中美两国对各自政策与战略意图的深入分析,请参见Andrew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2; David Shambaugh,ed.,The Tangled Titan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New York:Ra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2012; Michael D.Swaine,America's Challenge:Engaging a Rising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Washington,D.C.: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1。
(12)有关中美关系是国际体系中难以避免的结构性关系的论述,请参见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Press,2001; Thomas J.Christcnsen,"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4,2001,pp.1-23。
(13)有关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安全战略报告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内容,请参见http://www.defense.mil。
(14)有关对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和中国政策的深度观察,请参见Jeff Bader,Obama and China's Rise:An Insider's Account to America's Asia Strategy,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2012。
(15)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US-China Relations and Strategic Distrust," The Brookings Briefing Series,February 25,2012.
(16)Lingling Wei,"ICBC Picked as Yuan-Clearing Bank in Singapore," Wall Street Journal,February 8,2012.
(17)目前,美国学术界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即便是中国的经济崛起,也在改变全球经济秩序和全球经济治理的传统制度性安排。美国必须重新思考自己应对中国冲击的新的货币、金融和贸易体制。参见Michael Pettis,The Great Rebalancing:Trade,Conflict,and the Perilous Road Ahead for the World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
(18)Lyle J.Morris,"Incompatible Partnership:The Role of Identity and Self-Image in the Sino-U.S.Relations," Asian Policy,No.13,2012,pp.133-165.
(19)Edward Luce,"Lunch with Zbigniew Brzezinski:The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Explains Why He's Worried about Obama's Approach to China," Financial Times,January 14,2012; Paul R.Gregory,"Know Thine Enemy:China and Obama's Defense Cuts," The Forbes,January 8,2012.
(20)Zbigniew Brzezinski,The Choice:Global Domination or Global Leadership,New York:Basic Books,2004,p.107.
(21)对这一类型的大国对抗的经典论述,请参见Niall Ferguson,The War of the World:Twentieth-Century Conflict and the Descent of the West,New York and London:Penguin Books,2006,Part I:"Great Train Clash"。
(22)T.V.Paul and John A.Hal,eds.,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9-40.
(23)对于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中美战略互动关系的“乐观现实主义”的解释,请参见Robert S.Ross and Zhu Feng,Chinas Ascent,Power,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
(24)Oriana Mastro,"Sanshan Garrison:China's Deliberate Escal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 Bulletin 5,The 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September 2012.
(25)James B.Steinberg,"2012—A Watershed Year for East Asia?" Asian Policy,No.14,2012,p.25.
(26)《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载《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
(27)David Wroe and Daniel Flitton,"China's Domestic Problems a Recipe for Regional Disaster," Sydney Morning Herald,February 6,2013.
(28)James Dobbins,"War with China," The Survival,Vol.54,No.4,2012,pp.7-24; James Dobbins,et al.,Conflict with China:Prospects,Consequences,and Strategies for Deterrence,Santa Monica:RAND Corporation,2011.
(29)Keith Bradsher,"China Is Said to Be Bolstering Missile Capabilities," 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24,2012.
(30)Lolita C.Baldor,"U.S.Weighs Tougher Action over China Cyber-Attacks," AP,February 1,2013.
(31)Ellen Nakashima,"U.S.Said to Be Target of Massive Cyber-Espionage Campaign,"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11,2013.
(32)John V.Walsh,"US Goads Japan into China Confrontation," The Asia Times online,February 6,2013,http://www.atimes.com/atimes/Japan/OB06Dh01.html.
(33)Richard L.Armitage and Joseph S.Nye,US-Japan Alliance:Anchor of the Stability in Asia,Washington,D.C.:CSIS,August 15,2012.
(34)Gary Schmitt and Dan Blumenthal,"Rethinking Our China Strategy," Las Angeles Times,January 27,2013.
(35)有关将目前东亚局势与1914年一战前夕欧洲局势的比较研究,请参见Charles Emmerson,"Why 2013 Eerily Looks like the World of 1913,on the Cusp of the Great War," Foreign Policy,January 4,2013。
(36)G.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undono,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Asia-Pacific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 Thomas J.Christensen,"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4,2001,pp.1-23.
(37)Robert S.Ross,"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4,1999,pp.31-56.
(38)Richard Rosencrance and Gu Guoliang,eds.,Power and Restraint:A Shared Vision for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9; Stephen Hoadley and Jurgen Ruland,eds.,Asian Security Reassessed,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2006; Muthia Alagappa,ed.,Asian Security Order: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39)Muthia Alagappa,ed.,4sian Security Order: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Introduction.
(40)Evelyn Goh,"The US-China Relations and Asia-Pacific Security:Negotiating Change," Asian Security,Vol.1,No.3,2005,pp.216-244.
(41)Robert S.Ross,"The Rise of Chinese Power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al Security Order," Orbis,2010,pp.525-545.
(42)Richard J.Heydarian,"Japan Pivots South,with Eye on China," The Asia Times online,January 26,2013,http://www.atimes.com/atimes/Japan/OA26Dh01.html.
(43)2013年1月25日,澳大利亚总理朱莉娅·吉拉德发表《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中美关系的战略紧张和竞争已经成为影响亚太地区安全局势的最重要因素。有关该报告的具体内容,请参见Australian Government,Strong and Secure:A Strategy for Australia's National Security,January 25,2013,http://218.249.165.35/download/36214149/48650536/2/pdf/169/79/1359074350249_335/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44)Ramesh Thakur,"Turning China into an Enemy," The Japan Times,February 7,2013.
(45)"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U.S.Strategic Rebalancing," Asian Policy,No.15,2013,pp.1-44
(46)Zbigniew Brzezinski,"Balancing the East,Upgrading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Vol.91,Issue 1,2012,p.31.
(47)Evan A.Feigenbaum and Robert A.Manning,"A Tale of Two Asias," Foreign Policy Blogging,December 4,2012.
(48)习近平同志于2013年1月29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会议上指出,“别的国家不要指望中国拿核心利益做交易”。http://www.npopss-cn.gov.cn/n/2013/0130/c219468-20370274.html。
(49)Takashi Yokota and Kirk Spitzer,"Tokyo's Missing Muscle:How Japan's Politics Derail Its Military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October 17,2012.
(50)Roger Pulvers,"Abe's 'Unpredictable Past' Runs Counter to His People's Remorse over Wars," The Japan Times,February 10,2013.
(51)"China Must Stop Threats in Maritime Disputes,U.S.Says," Korea Herald,February 7,2013.
(52)例如,中日之间竞争,同样是一种“结构性关系”。例如,中日历史问题争议的本质是两国不同的“近代史认同”:中国人记住的是屈辱,而日本大多数人记住的是“荣耀”。而中日两国的这种认同对立比安全困境更难弥合,参见John Dower,Ways of Forgetting,Ways of Remembering:Japan in the Modern World,London:The New Press,2012。
(53)Jack S.Levy,"Declining Power and the Preventive Motive for War," World Politics,Vol.40,No.1,1987,pp.82-107.
(54)Sumit Ganguly,Andrw Scobell and Joseph Chinyong Liow,eds.,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Asian Security Studies,London:Routledge,2010,p.13.
(55)Hillary R.Clinton,"Remarks on American Leadership,"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January 31,2013.
(56)Hugh White,The China Choice:Why America Should Share Power,Collingwood:Black Inc Books,2012,p.5.
(57)Robert S.Ross,"The Problem with the Pivot:Obama's New Asia Policy Is Unnecessary and Counterproductive," Foreign Affairs,Vol.91,No.6,2012,pp.70-82.
(58)Julian E.Barnes,"China-Japan Dispute Puts U.S.in Tricky Spo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February 5,2013.
(59)Joseph S.Nye,Jr.,"Work with China,Don't Contain It," http://www.hks.harvard.edu/fs/jnye/fullbio.html.
(60)Jon Elster,Explaining Social Behavior:More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25.
(61)Kevin Rudd,"A Maritime Balkans of the 21st Century?" Foreign Policy,January 30,2013.
(62)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20214/161111376013.shtml.
(63)Timothy R.Heath,"What Does China Want? Discerning the PRC's National Strategy," Asian Security,Vol.8,No.1,2012,p.69.
(64)Kishore Mahbubani,The Great Convergence:Asia,the West,and the Logic of One World,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3.
(65)Michael Beckley,"China's Century? Why America's Edge Will End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6,No.3,2011/2012,pp.41-78.
(66)Fareed Zakaria,The Post-American World,New York:W.W.Norton,2008,p.43.
(67)《陈虎点兵:中国军工行业面临的三大难题》,新华网专稿,2013年2月8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3-02/08/c_124337392.htm。
标签:中美关系论文; 军事论文;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奥巴马访华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美国领土论文; 中美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奥巴马论文; 同盟论文; 中美集团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