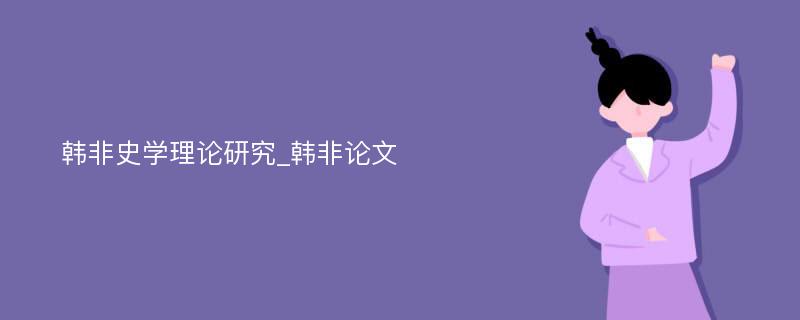
韩非史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韩非的史论既丰富又分散,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从变易史观出发,认为“古今异俗,新故异备”,提出了“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四阶段历史分期说;二他“观往者得失之变”,围绕着“抱法”、“处势”、“用术”总结了前人治国的经验教训;三在人物评价方面,他斥桀、纣为暴君,并揭示其国破身亡的具体原因;对尧、舜、齐桓公、管仲、孔子、皆作两面观,既肯定其才智、功业,又指出其过失与不足;盛赞前辈法家商鞅的变法及其成就,同时又批评他“无术以知奸”,其法也“未尽善也”。
韩非是思想家,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但“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章学诚语),和诸子一样,韩非也惯于谈古论今,引史论政,因而《韩非子》中有很大史论成分。笔者对韩非史论的内容、形式、特点及其历史观作了初步研究,今不揣谫陋写出来,以就教于史界同仁,并望能对韩非乃至整个先秦诸子史论给予更大关注,以便把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韩非的史论散见于《韩非子》各篇。史论的内容很宽泛,既有对具体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述,也有对某些历史现象(问题)的宏观考察、理论总结;既有关于政治得失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评议,也有关于思想学术的批判总结。因此,对韩非史论的内容只能作些概要介绍。
一、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总结
对“古今之变”问题,先秦诸子已有比较自觉的意识,提出了各种的历史分期说。如《礼记·礼运》篇的“大同之世”与“小康之世”说、《庄子》的“至德之世”与“大乱之世”说、《孟子》的“一治一乱”说,《商君书》的“上古”、“中世”、“下世”三世说。韩非是先秦诸子中的后起之秀,他的考察似乎更细致、更深入,因而提出了“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四阶段历史分期说,《韩非子·五蠹》篇(以下引文凡出自《韩非子》者,只标注篇名)曰: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
韩非的论述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认为上古时期人少兽多,人们过着采集渔猎、茹毛饮血的生活,是符合原始社会的实际情况的。把“构木为巢”和“钻燧取火”归功于有巢氏和燧人氏这两位“圣人”显然是错误的,但“圣人”毕竟是人而不是神,这就等于历史是人创造的,从而排除了宗教迷信的因素,在国家起源问题上,虽然没有从人类社会的内部矛盾中去探寻“王”产生的原因,但指出由于有巢氏、燧人氏功德卓著,“民悦之,使王天下”的这种猜想与原始民主制是相吻合的。
韩非的历史分期很明确,把有巢氏、燧人氏时代称作“上古之世”,尧、舜时代为“中古之世”,夏、商、西周为“近古之世”,他生活的“当今之世”,(春秋战国)这样前后就经历了四个阶段。有分期就必然有分期的依据。韩非意识到历史在变,而且发现“古今异俗,新故异备”。“俗”即社会习俗,“备”则是指以政治措施为主要内容的治国之道。韩非就是从这两个方面考察古今之变,并进行历史分期的。他认为古时候人口少而财有余,所以大家“相亲”而不争。当时民风惇厚,“寡事而备简”,当天子的也没什么特权,因而“有揖让而传天下者”。后来人口渐多,社会财富则越来越少。“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与此同时,社会内部的分化也在加剧,君主、贵族和各级官吏的权势愈来愈重,于是就出现了权利之争,起初人们主要是“斗智”,相互欺诈,相互戒备,后来发展为“斗力”,“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经过这番纵向考察和前后对比,韩非总结道:“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八说》、《五蠹》)。
韩非的历史分期并不十分科学,他对各个历史阶段的特征概括得也未必准确、全面,但比较而言,在先秦诸子中是最系统、最详细的,足以代表先秦诸子关于历史分期的最高水平。不过,称韩非是第一个进行历史分期的则是过誉之辞,因为先于韩非而对历史进行阶段划分的不乏其人。
二、“观往者得失之变”,总结治国的经验教训
韩非是韩国宗室成员,生当战国乱世,面对韩国日益衰败的局面,试图从历史中去寻找一条富国强兵之道。据司马迁讲韩非的著作是在“观往者得失之变”的基础上写成的,那么他究竟从历史上总结了哪些治国的经验教训呢?
首先,韩非认为“治民无常,唯法为治。”(《心度》)“法”就是政策法令,是治国牧民的依据。“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六反》)从历史上看,“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管仲为相,严明赏罚,厉行改革,结果齐国首成霸业,“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楚庄王任孙叔敖为令尹,改革法制,整顿军队,楚国也称雄一时,“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可是,等齐桓公、楚庄王死后,群臣官吏“皆释国法而私其外”,于是“其国乱弱矣”(《有度》)。到战国时期,“当魏之方明《立辟》、从宪令行之时,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天下,威行四邻;及法慢,妄予,而国日削矣,当赵之方明《国律》、从大军之时,人众兵强,辟地齐、燕;及《国律》慢,用者弱,而国日削矣。当燕之方明《奉法》、审官断之时,东县齐国,南尽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断不用,左右交争,论从其下,则兵弱而地削,国制于邻敌矣。故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到战国后期,七雄并争演变成了秦独强而六国弱的局面,韩非认为关键就在于秦明于法而六国慢于法。“彼法明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忠劝邪止,而地广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饰邪》)韩非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告诫人们:“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外储说右下》)如何以法治国,他谈了几点原则。譬如,制订法律要循天顺人,要因时制宜,而且内容要详明,要“布之于百姓”。执法者要公正无私,“有赏罚而无喜怒”(《用人》),“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大体》)韩非特别强调:“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楚廷理以“茅门之法”绳太子,晋文公不避亲贵斩颠颉,对这类行为韩非都大加赞赏。鉴于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韩非主张厚赏重罚。他赞成“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并引用商鞅的话解释说:“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内储说上》)不过,在强调明法治国,轻罪重罚的同时,韩非也反对“妄杀”。他认为“赏无功之人,罚不辜之民,非所谓明也”(《说疑》),并警告说:“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饰邪》)
韩非认为明主治国不仅要“抱法”,且要“处势”。“势者,胜众之资也”(《八经》)。对于君主来说,王位和权势是至关重要的。“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功名》)因此,“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难三》)君主的权势主要体现在赏与罚上,有时韩非又称之为“德”与“刑”,或简称“二柄”。为人君者必须牢牢抓住这两种权柄,“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如果“君人者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历史上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譬如,“田常上请爵禄而行之群世”,这就等于篡夺了齐简公的庆赏大权,结果“简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简公见弑”。宋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司城子罕对宋桓侯讲:奖赏是民众所喜欢的,请君主自己去施行;刑杀是民众所憎恶的,那就让我来掌管吧,“于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二柄失其一即有弑劫之祸,“兼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则未尝有也。”(《二柄》)
在韩非的政治学说中,法、术、势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所谓“术”,即君主驾御群臣的方法和手段。关于“术”的重要作用,韩非曾形象地比喻说:“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外储说右下》)对君主来说,用不用术,善不善于用术,情况大不一样。“君无术则弊于上”(《定法》),“主用术,则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和氏》)譬如,阳虎是有名的乱臣,“逐于鲁,疑于齐,走而之赵,赵简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窃人国政,何故相也?”简主曰:‘阳虎务取之,我务守之。’遂执术而御之。阳虎不敢为非,以善事简主,兴主之强,几至于霸也。”(《外储说左下》)这是君主执术御臣而建功立业的典型事例。不过,反面的教训也不少。譬如,“淖齿之用齐也,擢闵王之筋;李兑之用赵也,饿杀主父。”韩非认为齐闵王和赵主父的失误就在于“不操术”,防奸无术,“故身死为戳,而为天下笑。”(《外储说右下》)韩非很喜欢谈论“术”,仅《内储说上》就列举了七种御臣统治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每谈一术,韩非都连类比事,举若干史例详加说明。韩非所谈的帝王统治术很是复杂,但其中最主要的是用人术和防奸止乱术。
韩非对用人问题特别重视,认为:“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八说》)他指出如何择臣用人:“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有度》)明君不自举臣,臣相进也;不自贤,功自徇也。论之于任,试之于事,课之于功。故群臣公政而无私,不隐贤,不进不肖。”(《难三》)由于韩非主张以法择臣量功授官,所以他强烈反对“尚贤”学说。在他看来评价一个人贤与不贤往往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而君主心目中的贤人未必真的是贤能之辈。他举例说:“晋灵侯说参无恤,燕哙贤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贤不必贤也。”(《难四》)还有,“(鲁)哀公不知选贤,选其心之所谓贤,故三子(指孟孙、季孙、叔孙三人——引者)得任事。”(《难三》)由此看来“尚贤”是靠不住的,最好的办法还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定法》)这样,君安于上,臣劳于下,国家井然有序。
防奸止乱是韩非探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好利的,君臣、夫妻、父子之间都有一层利害关系,“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备内》)因此,君主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不为奸不作乱上,而是应该时时提防奸臣弑劫和宫闱之祸。韩非介绍了历史上大量奸邪行为,以及奸邪的活动规律和君主的种种失误。在《说疑》篇中把奸邪的行为归纳为“五奸”:“为人臣者,有侈用财货赂以取誉者,有务庆赏赐予以移众者,有务朋党徇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务解免赦罪狱以事威者,有务奉下直曲、怪言、伟服、瑰称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圣主之所禁也。”如果当疑而不疑,该禁而不禁,那么轻则君主被蒙蔽,重则被篡位。在《主道》篇中指出:“人主有五壅:臣闭其主曰壅;臣制财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义曰壅;臣得树人曰壅。臣闭其主观主失位;臣制财利则主失德;臣擅行令则主失制;臣得行义则主失明;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在《八奸》篇中则分析了奸臣篡权的八种手段:一曰在同床,即人臣贿通君后宫妃妾使之相机惑主;二曰在旁,即人臣通过君主的亲信侍从迷惑其主;三曰父兄,即人臣贿赂笼络君主的伯叔、兄弟及朝廷重臣,使其扰乱君主;四曰养殃,即人臣导君于奢,惑乱其心,以谋私利;五曰民萌,即人臣散公财或行小惠以收买人心而成其私欲;六曰流行,即人臣使能言善辩之士,用浮夸而流行的利害之词去引诱、恐吓或损害君主;七曰威强,即人臣养剑客死士,以恐怖手段挟迫群臣百姓而行其私;八曰四方,即人臣交大国,借大国之威诱迫或挟制自己的君主。“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奸,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不过,对君主来说威胁最大防不胜防的还是祸起萧墙,因此韩非又指出“备内”问题。《备内》篇中说:“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兑傅赵王而饿主父。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优施傅丽姬杀申生而立奚齐。”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日月晕围于外,其贼在内,备其所憎,祸在所爱。”
韩非还总结了治国的经验教训。如在《十过》篇中把历史上许多君臣的过失分为十大类:“一曰,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二曰,顾小利,则大利之残也。三曰,行僻自用,无礼诸侯,则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务听治而好五音,则穷身之事也。五曰,贪愎喜利,则灭国杀身之本也。六曰,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七曰,离内远游而忽于谏士,则危身之道也。八曰,过而不听于忠臣,而独行其意,则灭高名,为人笑之始也。九曰,内不量力,外恃诸侯,则削国之患也。十曰,国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势也。”对每一种过错韩非都用历史上有关君主大臣因这“十过”而铸成“穷身”、“亡国”、“绝世”之祸而加以说明。《亡征》篇中韩非又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对历史上许多政权四十七种亡国征兆进行了总结。
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韩非子》中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包括君主后妃,文武臣僚、隐士游侠、学者策士、名医巧匠、布衣百姓等多达六百人左右,可谓形形色色,应有尽有。韩非对这些人物的评价,重点是昏君佞臣、明主贤佐和学者隐士。现从中选择几组较有代表性的人物评价介绍如下:
1、关于尧舜的评价
尧舜是韩非着墨较多的两位历史人物,《韩非子》中有二十余篇谈到尧舜,评价比较分散,角度也各不相同,归纳起来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古代圣王,是人君楷模。他称颂“尧舜之贤”、之“智”、之“德”。如在《安危》篇中说:“尧无胶漆之约于当世而道行,舜无置锥之地于后世而德结。能立道于往古,而垂德于万世者这谓明主。”《难势》篇中把君王分为上中下三等,称尧、舜乃“千世而一出”的圣王。王良是古代著名的御马能手,韩非说:“夫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在《难三》篇中甚至称:“夫尧之贤,六王之冠也。”韩非对尧、舜如此大加赞扬,一因尧舜生活比较俭朴。他说:“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十过》)又说:“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五蠹》);二是尧、舜利百姓,得人心,于是“众人助之以力,近者结之以成,远者誉之以名,尊者载之以势。……此尧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功名》)值得注意的是,韩非常常用法家思想改铸尧、舜的形象,极力把他们描绘成奉法治国的古圣先王。为了强调法治,《守道》篇曾宣称:“托天下于尧之法,则贞士不失分,奸人不侥幸。”尧明于不失奸,故天下无邪。”《饰邪》篇中又称赞舜和禹奉法办事。“昔者舜使吏决鸿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
其次,关于尧舜禅让问题。儒、墨两家都好谈尧、舜禅让,并视为佳话。韩非则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肯定有尧舜禅让这回事,但强调尧舜“轻辞天子,非高也。”《五蠹》篇说:在尧舜禹时代,天子的权势还很薄,生活十分俭朴,而且还不脱离劳动。“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二是怀疑甚至否认有尧舜禅让这问事。在《忠孝》篇中称:“舜以贤取君之国,而汤、武以放弑其君,此皆以贤而危主者也。”在《说疑》篇,干脆否定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再次,关于尧舜的道德问题。儒家尚德治,对尧、舜的道德修养推崇备至。对此,庄子颇不以为然,大骂:“尧不慈,舜不孝”(《庄子·盗跖》)。韩非沿着庄子的思路作了进一步阐发。照儒家的说法,尧是圣明的君主,而舜是德化的楷模。尧在位的时候,历出之农常闹田界纠纷,“舜往耕焉,期年,圳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韩非问道:“方此时也,尧安在?”并认为:“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也。今耕渔不争,陶器不窳,舜又何德化?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难一》)韩非运用二难式推理,诘难圣尧在位而舜德化的矛盾说法,很有说服力。《忠孝》篇指出:“所谓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按照这个标准去衡量舜,“舜逼尧”,自然算不上忠臣;“瞽瞍为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而杀之。”“舜出则臣其君,人则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这显然是不忠不孝之徒,有什么好称誉的?
由上可知,韩非对尧舜的评价相当复杂,但总起来看褒多于贬,肯定多于否定。对尧舜的治国才能和成就评价甚高,尤其称赞其以法治国,以刑杀立威,但对尧舜尤其是舜的道德颇有微辞,这是韩非反对德治的政治观念在人物评价中的具体反映。
2、关于桀、纣的评价
如果说尧舜是“千世而一出”的圣明君主,那么桀、纣便是“千世而一出”的稀世暴君。韩非把桀、纣当作“悖乱暗惑之主”的典型,对其种种昏乱残暴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批评,同时也揭示了他们亡国灭身的原因所在。
其一、生活奢侈,荒淫无道,桀、纣均嗜酒。《说林上》说:“桀以醉亡天下”,足见其嗜酒的程度及其危害。纣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喻老》),而且还“为长夜之饮,欢以失日,问其左右,尽不知也。”(《说林上》)桀、纣的荒淫绝不止贪酒一项,纣就曾以象牙为著,又好“靡靡之乐”(《十过》)。如此荒淫,岂有不亡国之理?
其二,残虐百姓,无礼诸侯。“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为炮烙以伤民性。”(《难势》)轻民力,设酷刑,滥杀无辜。《安危》篇批评夏桀“诛于无罪,使伛以天性剖背”。《难一》篇指责商纣“斩涉者之胫也”。桀、纣不仅残虐百姓,且无礼诸侯,于是天下叛之。《十过》篇曰:“昔者桀为有戎之会而有缗叛之,纣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由无礼也。”
其三,是非不分,用人不当。桀、纣时,贤能敢谏之士往往身遭不测,而奸邪面谀之徒受宠信,“桀,天子也,而无是非:赏于无功,使谗谀以诈为贵”(《安危》),“关龙逄说桀而伤其四肢”(《人主》),“文主说纣而纣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韩非认为这些“皆世之仁贤忠良有道术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乱暗惑之主而死。”(《难言》)正是由于桀、纣是非颠倒,忠奸不分,所以才使得侯侈、崇侯虎和费仲这些“亡国之臣”倍受信用,祸国殃民。韩非愤怒地指出:“商辛用费仲而灭”(《难四》)。
因有“桀、纣暴乱”,所以就有“汤、武征伐”。对这一问题,韩非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既反对暴政,又强调君臣名分。从前者出发,他常常称赞“桀、纣作乱,汤、武夺之”(《难二》),并从民心向背来加以解释。他说:“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夺君者,以得相踦也。故非其分而取者,众之所夺也;辞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岷山之女,纣求比干之心,而天下离;汤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内服。”(《难四》)不仅肯定了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的合理性,而且把这一兴一亡视为“民之所夺”、“民之所予”。这无疑是非常卓越的史识。前人总以为法家尤其是韩非“刻薄寡恩”。其实,韩非固然是君主专制论者,但在“尊君”的同时也强烈地反对暴政。但是“汤放桀,武王伐纣”毕竟是“人臣弑其君”的行为,“臣事君”乃“天下之常道”,故而从君臣名分观念出发,韩非又主张“毋誉汤、武之伐”(《忠孝》)。
3、关于齐桓公、管仲的评价
韩非评人议事,重点是在春秋战国部分。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称雄中原数十年,管仲是早期法家代表人物,且佐桓公以成霸业。因此,韩非对这二位杰出的政治家特别关注,评价较多。
《韩非子》中屡屡称赞齐桓公霸业之盛,把他誉为“五霸之首”、“五霸之冠”。《有度》篇称:“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十过》篇说:“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桓公所以能成就如此辉煌的业绩,《韩非子》认为:
首先是齐桓公和管仲以法治国的结果。韩非认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管仲是“法术之士”,“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奸劫弑臣》)。齐桓公以他为相,变法图强,结果齐国大治,终于成就了一代霸业。管仲是如何以法治国的,《内储说上》介绍了管仲“断死人”的事:“齐国好厚葬,布帛尽于衣衾,材木尽于棺椁。桓公患之。”管仲建议以法令的形式向国人宣布:“棺椁过度者戳其尸,罪夫当丧者。”这是借助刑罚移风易俗的例子。《外储说左下》谈到齐桓公选官之事:“桓公谓管仲曰:‘官少而索者众,寡人忧之。’管仲曰:‘君无听左右之请,因能受禄,录功而与官,则莫敢索官。君何患焉’?”这是主张以法择臣,量功授官,反对私人请托。
君明臣贤,是齐桓公建功立业的另一重要原因。晋平公曾经向臣下问桓公称霸究竟是君之力还是臣之力,叔向认为是“臣之力”,师旷认为是“君之力”。韩非则认为:“叔向、师旷之对,皆偏辞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美之大者也,非专君之力也,又非专臣之力也。”不仅齐国的霸业如此,“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于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难二》)。显然,韩非的看法比较客观、全面。桓公即位以前,齐国相当衰乱。当他战胜公子纠夺取王位之后,选贤任能,励精图治。管仲本是公子纠的谋士,与桓公又有“射钩之怨”,但“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钩之怨”(《难三》)。对此,韩非大为钦佩。正是由于齐桓公心胸开阔,信用贤能,所以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贤能之士。据《外储说左下》篇讲:“桓公问置吏于管仲,管仲曰:‘辩察于辞,清洁于货,习人情,夷吾不如弦商,请立以为大理,登降肃让,以明礼待宾,臣不如隰朋,请立以为大行。垦草仞邑,辟地生粟,臣不如宁戚,请以为大田。三军既成陈,使士视死如归,臣不如公子成父,请以为大司马。犯颜极谏,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谏臣。治齐,此五子足矣;将欲霸王,夷吾在此。’”齐桓公知人善用,还很注意听言纳谏。有一次桓公微服私访,见“人有年老而自养者,桓公问其故。对曰:‘臣有子三人,家贫无以妻之,佣未反。’桓公归,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积有腐弃之财,则人饥饿;宫中有怨女,则民无妻。’桓公曰:‘善。’乃论宫中有妇人而嫁之。下令于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于是齐国“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外储说右下》)。总之,在韩非看来齐桓公是明主,管仲等人是贤臣,君明臣下,上下协力,齐国的霸业就是他们君臣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过,在“霸王之佐”中管仲最为突出,所以韩非常常称赞说:“桓公得管仲,立为五霸主。”(《奸劫弑臣》)
韩非对桓公、管仲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既看到他们的功业,也指出他们的缺陷。他对管仲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泰侈逼上”。据《外储说左下》讲:“管仲相齐,曰:‘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于高、国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为仲父”。“管仲父出,朱盖青衣,置鼓而归,庭有陈鼎,家有三归”。后来,“孔子闻而非之曰:‘泰侈逼上。’”韩非也批评说:“管仲不务尊主明法,而事增宠益爵,是非管仲贪欲富贵,必暗而不知术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难一》)。其二,以法治国不够完善。譬如:有一次齐桓公喝醉了酒,“遗其冠,耻之,三日不朝。”为了雪国君之耻,管仲建议开仓济贫,赦免薄罪。桓公称善,“因发仓囷赐贫穷,论囹圄出薄罪”。对此韩非很不以为然,认为:“发囷仓而赐贫穷者,是赏无功也;论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诛过也。夫赏无功,则民偷幸而望于上;不诛过,则民不惩而易为非。此乱之本也,安可以雪耻哉?”(《难二》)还有一件事,“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他怕管仲一病不起,所以特意问:“将奚以告寡人?”管仲认为易牙、竖刁和开方都是奸邪小人,所以很郑重地叮嘱桓公:“愿君去此三子者也。”韩非认为管仲根本就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和关键,所以他告诉桓公的“非有度者之言也”。在韩非看来,政治的明暗和国家的安危关键在君主。“君有道,则臣尽力而奸不生;无道,则臣上塞主明而不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数于桓公也,使去坚刁,一竖刁又至,非绝奸之道也。”(《难一》)韩非的观点虽有些偏激,但自有它深刻的地方。如果齐桓公在治国和用人的原则上出了偏差,那么“去此三子”就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韩非也指出齐桓公两大缺陷。其一,“妒而好内”。《外储说右下》篇说:“昔桓公之霸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桓公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二柄》曰:“齐桓公妒而好内,故竖刁自宫以治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齐桓公生活上的荒淫为奸邪小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也为他晚年的悲剧埋下了种子。其二,晚年由明转暗,忠奸不分,用人不当。易牙、竖刁、卫公子开方都是些善于阿谀奉承、投机钻营之徒,齐桓公为了满足私欲而失于察奸,一直把他们留在身边。管仲死后,桓公竟然像信任管仲那样使用竖刁、易牙,于是奸臣结党营私,内政日益衰败,并且出现诸子争立的局面。最后,桓公在内乱中死去。“虫流出户而不葬”。韩非批评说:“桓公不知臣欺主与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专也,故曰:桓公暗主。”(《难二》)
4、关于孔子的评价
孔子是春秋晚期一位非常活跃的政治家、思想家,由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到战国时期已经成为显学。对这样一位历史名人,韩非当然不会等闲视之。
对孔子的才智、品德和成就,韩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他的心目中,孔子“博习辩智”,是智士的典型,所以经常称赞“仲尼之智”、“孔子之贤”,并记述了不少诸侯或卿大夫向孔子请教的情况。关于孔子的道德修养和学术成就,韩非认为:“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显学》)又说:“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五蠹》)至于孔子的政绩,韩非称赞说:“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内储说下》)这是法治的成效还是仁政德化的结果,韩非没详谈。不过,从《内储说上》篇所谈的三件事来看,他认为孔子是主张以刑法治民的。有一次鲁哀公见鲁史《春秋》上有“冬十二月陨霜不杀菽”的记载,问孔子史官“何为记此?”孔子回答说:“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挑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人君乎!”孔子由陨霜讲到临民之道,强调该杀则杀。“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孔子认为:“弃灰于街必掩人”,容易引起纠纷,甚至会酿成“三族相残”的惨事,所以“虽刑之可也”。再说,不弃灰于街是很容易做到的事。“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孔子的这番话很对韩非口味,可以为他轻罪重罚、“以刑去刑”的法治主张作注脚,所以他引以为证。第三件是关于鲁国救火的事:“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众趣救火。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乃召问仲尼”。孔子分析说:“夫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鉴于火情紧急,又不可能“救火者尽赏之”,他建议:“请徒行罚。”哀公从其言,“于是仲尼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本来孔子是主张宽猛相济的,韩非取其“猛”而舍其“宽”,极力渲染他以刑罚治民的一面。
孔子的思想核心在礼与仁,韩非的“法”实际上脱胎于儒家的“礼”,二者颇有相通之处,所以韩非对孔子关于“礼”的言论大都持肯定态度。譬如,孔子曾侍坐于鲁哀公,哀公赐之桃与黍。“仲尼先饭黍而后啖桃,左右皆掩口而笑”,于是孔子讲了一通黍贵桃贱的大道理,说:“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不然就伤害了礼义,所以要先饭黍而后食桃。这是借饮食谈贵贱有序,不可颠倒(见《外储说左下》)。孔子的门徒子路曾为郈令,当时鲁国发动民众开挖长沟。“子路以其私粟为浆饭,要作沟者于五父之衢而郈之。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子路不理解,孔子说:“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今鲁君有民而子擅爱之,是子侵也,不亦诬乎!”(《外储说右上》)原来仁爱也是有规矩的,孔子认为子路的行为是“过其所爱”,错在“擅爱”,用韩非的话说这叫作“越职”。孔子重视“礼”,所以就很强调正名定分。卫文公名辟疆,当他朝拜周天子时周行人逼其改名以避讳,不然不予接纳,因为只有周天子才有开辟疆土的权力,诸侯不能用“辟疆”这个名号。后来,孔子听到这件事评论说:“远哉禁逼!虚名不以借人,况实事乎?”(《外储说右下》)孔子强调正名以尊王,这与韩非尊君重势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他对孔子的议论大为赞赏。
不过,韩非对孔子倡导仁义,强调道德教化,则颇不以为然,如孔子曾说:“为人君者,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水方,盂圆水圆。”一般情况下韩非并不认为君主可以放纵自己,相反在《安危》篇他还主张人主应以尧“自刻”。但一谈到治国临民的原则,他特别强调抱法处势任术,而孔子却强调君主以身作则,所以他批评:“孔丘不知,故称犹盂。”(《外储说左上》)还有,孔子重孝道。“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说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韩非认为:“夫父之孝子,君子背臣也”,“三战三北”理应处罚,孔子却“举而上之”,这样赏罚颠倒危害极大,所以他愤怒地指出:“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五蠹》)另外,孔子曾盛赞舜以德教化民众,又称赞城濮战后晋文公行赏先雍季而后舅犯,对此韩非也提出尖锐的批评,说:“仲尼不知善赏也”(《难一》),“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也”(《忠孝》)。
总起来看,韩非对孔子是作了两面观的。他似乎力求把这位儒家先师与其后学区别开来,一面骂周围的儒生是蛀虫,一面又称孔子为“圣人”。对孔子的思想学说,他从法家的立场出发,有肯定也有否定,“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5、关于商鞅的评价
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在各诸侯国中历时最长、成效最显著。韩非对商鞅的法治思想和变法活动特别重视。
韩非对商鞅的评价非常高,常将他与伊尹、管仲并列,称他们“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是“忠臣”的典型代表。对商鞅变法的成就,韩非从历史的对比中作了充分的肯定。《奸劫弑臣》篇说:“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因末作而利本事。当此之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于是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被刑者众,民疾怨而众过日闻。孝公不听,遂行商君之法。……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
商鞅变法的内容很广泛,其法治思想也相当丰富。韩非特别赞赏轻罪重罚、以刑去刑的思想主张。在《内储说上》中这样写道:
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
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
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
一日,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
去刑”。
表面上看轻罪重罚似乎有些残酷,但罚的对象是有罪者,重罚的目的是“以刑去刑”。韩非认为这是“利民”之道,所以表示赞同。
韩非对商鞅也不是一味地歌功颂德,缺点和失误也直言不讳。在《定法》篇中就分析了商鞅的两点不足:其一,言法而不言术,局限很大。他说:“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秦虽因变法而富强,但却“无术以知奸”,所以应侯、穰侯等人反而利用变法成果以谋私利,韩非认为这就是秦经几十年努力而没能成就帝王之业的原因所在。其二,“商君未尽于法也”,即商君之法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如:“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韩非认为这种按军功选拔官吏的办法是不妥当的。他打比喻说:工匠要靠手艺,医生要会调配药物,假如硬要立有军功的人干这些事,“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同样道理,“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以军功爵制取代世卿世禄制是历史的进步,但让有斩首之功的勇士去当官治民并不恰当。在战争年代这种选官制度的弊病表现得还不明显,那么天下太平,其消极作用便会明显地表现出来。秦一统六国后,地方统治力量的薄弱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韩非早在统一之前就看出了军功爵制的隐患,可谓远见卓识矣。
后记 《韩非史论研究》是一组系列论文,本文是其中的第一部分,其余三篇是:《韩非说史》(见《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3期)、《韩非史论的特点》(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访问学者论文专辑)、《关于韩非历史观的几个问题》(待刊)。
标签:韩非论文; 历史论文; 齐桓公论文; 管仲论文; 五蠹论文; 法家论文; 君主论文; 法家思想论文; 史记论文; 战国时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