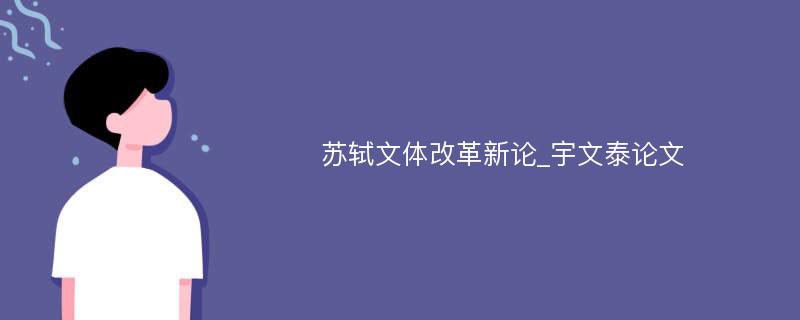
苏绰文体改革新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体论文,新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绰文体改革之意图、内容及背景尚有未发之覆,如能联系魏周的社会实际及政治文化发展过程,揆之以宇文泰、苏绰大统改制的实效,检视其作品本文,恐难简单否定或忽略文学因变的这一重要环节。本篇就此略作申论,以期对唐代文学的历史与逻辑起点有一较明晰深入的理解。
一、大统改制与文化精神的整合
北朝自北魏文明太后和孝文帝改革后,鲜卑族汉化过程得以稳步推进,逐草而生的游牧文明不断向定居的农耕文明过渡,草原帝国在军事上长驱直入,而在文化上则处于退却之势。但鲜卑贵族内部对汉文化的敌视与抗拒并未消失,胡汉紧张对立依然存在。六镇叛乱,北魏分裂为东魏(后建立北齐)和西魏(后建立北周)两个割据政权,东魏北齐政权中汉人与鲜卑人的冲突更加尖锐,鲜卑族封建化进程再次受阻。与此相对照,西魏的宇文泰则踵武孝文帝,使以鲜卑族为代表的北方胡族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进一步融合,而这种文化认同又是以汉化为旨归的。据《周书·文帝纪》记载,宇文泰出于武川军镇,本“田无一成,众无一旅”,但“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业,轻财好施,以交结贤士大夫为务”。进入关中后,所用“多是关西之人”,“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注:《北史》卷9《周本记上》。), 并先后给汉族大姓赐宇文氏二十多人,借以网罗英杰,为己羽翼,又赐上层汉人以鲜卑姓,以提高汉族士人在朝廷中的地位。关中秦雍大族仕于周室且被委以重任者多达数十人,紧张的胡汉关系得以调整,目的在于“以弱为强,取威定霸”。
早在魏大统元年(535),宇文泰鉴于戎役屡兴,民吏劳弊, 命所司斟酌今古,参考变通,制定《二十四条新制》,旨在“益国利民,便时适治”。大统十年(544), “魏帝以太祖(即宇文泰)前后所上二十四条及十二条新制,方为中兴永式,乃命尚书苏绰更损益之,总为五卷,班于天下。于是搜简贤才,以为牧守令长,皆依新制而遣焉。数年之间,百姓便之”,“德刑并用,勋贤兼叙,远安迩悦,俗阜民和”(注:《周书》卷2《文帝纪下》。)。 苏绰作为累世二千石的关中士族受到宇文泰的重任,故能尽其智能,赞成其事,又为《六条诏书》,具体内容为:其一,先治心,次治身;其二,敦教化;其三,尽地利;其四,擢贤良;其五,恤狱讼;其六,均赋役。宇文泰对此非常重视,“常置诸座右。又令百司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注:《周书》卷23《苏绰传》。)。就思想而言,“六条诏书”是搀杂了实际经验和法家行政学知识的儒家学说(注: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1页。);就具体措施而言,它能针对当时关中的胡汉现实,以儒家思想模式整合君臣、吏民诸种关系,并以行政命令来推行,逐渐取得了成效,为西魏北周的取威定霸、富国强民打下了基础。
《隋书·陆彦师传》:“隋承周制,官无清浊。”周一良据此进一步引申说,北周官制同漠视高门的精神有关系,官无清浊或由于宇文泰、苏绰等人的反门阀政策(注: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5页。)。 《六条诏书》其四曰“擢贤良”:“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末曹小吏,唯试刀笔,并不问志行。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伊尹、傅说是也,而况州郡之职乎。”杜佑评论说:“绰深思本始,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其所察举,颇加精慎。”(注:杜佑:《通典》卷14《选举二》,中华点校本第1册,第341页。)唐长孺亦对此分析道:“虽然这里只是针对州郡辟举而言,然而其整个精神既是在否定门第取人的习惯,那么秀孝之举的不限门资,自不待论。”(注: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131页。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6页。)北朝的举秀孝从放宽门第限制上说已经为唐代科举制度开辟了道路。
陈寅恪谓隋唐制度渊源有三:一是北魏北齐,一是梁陈,一是西魏北周。所谓西魏北周之源,“若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2页。)。这一混合品正是大统改制在政治文化上的产物,它昭示着一种新型文化精神的形成,其特征是强调文化个性与自律性的统一,现实关怀与形上思考的结合。就西魏北周而言,就是胡汉杂陈、兵农合一、德刑并用、勋贤兼叙、义利并重的政策。换言之,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精神,陈寅恪称其为“关中本位政策”(注: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91页;《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笔者则以经过界定的核心范畴“关中文化精神”来指称(注:参见拙著:《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第1 章《关中地域与文化精神》,(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版。)。
苏绰对于建构这一文化精神,既上下求索,又导夫先路。大统改制为这一精神的发荣滋长提供了土壤、气候等生态环境,而这一精神又引领着改制卓有成效地推进。“宇文周为我国南北朝隋唐间承上启下之一大枢纽,时代虽暂,而影响于后代之政治社会各方面者綦巨”(注: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35页。)。 而“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页。 )。从大统改制与新型文化精神确立的角度来理解这两位史学家的论述,便可豁然贯通,略无滞碍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统改制为重估苏绰文体改革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语境,循此来考察苏绰的文学主张,其功过是非就易于评说了,其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也就可以重新定位了。
二、托古情结与文化寻根
论者或诟病宇文泰、苏绰的托周官改制,认为是复古泥古,则其“文章的复古主张,实际上只是当时一系列复古措施中的一项而已”(注: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第528页。)。既如此,看来在我们讨论苏绰文章复古主张之前,首先要澄清宇文泰、苏绰托周官改制的实质。
用《周礼》改制是一种历史思维方式的重现,在宇文泰、苏绰之前有王莽的改制,在其后还有武则天的改制,每次的情形各有不同,不能一概而论。而宇文泰的宪章虞夏、援用周礼显然是出于对一种新型体制的追求,这一体制要求既有别于江左萧氏,又不同于东魏北齐的高氏,还要能适应胡汉杂居的关中现实(注: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1页。)。总括起来说,托《周礼》改制, 恐怕包含着尊重经典、预设统一模式、角逐文化正统、兼顾关中现实的多重意图。当然,宇文泰与苏绰的思想恐怕也既有交融契合点,又有区别不同处。其共同点当在殊途同归,对经籍原典所焕发出的文化精神的认同与寻根,其区别处当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民族利益。
《周书·文帝纪下》谓宇文泰“崇尚儒术”,“性好朴素,不尚虚饰,恒以反风俗,复古始为心”,他“以汉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统中,乃命苏绰、卢辩依周制改创其事”。魏恭帝三年,初行《周礼》,建六官。但正如史学界所指出的,他的托古复旧不过是“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其成败所以与新宋二代不同者,正以其并非徒泥周官之旧文,实仅利用其名号,以暗合其当日现状,故能收摹仿之功用,而少滞格不通之弊害”(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91~92页。)。着眼点并不在于对文献典籍亦步亦趋的模仿,而在社会现实的激励与调整。
另一方面,传说宇文氏“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注:《周书》卷1《文帝纪上》。)。 论者或以为这是附会神话。但这种自神其始实包含一种认祖寻根的观念,暗合文化学上的人种归类方式。炎帝神农氏与黄帝轩辕氏虽矛盾斗争,但其实是由一个部落分离出来的,有相同的血缘关系。黄帝与炎帝虽同出于少典氏,但既分为姬、姜两氏族异性异德,故可以通婚。后来生育周民族先祖姬姓后稷的,便是有邰氏的姜嫄。宇文泰据有姬姜两姓先民生活过的关中,孝闵帝宇文觉其始又以岐阳之地被封为周公,故后来国号为周。宇文部族虽自称神农氏的苗裔,但炎帝一系所留下的文献典籍较少,故“依附古昔,称为汉化发源之地”,攀附姬周,托《周礼》改制(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5页。《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92页。),遥想之中似乎产生了某种隐微的联系。因炎黄与姬姜本身就是剪不断、理还乱、不断矛盾斗争、又不断杂糅融会的两大集团,所以宇文氏的这种简单附会,既有强烈的政治功利目的,又包含文化上的寄命归宗。其托《周礼》改制,令苏绰作《大诰》,便成为一种有意识的文化寻根和溯源。魏周统治者“摈落魏晋,宪章古昔,修六官之废典,成一代之鸿规”(注:《周书》卷2《文帝纪下》。), 故其所恢复的并不是现代儒术,而是儒家的原始经术。这样对内找到了一种渊源有自的信仰与思想资源,对外则树起文明之始的标帜,睥睨汉魏,秕糠萧梁与高齐。对于素有回溯思维方式和托古心理模式的前喻文化来说,这是一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文化策略。至于西周制度与鲜卑族野俗因时代与文化原因造成的反差,《大诰》文体的质木无文、佶屈聱牙与北朝时期口语的方枘圆凿,雄才大略的宇文泰未尝不知,只是在他看来,这一切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是艰难的汉化历程中的必然代价。
就苏绰、柳虬等关中郡姓士族来说,托古改制未尝没有为汉族文化张本招魂之意。在野蛮强悍、能征惯战的军事胜利者面前,尚且能使汉族士人自傲自信的,恐怕就只有儒家的礼乐经典了。而草原帝国的统治者对中原礼乐制度并无强烈的敌意,“河西割为数国,秃发、沮渠、乞伏,蠢动喙息之酋长耳。杀人、生人、荣人、辱人唯其意,而无有敢施残害于诸儒者。且尊之也,非草窃一隅之夷能尊道也,儒者自立其纲维而莫能乱也。”(注: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5,中华书局排印本中册,第497页。)他们“汲汲然自同于华夏,即所行者未尽为周、 孔之道,而出于汉之说经家附会之词,亦可见文化之权威,足以折蛮野而使之同化矣”(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0页。)。胡族扩张者与关中士族各怀异想, 但在文化寻根中却能殊途同归,找到了一个文化契合点,这就是对西周典章制度的共同认可。
苏绰既考虑到宇文氏集团的现实利益,又为汉族士人加盟到这一集团找到了一个堂皇体面的文化借口。为弱化和消弭胡汉间的紧张对立,使汉族士人能在兵燹与血腥中保种保族,繁衍发展,可谓苦心孤诣,惨淡经营。这种文化承担精神是应该大大彰显的。钱穆曾称赞道:“苏绰为宇文泰定制,即根据周官。下迄隋唐,遂重开中国历史之光昌盛运。苏氏之功不为小。”(注: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新亚学报》第5卷第2期。)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多以托古复古的面目出现。政治改革如此,文学改革也不例外。郭绍虞干脆径称从隋唐到北宋是文学观念的复古期(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2页。)。 韩愈表示要“扶树教道,有所明白”,并且“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2《上兵部李侍郎书》、卷3《答李翊书》。)。陈寅恪认为韩愈首先发现《小戴记》中《大学》一篇,阐明其说,《原道》乃为中国文化史上最有关系之文字(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88页。)。 韩愈的重道明道也是强调儒家原典对社会现实的潜在作用,不仅是学理上的认同,而且由向慕之怀转化为一种实践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苏绰这位古文运动的先驱与主将韩愈的区别并不在对道的体认,而主要是对文的运用之妙(注:郑振铎即认为,韩柳的古文虽比苏绰高明万倍,然究竟还是“托古改制”。参见郑氏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2册,第374页。)。
三、《大诰》与公文体改革
论者多指出宇文泰、苏绰的文体改革,片面强调实用和政治功利,违背文学发展的规律。这些看法不无道理,但其中也包含着一些误解。因苏绰所针对者既非现代意义的文学,又非泛称各类文章,而是特指诏告文书等公翰。
首先看《周书·苏绰传》的记载:“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 ” 其事在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当梁大同十一年。论者或据这段话指斥苏绰导致西魏、 北周文学的倒退,是用行政命令干涉文学的反面事例。《资治通鉴》卷一五九叙此事时即说:“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体。”但揆以史实,却颇有出入。
刘知几《史通·杂说中》:“寻宇文初习华风,事由苏绰。至于军国词令,皆准《尚书》。太祖敕朝廷,他文悉准于此(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浦起龙《史通通释》此句校记曰:“一无‘他’字。”见该书第500页。下引钱钟书《管锥编》对此句的断句与通行本有异, 钱先生断“太祖敕朝廷他文悉准于此”为一句,则语意更显豁,说明太祖所干涉者只限于朝廷公翰。)。柳虬之徒,从风而靡。”浦起龙释此条曰:“始于令敕仿古,因而史笔从风。 ”(注:见前举《史通通释》第500~501页。)指出规摹《尚书》者,惟军国辞令。 “他文悉准于此”一句,或作“文悉准于此”,或与前句连,无句读,恐亦指文告公翰类,从风而靡者,亦仍限于史笔,与文无涉。“悉准于此”、“皆禀其规”,只能说语言风格的影响,使其更为简朴古质而已。亦步亦趋的模仿不可能,因为许多文体《尚书》中没有,何以模仿呢?
钱钟书对此公案曾有敏锐而明晰的分辩:
《周书·苏绰传》言绰《大诰》后,群臣“文笔皆依此体”,然《史通·杂说》中曰:“苏绰军国词令,皆准《尚书》,太祖敕朝廷他文悉准于此,盖史臣所记,皆禀其规”;则所“革”者限于官书、公文,非一切“文笔”,《周书》未核。征之见存诏令,惟魏恭帝元年太祖命卢辩作《诰》谕公卿、三年禅位周孝闵帝《诏》、孝闵帝元年登极《诏》稍“依”《大诰》体,明帝武成元年五月《诏》已作六朝惯体,去大统十一年颁《大诰》时不及十五年也。柳虬存文虽无丽藻,仍尚比偶,观其论史官《疏》可知;……隋文此诏未见,想其欲继周太祖志事而光大之,由“公”文而波及“私”著(注:《管锥编》第4册, 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51页。)。
郑振铎对此点亦指出:“宇文泰在魏帝祭庙的时候,曾命苏绰为《大诰》奏行之。后北周立国,凡绰所作文告,皆依此体。”(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2册,第368页。但郑说从史实上讲微误,苏绰卒于西魏大统十二年(546),享年四十九,北周建国在557年,故绰不可能为北周作文告。)说明宇文泰、苏绰的文体改革只限于实用性的“笔”,似与艺术类的“文”无涉(注:《周书》行文有变俚为雅的倾向,刘知几《史通·杂说中》已批评“其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故“文笔皆依此体”一句中之“文”,恐系行文时连类而及。)。只就公翰立论,并未殃及到私著。到了李谔上书隋文帝时,才欲波及“公私文翰”;苏绰只从正面积极倡导奖劝,并未如隋文帝动用国家机器执法纠弹。文体复古的时间既短,范围又狭,既未能最后扭转南朝浮艳文风的泛滥(注: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9页。),又未曾阻挡言情文学之发展。 而其所昭示的经验教训,则由唐代韩愈、柳宗元所步武,为古文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
联系苏绰的学术背景,《周书》本传说他“少好学,尤善算术”,他对宇文泰“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帮助宇文泰“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是一位长于吏治的大臣。而西魏当时的用人标准是:“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在一个常态的高效率管理机构中,主要应看重具有技术理性的吏干之才,譬如是否精通法典,是否熟悉账簿及计算等,至于文学才华的高下并非关键。而军国辞令、文告公翰、户籍账簿都应以信实、准确、鲜明为第一位,至于辞章是否富艳华美,当非要事。又据《周书·苏亮传》:“亮少通敏,博学,好属文,善章奏。……亮少与从弟绰俱知名。然绰文章少不逮亮,至于经画进趣,亮又减之。……所著文笔数十篇,颇行于世。”今无苏亮文传世。但以他“善章奏”推测,则当时行世之文笔、文章,恐怕亦多为章奏公翰之类。
诗赋注重声律,文章追求骈俪,在南朝由来已久,北朝文士多所向慕,随风景从。影响所及,军国辞令等公翰亦浮华艳丽。宇文泰、苏绰欲矫其弊,以提高行政效率和信实度,这是颇有政治远见的。惜南方浮艳之风愈演愈烈,遍及关右,深入人心。宇文泰、苏绰固不足挽狂澜于既倒,隋文帝、李谔假宪台执法,亦未能尽治不法之众。韩愈、柳宗元起衰振颓,生面别开,但影响亦止限于私著,终唐一代公翰官书仍为骈体一统的天下,骈俪文被家弦户诵、童而习之,文体改革仍未能最后告捷。积弊浸深,习惯使然,非一朝一夕可以移易,故不能以首战失败来论定苏绰文体改革的意义。所谓“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注:《周书》卷41《王褒庾信传》。)。王夫之对宇文泰、苏绰的大统改制颇多微辞,但对文体改革的评论却较为平实公允:“文章之体,自宋、齐以来,其滥极矣。……故自隋而之唐,月露风云未能衰止,而言不由衷、无实不祥者,盖亦鲜矣,则绰实开之先矣。宇文氏灭高齐而以行于山东,隋平陈而以行于江左,唐因之,而治术文章咸近于道,生民之祸为之一息,此天欲启晦,而泰与绰开先之功亦不可诬也。非其能为功也,天也。”(注: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5,中华书局排印本中册,第582~583页。)
四、《大诰》与魏周文学新诂
苏绰作《大诰》模仿《尚书》,时为人们所诟病,但究竟如何模拟,须细读作品本文才能评论。检《尚书》有《大诰》一篇,与苏绰所作认真比勘对读,则异同毕现。
《尚书·大诰》一般认为是在武王死后,管叔、蔡叔、武庚联合淮夷共叛周,周公摄政,东征讨叛,布告天下之文。而苏绰所作是在西魏大统十一年,宇文泰当国时。《尚书》是纯粹记言体,而苏绰所作则是在记言体中夹杂记事。《尚书》所记唯周公一人之言,而苏文则兼记魏帝与宇文泰两人之言。苏文完全袭用《尚书·大诰》篇的词句并不很多,《尚书·大诰》与苏绰同名之作俱在,两相比较,不难明白。其目的不过如陈寅恪所说:“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如一定说是模仿,也属于刘知几所谓“貌异而心同”:“其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镕铸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注:《史通》卷8 《模拟》。)以文辞而言,说苏绰模仿《尚书》质朴古奥的文体风格,多用单行散笔则可,说其句规字模,完全因袭《尚书·大诰》则不尽合事实。钱基博对此点早有卓见:
绰创制一代,乃欲以谟诰变俪偶,而效之者,惟一卢辩,可谓吾道不行。然则绰之师古,亦何补于矫枉哉。顾相其笔势,如镕铸而成,佶屈聱牙,出之自然,而往复百折,惟骨劲而气猛,固辞笔之鸷翰也。前之王莽,有其辞而无其气,后之王通,得其理而遗其笔;神气索莫,负声无力,同一摹古,生死攸别矣(注: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册,第244页。)。
无独有偶,其子默存对苏绰文章亦具慧心,多有评论:
一代文章,极“起衰”之大观者,惟苏绰《大诰》。细按之,貌若点窜典谟,实则排比对偶。《尚书》本有骈语,……《大诰》则不然。“允文允武,克明克义”;“天地之道,一阴一阳。礼俗之变,一文一质”;“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袭,惟其可久”;此等对句,固无论矣。“惟时三事,若三阶之在天。惟兹四辅,若四时之成岁”;“不率于孝慈,则骨肉之恩薄。弗惇于礼让,则争夺之萌生”;此非骈文排调而何。盖不特远逊新莽《大诰策命》,即视夏侯孝若《昆弟诰》,亦益加整齐;非昌黎《进学解》论《尚书》所谓“浑噩诘屈”之风格。几见其能糠粃魏晋、宪章虞夏哉(注: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第301~302页。)。
钱氏父子先后议论苏绰《大诰》,但观点并不一致,钱基博侧重强调其依古制以革今调,模拟谟诰而又能往复变化,骨劲气猛,笔势雄鸷。钱钟书则指出其文中亦有排比对偶,并上溯源头,谓《尚书》早有骈语,并非一味单散。但苏绰文中之骈偶,既非全袭《尚书》,亦非通篇铺排时调。正如人们所指出的,就是在韩柳文章中,也不是一味地单散,其中亦间有骈俪,这并非古文家言行不一,未能免俗,实因汉语言文字固有特质所在,无法违背而已。
苏绰所为《六条诏书》,被宇文泰置诸座右,令百官习诵。该文条理明晰,简约凝炼,句式亦以散笔为主,间有偶句,但出之自然,不主故常,事理相谐,文质统一,并非《尚书》体、《大诰》体。据《周书》本传知,绰还著《佛性论》、《七经论》,虽不知其具体内容,但亦恐非《大诰》体所能范围。柳虬著《文质论》,提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的观点,似持文质调和论的看法。他上疏论史官密书善恶,未足惩劝,宜当朝公开其事,然后交付史阁,使是非彰明,得失无隐(注:《周书》卷38《柳虬传》、《李昶传》。)。骈散交织,虽简短素朴,但明理达意,文质相扶。又据《周书·柳庆传》记载苏绰反对的是华靡轻薄,柳庆的《贺白鹿表》得到他的赞赏,主要是辞兼文质,并非模拟《大诰》体(注:从时间上考虑,苏绰作《大诰》在大统十一年六月,柳虬上疏在大统十四年前,柳庆贺表在大统十年后,虽不能确考柳虬上疏在《大诰》颁布后,但从绰言“宜制此表,以革前弊”云云知,柳庆贺表或在《大诰》颁布前,则文体改革不始于十一年作《大诰》,而始于柳庆贺表,且所欲革除者只是华靡轻薄的文风,并未有规定严格依循《尚书·大诰》的程式。)。
联系宇文泰的“恒以反风俗,复古始为心”,“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欲革其弊”云云,可见宇文泰与苏绰对文体改革的看法是一致的,谋之已久,前后持续,没有变易观点,并非一时即兴之举措。
李昶与苏绰同时受宇文泰的器重,当时的诏册文笔,多由他所作。他曾说:“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注:《周书》卷38《柳虬传》、《李昶传》。)似也是一位吏治之才。他所作《答徐陵书》,倾吐对徐陵文才的敬佩之情,通篇采用骈体,文笔流畅,轻松自然,虽有华美之色,但无雕饰之气。足见除公翰外,私著仍可用骈文。唐瑾的《华岳颂》也是一篇工丽的辞赋,刻画华山景色,意境浑成,说明辞赋类的作品并没有规定要模仿《尚书》。
其实,最能代表魏周本土文学特征的当推宇文护与其母阎氏的往复家书(注:文见《周书》卷11《晋荡公护传》。阎氏的信,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入《全北齐文》卷9“阙名类”。)。 阎氏的信虽由人代笔,但将家中琐事絮絮叨叨,娓娓道出,俚俗细碎,不假修饰,逼肖老妪口吻。宇文护的复信,字句虽较整齐,基本上是四言句,间有俪偶,但是以单行散句为主,出之自然。叙到伤心处,则又吞吐呜咽,一腔幽怨泻出。钱基博对此推崇备至,认为魏周作品中至情胜韵、自然英美者,不得不推宇文护为第一手,其文是北朝第一篇文字(注: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册,第244页。)。 钱钟书则誉阎氏的信为“‘笔’语之上乘”(注:《管锥编》第4册,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1512页。)。值得注意的是,阎氏信中提及“书依常体”,说明此类文体及写法在北朝齐、周之时极为普遍,并非《大诰》体所能局限。以口语琐事入文,已肇晚明尺牍小品,而质性天然,风骨嶙峋,则是南朝文士所无法模仿的。
五、关中地域与南北文风的统一趋势
刘知几《史通·杂说中》:“寻宇文初习华风,事由苏绰。”说明宇文氏集团进入关中时游牧文化的旧习仍非常浓烈,至苏绰辅政时才开始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行汉化措施。但起点较低,百废待举,戎马倥偬,征战不断,不可能专注于文学。“后周草创,干戈不戢,君臣戮力,专事经营,风流文雅,我则未暇。”(注:《隋书》卷35《经籍志》集部序论。)这一看法是基本符合实际的。
但是,草原帝国的征服者对中原礼乐制度及艺文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除宇文泰雅好经术如前所述外,明帝宇文毓亦崇尚文儒,“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又捃采众书,自羲、农以来,迄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云。所著文章十卷。”(注:《周书》卷4 《明帝纪》。)上有所好,下必有所效,于是一时间魏周亦人才云集。西魏、北周的文士除关右旧族苏绰、苏亮、苏威、柳庆、柳虬、柳机、柳弘等外,还有山东士人卢辩、卢诞、卢光、熊安生等。尤为重要的是,南朝经师沈重及文士庾信、王褒、颜之推等的先后入西魏、北周,给质朴贞刚的关中文坛带来了流光溢彩。
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即魏恭帝元年),西魏大军攻破江陵, 王褒、王克、宗懔等江南文士被俘至西魏,庾信则因出使而滞留长安,宇文泰对此曾欣喜地说:“昔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之矣。”对这批文士恩礼有加。当南朝陈请求以通好互换为条件放归这些流亡者时,周武帝宇文邕只放王克、殷不害等,而将庾信、王褒并留不遣。“是时,世宗雅词云委,滕、赵二王雕章间发。咸筑宫虚馆,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味于遗韵,眩精于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注:《周书》卷41《王褒庾信传》。)《北史·庾信传》亦说:“明帝、武帝,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志,多相托焉。唯王褒颇与信埒,自余文人,莫有逮者。”北周的“才子词人,莫不师教;王公名贵,尽为虚襟”(注:宇文逌:《庾子山集序》,中华书局点校本《庾子山集注》卷首。)。流寓关塞的庾信、王褒,不仅蝉联文坛,而且能执牛耳、主祭酒,这确实是一件令南方文士永远可以夸示的大事。从西魏、北周统治者对南朝文士的宠渥礼遇及北朝同行对他们的真诚推服来看,说明魏周文学起点虽低,素朴淳古,但具开放胸怀,对南方的藻饰、声律等形式美取拿来主义态度,并不一概反对,与政治军事上的开拓进取适相一致。这与南方士人居高临下,以正朔所在、文化优越者的身份鄙薄讥嘲北朝文学,恐惧忧患北方地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吸收进取与保守退却,两种文化态度实潜藏着两种机运。
魏周文学因庾信、王褒等由南入北作家的点缀委实增辉生色不少,这已为人们所知。但另一方面,艰危时世与雄奇关塞亦成就了天才的艺术家庾信,所谓“世厄其遇,天就其名”,“斯则境地之曲成,未为塞翁之不幸者也”(注:《诗比兴笺》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第87~88页。)。“至信北迁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浩气舒卷,变化自如,则非陵之所能及矣”,“其骈偶之文,则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8,中华书局影印本下册,第1275~1276页。 )。如果没有厄运危时的遭逢,关河形胜的履历,慷慨悲壮之气的熏染,恐怕就不会有文章老更成、“暮年诗赋动江关”的庾信,只剩下一个善写宫体诗的狎客弄臣,“为梁之冠冕”虽或有之,“启唐之先鞭”(注:杨慎《升庵诗话》卷9:“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 启唐之先鞭。”)则无从落实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中这一“五方杂厝”、多元并存的文化区域,不仅涵容了草原游牧文化,而且吸收了江南稻作文化,交融整合,又以新的姿态出现。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中指出南北文风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单一的清绮秀美或贞刚壮烈都失之过偏,不能蔚为大观。“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但南北文学交汇整合的趋势,则不始于隋代,而始于魏周时期的关中。苏绰、宇文泰所倡导的素朴文风与庾信、王褒所带来之南方绮艳美文,“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页。)。 “重乎气质”与“贵于清绮”虽为两个极端,得失相较亦各有所短,但两种风气奇妙地遭遇于长安,互相涵容吸收,隋及唐初,不过是此种趋势的继续与发展。进而言之,如果说苏绰的文体改革还仅仅是对散体文的尝试与实验的话,那么庾信入关则不仅标志着南北文学的交汇,同时暗示着新旧两种美学思想的转换,隋唐文学历史与逻辑的起点应当由此立下界碑。文学的新生代隐然呼之欲出,此后唐代文学发荣滋长的运势,已成一种无法逆转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