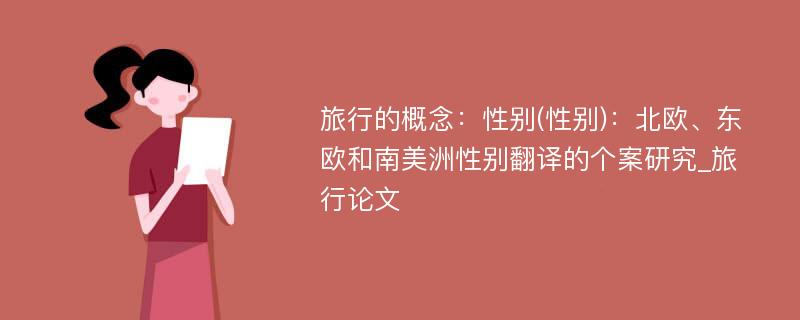
一个旅行的概念:Gender(社会性别)——以北欧、东欧和南美对Gender的翻译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北欧论文,南美论文,为例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的女权主义理论和知识在全球流动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绝大部分流动实际上走的是“单向道”,即从西方、北方流向东方与南方。即便是从“西方”来看,也只是小部分的理论和知识流动出来,大部分理论还是待在“家里”。思想、知识在全球化循环的过程中的断裂比比皆是。问题是:为什么一些思想、知识、理念在流动,而另一些同样重要的思想则不流动?它们是如何流动的?又如何被接受或拒绝的?原因是什么?谁参与和控制了这些理论的再次创造和推广的过程?谁没有参与这个过程?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这些思想、知识又是如何被翻译解释的?如何来分析和认识这种流动(或不流动)的过程,已成为全球化过程中妇女运动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注:对gender概念在中国的“旅行”过程,请参见闵冬潮的另一篇文章《Gender(社会性别)在中国的旅行片段》,载《妇女研究论丛》2003年第5期。)
爱德华·赛义德在1984年提出的概念“理论旅行”为认识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无疑,赛义德提出的“理论旅行”很有启发意义,但是,专注于在学术上探讨一种理论或概念如何被转换和接受,使理论旅行似乎成为了一种“自动”的过程。对理论旅行中的原因和动力问题,赛义德似乎有所保留。
70年代后期欧美思想学术界出现的“后现代转向”,对理论提出了重新定位的问题。赛义德的“理论旅行”也被进行了重新解读。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1989年发表的《关于旅行与理论的札记》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在他看来,理论已不是在西方的这个“家园”里了,或者是说具有特权的地方,理论已被其它的种族、性别、具有文化差异的知识所在位置的诉求所影响或打断。因此赛义德“理论旅行”的思想在后殖民时代应该进行修改。
同一时期,来自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的理论家们从不同角度质疑理论旅行。比如,来自拉美的理论家沃尔特·米格诺鲁(Walter Mignolo)将“理论旅行”的讨论推进了一步,提醒人们注意到,在理论旅行所到之处这些理论的接受人对这些理论提出的质疑。
在英语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今天,理论旅行的载体是什么?这也是赛义德所忽视的一个方面。大量的事实表明,“理论旅行”的复杂性还来自于翻译在理论旅行中的作用。
在此要强调的一点是,自70年代之后,对翻译的认识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那种认为翻译是一种透明的载体的观点已遭到种种质疑(见许宝强、袁伟,2000)。人们已从关注“什么是正确的翻译”转向关注“翻译在做什么?它是如何在世界上循环和引起回应的?”(Simon,1996)。也就是说,当一个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其意义的转换过程,与其说是找到与再现其文化的内涵的过程,不如说是在后者的地域环境中进行的再次建构与创造的过程。在此意义上,翻译“已不再被看成是中性的”哲学,“而是政治的卷入,语言,话语,意识形态的对立及社会冲突”(Venuti,1992,p.2)。可以说,正是这种翻译政治的浮出水面,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理论旅行中知识生产的权力关系。
在此,我将以在国际妇女运动中流传最广的女权主义概念gender(社会性别)为例,来看gender这一概念是如何在欧洲、南美通过翻译进行“旅行”的。回顾gender理论的发源地所关注和讨论的主要是性与gender的关系,从最初将二者分离到重新打破这个对子,这一过程代表了英美女权主义从70年代初至今gender理论发展的主要路径。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即便是“美国制造”的gender理论概念,也是名目繁多,有时还互相对立。另外,在30多年来的发展过程中,gender理论自身已变成了一个不断重复书写的结构。早期的概念还在应用,而后来的理论又不断地在上面重迭,因此,就更加剧了它在其旅行过程中的复杂性。
一、Gender的欧洲之行
在欧洲,翻译gender所带来的麻烦似乎比翻译其它女权主义理论概念要大得多。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曾经指出:“在现代英语和德语中,gender和geschlecht与性(sex)、性态(sexuality)、性别差异(sexual difference)、代际(generation)等词都有关。然而,在法语和西班牙语里似乎就不具有这些意义,与gender接近的词有亲属关系(kinship)、种族(race)、生物分类(biological taxonomy)、语言(language)、国籍(nationality)”。(Haraway,1991,p.130)
对使用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人来说,对这种翻译gender的‘麻烦’体会更深。欧洲著名的女权主义理论家罗斯·布雷多替(Rosi Braidotti)曾多次指出,把gender翻译成上述几种语言几乎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女权主义仍在使用性别差异(Sexual Difference)理论(Braidotti,1994)。当然,语言的障碍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性别差异理论自身的成熟发展使gender欧洲之旅在上述地区的确大大减缓了速度。
那么,gender理论在欧洲的其它地区又是如何旅行的呢?在2000年出版的欧洲妇女研究的学科化的报告中,谈及了在欧洲国家不同语言中翻译gender的个案研究。从中,对gender在欧洲语言、文化、背景中进行翻译的困境及紧迫性可见一斑。在此,仅以北欧、东欧为例,来进一步观察分析gender概念是如何通过翻译、解释在这些地区和国家旅行的。
个案之一:Gender在北欧斯堪地那维亚地区的旅行。
北欧国家的妇女研究几乎与欧美其它地区同时起步。由于受到英语世界的影响,gender概念便很快旅行到北欧诸国。
与英语相当不同的是,挪威语的"kjonn"、丹麦语的"kon"和瑞典语的"kon"同时表示sex和gender。例如,"kjonn"在挪威字典里的意思是:产生同样类型的文化个体生理特征的总称,女性、男性特征,色情的性质,性器官,语法分类。(Lempiainen,2000a)总而言之,在北欧的这几种语言里,没有对应于英美sex/gender区分的词语。因此,这3个字可以用来通指sex/gender。如果遇到必须要对两者进行区分的时候,则注明生物学的(biologisk kjonn)和社会的性别(sosial+kjonn)。
由于译出语言与译入语言的不同特点,如何翻译英语中的gender一词,在北欧各国便成了一个问题。一种办法是用与gender相对应的拉丁词"genus"来翻译gender,但似乎并不特别的成功。因此,在斯堪地那维亚同时对应于英语sex与gender的词—kon仍然被使用。有人认为,因为该词没有把生物学的和社会的意义加以强行区分,反到成为很有用的概念。(Lempiainen,2000a)
然而,在这几个国家里,因社会文化语言不同,对gender的翻译又有些差别。在瑞典,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于对妇女与gender研究的需要,genus一词很快被用来翻译gender。当然,也有人认为,应该区分genus与英语的gender的不同,因为gender在斯堪地那维亚语的翻译中意为“社会的kjonn",它将生物性的和社会性的区别表示出来;而genus一词本来强调的是这两方面的互相关联,因此,genus可被理解是在所指上可以变化的概念。“男人”和“女人”生物学上的区别总是被不断开拓的,由此推动着社会实践的变化,并需要对它进行重新表述。因此,生理是可以被影响和变化的,换句话说,genus是个比gender更具有符号的意义和“表演”意义的范畴(见Lempiainen,2000a)。然而,genus在瑞典的使用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近来出现的反对意见认为,根本不存在社会的性别(social+Kjonn),只有,一方面,男人和女人的身体;另一方面,个体的人类,他(她)们可以自由地塑造自身,来改造这个世界。在1998年一次关于sex和kon的讨论中,没有人再特别强调瑞典语中该词的用法,大家都或多或少地在某种程度上附和英美的观点来重写这些概念。(Lempiainen,2000a)
在芬兰,翻译gender则出现了另外一些问题。芬兰语里,用sukupuoli表示sex/gender的区分。该词原有的意思是男人与女人各占一半的“异性恋家庭制度”,suku的意思是亲属,puoli的意思是一半,两个字合在一起,意为“亲属制的一半”。无疑,这种翻译与芬兰的社会文化与历史是紧密相连的。有人认为,芬兰的gender系统是个无性别的性别(genderless gender),换句话说,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甚微。由于gender的这种“无性别”性,因此也就不需要特别地对男女的不同地位、权力关系进行质疑。然而,相继带来的问题是,关于两性之间关系的研究在芬兰的社会学研究中也就消失了。(Lempiainen,2000b)
当gender理论旅行到北欧时,其社会、文化和语言上的“距离”便显示出来。首先,语言的翻译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在北欧语言中原有可以同时表示sex和gender的词汇,为了翻译外来的gender概念,就需要找另外的词来区分sex和gender。然而,80年代之后的形势是,在gender理论的“发源地”已经开始讨论消除sex和gender之间的对立区别,北欧语言中原有的sex和gender通用的词汇似乎显得更有意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与世界许多地区相比,北欧的性别差异要小得多,处于这种“无性别的性别”(如上述的芬兰)的情况下,对gender理论的质疑、拒绝和重写,便是留给“当地居民”的重要课题。
个案之二:Gender在东欧。
在东欧的斯拉夫语系中,原有的词汇spol(斯洛文尼亚语),poi(俄语,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pohlavie(斯洛伐克语)等,包含着sex和gender两种意思(Bahovic,2000)。这一点与北欧的语言颇有相似之处。但另一点与北欧却相当不同,至80年代末,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在这些国家里还是个空白。然而,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苏联和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西方,特别是英美各种思潮大举流入。女权主义理论和思想随着西方女权主义者的“政治旅游”团,基金会资金的投入,和项目的引进涌进了东欧,其中,gender便成为这些“旅行者”们带来的重要理论之一。
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翻译gender。
一种翻译是保留gender原词。俄国妇女研究的创始人之一,波沙达斯卡娅·维德贝克(Posadskaya Vanderbeck)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回顾1980年代,为了取得赋权妇女的效果,我觉得用一个大家不知道的词更好。让人们来问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来解释。”(Grunell,1998,p.503)。
在1989年,维德贝克建立了莫斯科第一个gender研究中心。被问之为什么以gender为名?答曰:我喜欢这个概念。因为使用gender这个词,就可以强调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是社会所建构的,那么它便是可以改变的。在这种意义上,它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因为它对社会现象持一种历史批判的态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苏联社会科学声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当它解释诸如“妇女就业模式的特殊性”时,却绝对是本质主义的。认为妇女由于生育这种自然的天性,所以有不同的工作模式。当我阅读西方的文献时,我非常高兴地发现gender与性之间的区别。所以,我接受了这个词,对我来说,它是我们的语言(Grunell,1998)。
另一种被广为接受的作法是将gender译成斯拉夫语中的rod,该词原有的意思是:代际、民族、生育、亲属等,现在仿照英美传统的路子,把那种文化的和社会的所构成的意思移植过来了。(Bahovic,2000)还有一种做法是将rod加引号,以便与其原有的语法范畴,家庭制度等含义加以区别。这种译法,如保加利亚学者科尼拉·斯莱沃娃(Kornelia Slavova)所言:“给人的感觉是外来的,移植的,西方的和人造的,非但没有使人比较容易接受,反而加强了其外国化的意味和文化的距离,降低了其被接受的程度”。(Slavova,2002)由于女权主义在东欧基本上是个负面的概念,当gender的概念由西方的“旅行者”们空降到这样一种语境里,一系列的文化真空造成了结构上的空缺。斯莱沃娃列举了造成翻译困境的几个方面:缺乏与有关的话语的回应;缺乏女权主义的社会实践和鲜明的妇女运动;缺乏对妇女研究资料的积累和女权主义的知识生产;缺乏建立在东欧妇女经验上的妇女理论;缺乏在主流政治层次上的女权主义政治。而这些具有内在联系因素的缺席又会导致问题进一步的复杂化(Slavova,2002)。
随着gender概念向纵深旅行,其与当地的政治,文化的差异便越发明显。在此,翻译中的“意义等值”(equivalence)问题凸现出来。一般认为,通过翻译,可以将来源语言中的概念的意义传达到接受的语言中去。由此,这两个概念的意义大致上是相同的。但是,为了找到合适的词汇,就要尽可能地理解来源概念所产生的文化。因为这个概念的意义是建立在其文化的基础之上。然而,人们往往会迷失在这种探索之中,因为越是深入具体地探寻其文化上的定义,就越发困难地在另外的文化中找到相同意义的词汇。东欧妇女研究者对gender的翻译便面临着类似的问题。面对这种困境,许多翻译研究学者提出“意义等值”的问题不应视为寻找相同性(Lefevere and Bassnett,1990)。因为,即便在本源语言中,同一概念也是千差万别。其结果便是把翻译看作是围绕着本源语言和接受语言的符号和结构的一种辩证关系。
与北欧相比,东欧各国的女权主义现状与gender的“发源地”相距甚远,gender理论的旅行也差距很大。自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倒台之后,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形形色色的“旅行者”们携带着五花八门的女权主义理论,在各种国际组织和基金会的支持下,从西欧、北美涌入。在这种情况下,理论旅行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一种强行进入。而“当地居民”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对其进行选择的可能与条件就要大打折扣了。当然,经过了十余年的发展,不论是“旅行者”还是“当地居民”的认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时过境迁,10年之后的俄国已建立了大批的gender研究中心,此时的维德贝克也意识到:“实际上真正的事物比这些词意味着更多的东西,词汇也是社会所构成的。那么,一个相同的词的内容在不同的语境里意味着不同的东西。”(Grunell,1998,p.503)此时,身处“旅行者”地位的琼·斯格特在近距离观察了东欧国家与美国女权主义的“亲密接触”之后,深有感触地承认,在东欧,这些外来的专家想造成的气氛是要通过gender研究来铲除意识形态的烙印。从某种角度上来看,这与北美西欧女权主义者用gender来维护学术工作并无二致。但是,当意识形态在这些东欧国家里还决定着一切,妇女组织便要为国家支持的意识形态服务。在女权主义等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区别就显现出来了。在这些语境里,gender似乎是一个中立的概念。Gender研究的是一种社会对象,而不是已定型的结论。它可以成为为非意识形态,反意识形态的后共产主义女权主义的叙事。不要把gender像西方的全球化的工具那样解读而排斥当地的选择,这个概念为探索新的可能性开拓了新的空间(Scott,2000)。
Gender概念的欧洲之行,反映了妇女研究知识生产中的一个侧面。近来,令欧洲妇女研究学者焦虑的是,妇女研究和gender研究这一领域所用的术语词汇和大多数的教学材料都来自北美,并且使用英语。正如罗斯·布雷多替(Rosi Braidotti)所言,欧洲的妇女研究存在着被美国殖民的问题。她认为欧洲妇研的学者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她们要为这一新领域在自己的国家和机构被承认而斗争;另一方面,她们要发展自己的教学和研究的工具。那么,要形成“欧洲”的妇女研究,就要提出诸如民族认同、多元文化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等欧洲所面临的问题(Braidotti,2000)。
二、Gender的南美之旅
拉丁美洲女权主义的发展是与妇女运动紧密相连的。经过上世纪70至80年代的发展,拉丁美洲的妇女运动已成为新社会运动中的一支劲旅。在70年代反军人政权的社会运动中,一些妇女领袖代表人物特别关注妇女日常的,私人生活问题,诸如:性向,身份认同,强奸等,并且非常强调妇女运动与其它社会运动的关系。80年代之后,随着民主政权的建立,大街上的抗议斗争逐渐消失,女权主义者们建立了大批的社区、政治、文化、工会等专业性组织。进入90年代之后,女权主义者多在社会公共机构和NGO组织参与从地方,国家到国际组织的政治活动(Ronner and Azcarate,2000)。
从90年代初,拉美地区数千个妇女组织参与了95世妇会筹备工作和地区会议。其中围绕着如何翻译、解释"gender"这一概念,在95世妇会前后出现了一系列的斗争、曲折。其对立面主要是以梵帝冈为代表的天主教机构。
那么,有关"gender"概念翻译的斗争在拉美地区到底意味著什么?
南美洲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语言中与gender相应的词是genero,但这个字并没有包含着gender的现代意义。它具有种类(sort),阶级(class)等含义,以及在语法上分类的意思。在英语中gender所具有的与sex,sexuality,sexual difterence等意义,在法语、西班牙语中都不具有。那么,随着妇女运动、女权主义在拉美的发展,用genero或genero sexual来指涉在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社会结构的区别,就成为了一个主要问题。
在95世妇会召开之前,gender被写进大会的准备文件上,它被解释为:男女两性的区别为社会所构成,而不单是生物学上的区别。并且号召各国政府将gender的观点纳入立法,公共政策和各种项目中去。在95世妇会的准备过程中,天主教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来阻止gender一词的使用。他们指责女权主义的概念是来自外国的东西,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文件相背离。他们寄希望于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语言里的genero一词不包含英语中gender同样的含义(France,1998)。
为什么梵帝冈天主教会如此惧怕并反对使用"gender"的概念?因为他们对女权主义对妇女、妇女运动的影响,尤其是在其保护之下的妇女运动的影响很惧怕。因为在拉美地区,天主教会一向以穷人的保护者著称,是社区和草根妇女组织背后的主要支持力量(见Labon,1996)。相当一部分妇女组织,特别是草根组织是在天主教会的保护之下发展起来的。天主教会认为,一旦人们接受男女的差异是社会建构的,并且是可以改变的,然后就要承认接受人工流产的合法性,接受同性恋,接受单亲家庭等等“不正规”的家庭关系。而这个问题又是直接和拉美国家妇女有很大关联。总之,天主教会担心这个理论会毁掉婚姻、家庭和生育的所谓“自然关系”。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是一场文化革命。例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助理主教认为,把gender作为一个从生物学上分开的纯粹的文化结构,使我们成了激进的女权主义追随者。他还引用美国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舒拉密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的著作The Dialectic of Sex来证明女权主义的危险。在这部著作里,费尔斯通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来论证男女之间的关系。这位助理主教则说:“马克思都没敢下结论,要改变妇女性态的状况,把她从生育和对家庭的依赖中解放出来。”
为了反对女权主义对gender的翻译和解释,梵帝冈天主教会又开始打反殖民主义的牌。他们说,对非西方国家和对拉美国家来说,gender是一种外来的理论。在95大会期间,梵帝冈的外长声称:“行动纲领草案”中提倡“西方的家庭模式”、“西方的女性模式”,而没有考虑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妇女的价值。对"gender"、“sexuality"强调的太多,而对母道强调的不充分。”(见Franco,1998:282)然而,经过激烈的争论,95世妇会最后还是同意拉美国家的代表在所有文件上用genero来翻译gender。Genero这一概念,终於在其新的女权主义意义上,而不是在西班牙语语言家学术词典意义上被接受了。
95世妇会上拉美妇女翻译gender的成功,只是一方面的故事。另一方面的现实则是,军人统治时期对政治的控制和以“发展”为导向政治,使拉美地区30年来妇女研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大大高于对理论的研究(Ronner and Azcarate,2000)。80年代军人政权倒台之后,妇女研究才开始学科化。同时,由国外流亡回来的女权主义者们从欧美带回来妇女研究的新信息。Gender作为一个分析的范畴逐步取代了“妇女”。这一变化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巴西,由于gender概念的植入,使妇女研究逐渐走出学术界的隔离区(ghetto)。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在学术界被广为接受。而另一方面,gender也许只是一个新标签,实际上在研究内容上还是以妇女为主,但由于隐去了其赋权妇女的政治主张,则出现了学术上“去政治化”的倾向(De Lima Costa,2000)。90年代之后,理论旅行的路线也发生了变化,欧洲女权主义思想家们的到访,使拉美学术界领略了不同的思想路径。另外,女权主义刊物起的作用也功不可没,例如,墨西哥的Debate Faminista用很多篇幅介绍了意大利的女权主义思想。正是这些丰富的女权主义思想,推动了拉美女权主义的批判意识和创造性,为创造建立在本地区妇女经验基础之上的女权主义理论打下了基础(Ronner and Azcarate,2000)。
Gender概念依其在文化语言上的强势,旅行遍及世界各地。其中,既有国际妇女运动的推动,如自75年以来的联合国召开的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影响;也有以欧美为主的各种国际NOG组织和基金会的支持和导向;当然,最终还要靠各国妇女自身的选择,尽管,有时是一种被动的选择。从上述几例来看,gender概念旅行所到之处,首先带来的是翻译的“烦恼”,对gender的界定,既要与本地语言里原有的相应词汇所区分,又要寻找新的词汇来翻译这个英语概念。既有在拉美妇女运动中旅途“顺利”的范例,也有在东欧、北欧旅行受阻的个案。回顾这一旅程,虽然它要随着英美gender理论的变化而变化,但在本地语境中的重新解释则因时因地而异,旅途之中处处刻下当地文化的“痕迹”。“当地居民”在误读中创新,于挪用中重写。其中,当地妇女运动的有无、强弱、妇女政治主体性的建立与否,是进一步运用跨国女权主义理论开展学术研究及实践的关键。
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语言的,学力的,时间的等等),本文只是对gender概念在上述几个地区做了一个浮光掠影式的快照。许多重要的问题,需要做更深入地研究。写到结尾之处,仅想提出几个问题,与大家共同思考:
——消解了对一般的gender概念的追求,所看到的处处是差异。在差异中如何“对话”?在不同政治、文化、语言之间能否存在一种共鸣与回声?
——以gender的旅行路线来看,当女权主义的理论、话语和实践,旅行到另一社会实践之时,未必被看作具有同等性质的“理论”。那么,在这些理论旅行过程中,在哪些情况下,新的思想得以产生?
标签:旅行论文; 翻译专业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性别论文; 女权主义论文; 妇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