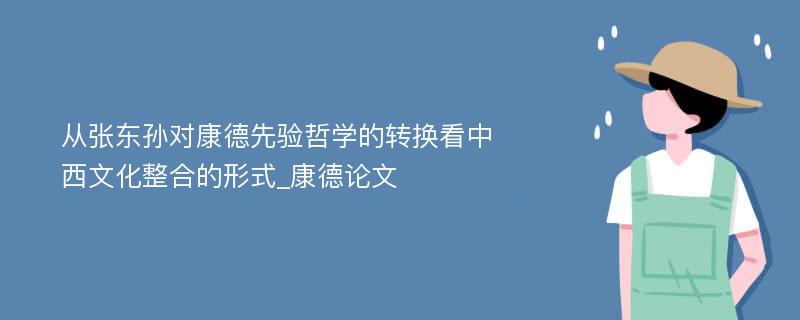
从张东荪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改造看中西方文化融通的形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西方文化论文,哲学论文,形式论文,张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哲学或多或少皆必须要回答康德所提出的问题,张东荪的知识论也经过了康德的批判哲学的洗礼。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张东荪知识论所要回答的也是康德所提出的问题:“知识何以可能?”,康德的知识论构成了张东荪知识论的理论起点,为张东荪知识论提供了基本理论渊源和架构,深刻影响了张东荪知识论的体系建构。同时张东荪对康德的“先验哲学”也做了多方面的富有启发性的批判和改造,具有与康德不同的建构知识论的思维方式和特点,在某种意义上说,使知识论从狭义向广义拓展,纠正康德知识论的形式主义的、抽象的偏颇,以多元文化为交互视域使知识论获得广义的整合与汇通,是“外来文化中国化”,也是“中国文化世界化”,这是文化融通的创造性、开放性模式。
一
知识论是张东荪哲学体系的核心。张东荪自称其知识论为“多元交互主义”知识论,他多元地、广义地、集合地、系统地看待知识的起源、结构、内容、标准等要素,这是张东荪知识论的理论特色,也是他建构知识论与康德不同的基本方向和特点。这也是张东荪自认为在哲学研究上的理论特色所在:“著者自信以往讲中国哲学的人其拿中国哲学与西方比较完全都是浅薄不堪的;而我这样的研究态度尚未曾被人采用过。亦想在研究中国哲学上开一新途径。”(注:“多元交互主义”(Pluralistic Interactionism)是张东荪本人的提法,见张东荪著《知识与文化》,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6页。)
他在《知识与文化》中说:“本书的目的在想建立一种独立的知识论其所以舆文化论相联,乃是由於注重於知识之‘集合性’(collectivity)。”“知识之有集合性是因为这一点乃向来知识论所忽略的。因知识有集合性,所以必从社会学以讨论之。”(注:张东荪著:《知识与文化》,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页。) 张东荪认为,传统西方的知识论只注重孤立地、抽象地研究知识问题,他剖析了中西方知识论各自和中西方文化和社会间的关系,指出知识是多元因素集合而成,尤其强调知识与文化、与社会各层次、要素、结构之间的多元交互关系,知识是具体的、历史的,也是多元相关的。他认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知识论,有不同的范畴论和逻辑体系,并有不同的存在论抉择和眷注。知识论总与文化系统、社会系统互为表里、交互作用,构成文化系统、社会系统的骨干和经络。他的《知识与文化》一书的基本宗旨就是以知识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为主线,建立一种以文化为视域的“广义的知识论”,对知识取广义的、多元的、集合的立场,提出了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广义知识论的问题。
他认为,要真正解决“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不能仅仅孤立地、以分析的方法抽象地、狭义地看待知识,而应综合地、广义地、实质地考察与知识相关的多元交互关系。他要求“对于知识系统采取‘多因素说’(multiple factors theory of knowledge),即谓知识不是决定於某一个因素。而却有多个因素互相作用於其中,感觉自是一个因素,而其背後的外在者亦是一个因素,概念是一个因素,而其发为指导作用的范畴亦是一个因素,不仅知识以内的感觉概念等为然,而在知识以外的文化影响又在暗中左右知识,何尝又不是一因素呢!”(注:张东荪著:《知识与文化》,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6、40、6、40页。) 他将与知识相关的“多因素”包括三个不同层次:(a)“本身的造成者”:包括感觉、概念、范畴等;即感官经验来源和知识的形式;(b)“背后的所与”:即“物自体”本身,他承认“物自体”是“所与”(given)的来源;(c)“外加的影响”:包括与知识相关的一切文化、社会、思想、历史、习俗等多元外来的因素,这三个层次的多元因素的交互作用、交互集合,共生共成,使知识成为可能。“把五个观念连合在一起,即一为知识,二为生命,三为社会,四为文化,五为价值。这五个在根本上不啻一件事。”(注:张东荪著:《知识与文化》,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6、40、6、40页。) 将多元因素综合而为一,多元地、多视域地、全面而广义地回答康德所提出的“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注重於知识之集合性,并对知识取广义的立场,在多元互动的关系中考察知识,以多元文化的“交互视域”为维度,广义地看待“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多元地、集合地建构起与康德的“先验哲学”迥异的,多元综合性的、“多元交互主义”、广义知识论体系,努力使各种对峙的思潮、方法、理论获得一定程度的整合与统一,这是其知识论的基本特色。
在思维方式上,康德和张东荪也有很大的区别,从中也表现出中西方思维方式不同的基本倾向性。
“多元交互主义”(Pluralistic Interactionism)方法(注:张东荪著:《知识与文化》,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6、40、6、40页。) 是张东荪的基本思维方式、基本立场和理论范式,也是与康德“先验哲学”抽象、分析的思维方式不同的突出表现。它贯穿其知识论、宇宙论、社会政治思想、人生价值理论等等所有思想领域,可以说是他的整个思想的基本精神。这个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有内在渊源关系,如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精神、“大易”精神等,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思维方式构成了外来文化中国化的理论视域。(注:毛翼鹏:《“多元交互主义”与文化纠偏》,《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1期。)“多元交互主义”是张东荪理解外来文化的理论视域、基本立场和理论范式。
“多元交互主义”思维方法是指将各方面因素、层次及其关系全面考究、统筹兼顾,在诸因素的多元互动,交互作用的有机系统整体中研究对象;在多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研究对象。用系统的、多元的、交互的、历时的、有机的方法看待问题,从而使张东荪的“多元交互主义”思想体系呈现出多元性、集合性、历时性和开放性等若干优点和长处。这和康德哲学的分析的、静态的、孤立的、非时间性、非历史性的思维方法形成对比。(注:毛翼鹏:《“多元交互主义”与文化纠偏》,《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1期。)
康德力求撇开文化的、社会的、现实的因素,以分析的方法、抽象的方法撷取“纯粹的”知识要素,如纯粹的感性形式、纯粹的知性认识形式,抽象地、割裂地、孤立地研究知识的各要素,企求纯粹的感觉,纯粹的时空,纯粹的、验前的知性认识形式,纯粹的、验前的范畴和理念等等,以分析的、抽象的方法力图求得纯粹的感性、纯粹的知性和纯粹的理性。而张东荪强调,不可能有纯粹的知识要素,一切都是多元相关的,是集合的。他说:“康氏的‘纯粹’与‘不纯粹’之分在我看来是没有多大意思的。”(注:张东荪著:《知识与文化》,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6、40、6、40页。) 张东荪认为,知识本身是“一种合成的产物(joint product)。整个儿的感相本来包括多元的因素在自身之中的,既包括有“所与”(the given)在内(外界对象的条理是包括于其中的);又含有感性的形式因素(时空);另外还包含有解释性因素、文化等多元的因素于其中;知性的范式和形上理念就更是如此,一切知识及要素皆是多元相关的,互为根据方可能存在,而不存在康德的所谓“纯粹”的知识的要素。康德的抽象分析法虽然是知识论研究所必需,但还是不够的,只使用这种方法就会产生理论偏颇,还应当有多元综合性的系统方法,对分析性的理论进行理论纠偏。
“多元交互主义”方法与康德的分析性方法可以互相补偿。康德的方法是豆剖法、分析抽象法;而张东荪的方法是融贯法、汇通法、循环法。其实这也是文化研究的两种互补的方法。张东荪说:“本书的目的在以文化而说明知识的性质,同时又以知识而说明文化的作用;在表面上看,好像完全是循环的。须知哲学上一切研究都不能免於循环。因为这完全是一个关於起点之问题。好像一个球体,任何一点皆可作为起点,同时亦都可作为终点。哲学上的对象其本身总是这样情形。他可以随你任择一点作起点。由这一点出发,而推广下去一直仍到原点为止。於是起点反变为终点了。换言之,即出发点同时即为结论了。”“由知识论来讲,我们处处将遇着循环。但我们不必怕循环。”(注:张东荪著:《知识与文化》,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8页。) 所谓的“循环方法”就是多元文化的“交互视域”循环中的系统、多元、集合、整体的融通法,是张东荪思想的基本方法。虽然张东荪的知识论以康德的知识论体系为出发点,为基本理论框架,但其方法却是与康德有根本的不同。虽然康德在总结西方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基础上,曾力图使知识的经验要素和先验要素内在地统一,力图对经验论和唯理论加以总结调和,但康德的方法总体上是孤立地、抽象地看待知识的各个要素,典型表现是形式和实质相分裂。张东荪则是具体历史地、以形式和实质内在统一的态度,多元交互、系统融贯汇通地看待知识问题。强调经验、历史、文化和社会的现实要素对知识所起的作用,在知识与多元文化和社会的“交互视域”上解决“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在古今中外多元文化的“交互视域”上创建“广义知识论”的一种可贵的理论探新。虽然他所理解和接受到的西方文化,其丰富程度不能与我们今日所及的相比,但可贵的是他的方法和思想方向,他的“多元交互主义”的“知识—文化—社会循环法”是中国式的系统循环法和解释循环法在知识论、文化论和社会论上的运用,某种意义上已领先于当时代的理论水平,成为中国现代思想上的空谷足音。十几年后西方系统论创始人贝塔郎菲才建立系统循环法;二十几年后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才提出“解释学循环法”。张东荪确是把握住了时代的理论脉搏,其思想方法和理论方向,超前一步,是难能可贵的,很有理论指南和思想启发作用,没有深入做下去确是个遗憾。(注:毛翼鹏:《“多元交互主义”与文化纠偏》,《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1期。)
二
张东荪的“哲学的改造”,说到底是对康德“先验哲学”改造。张东荪力图综合经验论和先验论中所包含的合理成分,建立一种以文化为视域的“多元交互主义”知识论。
在近代哲学史上,康德提出了所谓知识的“先验问题”,其实是提出了“人类知识的可能性的条件问题”,它是近代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在张东荪看来,这个康德哲学的基本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依然是现代哲学中的一个中心课题。如何能够纠正康德“先验哲学”中的偏颇,回答知识的可能性的前提条件问题?张东荪的“文化解释学”对此有独树一帜的探讨。他建立了一个“多元交互主义”文化解释学理论和视域:在多元文化的“交互视域”上,以他的“多元交互主义”方法,通过对知识与文化的交互关系的探究,寻求知识之所以可能性的前提条件。寻求知识的形式:时空、范畴和逻辑的多元的文化、社会和存在论根源,以及知识的内容与文化视域的关系。这是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文化解释学”改造:用文化的、经验的、过程的、多元的观念和范畴来取代康德的纯粹的、抽象的、不变的“先验自我”、先验范畴和先验逻辑。取消了康德主体性思想的“统觉”,而代之以“文化共同体”。在张东荪看来,人类知识的条件问题,必须在人类多元文化体当中才能寻找到满意的答案。人类必须把一个多元交往的文化视域作为知识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和基本背景。张东荪用多元文化的交互视域和它们的前理解范式来解释知识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条件,从而把康德的知识“先验问题”和知识的前提条件消解在多元文化同知识的关系问题中,这在中西方哲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康德的“先验哲学”的偏蔽。张东荪的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它的“多元文化的交互视域”作为“知识何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和基本理论视域。既从文化看知识,也从知识看文化,在两者的“视域循环”中使知识和文化共同“呈现”。
在感性论上,张东荪强调感觉的整体性,强调任何感觉总与文化、与解释相关,否认纯粹的感觉,否认康德的“杂多”。他认为,感觉本身是“整个儿的”,强调感觉的整体性。张东荪可能是受了西方完形心理学理论(格式塔理论)的影响,他不仅认为感觉不是“杂多”,本身自有条理和架构,而且是个整体,是与多方面因素“多元相关互动的”,从而是个“多元相关互动”的动态整体,这种整体性的感觉,他称之为“感相”。
他认为,来自于感官对象的“杂多”就包含有某种“客观的”形式,经验内容的大量积累和抽象必然产生概念和范畴,最后变成为知识的形式。他认为“所与”中自有“条理”,感觉一开始便有整体性,而无需“统觉”的整合作用。
因此他要“毅然决然把超越的综合能力的统觉删除。这个删除的结果在哲学上却有很大影响。就是把自我在超验界的根底去掉了。”(注:张东荪:《认识论》,世界书局,1934年,第121页。)
这样,张东荪就把先验的自我在超验界的根底斩除了,即把“统觉”作废了,目的是要完全自限于经验界,废除先验的自我,建立彻底的经验论,对康德先验论的经验论改造,其实是用“经验的自我”、“文化的统一体”来消解康德的“先验的自我”。
他反对康德孤立的、割裂的、静态的看待感觉、感性认识形式的作法,用这种“多元相关互动”中所形成的感觉的统一性,取代了康德的先验的“统觉”,用他的“多元交互主义”、“文化主义”改造了康德的感觉理论。这是二人在感性论上的根本区别。
张东荪批判康德将“综合”之所以可能的问题归于先验的“统觉”,用现实的、具体的、文化的成因来综合地建构知识之所以可能的问题。张东荪用“文化共同体”来解释知识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条件,从而把知识的“先验”的前提条件问题消解转化为文化共同体同知识形式的关系问题,这在中西方哲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他在文化系统的参照系中,用“多元交互主义”方法来改造康德的先验哲学,以文化为视域的范畴取代了康德的先验范畴,使知识论走向现实世界、具体历史过程以及多元的综合。
康德的apriori其本义是指在经验之前对认识形式和范畴的想象、抽象、建构和演绎,而并不是指天生、先天之义。这是康德关于“先验”问题思想易被人误解的关键一点。康德认为,普遍必然的知性的认识形式:范畴和逻辑并不是来自经验,而是在经验之前进行演绎所产生的,叫“纯粹演绎”,比如数学、几何学和知性的认识形式范畴等在验前的演绎。
关键在于范畴是不是人验前的纯粹的演绎和构造,范畴能不能和经验、和文化传统相隔绝?张东荪对此做了否定的回答:一方面用经验论来掺和改造康德的先验论,认为范畴最终来源于经验;另一方面又指出了认识形式和文化历史的关联。
他认为,思维形式和范畴体系是“思想轨型”和“文化轨型”(注:张东荪著:《知识与文化》,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23页。),范畴是文化的骨架和范型。思维形式和范畴体系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有着相当大的区别,是多元的、民族的、历史的。西方的思维形式并不是唯一合法的思维形式,西方知识论中的范畴体系也并不是唯一的范畴体系,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思维形式和不同的范畴体系。思维形式和范畴体系都是多元化的。知识和文化的关系在康德的先验哲学的视野之外。张东荪以“多元交互”的、“文化主义”的范畴论来改造康德的先验的范畴论,用多元的知识形式理论来改造康德的先验的认识形式学说,认为知识的“条理”、形式由多方面来源而形成:(1)外来的“所与”,是知识形式的来源。康德认为,“所与”是“杂多”,杂乱无章,没有条理;而张东荪则认为,“所与”的大量积累将显示来自客观的某些条理,构成经验性的规律。(2)文化、语言、社会、历史等外在因素,是知识形式的理论视域。(3)内在的建构:回忆、联想、比较、抽象等,也是知识形式形成的动力机制。内外在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融合而成知识的结构和知识的形式,这是多元因素互动的交互作用中建构而成的。张东荪认为,知识体系具有文化性、民族性,因而具有多元性、开放性。他反对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一元的、普遍的、封闭的知识体系。
他认为,纯粹概念(或称之为范畴)与经验的概念并没有严格的区别,经验的概念按照文化的需要可以提升为知识的形式:范畴。这只看文化的需要如何而定,都有时代的、民族的文化背景。因而范畴表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范畴表是随知识的发展而发展的。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时代的发展、文化需要的变迁等,都会导致概念、范畴的结合、变迁和损益变化。这样,他就打破了康德范畴体系的封闭性,使范畴体系多元化、过程化和开放化。
对于范畴的起源和形成,他用了“多因素说”,除了先验和经验、先天和后天的因素外,还提出了“文化需要说”。一切概念和范畴都有“文化的起源”(cultural origin)。这一点上也与康德不同。“一切无不是从当前的需要逼迫出来的。”(注: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20、20、18、20、19页。)“所谓风尚或民仪乃是需要与造作之混合物。需要是潜伏在根底上,造作则表现其外貌。前者为residues,‘隐根’;后者为derivatives‘显枝’。”(注: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20、20、18、20、19页。)需要是‘隐根’范畴是‘显枝’,把知识形式、范畴和文化、历史以及社会相联系,认为知识的形式、范畴总是文化传统根据“文化需要”自然选择、凝聚、积淀的结果。
知识论的社会文化根源是康德所忽视的。张东荪认为,“需要者,事实之母也,一切无不是从当前的需要逼迫出来的。”(注: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20、20、18、20、19页。)“解释文化须抱定那个‘需要者事实之母也’的原则。”“需要是潜伏在根底上,造作则表现其外貌……前者名之为' residues' 后者名之为' derivatives' ……这两个字我曾勉强译为‘隐根’与‘显枝’。”(注: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20、20、18、20、19页。)文化根源于社会需要,现实的社会和文化需要是“隐根”,文化和知识论的建构是“显枝”。他认为现实的社会和文化需要是文化创新的动力和目的,也构成他知识论建构的现实起点和实证基础。
他还更进一步认为,知识论与文化是内在的同构的关系。知识与文化并不是外在的因果相生的关系,而是一种内在同一的系统同构关系,但同一并不是等同,而是互为根据、互为结构、互相渗透、交互建构的关系。原先,二者并不可分,原本就是同一的,同一的过程,分之是主观上认识的抽象。
张东荪从他的文化学研究得出结论:知识体系、逻辑学体系、范畴体系都有文化的差异性,是多元的、历史的、民族的、具体的;而不是单一的、封闭的、一维的、普泛的。
不同民族的心理、思想、思维的特点不同,其文化也就不同,知识论也不同。没有一种统一的知识论。中西方文化的基本问题不同、文化取向不同,以文化基本问题、根本目标为目的的知识论也就不同,因而知识论也是多元的。在张东荪的知识论中隐含有他的“文化目的论”作为理论底蕴,不同文化所缘起的问题和目的是不同的,文化的走向、形态和特征也会有本质的不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路向,也有不同的知识论体系。他的多元的“文化主义”的知识论修正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一元知识论倾向。对不同民族文化及知识论的不同取向的合法性给以认定。
张东荪在文化比较上的成就得力于他采用的文化比较方法。他说:“比较法不是比附法”(注:张东荪著:《知识与文化》,商务印书馆,1946年,“附录二”。)。他对知识论、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比那种用西方的文化体系、哲学体系和范畴体系来“框套”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史的“削足适履”的作法要高明得多。他坚持多元的文化观,反对一元的文化观,从各文化不同的基本问题,以及由此决定的不同文化走向来研究文化,而不是用某文化(如西方文化)的体系和理论框架来比附,来强加在其它文化身上。“文化决不能有单线的发展。所以把呆板的分期而强勉加于各个不同情形的种族上乃是一个削足适履的事。”(注: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20、20、18、20、19页。)文化的发展是多元、多路向的,并不是只有单向固定的公式和若干固定程式段落。
三
张东荪力图超越康德对知识的狭义理解,建立起他的广义知识论。
康德严格限制知识的范围,划定知识的对象,严格区分和划定知识、意志、情感的范围;划定和严格限制认知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的功能和各自的使用范围。在康德知识论中,知识是被限制在狭义上使用的,仅限制于经验界,是先天综合判断,康德认为,知识一方面必须有经验内容,另一方面又必须有普遍必然的验前形式。而本体界、自我、自由等则不是认知的对象,是“不可知的”,不能成为康德所认为的“知识”;而是实践理性的对象,是“信仰”的对象。康德的知识论仅限于自然域,而自由不在康德的知识论的范围之内。康德的知识范畴仍是狭义的。
而张东荪提出“三类知识系统”理论,将知识的范围由狭义扩展到广义,将原先在严格科学知识之外的,并没有普遍必然性的常识,以及对经验总体、对自由的知识,形而上学的知识,都归并成为广义的知识中;使不同种类的思维方式获得某种形式的统一,形成多元的、广义的知识论系统,使知识的范围由狭义扩展到广义。
康德认为,形而上学的“本体”不能成为知识的对象。康德区分了知识和思想,认为,“思想一个对象和知道一个对象完全不是同一回事。”思想可以没有感性直观与之相应,而知识则除了有认识的形式之外,还必须具有感性直观作为内容。假如只有纯概念和纯形式的思维活动而无感性直观对象作为其内容,那就仅仅是思想而不是知识。由于没有感性直观对象与本体的概念相对应,所以康德认为,“本体界”不可“知”(不能成为知识),只可“思”,可“构思”、“想象”。如本体的观念:“自我”不是知识的对象,但可“反思”;上帝不是知识的对象,但也可“设想”,可设想为理想的目的或价值的悬设;“至善”也不是事实性认知的对象,但人可构想出“善”,在实践中践行“善”;同样,“美”也不是认知的对象,但人可以想象和感受“美”。康德严格区分“认知”和“思想”的功能:“认知”仅在“经验界”,才有效,才“合法”,“超验”使用则是“非法的”;而关于“自由域”中,“善”的问题,“美”的问题,则是思想、构思、设想、想象、体验、实践和创造的对象,是可以先验地构思(先验演绎),超验地构造的(即创造)。实践理性的立法和审美判断力的应用,都是一种创造。张东荪也继承了康德的这个思想,认为形而上学的对象是“理想”。在此张东荪的作为形而上学的对象的“理想”就是指“价值本体”,张东荪的所谓形而上学的对象是“理想”,就是指价值形而上学的对象:即“至善的理想(念)”。此理想如何产生、如何实现?这是价值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由康德以来,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实体本体”已被康德认为是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否的,是“超验”而非法的,而加以“解构”。实体的形而上学转向了道德形而上学。在这一点上,康德、张东荪是一脉相承的。而在此两人根本的不同是:康德的“知识”是狭义的,而张东荪的“知识”则是广义的。康德认为道德形而上学是“自由域”,不是知识;而张东荪则将对“理想”的认识(价值形而上学的知识)也当成一种基本的知识,而且是文化的根。从而形成了一种广义的知识论。
在知识的划分上,康德主分析、划界;张东荪主综合、集合。康德对知、意、情;认知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的功能和使用范围,严格区分划界,这澄清了西方哲学史许多重大的混乱和迷误,限制认知理性,限制知识,为实践理性和判断力,为自由开辟广阔的空间。这些都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伟大功绩。然而,康德将知、意、情三者分开,追求“纯而又纯的”“知识”、“纯而又纯的”的“情感”和“纯而又纯的”“意志”,这又不符合实际情况。张东荪指出:“认识不是单纯智能的作用,仍是含有情意要素,和意志作用的。因为心的活动是不可分的,所以智情意的区分完全是学术上的便利,而实际上却没有各自独立的三样东西。”张东荪比康德更近于实际。知意情、真善美是动态的统一的过程,本身就是同一个生命过程的不同方面,将其截然三分是分析过程所必需,然而截然分之却也必然要造成新的遮蔽和偏颇。张东荪认为三者原本是一个过程,将其分开只是为了研究的便利,集合地、广义地、多元地看待各种认识方式和知识形式之间的交互关系,强调知识最终要复归存在本身,要纠偏、去蔽。这些理论看法和态度都很有值得借鉴之处。
四
张东荪所处的时代是古今中外文化碰撞交汇的时代,被称为“古今中外”派的张东荪,他的思想是研究中外文化融通方式的一个范例。张东荪思想的“前批判”、“前理解”的视域,是一种“多元文化的交互视域”,在多元文化视域的交互循环当中构建他思想的基本理论视域。
外来文化的输入皆要受到本土文化基本范式和“前理解”视域的考究。使外来文化的材料和范式经过处理或改变,结合于本土文化基本范式的结构之中。每一新输入的外来文化结构都要纳入本土文化现有的基本范式体系之中。在文化交流与比较时,本土文化基本范式和视域与外来文化的范式和视域是同等重要的,因为只有当现有的本土文化基本范式和视域同化外来文化的范式和视域时,外来文化的范式和视域才能被理解。这是文化碰撞的最初始的阶段的情形。但文化碰撞接着普遍都会遇到难以将外来文化的范式和视域同化于本土文化基本范式的结构和视域之中的问题,于是本土文化开始接受或创造新的文化范式,并使两种视域融合与提升为更高的新视域,以顺应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适应新的现实与文化的需要。
文化新范式的产生,完全全盘接受的可能性极小,而更多的是通过“视域的融合”。当两种文化的范式相交流时,就会发生“交互视域”,并产生“视域的融合”,从而产生涵纳了两种视域和范式于其中的更高级的视域和范式,这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取长补短,补偏救弊,从视域的交互融合中提升并产生的更高级的新范式,来涵纳两种不同的视域和范式。
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构成了张东荪研究分析介绍外来文化的“参照系”和基本理论视域,同时外来文化也构成了张东荪研究分析中国文化的“参照系”和基本理论视域。本土文化的基本视域和外来文化的基本视域的交互融合,在多元文化“交互视域的融合”中达到“视域的融合与提升”,成为面向未来的文化创造的新起点。任何视域总有所见,亦有所弊;任何视角总有“死角”;任何方法总有其局限,有其合法性限度。任何文化总是时代的生存状况使然,有特殊性、民族性和历史性。文化真理的求得,需要补偏救弊,取长补短,在多元文化的“视域融合与提升”中“事情本身”才能全面地“呈现”。张东荪的知识论、文化比较理论和文化解释学就是在一种“视域循环”的思维形式中研究多元文化的融通的问题。
总之,张东荪对康德“先验哲学”乃至整个中西方文化所进行的现代改造说明一条文化融通进化的基本规律: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会产生“视域”交汇,形成“交互视域”,“交互视域”是不同文化之间互相理解的基础。在中西方文化的“视域交互循环”中,产生许多新的文化生长点。在多元文化视域的交互循环中,获得新思路、新范式;在多元文化的“交互视域”的循环互动中补偏救弊,择优汰劣,使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相融通。在多元文化的交互参照、竞争中,择优汰劣,提升和创新文化,使外来文化中国化,中国文化世界化。
标签:康德论文; 知识论论文; 张东荪论文; 哲学基本问题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认识论论文; 哲学家论文; 多元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