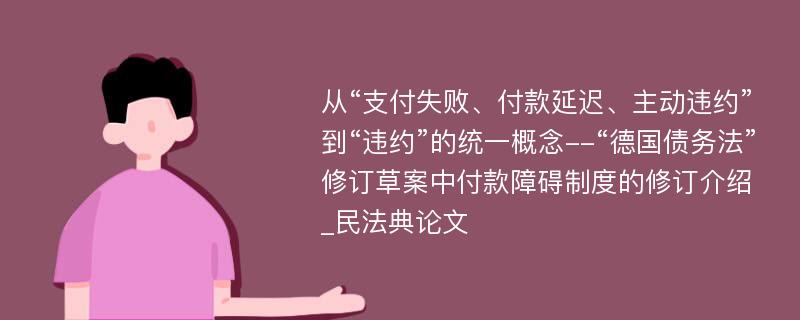
从“给付不能、给付迟延、积极违约”到统一的“违约”概念——德国债法修改草案中对给付障碍制度的修订介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中对论文,草案论文,障碍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德国联邦司法部于2000年8月4日在INTERNET上公布了关于德国债法修订的《债法现代化法讨论草案》(以下简称《草案》)①,引起了德国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原因是,如果这部计划于2002年1月1日实施的债法现代化法获得通过,即意味着现行《德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中的债法编的理论基础和结构体系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次修订事关一场深刻的改革,将是自《民法典》施行以来对债法的最大一次修改。”②
《民法典》的债法编(第241条—第853条)自1900年施行以来虽经历过近40次的改动,但基本仅集中于房屋租赁、劳务合同和店主责任等并非很重要的债法分则部分,而对于债法总则篇则几乎未有触及③。然则,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债法理论和结构中存在的缺陷日益凸显,可以说,债法的彻底修改已势在必行。
此前,债法修改委员会也曾于1981—1983年间和1984—1991年间进行过两次较大规模的修改讨论活动,虽最后均未获通过,但在法学界所引发的持久的讨论却为本次修订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和技术准备。同时,欧洲议会及欧洲理事会1999年5月25日关于消费品买卖及担保的第1999/44/EG号指令和2000年6月29日关于打击商业交易中迟延付款的第2000/35/EG号指令分别必须于2001年12月31日前和2002年8月7日前转化成德国法成为本次债法修订的契机,同时亦给本次修订草案的最终通过带来乐观的前景。
本次修订主要是在1991年修改草案的基础上进行的,内容涉及整个债法部分,除了将一些单行法纳入《民法典》之外,还包括消灭时效的重新规定,给付障碍制度中违约概念的全面引入以及关于买卖和承揽合同制度的修改等等,而其中尤以对给付障碍制度(Leistungsstorungsrecht)的修改对现行债法理论体系的影响为最大。本文即拟对该部分的修改情况予以简单介绍及评述。
二、现行法中给付障碍制度简介
给付障碍制度之所以被认为是债法的核心问题,是因为,不管是买卖合同或是其它任何类型的合同形式都必须解决当合同一方未正当履行时另一方享有何种请求权的问题。德国债法在解决此类问题时沿用了罗马法的相关制度,建立了一套相当繁杂的调整体系。《民法典》在制定时受到当时的“二元论”观点的支配,在法典中对于给付障碍仅规定了给付不能和给付迟延两种形式,直至1902年帝国法院开始采用一种不特定的补充形式,即积极违约④。
1.给付不能(Unmoglichkeit)
给付不能作为现行法中给付障碍制度的核心概念,其复杂的分类和相应的调整规范向来是掌握德国债法最大的难点之一,并也因此而饱受争议。首先,在适用关于给付不能的相关条款之前必须区分两组概念:主观不能(Unvermogen)和客观不能(subjektive Unmoglichkeit)及自始不能(anfangliche Unmoglichkeit)和嗣后不能(nachtragliche Unmoglichkeit),然后依交叉组合后得出四种情形,即主观自始不能、客观自始不能、主观嗣后不能、客观嗣后不能,予以区别对待,分别调整。除此之外,有时甚至还需区分完全不能(volistandige Unmoglichkeit)和部分不能(teilweise Unmoglichkeit)以及最终不能(endgultige Uatnoglichkeit)和暂时不能(vorubergehende Unmoglichkeit)。其次,还必须在区分单务行为和双务行为的基础上,从责任角度来进一步划分。对于单务行为,概括债务人过错原则,分为应归责于债务人的不能和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不能。对于双务行为,则需就下述四种情形区别对待:不可归责的不能、应归责于债权人的不能、应归责于债务人的不能以及应归责于双方的不能。其复杂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2.给付迟延(Verzug)
《德国民法典》中对给付障碍的另外一个支柱——给付迟延的规定要相对简单也相对实用得多。而在实践中被归为此类的也较给付不能为多。其中,“给付障碍届满,经债权人催告,债务人仍不履行给付时,自催告之时起债务人负迟延责任”(《民法典》第284条),称为债务人迟延(Schuldenrverzug);而“债权人不受领已对他提出的给付的,负迟延责任”(《民法典第293条》),称为债权人迟延(Glaubigerverzug)。
3.积极违约(positive Vertragsverletzung)
司法实践表明,《民法典》中对于给付障碍的两种类别规定远远不足以覆盖现实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其中所产生的巨大漏洞长期以来大多由成文法中未加规定的积极违约予以补充。积极违约属于在司法判例中发展出来的法官法,它主要担负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对虽然不存在给付不能或迟延但债务人对其负有的给付不当履行,即以不符合(或损害)合同规定的方式履行,而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予以调整;另一方面,使忠于合同的一方可以藉此以要求因不履行的损害赔偿或者解约权。积极违约在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但因其形式纷繁多样,且难以判定,从而构成了债法中的又一难点。
三、现行制度的缺陷分析及草案修订建议
1.以统一的“违约”概念取代对给付不能、给付迟延和积极违约的划分
迄今为止,对于债法中存在的问题,基本集中在对给付不能的批评上。其在《民法典》中的中心地位一直以来都不能让人感到信服⑤。“现行法的主要缺陷在于将给付不能作为给付障碍的两大支柱(除债务人迟延之外)予以强调突出”,对于给付不能核心地位的质疑源于1907年拉贝尔(Emst Rabel)的《论给付不能》(Die Unmoglichkeit der Leistung)⑥。对于给付不能纷繁复杂的划分以及每一不同类型均有不同的法律规范予以调整,令人望之而生畏,不仅使得法律适用难以把握,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的争议。
法律对其不同情况分别予以调整,显得详尽复杂,其实反而并不能周延。首先,对于自始不能的情况即无成文法规定,而法院对于此类案件的判决处理也历来颇受争议。其次,暂时性给付不能的规定(《民法典》第308条)仅适用于客观自始不能,而对于初始时已存在而嗣后才出现的情况却并无调整⑦。最后,给付不能一般仅限于特定债务,而对于种类债务通常则不适用有关给付不能的规定,债务人必须继续履行给付(《民法典》第279条)。而现今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买卖活动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种类买卖,就单个商品的特种买卖本身已经寥寥,而害际上被归属于给付不能的情况也确实并非很多,其适用范围越发显出其局限性。也正因如此,其复杂的分类也就愈显多余。
此外,对于主观不能和客观不能很难定义,在实践中也曾引发一系列归属性争议。但这一区分又恰恰是《民法典》第306条适用的前提,因此对该条规范的质疑历来也最多。第306条规定:“以不能的给付为标的合同无效”。该规范仅适用于客观自始给付不能,因此要求在适用前首先对给付不能的情况进行主观、客观以及自始、嗣后的区分。这条现行法中关于给付不能的重要条款源自于罗马法“不能做到的事情不产生义务”(impossibilium nulla est obligatio)的原则,但一直以来因其很难与其他责任原则协调一致且有违逻辑法则和利益的均衡⑧而受到颇多争议。另外,该条规范所规定的无效结果以及债务人的责任限于对消极利益的赔偿(《民法典》第307条)以及权利买卖时的例外处理(《民法典》第437条)均显得不够妥当⑨。“假如当事人对自始(客观)不能负有责任,则对嗣后(客观)不能情况下应同样负有赔偿积极利益的义务才是恰当的。”⑩
积极违约的概念虽然起到了重要的补遗和辅助作用,但实际上关于给付障碍,法律所规定的请求权与司法实践所发展的请求权之间并无严格的界定,且其不同的法律后果也缺乏统一一致的法学基础(11)。例如,瑕疵担保请求权与积极违约之间的相互排除在实践中即为导致纷争的源泉之一。
鉴于上述情况,本次债法修订在参考《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公约》的法律调整模式的基础上,综合司法实践过程中反映出的各种问题,对于给付障碍制度予以全面的修订,引入了国际通行的“违约”的概念,作为给付障碍制度的核心概念,以此取代对给付不能、给付迟延和积极违约的划分,“本次修订就其带来统一的给付障碍制度而言是值得欢迎的”,“其优点主要表现在免去了大量的界定性困难和争议性问题(12)。“违约”的概念虽然与《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公约》中的“违反履行”表述方法不同,但实质上并无二致。其基本特性在于仅注重对合同义务的实际违反,而对是否归责于债务人则在所不问。同时,违约的原因及其结果,特别是给付对于债务人员是自始不能还是嗣后不能亦无足轻重,不必加以区分。现行法中的第306条被取消,以客观不能的给付为标的合同亦有效,但债务人可以拒绝给付。虽然根据《草案》的第275条,给付不能对债务人的拒绝履行权仍不无意义,但即便如此,条文中并无“给付不能”(Unmoglichkeit)的明确表述,相反仅就“债务人根据债务关系的内容和性质负有努力履行的义务,而其虽尽了这些努力但仍不能履行”的情况予以调整。给付迟延的概念虽仍有保留(《草案》第283条),但也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形式予以规定。同时,违约的要件要充分覆盖积极违约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可认为是对积极违约概念的扩充:既然可将给付不能与迟延之外的障碍视作“积极违约”,那么对于因给付不能和迟延而引起的履行障碍又为何不可以视作“违约”呢?
总之,违约概念的引入使人们从此告别了对于给付不能、给付迟延以及积极违约的繁琐分类,大大方便并简化了德国债法中给付障碍制度。
2.确立履行期限,确保实际履行的优先适用
在德国法中,债权人普遍可以行使其履行请求权,除非实际上已不可能履行。这种对实际履行的过分追求在实践中表现得差强人意。很多情况下,债权人真正所需要的是对其财产重新获得自由处分权,而非继续履行(13)。基于这种考虑,本次修订汲取了《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公约》中的做法,以设立履行期限的方式来保障实际履行的优先权。债权人只有在事先给债务人确定了一个要求履行的期限,而债务人在该期限内未履行时,债权人才有可能主张履行请求权之外的其它权利,如损害赔偿请求权(参见《草案》第283条、第326条、第542条第1款、第634条和第635条),而债权人一旦提出以损害赔偿来代替给付的要求,其要求履行给付的请求权即不复存在(《草案》第282条第4款)。如此一来既确保了实际履行原则,又使债权人不必徒劳地固守其改造请求权。
3.损害赔偿权的全面适用
现行法中对于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散见于对于给付不能和迟延的各种规范中,且适用范围较为有限,如因货物瑕疵而解约或降低价金时通常不产生损害赔偿请求权。债法中对于损害赔偿权的狭隘规定一直以来也是法学界讨论争议的焦点之一。因此,《草案》在第280条中统一规定了债权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前提为债务人违反债务关系产生的义务。据此款规定,除非义务的违反不可归责于债务人,否则任何形式的违约均可导致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对违反的是何种义务并不加以区分,即不管债务人违反的是主义务还是从义务,是给付义务还是保护义务,是履行不当抑或根本未曾履行均在所不问。基本说来,该《草案》中对于损害赔偿的规定较之现行法要更为明确清晰。
4.合同解除权与归责情况相分离
《德国民法典》中对于债权人享有的另一项权利——解约的规定存有诸多不足。而针对这些不足之处,《草案》中分别予以了修订。
首先,现行法中关于解约权与损害赔偿不能同时使用的原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即债权人选择了解约就不能再要求因不履行而遭受的损害赔偿(参见《民法典》第325条和第326条)。对此,《草案》第325条规定:“债权人在解除合同后可以要求债务人赔偿因不履行合同而遭受的损害。”这表明,修改后的债法将允许解约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同时使用。但解除原因不可归责于债务人时不产生损害赔偿请求权(《草案》第325条第2款)。
其次,按现行法,仅当债务人应对不履行负责时债权人方可解除合同。债务人的过错原则对于债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不无意义,但如果同样适用于解约权则似有不妥。通常说来,解约权只应取决于债权人对于尚未履行部分的给付是否仍有利益存在,如果没有,则债权人就应该可以解除合同,即便债务人对不可履行的给付不负责任。与此相对,《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公约》规定,买方的解约权不以卖方的过错为前提。本次债法修订中即采用了《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公约》中的这一做法,使债权人的解约权仅以债务人违反义务(违约)为前提,但轻微违反义务(违约)时除外(《草案》第323条第3款第1项)。
此外,本次修订还拟将其他一些司法判例学说纳入到法典条文中,如缔约过失原则(《草案》第241条第2款、第305条第1款)、交易基础丧失原则(《草案》第307条)及因重大原因预告终止(《草案》第308条),但该草案对此仅做了笼统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尚有待于司法判例对其做进一步的发展适用。
四、结语
德国债法的此次修订(草案)在借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公约》的一些法律调整模式基础上,在给付障碍领域因入“违约”概念统领全局,从而屏弃了现行法中给付不能、给付迟延和积极违约“三分天下”的格局,使得法律规定更趋统一、明朗、简洁、易懂,同时亦降低了实物部门在处理个案时适用法律的难度。此外,修订后的债法将更趋向于与国际通行做法的接轨,尤其是与《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公约》保持一致对于德国国内的法律适用具有重要意义。很难设想,在一个国家通行两套不同的法律调整系统模式将会何等棘手(13)。
当然,对于给付障碍制度的彻底修改,使其与传统的调整模式和渊源相割裂,必然会带来大量的法律适用的新问题,而且由于统一的违约构成要件含义太过宽泛,如保界定亦待进一步的探讨。
历经百年的德国债法确实已显得陈腐过时,甚至千疮百孔,急需一些新鲜的血液的注入。此次修订(草案)虽然并无多少理论上的新意——违约、缔约过失、交易基础丧失等理论早已在全世界普及适用——然而对于古老且素以繁杂的德国法而言却不啻于一项现代化的革命。而此次的修订草案是否可以借着欧盟指令本土化的东风藉以通过,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邮编 210093
----------------------------------------
注释:
①http://www.bmj.bund.de/ggv/eschurmo
②⑤(12)Heinrich Honsell,Einige Bemerkungen Zum DiskusssionsentwurfeinesSchuldrechtsmodernisierungsgesetz,JZ 2001-1,S.18;2,s.19.
③Dieter Medicus,Schuldrecht I,Allgemeiner Teil,5.Aufl.s.21
④罗卜特·霍恩等:《德国民商法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
⑤⑥⑦⑨(13)Entwurf(《草案》),S.307;S.199、S.176、S.183
⑧vgl.Munchner/Thode Kommentar zum BGB.§ 306,Rd3,3.Aufl.
⑩vgl.Palant BGB,§306,57.Auf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