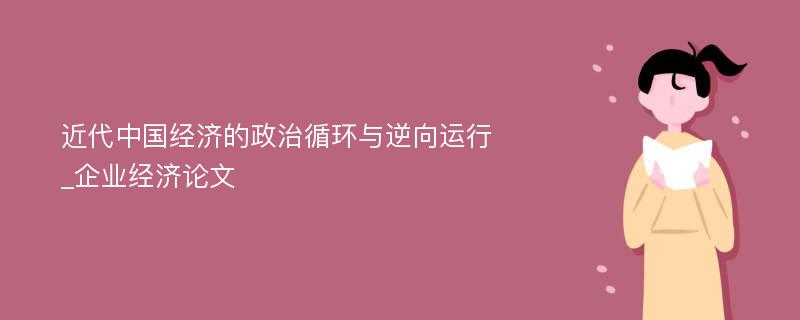
中国近代经济的政治性周期与逆向运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性论文,周期论文,中国近代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1)04-0063-12
一 政治性周期
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 or trade cycle),也可译作经济循环或商业循环,意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在经济分析中,每一个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经济扩张(繁荣,prosperity)阶段、紧缩(萧条,depression)阶段、危机(crisis)阶段和复苏(recovery)阶段。或者分为两个阶段和两个转折点,即把危机阶段作为由繁荣转向萧条的转折点,把复苏作为萧条转向繁荣的转折点。(注:参阅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93页。)
以往的经济周期理论都把周期性的经济波动看作是产出水平围绕一条已经确定的轨迹的偏离,是对正常状况的偏离。20世纪80年代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提出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一反以往的“偏离”说,认为经济波动是自然的,是经济增长的有机阶段,而不是对确定轨迹的偏离。他们认为经济周期的每一个阶段,无论是繁荣还是衰退,都是经济的均衡状态,政府无须干预。(注: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西方的经济周期理论流派繁多。二战以后,西方学者把众多的经济周期理论综合概括为两大类别: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外生的和内生的)理论。外部因素理论认为,经济周期的根源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之外的某些事物的波动,如太阳黑点或星象、战争、革命、政治事件、金矿的发现、人口和移民的增长、新疆域新资源的发现、科学发明和技术进步等。内部因素理论则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内部的某些因素(如投资、消费、储蓄、货币供应量、利率等)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运行机制来解释导致社会经济周期性循环往复上下波动的原因。而萨缪尔森、希克斯等人则建立或完善了内外因素相结合的理论模型。此外,波兰的卡列茨基于1943年提出“政治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西方政府在实施反经济周期的政策时,由于迁就大企业家利益的政治立场,常会发生干预不当,反而加重了经济周期的程度。(注:参阅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第900-901、919-923页。)
将西方的任何一种经济周期理论生搬硬套于近代中国,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近代中国处于一种畸形的社会形态之中,中国的经济缺乏自主性,还没有形成自主的增长轨迹,就经济因素而言,还不足以形成决定周期的主要内因。因而,一些学者主要用外部因素来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周期,如:一战时西方国家减轻了对中国的经济压力,中国经济就发展得较快;战后西方国家重新加重对中国的经济压力,中国经济就陷于停滞。
但是,我们在深入考察了影响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后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内部因素(即国内政治因素)是十分重要而决不可以被忽略的。也就是说,政治因素在中国近代经济周期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文提出的“政治性周期”,是指像近代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由政治因素所引起的经济制度、产权结构、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周期性变化。这一周期由四个阶段构成,即: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官营经济发展和政府规模膨胀阶段、政府维持成本提高和财政困难阶段、扶持民营经济或失控阶段。然后经战争改朝换代以后,又以强制性变迁开始新一轮的周期。
第一阶段:强制性制度变迁。林毅夫将制度变迁分为两种类型,即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诱致性变迁指的是一群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注: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4页。)笔者经过对近代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史的比较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国家的强制性变迁是建立在诱致性变迁的基础之上的,而强制性变迁完成以后,又能促进诱致性变迁的深入开展;近代中国的强制性变迁不是建立在诱致性变迁的基础之上的,而是政府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在强制性变迁完成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压抑诱致性变迁的重新发生。中国传统政府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其“变法”总是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入手。晚清的“洋务运动”,民国初年的建立国家银行体系和各经济领域的国家主义、中央集权主义倾向,(注: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5-1581页。)1935年南京政府的金融改革,都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洋务运动是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企业制度引入中国的一次尝试,民初的国家主义倾向是希望建立由政府控制的经济体系,1935年南京政府的金融改革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第二阶段:官营经济发展和政府规模膨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直接结果,就是官营经济发展。官营经济指的是由政府控制的经济形态,晚清的官督商办企业,政府虽然不是投资人,但仍能实施对企业的控制。新式经济,包括新式银行发展起来,政府以为自己的实力强了,就扩张自己的规模,特别是扩充军队的数量。另一方面,经济事务的日益复杂、新税的开征,也使得政府必须扩大自己的规模。但政府规模的这种扩大,基本上都是自我服务型的,而不是服务社会型的。扩张军队是为了争权夺利,收税敛财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至于如何为经济的稳定和持久的发展服务,则并不是它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第三阶段:政府维持成本提高和财政困难。由于政府规模膨胀和军阀间为了争夺统治合法性的战争,政府的维持成本越来越高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式经济的存在和收入来源的开辟不仅没有促进传统政府本身质的改良,反而刺激了它们扩张军政势力的欲望。军、政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在军阀战争的情况下,政府的维持成本远远超过了收益,财政困难越来越突出。政府在掌握货币发行权的情况下,就会不顾一切地通过各种形式不加限制地发行货币,包括政府向国家银行无限制透支、滥发纸币等,将国民财富最大限度地聚敛到政府手中,其用途却是破坏社会福利的战争。
第四阶段:扶持民营经济或失控。第三阶段会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基本没有发生内战,政府虽然财政困难但仍维持着统治。严峻的局面使政府不得不作出重大的政策调整,即放弃对新式经济或主要产业部门的政府垄断,因为这种垄断的成本太高,而其成果对国家而言并不明显。这时的政府就可能转而采取扶持民营经济的做法。清末新政就是这样。第二种情况是发生了军阀内战,政府的合法性虚悬,原先政府控制的经济部门渐渐脱离政府,转向商业化经营。在政府失控或政府合法性虚悬的情况下,民营经济自然也能获得长足的发展。这是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情形。第三种情况是发生了国共战争,原先控制国民经济要害部门的国民党政府垮台了。在第三种情况下,这第四阶段也就不存在了,周期提前结束。
需要指出的是:只有经过政治性周期第三个阶段而仍能掌握政治权力的政府才会主动采取扶持民营经济的政策。在这一点上存在一条“隔代遗忘”的规律,就是在战争中上台的新的统治者,他们不会记得前朝周期变化的教训,而又会谋求政府对经济的全面控制,除非能力过弱而政府合法性虚悬。
政治性周期有长短之分,有完整和不完整之分。晚清的周期较长,进行了近半个世纪,而北洋军阀时期的周期较短,袁世凯死后,政府控制力急剧下降,体现国家主义倾向的强制性变迁成果很少,反而出现了一段失控期。而南京政府统治时期则缺少第四阶段。
政治性周期并不是决定中国近代经济长期趋势的唯一因素,西方国家的经济周期因素和本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在1935年前的近一个世纪中,中国社会是处于一种对外不平等条件下的经济自由化状态,外国资本进出自由,货币兑换自由,政府干预极少,中国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有机的补充性市场。西方国家的经济波动会通过世界市场的传递作用波及中国。19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波动牵连一些当时在中国的洋行破产倒闭。1910年世界橡胶价格的剧烈波动造成中国外商橡胶公司股票的崩盘,连环地拖累大批钱庄倒闭、大批企业破产、大批工人失业。20世纪30年代初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使得中国市场物价低迷、需求萎缩、企业不景气。另外,中国新式经济尽管稚嫩,但仍会遵循某些内在的规律发展,外国在华资本的经营活动就包含在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近代大部分的时间内,外国在华资本受中国政治的直接干预很小。本文所称“中国近代经济”,是指由中国人经营的官办及民营经济。
政治性周期、世界市场经济周期波及和本国经济因素三者的交互作用会产生三种效应,即:叠加效应、抵冲效应和替代效应。
(一)叠加效应。当政治性周期、世界市场因素和本国经济因素中,至少有两方面的因素有利于经济发展时,就会产生叠加效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几年通常被称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叠加效应。人们一般把这段时期中国经济的较快发展归因于西方国家减轻对华经济压力这一外部因素。这一因素确实是存在的,但不是唯一的。从政治性周期来看,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一次大战的后半期及战后几年,第四阶段的政府失控是相当明显的。这为中国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机遇。这种有利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叠加在一起,产生了非常良好的效果。
(二)抵冲效应。所谓抵冲效应,就是不同因素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正负影响相互抵冲,使最终结果表现得比较缓和。中国经济的政治性周期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周期显然是很不相同的,当中国经济在政治性周期中处于上升期,而西方国家处于大萧条期时,正负影响会通过抵冲而使最终结果变得不十分典型。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这时虽然南京政府已经建立,但军阀间的战争仍在继续,南京政府还须解决它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它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以及还腾不出手来对中国经济实施新一轮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经济仍在继续其以民营经济为主的较快的发展,这种内部周期的上升势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外部周期下跌势头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在这种抵冲效应中,中国经济的银本位因素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根据中国(上海)与英、美等国批发物价指数比较,(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8页。)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大萧条中,中国的批发物价与西方主要工业国相比,其指数的下跌整整晚了3年,而且下跌所持续的时间较短,跌幅也远低于西方国家。1929-1931年间,在实行金本位货币制度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银价的跌落甚至比一般商品的幅度更大(注:谷春帆:《银价变迁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3页。)。中国银元对美元的兑换率从1929年起大幅度下跌,若以1929年的汇率指数为 100,1930年降至73,1931和1932年更降至54,即使是中国白银外流最厉害的1934年,汇率指数也只回升到83,1935年为88(注:《国际联盟统计年报》,1932-1933,第168页,1937-1938,第225页。)。那就是说,1933年起银价回升,也没有超过1929年的水平,无论是对美元还是对英镑的汇率都是如此(注:Tang Leang-li,China'sNew Currency System,1936,pp105-106.)。银价相对金价和外汇大幅跌落,这对实行银本位货币制度的中国来说,构成了一道天然的进口贸易屏障,阻遏了危机中的西方列强向中国倾销商品。所以中国的市场萧条出现得晚得多,也缓和得多。
(三)替代效应。政治性周期在它的前两个阶段,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决定一切的,它在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时,是不会考虑经济发展内在的规律的。政治性周期的强制性变迁替代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内在需求。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的资本集中趋势已经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在金融业方面,不仅表现为若干银行的合并,以及银行对保险业的投资和控制上,还更细微和更广泛地表现为金融业内部的相互投资上。甲银行或甲银行的董事长投资于乙银行,并在乙银行的董监事会中占有席位,乙银行或乙银行的经理在甲银行投资,并在甲银行的董监事会中占有席位。这种内在的变化促使金融业向联合、联立及合并的道路发展。仅以在中国金融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金城银行为例,就可清楚地看出这一趋势。金城银行是一些军阀、官僚在1917年投资创办的,1917年实收资本50万元,其中军阀、官僚的投资占90.4%,1919年收足200万元,军阀、官僚投资仍占82.1%,而到1927年,这个比例下降到50.5%,1935年更下降到16.9%;而金融业持有的股份,则由1927年的25%上升到1935年的35.7%,这里既有盐业、中南、大陆等银行持有行股的增加,又有王轶陶、胡笔江、任振采、常朗斋、马式如等银钱业资本家个人所持股份的增加(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前言,第7页,正文,第243-245页。)。在金城银行的董监事中,有盐业银行总经理兼董事长吴达诠(吴还是四行储蓄会、四行准备库的负责人,兼中国银行的董事),有继吴达诠为盐业董事长的任振采,有中国银行总经理兼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有任过大陆银行董事长的四行储蓄会副主席钱新之等。银行界的相互投资和兼职(注:关于银行界的相互兼职情况,笔者根据《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1936年)和沈雷春的《中国金融年鉴》三本书中各家银行的董监事名单,并参阅《银行周报》、《申报》等资料,汇总了详细的资料,因限于篇幅,这里从略。),以及在金融业务的相互配合,为今后银行的联立、合并,为银行资本的集中奠定了基础。也可以说,这是银行资本集中按其固有规律发展的第一步。另外,银行家和企业家的相互投资和相互兼职也同样成为一种趋势性的现象。
这种集中趋势是在经济生活中自发出现的,它的主体是私人资本。但这种发展趋势却为政府发起的另一种集中趋势所替代。(注:参阅杜恂诚:《抗战前中国金融业的两种集中趋势》,《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政府发起的金融集中由政治性周期的第一和第二两个阶段所体现,它完全无视私人金融集中所取得的市场成果,而令其归于夭折。在政府对金融机构和货币发行实行垄断,对金融市场和金融规则严加管制,对民营金融业施行严格管制和限制的条件下,民营金融谈不上自主发展,更无趋势可言了。
政治性周期、世界市场周期波及和本国经济因素三者的交互作用中,哪一种因素起主导作用,要视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形而定,在上述替代效应发生时期,政治性周期的作用是最重要的。
二 制约政治性周期的制度性变量分析
西方学者对于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各有不同,(注:参阅奥斯特罗姆、菲尼、皮希特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本文根据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就某几个在政治性周期中起重要作用的变量因素作一分析。
影响制度供给的变量因素主要有四个,它们是:产权制度、宪法秩序、政府能力和意识形态。这四个因素决定了政治性周期前两个阶段的走势。
一,产权制度。表面上看起来,中国的土地私有产权制度形成很早,但细细琢磨,这种私有产权制度很不完整。王家范教授认为,在中国古代,“国家主权是最高产权”,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历史特征,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侵犯和变更私有产权。(注:王家范:《中国传统社会农业产权辨析》,《史林》1999年第4期。)
产权是一组权利,包括对资产的使用权、收益权、改变资产形态和实质的处分权、以双方一致同意的价格把所有或部分以上三项权利转让给他人的权利。平乔维奇认为:“最后两个方面是私人产权最为根本的组成部分。它们确定了所有者承担资产价值的变化的权利。”(注:平乔维奇:《产权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而中国传统社会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的“不充分、不独立、不完全”恰恰就是体现在产权的这后两个方面。这种产权制度的缺陷不会因为一场鸦片战争和西方企业的进入而嘎然而止,而必然会向近代延伸。清政府倡办的一批所谓“官督商办”企业,就是产权关系很不清晰的,这些企业虽然都是由私人投资创办,但处分权、转让权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就收益权而言,企业也要以“报效金”等形式满足政府的需求。有的企业,如电报局,经营不好时让商人“民办”,经营好了又收回官办。
从北洋军阀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只要政府认为是它所需要的,就可以任意将私有产权变为政府产权(或虽企图这么做但因控制能力不够而作罢),而且转让的价格绝对不是公平的价格,而是一种由政府单方面决定的、掠夺性的价格。例如南京国民政府在1932年仅以相当于净资产总值六分之一的价格将民营的轮船招商局收归国营。1935年南京政府决定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强行增加官股、委派代表官方立场的总经理时,商股股权是占绝对多数的,而且商股股权是一致反对政府改组两行的决定的,但最终还是政府说了算。如果没有“政府权力是最高产权”这把达摩克利斯剑,南京政府是很难推行1935年那场强制性金融制度变革的。
二,宪法秩序。宪法稳定,有利于诱致性变迁,而宪法(或国家的根本大法)不稳定,则有利于强制性变迁。中国古代只有封建专制主义的“祖宗之法”,而没有基于民主思想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宪法。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清末的宪政运动都失败了。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搞了一个《临时约法》,确立了“主权在民”及一系列以西方国家宪法体系为参照系的宪法原则。它在思想认识意义上是划时代的,但在实践意义上,只是一个纸面的东西,不能象征真正的、现实的“宪法秩序”。袁世凯任意修改约法,实行总统集权。以后的军阀执政者又多次对“宪法”进行随意改动。国民党执政初期以“训政”代替宪法,把人民大众看作是“不知不觉”的“襁褓中的婴儿”,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保姆”。也许是为了回应人民大众对训政制度的不满,国民党立法院于1936年5月5日通过了一部宪法草案,通常称作“五五宪草”。其所确定的中央政制是总统独裁制,集权程度之高是空前的。“五五宪草”规定了政府有“节制”私人资本和私人产权的权力,为国家资本的一统天下奠定法律基础。宪草第121条规定:“国家对私人财物及私营业,认为有妨害国民生计之均衡发展时,得依法律节制之。”(注: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页。)什么叫“妨害国民生计之均衡发展”?其解释权在政府。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均衡发展无从谈起,因此政府可以节制一切。事实上南京政府后来也是这么做的。这样的法,不管字面上打扮得如何靓丽,其实质仍然是专制主义的法,而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宪法。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发动强制性制度变迁,推行官办经济,同时扩张自身规模。
三,意识形态。中国老百姓历来有好皇帝、清官能够代表国家利益和全民利益的观念,流传着许多好皇帝、清官为老百姓平反冤屈的故事。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也坚信革命党人如果掌权,其政权一定就是代表全民利益的。孙中山说:“要革命成功以后,不受英国、美国现在的毛病,多数人都有钱,把全国的财富分得很均匀,便要实行民生主义,把全国大矿业、大工业、大商业、大交通都由国家经营。国家办理那些大实业,发了财之后,所得的利益让全国人民都可以均分。”(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2、895页。)
“均贫富”是中国贫苦大众多少代、多少年来一种朴素的愿望,也是历次农民起义的口号。一些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统治权的古代政治家也常发起诸如“均田”、“限田”、“抑兼并”等措施来遏制地产和物产的过分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在这时,“国家权力是最高产权”则体现了它无比的权威。尽管这触犯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非既得利益者的大众是能够接受政府对私有产权的侵犯和对私有产业的限制的。这种情况在确立了私有产权制度的西方国家不可想象。
四,政府能力。国家的根本大法多变,私人产业和私人产权得不到保障,当然不利于诱致性变迁,而有利于强制性变迁,但如果政府的能力很弱,则强制性变迁还是不会发生。如果政府是很弱的,那么它的控制力就一定十分有限,它就难以做到“节制”私人产业和私人产权。在这方面,北洋政府时期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政府的财力和行政控制力十分软弱,它对原先名份上该它控制的企业和银行都控制不住,当然就更谈不上去控制普通的民营企业,去控制市场和控制国民经济。这样,通过控制经济去推行强制性变迁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当然,这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而言的,对于西方国家,推行强制性变迁不需要由政府直接控制市场和经济,而是主要通过法和间接机制进行。南京国民政府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基本完成了政治的统一,因而政府的行政控制能力大大提高了。但行政控制能力的提高也意味着行政控制成本的提高。行政控制成本包括行政经费、军事开支在内,而尤以后者的需求最大。如果不能满足行政控制成本的需求,那么政府的行政控制能力就会大打折扣。从1929年到1937年,南京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都要占到每年财政支出的20%-30%。赤字的弥补主要靠发行国内债券和向银行借款。但在以信用为基础的金融制度中,政府如果只借不还的话,信用丧失,以后就再也借不到钱了。要是借不到钱,政府就维持不了庞大的局面。因此,改变原先的自由市场金融制度就成为维持政府控制能力的必要环节。在这一点上,政府能力的提高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互为因果。
影响制度需求的变量因素主要有两个,即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技术进步。这两个变量主要对政治性周期的第四阶段起制约作用。
一,市场规模的扩大。民营经济的发展条件中,市场的发展潜力因素十分重要。这里所说的市场规模扩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国内市场的扩展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本国企业的发展。
中国自五口通商开始,对外贸易便有了持续的、长足的发展。若以1913年的进出口贸易总值指数为100的话,1864年仅为9.7,可见在半个世纪之中有相当的发展,而1931年这一指数更增至240.7。(注: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1840-194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337页。)1932-1934年中国国内市场因受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出现过一度的困难,但从长期趋势看,中国国内市场的扩展是持续的。国内市场覆盖面不断扩大,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天津为例,1906年天津的进出口商品流通的势力范围,不仅与上海等通商大城市密切相关,而且深入许多省份的广大区域,甚至包括东北西部、蒙古和俄国的西伯利亚。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五省人口共计1.15亿人,而纳入天津通商范围的人口达0.64亿人,约占55.4%。(注:《商务官报》1906年17期。)天津通商范围的扩大标志着新式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相反,凡不纳入进出口商品流通渠道的旧式商业则呈凋敝景象。如在以盐商为首富的江西,进出口商业并不发展,至清末则各“商埠寥落之形见”。(注:《商务官报》1907年1期。)
随着国内市场的开拓,农产品商品的绝对量和商品化程度均有大幅提高。最主要的农产品是粮食,其商品化率1840年约为10%,1894年约为16%,1919年约为22%。(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页。)
根据笔者的测算,1933年中国国内市场商品流通量达到108.6亿元,而1933年全国所能支配的国民所得是200亿元,这说明国民生产的商品化程度已有过半之势,达到54.3%。(注:参阅杜恂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流通量的一个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巫宝三主编:《中国国民所得,1933》,中华书局1964年版。)
企业发展也是市场规模扩大的重要内涵。这一阶段企业数量增加,规模扩大,本国企业的发展以民营企业为主,并从中涌现出一批比较优秀的企业,如荣氏企业、刘鸿生企业、“南三行”、“北四行”等。企业的成长为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和市场容量的进一步扩大奠定了基础。
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会促使企业规模的扩大,会促使企业制度的提升,会促使贸易方式的改变。技术进步与市场规模扩大一样,给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和机遇。
鸦片战争后西方企业的进入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技术进步,但首先表现为商品流通方式的进步,包括新式商业企业、运输企业的兴起,随之就提出了金融服务的创新,因为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不能满足进出口商品贸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第二次技术进步发生在1870年到1871年前后。1870年苏伊士运河通航,把欧洲到中国的航程缩短了一半以上。绕道好望角的旧航程,需时120天,通过运河,只需55天至60天,快的乃至六个星期,就能完成一次航程。而新式的使用蒸汽动力的轮船又代替了原先使用风力的飞剪船,又加快了航行速度。1871年,从伦敦到上海和从伦敦到香港的海底电缆先后贯通,欧洲与中国间就此建立了电讯联系。航运和电报的富于革命性的技术进步,使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条件和贸易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外国人到中国来做生意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巨额资本,因而出现了大量的小洋行,大洋行的垄断地位削弱了。而为小洋行服务的外国银行的势力上升,取代了原先大洋行在金融业方面的地位。
第三次技术进步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前20年。这次技术进步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这次技术进步的第一波就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清政府在19世纪下半叶发动的所谓“自强”、“求富”运动,从国外引进设备和技术,办了一批新式企业。尽管最终这批企业中成功者极少,问题多多,但如果将洋务运动看作是中国技术和产业进步的一个环节,则它的积极意义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不能因为甲午战败而将洋务运动一笔抹杀。
第三次技术进步的第二波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外国对华直接投资。日本从马关条约中获得了在华设厂权。西方列强对于这种权利的获得,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表现了极大的侵略性,而从经济意义上讲,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展开,推动了中国产业的技术进步。
第三次技术进步的第三波在时间上可能与前两波有一定的交叉,那就是使用新式生产技术的民营制造企业的兴起。民营企业的发端虽然很早,但大型民营企业的出现则比较晚,是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转变产业政策,收缩国家资本主义,鼓励民营以后的事。清末10来年清政府有意识地放松对产业的控制,北洋军阀政府想控制经济却又明显地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客观有利因素,中国的私人产业蓬勃兴起。这些产业中凡是比较大型的企业,一般都从西方国家进口机器设备,引进技术,雇用学成归来的留学生,甚至雇用洋工程师。
在政治性周期的第四阶段,民营经济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仰赖于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市场机会和发展空间。
三 强制性变迁的逆向运作
一个非常有趣而耐人寻味的现象是近代中国强制性变迁的逆向运作。这是发生在政治性周期第一、二阶段的现象。逆向运作是相对于顺向运作而言的。所谓顺向运作,是指事物按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顺序渐次展开,循序运作。而所谓逆向运作,则是指人们为了求得发展速度或某种特殊的利益,跳过事物低级和简单的基础发展阶段,而致力于“高级”和“复杂”的经济事务形式,尔后却从“高级”向低级,从“复杂”到简单的逆向而行。这里之所以给“高级”、“复杂”等形容词打了引号,是因为这类形容词所界定的近代中国的实际情况,往往只是经济形态的形式,而非实质内容。
(一)主导体制的逆向运作。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市场一直起着主导的作用。当经济生活日趋复杂以后,政府的干预渐渐增多,甚至在某个特定时期可能表现为主导力量,但这样的主导毕竟是短暂的,而且必定是既有市场主导的积淀在前,又有重新过渡到市场主导的结果于后。
中国近代经济的主导体制,撇开外资因素不谈,与西方国家相比,表现为一种逆体制,即从一开始就强调政府主导。洋务运动就是清政府主导的产业运动。在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对于纺织、轮运和主要的矿业采取由国家直接控制的政策。这种控制表现为对洋务企业的控制,同时表现为禁止华商私人投资设立与政府控制同类型的企业。根据笔者对1874年到1883年间民用工矿企业经营性质分类统计,就产业而言,不说洋务运动前期的军事工业一律官办,即使是后来的民用工业,清政府明显处于主导地位。(注: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中国本国的新式银行设立较晚,甲午战败以后,清政府对私人投资敞开了大门。但即便如此,中国最早的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也是政府创办的,清末最重要的另两家银行——交通银行和户部(大清)银行——也都是政府创办的。
在每个政治性周期的前两个阶段,政府都会成为经济生活的主导力量,以后才有可能从政府主导过渡到市场主导。
(二)经济结构的逆向运作。经济结构的逆向运作包含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政府投资并不是为了补充私人投资的不足,或出于提供外部性很强的公共物品的需要,而是投资于与民争利的行业,并禁止私人进入这些行业。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曾独霸利益最为显著的棉纺织、矿业和本国轮运业,为了维护上海织布局,规定:“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同时也禁止外商设厂。(注:《申报》1882年8月24日、9月2日、5日、16日。)1882年李鸿章禁止叶澄衷设立广运局,所谓“不准独树一帜”。(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航政编》下册,1935年刊印,第222页。)南京政府独霸金融业是更高层次上的与民争利。第二层涵义是政府从投资于重矿工业开始,渐次向轻工业发展。洋务运动初期,政府所投资的军火工业都是重工业,以后又在技术、资金、市场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长年经营办理无成效的汉冶萍企业,受累颇深。南京政府则从资源委员会的重工业开始,抗战胜利后接收敌产,才有中纺公司等公营轻工业企业的经营。1936年度,南京政府拨交资源委员会建设经费1000万元,1937年度则为2000万元。(注:宁档28-2409。)1937年3月,资源委员会制定了一份“重工业五年计划经费表”,经费预算总额为27120万元,其中国库应筹部分为11831万元,信用部分为15289万元。(注:宁档28-5965。)资源委员会计划建造一大批钢铁、飞机制造、冶炼、采矿、机电、化工等重工业企业。(注:宁档28-5965、6223、2360、110、8260。)
(三)发展层次上的逆向运作。发展层次上的逆向运作,表现为基础尚未奠定的情况下,把高级阶段的事情提前来做,顺序出现颠倒。譬如在金融领域,表现为先直接金融,后间接金融;先中长期金融,后短期金融;先财政性证券,后商业性证券。
晚清、北洋、南京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热情,除了向其控制的国家银行借款之外,就是发行中长期政府债券了。政府公债的发行和交易,构成了中国近代证券市场的主体。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上海的华商证券交易所中,每日成交额常在1000万元以上,最高达到每日6000万元。(注:上海市档案馆编:《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相关各页。)
1898年清政府发行的“昭信股票”,是中国近代第一笔政府公债,期限原定20年,但发行很不成功。进入民国以后,政府发行公债的势头越来越猛。从1912年发行624.8万元、余额624.8万元,到1939年发行12亿元、余额42亿元。(注:《上海之金融市场》,1941年版(编者及出版单位不详),第376-377页。)
此外,交通、经济两部所经管的公债年末总余额,1924年末为500万元,1926年末为1300万元,1936年末增至12200万元。(注:《上海之金融市场》,第377页。)
在中国近代的证券市场上,华商企业的股票很少,除若干特定的时间外,交易也非常清淡,常处于有行无市状况。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因为华商企业的总体素质较差,二是因为社会动荡不定,长期金融容易因经济和货币的不稳定而受到伤害,因此难以在市场环境下自发地得到发展,三是政府公债的挤出效应。按照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金融业的发展总是从间接金融发展到直接金融,从短期发展到中长期,从商业性证券发展到财政性证券。近代中国政府的逆向运作,是与他们把政府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分不开的。
(四)营运机制的逆向运作。营运机制上的逆向运作,表现为政府过多地依靠行政控制,而淡化市场机制。南京政府在1935年前后的金融改革中,把当时西方世界最先进的金融制度形式搬到中国来,如实行脱离金属本位的纸币制度、中央银行制度等。由于有力的行政倡导,这些制度很快建立起来,但政府完全用行政手段来运作这些制度,出现了这些制度的内容与形式完全脱节的后果。本该维护货币和经济稳定的中央银行制度,成了滥发货币、扰乱金融的根源。
(五)开放次序的逆向运作。近代中国的一个重大背景是中外关系的不平等,是中国在屈辱条件下的被迫对外开放。这一点也许成了近代中国历朝政府的思维定势,他们在作出经济变革的决策时,其开放次序往往是先对外开放,后对内开放。
清政府在创办轮船招商局及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中,禁止华商设立轮船公司,但外商却不在禁止之列,怡和、太古等外国轮船公司称霸中国沿海及内河的各条航路。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列强取得在中国的设厂权,清政府也就失去了对棉纺织等产业的控制权。同时,洋货进口也越来越多。清政府已没有必要继续对中国投资者实行市场禁入政策。再说,它自己的财政包袱越来越重,如果继续实行禁止本国人进入某些产业的政策,其后果一方面减少了税源,另一方面则加重了自己的财政拖累,经营不佳的由政府控制的企业没少在财政上出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政府才对中国投资者也放开了设厂权。所以,对外放开在前,对内放开在后。1935-1936年间,南京政府特许美商琼斯在中国开采和提炼石油,却不准中国私人投资者参与开发。(注:宁档28-480。)抗战胜利以后,在南京政府对中国经济实行垄断程度越来越高的统制经济,因而本国私人投资者越来越无所作为的时候,南京政府却对美国投资人大开方便之门,连政府的大型企业轮船招商局都被美国投资人所控制,美国银行家通过巨额资金的投入,甚至可以左右南京政府垄断全国重工业的资源委员会。(注: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50页。)
四 对政治性周期和逆向运作的两点补充评价
关于政治性周期和逆向运作的评价,上文已多有涉及,这里再补充两点:
(一)历史视角:不全是负面作用。
政治性周期和逆向运作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有正面作用。其正面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具有开辟新的经济时代的启动作用。过去,人们常以战争的胜负来评论洋务运动的成败,其实,一场战争的胜负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即使是两个强国之间的战争,也总有一胜一败。正因为有洋务运动在前,才有清末新政在后,这是一个过程。在中国近代的社会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足以在短时期内成为开辟新的经济时代的主导力量,这个历史任务只能由政府来承担。
在中国主要民用产业的发生期,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产业形式。清政府对于这些产业的控制和扶持是互为表里的,离开清政府的扶持,许多大型的竞争型企业都难以创设,或难以维持。轮船招商局之所以没有被外轮公司挤垮,除了因为得到具有爱国思想的中国商人的支持外,还因为从清政府方面得到了漕运专利、减免税厘、官款接济和扩大营业范围等扶持。招商局在运漕方面虽然受到沙船业的掣肘,但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它所得到运漕额还是增加的,运漕水脚收入为“商局命脉所系”。(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0。)外国人称此项特权为清政府对招商局的变相补贴,若“没有这项补贴,招商局非亏本不可”。(注:《捷报》1879年8月8日,第136页。转见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26页。)收买旗昌以后,太古一意倾轧,将长江各口客货水脚大大减低,使招商局也不得不相应减低。这时招商局“专以北洋运漕之盈余,稍补长江减脚之短绌”。(注:《招商局总管理处汇报》,1929年,第3页。)招商局的船只从上海到天津随漕运货,可免天津进口税二成。1881年清政府规定:“凡由招商局运茶,自汉运津者只完正半两税以外,概不重征。”(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编:《洋务运动》,第6册,1961年版,第49页。)1886年又规定卸漕空船载货可免税二成。清政府对招商局的长期低息贷款额很大,到1878年即达190多万两(注:《申报》1880年9月26日;《字林沪报》1882年10月14日。),其中为盘购旗昌资产即贷了100万两。招商局正是靠了清政府的贷款,才成功地买下了旗昌。在外轮公司对招商局倾轧最厉害的时候,清政府还准令招商局扩大营业范围。从1877年起,招商局获得了沿江沿海承运各省官物的特权,(注:《洋务运动》,第6册,第27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0。)又获准可在“沿江沿海及内河不通商口岸自行贸易”。(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7。)1883年金融风潮发生,“存局各户,纷纷提款”,李鸿章拨官款36万两,“以支危局”。(注:《招商局总管理处汇报》,第4页。)1895年,清政府总理衙门的一份奏折中说,招商局“所以能自立者,实赖官为维持,故虽怡和、太古多方排挤,该局犹能支柱”。(注:杨家骆主编:《戊戌变法文献汇编》,2册,台北1973年版,第401页。)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如果没有清政府的扶持,像招商局这样的大型轮船公司的创立和维持都是难以想象的。
在矿业方面也是如此。中国的矿业既要受到封建守旧势力的多方阻挠,又要受到外国资本的竞争压迫,可谓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在这样的情况下,由清政府出面倡办,并给予扶持,也就成为这个产业起步的必要条件。开平矿务局到1882年投产时,已借用官款24万两,以后在1883年金融风潮发生时和几次铁路扩建,都借用了政府的官款,(注:参阅陈绛:《开平矿务局经济活动试析(1878-1900)》。《复旦学报》1983年3期。)它还享受减税的优待。(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0。)其他如上海织布局等企业也都得到官款的扶持和减免税的待遇。可以说,政府的扶持是这些企业初期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
如果南京政府在财政改革、控制政府规模等配套制度改革方面作出努力,不打内战,那么它的法币和中央银行制度改革也会开辟一个新的经济时代。
第二,它具有资本集聚的作用。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缺乏资本原始积累的前提条件下起步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首先出现在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领域,中国的新式商业作为外国在华资本的补充而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买办是新式商人的一部分,按照郝延平先生的估计,1842-1894年买办总收入高达53080万两。(注:Yen-P'ing Hao,The Comprador in 19 Century China:Bridge between Eastand West,p.104,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当然,从新式商人的总体而言,他们所积累的资金数额更要大得多。当一部分新式商人将他们在流通领域积累的资金向生产领域转移时,他们有很强烈的依托官府的愿望。在民用产业兴起的初期,新式商人有鉴于中国风气未开,有意依托官府来排除企业创办和前进中的障碍,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新式商人领袖振臂一呼,响应者甚众,洋务企业很快筹集到相当可观的资本。(注:参阅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第一章。)另外,在实行不兑现纸币制度的条件下,政府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纸币发行税和通货膨胀税。如果通货膨胀率处于可控制的限度之内,那么政府由此可以集聚起相当的财力。
(二)政治稳定与政府规模缩减是一对矛盾。
在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单纯的政府更替只会启动新一轮周期;而每一轮周期的强度和长度要依政府控制力的强弱来定。近代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政治性周期第三和第四两个阶段,即政治是否能够保持稳定和政府职能转变。
根据上文定义,政治性周期的第三阶段是政府维持成本提高和财政困难时期。在这一阶段,政府是脆弱的,要维持其合法性地位很不容易,如果一个政府垮台了,其第四阶段的政府职能转变就无从谈起。政治稳定的课题从第三阶段一直向第四阶段延伸。
第四阶段政府职能转变更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政府规模缩减,政府改变干预经济的行为模式,扶持民营经济等。政府规模缩减包括裁军、裁减政府机关和人员、职能部门结构调整等。
这样,政治稳定与政府规模收缩就可能成为一对矛盾。一个二律背反的命题始终困扰着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稳定是建立在政治足够控制力的基础上的,这意味着军队和政府规模的扩张,但这会加重财政的困难,为了克服财政困难所采取的加税、增发纸币等措施又极容易引起社会的动荡,这又造成了政治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政府如果选择转变自身职能、缩减规模、扶持民营经济的另一条道路,如清政府在清末新政时期所做的那样,则可能在另一条路径上削弱政府的控制力。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人们对政治民主化的追求,也会引起社会的动荡。
标签:企业经济论文; 经济周期理论论文; 制度变迁理论论文; 产权理论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宪法修改论文; 银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