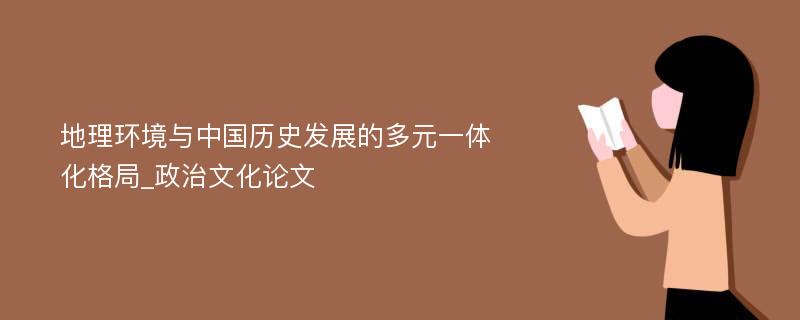
地理环境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多元一体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环境论文,体格论文,中国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6文献标识码:A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空间场所,长期以来,地理环境仅被静态地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背景和舞台,而忽略了它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作为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必要前提,地理环境必然影响并制约社会的发展。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自成一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以中央集权和小农经济为本质特征的封建结构体系得到高度完善和充分发展,大统一的思想观念深入民心,多元一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理格局逐步成型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鲜明特色。当然,社会的发展是极其复杂的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地理环境因素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
1 地理环境的封闭性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始于秦汉时期。但是,早在夏、商、周三朝就已形成了松散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雏形。 “禹合诸侯于涂山, 执玉帛者万国”(注:《春秋左传正义》卷58。),夏、商、周的天子是所属众多诸候的共主。与此同时,大统一的思想开始在中国萌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注:《诗经·小雅·北山》。),以及孔子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都是大统一的思想。这种大统一的思想的出现,固然有其深厚的经济、历史和政治原因,但其地理原因,即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的结构特征决不容忽视。中国位于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临太平洋,北界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和苔原冻土地带,东南濒海,西南是山;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封闭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一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地,因而称之为“天下”,又以为四面环海,故称四海之内,《诗经·商颂》中即有“帮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的诗句。这种地理环境的整体的统一性,极有利于产生“百川归海,心向统一”的大统一思想,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历史上政治形式的发展。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外敌不易入侵,亦使历史上中国各民族的活动具有自然的内向性。世界上其他灿烂的古代文明均在外敌入侵下消失,“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1]。第二,地域辽阔,地形复杂, 内地农耕社会即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所流经的地区是地理条件最好的地区,地势低平,交通往来方便,水热资源丰富,农业经济发达,易于构成统一的核心。第三,内地农耕社会先进的经济、文化对周边地区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种凝聚力和前述内向性相结合,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各族间联系的纽带。第四,大河(黄河、长江)流域需要中央集权政府执行公共工程的职能。关于这一点,冀朝鼎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中亦明确指出了水利事业的发展与封建专制的强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自秦汉以来,中国虽然不只一次地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但每一次的分裂都形成更高强度的统一。无论分裂还是统一的斗争,都没有超出这个封闭地理环境之外,正是这种封闭性,使各种力量在同一空间里消长,最后结果是统一占了上风,亦即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2 地理环境的地带差异
如果以天水为中心,北至大兴安岭北端以西,南至云南腾冲,可将中国划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东部为湿润半湿润地区,平原丘陵面积广大,水热资源丰富,利于农业发展,自古以来就是汉族人的聚居区,中国社会的主体;西部为干旱半干旱地区,多为高原、山地和草场,气候寒冷干燥,是少数民族从事游牧业和小块农业的地区。天然的地理条件造成内地农耕社会与周边游牧社会经济类型的不同,从而导致双方在社会发展上的巨大差距。社会发展程度较为落后的周边民族由于受内地农耕社会先进的经济文化吸引而不断内侵,如秦汉与匈奴的对立,五胡十六国的大动乱与南北朝的对立,隋唐与突厥的对立,两宋与辽、金、元的对立,明与蒙古、满族的对立等。因此,可以说,正是中国的地理环境差异孕育了中国古代民族战争的胚芽,并促使其长期延续下来。众多民族的大混杂、大融合,促进了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形成。费孝通教授曾对此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2]。
中国历史上周边地区几乎都有少数民族分布,但从历史记载的大规模的民族战争来看,主要的入侵对象是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包括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如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和东北地区的狩猎民族,如女真、满族。南方的少数民族,除了来自青藏高原的羌和吐蕃曾给中原王朝带来一定军事威胁以外,云贵高原的民族只在南诏时期与中原地区有过较大冲突。这一历史现象也有它的地理原因。北方民族居住的地区,高寒干旱,多草原、沙漠,集体的游牧生活和便利的交通使其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容易走向联合,而艰苦的自然环境也有助于他们养成勇敢顽强的性格。突厥曾总结与唐的作战经验,“突厥众不敌唐百分之一,所能与抗者,随水草射猎,居无常处,习于武事,强则进取,弱则遁伏,唐兵虽多,无所用也”(注:《新唐书·突厥传》。),也说明了地理环境对北方游牧民族有利方面的影响。而来自东北白山黑水的肃慎系民族,虽位于湿润半湿润区内,但冬季寒冷漫长,原始森林广布,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经济生活落后,恶劣的自然环境同样培养了狩猎民族英勇好战的尚武精神,与北方游牧民族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至于南方各少数民族虽然在民族种类数量上超过北方民族,但所处的青藏高原雪山林立,峡谷深邃,云贵高原偏居西南一隅,地形破碎崎岖。闭塞的环境,不便的交通,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有利于保护民族差异和小区域经济政治的地方性,但极不利于联系和融合,形成强大的地方统一政权。因此,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曾一次又一次地入侵中原,而南方民族却很少有类似的活动。这也不能不归结于地理环境的南北差异。
3 地理资源分布差异
以秦岭、淮河为界,可将中国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南方属亚热带、热带,雨量充沛,多山地丘陵,以水田农业为主;北方属暖温带、温带,雨热同季,平原面积广大,以旱作农业为主。从自然资源条件来看,南方更具有发展农业的潜力,但由于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简陋的生产工具不便开发森林沼泽地带,所以北方,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首先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有两大显著特点值得注意,一是统一与分裂的交替出现,二是经济、文化重心由北向南的推移。事实上,我国历史上的几次大分裂,也多以南北对峙的形式表现出来,如三国时魏、蜀、吴的鼎足而立,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与北方五胡十六国、北朝的对立,南宋与金、元的对立。南北对峙的局面之所以形成,秦岭、淮河与长江天堑的自然阻隔,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而几次南北对峙,从北方带来大批高素质移民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也极大地促进了长江流域及两湖、四川、珠江流域的开发。汉时的长江流域,仍然是“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嬴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西晋末年,晚唐五代期间和两宋之际,北方几次大动乱,造成自北向南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仅永嘉之乱后的一个多世纪中,移入南方的人口(编于户籍)就高达90万,占当时南方官方统计人口的1/ 7[3]。迁入移民最多的长江流域则迅速发展成为人烟稠密、经济发达的地区。而北方地区,由于战争破坏、黄河改道、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恶化等原因,“户口亡匿,田畴荒废”(注:《大金国志·东海郡侯记》。),经济逐渐萎缩。唐中叶以后,我国经济重心南移,宋代已有“苏杭熟,天下足”的说法。北宋之后,我国文化重心南移。至此,南方终于后来者居上,长江流域成为我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尽管经济、文化重心不断南移,但我国的政治中心始终位于北方。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重心相分离,原因是多方面的,地理因素应是其中之一。一方面,历史上大规模的动乱和战争多起因于北部边疆,因此,为便于战时调度,历代统一王朝的首都均设于北方,如长安、洛阳、开封、北京。而位于南方的杭州、南京虽然物产丰富,经济发达,又有长江天险可守,但却对北方地区鞭长莫及,控制不力,因此,只能在分裂时期作为暂时的都城。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河流多为东西流向,大运河作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也是唐以后历代统一王朝政治中心能与经济、文化重心相分离而存在的物质基础。关于漕运的重要性,古人早已作过精辟的概括,“若乃京师大众之所聚,万旅百官之仰给,邦畿之赋,岂足充国?逮于奉辞伐叛,调兵乘鄣,或约赍以深入,或嬴粮而景从,曷尝不漕引而致羡储,飞挽而资宿饱”(注:王钦若,杨亿.《册府元龟》卷498。)。可见,南北大运河的畅通, 是为弥补地理资源分布不平均所采取的关键措施,对于维系统一王朝的安危具有重大的意义。
4 地理环境的变迁
地理环境是个历史范畴,随时代而变迁,这种变迁必然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地理环境诸要素的历史变迁包括很多方面:如古今气候的变化,江河湖海的变化,森林植被的变化,土壤肥力的变化,水陆交通的发展,自然灾害的周期性变化等。在此,只需择其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较大的一些事件就可窥见其变迁对社会发展作用之一斑。
4.1 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
黄河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很多。总的说来,上游变化最小,中游侵蚀最为严重,下游变迁、改道最为频繁。历史时期,黄河中游黄土高原本是森林茂盛、土地肥沃的“八百里秦川”,古人称之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注:班固.《汉书》卷40, 《张良传》。),秦汉以来,大规模的移民戍边垦荒,造成对土地的过度开垦,植被的大面积破坏,水土流失日益严重,随之而来的就是下游的决口和改道。根据历史文献资料记载,历史时期,黄河下游决口泛溢约有1500次,大量泥沙在下游的淤积是主要因素。黄河的变迁对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危害,洪水吞没大量的农田、城镇,洪水过后留下大片碱地沙荒。同时,对下游的地理环境改变很大,原有的湖泊被逐渐填平,如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山东省西南部的巨野泽、太行山东部的大陆泽。此外,还给海河和淮河流域造成严重灾害。历史上黄河流域在经济发展上的地位逐渐为长江流域所代替,经济、文化重心由北向南转移,黄河河患是重要的原因。
4.2 历史时期沙漠变迁
我国沙漠多集中于北部和西北部。历史时期沙漠变化的总趋势是沙漠面积的不断扩展。如位于天山以南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著名的丝绸之路曾在此贯通沙漠南北的主要绿洲,形成楼兰、且末、精绝、渠勒、于田、沙平等文明古国。魏晋后由于沙漠向周边绿洲的扩展,这些国家均已从文献记载中消失,今日已是一片废墟。又如河西走廊,虽然很早就有沙漠,但最初范围狭小,整个环境还是水草丰茂、森林广阔的好地方。自公元前2世纪以来我国就在此屯垦经营, 唐代时号称天下富庶“无出陇右”(注:《资治通鉴》卷216。)。其它如毛乌素沙地、 科尔沁沙地、乌兰布和沙漠等,历史上也都曾经历过水草丰美、河川交错的时期。只是由于人类长期的经济活动尤其是过度的开垦、农牧经济的交替发展,严重破坏了当地生态平衡,才造成连绵不断的沙荒地。沙漠的变迁对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侵与这种生态环境的恶劣也不无关系。
4.3 历史时期水陆交通的变迁
陆路交通的发展,以秦朝最具开创性。秦统一六国后,在辽阔的疆域内开辟“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注:班固.《汉书·贾山传》。)的大规模交通体系, 从而大大促进了各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中国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陆路交通的历史发展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的开辟。这条被誉为“文化运河”的中西交通干线,自西汉、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盛世,经久不衰,极大地推动了东西方各国经济、贸易和文化的繁荣,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历史上我国古代人工运河开凿之早、规模之巨,都是世界运河开发史上所仅见的。楚庄王于鲁文公十四年(前613 年)任用孙叔敖开凿的通江、汉的荆汉运河”,《史记》载,“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注:司马迁.《史记·河渠书》。), 这是我国最早开凿运河的记录。历史上各朝代均十分重视运河在漕运、交通、水利及军事等方面的作用,开挖并疏浚了多条运河。而始于隋、历经元明清三代所形成的京杭大运河,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经6个省市,跨10个纬度,堪称运河成就的伟大杰作。如前所述,运河的开凿,便利了各地的交通和运输,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确曾起到了重大作用。
我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晚期,人们已在渤海沿岸及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海上航行。历史上我国航海事业经历了三次发展高潮:第一次是两汉时期,第二次是隋唐,第三次是宋元明时期。海上交通的开辟,首先推动了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也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如造船技术、地理学、天文学、海洋学等领域的研究和进展。此外,海上交通发展的意义还在于沿海地区的开发和兴盛。航海事业的发达,使港口发展十分迅速。广州、泉州、福州、温州、杭州等城市不仅是东南沿海地区著名商业城市,也是当时主要的航海贸易港口。不仅如此,港口的发展,还直接促进了周边经济腹地的繁荣。如广州的兴起,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开发就具有重大意义。
5 地理环境综合作用
中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从而导致各个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很不平衡,存在着多元性;同时中国又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地的发展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又必然存在着一体性。这种多元性与一体性的辨证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伟大奇观,但归根到底,又是中国地理环境综合作用的产物。
这种多元一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格局,是以高度发达的中原农业社会为核心,并不断向周边地区辐射与扩散,从而促进全国各地既同步又不平衡的发展而建立的。具体表现如下。
5.1 政治上的多元性
首先,表现于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差异。在汉族人聚居的中原地区,很早就脱离了原始社会,建立了国家政权——夏朝。在经历夏商周三代奴隶社会后,就进入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并建立了完整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而周边少数民族,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社会发展极其缓慢,长期徘徊于原始氏族社会与早期奴隶制阶段。政权组织形式以氏族和部落为主,而部落制度的发达,势必造成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的不发达。以匈奴为例,“匈奴政权的机构是比较简单,这是一个刚从原始社会过度到阶级社会的不发达的政权,这个政权是建立在游牧经济的基础上的,它与匈奴的不发达的奴隶制是相适应的,这个政权的形成,直到公元一世纪匈奴衰落,基本上没有改变”[4]。而这种状况在鲜卑、柔然、突厥、回纥等游牧民族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此外,即使在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由于山川阻隔,一些地理区域存在一定闭塞性,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也可凭借自然优势发展为独立的割据政权。如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的出现,就不能排除江东“国险而民附”、“益州险塞,沃野竿千里,天府之土”(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等地理因素。这也是政治地理格局中多元化的一种表现。
尽管如此,历史上不论是统一时期,还是分裂时期,都不能排斥政治地理格局中一体性的存在。契丹、鲜卑、女真、满洲等都曾以华北或全中国建立起比较稳固的政权,与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受中原地区的影响,易于认识、理解并接受汉族政治制度,逐步走向封建化密切相关。
其次,这种政治上的多元一体性,还表现在历代王朝在内地与边疆地区总是实行不同的政区制度。以清朝为例,在内地实行省、府、县三级行政建制,在边疆地区则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管理方法。包括:在蒙古族地区实行盟旗制;在西藏地区实行互参制;在维吾尔族地区实行“伯克制”;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等等。
5.2 经济上的多元性
经济上的多元性最明显的莫过于农业区与牧业区的差异。此外,在中原地区以秦岭—淮河为界,又可分出旱作农业与水田农业的差异。在平原、山地、森林、草原、河滨海岸地区,又分别有宜农、宜林、宜牧、宜渔等经济差异。在这一方面,司马迁提供了极为生动的历史资料:关中平原,人民“好稼穑,殖五谷”;马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器”;天水、陇西一带,“畜牧为天下饶”;燕地,“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吴郡,“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源之利”等等[5]。
经济上的一体性,表现于中原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对周边地区的强大吸引力,民族间与区域间的经济交流和同步发展。应该说,经济上的多元一体性是政治、文化上的多元一体性的基础和前提,这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辨证关系所决定的。
5.3 文化地理格局的发展
首先,表现为文化起源的多元一体性。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我国已发现了7000多处,年代从公元前6000年延续到公元前2000年,大量考古资料证明,这些分布广泛、各具特色的文化遗址和遗存分别是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从而证明文化起源的多元性。以文明起源最早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为例,黄河中游和下游分别存在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中游的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下游的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长江中游和下游也存在相对的两个文化区: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龙泉文化,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事实证明,在这个多元格局中,也出现了区域间的接触与交融,相互吸收比自己优秀的文化而不失其原有个性,如黄河中游兴起的仰韶文化,在接触到比它优秀的黄河下游山东龙山文化时,就出现了取代仰韶文化的河南龙山文化,从而在多元之上又增添了一体的格局[2]。
其次,文化的发展既有时代变迁,也有地区差异。“高大山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注:班固.《汉书·地理志》。), 不同地理环境必然会孕育出不同性质的文化。如已为人所共知的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等,都反映了鲜明的地方特色,证明区域文化发展的多元性。文化景观的地域差异,可表现于语言、宗教、风俗、建筑、文学艺术、音东舞蹈等多个方面。如语言,延续至今的全国七大方言的并存,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如风俗,“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早已是人之常识。区域文化发展的一体性,同样表现为区域文化间的交流、整合。人是文化的载体,人口的迁徙是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如七大方言的形成,并非是封闭环境的内部产物,而是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的人群杂处交融的结果。不同性质的文化相遇,必然会产生碰撞、冲突,互相吸收又互相排斥,即文化的整合。正是这种区域文化的多元性发展和交互影响、相对统一,最终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姿多彩、内蕴丰富的历史文化。
综上所述,地理环境及其变迁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政治、经济、民族和文化发展及其分布格局都产生重大历史影响。这种影响,将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正确认识这一规律,即使在现今信息时代,仍具有深远意义。
收稿日期:1999—07—09;修订日期:1999—1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