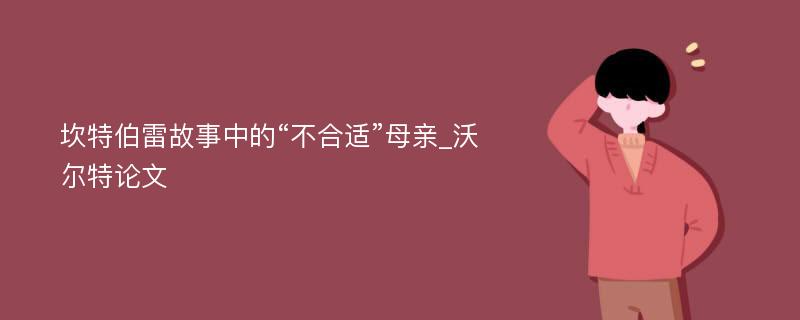
《坎特伯雷故事》中“不合适”的母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合适论文,母亲论文,故事论文,坎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界通常认为女性和两性关系是乔叟探讨伦理、社会和宗教问题的核心所在,①但乔叟笔下的苏丹之母、多纳吉、无名的寡居母亲、阿格丽品娜和格里泽尔达作为“不合适”的母亲,并未引起足够的学术关注和研究。“不合适”(unbecoming)一词指“从已自然化、确定的母亲身份到丧失合法母亲身份或变为坏母亲这一过程,涉及亲生母亲在身体、情感、社会、法律方面和孩子的关系在本质上的改变,同样指那些放弃母亲义务和责任的不合适行为”。②《坎特伯雷故事》中这些“不合适”的母亲与子女的互动关系说明母性不仅仅是女性经验的再现和社会体制的简单承载物,它还蕴含了中世纪英国宗教、政治、种族、文化和性别话语对母子关系和母性体制的影响和干扰,展现了这些女性的母性思考及其在母性实践活动中的精神习惯和认知方式,而母亲与子女之间的关怀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中世纪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一、反母性的母亲:化解身份危机感
美国社会学家兼精神分析学家南茜·乔德罗指出,女性渴望从为母之道中获取心理上的满足感,这种获得满足感的能力都被强烈内化,逐渐在女性的心理结构中形成。③乔德罗认为男孩一般趋于否定与母亲之间的认同感,拒绝女性化的世界,而他们身上女性气质的形成处于断裂状态。在乔叟的笔下,几位母亲与儿子之间的关系从早期的俄狄浦斯的同一感(oneness)转变为母子关系的彻底断裂,宗教信仰、血统纯正性和政治参与成为矛盾的导火线。这几位母亲成为反母性的母亲,因为这些母亲的行为举止违背了男权社会母性体制。
《律师的故事》以商人向叙利亚苏丹描述罗马公主康斯坦丝开始,而苏丹能成功娶她为妻的条件是放弃伊斯兰教并皈依基督教。他通过“双膝跪地”和“央求”的方式请求母亲同意接见康斯坦丝。苏丹之母佯装同意,但在宴会上劈杀了改信基督教的苏丹及其谋臣,康斯坦丝被流放在大海之上。苏丹之母说道:“宁可不要我躯体里的这条命,/也不让伊斯兰信仰离开我心!”(第4158-9行)④滨口惠子认为苏丹之母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与儿子追求的自由主义无法达成一致,故导致苏丹被杀的悲剧。⑤显然,母性、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身份产生难以融合的矛盾。苏丹的话“我必须是她的(康斯坦丝的)”表明他想从过去与母亲精神信念的一致性转移到对新的客体对象康斯坦丝的情感依赖上,母子之间持续、稳定的情感依赖和精神关怀面临着重新调整的可能。母亲通常在心理上把孩子看作是自我的延续和再生,而苏丹的叛教行为完全否定了母子之间精神信仰传承的完整性。这种母子关系的瓦解在本质上是两种信仰和文化在个体冲突中的具体外化。苏丹之母并非美狄亚式的母亲,她心理上伴有对叙利亚政治稳定和信仰一致的民族忧虑感。她劈杀儿子来维持母子关系中情感和精神信念的延续性和纯粹性,目的在于维护以她为代表的伊斯兰文化血统的纯正性。
康斯坦丝后来嫁给诺森伯兰之王阿拉,这同样引起公婆多纳吉的厌恶和排斥,“使她(多纳吉)感到丢人的是她的儿子/竟然娶这种外邦女子为妻”(第5119-20行)。舒劳诗指出嫉妒是多纳吉产生仇恨的心理原因,⑥丁肖认为多纳吉有乱伦欲望,⑦滨口惠子认为宗教分歧是多纳吉反对这场婚姻的直接原因。⑧故事中,多纳吉认为康斯坦丝生育的儿子莫里斯是妖魔般的怪物,而康斯坦丝是具有巫术的女性。显然,多纳吉以母子血统为挡箭牌企图维持她和阿拉之间生物血统的完整性和纯粹性,异族血统被妖魔化。如果说苏丹之母杀子是因为文化血统面临着被改写的威胁,那么多纳吉的敌意来自生物血统要被改变的焦虑。总体来看,这两位母亲维护的是血统的纯正性,而这是以母子之间血统关系的纯正性、连贯性和一致性为基础的。这两位母亲把儿子当作控制的客体对象,在母子关系同一性的基础上保持血统的纯正性,因此,她们的后母性生活被赋予意义和价值。她们是反母性的母亲,因为她们的行为与中世纪传统文化对理想的母亲的期待和体制化的母性格格不入。
《修士的故事》再现了历史人物阿格丽品娜的故事,仅以12行诗句描述了尼禄弑母的动机和母亲死后他的冷漠无情。朱迪·金斯博格在研究历史学家塔西佗、苏东尼斯和奥·科克亚努斯笔下的阿格丽品娜的时候忽略了乔叟笔下的修士讲述的阿格丽品娜的故事。金斯博格指出:“古文学中对阿格丽品娜的刻画一律充满敌意。”⑨现代学者的看法如出一辙,但笔者从她作为母亲的角度出发去解读这位颇有争议的女性。尼禄的角色习得和定位经历了早期和母亲的认同到后来彻底否定母子关系的过程。据历史记载,阿格丽品娜费尽心机扫清一切障碍使尼禄成为罗马皇帝,登上权力的巅峰,但尼禄在她看来不过是她要掌控的他者。她企图对尼禄的个人生活、政治事业和意识观念进行有效控制,反而成为儿子的政治对手。
在《修士的故事》中,尼禄看到母亲的子宫被剖开的情景时说道:“多美的女人!”(第14406行)⑩遂吩咐随从送酒给他以表祝贺。尼禄饮酒验尸实现了彻底拒绝母亲的目的,完全割断了母子之间的纽带关系。在阿格丽品娜的事例中,被边缘化的东西不仅仅是母亲的身体,而是母亲所代表的女性气质,是对母亲把儿子看作他者这一关系的逆转,是儿子把母亲改变为他者的举动。尼禄祛除的东西不完全是母亲企图实现的政治权力和自我权威感,他企图压抑的是控制欲望强烈的母亲所具有的潜在威胁,以此释放他的恐惧感。弑母平息了尼禄内心的焦虑,抑制了任何会对保持男权社会秩序造成威胁的个体行为,尤其是来自母亲的控制与干涉,维护了儿子—男性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男权社会秩序。尼禄手中的红酒和“多美的女人”的感叹不仅是在庆祝两性之战中女性屈从于两性等级秩序的胜利,也是庆祝他成功摆脱母亲控制他这一生活模式的胜利。子宫通常被看作是母性权力的源泉。在修士的讲述中,尼禄剖开母亲的肚皮是为了看“孕育他的地方”(第14404行)。法国女性主义者露丝·伊里加蕾认为回归本源意味着“为了重建和它之间的连续性,打探并理解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在那里再生自我”。(11)母亲子宫被剖开这一举动是尼禄对母亲权力的极端抑制,他不是通过此举恢复和母亲之间的本源关系,而以怪异的方式再生自我。
故事的讲述者在文字叙述层面对不同的母亲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苏丹之母被描述为“邪恶之源”、“长得像女人的毒蛇”和“花言巧语的毒蝎子”,多纳吉是“魔鬼”、“狠毒的恶婆”、“灵魂在地狱”等,而基督徒康斯坦丝“年轻、美丽、谦逊”,“圣洁、慷慨”,“仁慈、温柔、虔诚”。从文字层面上看,乔叟表述了中世纪人对具有男性气质的女性的厌恶,对控制欲强烈的母亲和文化他者的仇恨与排斥。伊丽莎白·罗宾逊认为乔叟批判的是“她们身上具有的男性力量,它具有暴力、欺骗和残忍的特点”。(12)劈杀了儿子的苏丹之母也许在罗马皇帝为康斯坦丝雪耻中丧生,多纳吉被儿子阿拉所杀。她们遭遇边缘情境,反衬出乔叟对以康斯坦丝为代表的基督教母性的极力推崇。苏丹之母和多纳吉不仅遭遇暴力杀戮,还有文化谋杀和文字暴力,更是基督教文化对文化他者进行消音的牺牲品,她们成为不合适的母亲。《修士的故事》中的阿格丽品娜利用母亲身份参与政治,把女性气质和政治体制联系起来,成为政治斗争和权力攫取的牺牲品,她不可避免地、非自然地成为不合适的母亲。尼禄和那些没有威胁感、没有控制欲、具有依赖性的被动型女性之间的亲密关系不仅是在否定母亲阿格丽品娜,而且在母子关系的疏离之中,企图塑造起独立治国、完全凌驾于他人之上的自我理想化形象。
二、寡居母亲:圣母玛利亚“晕厥”形象的现实再生
《修女院院长的故事》是《坎特伯雷故事》中唯一以孩子作为主角的故事,一般被归类在“圣母的奇迹”故事之列和“孩子作为祭品”的主题之中。(13)这个故事并非乔叟的大胆杜撰,它和欧洲历史上误传的犹太人血污案和中世纪欧洲反犹思潮有关。对中世纪英国来说,1215年是分水岭:1215年之前的反犹行为属于民间行为,次数少而规模小;1215年之后教会与政府明确推行持久的反犹政策,在基督教世界引起强烈的民族仇恨。(14)虽然有学者认为这个故事可能是乔叟在婴儿殉教节时听到的布道文,多数评论强调故事中的反犹主义思想倾向,很难脱离历史背景对其进行中肯评价。
故事中的寡居母亲教导儿子赞美圣母玛利亚,他歌唱的《救世主的慈爱之母》(Alma redemptoris mater)引起社区犹太人的不满与憎恨,从而引发血腥的残杀案。小学童被杀之后,不知情的寡居母亲含着母亲的“怜悯”(pitee[pity]),可怜地(pitously [piteously])四处寻找,在他尸骨未寒的深坑(pit)周围呼喊,小学童被抬起的时候,她可怜地(pitiful)恸哭。吉拉·安罗妮和雪丽·莎蓉—赛瑟认为小学童所处的物理空间和母亲内心的怜悯情感在结构和语音学上紧密联系,更与母亲的乳房(bresit [breast])相连。(15)事实上,在焦虑的寡居母亲和身陷深坑中的儿子之间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精神空间,即这种语音关联性创造了一种母性科拉(chora):在母亲寻找儿子的悲痛感与儿子痛苦挣扎之间形成一种隐形张力,显示出母亲身体具有的流动性和节奏感特点,而只有处于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孩子和母亲才可能共同感受得到。
故事结尾处提到圣徒林肯的休(Hugh of Lincoln,1247-1255)。休于1255年在英国林肯镇被犹太人杀害,此后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英国反犹思潮更是此起彼伏。(16)故事在谴责犹太人祭祀性杀戮与文化构建后面隐藏着基督教话语需要澄清的问题:在寡居母亲与儿子、圣徒休与母亲贝垂斯、耶稣与圣母玛利亚这三组关系中再现的都是母亲失子之痛和犹太人的暴力残害行为。这些母亲被动地转变为“不合适”的母亲:母亲在痛失爱子或情感寄托客体时表现出悲伤、痛苦和无奈,出现母性角色实现中的彻底短路和母亲身份的模糊性,真正而自然的母亲角色转变为非自然、非正常的母性角色,谴责矛头直指犹太人,这也是对福音书中鲜有描述的圣母玛利亚的母性悲恸做了生动的脚注式补充。
寡居母亲突然“昏厥”,这说明她强烈拒绝接受儿子死亡这一事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乔叟再现了十字架下悲伤的圣母玛利亚的故事,是母亲悲恸的典型表征。寡居母亲见到被杀的儿子的“昏厥”和女修道院院长对死亡的小狗的“哭泣”是对圣母玛利亚“昏厥”这一母亲形象的呼应和现实再生。阿米·奈夫指出“圣母玛利亚昏厥”(Mary's Swoon)这一形象的产生源自中世纪情感虔诚,她对耶稣受难的反应实际上是神圣的母性的表现,在人类救赎史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而“玛利亚的昏厥表达了她的怜悯、母性和牺牲精神”。(17)中世纪时期,欧洲大陆艺术家在绘画中展现“圣母玛利亚昏厥”这一形象,这是对天主教修士托马斯·阿·凯姆佩斯的《模仿基督》中神秘主义体验的直接回应。它呼唤目击者对基督与圣母玛利亚所遭受的痛苦产生情感认同,圣母玛利亚所具有的普世母性使她心甘情愿把爱子奉献给全人类。对中世纪人来说,好母亲就应该像圣母玛利亚一样在遭遇失子之痛时显示出极度悲伤和怜悯之情,而神圣的母性总是与痛苦、爱和虔诚关联,当然,这和当时流行的圣母玛利亚崇拜不无关联。圣母玛利亚崇拜在英国从产生到盛行有其历史渊源,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有关玛利亚的描写主要来自布道集,在诺曼征服之前,圣母玛利亚崇拜已经在英国开始盛行,无论是在艺术领域还是在宗教仪式中,圣母玛利亚通常被看作是站在基督右手边的调解人和基督受难时的目击者,更是悲恸不已的母亲。乔叟高明之处在于使像寡居母亲一样的普通母亲的丧子之痛升华为圣母玛利亚丧子之痛,由此升华普通女性的母亲身份,再生了圣母玛利亚的母性悲恸和孤独感,歌颂她的神圣母性。
把这位母亲塑造成圣母玛利亚式的母亲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圣母玛利亚生活在这样一种光环中,即她神圣的母亲身份源自她是“上帝之母”这样一个事实。在英国民谣《樱桃树颂歌》中,耶稣对玛利亚说道:“在复活节,母亲,/我将重返人间,/那时太阳与月亮,母亲,/将随我一同升起。”(18)耶稣被称作“天堂之王”和“救世主”,母亲身份因为儿子的卓越地位和与日月同辉的永恒而得以彰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中世纪普通女性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是对其母亲身份的崇拜与艳羡,若成为“基督—儿子”的孕育者,母亲身份自然会被提升,自我的理想化形象得以实现,普通母亲自然可以充分体验到一种卓越感和优越感。当儿子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他的母亲借此俯瞰世界,从而实现母性权威。寡居母亲的“昏厥”是圣母玛利亚神圣母性的现实再生,是诗人乔叟对圣母玛利亚痛失爱子的重写和策略性重述。
三、格里泽尔达:世俗世界中的母性殉道者
《学士的故事》中的格里泽尔达在丈夫两次企图杀子的考验中唯命是从,以超常的耐心经历了母性异化,是世俗世界中典型的母性殉道者。沃尔特通常被看作统治者、精神之父和上帝的化身,格里泽尔达被看作臣民的代表和耶稣的化身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沃尔特考验格里泽尔达的动机和意图引起学界的广泛争议和热评,这些评论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四类:一、他考验格里泽尔达是否在履行听命于丈夫的婚姻承诺;二、考验国王和臣民之间的关系;三、他们分别扮演性别角色,沃尔特寻找他可以驾驭的他者;四、格里泽尔达是“耐心”和“女性气质”的象征。这些评论和研究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细节,即沃尔特对格里泽尔达的考验是建立在母性异化基础之上的。“母性异化”(maternal alienation)指男性通过虐待女性和儿童,达到破坏母亲—子女关系的目的,旨在树立自己的英雄形象。(19)
格里泽尔达的善良和仁慈使她好名远扬,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到萨卢佐“看”她,显然她成为颇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沃尔特考验她的动机源自一种“奇怪的冲动”,这种冲动是他对格里泽尔达成为萨卢佐人人膜拜的公众人物显示出的嫉妒。沃尔特清楚地知道“除了爱他,她最爱孩子”(第8570-1行),这是他反复考验的前提条件。他期待她在孩子被杀的情况下具有母亲合适的本能反应。这表明他相信人性中的矛盾性和人身上具有的角色面具,但格里泽尔达的克制行为延长了沃尔特的理解限度,自身完全神秘化。沃尔特佯装杀子、离婚和结婚是他消解角色矛盾的手段,旨在揭去格丽泽尔达的角色面具,恢复她本应扮演的从属角色,消除社会性自我和真实自我之间的差异,通过支配她从而恢复自己的权威感,以保持作为男性的优越性和主导地位。
格里泽尔达徘徊在体制化的母性和婚姻之间,前者要求女性具备母亲的本能,积极地实现为母之道;后者要求女性履行妻子的义务和责任,女性不得不保持被动性。安莉森·纽顿指出,格里泽尔达极好地证明了亚里士多德有关母亲的被动性的观点,而这种被动性完全体现了中世纪理想的母性形象。(20)显然,纽顿误解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人类生殖繁衍过程中女性作为质料而具有被动性,而非实现母道、履行母亲义务时具有被动性。女儿被他的亲信带走佯装杀死,沃尔特仔细观察,期待妻子有某些行为或情感变化,但却发现:“女儿的事,她只字不提/脸上看不出悲伤痛苦的表情/无论是认真或说笑时/她从未提及女儿的名字。”(第8482-5行)儿子出生后,沃尔特准备如法炮制,说道:“我事先提醒你一下,/免得你难过而突然失常,/我请求你,千万要有耐心。”(第8518-20行)他的提前警告表明他内心期待格里泽尔达在听到儿子要被杀的消息后在身体和心理上会出现强烈的母性反应,但她却依然面不改色,他“疑惑”她如何做到耐心地忍受痛苦而未有任何流露。事实上,沃尔特本人是表里不一的人:在听到格里泽尔达的婚姻誓言后,他内心异常高兴,但表面上却故作郁郁寡欢。这个细节说明沃尔特以己度人,坚信格里泽尔达必然是表里不一、口是心非的女性。这是他考验格里泽尔达的起点所在。
时隔多年,母子重聚,当真相被揭穿的时候,格里泽尔达当即晕倒在场。从面临两个孩子被杀时表现出的“愉快和平静”(cheerful equanimity)到母子相认的“昏厥”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情感反差。虽然有学者认为她有斯多葛式精神,(21)但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发现格里泽尔达其实是位富有仁慈心肠的女性。当女儿被带走的时候,她的脸显得“悲伤不已”(第8428行),但在沃尔特面前,她始终克制自己而不露任何痛苦之情。显然,格里泽尔达以女性的顺从为面具进行伪装,以中世纪人崇尚的耐心和克制为策略,自发地戴上角色面具保持社会距离,通过隐瞒真相而创造出高度一致的自我理想化形象,证明她所处的绝对从属地位,把孩子献祭给了男权社会。她在“晕厥”中解构了先前企图保持的母性殉道者的理想形象,而沃尔特通过母性异化的方式彻底削弱了格里泽尔达在萨卢佐作为公众人物的社会影响力。格里泽尔达的晕厥状态是母亲心理崩溃、自我身份完全模糊、彻底失语的极端表现,而沃尔特对她作为母亲的角色期待终于在她与孩子相见的“晕厥”中实现。在安慰恢复了母亲角色的格里泽尔达的时候,沃尔特成功恢复强者、控制者和秩序维持者的英雄角色,格里泽尔达则成为弱者、被保护者和被控制的对象。
围观者在她们母子相逢瞬间流出了眼泪。这些眼泪不仅代表他们对她的怜悯和同情,而且也是统治者给以格里泽尔达为代表的被统治阶层所施加的无形的政治压制的即兴情绪释放。她的母性“晕厥”满足了围观者的心理期待,把他们从令人窒息的考验游戏中体现出的情感张力和不安中解脱出来。沃尔特考验格里泽尔达是对两性权力关系和群体身份等级制的策略性维护,而它的实现是建立在母性异化基础之上的。格里泽尔达成为典型的母性殉道者,这不仅由沃尔特的系列考验造成,它还与中世纪“文化虐待逻辑”(cultural logic of torture)有关。从中世纪母性殉道者的经历中可以看出,母爱必须屈从于宗教信仰,即使情愿把孩子作为宗教祭品,这样的母亲仍然被看作是好母亲。显然,这些角色认同并没有脱离传统家庭结构中母性殉道者本应该扮演的女性角色和社会性别劳动分工。格里泽尔达和中世纪那些放弃家庭而一心致力于宗教追求的虔诚母亲或母性殉道者极其相似,她最后见到孩子的时候怀着感激之情说道:“仁慈的上帝/和你们体贴的父亲,/保全了你们的性命。”(第8942-7行)她把孩子献给了以上帝为代表的教会和以沃尔特为代表的男权社会,自己成为“不合适”的母亲。
结语
在乔叟笔下,非基督教母亲被妖魔化,成为基督教世界排斥的文化他者;基督教母亲或圣母玛利亚式的母亲被美化,是基督教社会极力推崇的理想化母亲形象。康斯坦丝和多纳吉代表两类不同的母亲,其后潜藏着中世纪文化中更为微妙的东西:中世纪人在心理上崇拜年轻母亲,极端丑化年老母亲;赋予年轻母亲以美德,而年老母亲与邪恶为伍。这说明中世纪人对青春活力的追求和对死亡的恐惧,进一步说,这两类母亲成为中世纪人反思生命与死亡的典型代表,这也许是他在诗歌中反复歌颂圣母玛利亚式女性的原因之一。在乔叟的笔下,母性成为一个隐喻,有助于乔叟探讨潜在的权力运作机制和体制化母性之间多元的互动关系。他对欧洲大陆作家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故事进行了重写,这有助于把他归类在中世纪欧洲大陆文学传统之列,填补了英伦岛和欧洲大陆之间存在的地理、政治、文化和宗教上的鸿沟,削减了14世纪英国所具备的他者性。
注释:
①Ethan Knapp,"Chaucer Criticism and its Legacies",The Yale Companion to Chaucer,ed.Seth Lerer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p.349; Jill Mann,Feminizing Chaucer (Cambridge:D.S.Brewer,2002),p.vii; Susan Crane,Gender and Romance in The Canterbury Tale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3.
②Diana L.Gastafson,Unbecoming Mothers: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Maternal Absence (New York:The Haworth Clinical Practice Press,2005),p.24.
③Nancy Chodorow,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p.34.
④Geoffrey Chaucer,The Canterbury Tales,ed.W.W.Skeat (Encyclopedia Britannica,1952).(凡出自本书的引文,只在文后标明诗行,不再另行做注。)
⑤⑧Keiko Hamaguchi,Non-European Women in Chaucer:A Postcolonial Study (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2006),p.39,p.20.
⑥Margeret Schlauch,Chaucer's Constance and Accused Queens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27) ,p.113.
⑦Carolyn Dinshaw,Chaucer's Sexual Poetics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9),p.105.
⑨Judith Ginsburg,Representing Agrippina:Constructions of Female Power in the Early Roman Empir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2006),p.4.
⑩Caroline Walker Bynum,Fragmentation and Redemption:Essays on Gender and the Human Body in Medieval Religion (New York:Zone Books,1991),p.281.
(11)Luce Irigaray,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trans.Gillian C.Gi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 ,p.41.
(12)Elizabeth Robertson,"Nonviolent Christianity and the Strangeness of Female Power in Geoffrey Chaucer's Man of Law' s Tale",Gender and Difference in the Middle Ages,eds.Sharon Farmer and Carol Braun Pasternack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3),p.332.
(13)Denise Louise Despres,"Cultic Anti-Judaism and Chaucer' s Litel Clergeon",Modern Philology,1994,91 (4),p.414.
(14)王本力:《中世纪反犹现象的演变及其特征》,载《历史教学》2009年第9期,35-40页。
(15)Gila Aloni and Shirley Sharon-Zisser,"The Prior Root:The Transit Through Hebrew in The Prioress's Tale",http:// www.chass.utoronto.ca/french/as-sa/ASSA-Nol7/Article3en.html,16 June 2008.
(16)Deraldine Heng,"Jews,Saracens,'Black Men',Tartars:England in a World of Racial Difference",A Companion to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c 1350-c 1500,ed.Peter Brown (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7),p.253.
(17)Amy Neff,"The Pain of Compassio:Mary's Labor at the Foot of the Cross",The Art Bulletin,1998,80 (2),p.254,p.255.
(18)Francis James Childe ed.,English and Scottish Popular Ballads,Vol.2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2003),p.1.
(19)Anne Morris,"Naming Maternal Alienation",Motherhood:Power and Oppression,ed.Marie Porter,Patricia Short and Andrea O' Reilly (Toronto:Women's Press,2005) ,pp.223-235.
(20)Allyson Newton,"The Occlusion of Maternity in Chaucer's Clerk's Tale",Medieval Mothering,eds.John Carmi Parsons and Bonnie Wheeler (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 Inc.,1999),p.70.
(21)Alcuin Blamires,Chaucer,Ethics,and Gender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p.173; S.Deborah Ellis,"The Color Purple and the Patient Griselda",College English,1987,49 (2),p.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