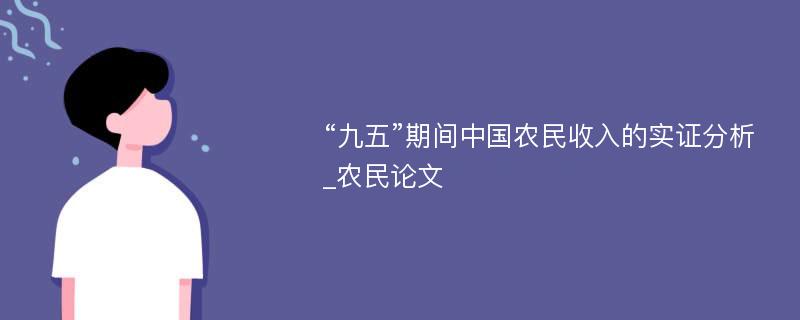
“九五”期间中国农民收入状况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中国论文,农民收入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最后5年,是中国(未含港、澳、台, 下同)组织实施国民经济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年,简称“九五”)、迎接新世纪的重要转折时期。“九五”时期,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步入了农产品供给从长期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着力进行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农村居民收入渐进式增长,生活水平由温饱向小康平稳过渡的发展新阶段。研究、分析这一时期国内外相关人士普遍关注的农民收入构成特征和变化态势,对于指导新世纪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向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有着特殊和重要的意义。
一、农民收入增幅趋减,贫富之间差距拉大
“八五”(1991—1995年)和“九五”期间,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8.92%和2.89%(扣除物价因素),“九五”期间比“八五”期间下降了6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注:指农村常住居民家庭总收入中,扣除从事生产和非生产经营费用支出、缴纳税款和上交承包集体任务金额以后剩余的,可直接用于进行生产性、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生活消费和积蓄的那部分收入。中国农民人均收入的主要构成:家庭经营纯收入+外出劳务纯收入+其他收入。本文其他收入主要指农户从集体得到的收入、企业经营中得到的收入以及其他非借贷性收入和利息、股息、红利收入)出现了增幅持续减缓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农户家庭经营纯收入增幅下降,而农民外出务工、从集体得到的工资、从企业经营中得到的其他收入,成为“九五”期间农户家庭纯收入增加的主体。
2000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纯收入10642元,与1995年的9555.4 元相比增加了1087.52元,其中家庭经营纯收入减少295.4元,而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和其他收入分别增加1032.08元和350.83元。“九五”期间, 在农户家庭纯收入增加值中,家庭经营纯收入、外出务工收入和其他纯收入的贡献份额分别是—27%、95%和32%。
从家庭纯收入的结构看,2000年农户家庭经营纯收入、外出务工收入和其他纯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份额分别是59.95%、23.55%和16.49%,农户家庭经营纯收入所占份额比1995年下降近10个百分点;而外出务工收入和其他纯收入份额则分别增加了8.12和1.79个百分点(见表1)。
表1 1990-2000年农户家庭纯收入及其构成变化
项目1990年
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
农户平均纯收入(元) 3920.16 9555.40 10392.65 10572.96 10229.43 10260.63 10642.91
1.家庭经营收入 2900.68 6676.30
6911.29
6955.99
6713.16
6394.28
6380.91
2.外出打工收入 354.28 1474.74 1780.46
1929.651964.10
2259.58
2506.81
3.其他收入 665.20 1404.37 1700.90
1687.321552.17
1606.76
1755.20
收入结构(%)
1.家庭经营比重
73.9969.8766.50 65.79 65.63 62.32 59.95
2.外出务工比重9.0415.4317.13 18.25 19.20 22.02 23.55
3.其他比重
16.9714.7016.37 15.96 15.17 15.66 16.49
2000年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是6380.9元,比1995年的6676.3元略有减少。“八五”期间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年均增长幅度为18.4%,比“九五”期间的—0.9%高出19.3个百分点。 “九五”期间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比“八五”期间有所下降,其中1998年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下降。尽管其所占份额逐年下降,但由于目前仍占总纯收入的60%左右,因而是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增长幅度持续下降的关键因素。
由于不同收入组农户家庭拥有的生产资源(劳力、资金和技术等)条件有很大差异,家庭经营结构与生产水平的初始条件也不相同,农户在经济活动过程中获得收益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就会产生差异,如果社会再分配机制不能对这种收益和获得收益的机会进行有效的调整或再分配,不同农户的家庭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速度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差异。按照农户家庭纯收入的“五等分”分组统计结果,以中等收入组农户(20%)的人均纯收入水平为100,1990年最低收入组农户(20 %)的人均纯收入、最高收入组农户(20%)的人均纯收入与中等收入组农户的比值分别是43∶100∶275,1995年这一比值扩大到40∶100∶299,到2000年这一比值进一步扩大到36∶100∶342(见表2)。结果表明, 近年来中国农村居民内部人均纯收入水平分配差异逐年扩大了。即与中等收入组农户相比,20%最低收入组农户家庭的纯收入水平和增长速度越来越慢,而20%的最高收入组农户家庭的纯收入水平和增长速度越来越快。
表2 不同收入组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及其差异
最低收入组 次低收入组 中等收入组 次高收入组 最高收入组
人均年纯收入(元)
1990年
298.20 503.45
688.79 948.76 1891.05
1995年
691.59 1242.60 1748.592474.97 5236.73
2000年
691.95 1344.34 1927.542801.00 6582.93
人均年纯收入比值(%)
1990年0.430.73 1.00
1.38 2.75
1995年0.400.71 1.00
1.42 2.99
2000年0.360.70 1.00
1.45 3.42
定量描述居民收入分配差异情况,国际上广泛采用基尼(Gini)系数和洛仑兹曲线的方法评价。基尼系数是一个由人口和收入参数计算出来的表征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参数,基尼系数的变化范围是从0 (完全的平等)到1(完全的不平等)。为便于比较,表3列出了1995年和2000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GINI)系数。
分析表3数据可知,2000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已达到 0.43,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比1995年的基尼(GINI )系数0.39 高出0.04。由此可见,“九五”期间农村居民的不平等程度扩大了约10%。
2000年最高收入20%的农户(拥有人口18.58 %)拥有全部收入的47.30%,相比较1986年、1999年的比重分别是42.0%、46.4%; 2000年最低收入的20%农户(拥有人口的20.4 %),仅占全体农户收入的5.6%,次低收入的20%农户(拥有人口的21.1%),占有收入的10.9%;中间收入的20%农户(人口占20.5%),占有收入的15.2%;次高收入的20%农户(人口占19.4%),拥有收入21%。
在被调查农户中,1%最高收入的农户拥有全部收入的9.6%,是最低20%收入人群收入合计的1.7倍,人均收入达到26290元,每户家庭纯收入达到102700元,分别是最低20%收入人群的37.34倍和33.94倍。
2000年农户家庭收支状况分析结果显示,18.73 %的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在0—999元(低于全国贫困线),34.50%在1000—1999元,21.09%在2000—2999元,10.28%在3000—3999元,15.4%在4000 元及以上(见表4)。
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为2564.19元(2574.5元), 调查数据显示:其中67.00%的农户人均纯收入低于平均值,有53.23%的农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不到2000元,尚在温饱阶段;21.09 %的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在2000—2999元,处于温饱有余、接近小康的生活水平; 25.68%的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在3000元及以上,这部分居民的收入超过小康水平,有的已经比较富裕。农村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已达到引人关注的程度。
表3 1995、2000年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比较
年份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2000年 0.4296 0.42290.3546
0.4094
1995年 0.3932 0.38750.3283
0.3798
表4 2000年不同收入组农户家庭所占份额
人均年纯收入水平(元) 0-9991000-19992000 -2999
3000 -3999 4000以上
农户家庭数(户)3803 7006
4283 2087 3126
农户年占比重(%)18.73 34.50 21.09 10.2815.40
二、种植收入贡献下降,非农收入增幅趋减
由于受宏观经济环境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农产品的需求制约问题开始凸现,农产品总量的扩张已不能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农业增产不增收、或增产与增收严重不同步的矛盾比较突出。
中国自1996年以来农业连续4年获得丰收, 长期短缺的农产品供给实现了总量平衡、丰年有余,农户家庭纯收入的增长受到市场需求因素的严重制约。自1997 年开始, 全国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逐年下降,1997、1998、1999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分别是上年的95.5%、92.0%和87.8%,受农产品价格下落因素影响,2000年农户家庭经营纯收入比1995年减少了4.42%。
表5 1990-2000年农户家庭经营性纯收入水平及其构成变化(元、%)
1990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八五期间年均增长 九五期间年均增长
家庭经营纯收入 2900.68
6676.30
6911.29
6955.99
6713.16
6394.28
6380.91 18.14
-0.90
1.种植业
1645.53
3769.69
3755.61
3469.81
3445.99
2962.48
2735.93 18.03
-6.21
2.林业
79.66151.55174.88153.98137.41141.92143.57 13.73
-1.08
3.畜牧业390.24628.94673.39735.93634.23641.52660.61 10.020.99
4.渔业
74.12210.81223.87193.17173.03162.78220.67 23.250.92
5.工业 167.38517.09411.58462.88393.17480.73441.57 25.31
-3.11
6.建筑业 44.55187.06201.89189.50189.69154.75163.95 33.24
-2.60
7.运输业150.88402.74465.04499.11446.98469.67516.87 21.705.12
8.商饮服务业211.62657.16733.89921.47938.48
1036.94
1112.72 25.44
11.11
9.其他 136.70256.60271.15329.78354.43343.18393.16 13.428.91
从表5可知,种植业、林业、 工业和运输业为农户提供的纯收入由“八五”时期的增长转为下降,其中种植业下降幅度最大。在农户家庭经营纯收入中,种植业为农民提供的收入在迅速减少,而牧业、渔业和工业所提供的收入增长幅度也明显下降。1995—2000年间,在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来自种植业、林业、工业和运输业的收入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分别由1990—1995年间的18.03%、13.73%、25.31%和21.70%下降到—6.21%、—1.08%、—3.11%和—2.6%;来自畜牧业、渔业、 商饮服务业和其他收入的增长也明显变慢。由于各业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发生较大变化,2000年农户家庭经营纯收入中种植业纯收入所占份额已从1995年的56.46%下降到42.80%;而商饮服务业收入所占份额从9.84%上升到17.44%。
从种植业内部纯收入增长和构成看,2000年农户家庭种植业纯收入为2735.93元,比1995年3769.69元减少1033.76元,下降27.4%; 其中农户家庭粮食作物纯收入由1995年的2436.55元减少到1499.21元,减少937.34元,粮食作物纯收入的减少占种植业纯收入减少的90.67%。 对于家庭经营中非农产业不发达、种植业结构单一的粮食生产农户来说,近年来粮食价格的不断下降,成为增加农户收入水平的主要制约因素。
三、东部发展保持强劲,中部西部增收受阻
2000年,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593元、1953元和1797元,“九五”期间的年递增率分别是4.49%、1.26%和2.48%,比“八五”期间的年递增率分别下降了16.29、19.66和17.96 个百分点(见表6)。
表6 1990-2000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户家庭纯收入水平及其构成
东部地区农户 中部地区农户
西部地区农户
1990年 1995年2000年1990年 1995年2000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家庭常住人口(人) 4.504.34 4.16 4.604.24 4.025.154.634.36
家庭年纯收入(元)
5051.1 12517.1
14939.3
3263.5
7770.47854.1 3231.0 7356.5 7830.8
人均纯收入(元) 1122.5
2884.83592.6709.5
1834.41953.0
627.4 1589.9 1797.0
(1)家庭经营纯收入 3165.0
7620.38136.6
2721.6
6111.45205.1 2775.9 5989.1 5292.49
其中:种植业1501.9
3423.92615.8
1734.2
4152.9
2941.9 1725.6 3757.6 2641.9
其中:粮食作物
793.7
2095.81131.8
1202.43039.2
1971.8
966.4 2036.5 1339.4
(2)外出打工收入 512.3
2216.03422.6256.41083.2
1960.6
266.7
828.1 1818.4
(3)其他收入1373.8
2680.83380.0285.6 575.7688.3
188.4
539.3
719.9
1990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户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79∶1.13∶1.00,1995年扩大为1.81∶1.15∶1.00,到2000年进一步扩大为2.00∶1.09∶1.00。东部与中部、西部地区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差异逐年扩大,而中部与西部地区的差距有所缩小。在东、中、西部农户家庭纯收入结构中,家庭经营收入比重均有所下降,外出务工收入和其他收入均有所上升。
2000年,东、中、西部农户家庭经营纯收入在家庭纯收入中的比重分别为54.46%、66.27%和67.59%,同比1995年下降6.42、12.38和13.82个百分点; 农户家庭种植业纯收入在家庭经营纯收入中所占份额是32.15%、56.00%和50.00%,分别比1995年下降12.78、11.95和12.82个百分点;粮食作物纯收入在家庭经营纯收入所占份额为
13.91%、37.88%和25.31%,分别比1995年下降13.60、11.85和8.69个百分点。表明东部地区农户家庭纯收入中来自种植业的收入份额,特别是粮食作物收入份额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而来自非农产业收入份额高于中西部地区。
由表3列出数据显示,2000年东、中、 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0.42、0.35和0.41,均比1995年有较大提高,而且在“九五”期间,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从全国看,200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较1995年增长了16.6%,其中东部地区增长了19.2%,中部地区增长了9.7%, 西部地区仅增长了1.8%。1995 年东、中、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是1.86∶1.10∶1.00,2000年东、中、西部的比值扩大到2.18∶1.19∶1.00。下面具体分析东部与中、西部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在农户家庭收入中,家庭经营收入和外出劳务收入所占比重最大,所以这些收入波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最大。“九五”期间中部、西部的家庭经营收入都处于减少态势,中部下降了4.2%,西部下降了4.3%。只有东部地区的家庭经营收入依然保持着稳步增长态势,总共增长了25.5%,年均增长3.1%。
农户的外出劳务收入,全国呈大幅度增长的趋势,“九五”期间人均提高了265元,上涨幅度为78%,按东、中、西部划分, 绝对值增长最多的是东部,为285.5元,其次是中部231元,西部为217元。
从集体获得的收入,全国平均继续呈下降趋势,人均减少11元,主要是东部大幅下降,从1995年的人均463元降为2000年的378元,减少了85元,减幅为18.0%;这项收入中、西部均略有提高,分别增加了 3.5元和9.5元。
农户参加企业经营的所得收入呈增加趋势,东部增加最多,人均达36元,中、西部分别增加了1.6元和16.6元。
在其他收入项中,东、中、西部均有较大增长,但东部和西部增长显著,分别增长了165元和130元,中部地区人均增加了74元。
综上所述,中、西部地区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的下降是造成东部与中、西部农民收入差距拉大的最主要因素。从家庭非生活性支出方面看,中、西部地区农户上缴各种税费的增长是拉大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又一因素。“九五”期间东部地区人均税费仅上升了9.0元,增长幅度为7.0%,而中、西部则分别增加了22.6元和32.7元,增幅分别为17.6%和40.0%。收支相抵后,2000年中、西部农民的纯收入分别为1994元和1676元,比东部地区分别相差了1654元和1972元,而1995年东部与中、西部农民人均纯收入差分别是1243元和1414元。
四、差距拉大原因种种,增收困难矛盾重重
统计分析了5个等分组农户的地理分布、劳动力就业率、 家庭投工量、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农业和非农产业收入等数据后,可以得出如下农户收入差距拉大的结论。
(一)地域差异导致收入的差异 在最高收入组中,有近70%的农户属于东部地区,其次是中部(20.2%),西部的农户仅占10.3%。由于东部地区对外开放和开发早于中、西部地区,东部的自然和经济环境以及交通运输状况优于中、西部,区域环境的不平等导致了农民收入的明显差异。
(二)家庭人口差异导致收入的差异 近十几年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取得进步,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农户家庭人口数不断减少,相对人口少、劳动力抚养指数低的家庭人均收入较高。由低到高各收入组的抚养指数分别为1.79、1.71、1.63、1.56和1.47,最高收入组的抚养指数为最低收入组的82%。由此不难看出,坚持计划生育国策,降低人口出生率,是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受教育程度差异导致收入的差异 对于任何一个取消绝对平均主义政策的社会,人口素质的差异都将直接导致效率的差异,进而导致收入结果的差异。以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作为人口素质参数,验证与农户收入关系的结果是:文化程度高的群体也是收入高的群体。最高收入组中初中和高中劳动力的比重合计为56.9%,其他收入组由高至低,初、高中文化比重依次为52.3%、47.7%、44.8%和39.3%。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人数比重,由高至低收入组依次为8.6%、5.4%、4.3%、3.9%和2.9%,最高收入组是最低收入组的3倍。因此,增加对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提高人口素质,是政府提高农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决策之一。
(四)就业率差异导致收入的差异 “九五”期间,是中国年新增农村劳动力数量处于顶峰的时期,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严重的隐性失业,由于家庭之间各种差异的存在(如成员素质、资产存量、社会交往等等),其劳动就业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各收入组由低到高就业率依次为62.3%、68.6%、73.6%、80.1%和89.3%,最高收入组就业率是最低收入组的1.4倍。
进一步分析其就业引起的收入差异,主要原因是由于低收入组在非农产业方面的就业不足,最低收入组和次低收入组非农产业投工分别仅占25.5%和35.6%,其中外出劳务投工仅占12.0%和17.0%,而最高收入组非农就业比重达70.5%,外出劳务投工在21.5%。因此调整农村的产业结构,扩大非农就业机会,尽可能给农村居民以充分就业机会,对缩小农村收入差距是至关重要的。
(五)非农产业经营不平衡导致收入的差异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中非农产业比重有大幅度提高,同时也带来了农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收入分组中由低到高,非农产业投工比重依次为25.5%、35.6%、48.7 %、52.9%、70.5%,最高收入组是最低收入组的2.8倍,农户总收入中来自非农业的比重依次是33.0%、 39.3%、 46.9%、 56.4%、74.6%。
(六)资产存量差异导致收入的差异 在不同的农户分组中,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和年末存款余额的差异也是很明显的,由低到高五个收入分组中,农户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分别是2908元、3495元、3774元、4852元、14556元,最高组是最低组的5.0倍。农户家庭存款余额分别是838元、2314元、2961元、5469元、18084元,最高组是最低组的21.6倍。表明在目前农户家庭经营仍居主导地位、 但非农产业呈日趋重要的阶段,农户增加收入不仅依赖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同时也强烈依赖于家庭资产(包括固定的和流动的)再增值,这就使得农村中出现了越富的家庭收入增加越快、越穷的农户收入增长越慢甚至下降的局面。
(七)社会背景不同导致收入的差异 调查数据还表明,在收入越高的农户组中,国家干部、职工户比重和村干部户的比重越高,分别为7.9%和11.4%;而在最低和次低收入组中,国家干部、 职工户比重和村干部户的比重仅为2.3%和3.5%。同样,村干部户在次高和最高收入组的比重分别为 4.9%和 6.5%,而在最低和次低收入组的比重则均为2.8%。
现代农业政策理论认为,在不断增长的国民经济中,以占GDP 的份额和劳动力的比例来衡量,农业部门所占的份额在持续不断地下降,这被称为农业的改造过程(transformation process)。这一过程的根源在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对农产品相对需求的变化,即在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同时,社会对农产品的相对需求却越来越少(即恩格尔定律)。其结果是,这一过程会对资源、尤其是对劳动力资源产生持续的压力,劳动力需要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进入到其他增长的经济部门中。然而,如果存在资源不流动性这样的缺陷,就可能会导致结构失衡(structural disequilibrium),这就出现了所谓“农业调整问题”。这一问题是由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造成的,这种收入差距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有的是暂时的,有的则是长期的;有的比较严重,有的则无足轻重。在农产品供过于求的开放经济社会中,运输条件改善和技术迅速提高导致农产品的真实价格迅速大幅下降时,农业调整问题就会变的更为严重。
中国是耕地资源非常稀缺的国家,农业和农村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而且是基本的难题。目前农村大多数劳动力仍然从事农业,收入的源泉也主要是农业活动,而中国的农业又受人多地少之困,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人均占有土地尤其是耕地面积一直在减少。由于难以开展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技术落后,人均劳动收入也非常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业要想取得发展,只能依靠资金和技术的集约投放,才可在有限的土地上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农产品。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是农业的经营主体,如果农业发展不能给农民带来所期望的收益,他们就绝不会向农业增加资金和技术投入,最终导致农业发展的萎缩。在现阶段,当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农民越来越关心收入问题,农户家庭在发展农村经济中的首要目标就是增加收入。面对这种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就更加取决于农民收入状况了。但是,从当前的经济发展实情分析,农民收入持续增加面临着以下几个尖锐矛盾。
1.单纯依靠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收入的空间越来越小。近年来,农民在农业方面收入的降低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农产品价格,二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由于受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对农产品相对需求的变化规律影响,即在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同时,社会对农产品的相对需求却越来越少(即恩格尔定律)的制约,如今,中国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平均水平,而且,消费需求约束也已经制约了价格的继续上扬,农产品继续提价的支撑因素变了,提价的空间已经很小。而且,受国际市场影响,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作为国内市场价格变动的参照系,对其将会起“封顶”作用,更难对提价表示乐观。
2.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的差距再度拉大。城乡居民收入比(以农村为1,下同)1995年为2.71∶1.00,到2000年扩大为 2.79∶1.00,差距之大,已超过改革之初的1978年,并由此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拉大。5年间,农村居民全年生活消费支出净增360元,比同期城镇居民全年生活消费支出净增额1460元低3/4,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比由1995年的2.70∶1.00扩大到2000年的2.99∶1.00。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1%,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由1997年的39.0%下降为1999年的38.7%。
3.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滞后于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近年来,受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影响,人们的食品消费结构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1)人们对粮食的直接消费需求在逐步减少。 据统计,从1990年到1999年,中国城乡居民每人每年对粮食的直接消费量分别减少了45.8千克和14.6千克。(2 )城乡居民对动物类食品消费需求在明显增加。城市居民肉禽蛋水产品的消费量由40.1千克增加到46.2千克,增长了15.2%;农村居民肉禽蛋水产品的消费量由17.1千克增加到24.5千克,增长了42.7%。(3 )对营养类和方便类食品的需求也在迅速增长。面对这种消费结构变化,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相对落后,种植业比重仍明显偏高,而种植业中又以粮棉油占主导地位。
在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面临明显的需求约束的情况下,盲目增加粮棉油等生产,自然将导致增产不增收。但是,多年来,中国粮油等农产品的生产在宏观政策诱导下,一味追求产出量的增长,难以适应消费需求变化,农民家庭由于市场信息、种植品种和管理技术的制约,种植业结构调整缓慢。一些劣质农产品因无市场需求而实现不了价值,农民收益也因此得不到提高。而如果农业的增长不能给农民带来实惠,来之不易的农产品供求局面就可能逆转,近几年农民对农业的投入下降、耕地撂荒现象抬头,即是不良征兆。
4.家庭经营规模不断缩小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当农业领域中的劳动力拥有足以提高生产率、增加商品产出的土地等自然资源时,农民才有机会提高收入水平。只有农民通过土地经营增加了收入,他们也才会对农业产生兴趣。然而,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农业中滞留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土地经营规模愈来愈小。1990年以来,全国乡村劳动力平均每年以543万人的速度在增长,到1999年底, 乡村净增加劳动力4887万人,使劳动力总数达到46896.5万人。与此相对应, 农户家庭拥有的耕地面积一再减少,由1990年的0.53公顷减少到2000年的0.49公顷。2000 年,平均每户拥有的耕地块数仍多达5.86 块,其中耕地面积不足0.07公顷的有4.16块,占总耕地块数的71%。
十多年来,在劳动力供给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由于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业生产中却出现了一种不断减少劳动用工量的现象。根据固定观察点农户家庭调查资料,在1990年农户家庭粮食作物生产每公顷平均用工量为297.6个工日,2000年减少到246.5个,实际用工量平均每公顷减少了51.1个标准劳动日,这与劳动力供给量的迅速增长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很显然,要想消除对这对矛盾,尤其是减轻劳动力资源对土地资源产生的持续压力,农村劳动力需要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进入到其他增长的经济部门中,即将农业中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5.乡镇企业和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近年来,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适应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乡镇企业面临着从粗放经营型向集约经营型的调整、收缩、改制、淘汰,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吸纳,无论从质上还是量上,都有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乡镇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采取了用资本替代劳动的方式,使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明显变弱。对于企业本身,这是好事,但是对于急需谋求就业机会而又素质不高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却意味着离土不离乡挣钱不大容易了。与乡镇企业近年来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吸收增长成为负数相同,城市吸收农民工的大门也开始逐年变窄,针对下岗职工增多的现实,为了减轻就业压力,很多城市或明或暗地出台了一些对农民工使用的限制措施,为此,仅仅靠出卖力气外出务工挣钱的想法已经不再轻易就能实现。尤其是1998年以来,自1992年开始的第一产业劳动力数量绝对下降的势头逆转,两年又新增农业劳动力500多万人。1999年,第一产业的GDP份额下降到17.7%,而第一产业就业份额仍高居51.0%,农业与非农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自90年代以来明显扩大,已达4.7倍。
6.资金短缺严重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出于化解和防范农村金融风险的需要,国家从1998年开始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同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收缩了在农村的信贷业务,有的只清收陈贷不发放新贷,有的将审贷权上收到地区中心支行,加之信用社改革不到位,农村流动资金投入大幅度减少。由于农行、信用社贷款条件硬化,农户和乡镇企业资信度低和缺乏必要的抵押、担保条件的问题尚未解决,以致农户结构调整贷款难,民间信贷又有抬头。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农村信贷仍以私人借贷为主,占信贷总额的68.3%。乡镇企业的GDP 占全国GDP的30%,而其贷款余额占全国贷款余额的比重不足5%。1999年全国金融机构新增贷款比上年增加18%,但乡镇企业贷款余额却比上年下降了12%。
7.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未能拉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在大量增加投资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较少使用农民工;另一方面,1999年国家财政支出540亿元,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水平、 失业保险金水平、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提高30%,增加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提高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一次性补发拖欠的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提高部分优抚对象发放标准等,使8400多万人受益。但由于城镇居民生活已越过温饱阶段,增加的收入基本没有转化为农产品消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继续在低价位徘徊,农民并未因此而增收。
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善农民增收环境
农民增收困难,农民负担过重,是新世纪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事关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全局。千方百计扭转农民收入增速连续下降的趋势,是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应对国际竞争和挑战、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必须采取综合性措施,坚持不懈地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坚持不懈地积极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坚持不懈地努力减轻农民负担,坚持不懈地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政策和体制环境。
(一)转变增长方式,拓展增收途径 加快由数量型向效益型增长方式的转变,适应市场消费变化调整产业、产品、质量结构,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农业生产布局,以“专用、优质”为核心稳定粮油等主要农产品面积和产量,因地制宜、各有侧重地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增值,积极稳妥地推进名优品牌战略,重点发展无公害和无污染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生产,注重节本增效、截流增收、科学管理,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更新观念,大胆创新,把发展生态农业、旅游农业、观光农业、教育农业,与保护生态环境、陶冶生活情操、提高学生素质、增加农民收入,有机结合起来,确立新型的“农业概念”,开拓新颖的“增收工程”,造就新式的“农业财神”。
(二)培育龙头企业,创新经营体制 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运作的关键是大力培育新型的法人主体——龙头企业,核心内容是资产整合、产业重组、建立新型的利益机制。国家从财政、信贷、税收、进出口等方面支持龙头企业的发展,逐步在全国范围内的相关产业领域,营造一批能够保障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的新型法人主体,形成在政府调控下,以大型企业为龙头,连接科研教育单位,辐射或联合社区(专业)经济组织、市场中介组织、中小型企业,带动基地建设和农户经营,以农业产业化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格局。
针对中国人口众多、耕地等资源较少、以小规模农户经营为主体的经营方式将长期存在的基本现实,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在农户自愿和保持土地等自然资源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依法促进使用权的流转和集中,或者推进产前、产中、产后的联合和有效服务,实现新的规模经营。严格防止以推进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为名,采取行政手段强行将土地等资源“归大堆”,侵害农民的承包经营权。
(三)放开粮棉市场,理顺流通渠道 现行粮棉购销政策和管理体制,无论是国家、地方,还是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都不满意,必须进行彻底改革。抓住粮棉已是买方市场的有利时机,全面放开粮食市场和价格,随行就市,实行市场调节;各类按国家有关规定经工商部门资质认定的企业,允许从事粮棉经营;粮储和棉花经营部门根据国家储粮、需棉数量,与农民签订产销合同,以预付定金等产业化运作方式指导粮棉生产;农发行按照资金封闭运行的原则,对承担国家储存粮棉任务的收购、储藏企业提供足额贷款,对以粮棉加工转化为主营业务、并与农民建立新型利益机制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给与贷款支持;加大对农业基础性和科技性投入的力度,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减免种粮农民税收,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从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有利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稳步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理顺粮棉购销体制出发,借鉴国际有益经验,组建产供销一体化管理的行政运行机构。
(四)拓宽就业门路,促进非农转移 以确定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为标志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实现农村居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最大体制障碍。应当逐步在全国实行统一居民身份的一元户籍制度,在政策上对城市和农村居民一视同仁,使其具有同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力。近期,这种改革可先在小城镇试行。考虑到现行城乡隔离政策形成的长期性和原有利益格局的顽固性,对进入城镇的农民,可以暂时实行蓝卡户籍登记制度,除了不享受原有城市居民的诸多福利补贴外,在就业、子女上学、社会保险、购买商品住房等方面应有同等的权力。待条件成熟后,再取消蓝卡制度,实行统一身份的城镇一元户籍制度。在政策上鼓励和支持农民自己建设“农民城”,以此吸引农民到城里发展乡镇企业。深入改革大中城市企业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逐步放开大中城市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用工市场,允许农民依据市场供求规律进入轻纺、服装、建筑、建材、环保和一些服务行业,进行自由择业。
(五)推进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 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是加快农村税费改革,依法从分配上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利益关系,杜绝一切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开展专项治理,加强对行政事业型收费和经营性收费的监管,严肃查处加重农民负担的违纪违法案件;尽快改变义务教育城乡区别对待的不公平现状,将每年递增的国家预算内财政教育拨款主要用于农村义务教育,减免贫困学生学杂费,冲抵农村集资办学确实无力偿还的债务;加大乡镇机构改革,精简机关工作人员。
(六)创新金融服务,改善农村信贷 配合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需求,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增加农村资金供给。放宽乡镇企业和开发性产业的融资限制,集纳社会闲散资金,采取多种方式解决投入不足的矛盾。抓紧研究和建立农业投资保障体系和农民收入保险体系。
(七)实施分类指导,坚持扶贫济困 引导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农民面向国内外市场调整结构,带动中西部发展并为之腾出市场空间;帮助中部地区立足本地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扶持西部欠发达地区有效利用本地资源,努力拓展特色经济,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强化东西互助,坚持开发式扶贫,培育新的增长点。
(八)构建直通网络,完善信息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