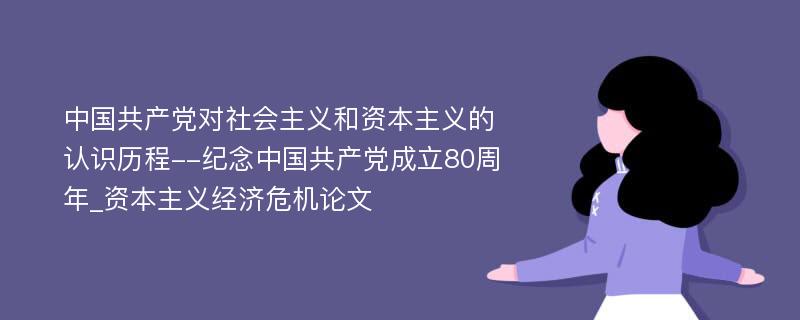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认识历程——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而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资本主义论文,而作论文,历程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1)03-0001-06
中国共产党在走过了80年历程的今天,正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但现实生活告诉我们,当前对我们奋斗目标和理想信念的最大困扰因素是在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正确认知上。因此,江泽民在2000年提出了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研究课题,学术界就此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不过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仍存在着需要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一是在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分别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应将它们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因为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困惑往往来源于对资本主义认识的误解。二是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同时,还应检讨一下我们以往认识存在的误区,这也是造成我们思想困惑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就是试图将二者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对既往的认识进行梳理,反思历程,以达到总结经验教训,获得全面认识的目的。
一
如果我们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么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认识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
历史从19世纪向20世纪跨越的时刻,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时刻。满清政府在全副武装的西方列强面前变成了一条顺从的走狗,中华民族在西方富豪面前成为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奴隶。面对欺压和凌辱,不甘沉沦的中华男儿们痛心疾首,信誓旦旦,发誓要“除弊兴利”,“振兴中华”。而振兴中华的出路何在呢?那时先进的中国人有如漫漫长夜里身陷泥沼的斗士,他们以渴求的目光憧憬着卢梭、孟德斯鸠们所勾画出来的光芒四射的“理性王国”,在他们看来,只有资本主义才是普降甘霖的人间天堂。
然而,事实却与人们的愿望相去甚远。在国际上,此时的西方列强已先后转入帝国主义阶段,人们见到的并不是甘霖普降,而是列强们在瓜分世界餐桌上的争吵与殴斗,结果引发了一场灭绝人性的世界大战。开初,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还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的窃窃私喜之中;很快,巴黎和会上对山东问题的处理就把欣喜变成了愤怒:“难道公理战胜强权,就是按强弱分配权利吗?”在国内,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成功地发动了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的建立似乎给人们带来了一线希望,然而随着袁世凯的篡权,资产阶级共和国很快就化为泡影。而后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继续努力,但仍招不来理想中的“理性王国”。在严峻的事实面前,人们不得不进行反思,资本主义到底是甘霖还是罪恶?它难道还是一个值得奋力追求的目标吗?于是,怀疑产生了,信心丧失了。“资本主义支配下的社会,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他的黑暗,他的势力和消费量的不均,他的残酷,‘以人类为牺牲’以及其他种种,已经使生活在它底下的大多的人类,感到极端的痛苦,而想用各种的方法,做各种的运动群起而推翻之了!”[1]
正是在失落后的迷惘之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中国人的眼前才豁然开朗,科学社会主义成为观察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工具。李大钊在洞察了十月革命是“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之后,坚信“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2](P5)。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标志着先进的中国人最终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
总之,20世纪20年代,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它既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其划时代的意义是勿庸置疑的。支持这一历史性选择的价值取向是:资本主义已变成了历史的罪恶,社会主义则是完美的象征。但是严格地说,这种选择是发展道路的选择,而不是生产方式的选择。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复杂的国情要求价值观要进一步深化,即抛弃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不等于应当抛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并不意味着立即就可以搞社会主义。这一点对于刚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中国人来说是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的。
第二阶段: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在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诞生的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大体上没有超出马克思的分析和列宁对世界历史时代的估计。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劫难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1923年至1929年的短暂“繁荣景象”,饱经大战之苦的西方人以为,和平、安宁、繁荣的局面会从此降临人间。孰曾料到,一场更大规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于1929年始发于美国,很快就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德国和日本在其西方伙伴别有用心的“辅导”之下,为摆脱经济危机而骑上了“军工生产的野马”,走上了军事法西斯的道路。法西斯势力的泛起,最终把整个人类又卷入了更大规模的世界大战的灾难之中。可以说资本主义是用自己的充分表演一再强化着人们的“资本主义就是罪恶”的价值取向,毛泽东在1940年对这种价值取向作了明确的表述,他说:“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1](第2卷,P686)
在这30年里,社会主义对于中国来说还不是现实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是要探索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东方之路。而在探索过程中,困扰我们的核心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
1921年中共“一大”党纲确定的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有着功垂千秋的历史意义。然而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着一种把奋斗目标等同于现行政策的认识。如陈独秀在《社会主义批评》一文中认为:“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这样的认识显然与中国的国情不符。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对这种幼稚的认识进行了匡正。但是此后党内出现的多次“左”右倾错误,仍然还是在怎样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搁浅。陈独秀的右倾似乎是对资本主义表现出了一种无奈的热衷;三次“左”倾则好像是唯我才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其结果都是金石未开,却撞得头破血流。只有毛泽东成功地拓开了新民主主义这一通向社会主义的东方之路。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固然是美好的前景,但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眼下的目标是要先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因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地经义”。在中国,“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同时,毛泽东还认为,由于世界历史时代的变化,中国已经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不能发展资本主义。他认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3](第3卷,P1060)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反对那种“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的民粹主义思想。[4](第3卷,P323)因为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是工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如果不利用资本主义的发展去具备工业基础,完成由农业基础向工业基础的转变,那么社会主义永远也不会到来。[5](P238~239)
总之,在这个阶段里,截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基本上没有超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估计,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特征也被二战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事实所证明。因此坚持上述的认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阶段里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同时,在国内问题上,毛泽东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把发展资本主义同走资本主义道路严格区分开来,从而能够把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气息奄奄的估计同在中国资本主义尚需存在和发展的认识辩证地统一起来,由此成功地探索出了通向社会主义的东方之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沿着这条道路才取得胜利的。
第三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重大转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旧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为战后西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同时,西方国家依据凯恩斯主义采用政府干预的手段使资本主义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也得以缓解;加之以原子能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又使西方国家如虎添翼。于是西方国家在度过了短暂的战后恢复期之后,很快就进入了长达20多年之久的快速增长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大体上从1950年到1973年)增长率高达5.5%,出现了所谓帝国主义僵而不死的现象。
这种现象本来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但是,由于二战后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冷战对抗的政治局面;也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长期实行孤立封锁,我们不得不在政治上采取“一边倒”政策和封闭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政治上的对抗影响了我们观察资本主义的视角,即越来越多地从政治关系上,而不是从经济发展上去观察和认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致使西方经济发展中的这些重大变化长期未能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相反,在冷战对抗的环境中,舆论引导只是片面宣传和渲染资本主义的阴暗面,这就更加大了主观认识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人为地强化了“资本主义就是罪恶”的价值取向。
在国内,50年代初我们正处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前述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物质条件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思想,理应成为过渡时期的指导思想。但是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毛泽东却改变了初衷,把“利用、限制”的政策改变为用改造的方法消灭资本主义的政策,并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的目标。尽管过渡时期总路线中也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但计划中15年的任务仅用了4年就宣告完成。当1957年我国跨入社会主义社会时连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我们并没有牢固的工业化基础。此后,他虽然也试图用“大跃进”的方法发展生产力,但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他基本上是以马克思阐述的社会主义原则和苏联模式为依据,建立纯净无瑕的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断追求生产关系的升级净化,“一大二公”,并坚信自己坚持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视其他不同意见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使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无论是其思想内涵,还是其评价标准都越来越趋于政治化。当他以惊人的气魄,不惜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代价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捍卫其“纯净的社会主义”的时候,孰不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借助科技革命的翅膀飞快地发展着生产力。事实无情地说明:认识上的误区会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损失!会使我们同西方国家拉开多么难以缩短的差距!
总之,冷战时代的国际背景和西方封锁的客观现实,加深了这一阶段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敌对情绪,强化了对两种社会制度对抗性的理解,从而使我们难以客观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变化。同时,毛泽东在这一阶段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又不自觉地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显现出政治化、教条化的特点,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挫折。这就使得我们无论对社会主义还是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都离开现实越来越远,带有越来越严重的片面性。正是由于这种片面性的认识,才导致了1957年以后的10年曲折和1966年以后的10年动乱。
第四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
进入80年代以后,世界和中国都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在世界范围内,随着冷战对抗局面的结束,和平与发展越来越成为时代的主题。虽然世界仍不安宁,但爆发大规模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减小,因而两种社会制度的激烈对抗也被相持共处的格局所取代。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经过20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在70年代中期出现了滞涨病症,西方国家为“黄金时代”的无情离去扼腕痛惜,一筹莫展。无奈之中,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开出了“货币主义”和“供给经济学”的处方,对西方经济的病躯进行了将近10年的将养调理。9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进入了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加速转变的新时期。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东欧各国在通过改革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时却出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惨痛局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这些沉重的课题都不能不引发我们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问题的重新思考。恰逢此时,在国内也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为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阔视野,消除偏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思想和政治前提。
面对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和变化了的时代特征,邓小平首先思考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大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第3卷,P373)从已经变化了的时代特征出发,邓小平认为,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改革开放,而要改革开放就有一个怎样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他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6]第2卷,(P167~168)“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6](第2卷,P351)进而,他又从发展阶段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6](第3卷,P252)中国共产党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策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总之,邓小平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中国和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进行了深入分析,抓住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科学地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定位问题,抛弃了过去对社会主义政治化、教条化的理解,从而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同时,他还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态势和矛盾作了正确分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和发展局限性,指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既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继承性的一面,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只用政治标准看待资本主义的片面观点,形成了完整的资本主义观,为改革开放,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
回顾近百年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认识历程,我们可以从中引出以下有益的历史启示。
首先,必须正确处理拒绝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与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从上述历史进程中我们不难看出,资本主义一直是缠绕在我们身边的一个久驱不散的幽灵。当我们正确地处理了同它的关系时,我们的事业就前进;反之,我们的事业就受挫折,足见正确认识资本主义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而获得正确认识的关键是要正确处理拒绝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在发展方向上,中国不能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了捷足先登者是从不给落伍者以均等的发展机会的,发达国家绝不允许中国循着它们的老路发展而与它们并驾齐驱,我们只有另辟社会主义的新径才能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也要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同抛弃。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过去是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优势而市场经济未能得到充分发展,今天也远没有实现生产的市场化、社会化和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就不会有真正“够格”的社会主义。而从西方经济发展的历史上看,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或称市场经济)的转化是借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完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而不是发展道路)当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之前是不会灭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资本主义还有其用武之地,毛泽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慨叹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因此,我们不能只看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对立的一面,还要看到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和前后承继的关系,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其次,必须正确处理经典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关系。如上所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但选择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并不等于解决了所有的认识问题。回首我们走过的历程就会发现,我们经常是与超越阶段的“左”倾错误相伴而行,其根源就是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经典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即不够经典社会主义的格),它与经典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它不具备在经典社会主义那里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所准备好了的物质经济基础。因此,要弥平现实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之间的沟壑,就必须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生产的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以具备转向“够格”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实社会主义(或称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同西方资本主义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是相对应的(即都是要完成由自然经济向商品市场经济的转化,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由于历史使命的相似,二者在运行机制上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通之处(我们当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运用市场经济的原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什么要学习、借鉴、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理论依据。一句话,这一切都是由中国现实的国情决定的。如果离开了现实的国情,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的定位问题,用经典社会主义的原则(如单一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等)当作衡量现实社会主义的标准,就必然会犯超越阶段的“左”倾错误,造成思想认识上的困惑。
最后,必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不断校正既往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认识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自觉守望世界风云变幻,跟踪时代发展大势,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我们的认识跟上时代的发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是要注意立足高远,放眼全程,不要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古语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立足高远就难以看清历史发展的方向。事实上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凡是大的社会变革都是以百年乃至千年作为计算单位的。例如在中国,奴隶制取代原始公社制用了1900年;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用了500年,就是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在英国、法国也都用了200多年的时间,且曲折、反复充斥其间。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才仅有80多年的历史,出现当前的低潮形势,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片断,不足以证明社会主义已彻底败北,资本主义将永远不替。二是在解决理想和信念的问题时,不是也不应当是从既有的结论出发,根据主观需要选择“有用”的事实去印证原有的结论,这种唯心主义的作法是与事无补的。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今天的发展都遇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未曾遇到过的问题,既有的结论有些已经不能说明现实问题而需要进一步发展了。因此,我们必须从现实出发,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审慎、严谨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发现新规律,引出新结论,然后在这个新的基础上再去建立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我们坚信,这样树立起来的理想信念才是坚不可摧的。
收稿日期:2001-03-27
标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道路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