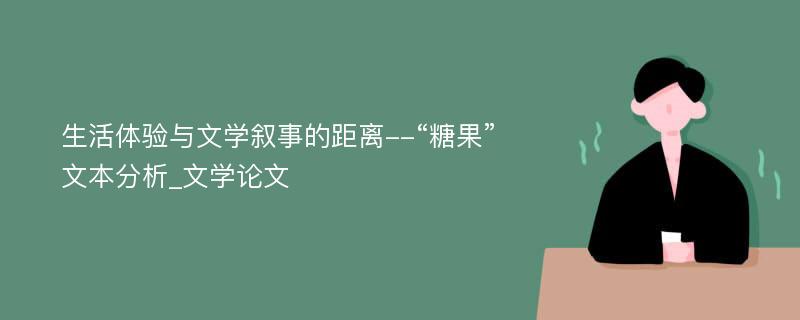
生活体验与文学叙事的距离——关于《糖果儿》文本的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糖果论文,文本论文,距离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4)02-0114-05 河南作家邵丽的中篇小说《糖果儿》[1],无疑是作家投入情感最集中的一部作品。这部被论者称作“自传体”的作品之所以汇集了作者全部的情感,是因为作品所述可能来源于作者的亲历实感。但是,这种亲历实感在进入作品或者说转化为作品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叙事方式,会成为作品什么样的血肉,甚至对文本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都是值得研究的。《糖果儿》恰恰成了阐释这些问题的典型文本。 一、在场体验与文学叙事 小说叙事完全是以一种“在场”的“我”的身份,大致讲述了“我”的家庭或家族的故事。作品一开始就体现出了“自述”性的特点:“我喜欢五月……最重要的是我在五月,满地黄花的季节生出了一个女孩儿。……女儿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奖项,我平生最好的作品。”“我”从给我带来最多喜悦、最大骄傲的女儿开始叙事,虽然作者接着就设置了一段苏天明和金地的故事,横亘在作品叙事的路径之前,似乎在提醒读者故事的虚构性之存在,但真正的故事仍然是“我”及其家庭生活、经历、情感、牵挂等等。作品的基本构成表明,这是一个在场经历者的述说,“我”既是作者、叙述者,又地是作品中的一个主人公,因为作品中既有关于“我”的描述,也有“我”活动的清晰明确的线索,更重要的是,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我”的关系人,作品中的故事都是“我”经历的事件。在作者叙事和情感自白中,幺幺、敬川、父亲、母亲、公公、婆婆等是故事构筑的链条,叙事的基本要素。无论是幺幺、敬川,还是父母、公婆的故事,都是“我”的故事,因为他们是“我”的关系人,表现出在场的无距离叙事的特征。 诚然,文学作品存在着虚和实的构成,即使是实的构成也存在着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考察文学作品中的虚与实,当然不能仅看作品中设置了什么人物、要素、符号,还要综合考察作者的叙事和表达的口吻,情感流动的轨迹,人物活动的情理可能以及作品传达出的其他信息。《糖果儿》以第一人称叙事。通常而言,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身份叙事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确立一个观察和表达的视角,我是虚拟的;二是我就是作品中实有的人物,是故事的经历者和参与者。《糖果儿》无疑属于第二种情况。这从作者的情感投入,作品叙事表现的症候和信息可以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得到。毋庸置疑,邵丽是一位情感丰富,甚至情感依赖的作家,这当然也是女作家独具的优势。在现实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真实的生活内容,这些生活经历和内容都可能成为作家创作的参照和素材;每个作家也有自己的生活阅历和感受,这毫无疑问是作家创作最直接的动力源。《糖果儿》的作者生活中经历了一些变故,或者说产生了某种故事性的生活真实,这些变故冲撞着作家的生活,促动着作家对世界、生活的感受,当然也荡涤着作家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对于作家而言,这种在场体验和真情实感常常成为创作的爆发点。但是,文学创作不是简单的生活记录,特别是叙事性的小说,其核心要素是人物、故事和情节的完整性和丰富性。这就需要让经历、故事、生活真实经过必要的发酵,再由作家提炼、创造进而转化为文学叙事。 “好作品都是由作家的血肉写成的。人物的精神身躯中一定有作家的血液奔流,人物的命运跌宕中,一定有作家的泪水飞溅”[2]。作家对自己的家庭和亲人充满着真情、真爱,正因为如此,当家庭出现了未曾预料的变故,这一未曾真正纳入作家文学关注的领域成为她眼前的困惑,成为生活旅途的阻碍,甚至成为需要文学解说的问题。作为官场中人,作者的丈夫未出事之前,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情感是完整的,是一种正常状态,不需要为之纠结。但现在,家庭的完整、稳定出现问题,“我”及其家庭的生活状态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就需要对生活进行新的认识和体验。关键是,这种亲身经历和体验如何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糖果儿》的故事比较简单。概括起来就是:“我”的丈夫在官场突然出事,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我”错愕、手足无措。朋友、亲人的关注、安慰都不能让“我”静下来。女儿在外地上学,在一个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夜晚,“我”不顾一切地出门,挤上出租车和火车,“我那时只有一个信念,找到我的女儿,我唯一能见到的亲人,我要和她待在一起”。但这不是小说故事的全部,充其量是小说故事或叙事的线索。其实,作为文学叙事,人们(读者)对“官员出事”这样的文学冲突有更多的期待,读者期待着作者沿着这一线索演绎出更多的故事。但是,作者恰恰在这里把线索储存起来,把紧张的气氛转移出去,然后真正静下心来,开始另一番别样的叙事。 《糖果儿》的故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当下性的故事,包括敬川出事,“我”的文学活动,幺幺的活动以及三者之间的互动。二是过去时的故事,包括“我”的经历,爸爸、妈妈、公公、婆婆等经历的故事。这些都是具有真实性质的故事。三是虚构故事,即作品中穿插在作者叙事中的苏天明和金地的故事。当下性故事是与作品原发线索联系最紧密的故事,也是最有故事性的生活情节和矛盾冲突。这里,作者完全可以撷取以“我”,特别是以敬川出事为关键点的生活情节和矛盾冲突,展开更开阔、更丰富的叙事,让作品产生更多的跌宕和起伏。作者此时转移了线索,对叙事简化处理,体现着作者的用意和策略。我们知道,“官员出事”是非常具有轰动性、故事性的社会事件,它的连续发酵,直到尘埃落定,得出最终的社会结果,形成的冲击波在社会层面具有强烈的穿透性,而对一个家庭的打击具有毁灭性。且不说作者能否驾驭这种复杂事件,也不论对这种事件在作品中如何评价,单就事件对家庭和情感的摧残,考验着人的承受底线。作者堵住了线索的蔓延,使敬川出事不再蔓延故事,个中缘由读者应该能够明白三分:作者(即“我”)作为故事的当事人,与事件及其核心人物敬川直接关联,“我”既难以把握事件的发展,更难以对事件的是非曲直做出泾渭分明的评判,倘若直面事件,这种无距离叙事对作者无疑是一个有难度的问题。作者这种处理办法,避免了故事的复杂化,增强了叙事的易控性。 过去时的故事是作者转移线索的结果,也是故事背后的故事。《糖果儿》是一篇叙事作品,它需要构筑故事,需要用故事体现文本的特性。作者选择了讲述故事背后的故事。作品写了“我”的一个职业革命者、“地方主官”的爸爸,和一位“职业妇女”的妈妈,以及他们之间的故事;写了“我”的公公、敬川的父亲——一个旧知识分子文臣,以及文臣女人的故事;还写了“我”的祖母裳的一生;等等。作者仅仅是在简略地讲述这些人物和故事,说不上是描写人物,更称不上完整地塑造人物形象。我们通过作者的讲述仅仅了解这些人物的大致情况,人物的丰富性并不能从作品中得到。严格地讲,《糖果儿》中过去时的故事,与作品开始引入的故事线索没有太大的关联,或者说,这并不是必需的故事。作者终止原有的可能掀起“高潮”故事线索转到这种平淡无彩的叙述,是作品浮现的另一个线索。平心而论,敬川事件在作品中提出作为引子之后,的确已经无法展开。作为作者的“我”无法平息事件,也不知道事件向何处发展,更不愿预测事件的结果,至少对于当前的“我”是一个无解的事件。这样一个人生劫难,给“我”提出一个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生命,生活意味着什么?劫难意味着什么?于是,作者便撇开敬川事件,进入到与这一命题相关的故事中来。人生是一段历史,思考人生必须进入到历史中去。爸爸、妈妈、公公、婆婆、爷爷、奶奶等都是历史,而且,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历史。作者回归到父辈的历史、家族的历史并非在于讲述故事,其实质是为了把劫难置入历史的长河,以历史的视野和心胸看待劫难,淡化劫难对人的困扰,当然也是为了从精神和心理上消解劫难。历史是一个参照,爸爸、妈妈、公公、婆婆、爷爷、奶奶生命的经历是一个真切的参照,劫难不是不可逾越的,生命中充满温情、温馨和余味,它足以化解人生中所有的困扰,让生活滋生蜜意和温暖。 虚构的故事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最多与作者的叙事形成一种映衬或对照,用以提示敬川的出事是否存在着另外的可能。由于《糖果儿》内容的特殊性,作者在叙事中可能一直存在着一个困难,那就是如何把生活内容、生活体验转化为文学叙事,换言之,怎样把“我”的亲身经历以合适的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其中“我”的亲身经历本身不乏矛盾性,甚或有“难言之隐”。但是,这一亲身经历的事件又是触发作者创作的巨大动力,不吐不为快,难以阻遏。所以,作品中尽管以大量的篇幅进行叙述,但仍然让人似乎觉察到存在着欲言又止的羁绊。毕竟这种无距离感的经历需要必要的空间审视和过滤,原生的生活内容不可能直接涌入作品。应该说,作家在叙事方式的处理上已经表现出较高的水平。敬川事件虽然也可算作家庭变故,但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事件和社会事件。这样一个事件存在着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伦理的等多重评判维度和标准,作为局外人当然完全可以任意评说,而作为直接关联人“我”即使是以文学的方式,也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等双重的局限。所以,敬川出事到底事出何因?作者没有直接进入叙事,而是煞费苦心地设计了苏天明和金地的故事。在苏天明和金地的故事中,作者也没有进行酣畅的叙事,也仅仅片段性讲了一些与作品其他内容对应的故事,有一种欲言又止的意味,反映了作者对虚和实把握、拿捏过程中的心迹,但尽管很隐约,我们仍然能够自然地与敬川和“我”联系起来,成为进入敬川事件的一个难得的路径。在这个意义上,虚构的苏天明和金地的故事有了存在的价值。 我们看到的三类故事,仅仅是作者的简要叙述,并非完整的事件描写和叙事,所以,给人的感受是,有故事而无情节。作者淡淡地叙述的这些经历和故事,目的是为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做铺垫。 二、叙事:主观与客观 《糖果儿》的叙事是一种家庭、家族叙事,而且是“我”的家庭、家族叙事。家庭、家族叙事与叙事者的关联性更强,虽然成熟的作家在处理叙事资源和叙事手法时,都会考虑作者在其中的位置或与事件的距离,但是,利益关联、情感关联、精神关联会影响到人的心理、隐秘、自尊等,他述和“自述”在分寸和限度上还是存在着纠结。这体现着作者的立场和价值判断。“文学无论如何都脱离不了下面三个方面的问题:作家的社会学、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以及文学对社会的影响等。”[3]诚然,家庭、家族生活也是一种社会生活,也可以纳入社会视野做出社会判断。关键是置身其外的社会生活与置身之内的社会生活给人的影响和感受是不一样的,因此做出评判的立场就会存在差异。一般而言,局外人相对客观、理性,当事人相对主观、感性。文学叙事是一种处理社会生活的特殊方式,但与人的一般认识规律仍然有相通之处。作为当事人,作者如何对待“我”的家庭、家族事件,“我”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与事件、与关系人保持什么样的时空、心理、情感距离,所有这一切都直接影响到叙事的状态和面貌。显然,作者在作品中选择了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这是一种能够让“我”理清人物、事件、情感、事理关系的方式。 “我”是作者设定的第一人称叙述身份,但同时也是作品中有实际意义的一个人物存在,而且,“我”在故事、叙事中具有关键的作用。作品叙事的对象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个家庭、家族过去、现在的经历和生活,其中并没有涉及这个家庭、家族以外更多的其他社会生活。作者不是按照这个家庭、家族生活的自然起始的顺序展开的,而是以家庭突然出现的变故——“我”的先生敬川“出事了”为缘起开始的。“我”本来是可以没故事的,退一万步说,即使是作家自己有丰富曲折的经历和故事,但在作品中往往予以嫁接、虚拟和转移。在《糖果儿》中,敬川是“我”的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幸福共同体的关系人,敬川出事直接危及家庭、家族的稳定、幸福,打破了家庭情感状态的平衡,作为敬川最直接关系人的妻子“我”,难以置身事外。在实际生活中,家庭主要成员毫无疑问是家庭故事的主角,在文学中,家庭的故事也不可能由其他人来演绎。“我”是事件的当事人,是在场的亲历者,理所当然地是故事的主角。更重要的是,没有“我”的存在,故事中的人物就可能没有了存在的依据。在作品中,作者没有改变“我”的作家身份,进一步拂去了“我”的虚构色彩,同时也赋予“我”叙事、抒情更大的空间。“我”是作家、妻子、母亲、女儿、媳妇,家庭的失重使“我”别无选择地处在前沿,既要承接原有的故事,又要继续新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抚平家庭的创伤,维系失衡的局面。此时,作家的身份于“我”并无太大的意义,“我”所履行的是一个妻子、母亲、女儿、媳妇的义务和责任,体现的是一个妻子、母亲、女儿、媳妇的形象。作品是通过“我”的活动、追忆、补录把其他人物、活动、细节续接上的,如果说把作品的叙述置换成画面镜头,“我”绝对是重头。所以,作者虽然没有刻意塑造“我”的形象,但由于故事由“我”而来、由“我”承接,“我”的分量就大大加重了。同时,由于故事完全是由“我”道来,叙事的主观性、情感性就显得突出了。 敬川是作品故事的缘由。他是“我”的丈夫,一个官场中人。在作者叙述中,敬川是一位有才气、有个性、想干点事的官员,似乎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在其还在踌躇满志时不幸落马。正是敬川的落马导致了这个家庭一隅的陷落,对“我”的身心形成强烈的震撼和冲击,进而牵动了这家族,引出了关于“我”和敬川以及家族的背景和故事。其实,作品中关于敬川的文字并不是很多。但是,敬川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牵动“我”以及与“我”相关人物情感的关键,也是牵动作品神经的关键。没有敬川,就不可能有作品中的故事,更不可能有“我”如此深情的倾诉和抒写。幺幺是“我”和敬川这个核心家庭的一员,作为父母的孩子,一个学生,阅历有限,她可能是天真的、稚嫩的,甚至是幼稚的。当家庭变故撞击着这个家庭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保护幺幺,避免让孩子受到伤害。然而,在这样的变故中,孩子表现出意外的成熟和坚强,成了即将崩溃的“我”的精神支柱。幺幺为什么能够成为一种依赖,这是一种叙事的需要,是一种精神的支撑。因为幺幺年轻,她没有承载这个家族沉重的历史,也没有形成上一代人的处世思维,她没有负担,能够冲破这场变故所形成的精神和心理困扰,她是“我”的希望,也是这个家庭和未来的希望。 至于相关的父亲、母亲、公公、婆婆,甚至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是故事的要素,是“我”叙事的符号,更是“我”抒情的载体。作者把作品中出现的人物严格限定在自己的家庭、家族范围,从而也就界定了这是一种纯粹的家庭叙事,尽管这个家庭是一个与社会存在着广泛而深刻联系的家庭,尽管敬川是一位“入世”的官场中人,有关他的经历和故事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但是,这些都被作者剪切、过滤掉了,仅仅把“我”的家族中的人物“请”了出来。家族中有多少人物?家庭中有多少故事?我们是能够想象的。作者这样安排,原因在于每个家庭成员都是一个抒情的载体,能够满足作者抒情的需要。 三、作品形态:个人抒情与公共叙事 文学作品作为作家的创造性劳动,是一种个性化表达,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个人叙事。但文学作品表达更多的是一种人类普遍的生活、共有的情感,文学作品最终要提供给社会,供人们阅读和消费,在此意义上,它又是一种公共叙事和公共产品。之所以把《糖果儿》当作个人叙事,是因为作品叙述的内容与作家紧密相连,或者说就是作家自己的生活内容。《糖果儿》虽然没有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但作品蕴含着丰富深厚的思想和情感,甚至思想和情感胜过了故事和情节,这正是它的独特之处。 作品的思想体现在对人生和家庭的思考。作者漫过了开头设置的故事和线索,转入平缓而无节奏的叙述,把“我”爸爸、妈妈、公公、婆婆、爷爷、奶奶的一生一世历数一遍,作者的确切意图不是为了讲故事,而是在于考察他们的人生。譬如,爸爸一生革命,身居地方要职,坚定耿直,率直倔强,晚年孤独,对儿女的顺从妥协;妈妈的勤劳节俭、朴实无华,“她是个完全彻底的革命者,她的精力百分之八十给了工作,百分之十给了我父亲,剩下的百分之十才是孩子们共同拥有的”;公公文臣是锦衣玉食之家的秀才,家道破落走投无路之际投靠其父母定下亲事的人家,生不得志,衣食无忧,无所用心,吃喝为乐;文臣的女人极其要强,一生为丈夫和儿女活着,“丈夫就是天,哪怕他只是一个象征,天塌不下来,她就拥有完整的世界,她是一个妻子和母亲”。祖母裳是大地主家的女儿,“一生吃斋修行”,“目光里有万物生光,却唯独没有人”,“她最喜爱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种树种花,一件事情就是吃斋念佛”,活得清清爽爽、平静从容。虽然都是亲人,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和不同的人生态度,都以自己的方式度过了一生,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活法,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生活的道理。虽然在看似简单的人生中都存在着复杂性,但无论是逆境也好,顺境也好,都坦然面对,顽强走过,让生活酿出了甜蜜和诗意。人生多有挫折,家庭也并非都是阳光,但家庭是人生的基本憩息地,无论是人生的不测还是家庭的厄运,都不是人生之路中断、家庭生活崩溃的唯一理由。譬如对于“我”而言,敬川出事直接影响了家庭的生活秩序和稳定。如何应对这一变故,如何将生活进行下去,如何将家庭维持下去,就需要跳出事件之困,从伤痛中解脱出来,重新认识人生和生活,人生不可能永远沉浸于顺境,生活不可能永远充满阳光,厄运和伤痛只是生活中的一种状况,人生中充满着更多美好的东西值得人们去憧憬、去追寻。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意念,作者转移线索和笔锋,进入对家族、对父辈历史的追寻,“我”的情绪得到沉淀,激动和愤懑逐渐冷却,并从中获得了理性的历史的审视,大而化之,伤痛总是可以抚平,活着并好好活着总是有意义的。 《糖果儿》最大的亮点是充沛和丰富的感情。毋庸置疑,“我”是挚爱着自己的家庭和亲人的,“我”的情感完全寄存在这个社会单元里,这个情感寄存地发生任何问题都会对“我”的心灵和精神形成强烈的震动和冲击,所以,敬川出事直接牵动了“我”感情平衡的砝码,致使我多年积存的情感迸发出来,敬川出事既是“我”情感迸发的契机,也是“我”抒发情感的载体。阅读作品,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与其说作品在叙事,不如说作品在抒情。作品中的“我”在抒亲人之情、家庭之情、伦理之情,“情”这种形态是贯穿作品字里行间始终的线索。“我”充满着对敬川的爱情。“敬川是个少年诗人,当年在大学生诗人里面还有点影响”。“我和敬川十七八岁那年开始恋爱,二十一岁结婚至今,婚姻很美满,没有出现过大的情感故障”。虽然恋爱时两个家庭都反对,虽然“两人长达十几年不在一个城市生活”,但彼此依恋着、喜欢着、欣赏着,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当然女人的一半是男人,彼此不可分离。虽然平淡如水,但敬川出事让“我”与敬川的一幕幕爱情与温存都浮现出来,是那样值得回味和珍视。幺幺是“我”和敬川的杰作,是“我”的宝贝,也是“我”困境中的精神依靠和情感寄托。爱孩子是所有母亲的天性,但“我”对女儿幺幺的喜爱达到了自恋的程度。“我”在“满地黄花的季节生出了一个女孩儿。她一天天长大,我总是带着炫耀的心情召唤我的朋友来看她。我说:看,我的女儿!我不怕他们或者她们骂我自恋狂,我不能吹嘘自己的小说写得好,但我完全有理由炫示我的女儿生得好。我的朋友们看了我的孩子,都由衷地赞叹,这活儿的确干得漂亮。……女儿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奖项,我平生最好的作品”。所以,女儿的健康、女儿的成长、女儿的恋爱、女儿今后的一切都是一种卸不掉的牵挂,而敬川出事后嘱咐“我”的首要任务也是照护好女儿。“我”深爱着父亲,但对父亲也有一种深深的愧疚。“他退休之后就随最小的女儿去深圳了,我们借口那里的气候多么适合老人生活,不让他回老家来。……他最后几年在我们跟前完全软塌下去了,他什么都不要求,看我们的目光像羔羊一样。我明白他想干什么,可我根本不给他说的机会,武断地阻止他的表达”。“爸喝了一辈子酒,一天抽三包烟。我总是吓唬他,不让他抽。我说抽烟喝酒会要了他的命。管了他一辈子的妈妈恳求我,让他少抽一点可以吗?我不答应。他怕我生气,真的就戒掉了”。经历了家庭的变故和伤痛,倍感亲情的重要和珍贵,但对于父亲,“我”施与的亲情是如此的稀少和欠缺,和“从我有记忆起,他就供着我零花钱”的父亲给予“我”的爱相比,相形见绌,让“我”深深地忏悔,这是终生的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作者正是沉入亲情的激流,让灵魂接受了一次透彻的洗礼。 作为女性作家,邵丽更擅长情感的描摹和抒发。所以,《糖果儿》与其说是一篇中篇小说,不如说是一部长篇叙事抒情散文。尽管我们说情感是文学的核心要素,但《糖果儿》中的情感因素超乎寻常的丰沛,字里行间都浸透着作者的情感、情绪,甚至我们从作品的结构中也能够看出端倪,作者根本没有按照时间、空间顺序和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叙事,而是基本按照情感流动的态势进行写作和表达,情感是基本线索,因此,作品的结构就显得平缓、疏散,没有叙事作品中那种故事情节的环环紧扣。作者“在现实和虚构之间自由往返,通过文字,把现实生活中的缺憾加以艺术化修复,把人生中的伤痛给予想象性抚慰”[2]。完全可以理解为,《糖果儿》是通过家庭、家族的经历对“我”的人生感悟的抒写,当然,这种人生感悟和个人抒情是可以与读者分享的。